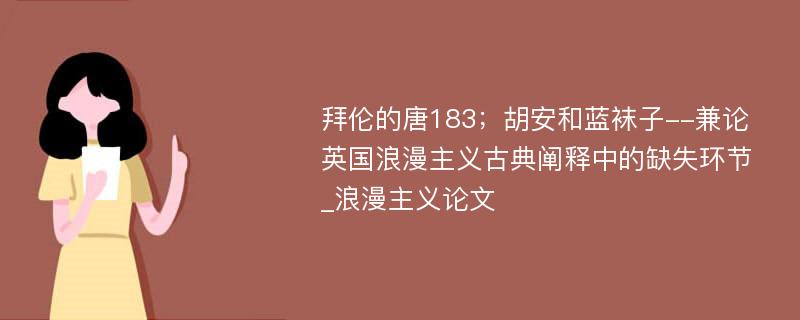
拜伦之《唐#183;璜》和“蓝袜子女士”——兼论英国“浪漫主义”经典解读中缺失的一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拜伦论文,英国论文,浪漫主义论文,缺失论文,袜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4-127-07
“夹叙夹议”是拜伦《唐·璜》行文的特点。在这部包含十六支歌的长篇叙事诗中,“叙事”(narrative)和“杂议”或曰“旁白”(digression)基本上互为交织,交替并进。“叙事”部分主要围绕主人公唐·璜的洲际旅行展开,包含他在“东方”的爱情艳遇,军事冒险,同各色当权者的周旋;而“杂议”则从讥讽朝政,调侃民俗到对故土的回忆,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叙事”和“杂议”并列存在,引发了丰富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方面使《唐·璜》成为互文性研究丰富的材料库,另一方面诗人自身的创作意图越发扑朔迷离,让人莫衷一是。不过,当下关于《唐·璜》的评论日益突出“杂议”的作用,例如杰罗米·麦甘(Jerome McGann)和简·司泰勒(Jane Stabler)均肯定杂议是《唐·璜》创作手法和理解作者意图的关键,并认为这些看似偏离情节的自说自话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1](P3)。史蒂芬·白格芮(Stephen Bygrave)则借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在其《项迪传》(Tristram Shandy)中的话说:“毋庸争辩,杂议是阳光,是生命,是阅读的精魂,假如将它们从书中抽出,那么你就不用携带此书了。”[2](P172)可见,“杂议说”是目前的学术主导。于是“叙事”在《唐·璜》结构中的作用便被贬低,主人公唐·璜被动地成为“纯粹的过渡性角色”,“叙述者借助他得以再现18世纪末地中海区域真实的历史图景”;他不过是作者意图的木偶,一个毫无个性可言的扁平角色,正如窦蓝(Donelan)所指:“唐·璜的传说赋予拜伦的是一个形式,借以言说他个人经历。”[3](P176)这样,叙事和杂议便对立起来,其中的一方可有可无。可是,一旦破坏叙事和杂议的平衡,《唐·璜》的阅读和理解也就破碎了。显然,不论重视“杂议”还是“叙事”,都失之片面。那么,真如以上论者所说,“叙事”只是一个形式的空壳吗?如果不是,哪儿才是理解作者意图的突破口呢?我以为,在叙事和杂议之间频繁出现的“蓝袜子女士”,或许能让读者开掘出另一条联系两者而达于新途的路。
一.“蓝袜子女士”的身份
拜伦在《唐·璜》中一直对蓝色耿耿于怀。他对“蓝色”接二连三的揶揄、嘲讽、挖苦甚至取笑,不禁引发细心读者的好奇与思考。例如在第一歌篇的第二零六节的杂议部分他奉劝读者:“你等不应像‘蓝袜子’那样作伪证”。再如当唐·璜来到英国,他必须学会同一群“blues”(蓝色的)女士周旋,只见“娇弱的蓝女士部落,习惯对十四行诗长吁短叹,/用上一期《评论》的纸页/塞满头脑或风帽,/此时却披戴着眩目的亮蓝款款而来”(第十一歌,第五十节)。又如,就在主人公被押上贩奴船的空隙,叙述者对“蓝”女士突然大发议论,“噢,‘暗暗的,深深的,美丽的蓝’/恰如某人于某地这样赞叹天空,/而我则用在你们这些饱读女士的身上;/有人说你们的袜子是这个颜色(天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袜子可不多见)”。(第四歌,第一百一十节)其实有关“蓝袜子女士”的描述和评论在《唐·璜》中还可以举出不少。虽然比较零散,但是熟悉《唐·璜》嬉笑怒骂、“仿英雄体”风格的读者都不难发现,拜伦对蓝袜子女士极为不恭。在他的笔下,这些出入上流社交场合的淑女名媛,一个个不过拿腔作调,背诵十四行诗,用最新的文学评论充当谈资,来掩饰内在空虚。面对这样一群装腔作势的女士,诗人真有些厌恶,必然要对她们冷嘲热讽。而当“蓝袜子”同“博学的女士”被不断联系在一起时,诗人的倾向愈发明朗。
唐·璜母亲伊内(Inez)是一位博学的女士,也是出现在叙事部分的首位女性。精通格致之学,尤喜算术,超凡的记忆力更让她熟知基督教世界古往今来的语言,但诗人表面的溢美之词无时无刻不夹杂着调侃和讥讽。一方面说她精通多国语言,但实际上不过是拉丁文的祷词,希腊语的字母,而法语的发音也不甚纯正,对本族的西班牙语更了无兴趣。虽然是调侃式的奉承,伊内(Inez)还是被渲染成一位“无与伦比”的母亲,“完美”的化身,历代的圣女同她相比都黯然失色。最后叙述者这样戏弄这位“非凡的女士”:“一句话,她是会走路的计算器,/像从艾基华斯小姐小说的封面走下来,/或者来自托墨夫人的教育书籍,/抑或是寇勒博探寻的妻子,/她是道德古板的化身,/就是‘妒忌’也难寻丝毫的瑕疵。/‘女人的谬误’都摊到别人份上,/因为她就不曾有过——这岂不更糟”(第一歌,第十六节)。
这一诗节提到的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足以说明伊内是一个以英国“蓝袜子女士”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典型。其实也正是这幅肖像描写让拜伦的出版商极为不安,因为书商怀疑诗人正不怀好意地嘲笑他离异的妻子安娜贝尔·密尔班可(Annabella Milbanke),因为这位女士同伊内一样,只对所谓数学和完美的道德感兴趣。就在这一诗节里,诗人毫不掩饰对她们的不屑,还无意中揭示了妇女与知识文化问题的潜在意义。这就构成两个问题:1)“蓝袜子女士”到底身为何人?2)拜伦所处的英国社会,对于女性阅读或者说女性智识的发展持怎样的态度,而这又会对《唐·璜》杂议和叙事的理解产生怎样的影响?
显然,拜伦借伊内这一形象试图嘲笑的并非西班牙女性,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英国上层女性。以上的诗节提到的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女性的文化生活。玛丽亚·艾基华斯(Maria Edgeworth)(1767-1849)是畅销书作家,她同父亲理查德(Richard)合作出版的《实用教育》(1798)是当时流行的“行为书籍”,大力倡导对儿童尤其是女童进行现代科学教育。撒拉·托墨(Sara Trimmer)(1741-1810)是改良主义者,通过小说创作突出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寇勒博寻妻记》(Coelebs in Search of a Wife)出版于1809年,作者汉娜·摩尔(Hannah More)(1745-1833)是位宣扬清教徒美德的畅销小说家。三位女作家共同捍卫的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核心道德观,然而如果将清规戒律贯彻到生活中,就像伊内那样没有任何变通,这位母亲便成了苛刻、拘谨、死板、甚至伪善的道德木乃伊。然而像这三位女作家一样的蓝袜子女士们已经成了不可小觑的社会势力。
十八世纪五六十年代,“蓝袜子女士”在伦敦逐步形成,其成员大多是富裕有闲阶层的知识女性。由于厌倦在无休止的打牌和探亲访友中消磨时光,同时也渴望融入能言善辩的文人清客的圈子,这些女子模仿欧陆都市例如巴黎、柏林和罗马组织时尚的文艺沙龙。伊丽莎白·蒙太古(Elizabeth Montagu)和伊丽莎白·韦兹(Elizabeth Vesey)是其盟主。她们邀请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大卫·盖里克(David Garrick)这样的社会贤达出席她们的活动[4](P178-93)。对于“蓝袜子女士”来说,智力探询是无穷的,她们相聚一起讨论道德问题,翻译经典著作,开展文学评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斯图阿特·居兰(Stuart Curran)认为:“蓝袜子女士”这个群体的出现说明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有关社会礼仪和人文价值的讨论和思考已经延伸到部分女性当中[5]。可以说“蓝袜子女士”是18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化生态的重要一环,独特的社会身份使她们享有一定的文化特权,能结成相当规模和层次的文艺网络,专注于人文精神和艺术理想的追求。她们是启蒙运动在伦敦都会人文荟萃条件下的衍生品,对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文坛有相当大的推动力。
“蓝袜子女士”的出现标志着英国女性开始扮演新兴阅读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艾基华斯在《致文学女士的信》中这样描述:“近来从事文学活动的女士比过去几年大大增加。她们成为一个阶层,吸引公众的视线,由此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影响和性格。”[2](P92)这里所提的文学活动更专指小说创作。女性不断加入到小说创作的队伍当中,通过写作获得社会身份和某种意义上的独立。这一现象对文化生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女作家可以和男作家一样精确地把握日常细节,另一方面,也使小说成为“女性化”的文体,同诗歌对立,并日益突出诗歌是上流社会男性专有的文体,折射出门第出身、文化教养和贵族品味[4]。小说的兴起标志着女性日益介入公共话语,大众阅读活动也蓬勃发展。邓肯·吴(Duncan Wu)认为:“典型的十八世纪的读者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社会教养,具有内在的文化归属感,而在八十年代,这样一位读者极可能是女性。”[5](P91)需要补充的是,蓝袜子女士仅是这个大众文化塔尖的华丽亮片,下面还有大群的普通女作家和家庭教师。
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职业女作家的增加使“女性化”写作迅速成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引发了男性权威的不满。1801年时任皇家学院院长的亨利·富斯里(Henry Fuseli)在题为“论当下的艺术,以及妨碍其发展的原因”的演讲中这样说,“我们所处的时代同往昔相比,并未给伟大的作品保留多少适宜的环境,这也正是为何巨作寥寥无几的原因。雄心,公共活动与精神,萎缩成室内布局的琐碎细节。我们周遭私密的一切变得舒逸,狭隘,零碎和微不足道。或许大家并未因此感到伤心,但是想指望从自私的鸡零狗碎的事务上建立恢宏的艺术系统,如果没有彻底的革新,即使不是疯颠也是有点狂妄的。”而在另一处讲演中,他更是将庸俗繁琐的社会氛围归咎到新兴女性。富斯里认为自己处在一个阴盛阳衰的时代,而“在奢侈的时代,女性拥有品味、主见,可以发号施令;在奢侈的时代,女性渴望发挥男性的作用,而男性退缩到女性司掌的范围。太监的时代势必也是河东狮的时代”[2](P96)。富斯里其实表达的是男性传统权威受到挑战的集体焦虑。柯尔律治(Coleridge)对于女性不自觉推动的文艺平民化也是心存芥蒂,因为公共性阅读的普及损害了作家神圣的话语特权。1798年,理查德·坡韦的小说《无性的女性》(Richard Polwhele’s The Unsex’d Females)更是一本厌女情结的小说,女作家被诬蔑成社会的怪物,不容于世俗想象。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个时期最畅销最受好评的作品,均来自女作家。拜伦在《唐·璜》中所表现的倾向显然与此有关,却被评论界所忽视。
二.女性作家的消失与回归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写作却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英美大学的“浪漫主义”文学教材中消失了,这种缺失体现了男性意志和话语的仲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麦甘出版的《浪漫主义意识形态》(Romantic Ideology)一书和由此引发的“历史学转向”,才将女性写作从历史的故纸堆中挖掘出来。随着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越来越吸引学人的目光,她们的文字迫使文学史家对“英国浪漫主义”进行重估,她们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版图,同时提出了有关文学史重写、公共话语以及男性话语霸权等一系列问题。可是传统观念的霸权地位仍然牢固,目前在英语系的文学教材中,英国浪漫主义“六大头”(Big-six),即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雪莱,拜伦和济慈仍是通用的版本。但历史的真相却是,男作家中只有瓦尔特·司格特和拜伦才能与当时如艾基华斯这样的女作家相抗衡,而不是如现在所描述的清一色男性作家。就读者接受的效果而言,雪莱和济慈的诗歌极少有人问津。因此,蓝袜子女士代表的女性写作不应被忽视,甚至是难以绕过去的读本。
出于对女作家被文学史忽略的不满,罗杰·隆斯戴(Roger Lonsdale)出版《十八世纪女诗人》(1989)一书,希望补上文学史图的缺陷。他注意到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选集极少收录女诗人的作品,例如对十八世纪诗歌研究影响较大的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以及亚力山大·钱默斯(Alexander Chalmers)分别于1792年和1810年编撰了多卷本诗歌选集,均未收录任何女作家的作品。他认为在“浪漫主义”的历史话语中,蓝袜子女士们失去了“作家”的身份,这是极为不公的。他甚至认为“这是当时的男性作家企图从女性作家和读者那里抢夺诗歌的阵地”[4](P92-93)。
可见,“蓝袜子女士”及其女性写作是不可忽视的。《唐·璜》中大量存在的有关“蓝袜子女士”的诗行,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浪漫主义时期存在的女性写作,对其声音的缺失加以反思,也可以说明拜伦是如何同当时女作家们产生历史互动,她们是否是男性话语的潜在对手。假如十八世纪末女作家真是所谓男性经典话语霸权的牺牲品,那么拜伦的评论或许揭示了一位历史在场者的真实感受。
文本的盲点往往是在不经意的对照中发现的,无论是宏大的历史话语,还是具体作品中的吉光片羽,都拥有平等的叙述地位,并不因其中一方,由于特定文化语境中相对的强势而获得更多的合法性。《唐·璜》对于“蓝袜子女士”的记录至少说明拜伦并未刻意隐瞒什么,其中透露的不满更可以烛照时光长廊中的死角。与拜伦同时代的托利党人约翰·罗卡特(John Lockhart)在读了《唐·璜》之后,放弃党派的成见(拜伦是辉格党),这样评论拜伦:“你的确了解英国社会,既了解英国绅士,也熟悉英国女士,这种洞察是宝贵的。”[6](P189)事实上,正是出于历史的坦诚,拜伦才多少同经典英国“浪漫主义”有些格格不入,他的存在无时不逼问着华兹华斯式的“神秘的隐遁”、“想象”和超越世俗困扰的浪漫品格,让我们质疑这些是否有真实的历史出处,还是后世学者的臆想与杜撰。其实面对世俗的“女性化”公共空间(当然也有其它原因),男性日益感到不满和无能为力,如果承认这一点,很多形而上的建构就是多余的。接下来,本文将以蓝袜子女士为基点,把论述的重心转移到文章开头提出的叙事和杂议的问题上,对拜伦的创作动机加以勘查。
三.《唐·璜》与来自女性的挑战
拜伦在《唐·璜》中对“蓝袜子女士”的贬低排斥,仅仅是一场“性别之战”的几缕硝烟吗?并不全然。在拜伦眼中,蓝袜子最突出的特点是炫耀知识,崇尚科技理性,这正是近代工业文明的特征。所以拜伦对蓝袜子女士的抵触情绪也折射出对近代工业文明本能的反感。正如席勒所说,“他们始终完全看不见人性,因为他们把人性同纯粹智力的产物混淆起来。”[7](P146)当蓝袜子女士们陶醉于知识的炫耀时,她们获得的是虚荣,异化的是人性。而拜伦的反感正是在他同这个“女性化的空间”的接触中产生的。一方面,《哈罗德游侠传略》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伦敦沙龙的座上宾,他频繁出入贵族之家,同一些知名的“蓝袜子”女士有了接触。很多贵妇,除了后来成为拜伦夫人的密尔班可(Milbanke),还有同拜伦闹得满城风雨的卡罗琳·兰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以及同拜伦交好的牛津夫人(Lady Oxford)、布雷斯顿伯爵夫人(Countess of Blessington)均是当时圈中的突出人物。另一方面,诗人在日记或者私人信件中的坦白,让我们了解到两性在写作中的智力角逐和他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博弈。比如,1813年5月,拜伦在戴维夫人(Lady Davy)的聚会上遇到了艾基华斯,他坦言,狄拉括夫人(Ly.Delacour)的机敏和纽金特小姐(Miss Nugent)的理智让他极为沮丧。这两个人物分别是艾基华斯小说《伯琳达》(Belinda)和《缺席者》(Absentee)中的女主人公。在拜伦的眼中,这些女子虽然都聪明机智,却虚伪自私,心机重重。又如他初识密尔班可时,曾这样写道:“我其实并不想同密尔班可小姐很熟。我这样一个堕落的人,并不怎么期许认识这样好的一个人。如果她没有那么完美,我可能还会喜欢她些。”[8](P48)
很明显女性智识的提高,已经让拜伦这个破落贵族的后代倍感压力,而在《唐·璜》中他毫不隐讳这种社会现象对家庭生活的压力。在乔兹和伊内家庭闹剧的间隙,他这样讥讽娶了博学女士的丈夫们,因为他的经历使他比谁都更有发言权。“可惜才女总嫁给没什么教养的人。/即使是有门第有教养的绅士,/也会厌烦科学对话。/我在这方面没什么多说的,/我是平常人,单身,/但是-噢,聪明女士的老爷们,说实话,你们受得了‘妻管严’吗?”(第一歌,第二十二节)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女性似乎掌握了家庭内部话语的主动。拜伦曾戏谑妻子是“平行线公主”,他同妻子的矛盾与其简单归咎于厌女症的嫌疑,不如说他本能地反感工具理性对人性的约束逼迫。或许他同密尔班可本来就像两条平行线,注定不会有交点,却有意无意地被纽结到一块。甚至当拜伦漂流海外,摆脱了家庭束缚,他还不忘幸灾乐祸地嘲笑忍受着“妻管严”的男人们。无论他们的个人教养如何,妻子们滔滔不绝的科学谈话,也会让他们厌倦。
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在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欧洲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对男性霸权提出挑战。她们的声音和表现说明女人在智力上并不比男性低下,而且女性的角色不应局限于家庭内部。前文提到的有关儿童教育、社会道德的书籍都可以说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开始利用写作介入社会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拜伦对于蓝袜子女士的抱怨,一方面部分印证了两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说明即使在家庭范围内,女性凭借新的崇尚科技的话语模式,开始获得话语领导权。在此种态势下,性别的差异,在一些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家庭内部,表现成科学理性和感性诗意两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差异,而后者的载体,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开始事实性地边缘化了。在叙事部分,诗人对伊内的刻画,其实反映的不完全是男性对于女性话语的不满,而是当女性自愿同工具理性结盟后,即使在家庭范围内,也可以构成对男性的话语压力场。这是因为工具理性同女性的结盟,表面上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也是对人性的异化,包含了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的一切弊端,所以拜伦的反感也可以理解,这从他对妻子“太过完美”的评价能体会出来。
此外,拜伦还受到外部日趋“女性化”的公共空间的压力。虽然此种提法本身隐含男性的倨傲,但说明女性在诸多社会层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这本身就是多重文化合力的结果。比如在社会改良的范围内,伊丽莎白·福莱(Elizabeth Fry)(1780-1845)就是位格外引人注意的女士。她积极投身到伦敦东区新门(Newgate)地段妇女儿童社会环境的改善。拜伦写道:“同胞们,接着说咱们的老相识:/至少我说的是实话,即使你们不信/因为事实就是如此。/我像是男性的福莱夫人,/用软软的笤帚从墙上刷下一两个蛛网。噢,福莱夫人,何必去新门?/为何向穷鬼们宣教?/为何不从卡尔登府或者其它府邸开始?/试试矫正顽固的帝国罪恶/劝善改错何其荒谬,/除非逼比他们强的人更好/呸,这无非是套话,发慈悲的陈词滥调。/福莱夫人,原以为您道行深些呢”(第十歌,第八十四,八十五节)。
福莱夫人的活动体现了女性通过英国福音运动在传播中产阶级道德方面的载体作用,因为这种行为只是资产阶级工业文明的装饰品,没有实际的作用,所以拜伦始终对福莱夫人抱着嘲讽的态度。在他看来,所谓的改造社会和人性的举动是徒劳的,不过是慈善家的空话。所以他开玩笑说,自己也愿意成为福莱夫人式的人物,拿着软软的笤帚,从墙上扫下几根蛛丝网。言下之意,贫穷实是帝国的罪恶,要想消除贫穷,只靠圣经宣道是不行的,还得打倒貌似体面的老爷们,而这可能吗?可见诗人表达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怀疑。
如果伊内的形象折射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冲突,福莱夫人的活动让拜伦对于女性介入社会改良颇有微词,那么当发现蓝袜子阶层开始左右社会的精神“品味”(taste)时,他的愤怒难以克制地爆发了:
“嗨,你们这些靠书籍发家的人!/蓝色的好心肠女郎!/你们的容貌是新诗的好招牌,/难道尔等不靠它打开销路吗?/为何我的书只落到厨子的手中,暗然无闻?”(第四歌,第一百零八节)//“什么,难道我再不能名扬四海吗?/只是个舞厅诗人,小傻瓜,小报追捧的宠儿?/忍受着乏味的恭维话,/像约里克的八哥一样叫:‘我出不来!’/天啊,我竟像罗索诗人华氏一样诅咒,/(因为诗没人读,他总爱吼)/品味消失了,名声不过是彩票,偷偷由蓝色小姐们抽取”(第四歌,第一百零九节)。
这两节诗包含的细节主要体现了女性,尤其是女作家与大众品味,和男性作家同女性阅读市场两方面的历史语境。第一节印证了男女作家之间的市场竞争。拜伦对蓝袜子女作家群的鄙夷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鄙夷不仅仅同女作家书籍的畅销有关,还同其促销手段有关。在拜伦看来,女作家的诗作是靠她们的外貌才得以行销,而他的滞销书(或许没有某些女作家那么流行)最后只能作废纸处理,被厨子用来包裹面点。第二节则描画了拜伦在仕女云集的沙龙里被戏弄的窘迫。成名后的拜伦不过是浮华世家的过客,成为舞场的点缀和小报炒作的对象。他不得不忍受乏味的恭维和打趣,因为他明白蓝袜子女士们的喜好是包括他在内众多男作家的命运。他还不忘拿华兹华斯开开玩笑,虽然这位同行很明白“品味”的重要,但是他的诗作却冗长拖沓,无人问津。如今拜伦漂流海外、回忆往昔,他不禁自问,难道再也不能成为叱咤风云的英伦雄狮了吗?
1818年拜伦开始创作《唐·璜》,抚今追昔,伦敦岁月反复出现在叙事和杂议的部分,蓝袜子女士们频繁出现,牵扯出诗人的懊恼、愤懑和玩世不恭的心绪。盖瑞·克里(Gary Kelly)用“蓝袜子女性主义”(Bluestockiag Feminism)说明伴随英国社会逐步成为现代消费性社会,“蓝袜子女士”标志着妇女成为新兴的文化力量(即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种力量),她们在资本的扩张中自觉扮演着可怜的工具角色。而“蓝袜子女士”便是《唐·璜》时代背景的生动例证。这些极富个人传记色彩的回忆,让读者可以领略有别于主流“思想史”或者“社会文化史”的历史叙述。其实拜伦较为真实地记录了当女性成为新兴文化趋势载体,以及男性个体体验的社会错位和由此产生的失落和沮丧;还有诗人出于人文关怀对现代工业文明和科学主义造成的蓝袜子现象所折射的人性异化的本能拒斥,这可能是目前拜伦研究所忽略的方面。
总之,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蓝袜子现象在《唐·璜》写作的文化语境中所占的独特位置。可以说假如忽略了这样重要的线索,就难以准确解读拜伦的《唐·璜》。
《唐·璜》体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过程。随着英国在十九世纪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帝国,中产阶级日益成为工具实用主义的载体,女性为资本逻辑和中产阶级道德所驱使,她们的存在价值日益得到挖掘和肯定,使得贵族阶级的中心话语被慢慢消解,篡改和颠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唐·璜》的叙事不能视为诗人意图的简单空壳和杂议的某种前提,而是拜伦企图通过话语和想象抵御“女性化”社会舆论和历史压迫的举动,因此《唐·璜》的叙事具有特定的反现实性和对当时社会的超越性。拜伦的唐·璜无论是在西班牙的乡镇、希腊的海岛、土耳其的后宫,抑或是沙俄的宫廷和英国的乡间别墅,虽然行为上是被动的,习惯依赖女性,但是他不断迫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宰,例如在伊斯梅战场上他挺身解救了小女孩莱拉(Leila),并一次次逃离令人窒息的母性呵护。《唐·璜》的叙事部分虚构了一个女性主导的个人成长空间,主人公成为母性力量的俘虏,而这种温柔的力量又和无处不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魔力纠缠在一起,他无时不为此感到焦虑,感到痛苦,使他难以摆脱,也不愿摆脱。他潜意识想要突破这样的依靠,但也明白如果脱离了这个圈子,就连生命也很难存活,这也许是他的贵族出身给他制造的悲剧性宿命。
在《唐·璜》中,从杂议中强势的“蓝袜子女士”到叙事中被动却不安分的唐·璜,可以看出诗人在同故国往昔对话的同时,也努力实现对这段回忆的超越。以蓝袜子女士为典型例证,拜伦在杂议里言说了对“摄政王时期”英国“女性化”公共文化空间的不满,叙事中的虚构体现了重新树立贵族精神和男性主体的努力。简言之,杂议是以现实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叙事实现了对杂议的诠释和虚构式超越。离开杂议,我们就无法了解诗人创作的现实和历史基础,而只谈叙事,《唐·璜》只不过是一部平庸的走马观花的旅游札记。只有将两者合而为一,作家、历史和写作才能呈现生动的对话关系,体现出诗意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