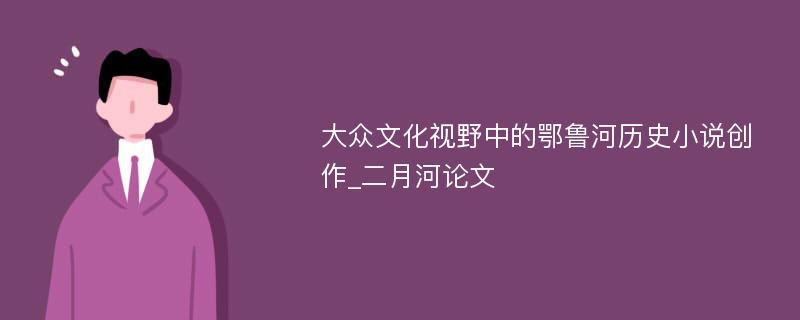
大众文化视野中的二月河历史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历史小说论文,视野论文,文化论文,二月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6-0078-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商品大潮和西方后现代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大陆境内的大众文学羽翼渐丰并随着政治理性与启蒙语境的转换,在世俗化所设定的框架内与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呈现某种合流的趋势。历史小说也不例外。虽然历史小说不同于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它的写作的主体不是大众化的路子,但在大众文化日益喧嚣的今天,其创作思想和艺术诸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风尚的影响。本文所说的二月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出版于1985至1999年期间的三大部十三卷、计530余万字的“落霞”系列(内含《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也许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但他通过自觉的艺术实践为历史小说的大众化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其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对历史小说的多样化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有必要值得重视。
一 “落霞”世界中的欲望叙事
大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现代的通俗文化。它的娱乐消费特征决定了其创作要顺从普通民众的欣赏习惯,对以往被社会性、阶级性压抑了的世俗欲望给予充分的关注乃至放大描写。二月河也是这样做的,作为底层出身的平民作家,也是基于对广大读者接受心理的了解——一般普通民众在意识深处存在对权力的膜拜以及对权力运作的兴趣。因此,在创作之中,他不仅自觉地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为“在不违背大的历史史实的原则下,那些小的历史史实我并不拘泥,因为我必须讨好我的读者”[1],而且还集中笔力和才情,驰骋想象,淋漓尽致地揭示深藏在皇权世界背后对大众具有极强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各种世俗欲望,从而使一向拘板沉滞的历史小说变得诡谲无比,充满了诱人的魅力。一时之间,其所推出的卷帙浩大的“落霞”系列洛阳纸贵,盗版四起,创下了历史小说发行量的一个奇迹。
当然,这里所说的世俗欲望对二月河来说,主要是权欲和情欲两个方面。而前者,可视为是透视作家皇权世界的一个窗口。它既是二月河解读封建文化特别是封建政治文化的极佳的切入点,同时也是作家提高作品趣味性和娱乐性的有效手段。众所周知,权力作为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驱动历史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所说:“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的”[2]。而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权谋文化向来十分发达,它也因其诡秘性和残忍性而成为蕴含极为丰富的创作资源。这些权力斗争的引进,既能增加文学叙述的戏剧性,又可迎合普通民众潜意识中的权势崇拜心理,故深受历代作家的青睐。二月河自然也深谙此道。在他所构筑的“落霞”世界里,作家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宫廷内部皇帝与大臣、皇帝与皇子以及皇子与皇子之间围绕着政治权力的争夺而展开的生死角逐。如《康熙大帝》开头和结尾所写的康熙在险恶政治环境中与阴谋篡位的鳌拜之间的较量,康熙与皇子们之间围绕储位继承展开的争斗。《雍正皇帝》对此的描写就更多也更集中了,全书三卷干脆以储位或皇位之争作为小说叙事的主干,通过整顿吏治、八爷党政变、铁帽子王逼宫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挟雷携电地描绘了众皇子之间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灭绝人伦的权力争夺战,并进而深入细致地挖掘这种严酷惨烈的权力争斗给人性带来的极度扭曲和畸变。尤其是雍正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最怵目惊心:一次又一次的权斗,半是逼迫、半是自愿,竟使他身不由己地由一个性格怯懦、生性淡泊的阿哥变成豺声狼顾、鹰视猿听的一代阴鸷枭雄,并逐渐被异化为可怕的反人性反人伦的受害者和迫害者。作家借雍正身边的“红颜知己”乔引娣之口曾这样评论雍正:“我留心来着,你越是心里苦闷,身弱,越是爱翻牌子……你这人真怪”。雍正与乔引娣之间的“情爱”悲剧,虽纯属虚构,于史无据,但通过乔引娣这“第三只眼”,作家却可有效地将权力叙事与人性嬗变融为一体,从而为作品的大众化写作平添了某种生命的思考和理性的深度。
与权欲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是情欲,它也是构成作家有关世俗欲望描写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才子佳人式的清纯韵事,还是风流皇帝式的民间艳遇,无论是雍正扭曲压抑式的乱伦,还是太监与那拉氏的荒诞性交,它贯穿了二月河欲望叙事的始终。这些诸如偷情、乱伦、狎妓的情欲描写,不仅极大地吸引和刺激大众的眼球,满足了他们潜在的猎奇心理,而且还对隐藏在性爱本能背后的封建文化体制和权力关系进行了透视与剖析。如被作家称之为主要是“说感情”[3] 的《乾隆皇帝》一书,内中有关乾隆与妻弟媳棠儿的畸形情欲描写便形象地展示了权力与性的互动关系:棠儿为丈夫的政治前途与乾隆乱伦,而乾隆则凭着帝皇的身份和事业有成的骄傲与棠儿偷情。对于乾隆而言,性是权力的果实,而权力则是实现性的手段。它们之间看似矛盾冲突,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又是可以统一和置换的。中国政治文化的诡秘性、残忍性和实用性,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欲望书写并非是二月河的专利,历史叙事的欲望化或曰欲望化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一大突出景观。放大地看,即使在一些精英化或趋向精英化的历史小说作家(如唐浩明、凌力、熊召政)那里,也都融进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描写。二月河不同之处在于:从大众文化的人学理念出发给予较多的欣赏和认同,同情大于批判,有时乃至把欲望的追逐和谋划当成政治智慧进行描绘。另外对大众阅读兴趣的过分迎合,也容易使作品的欲望叙述从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层滑落到形而下的物质身体层,而影响了小说的思想艺术品位。《乾隆皇帝》中出现的过多不当和雷同的性爱场面,就凸显了作家这方面的缺陷。这也是《乾隆皇帝》之所以在“落霞”系列中不被看好的主要原因。
二 超越大众的另一面
尽管二月河以较著的篇幅揭示了历史中的世俗欲望的因素,有时甚至作了过度阐释,沾上了大众文学的通病。但这只是一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在对康、雍、乾三朝的历史进行大众化书写时,并非简单使用一般大众文学惯用的伦理道德化评判机制,或按照“历史的流言”进行写作,而是努力站在国家、民族和百姓的文化立场,用历史唯物史观予以观照把握:“在我的历史观里‘英雄和人民同时创造历史’。这里指的是英雄人物,并不是帝王。有的帝王也很差,我指的是杰出的帝王。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王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4] 这使得他的“落霞”系列超越了一般流行的历史演义或戏说路数,与习见的大众文学是有距离的。
二月河这种追求,突出体现在《雍正皇帝》中的雍正的描写把握上。作家尽管揭示了他强烈的政治权欲和狡诈的权谋,但并不因此否定他的历史作用,将历史道德化、私人化。相反,以理想的“明君”尺度打造之,寄托自己的文化理想,曲折地表达对现实的关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写这书主观意识是灌注我血液中的两种东西。一是爱国,二是华夏文明中认为美的文化遗产。我们现在太需要这两点了,我想借满族人初入关时那虎虎生气,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5] 因此,在保留基本史实的前提下,二月河在雍正形象塑造中输入了诸如励精图治、勤政廉政、惩治腐败、整饬吏治等鲜明的“警世”意识。如雍正继位之前,为了国家和社稷利益,不惧骂名,得罪盐商,大刀阔斧刷新吏治。继位之后,继续贯彻“以民为本”的治国政策,不怕得罪群臣,大胆实施摊丁入亩、实行养廉银等。这就使其大众写作具有了某种超大众的文化内涵,由之,对雍正的历史还原也就有了颇扎实的思想基础,它比之道德化的历史翻案更加有力也更为可信。而过去,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狗咬狗”的斗争,它没有是非曲直、忠奸正邪之分,更没有评判的基本尺度。
当然,这并非是雍正形象的全部,作为艺术创造,最具新意和深度的恐怕还当推其思想性格被权力异化的另一面:从得势前的“龙骥虎步”到得势后的“鹰视猿听”的性情转变。作家将雍正放在“落霞”的历史情境中,既描写了雍正的勤政与廉政、“振数百年之颓风”的政绩,又展现了他为追索亏空,革新吏治,不惜得罪众阿哥以及年羹尧、诺敏、杨名时、岳钟麟、张照和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最后落得个阴谋夺嫡、杀兄屠弟、杀人灭口的千古骂名。这正是他的历史悲剧性所在,而雍正的悲剧则是封建文化的悲剧,是历史回光返照的一个具体表现。在这点上,作家可以说是相当清醒的。他曾感叹道:“从康熙初政虎虎灵动的生气,勃然崛起到乾隆晚期江河日下穷途末路,时光流淌了近一百四十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所谓‘最后的辉煌’,可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雍正这十三年是这段长河中的‘冲波逆折’流域,宏观地看,它是嵌在大悲剧中的一幕激烈的悲剧冲突。”[6]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同意将他的三部作品称之为“清帝”系列。在他看来,康、雍、乾三世所在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日薄西山,落霞满天却衰势尽显。这使得他的作品无意中平添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况味,并深深触摸到了中国晚期封建社会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上述这种既立足于大众又努力超越大众的创作理念,最真切的也许体现在伍次友、邬思道、方苞等士人形象的塑造上。这些人物以帝师的身份活跃在帝王身边,用他们的智慧,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和巩固王权殚精竭虑。每当关键之时,他们往往出来指点迷津,化险为夷,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月河通过他们的遭遇,一方面探询儒道文化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批判民族传统文化的残酷和虚伪:“那种东西,我并不喜欢,我并不欣赏,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残忍的东西,封建社会中那些温情脉脉的很虚伪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7];另一方面批判封建君王的政治权术,也就是所谓的“帝王之术”。这些封建文人浸渍着浓厚的儒家民本思想,他们胸存济世之志,身怀旷世之才,然而命途多舛,仕途不达:或抑郁惆怅,浪迹江湖;或悲患忧戚,归隐山林。如伍次友,虽为帝师而深得皇上器重,但“不耐这京师人事纷扰,更厌宦海浮沉,勾心斗角,相互倾轧”,最终只得悄然身退,意气还山。邬思道虽为雍亲王登基殚精竭虑,立下汗马功劳,但最终却只能远离庙堂,归隐山林。在他们身上,都带有明显的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悲剧的色彩。而这种悲剧,则来源于儒家民本意识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忠君”的界限。它实际上隐含了作者对民本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现代理解,这里的视角是批判大于借鉴。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仁政只是幌子,巩固封建政权才是目的。一切都以“君”为主体和本位,“民”只不过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重视人民只不过是“驭民”、“治民”之术。因此,他们注定要把民本思想变成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至于对“士”的倚仗与警防问题,他们就表现得更为矛盾。如乾隆就说过:“汉人聪明博学处事练达阅历深广,文明典型历代昌盛,这是其长。若论阴柔怀险,机械倾轧尔虞我诈,谁也难比他们。所以又要防他们又要用他们,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一不小心就落入圈套陷阱里头。”而开“博学鸿词科”、安抚士林的康熙,对待身边“士”的那种“洞悉一切”,那种刚柔并举和突然发难,更令人不寒而栗。由此也不难看出,清朝统治阶级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其低下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二月河正是以之为视点,写出了封建末世之际传统知识分子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两难处境和他们的精神痛苦。就这点而言,他的描写与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世逸才》、《张之洞》,熊召政的《张居正》并无多大区别,应该说是真切而深刻的。它揭示了在这盛世的背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所谓的民本的真实涵义。
然而在认可作家上述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大众立场毕竟对他这方面的深入探讨带来一定的制约和影响。比如乔引娣作为关照雍正的一种民间视角,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本应更具有批判的力量,但过分沉迷于她与雍正之间情感爱欲的描写,使它显得平面化、传奇化;邬思道作为作家的人格化身,也没有达到以现代眼光烛照历史的效果,只是以逃避和无奈显示传统文人无一例外的“独善其身”。这就使得他对大众文化的超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难以在整体本质上有大的突破。
三 汲取民间资源的奇趣活水
大众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迁的重要元素,充分体现着传统文化对现代化所做的适应性转变。与大众文化形态各异的西方文化体系的欧美各国相比,中国的大众文化更是打上了特有的历史文化烙印。一方面,我国的大众文化以其商品意识、开放意识和参与意识,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等级秩序、尊卑长幼的封建伦理思想,推动着转型期文化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着如仁爱思想、民本思想、务实观念等精华;丰富充实自身。而从艺术形式上看,大众文化往往体现在对传统文化颇富现代大众旨趣的诗性阐释,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资源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阐扬,以此来滋润和充盈大众叙事,赋予作品鲜活的生命感。
这里所说的民间资源,撮其要者,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叙事策略上大胆突破历史政治化、本质化的思维定势,采用符合民间趣味和标准的历史人性化、平民化的创作范式。比如《乾隆皇帝》便摒弃了以往的既定模式,眼睛向下,以平视的眼光有意将帝王平民化,当作普通人来写。作家花费了相当的笔墨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的乾隆,描写他政事之外如读书、吟诗、听戏、书法、骑射、闲游、私访、寻花探柳等生活内容。这使其笔下的乾隆不仅有威镇四海的皇权尊严,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充分显现出作为真实历史情境而不是观念形态中的皇帝形象,人物也因此有了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当然,严格地讲,历史人性化、平民化就是历史的自然生命化,它是作家从民间质朴的人道情怀出发,对被政治事件封尘的人的生命世界的关爱。因此,它的眼睛向下,不仅表现对帝王英雄的平视,而且也体现在对普通人物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上。在历史对象的描写把握上,二月河似乎有一种偏“下”、好“下”的取向,他更加愿意赋予小人物以传统的人伦和道德。如被康熙解救的死囚替身张五哥,作康熙侍卫时始终是逆来顺受,忠心耿耿;民间女子乔引娣历尽坎坷始终如一,不畏权势,宠辱不惊。这些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化身的小人物,在作品中起着连接帝王与百姓的中介作用。通过这些历史人物的书写,作家不仅发掘了一种古今共有的民族精神,而且可使读者在历史与现实中感受到相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蕴,从而有效地缩短了与陌生异己的历史间的距离。
其次,在虚实关系处理上,打破正史或仿正史的“按鉴”传统思路,择取百姓偏爱的重艺术真实和大众趣味的通俗化写法。如康熙智擒鳌拜一事,在清史上原本只有寥寥四行文字记载,《康熙大帝》在此基础上展开丰富的想象,设计穿插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而将康熙与鳌拜争夺皇权和政权的这段故事演绎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二月河如是创作与唐浩明、凌力等是有区别的。在唐浩明、凌力那里,不仅小说中的主要事件是真的,而且有关的细节描写也力求真实,做到合情合理,在此前提下讲艺术虚构和创造。而二月河却更加“忠实于艺术的真实性”,他把艺术的真实性置于历史的真实性之前,看得很重,明确表示:“当两者发生矛盾时,我在总体上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历史细节的描绘让位于艺术的真实性;当读者与专家发生矛盾时,我尽量的去迎合读者,历史小说允许虚构。”[8] 基于此,他不仅追求史实的真实可信性,同时更喜欢在小说中挖掘世俗文化背后所隐含的诗性,追求文学的趣味性,于精彩绝伦中实现质文同胜。以上文提到的虽有其人而并无实事的邬思道为例,野史记载他系田文镜的幕僚,作家以这有限史料为基础进行大胆虚构,才使得这位才思机敏、料事如神、几乎可与民间“智圣”诸葛孔明相媲美的权谋家形象,逼真酷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全书艺术整体来看,引进这样的人物不仅有助于深入批判和揭示帝王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化,而且大大推动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为我们提供了精英化、主流化之外的另外一种叙事,使历史叙事最大限度地走向大众。
再次,在表现方法和手段上广泛借鉴非主流的野史和民间资源,将民间文化的活水引入文本。这方面作者用力最多,成就也最为突出。首先是对历史传说、民间传奇故事、神秘文化特别是巫道之术的借鉴。如《雍正皇帝》中所写的道士贾世芳,清野史《悔逸斋笔乘》的两段野史记录其有异术,但又记录了他的法术并非百分之百灵验。作家抓住这一点,展开了丰富的联想,他用夸张的手法描述了贾的巫术,如用仗桃木剑给雍正施术作祟的番僧斗法,以天雷毙之于神武门外。另外还有史贻直弹劾年羹尧,其诚心感天动地,以致大雨滂沱的奇异情节;弘时魇镇雍正、弘历等妖迷鬼道之事等。凡此种种,这里虽有一些怪诞夸饰的成分,不足为取,但对增强小说的趣味是有益的。它不仅使小说因此具有某种历史文化意识和生活实感,而且还平添了些许的诡谲神秘色彩和奇幻之趣。其次,是对民间故事中广为流传的忠奸对立、才子佳人、落难拯救、侠义英雄等叙事模式的借鉴。如雍正与八王党、张廷玉与明珠等宫廷上的忠奸对立,苏麻喇姑与伍次友、刘墨林和苏舜卿、曹雪芹和芳卿等的才子佳人情,胤祯落难被小禄一家搭救、勒敏落魄幸得张屠户家收留等,更有胡宫山、史鉴梅、江湖女杰“一枝花”等侠义英雄,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再次是对民间语言资源的借鉴。无论是拟回标目的章回体形式还是叙述描写的文言形式,二月河在语言上都尽力“拟古”,而且还竭力模仿古典白话小说的风格,甚至借鉴评书、说书的口气。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正说话间”,“走着走着,但见斜阳西下”等。由之,使小说语言既有古典的韵味,又有民间的情趣,颇适合现代一般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
需要指出,二月河大众化写作有一个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欲望极度膨胀而精神日趋稀薄的当下社会,他并非一味迎合,而是有自己的清醒定位:“专门迎合是不成的,读者的审美情趣太不统一了”[9],“既然理论家和读者都不可迎合,我只好迎合我自己。拿什么迎合?我想了想,一是凭我的文史知识,二是个人阅历,三是我的自我感觉。把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理解融进自我,变成一个社会人,这个社会人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对人面的洞察和内心灵魂的挖掘去组编,去结构”[9],“让尽可能多的人各自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9]。他的三部“落霞”系列就是他的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可以看作是他对大众化历史小说或历史小说大众化的一种吁求。历史小说是多样的,不必画地为牢,强令作家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一切有志向抱负的历史小说作家也应该而且需要打破陈陈相因的创作模式,按照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才能发展,为时代和人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食粮。这就是二月河大众化历史小说创作给我们的启发,也是我们从评论中引发出的结论。
标签:二月河论文; 大众文化论文; 雍正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乾隆论文; 康熙帝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