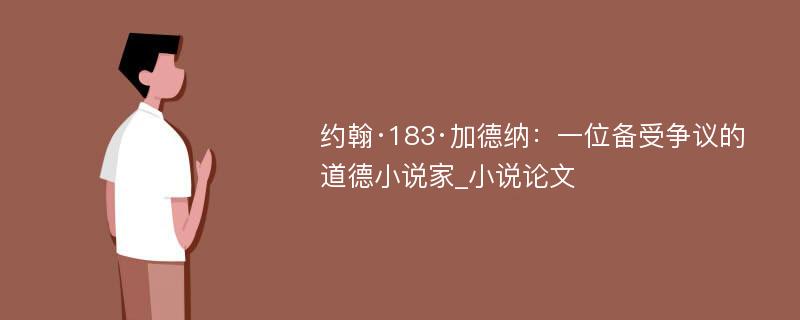
约翰#183;加德纳:一位有争议的道德小说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小说家论文,道德论文,加德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当代小说家、评论家和学者约翰·加德纳(1933—1982)在其短暂的四十九个春秋中,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从他出版第一部小说《复活》的1966年至他遇车祸身亡的1982年这十六年间,共创作长篇小说十余部,还有两倍于此数的学术专著、译著、广播剧、歌剧剧本和儿童文学作品等。不过,多产并不是使加德纳成为七八十年代美国文坛风云人物的唯一原因。另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观,与当时大多数作家、学者的观念格格不入,从而引发了一场当代美国文坛少有的大辩论。本文拟就加德纳于1978年出版的论著《论道德小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引发的大辩论作一简要介绍,并对此论战的思想根源作一探讨。
《论道德小说》是加德纳的一部批评论文集,它的出版成了加德纳的批评宣言,是对在他眼里已变得琐碎不堪、在谬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当代小说创作的宣战。早在1965年,本书的初稿便已成形,几经修改后,部分独立成篇的论文先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比如名篇“论道德小说”发表后就曾获得了“普什卡特奖”。后该论文集经过多次修改润色,几经波折,终于1978年出版。所以,可以说该书是加德纳创作思想和原则之集大成。
《论道德小说》开宗明义:“艺术基本是、首要是道德的——亦即,是赋与生命的。”(注:John Gardner,On Moral Fic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78)。)鉴于“道德”(morality)一词由于滥用而多呈贬义,加德纳特意对该词作了细致的定义:它并不意味着是说教的,因为教条主义与真正的艺术水火不相容。对加德纳而言,“真正的艺术是道德的”,因为“它澄清生活,建立人类行为模式,向未来撒出机会之网,小心判断我们正确的和错误的方向……它如闪电般触发,或者就是闪电本身……”艺术的道德从何而来?它并非“启示”(message )或“教条”(doctrine)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过程”(process ):“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发现、写出并检验自己的思想”;它“是一名艺术家借以产生洞见的手段,它是那独特的、高度复杂和极其苛严的发现技巧”。真正的小说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哲学方法”,它“表现理想、矢志维护和阐明真、善、美。理想是艺术的目的;其余都是方法论”。艺术的道德正是来自这个澄清生活、反对混乱的“过程”。艺术的道德表现在艺术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加德纳坚信,“生活追随艺术”。如果社会生活变得玩世不恭和堕落,那是因为艺术正是如此。他向人们警告说:“假如我们在我们的艺术中宣扬坏的价值观,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坏的社会。”正是“因为坏的艺术对社会产生坏的影响,所以不能让它未经盘查就蒙混过关”。而在加德纳的心目中,文艺家应该是其社会的自觉的卫士,要担当起“盘查”的责任;艺术家的任务是“寻求积极的道德观念,提供善的榜样”,而“批评的首要任务…… 应该是在作品的道德观念层面上去评判文学作品”。
加德纳在阐述自己的这一系列艺术观和批评观的同时,尖锐批评了当时的一些知名作家及其作品。《论道德小说》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分析近年来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偏差,来解释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大多数艺术要么琐碎不堪,要么谬误百出”。他认为当时大多数作家轻视对真理的追求,反而将技巧凌驾于真理之上,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吸引读者只关注小说中的语言结构或用加德纳的用词: 肌质(texture)。 因为“我们总觉得没什么好说的……肌质是我们的庇护所,是我们知道自己唯一拿手的东西”。于是乎,作为纯语言的小说成了一种时尚,那些倾心追求真、善、美的作家反而显得“老派”了。加德纳明确指出,这种对语言的聚焦带来的最终结果便是作家与读者之间交流的缺失:“语言晦涩表明了[这些作家]对读者的需求和希望以及对所有可能被埋葬在那种手法之下的思想的漠不关心。”他举例说,他的好友,著名作家威廉·盖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为语言而关注语言的小说家。他例举了一个长名单,其中包括J.P.唐里维,詹姆斯·帕笛,斯坦利·艾尔金和约翰·巴斯等,说他们“比起创造小说世界来,在原则上更钟情于词语的声音——或者说是标新立异”。
加德纳指出,有些作家虽然注意了作品的思想性,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使其作品变成了宣传品。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扎根于爱”,而“扎根于爱”正是对真正伟大作品的一个要求。加德纳认为,道德和爱是密不可分的,真正伟大作家的创作动因是爱,而读者阅读的动机也是出于爱。因此,那些只顾维护事业、只对风格情有独钟而对人物毫无感情或羞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家,其文学生涯逃不脱昙花一现的命运。加德纳历数当时许多已成名作家的种种不是:罗伯特·库弗是个“隐蔽的法西斯”,“永远在那儿故作高雅地大谈特谈或者令人作呕地散布他那套不可知论”。托马斯·品钦“可能是现在活着的最枯燥无味的作家”,其作品充溢着“挤眉弄眼扮鬼脸式的绝望”。他还无情鞭鞑琼·狄迪翁的“时髦的痛楚”,E.L.道克托罗的诡辩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局限性。其他著名作家诸如诺曼·梅勒、库特·冯尼戈特和约瑟夫·海勒在加德纳看来也都因为对人物关注不够,只把他们当作勉强拉来的例证使用而令人失望:他们尽管也在讲述事实,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他们的时代精神的译写员”。加德纳对索尔·贝娄尤为不满,他认为“散漫的思路并非小说最有效的工具”,而贝娄的作品“最后给人的印象是某种拉拉扯扯的劝勉作品,而不是艺术品”。所以在加德纳看来,贝娄本质上是个“伪装成小说作家的散文家”。他甚至破口大骂贝娄“显而易见是一头令人厌恶的男性沙文主义蠢猪”。(注:John
Gardner, On Writers and Writing,Stewart O'Nan,ed.,Charles Johnson,intro.,Reading,Ma.:Addison-Wesley,1994.)
被加德纳点名批评的作家则反唇相讥,指责他的作品过于老派,过于简单化和过于拘泥于过时了的道德和文学价值观。约翰·厄普代克说:“‘道德’是个如此有争议的词。当然,小说中的道德是精确的真理。世界已经改变了,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绝望的产物。比起去做他[指加德纳]所提议的无论哪种拔高生活的事情,正视生活并说出实情(无论这种实情有多么令人忧郁)要好得多。……我觉得他对贝娄也太过傲慢无礼了。”(注:Stephen Singular,"The Sound and
the Fury Over Fiction",New York Times Magazine,8 July 1979,PP.13-15.)约瑟夫·海勒则说:“加德纳是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侃侃而谈却少有隽永之语。他写沉闷乏味的小说和沉闷乏味的、鸡蛋里挑骨头的评论。”(注:Ibid.,P.34.)诺曼·梅勒则显得不屑一顾:“无话可说。我们会在天堂里再见的。”(注:Ibid.)
最猛烈的回击来自约翰·巴斯:
他的论点有很浓重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意味。他是在声嘶力竭地为文学右翼鼓噪,这一文学右翼想拒斥所有的现代主义并跳回到其19世纪的文学祖父们的怀中。加德纳自己的后期小说正是这么做的,当然也就受到欢呼。他是在用术语猛击比他出色的人们的头部,然后,当硝烟散尽之后,房间里除了加德纳先生自己之外,谁也没剩下。(注:Ibid.,PP.36-37.)
伯里娜·开普兰认为加德纳有关“真正的艺术表现理想、矢志维护和阐明真、善、美”的观点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是将自己陷入了哲学泥淖之中。她质问,何谓“善”?其本质又是什么?它内在于个人行为还是社会群体之中,抑或在宇宙范围内显现?在大多数时候,加德纳的“善”只不过是其自己善良心地的流露,是将自己的个人信念拔高到普渡众生的信仰。另外,对小说的社会责任和严肃性的强调无形中却是对所有富于天才原创能力的文学的排斥。她说,像《呼啸山庄》和奥斯卡·王尔德、伊芙琳·沃的那些非理性甚至荒诞的作品在加德纳的标准之下就永远不能被称作是伟大的作品,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可以激励和引导人类崇尚美德”的榜样。(注:Brina Caplan, "Book Reviews:'On Moral Fiction',in The Georgia Review,Vol.ⅩⅩⅩⅡ, No.4,Winter,1978,PP.936-38.)
评论家韦伯斯特·肖特则对加德纳关于“生活追随艺术”这一论断进行了驳斥。他认为,艺术不能改变我们,是我们在改变艺术。他举例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纳粹刽子手们在干完了一天的血腥屠杀之后照样在晚上欣赏贝多芬的音乐;而喜欢阅读加德纳最为钟情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的俄国贵族们却心狠手辣地蓄着农奴、发动战争。所以,他总结说,不是艺术家,而是象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思想理论家改变了俄国的命运和社会结构。至于如何看待加德纳的《论道德小说》,他建议大家把它看作是加德纳(同样也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可惜的是我们(包括加德纳)无法把它变成现实。
艺术是人类想象的表达。它可能确认;但它更经常在抗议。它的存在可能只是为了被消费掉。它可能没有任何可以量度的用处。艺术直接来自产生它的文化的复杂情况。……加德纳不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来自现代知识的艺术理论,因此他编造了一个建立在对这种知识所创造的艺术的遗弃基础上的理论。假如不能跟他们合伙, 就打倒他们。( 注:Webster Schott,"The Sound and the Fury",in
Book
World—TheWashington Post,April 23,1978,P.E 3.)
加德纳的观点将大多数其他作家推向自己的道德藩篱的对立面。在一次《大西洋月刊》对他的访谈中,他承认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几乎没有什么人跟我合得来”,因为“很少有人相信可以把小说当作探索,当作理解”。(注:Don EdwardsandCarol
Polsgrove,"AConversation with John Gardner," Atlantic Monthly,239(May 1977),PP.43-47.)其实不然。尽管加德纳将艺术家当作道德代言人的观点显得有点过时,但他对“道德小说”的呼吁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这是些对当前小说大为不满的读者和评论家,他们跟加德纳一样,认为这些小说脱离生活实际并且缺乏真诚的情感。评论家朱利安·莫伊纳罕就是加德纳的同情者,他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宣称,“看到各种各样时髦的忧郁散布者和世界末日贩卖者受到他的严厉谴责真是大快人心。”(注:Julian Moynahan,"Moral Fiction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17 May 1981,P.28.)托马斯·勒克莱尔虽然在《当代文学》上批评了加德纳的“傲慢”和好斗以及毫无想象力地对近年来的小说进行解读,但他却公允地指出,《论道德小说》“仍不失为一部必不可少的书。……它急切的力量甚至要求那些对它逐页批驳的读者都去研究他有关小说的论断,因为没有其他任何作家……最近提醒过我们艺术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因此,勒克莱尔总结说,《论道德小说》“并没有因为它的诸多缺陷而不攻自破,因为最终加德纳跟伟大的艺术站在一边,这是一种显示作者对其职业、世界和读者之挚爱的志向远大的高雅艺术”。(注: Thomas LeClair,"Moral Criticism,"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20,No.4,Autumn,1979,PP 509-12.)查尔斯·约翰逊则将加德纳比喻为“美国文坛的拳王阿里”,因为《论道德小说》中虽不乏偏颇之辞,但它毕竟是部勇气非凡的论文集,其有关艺术的责任感、爱和对读者利益的关注等主张在当代文学史中自有其一席之地。(注:"Tributes to John Gardner",DLB Yearbook,1982,P.163.)
对于这场牵涉面极广、影响深远的论战,20年后的今天美国文坛仍记忆犹新。不少学者试图从不同角度对此作出客观的解释。评论家博·G.厄克伦德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在没有道路的森林里:约翰·加德纳的文学方案》独辟蹊径,运用比埃尔·鲍狄尔的社会学模型对加德纳的禀性(habitus)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 加德纳的禀性是由他在乡村成长的家庭背景、从小接受的宗教熏染以及对高雅文化的笃信等因素综合塑造而成的。最后一个因素引导他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作家,他的禀性决定了他写出来的东西与当时以约翰·巴斯和托马斯·品钦为代表的后现代派小说格格不入,也是出版商不屑一顾和断然拒绝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他不得不改变禀性,以求为文学主流所接受。但他的种种努力每每得不到回报,直到1966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复活》才得以出版,可是评论界对它评价并不高。《论道德小说》的初稿写成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点在厄克伦德看来显然并非偶然:这是他内心愤懑之情的集中体现。及至取得一定的成就和声望之后,加德纳便开始挣脱强加于自身的枷锁,并对那些长期压在自己头上的文坛成名人物发动反攻,以期获得表达自己真正禀性的自由和争得在文坛上的象征性支配地位。(注:Bo G.Ekelund,In the
Pathless Forest:John Gardner's Literary Project,Uppsala: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1995.)这种从个人禀性入手、以社会学模型分析作家作品的做法虽有新意,却不免失之偏颇。《论道德小说》所引发的论战并非只是针对加德纳的个人行为,而是以加德纳为代表的传统文学对60年代以来美国后现代小说所走的偏激道路的一种反拨。
二战以后的近二十年里,所谓的“沉默的一代”无论在道德、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与官方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因此就总体而言,那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提供给人们的是乐观的、道德的处世原则。可是1963年肯尼迪总统的遇刺事件改变了一切。随着大量内幕和真相被揭露,美国人发现原先如此信赖的官方话语竟然是由一丝丝谎言编成的网,于是困惑、怀疑、幻灭取代了相互信任,一种新的历史观和小说观应运而生。历史已经毫无真实性可言,它已经变成欺骗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个弥天大谎,于是去检视并揭示其骗局就变得尤为重要。由于语言是历史骗局的同谋并成为使历史的谎言和幻像得以长存的“罪魁祸首”,检视语言、使之失去其原有的象征能力便成为重中之重的事情。其结果是,六七十年代涌现了无数具有强烈内省(self-reflexivity)色彩的小说,它们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片断的集结、令人困惑的货单的罗列以及毫无关联的事物的拼贴。这些以无序、故意的混乱、碎片化和误置为基本特征的小说其语言也变得非理性、无逻辑性、不连贯,甚至毫无意义。威廉·巴罗斯于1959年出版的美国内省式小说的开山之作《裸餐》中的一段话正是对其开导的小说类型的最好的定义:“世界不能被表达,可能它可以被一些并置的拼凑物所显示,正如被遗弃在旅馆房间里的物品,消极和不在场成为它们的特性。”(注: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mory Elliott et al,ed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P. 1145. )此类小说的不可阅读性(unreadability)和虚无主义思想引发了人们对小说作用的焦虑。 加德纳可谓坚决反对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加德纳曾抱怨说,“在糟糕的或者是平庸的小说中,我们阅读时感觉到的不是某个居支配地位的声音,而是一系列有差异的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是些令人困惑的互相抵触的声音。”(注:参见Ekelund,In the Pathless Forest:John Gardner'sLiterary Project.)但是60年代以来发展并盛行起来的文学理论, 特别是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对此却有另一番评价。加德纳所说的“有差异的不和谐的声音”,甚至是“互相抵触的声音”,其实并非“糟糕的或者是平庸的小说”的特征,而是伟大文学作品的特征,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而正是加德纳推崇备至的托尔斯泰(加德纳曾说过:“我说,作为一条原则,假如苏格拉底、耶稣和托尔斯泰不愿做的事,就别去做。”)(注:参见Ekelund, In the Pathless Forest:John Gardner's Literary Project.),在巴赫金看来,作品只拥有“单调的、天真的视角”,势必要被一种对话的复调的想象力所取代。所以,这场论战其实是传统思想与后现代思想之间的一次正面交锋。
曾有评论家批评加德纳言行不一,说他所提出的“道德小说”原则连他自己都未必能遵行。比如,紧随《论道德小说》之后出版的《弗莱迪之书》(1980)所用的结构和技巧与其说是“道德小说”,不如说是跟约翰·巴斯的作品毫无二致的后现代派小说。“加德纳是个比他自己知道的更好的现代派作家。”(注: John Romano,"A
Moralist's Fable,"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rch 23,1980,PP.1 26-7.)这显然是种误解。因为加德纳在《论道德小说》中倡导的是一种既有技巧创新又有道德基础的小说:前者要求作家充分利用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作家的种种技巧,后者则需要作家意识到文学作为一种宣扬和证明人类生存之尊严的工具的重要性。两者并不矛盾。比如《格兰代尔》采用古英语韵律和自我意识的技巧,描写了虚无主义者格兰代尔的道德重建;《十月光》广泛运用了写实主义、框架小说和科幻小说等手法,描写了极端保守主义者詹姆斯·佩其和极端自由主义者萨莉·阿博特在相处中如何学会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并友好共处、最终实现各自的道德重建。而《弗莱迪之书》则从哥特式小说和寓言中汲取诸多技巧,通过拉斯—高伦·伯格基斯特和汉斯·勃拉斯克主教这两个人物形象,意在说明信仰在道德重建中的必要性。综观他的十几部小说,可以归纳出一个共有的模式:加德纳通常描述没落文化背景之中的一个丧失信心的人物,如何在自己、他人身上和社区中发现某种给予他希望的东西,最终又能保持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加德纳的根本的文学观就是认为它是“一种共有的话语,一个道德样板,一种将人们紧密团结而不是离间拆散的互相理解”。(注:"Tributes to John Gardner",DLB Yearbook 1982,P.159.)加德纳的生前好友戴维·科沃特曾感叹,加德纳的大多数同代人对人类命运感到悲观,而他却坚持认为20世纪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关键是艺术家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不仅仅是记录凄惨的生存现实,更要重新想象现实并使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以达到对该现实的重组。(注:Idid.,P.161.)这种积极的小说观和乐观的人生道德观的结合正是加德纳最可贵之处。
毋需讳言,加德纳曾极力贬低的那些作家,在当代美国文坛的艺术成就和地位都是无可争议的,而且似乎都比加德纳更受人重视。但是,不必以成败论英雄,更何况对作家的评价往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加德纳对小说的道德作用和作家责任感的强调以及对人生的乐观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正如评论家麦克斯·艾普尔所指出的那样,加德纳的论点,是一个不为昙花一现的特定时代所蒙蔽的预言家的论点;加德纳是一个以托尔斯泰为楷模的当代道德小说家。 (注: Max
Apple,"Merdistes in Fiction's Garden,"in The Nation,April 22,1978,P.4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