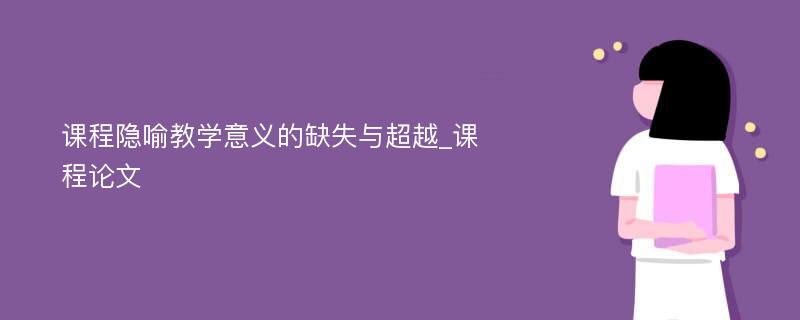
课程隐喻的教育学意义缺失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缺失论文,意义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课程概念的逻辑界定依从、取决于对其自身隐喻的理解、把握和定性。但由于隐喻内涵的广域性、扩散性、兼容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其解读和阐释也就引发出来许许多多生动、鲜活的多元解说或对立、相斥的意义框定及学术化疆界。正是这种课程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各行其是”,也就导致了实践范畴的偏执一方和固守一端。所以,对教育问题、疑难和矛盾的穷诘和叩问最终化约为对课程隐喻本质的价值选择上。笔者认为,应当扭转和脱离传统教育哲学中对课程概念的实证分析、逻辑演绎和抽象思辨的旧轨,转而寻求和追诉课程隐喻的人文性、价值性和时代性,凸显和彰显课程隐喻在本体属性上的文化内涵及教育学意义。
一、隐喻的意蕴及其特征
“‘隐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metaphora,其前缀meta的意思是‘超越’,而词根pherein的意思是‘转送’,因此,隐喻的基本词义就是把一个对象的诸方面‘转送’或‘转换’到另一个对象上去,以便使第二个对象似乎可以被‘说’成是第一个对象。亚里士多德为隐喻所下的定义就是‘为一事物借用属于另一事物的名称’。”[1] 在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化中,“早在先秦时期有了‘妙喻取譬’、‘辞喻横生’的文化取向。《诗经》最主要的写作手法就是‘赋、比、兴’。‘比’就是‘比喻’,包括隐喻和明喻”。[2] 隐喻作为众多修辞形式的一种,由于其运用手法及表征方式的含蓄性、朦胧性、想象性、“指物性”而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倍加青睐。随着文化的发展和研究范围的扩大及各种视角的不同解读,隐喻便突破了单一、狭隘修辞功能的原始形态,使其内涵和外延得以拓展和深化。隐喻也就成了众多学科竞相关注的焦点和对象,逐渐成了学术研究的一种强势话语。它具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建构性
隐喻在本质上不是以追求确定性、纯粹性、逻辑性为目标的科学定义,而是一个以描述性、形象性、意义性为特征的简约化命题。不同的读者由于根植于各自的理论背景、思想观念和审美旨趣,对隐喻的诠释和阐发必然会呈现出迥异的多元视角和价值判断。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学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表征了其本身意蕴的多视角性和深拓展性。所以,隐喻这种自身的特殊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类思维视角转换的频率,拓宽了人类探究外在空间的视野,开启了人类主体能动创新的阀门。
(二)精神象征性
“从语言学角度看,隐喻就是由一事物、过程与他事物、过程之间的诸多相似性而产生的事物间的指代或转移。”[3] 具体来讲,隐喻其实就是人们在事物与事物之间通过相似原理架构起来的有机联结。其中,由于人类的情感参与和价值赋予,它就改变了单一事物在物质实体层面上的简单呈现,而成了具有某种意识品格的精神实体,成了一个负荷和承载充满智慧、想象、情趣、希冀、诉求的精神象征体。它是人类内心生存理念的延展和美好愿景的独特表达,是人类行为的标杆和指向,是人类心中的神圣图腾和灵魂的最终归宿。
(三)人文价值性
隐喻作为人文思想、理念、信仰的托寄和申诉,表赋着厚重的人文蕴涵和隐性价值,它以一种缠绕不清的混沌状态来“磁化”、影响、渗透存在体,从而共同构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无所不在的“场力作用”。在某种情况下,它更像是一种心灵开放的权力,一种人类突破自身极限向外扩张的意志,同时也是对人类主体价值的守护和张扬。“隐喻是一种诗化的表达活动,融合了许多感性的因素和文化的内涵,超越了理性语言的冰冷,穿越了时空的限制,使教育活动的生命化和教育研究的人性化得到充分凸显。教育隐喻的使用,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是人们深深感悟教育和理解教育的创造性和独特性的彰显”。[4]
二、传统课程隐喻的多元指归及教育学意义缺失
教育发展史上对课程的隐喻性陈述可谓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一方面,传统教育哲学中的要素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了隐喻内容的意义和旨趣,极大地丰富、扩充和完善了课程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使其略显充盈和丰满。另一方面,因为“隐喻性陈述以事物的某种相似性、可比性为基础,故用这种语言陈述命题,往往带有模糊性、不规则性”,[5] 在对课程隐喻丰富内涵进行多元阐述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其价值取向的冲突和对立,也就导致了人们认识上的偏颇和狭隘及在实践层面上的无序和混乱。更为严重的是,它过多赋予和秉持了隐喻的工具化、手段化、技术化的逻辑和使命,而忘却了隐喻的文化性、人本性、精神性的品质和底蕴,造成了其文化内涵及教育学意义的现实性缺失。
(一)跑道式课程隐喻
跑道是课程最原始的隐喻样态,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由于我们所熟知的跑道这个具体物质实体有其固定的起点和终点、一定的长度范围、鲜明的档位界线以及椭圆式的外观形状,倒映和折射在课程理论研究及实践领域,导致了课程理论研究逻辑起点的单一、静止和褊狭,学校教学科目之间的硬性冲突、多元分化和“二元对立”,以及使整个课程编制过程始终在课程系统运行轨道上做一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单调、划一、僵化、机械的圆周运动。尽管后期“跑道”的意蕴得以扩展和深化,即从静态的维度上转移到动态的“跑”的维度上来,这种样态的课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主体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虽有利于主体者的能力发挥和主观创造,但它仍然遵循和规约在一定的运动弧线上,仍然是在计划好了的、规定好了的模式、套路、框架、范畴内秩序地前进,并没有“脱轨”和“出轨”,这种能动性的“跑”,也只是在技术的层面上提高了“跑”的效率,提高了“跑”的时速罢了,仍然没有跳出“跑道”的怪圈。“课程是‘跑道’似乎已成为定式,它是预定的、统一规划的,学生只需按要求进入跑道,根据规定的时间、速度和距离,按时到达终点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实际是在课程之外,而不是在课程之中,学生是‘容器’而不是‘反应堆’,教育是强制而不是自由,教学是灌输而不是对话,教师是权威而不是合作者”。[6]
课程是跑道的隐喻暗含了课程目标选择的预设性、固定性和先验性特点,课程编制取向的序列性、结构性和线性逻辑,课程实施标准的静态性、单一性和中立性旨趣,以及课程评价手段的终结性、量性和工具性表征。在本质上,它所呈现和展示的是一种静止的、封闭保守的课程模式,传承和授受的是一种模式化、功利化、工具化的教学内容,凸显和外化的是一种思想控制、行为约束的意识形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跑道课程呈现的是封闭、僵化、静止、外在的知识,运用的是简单机械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将学生置于枯燥乏味的学习环境中,置于复杂关系的重重压力之下,将生命个体的活泼的思维活动、创造探究欲望塞进、限制、束缚于课程‘跑道’,把作为人的心智活动与情感历程交织的学习活动等同于形体竞技的体育活动,在当代科学技术努力使机器变成‘人’时,却在将人化为‘机器’——信息储存的机器,技能操作的机器、应付考试的机器,戕害的是学生思维的发展,泯灭的是学生创造的渴求,违反了人的天性,违背了教育的规律,也违背了教育的初衷”。[7]
(二)学科式课程隐喻
把课程简单、肤浅、划一式地等同于教学中的科目,在中外教育史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我国古代的课程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欧洲中世纪的课程有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七艺,即为明证。科目编写者通过对人类文明、文化发展、历史史料的过滤和筛选,并根据特定的选择标准和价值取向,从中凝炼和编纂出具有一定理论体系、学术规范和逻辑结构的知识范畴,它承担着传统文化知识、崇高理想、宗教意识、道德信念等等的全部内容。首先,它是人类理性主义的外在表征,它强调纯粹理性而不是经验感知,强调价值中立而不是价值负载,强调学科的理论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及学科知识的科学化阐述和逻辑化建构,而丧失了对学生接受能力和认识现状的考虑。其次,掌握制度化学科的内容和体系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学科式课程隐喻里昭然若揭、不说自明。它并不强调人类认识结构的优化组合及整体经验的有机生成,而只是对一种僵化、繁琐、单一知识的简单认识和机械记忆。在学生学习效果考核上,则更多表现为对要求背诵内容的复述程度和转移能力,学生只需要把智慧、精力和时间全部放在书本里,也就算完成了对人之为人存在价值的建构和彰显,而对学生当下的生活世界、情感世界则漠不关心、弃之不理。它祈求通过对教学科目这一工具性形态的传递和授受来完成对人类经验的整体描述和薪火传递。
课程即学科的隐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揭示了其本质属性的教学科目维度,反映了课程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的物质载体形式和可操作性的蓝本。但这种隐喻指向在实践中却处于一种单向度、极端化的状态。它过度强调学科知识的学术性、结构性和逻辑性维度,只是褊狭地注重对学生的智力开发和理性思维的训练而淡漠和丧失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的关注;过多注重教学效率和教学控制,而使学生沦为毫无主体性可言的被动、异己的存在;过多注重单一学科的深层次探究,而缺乏各学科相互交叉、渗透、互融的综合性、整合性课程建构意识,造成了学生的有机整体经验处于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分化和肢解局面。就是在现在,这种单一、堡垒化、离散性的学科式课程在当前的学校课堂上仍大行其道,占据统治地位。同时,这种课程即学科的隐喻诠释也仅仅只是基于教学现象层面上的简单描述,并没有揭示和彰显出其内在的本质属性及其教育学意义。“将课程视为学科,只不过是对课程发展形式的一种约定俗成意义上的现象式描述、演绎与总结。而一个具体的、单质性的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是不可能通过形式及现象描述与总结的方式揭示的”。[8]
(三)经验式课程隐喻
经验式课程在杜威的学术世界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在自己的理论著作中曾不厌其烦地阐述其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课程价值观。他有一句名言:“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或改组。”杜威的经验课程观是对传统学科式课程的解构与反叛,是对在学科式思维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批评。他认为传统的教育是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教育实践,完全割裂和切断了目的与手段、价值与效用的有机联结,并指出这种教育是一种忽视人存在的教育,是对人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的扼杀与湮灭,是对丰富、美好儿童心灵上的破坏与摧残,是一种僵化的呆板透顶、极端无聊的教育实践。而他所谓的经验则消解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教育就是儿童对自身经验的不断认识、反省与改造,就是让学生在能动的实践活动中受到教育的启示。它注重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探究精神和能动钻研意识,注重了学生当前的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的结合与再造,从而有利于科学知识的内化和生成。
课程是经验的隐喻一方面大大突破和拓展了课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改变了人们对课程的单一、简捷化认识,更突出了学生的能动探究和参与体验精神;另一方面,这种范式也并非尽善尽美、无懈可击。首先,他所描述的“经验”始终是处于随机、无定的无限循环之中,而缺乏一种自我反思的精神和品格。这样,也就使得生成的经验的价值性及教育学意义大打折扣,只是一种肤浅、形式化、表面化的经历而已,而不会在学生的内心深处留下深刻的印记。其次,它过多看重了学生的主观体验及心理需求,把学生当下的现实需要当作课程存在的根本依据,这无疑否定和消解了教育的功用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确有忽视系统知识传授之嫌。再者,把生成后的经验机械地确立为课程的根本属性,这本身就是一种本末倒置。“这种把课程实施后的结果定义为课程本质内涵的观念造成了极大的逻辑混乱,……这种课程本质观把课程由前期性的一个手段、媒体变成了后期的结果、评价指标,完全颠倒了课程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9]
三、现代课程隐喻的价值表达及教育学意义生成
基于对以上课程隐喻价值取向的反思和批评,可以看出这些定义方式仍然是传统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外在表现,仍然局限于从某一个角度、层面、视域去窥视、探析、揭露课程的本质、属性和内涵,从而表现出一种静态性、模糊性和狭隘性。因此,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创设和生成一种新型的、开放式的、符合个性化生存和人类文化存在的具有教育学意义上的课程隐喻。它应当摆脱和消解工具主义、“技术理性”、功利主义的樊篱,呈现和彰显其内在的文化生成性、整体复合性、有机建构性和价值多元性的特点和旨趣。
(一)课程:开放的“通道”
作为对课程原始定义(跑道)的概念重建,后现代主义者大刀阔斧地、别具一格地开创了课程本质的深层次转换,课程在后现代的话语里具有了更多的意蕴和解释。小威廉姆·E·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这样指出:“课程不再被视为固定的、先验的‘跑道’,而成为达成个人转变的通道。”[10] 这种课程是“一种形成性的而不是预先界定的,不确定的但却有界限的课程”。[11] 这种界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延续了“跑道”的形体,但内涵却与其有着天壤之别。因为“跑道”更多是作为一种限制性和规约性的存在,是将学生牢牢地禁锢、捆绑、局限于这一狭窄的天地里,就像一个上了枷锁的牢笼或一座永远封闭的围城,使学生只能是望天兴叹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而“通道”的课程理念则消解了这一指向,这种“道”只是被作为学生施展才华的一种最基本的物质载体,只是学生认识世界、增长见识、积累经验和提升境界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以此为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由此,学生可以在这个澄清的世界里任性奔跑和呐喊,甚至可以享受理性的冲动和大胆的“越轨”所带来的无限的惬意和快乐。
课程的“通道”隐喻给予了我们颇多启示。首先,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它从根本上颠覆和超越了长期以来一直盘踞、笼罩、统治在课程领域的“泰勒原理”,突破和消解了传统单一、封闭化的课程价值观,从而为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等对课程理论研究的嵌入、融合及渗透提供了可能性依据。其次,在课程研制的价值取向上,改变了传统静止的、单质的、茧式化的课程开发维度,而呈现和生发出动态的、多元的、开放的课程理解范式,即其“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钟启泉语)。再者,在这条开放的通关大道上,我们与邻居、陌生人的相遇同样激动人心。“借鉴帕尔默(Parker Palmer)的概念,休伯纳运用‘异乡人’为隐喻来表达课程具有的‘更多性’与‘超越性’,促使教育成为不断向生活的新鲜感、新奇性与神奇感开放的超越的旅程。”[12]“异乡人是我们不熟悉的人,是外来人,同时也是拥有不同语言、形象、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人。向异乡人的视野开放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寻求人类生活更多的可能性。”[13] 与异乡人遭遇并与之对话、交流、沟通、相融的这段精神旅程及其过程的随机性、情趣性、即时性也使整个课程世界充满了惊讶、生机和美妙。
(二)课程:生成的“文本”
课程作为实现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目的的手段,其物质载体和外在表征已不能完全被简单、肤浅地化约为传统意义上的课本、教材或学材,使其处于一种完成时或被动态,成为只是摆放在学生课桌上的“文物”,让其硬性掌握和无聊背诵的蓝本,而应当是作为一种正在进行时或主动态的有机存在,一个正在等着被书写、描绘、刻画、阐发的生成性文本。首先,这种课程文本具有开放的性格。开放意味着对话,意味着阅读者的心灵敞开和话语表达,意味着不同视界的情境交融和价值集聚,它从根本上去除和解构了传统文本所谓的中心化逻辑、确定性旨趣和终极性答案,而走向了与不同的思维、话语、立场环环相绕、相融共生的“和合之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课程不再被视为由一组固定意义的符号构成的封闭结构,而是隐匿着无限多意义的、开放的、不断扩展着的‘隐喻’。现代课程文本论否定了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而坚持文本意义的动态性和开放性;作者的意图变得模糊和难以捉摸,而读者的创造性则得到了认可和尊重,读者不再依附于文本的指示和作者的意图,而是独立自觉地参与文本的理解和解释。”[14] 其次,这种课程文本具有生成的品质。它的存在不再是被某些专家、学者们通过理论假设所预先安排和固定,不再是单一局限于某一学科狭隘视域下知识的无机拼凑、机械组合和简单呈现,而是融合了教师、学生、家长及教育管理者等等所有相关主体,并在平等、对话、交流、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和创制出课程文本,从而完成对文本意义的整体建构和有机生成。
(三)课程:流动的“乐谱”
美国学者塞勒在探讨课程与教学的关系时指出:课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乐谱,教学则是作品的演奏。同样的乐谱,每一个演奏家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从而有不同的演奏,效果也会大不一样。为什么有的指挥家和乐队特别受人欢迎,主要不是由于他们演奏的乐曲,而是他们对乐谱的理解和演奏的技巧。[15] 受此观点启发,笔者认为课程不应当作为在刚性制度下的一种指令式存在,不是再单纯局限、依从、附庸在某一权威解释下的简单复制和转述,它的实际效用和意义呈现必应包涵了主体者的主观表达和有机建构,必定融入了主体者的理性思维和个性情怀。首先,教师的角色得以重新赋予,即从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释”形象中而转化为学生的引导者、启发者和促进者,转化为与“乐谱”的对话者、交流者和生成者。这样,“乐谱”(作为课程的隐喻存在)的意义由于教师的学术背景、价值旨趣及个性、视角的迥异而产生了多种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乐谱”不再被看作是一种静止、沉寂和陌生的数字化符号,而成了一条洋溢着热情、活力、朝气的生命曲线。其次,传统的机械式、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模式得以消解和重构。即我们的教学应当从简单授受、单向灌输和被动强化的规约中解脱出来,弥补和增添了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演奏的技巧”。这种把学生的乐趣、爱好、兴奋点融合一体的教学是对学生内心情感诉求和完美人格的保护和尊重,是对学生主动创新和审美意识的唤醒和激发,它应当成为满足学生心理需求,使学生在快乐和享受中接受和理解知识的一门艺术,成了一种极富创造性、审美性、人文性的实践活动。阐述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尽管“通道”、“乐谱”与“文本”在语言表述上不大相同,但其追求课程隐喻教育学意义的价值表达却是一脉相承、殊途同归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