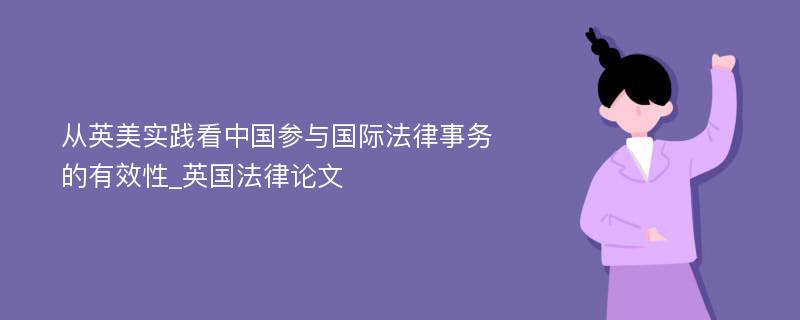
从英美实践来看我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美论文,性问题论文,法律事务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效参与”的含义及其意义 近年来,在对待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无论是在国际组织的问题上,还是在国际争端的解决方面,相较于传统的“韬光养晦”政策,我国的立场与态度,已有了一些细微然而却意义深远的改变。在国际组织方面,我国不仅积极地参与越来越多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活动,还积极组建了上海合作组织;在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我国已经习惯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利用该机制来解决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有关争端。 但是,必须同时注意到,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回事,是否有效地参与则是另一回事。一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地参与(effective participation)。 所谓“有效参与”,是指一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参与来有效地影响规则的制定、形成与发展,从而能够确保自身利益在参与过程中得到有效维护。有效参与有两个不同层次:一般层次能够做到有效地影响规则的制定与形成,能够在参与中有效地保护本国利益;高层次的有效参与则是指国家在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能够做到把本国相关规则国际化,即以本国规则为蓝图和底本来制定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而无论是何种层次的有效参与,均有一个基本前提:参与该国际事务谈判的代表应对谈判事务所涉及到的规则非常熟悉和精通。不精通相应规则,任何时候的参与都不可能“有效”。关于此点,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王江雨副教授回忆其1999年参与一次国际公约谈判的经历可以非常形象地说明:① 1999年春天,正在中国银行法律部工作的我忽然接到法律部老总的命令,要求迅速做好准备加入外经贸部牵头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参加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关于应收账款融资转让公约谈判的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联大一个很大的会议室召开的。我初到会场,坐在放着“China”牌子的桌子后面,亲身经历以前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场面,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膨胀的气球,充满着自豪、兴奋、忐忑不安,还有一丝受宠若惊。 但气球很快被捅破了。第一天开完会,我的心情就由兴奋转入气馁。会议讨论的内容大而化之地知道一些,但具体细节完全不懂。当少数几个代表情绪激动地讨论每一条该怎么起草时,大多数代表包括我,都陷入不知所措茫然不语的境界。原来国际条约谈判是这么难啊,是这么的抠字眼。严重缺乏此方面专业知识的我,只好缄口不言并倍感痛苦。 我很快发现,会议的发言基本上是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代表垄断了。这少数几个国家的代表争吵激烈,但争的内容,以及为什么争吵,我基本上不懂。其中,美国占据了当然的主导地位,两位代表让人印象深刻。一位是国务院的官员,人显得极为专业。有一次,他要求大会秘书处架起PowerPoint设备,在开会时间为所有代表讲述贸易应收账款转让的基本原理,秘书处二话不说,就让他把国际公约的谈判场所变成了个人的讲堂。另一位是Peter Winship教授,人显得极为儒雅有范。有一次会议休息期间,他跑来和我攀谈,问我学术专长是什么,对这个公约草案有什么看法等。一时间我面红耳赤。我时年二十六岁,有什么学术专长?对这个我基本不懂的公约又能有什么看法?但我是谁?我来干什么?我难道不是正式受到指派的参加公约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我难道不该懂这些问题?面对该教授,一向伶牙俐齿的我顿时被令人窒息的羞愧、自责和负罪感所包围。Winship教授见我支支吾吾,就闲扯了几句,说他感到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他参加这个公约起草好几年了,会议开了若干,但发现每一次会议来自中国的代表都是不同的人,这样不利中国的有效参与等。 通过上述实例可以看出,在有效参与该公约谈判方面,同英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参与非但“无效”,在很多方面更暴露了我国参与的“技术性”缺陷。我国参与为什么“无效”?导致无效的原因有哪些?可以从哪些方面予以改进?本文的目的,即是通过对我国和英美国家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实践的比较研究来为上述这些问题初步提供“答案”。而在研究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有效性问题时,笔者将主要从中国参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活动和中国参与国际法院的实践为例进行讨论。②在中国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方面,将主要以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例来进行讨论。笔者将首先简述英美国家在上述两个领域的相应实践,然后就我国的实践进行概述,并结合英美的实践来对我国参与实践的得失进行检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二、英美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的实践 《联合国宪章》第13(1)条规定,“大会应发动研究,并做成建议:(子)以促进政治上之国际合作,并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为履行此职责,大会于1947年决议设立国际法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将其作为联合国负责国际法发展与编纂的主要机构。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与流程是:选定专题;为每一专题指定一特别报告员;请各国政府提供有关法律、司法判决等有关文件;请秘书处提供调查报告等;特别报告员提出报告;委员会通过以报告为依据的附有评论的一读草案;一读草案分发各国并提交联合国大会;委员会在研究对草案的评论和大会第六委员会在辩论中所作评论后再行提出报告,对一读草案作适当修改;一旦认为比较成熟,委员会即会在报告基础上通过二读案文并提交联合国大会,由大会第六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议,并在审议基础上作出关于进一步行动的建议:(a)不采取行动;(b)通过决议表示注意,或通过该报告;(c)向会员国推荐以缔结公约。③委员会工作特点在于:把各国政府意志、成员国代表要求和国际法专家的研究结合起来。④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在国际法委员会编纂过程中,各国都可以参与委员会的活动,将本国的立场、建议与实践提供给委员会以便其编纂借鉴和考虑。委员会对各国所提交的意见,通常会重视并积极考虑,将其尽可能地吸收到自己所编纂的草案之中。毕竟,离开各国实践而只是单纯学理上的草案,不会引起各国兴趣,最终也不可能获得各国支持。 下面将以《外交保护条款草案》为例,对英美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的实践进行描述。 国际法委员会于1995年决定将外交保护列入其工作议程,随后,在第48届会议上将其确定为适宜于“编纂和逐步发展”的三个议题之一;⑤1995年12月11日,大会在第45次会议上,请求各国政府就此议题向委员会递交建议。根据大会这一决议,1996年8月5日,美国向委员会递交了书面评论意见。在评论中,美国就外交保护的性质、用尽当地救济规则、法人的外交保护、持续国籍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或提出了希望委员会重点关注的法律问题。⑥ 委员会在第56届会议上完成了《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一读,随后,根据章程规定,经由秘书长将草案转发给各国政府以进行评议。截止到2006年1月26日,共收到包括英、美等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书面评论。⑦ 英国在其评论中对草案的全部条款逐一进行了评论。英国不仅评论了草案诸规定的优点和不足,也逐一介绍或陈述了本国的实践或立场,以及支撑本国立场的相应国际案例。⑧特别是针对草案第11条所涉及到的多国籍股东的多重求偿问题,英国主张“协调求偿”的观点,⑨被吸收在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案文中,尤其是案文第11条“对股东的外交保护”的相关评注中。⑩ 美国分别对草案的第5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4条第1款,第16条(a)项、(c)项,第19条等条款发表了评论。(11)例如,对于草案第5条有关“持续国籍”的规定,美国认为,该条第1款应增加一个“仅”字,从而能够突出第2款和第3款规定的外交保护权仅限于符合持续国籍条件的人提出的要求。(12)对于第10条关于“公司的持续国籍”的规定,尤其是第2款“国家继续有权为在发生损害之时为其国民,但由于损害而按照该国法律终止存在的公司行使外交保护”的规定,美国认为,此款所属原则并不反映习惯国际法,其政策依据并不充分。(13)美国在陈述自身意见过程中同样注重援引相关案例。 对于美国的这些评论,特别报告员在其所提交的第7次报告中给予了不同的反馈。在评论每一条款的时候,对于美国所提出的这些意见,无论是建议部分采纳、完全采纳还是拒绝,特别报告员都会提到并阐述具体原因。例如,对于第5条所提意见,特别报告员认为,此意见值得考虑并建议接受此项建议。(14)对于美国针对第10条第2款的批评,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意见并未考虑国际法庭的法官(特别是巴塞罗那电力、电车和电灯公司案中美国籍法官杰赛普)及学者等对此问题的关切。(15)美国的这些意见及特别报告员的不同建议,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委员会最终通过的二读案文之中。(16) 对于二读案文的处理,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主张,将条款草案制定成公约的基础尚不成熟,因此,不主张现阶段将其制定为国际公约。(17)目前,该案文依然维持着草案的形态。 通过英美的上述参与可以看出,尽管参与方式和时机有所不同,但通过参与,它们都把本国的利益和意志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国际法委员会最终通过的案文之中。 三、英美参与国际法院活动的实践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关之一,在通过法律方法解决争端并进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包括诉讼管辖和咨询管辖。 英美参与国际法院活动的实践,在诉讼事项和咨询事项领域,表现并不完全相同,因而有必要分开描述。 在诉讼事项领域,英国是到目前为止,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惟一接受了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国家。美国在国际法院成立之时,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愿意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但在经过1984年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判决之后,美国在对法院的判决表示失望之余,撤回了自己所发表的声明,不再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从参与诉讼角度看,都实质性地参与了在法院的多起诉讼。在这些诉讼中,它们或作为原告国出现,或作为被告国出现,或与其他国家达成将争端交付国际法院裁决的协议,共同将案件提交法院裁决。 国际法院受理的第一起诉讼案件是1947年的“科孚海峡案”,是英国针对阿尔巴尼亚提起的。1949年,英国再次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不过,这次针对的是挪威,争执对象是渔业管辖权问题,这也是国际法院所受理的第二起诉讼。从1947年到2014年1月,英国作为当事国在国际法院的诉讼案件一共是13起,其中,作为原告国提起的诉讼共7起,作为被告国应诉的案件共5起,以特别协定方式由两国共同启动在法院的诉讼程序的案件1起。最近的一起案件,是塞尔维亚和黑山诉英国“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 从1950年法国诉美国“在摩洛哥的美国国民权益案”起,美国先后以原告国或被告国身份参与国际法院诉讼案件24起,其中,最近的5起案件都与美国在国内实施《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有关。在这24起案件中,由美国作为原告国提起的案件共9起,由美国作为被告国的案件共15起。另外,美国还曾与加拿大一起,将两国间围绕缅因湾海域划界的争端提交给法院裁决。在美国参与法院的诉讼案件中,不乏一些经典案件,如美国诉伊朗“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尼加拉瓜诉美国“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等。 国际法院还拥有咨询管辖权。自法院成立至今,法院共受理了26起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除1起拒绝发表咨询意见的请求案件外,(18)对于其他25项请求,法院都发表了咨询意见。在这26起案件中,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积极地参与了相应咨询程序。 《国际法院规约》(下称规约)第66(1)条规定,“书记官长应立将咨询意见之申请,通知凡有权在法院出庭之国家”。第2款规定,“书记官长并应以特别且直接之方法通知法院所认为对于咨询问题能供给情报之有权在法院出庭之任何国家,或能供给情报之国际团体,声明法院于法院所定之期限内准备接受关于该问题之书面陈述,或准备于本案公开审讯时听取口头陈述”。在收到法院通知后,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会根据问题的性质与重要性等因素确定是否参与。如果参与,可以在两个不同阶段参与。第一阶段,在法院所确定的时间内,向法院递交书面陈述意见(written statement)或针对他国意见的书面评论意见(written comment);第二阶段,如果认为必要,在口头审理阶段派员参加口头审理程序。国家既可以决定只向法院递交书面陈述意见或只参与口头听审程序,也可以决定同时参与上述两个程序。 在国际法院审理的26起咨询案件中,英国共参与了13起,(19)其中,在12起案件中发表了书面陈述意见,(20)在11起案件中参与了法院的口头审理程序,(21)在9起案件中同时参与了书面和口头审理程序。(22)特别地,在两个与核武器使用有关的咨询意见案中,针对他国递交的书面陈述意见,英国向法院递交了书面评论意见。 在26起咨询意见案件中,美国参与了23起。(23)美国除了在这23起案件中发表了书面陈述意见外,还在其中的10起案件中参与了口头审理程序。(24)与英国一样,在两个与核武器使用有关的咨询意见案中,美国针对他国所递交的书面陈述意见,向法院递交了书面评论意见。在1998年“关于执行人权使命的特别报告员豁免于某些法律诉讼的问题咨询意见案”和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中,美国同样递交了书面评论意见。 有必要特别提及英美在两个与核武器使用有关的咨询意见案和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案中的表现。为了影响到国际法院即将发表的意见,它们在法院展开了有效博弈。 在“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中,美国在其所递交的书面陈述意见中,一方面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问题超出了其职权范围,法院应拒绝发表咨询意见,另一方面又附带强调,并不存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普遍性国际法律规则。(25)英国在其书面陈述意见中,同样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问题超出了其职权范围,法院不应发表咨询意见。同样,英国强调,无论是条约国际法还是习惯国际法,都不禁止核武器的使用。(26)这些意见明显地对法院产生了影响。法院经审理后指出,世界卫生组织所提问题超出了其职权范围,因而拒绝发表咨询意见。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中,美国在书面陈述意见中再次强调,不存在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普遍国际法,武装冲突法、国际环境法、国际人权法也均不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英国也在其书面陈述意见中强调了类似观点。(27)国际法院最终所发表的咨询意见,明显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影响。国际法院一方面指出,在一般情形下,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违背了人道法及武装冲突法,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在自卫的极端情形下,无法得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的结论,这样,就为核武器的使用留下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例外。 在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中,同上述两案一样,英美既递交了本国的书面陈述意见,也递交了对其他国家意见的书面评论意见,同时还派人参加了法院的口头审理程序。无论是英国长达138页的书面陈述意见,还是美国长达152页的书面陈述意见,(28)二者均认为,科索沃的行为并不违反国际法。这与国际法院最终发表的咨询意见高度一致。 四、中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实践 (一)中国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的实践 在国际法委员会制定《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的过程中,无论是启动阶段、一读,还是二读期间,我国既没有向委员会递交有关我国相关实践的材料,也没有递交对草案中任何条款的评论意见。仅在二读案文已经通过,并被送到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审议的时候,我国出席该委员会会议的代表才对草案进行了评论。我国代表段杰龙除发表了总体性评论观点外,还特别对草案第1、4、7、8、12、13、15、19条进行了具体评论,并声称“保留今后对条款草案进一步作出评论的权利”。(29) 将我国的上述参与实践与英美的相关实践相比较就会发现,我国参与实践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参与时机看,我国对于参与时机的把握不“敏感”,显得过迟。从国际法委员会工作流程可以看出,在其对国际法任一议题进行编纂的过程中,国家参与的最好时间点应该是启动该议题编纂阶段和对一读案文的评议阶段。因为在此阶段,国家既容易寻找到自身的相关利益点,也容易找到能够支撑和证明自身观点的国际案例和国家案例,从而能在第一时间影响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并在此基础上把本国利益渗透进该议题之中。而在后面阶段的参与,尤其是二读案文通过之后的参与,其效果则相当有限甚至没有效果,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从国际法委员会的角度看,其编纂活动已经结束,国家不可能在此层面再影响到该委员会;另一方面,即使国家想在其他场合——如以草案为基础进一步制定国际公约的场合——试图说服其他国家接受自身论点,进而达到修改甚至抛弃国际法委员会此前已经制定成型的某一案文,就必须首先找到足够多的案例和实践来证明自身立场的正确。由于相关案例和实践在该案文的最初形成阶段基本上已经为其他国家所穷尽,国家在此背景下要寻找到足够的案例来证明自身论点,从操作层面来看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国际法委员会在编纂国际法的过程中,英美的参与实践主要集中在启动阶段和一读审议阶段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我国能在国际法委员会一读和二读期间及时递交相关实践与立场,参与效果会更好。 第二,评论比较空泛,不具建设性。仔细研究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流程和英美参与实践就会发现:一方面,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任一议题的编纂,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国际案例和国家案例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一项编纂成果完全建立在纯粹的法理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国家参与效果的好坏,也与国家所提建议事由是否有充分依据,是否有相应案例支撑密切相关。一国要让自己的立场和论点为国际法委员会所接受,要想成功地把本国利益渗透进相应的国际规则之中,其所提建议就一定要具有建设性,要建立在相应的国际实践和本国实践的基础之上。完全脱离案例等实践的单纯建议或纯理论性的建议,被认为不具有建设性,既很难为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也达不到影响相应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和形成的目的。我国代表在对《外交保护条款草案》发表意见的时候,尽管提出了比较多的意见,并且,这些意见大体上也体现了中国的立场与利益,但是,由于意见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援引任何案例,都是基于“我们认为”、“我们理解”这一“想当然”的逻辑,(30)缺乏国际案例作和国家案例为支撑,其说服力就非常弱,很难说服其他国家同意和接受中国观点。 第三,对在外交保护领域的本国和国际实践,研究不够。这也是导致我国最终所提建议不具有建设性的原因之一。其实,就外交保护这个话题而言,我国至少在如下两方面是有独特利益的。第一种情形与当前的民间对日诉讼有关。在八年的对日抗战中,对于那些处于日本占领区内的国人而言,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力无法在该区域有效行使,因此,对于在该区域内遭受伤害的平民而言,如慰安妇,尽管伤害是在中国领土内发生,但由于其权力行使者为日本,因此,应该承认在此特殊情势下,如果遭受伤害的国人无法得到日本的有效救济,中国应该同样享有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第二种情形是有关双重国籍的外交保护或经常居住国针对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的问题。中国移居海外的国民越来越多,其中部分取得了另一国国籍,部分在他国永久居住。在此情形下,另一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国针对中国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形就会出现。在此情形下,我国该持何种立场,同样需要斟酌与研究。 (二)中国参与国际法院活动的实践 我国参与国际法院活动的实践可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以前和1971年以后。 1971年以前,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是“非法占据席位”的“中华民国”。从1946年到1971年,无论是诉讼案件还是咨询意见案,“中华民国”的参与均很积极。(1)诉讼案件,“中国民国”在国际法院成立之初就发表了接受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此外,在“中华民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部分双边条约中,均载入了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31)(2)咨询意见案,从1946年到1971年,“中华民国”共参与了7起咨询意见程序,递交了对相关问题的书面陈述意见。(32) 在联合国大会于1971年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决定“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并“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后,(33)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国际法院的实践,也可以从诉讼案件和咨询意见程序两个角度观察。(1)诉讼案件,截至目前,我国尚没有发表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声明;对于“中华民国”1946年所发表的有关声明,我国明确地表示不予承认。(34)我国也从来没有尝试利用国际法院来解决与他国间的争端。对于我国加入的多边条约中载有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条款,除个别技术性条约外,(35)我国一般都提出了保留。(2)咨询案件,自1971年以来,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案外(下文将单独分析),我国没有参与国际法院的任何咨询意见程序。即使是对于涉及到核武器使用这样敏感和重大的问题,在其他有核国家和中间状态国家都参与的情形下,甚至在从来不参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的朝鲜都参与的情形下,(36)我国依然没有参与,尽管我国在有关核武器使用的主张具有伦理优势。(37)同样,无论是在大会还是安理会,我国也没有试图推动大会或安理会积极利用法院的咨询管辖权。(38) 科索沃咨询意见案是我国自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第一次参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我国不仅向国际法院递交了本国的书面陈述意见,(39)还派人出庭参与了口头听审程序。仅就这些表现而言,我国的此次参与是积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此次参与就是有效的呢?答案恐怕并非如此。 将我国此次参与实践与英美相关实践进行认真比较就会发现存在如下几方面的问题。 (1)从书面陈述意见的篇幅来看,我国8页纸的篇幅与英国138页、美国152页的篇幅完全不“对等”。 (2)从书面陈述意见的内容来看,我国的意见通篇都只是在强调原则的重要性,对于科索沃问题则没有具体的分析与评论。无论我国在自身意见中强调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的重要性也好,还是在强调领土完整原则的重要性也好,抑或是在强调民族自决原则也好,其共同点都在于强调原则的重要性。但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看,由于任何原则都有适用的例外,(40)在没有对原则的适用进行精细讨论的基础上强调其重要性,实际上对于解决具体问题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反观英美陈述意见,其对于科索沃问题的来龙去脉,国际法院是否应该发表咨询意见,本问题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每一个法律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分析等,都作了详细分析与讨论。无论是就其说理性而言还是就其分析的明晰性、详尽性而言,都要远远超过中国所递交的意见。这些意见都明显地影响了国际法院最终的咨询意见。 (3)从参与技术角度来看,尽管中国和美英一样,都递交了书面陈述意见并发表了口头意见,但中国却并没有像英美一样,针对其他国家的书面陈述意见递交本国的书面评论意见。(41)英美递交评论意见的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充分博弈来最大程度地影响国际法院,推动和说服国际法院在咨询意见中吸收本国意见。 (4)中国的参与意见完全“无视”参与咨询程序的基本“套路”。从国家参与咨询意见的实践来看(包括国际法院自身发表咨询意见的实践),书面评论意见一般都会首先分析和“重新”界定所提请发表咨询意见的问题,然后,会进一步分析国际法院对该咨询意见是否拥有管辖权、该咨询意见是否应予受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之前需处理的“先决性”问题,会直接影响国际法院考虑决定还是拒绝发表咨询意见。遗憾的是,中国对于其他国家既往参与咨询程序的“成熟”实践“视而不见”,一开始就进入到了对实体问题的分析。这种不遵循“套路”的做法对于国家的有效参与实际上并无益处。 (5)从实质内容看,中国的部分意见还包含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书面陈述意见中,中国最大程度地强调了领土完整原则的重要性。但正如国际法院所指出的,《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中所载“领土完整原则”是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42)英国在其书面陈述意见、(43)美国在其书面评论意见(44)中同样强调了此点。在此背景下,我国意见强调此点实际上隐含了一个重要前提:科索沃是一个国家!而这,与我国意见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相背离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参与国际法院活动方面,无论是参与诉讼案件还是咨询意见程序,同英美国家相比,我国在1971年之后的参与效果同样是不理想的,几乎没有参与。即使个别案件参与了,但参与效果也不好。甚至从某种程度来看,此种参与更“暴露”了我国参与国际法律事务的缺陷与经验的不足。 五、总结和建议 通过前述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在参与国际法律事务方面,无论是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也好,还是参与国际法院活动也好,与英美相比,我国的参与均有相应不足,参与效果不理想,离“有效参与”的标准差距还很远。 有效参与国际法律事务是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将本国利益融入相关国际法律规则中的一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的活动也好,还是参与国际法院的活动也好,目的与意义均在于此。这也是英美选择积极参与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院活动的主要原因。 从国际法委员会的角度来看,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无论是最后被制定成国际公约,还是仅仅维持草案形态,都会对国际社会成员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就维持草案形态的公约案文而言,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其不妨碍国家与国际法庭在实践中援引有关条款,(45)通过援引来积累更多实践,推进该规则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特定条款而言,即使不同国家分歧甚大,也不影响相关国家继续推进自身实践,通过实践来积累案例,并以此来影响该领域国际法规则的发展。(46) 从国际法院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就诉讼案件还是就咨询意见而言,参与意义同样明显。 从诉讼案件角度看,尽管在理论上,国际法院的裁决仅约束当事国,(47)但由于很多案件既涉及到重要的国际法实体问题,也涉及到精致的程序问题。国际法院就这些问题所作裁决,是当代国际法重要内容的一部分,对所有国家都有重要意义。而从参与角度看,参与一方面可以锻炼自身运用和解释国际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给国家参与其他国际法庭的诉讼提供经验。中国现阶段已经在频繁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而从国际法院角度来看,WTO争端中碰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从国际法院相关案例中找到可利用或者借鉴的“营养”。 从咨询意见角度看,国际法院迄今所发表的很多咨询意见属于对某一国际法问题的权威表达或澄清,其中部分意见甚至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有关国际组织国际法主体地位的意见,有关联合国经费的意见等,这些意见都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实践中所尊重和遵守。一旦国家不参与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程序,实际上会丧失一个很好的将本国利益融入该意见中的机会,而在国际法院发表该咨询意见后,又不得不正视此意见给自身所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不利后果。 通过对我国参与实践的上述研究,笔者认为,英美的参与实践可给我国如下启示。 首先,一般而言,对于所有的国际法律事务,我国都应该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而不是仅局限于参与国际法委员会和国际法院的活动。只有通过积极的参与,我国才有机会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也才有机会把自身利益融入相应国际规则之中。长期以来,我国一贯主张和呼吁改变旧的国际法律秩序,但改变旧的国际规则秩序单靠主张和呼吁是难以成功的,只有通过勤勉的参加才会有希望与可能。 其次,为保证参与的效果,在参与任何国际法律规则制定的时候,还应确保本国选派的代表对相应国际法律规则有独到和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应确保参与代表的连续性。我国参与国际法委员会活动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一定程度上与我国选派参与代表的机制有关。(48)在很多时候,我国参与的代表都是行政系统派出的外交代表,而非相关专家。由于代表来自于行政系统,受限于时间及工作性质等,很多时候他们并未对相应规则作过精深研究;即使在某些谈判场合有相关专家参与,由于专家参与权限受到诸多限制,也会导致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代表的连续性问题同样重要。对于同一国际法律文件的先后多轮谈判,我国应最大可能地确保参与代表的连续性,而不是先后选派不同代表参与。反观英美,在多数情况下,其派遣参与国际谈判和规则制定的代表均为本国研究相应问题的著名学者,如参加1998年罗马规约谈判的美国代表即为国际刑法领域的顶尖权威巴西奥尼教授,而且,参与同一问题谈判的代表一般也很少轮换。专家领衔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谈判,其参与效果当然要好于一般行政官员参与的效果。 再次,应注意对参与时机和方式的把握。以国际法委员会的编纂活动为例,在国际法委员会开始启动对某一议题编纂的时候,我国就应积极参与,在规定时间内递交本国有关实践并提出自己认为应关切的问题或建议。与此同时,还应抓紧时间研究相关领域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实践,为后续参与做好充分准备。在一读案文通过后,更应抓住机会,结合本国利益提出建设性的评论与意见。在二读案文通过后,应结合本国利益向该委员会提交本国有关该案文处理的建议。 最后,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为了中国今后参与国际法律实践更有效,学者应认识到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并重视对正在发展中的国际法律问题的研究。从前述研究可以看出,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形成的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所提意见的建设性,相关建议是否有国际案例和国家案例的支撑。一国如果不重视对国际法的实证研究,不充分掌握他国实践和国际实践,在参与国际法律规则制定和形成的过程中,无论是外交代表还是学者,将很难有效地影响他国,说服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立场与建议。所以,做好国际法的实证研究是本国有效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学者实证研究做好了,还可以为外交代表参与提供智力支持。为此,学者应加强对本国实践、其他各国实践和国际实践的研究。此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国际法问题,尤其是国际法委员会正致力于编纂的议题,国内学者同样应积极关注。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国际法议题,正是本国要参与或即将参与的形成中的重要国际法律规则。 注释: ①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ac2db10100jo5r.html,2014年2月18日最后访问。 ②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目前已经比较熟练,因此,本文不以其为样本进行研究。 ③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④梁西主编:《国际法》(修订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⑤《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95年年鉴》第2卷,第501段;《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年鉴》第2卷,第248段和附件2,增编1。 ⑥参见联合国文件:A/51/358/Add.1。 ⑦这些国家包括:奥地利、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荷兰、挪威(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巴拿马、卡塔尔、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参见联合国文件:A/CN.4/561,第8页。随后,又有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发表了评论。参见联合国文件:A/CN.4/561/Add.1,A/CN.4/561/Add.2。 ⑧关于英国的评论,参见联合国文件:A/CN.4/561/Add.1。 ⑨同注⑧引文,第8页。 ⑩参见联合国文件:A/61/10(英文本),第59-60页。 (11)美国所发表的具体评论,参见联合国文件:A/CN.4/561(中文),第8-43页。 (12)同注(11)引文,第16页。 (13)同注(11)引文,第26页。 (14)关于特别报告员对美国等国所提意见与建议的立场与态度,参见联合国文件:A/CN.4/567(中文)。 (15)同注(14)引文,第23-24页。 (16)关于此点,可参见联合国文件:A/61/10(英文本),A/CN.4/567。 (17)参见联合国文件:A/62/118(中文),第7-9页。 (18)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请求国际法院对“国家在战争或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是否违反了其根据国际法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章程在内所承担的义务”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一请求不属于其职权范围,因而拒绝发表咨询意见。 (19)这13起案件是:1949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问题咨询意见案;1948年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咨询意见案;1950年灭种罪公约的保留问题咨询意见案;1953年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赔偿的效力问题咨询意见案;1955年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问题咨询意见案;1955年西南非委员会是否接受请愿者听证申请咨询意见案;1959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组织问题咨询意见案;1961年联合国某些开支问题咨询意见案;1993年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1995年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1998年关于执行人权使命的特别报告员豁免于某些法律诉讼的异议问题咨询意见案;2003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筑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案。 (20)就上述13起案件而言,除西南非委员会是否接受请愿者听证咨询意见案外,英国都递交了书面评论意见。 (21)在上述13起案件中,除1955年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判决问题咨询意见案和2003年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修筑隔离墙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外,英国都参与了口头审理程序。 (22)这9起案件是:1949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问题咨询意见案;1948年为联合国服务而受损害的赔偿问题咨询意见案;1950年灭种罪公约的保留问题咨询意见案;1953年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赔偿的效力问题咨询意见案;1959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组织问题咨询意见案;1961年联合国某些开支问题咨询意见案;1993年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1995年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案。 (23)美国没有参与的三个案件是:1972年请求复核联合国行政法庭第158号判决问题咨询意见案、1974年西撒哈拉问题咨询意见案和2010年复核世界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2867号判决案。 (24)这10起案件是:1949年对保、匈、罗和约的解释问题咨询意见案;1953年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赔偿的效力问题咨询意见案;1959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组织问题咨询意见案;1970年南非不顾安理会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案;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埃及间关于1951年3月25日协定的解释问题咨询意见案;1989年联合国总部协定适用的解释问题咨询意见案;1993年国家在武装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1995年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问题咨询意见案;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咨询意见案。 (25)See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A Concerning the Case of 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s,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93/8770.pdf.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26)See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ing the Case of Legality of the Use by a State of Nuclear Weapons in Armed Conflicts,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93/8742.pdf.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27)See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A,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Concerning the Case of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95/8700.pdf.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28)See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ritten State of the United Kingdon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index.php? p1=3&p2=4&k=21&case=141&code=kos&p3=1.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29)中国代表段洁龙在第61届联大六委关于“国际法委员会第58届会议工作报告”议题中“外交保护”和“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两项专题的发言(2006-10-13),来源:http://www.fmprc.gov.cn/ce/ceun/chn/zgylhg/flyty/ldlwjh/t348875.htm.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30)在我国意见中,“我们认为”出现了五次,“我们理解”出现了两次。“我们建议”出现了一次。但无论是“认为”、“理解”还是“建议”,均没有提供可以作为证据支撑的案例。 (31)部分这类条约如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28条),1947年《中菲(律宾)友好条约》(第2条),1948年《中美经济合作协定》(第10条)等。 (32)这7起案件分别是:1947年联合国接纳会员国的条件咨询意见案;1948年为联合国服务人员遭受伤害的赔偿咨询意见案;1953年联合国行政法庭判决赔偿的效力咨询意见案;1955年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就尼斯科所作判决的咨询意见案;1955年西南非委员会就请愿举行听证的可受理性问题咨询意见案;1959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海上安全委员会章程咨询意见案;另外,在1954年接受西南非请愿书和报告的程序问题咨询意见案中,“中华民国”虽然没有递交书面陈述意见,但特别提到了本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大表决通过请求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决议时陈述的立场。国际法院在其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中特别提到了此点。因此,本案也计算在“中华民国”参与的案例中。 (33)参见联合国文件:A/RES/2758(XXVI)。 (34)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页。 (35)例如,对于《保护文学与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33条(有关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我国就没有提出保留。但有意思的是,对于同为知识产权领域的另一公约,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28条第1款(有关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我国却提出了保留。 (36)这是朝鲜参与国际法院活动仅有的两个案例。 (37)例如,我国一直主张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等。 (38)国际法院前院长、中国籍现任法官史久镛先生在院长任内曾呼吁应多推动利用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参见史久镛:“国际法院的咨询职能——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委员会的演讲”,载《中国国际法年刊》(2004年卷),第11-12页。 (39)中国的书面陈述意见,参见: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611.pdf.2014年2月23日最后访问。 (40)前南斯拉夫刑庭和卢旺达刑庭上诉法官刘大群先生曾经在多个场合都强调,国际法原则均有例外。就原则的研究而言,与其研究其重要性,不如研究其适用的例外。只有通过对其例外的研究,对于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我们才能获得充分和准确的认识。 (41)英美的书面评论意见分别参见: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702.pdf 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704.pdf.2014年2月22日最后访问。 (42)"Thus,the scope of 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 integrity is confined to the sphere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See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Respect of Kosovo,Advisory Opinion,I.C.J.Reports 2010,p.437,para.80. (43)See Written State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n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pp.86-87,paras.5.8-5.11,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638.pdf.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44)See Written Com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p.15-18,available at: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41/15704.pdf.2014年2月21日最后访问。 (45)例如,就《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而言,迄今已经有多个国家、国际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多次、反复援引了该条款草案的多个条款。有关这些援引的具体情形,参见联合国秘书长报告: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Compilation of Decisions of International Courts,Tribunals and Other Bodies,A/62/62. (46)以《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为例。对于该条有关“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不法行为的责任”,由于其给一国干涉另一国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包括中国等在内国家是持排斥立场的。但对于那些热衷和支持干涉的国家而言,中国等国家的排斥却并不妨碍其在实践中继续推进相关干涉实践,并通过此类实践反过来为该款提供存在必要性的证据与基础。在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或引渡或起诉义务问题案”中,比利时即第一次尝试以“受害国以外的国家”身份来援引塞内加尔的国家责任。关于此点的分析,参见宋杰:“国际法院参与下的国际司法干涉——以‘比利时诉塞内加尔案’为切入点的研究”,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6期,第96-97页。 (47)《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规定:“法院的裁决除对于本案及当事国外,无约束力。” (48)仔细研究我国自1971年以来选派参与国际谈判和国际会议代表的机制就会发现,在不同阶段,我国选派代表时关注重点也不一样。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之前。重点强调的是所选派代表的政治素质和外语水平;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近90年代末期,重点强调的是“利益均沾”,出国参与国际事务和谈判被视为一种“福利”,参与人员“配额”会“公平”地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标签:英国法律论文; 国际法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法律论文; 口头协议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特别程序论文; 外交活动论文; 案件分析论文; 外交争端论文; 美国法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