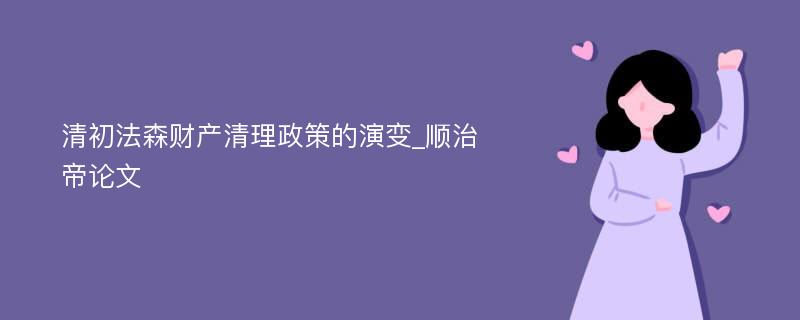
清初清理藩勋逆产的政策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逆产论文,清初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5)-03-047-13 康熙“更名田”诏是清理明代藩勋产业的关键法令,基本奠定了清代更名田的赋役格局,因此学界对其研究尤为重视。然而,顺治朝相关政策乃“更名田”诏出台的基础,在已有研究中,前者多被视为后者颁行的背景,着重论述该时期的土地占有关系、清理方式以及粮租负担渐趋繁重等内容,而对清理政策着墨较少。①究其缘由,一者清代政书中相关内容比较罕见,二者记有典章的私家著述亦多阙如,②以致人们对其知之甚少,甚至形成清理工作是杂乱无章、各行其是之印象。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细致爬梳、分析档案等史料中的零碎记载,重构清初清理藩勋逆产的政策演变,以期更深入理解“更名田”制度。 所谓藩勋逆产,是指明代宗藩、勋戚及相关反抗清政权者的产业,其具体形式庞杂多样,主要为田宅产业。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藩勋与田产,本文所论则不限于此,还涵盖逆产与房产、店铺等。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用“产业”一词,并非经济学概念,而指田地、房屋、店铺等财产;因文献记载的零星分散,对逆产的考述并不系统,仅略及而已。 一、处置政策的演变 一般认为,清廷清理藩勋逆产之目的是为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困境。然而,追溯清理之肇端,这一认识恐非十分全面。纵观顺治一朝,处置明代藩勋产业的政策在不断演变,其目的亦随之发生重要变化。③ (一)清理之肇端 清军入关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明朝宗室、贵戚遭到沉重打击。大顺政权施行“追赃助饷”的政策,没收了明朝宗室、国戚、勋贵、太监等全部家产。④质言之,兵燹之后,大部分原属藩勋的产业已不由其实际控制,占有关系已经混乱。入关伊始的清政权,为减少政治和军事上的阻力,更快获取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大力推行“怀柔”政策,名义上认可明代藩勋对原属产业的所有权。⑤换言之,基于政治要求,清廷起初无意清理藩勋之产,其“名义上认可”仅为保持现状而已。但是,为有效管理土地和增加赋税收入,清理这些产业势在必行。 清理之肇端则为“圈地令”的颁行。大量满洲官兵入关,其安置问题成为急务。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顺治帝谕令户部: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⑥据此,为使满洲官兵有安身之处,顺治帝命令户部着手清理京畿及周边土地,圈占为旗地。谕令中只明言田地,而实际圈占还包括房产等。其中含有明代宗藩勋戚产业,执行对象有二,一是无主田地,二是“量口给与”后的有主“其余田地”,圈占前者无可厚非,而圈占后者明显有悖于“怀柔”政策。 次年正月,户部奏请圈拨土地之事,得旨: 凡圈丈地方,须令满汉分处。至于故明赏赉勋戚庄地及民间无主荒田,悉令输官,酌行分拨。⑦据此,明代赏赉勋戚的庄地“悉令输官”,连“量口给与”亦不存。推测其由,勋戚与宗藩的地位实有不同,其所得赏赐庄地乃明廷的恩泽,入清以后自然不再具有合法性了。 合而言之,宗藩土地“量口给与”后余田入官,勋戚赏赉土地则完全没收,尔后分配给满洲官兵。这说明,一年之内,处置政策出现了重要变化,即从名义上认可明代藩勋对原属产业的所有权,转为将其没收入官、圈占为旗地,由此开清理之肇端。 从实践看,圈地活动基本遵循这两道谕旨。以“基本”言之,是指对勋戚产业的政策又有所调整,不再全数没收。例如,顺治二年九月,有谕旨二道: 谕户部:河间、滦州、遵化等府州县……其故明公、侯、伯、驸马、皇亲、太监地,酌照家口给发外,余给八旗。⑧ 谕户、兵二部:近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如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着满洲统兵驻扎,务期剿抚得宜,以安百姓。以上八处驻扎满兵,著给以无主房地。其故明公、侯、伯、驸马、太监地,察明量给原主外,余给满洲兵丁。⑨由是悉知,清廷给明代宗藩、勋戚均留有一定量的土地,大致按“量口给与”原则分配。不过,旗地圈占已经突破京畿地区,延展至山东、南直隶、山西等省,规模日渐宏大。此外,顺治二年七月,制定明代宗室赡养岁给之制,“亲王银五百两,郡王四百两,镇国将军三百两,辅国将军二百两,奉国将军一百两,中尉以下无论有无名封及各王家下人丁,每名各给地三十亩。”⑩赏赐以没收原属产业为前提,再依“量口给与”原则分配赡银及赡田。该项定制说明这并非临时或针对个案的特例,而是一从制度层面强化没收宗藩产业的政策。从制度规定上讲,藩勋之产已被没收,所谓“量口给与”的赡田,只不过是清廷的恩泽,已不再具有显著的制度意义。 圈地令旨在安置入关满洲贵族,出发点本不在专项清理藩勋之产,却因与其关涉甚多,由是形成了清理之肇端。众所周知,旗地圈占规模虽大,但局限于一定地域内,(11)因此它并不能指导所有藩勋产业的处置。换言之,圈地令的适用范围有限,而随着统治区域日趋扩大,所涉及的藩勋之产水涨船高,专项处置政策便应运而生。 (二)土地赋税民田化 自圈地令颁行为始,所谓“怀柔”政策便化为乌有,没收入官是绝大部分藩勋之产的定数。除划拨为旗地及由其导致的拨补民田外,清廷酝酿并出台了新的处置方案。顺治二年闰六月,宣大总督李鉴汇报清查明朝代藩宗禄的情况,得旨: 明朝宗室故绝者,产业入官;见在者,分别等次,酌给赡田,入民册内,其则例户部定拟。(12)据此,大同地区的无主宗藩产业入官;有主者则依等次拨给赡田,编入民册,并按户部拟定则例承担赋税,但未指明余田的处置方式。该道旨意明显沿袭了圈地令的规定,给“见在者”拨给赡田,余田理应与户绝田一道入官。不同之处在于,此处明令赡田无赋税优免特权;入官产业亦未被圈为旗地,表明清廷在另谋新的政策。 时隔不久,顺治三年四月,户部议覆招抚江西兵部尚书孙之獬题请处置本省宗室问题的建议: 宗禄照故明初征额数解部,其加派庶禄,概行蠲免,应如所请。即认可孙之獬的方案,以“初征额数”征解江西宗禄,蠲免加派负担。而顺治帝借机颁旨于全国,如是批示: 各省前朝宗室禄田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造册报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与小民一体治罪。(13)旨令的核心是赋税问题,且就明代宗室田产而言。主要内容是规定则例,即“与民田一体起科”,明确赋税征收标准。联系旨意颁行的缘起,其“宗室名色”或指“加派”负担,或指宗室特权,即特殊化内容全部革除;与民田一体起科,治罪自与小民一体。据此,处置宗藩产业的专项政策产生,即“与民一体起科”,推行土地赋税民田化。不过,该政策不适用于已被圈为旗地的宗藩土地。 与此同时,处置勋戚产业的政策亦有调整。顺治三年正月,工部议覆操江巡抚陈锦清丈芦洲的建议: 请将故明勋戚及各衙门自占芦洲查出归公,其有主者丈量入册。得旨:苇地果属无主并各衙门自占者,查出归公,其有主者不必入官。(14)皇帝与工部的表述文字虽有差别,意见则一致,无主及衙门自占者入官,有主者丈入民册。可喜的是,对此旨意的认识可进一步落实到实践层面。该年十一月,主持清丈的卢钦谷称“自履任以来,夙夜匪懈,思效涓埃,于赐拨等洲已经悉行清理矣。”即将明代拨赐的芦洲已清理入官,并又清查出“前朝国戚田弘”、“乡官王芝瑞”、“前朝常勋”等所属洲场12 236亩零,定为无主之地入官。(15)将其与圈地令比较,在制度规定及实践中全无拨给赡田的身影,有主之地依照土地来源的性质加以处置。在稍后的政令中,江南芦洲的清丈原则通行于全国。顺治四年七月,户部奏言: 故明勋戚田地,赏赉及私占者俱应入官,自置者仍给本人赡养,与民一体纳赋:从之。(16)据此,钦赐及私占田地入官,自置者则保留所有权。“与民一体纳赋”,与对宗藩土地的规定一样,即推行土地赋税民田化,并适用于所有未被圈占的勋戚土地。 正如学界所公认的,清政权逐渐扩张的同时,财政开支随之剧增,逐渐形成入不敷出的困境。而圈地规模日增,各种弊端亦日渐凸显。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停止圈拨田屋,(17)大规模圈占旗地的活动止步。于是,处置藩勋产业的政策,由大规模圈占为旗地,逐渐转向推行土地的赋税民田化,以增加财政收入。换言之,清理目的发生变化,由安置满洲贵族转为开源济困。顺治三年以后,对藩勋产业的处置,无论具体运作方式如何变化,均以增加税收为中心。 综上所述,清廷处置明代藩勋产业的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入关伊始,名义上认可明代藩勋对原属产业的所有权,基本保持占有关系的现状。当安置满洲官兵成为急务,清廷遂于顺治元年末、二年初颁行圈地令,开启清理之肇端,除留有少量赡田外,渐次圈占藩勋产业为旗地;施行区域则以畿辅为始,逐渐向其他省份延展。随着清朝政权不断扩张,涉及的藩勋产业大增,而政府财政支出亦步入窘境,加之圈地弊端日益凸显,顺治三年遂有专项处置政策的推行,即土地赋税民田化,并于稍后停止大规模的圈地活动。简言之,清理政策由附属于圈地令到颁行专项政策,清理活动由局部施行到全面展开,而清理目的亦相应地出现变化,起初为解决满洲贵族的安置问题,尔后转为纾解国家财政困窘问题。(18)直至康熙“更名田”诏颁行,处置政策再无大变化。 二、变价与召佃辨析 土地赋税民田化是清廷欲达到的结果,其实现过程则有不同路径。据前引史料,清廷拨给明代宗藩的赡田、勋戚自置之田,大概是田地归原主所有,与民一体纳赋,直接实现赋税民田化。而入官田地则必须经历“田归与民”的环节,具体实现方式便是变价。但是,顺治时有大量入官田产是以召佃而非变价方式加以处理,并未实现其赋税民田化。本节就这两种方式加以辨析,阐明二者施行的历史脉络。 变价与召佃是具体处理方式,适用于田产、房产等对象。变价是官方估定时值、承买者支付相应钱款价值的交易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交易对象不同,后续政策则相异:土地交易完成后,其所有权为承买者所有,与民田一体起科,即实现赋税民田化;房屋为承买者购得后,一般无需再承担其他负担。召佃则没有这些差异,无论田产、房产等,承佃者均向官方纳租。可以说,变价是土地赋税民田化的一个必须环节,是政府财政开源的一种策略;召佃则是适应社会现实的必然选择,是历史既定模式的继承和延续。 (一)变价始行时间考 那么,变价始行于何时呢?学界现有两种观点,一为顺治元年,(19)二为顺治三四年间。(20)在此强调,这里的变价是指中央指令、地方遵行的统筹行为,而非地方偶然无计划的个别案例。入官藩勋逆产作何处置,顺治初的官员们持有不同意见。顺治二年二月,顺天抚按傅星景奏请将入官绝产分拨与民,让其盖房或纳租,下户部酌议,(21)其中应含有明代藩勋绝产;顺治三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云长疏请将畿辅明代勋戚、内监、皇庄、军屯补与贫民,起科征赋,下所司议处;(22)同年,监察御史马兆奎建议将王田归入民田,按民田则例一并征赋。(23)这些建议表明,时至顺治三年伊始,除被圈为旗地外,入官藩勋逆产的具体处理方式还在讨论中,变价尚未成为一项中央政令。 或在顺治三年稍后,有证据表明清廷已部署全面变价工作。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载录的相关史料中,变价案例的最早时间是顺治三年,共有四宗:一、北直隶天津道盐山县变价叛逆杨王休房地;(24)二、河南“奉文”照时估酌变废藩王宗等项遗留产业;(25)三、八月,湖北安陆府景陵县变价叛贼胡公绪逆田;(26)四、江南变价明代勋戚洲场。(27)变价对象涉及宗藩、勋戚、叛逆的房产、田产,所在区域有直隶、河南、湖广、江南四省份。尤为关键者是河南“奉文”估变,“文”应指户部咨文,表明中央已向地方下达变价政令,地方须遵照执行。在一份顺治十八年的档案中,户部尚书追溯河南宗藩产业变价银两的征解情形时,有“除顺治三年以后废藩产业杂项估价完过外”(28)一语,间接印证河南始行变价于顺治三年。由于征服时间有先后,产业被清出亦非同时,自顺治三年以后,各地历年均有奉文清查变价的活动,但就政策起源而论,顺治三年开始统一施行变价应无疑问。 (二)变价与召佃双轨制的形成 进而另一疑问是,何类产业执行变价?有迹象表明,清廷倾向于尽数变价。例如前引顺治三年户部给河南的咨文规定,“无论府第、别业,赐田、自置,俱照时估酌变”,(29)至少能明证河南的入官宗藩产业要全部变价;又如顺治三年卢钦谷在江南清查出三宗藩勋芦洲共12236亩零,该上价银5120.62两,奏文中有“召佃上价”一语,结合文义应指招纳佃户上价,全部实行变价;(30)再如顺治九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王祯题请让户部“行文各府州县,查已经变价若干,其未变价佃种纳租”(31),话语间透露变价优先于召佃,未变价产业才召佃纳租。历年均有地方官题请某些产业不便变价,其前提则是要求实行变价。对中央而言,变价可在短期内获得大量收入,与开源解困的财政需求相一致。它不仅是一种增收策略,还与前述土地赋税民田化政策紧密相连,变价将成为其先决条件。换言之,土地赋税民田化政策与变价方式同时施行于顺治三年,是二者具有内在联系所致。 但是,变价作为一种市场交易行为,即所谓“依时值估变”,完成交易需要买卖双方,缺一不可。就清初社会经济形势而言,短期内尽数变卖入官产业显然很困难。有如湖广上湖南道佥事张武烈所言:“盖湖南田地既荒,即以田让人,听其认垦纳粮,犹有称艰不为者,况以久荒之田,追其价值,恐徒悬以追价之名,终遗莫结之案也。”(32)此为顺治十三年湖南土地变价名实不符的情状,之前的情况恐更有不及,而其他省份的情形较之亦不会更好,可见在短期内尽行变价乃不现实。 变价或许令无力承买的原承佃者失去生计,亦难确保产业流入市场后大有销路,而召佃纳租这种经营模式相沿已久,地方官深入民间实际,对社会经济的现实较为清楚,因此基于各类理由题请施行召佃。对官府来讲,召佃的短期经济效益虽不如变价,但可维持长期相对较高的地租收益。因此,清廷不硬性规定全数变价,对变价与召佃的择取基本尊重地方官的建议。各种权衡利弊,清廷在处理方式上做出务实调整,最终形成了变价与召佃并行的双轨制。 (三)方式择取的惯行 双轨制意味着处理方式有选择性,而清廷并未具体规定各自的适用范围,致使二者在实际运作中的择取似乎无章可循,但从案例中能管窥出一些惯行。 变价优先于召佃。除前引史料可资证明外,又如顺治十三年,户部让河南地方官商议“所有零星房屋”的招赁与变价方案,因意见不一,户部最终题请尽数估变;(33)同年,户部指令各直省清查藩勋逆产时,旧遗房屋“从公酌估变卖”,所遗土地“召人承种”,基本确定房屋变价、未能变价土地召佃的政策;(34)至康熙七年(1668)十月,清廷仍明令清查明代废藩田房,悉行变价。(35)虽然实行双轨制,但基于短期财政增收的需求,尽力与土地赋税民田化政策相协调,从总体政策趋向来看,变价为主,召佃为次。 有损收益者不宜更张。比较变价与召佃,择取收入为多者。例如,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郧阳巡抚胡全才认为“废楚藩鸡鹅食田纳租数倍民赋,减租变价反亏饷额”,不支持变价;(36)同年,河南彰德府知府宋可发称“本府与磁州废藩所遗盐店,每岁租银三百余两,较变价有益”,卫辉府知府郑茂泰称“南北两盐店随盐行租,岁可得银二千有余,不当变价”,巡抚亢得时因此题请“彰德等属盐店,变价不如输租,似应照旧征课”,不支持变价。(37)从户部议覆看,这与增收目的相合,清廷基本认可地方的建议。 原系民产者不便变价。例如,顺治十三年,湖广布政使司称“襄藩护卫田地,原系民产,不便变价”;(38)顺治十四年,巡按湖广湖北监察御史题称“有系民间产业,难以变价”;(39)顺治十七年,山东兖州府在给布政使司的详文内称,“看得德、鲁钦赐地亩皆民间买卖己业,也照例输课为藩府禄粮,原与钦赐房屋自置产业不同,实无官民隐占情节”;(40)等等。这多为地方官题请民产不便变价之案例。清廷的意见较为明确,如顺治九年山西抚刘弘遇题请归还已变价的民间所购宗藩田房,得到批准。(41)这表明,原系民产的藩勋产业免行变价,官府认可民间对其拥有所有权。 逾越礼制者不便变价。宗藩勋戚为特权阶层,在讲究礼制的传统社会,诸多产业打上了等级的烙印,房产即是如此。例如山东青州府“衡藩府第有大小楠木共一百七十三根,不便变价,俟有紧用处所,差官拆卸。”(42)楠木在民间不得擅用,因此免行变价,听候朝廷用在所需之处。又如在拆变山西废藩府第时,布政司称“今所存府第规模阔大,与散宗房屋不同,委非民间可以居住”,(43)主张将其留作公馆或派兵看守。概而言之,在处理藩勋逆产时,政府虽以增收为主要目的,但也兼顾儒家的礼制规范。 综上所述,变价与召佃的具体操作过程纷繁复杂,既要遵从开源济困的大原则,亦要关切到民间实际、儒家礼制等因素,而将民产及不适宜民间应用之物排除在双轨制之外。 (四)“价”与“租”的分析 变价土地,承买者交付一笔地价,然后向国家缴纳正粮,即实现赋税民田化;召佃土地,承佃者向国家既缴纳正粮,亦上交地租,即“粮租并征”。承买者与承佃者均须缴纳正粮,不同之处在于纳价或纳租。有关“赋”、“价”及“租”的关系,河南开封府封丘知县余缙在议论增租时如是说: 今复蒙驳增,卑县通拘诸地户,曲谕以急公之大义,每亩令其再增银二分二厘四毫,较民田额粮适加一倍。盖半为地赋,半为地租,赋从地出,租从价出,似得其平也。然抑有请者,废藩地亩原未经变价,故可酌增,万一日后有奉文变价之令,则此地额赋便应照民地起粮,庶使垦土者无偏苦之叹,而催科者有画一之条,实永久可行之法耳。(44)“半为地赋,半为地租,赋从地出,租从价出”,这是身为知县的余缙对粮租并征的一种合理解释。“租从价出”的含义是未纳价土地须缴租、纳价土地则免租,“租”与“价”为非此即彼的对应关系,其实质则是变价为实现土地赋税民田化的必须环节。(45)此类理解恐非余缙的个人独见,而是社会对粮租并征的普遍认识。因此,封丘县官民虽接受未变价土地粮租并征,但主张若土地奉文变价,则要改为“照民地起粮”,即粮租并征的土地一经纳价,其赋税则须民田化。由是观之,“价”与“租”均是“赋”之外的负担,与其说它们产生的根源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倒不如说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策略,(46)这在增价、增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初实行安民政策,蠲免民赋尚且犹恐不及,遑论增加民赋。于是,为增加财政收入,清廷以不符时价为由增价,以租额偏少为由增租,如此则避开了增加民赋的恶名。有关增价、增租的内容,前人已作过全面深入的论述,本文不再赘述。但是,分析寓目文献可知,加增是中央的政令,而地方官却并不十分情愿执行。清廷要求“量为增加”,地方则适可而止,往往以“实估之确价”(47)、“价过时价”或“实难再增”(48)等情由予以回复。换言之,虽然中央提出的“价廉”、“租少”未必尽数失实,但确如学者所言,清廷在不断掠夺、勒索藩勋逆产的承买者和承种者,(49)而深入民间基层的地方官,对加增则保有节制的态度,以近乎消极的方式消磨中央的苛求。 综上所述,变价与召佃是清廷处置入官藩勋逆产的两种方式。变价约始行于顺治三年,作为开源济困的财政新策略,清廷倾向于全数变价,而受社会经济现实的制约,又不得不兼行召佃,由此形成二者并行的双轨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主要考虑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同时兼顾历史传统与礼制规范,承认原系民产的所有权,对不适宜民间应用的产业则另作处理。变价是土地实现赋税民田化的必须环节,否则视为召佃而粮租并征,“价”与“租”均是清廷增收的策略。在不加民赋的基础上,清廷通过加增价租来增加财政收入,而深入民间的地方官则审慎对待加增之法,致使顺治后期形成中央积极指令、地方消极回复的格局,而这正是促使康熙“更名田”诏颁行的基本情势之一。 三、清理规制的颁行 清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效果和时长不仅受处置政策的制约,(50)亦与清理规制密切相关。明清之际的土地占有关系混乱,清理工作已是艰难,而变价徒增一笔地价,召佃亦粮租并征,无疑会加剧欺隐之弊,增加清理难度。顺治初期虽已着手清理藩勋逆产,但中央并未出台统一的规章制度,地方基本各自为政。有学者指出,顺治初年“负责清查各地庄田的官员,有州县官吏,有兴屯道官员,也有驻军总兵等,互不隶属,各行其是”。(51)因此,顺治初年的清理效果不甚理想,这从官员的描述中可窥一斑。如顺治八年,户科给事中陈协如是说: 如陕西平凉府固原州地止一千九百余顷,民止二千三百余丁,赋役皆取诸此,外有楚、韩、肃、沐四王府地数万顷,民数万丁,而地粮丁差尚不及一州之半,均是赤子,何劳逸相悬若是也。臣思一州如此,一省可知,一省如此,天下可知。(52)陈协指出楚、韩、肃、沐四府的地粮丁差不及固原州一半,而地丁数则为固原州十数倍,足见赋役“欺隐”程度之深,因此题请严查。虽然他由一州推及一省、再推及天下的说法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至少能反映出清理的糟糕情形。 顺治十二年初,户部对全国清理形势有清醒的认识: 窃照各省册报亲郡王、将军、中尉等及藩府官员人等田土房屋等项,有钦赐者,有自买者。自我朝以来,有变价者,有租佃者。但此等产业《赋役全书》原不开载,藩府册籍经乱无存,必有官吏侵肥、豪强隐占之弊,且变价有多有寡不等,难以尽信,输赋或租或粮,又多不平。(53)户部认识到清理工作杂乱无章,各省情况各不相同。加之藩勋产业在明代不载于《赋役全书》,藩府册籍又经乱无存,侵肥隐占之弊丛生,而入清后处置方式灵活,难免有失公平。概而言之,清理局面混乱,效果欠佳。基于此,清廷重新布局,建立有章可循的清理规制。 (一)规制的出台 顺治十二年三月,户部题请以各省右布政使专任清核,并规定清理的具体内容: 臣等议得各省右布政使职司简少,勘以专任清核。应请敕下各督抚,责令右布政使定限将前项田土房屋等项逐一清查:故明钦赐若干,自置若干;成熟若干,完好若干,荒芜坍废若干;已变价者若干,应续变者若干,应留者若干;完租者若干,完粮者若干。务要款项数目一一分明,价值租粮件件确实,定限本年八月内查完,造册报部。如有官吏豪强侵隐不吐者,听右布政使指明,呈报督抚参究,庶侵隐之弊可以清查矣。(54)该建议得到顺治帝的批准,通行于相关各省。此一政令的颁行,标志着清理工作专任专责、有章可循的开始,清理内容有了具体要求。条款归纳有四:一、分清历史来源,即钦赐或自置;二、弄清现行实况,即土地成熟与荒废、房产完好与坍废等形态;三、明确处置方式,即已变价、续变价、应保留等类别;四、厘清执行情况,即完租与完粮数额。右布政使专任清核,明确了责任所在,并授予其检举之权,以此来加强清理力度。 户部在三月布局清理工作,要求各省在八月内查完并造册报部,地方用于实际清理的时间不足四个月。尽管由右布政使专任,清理内容亦条款明晰,但迫于期限的紧迫,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顺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户部如是描述: 今据各省造报前来,臣等逐一查核。如河南王府甚多,该省册报地土房屋数目甚少,且每亩估价止一钱或五六分不等,承种地亩,每亩除正赋外,止纳租一二分。山西省有每亩止纳租五升。山东省有未经变价竟编入民产纳粮,房屋尚多无租。湖广省每亩输租不过一分。江西省王府每府止报地十余亩,甚至一二亩,并藩宗叛逆竞不开报房屋,且上等熟田估价仅止一二两。江南勋逆腴田每亩止变价银一二两不等。各省地方更有无价之房,无租之地,匿不开报,欺隐尚多,即先经行文估变价值,包纳租课,又复玩延拖欠,此等情弊,必系势豪、衙蠹、悍将、骄兵占踞,而地方有司瞻徇顾畏,督抚按又漫无稽核。(55)所谓“各省造报”便指顺治十二年户部所要求的“八月内查完,造册报部”。户部简要总结了各省清查造报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册报数额偏少,价额、租额偏低,匿报欺隐之事尚多,价银租课玩延拖欠等等,可谓弊端累累。对其成因,归结为二:一是势豪等权贵占踞所致,二是地方有司及督抚按未认真执行清理政策。前者是现实情状,正是政府清理的对象,户部所能为之者则是完善规制,提高地方的执行力度,从而革除业已存在的诸种弊端。因此,户部进一步完善清理方案: 请敕各省督抚按专遴精明廉干道臣或推官一员,设法清查。要见:某藩某产坐落某州县土地若干,房屋园地等项若干;某勋戚某叛逆坐落某州县地土若干,房屋园地等项若干;以前估变数目,曾经何官确估变过价银,见今存贮何处;见在承种是何姓名,输租甚薄者,确议量增;未经变价竟编民产者,察明输租;俱要逐款分晰。(56)两天后,顺治帝批准了该方案,下旨各省严行确查。新订条款概要有四:一、产业的具体坐落和数额;二、已变价产业的数目、经手官员及价银储存地点;三、已召佃土地的承种人,租额薄者量增;四、未纳价而入民产者,重新纳价。与顺治十二年条款相比,该条款不仅内容更为精细,其清查重点也有所变化。前一条款主要清查产业的历史属性、现存状况以及处理情况,基本以究明产业信息为核心,而这一条款不仅重视产业信息,细化到界址、估变价银的储存地等内容,更重视与之相关的人员信息,要求查明经办官员、承种人姓名,可以说是产业与人员并重。 不仅更新了条款,对自首免责、官员调配、变价与召佃的择取、奖惩制度等内容亦作了新增或调整,其内容为: 又能出首者,即宽以从前隐匿之罪。至于旧遗房屋,恐年久不修,多有倾坏,应从公估变;所遗地土召人承种,除正赋外,酌租多寡,按亩输租,不得借口荒芜,再滋欺隐。通限文到三月内造册汇报,以凭复核充饷。敢有违抗,即据实题参,以凭从重治罪。其经管道官、推官果能清厘有法,钱粮增益者,臣部察明议叙纪录,以示激劝。如因循徇隐,违限不完,察参议处。督抚按奉行不力,仍前瞻徇,臣部别有报闻,一体参处。所有清查各官职名,先行报部察核可也。(57)概而述之,有如下几条:一、从前犯有隐匿之罪者若能自首,从宽处理;二、房屋实行变价,未处置土地实行召佃,粮租并征;三、由道员、推官专责清核,认真清理而卓有成效者奖励,因循徇隐而违限不完者察咎;四、督抚按负有遴选专任官员之责,且要报部查核;五、文到三个月内造册汇报清理结果。显而易见,这些新规比顺治十二年的规定大为全面,形成了自首免责、变价与召佃并行以及对专任官员选任、考核、奖励、问责的系列章程。合之前述精细条款,标志着清理规制的基本成型。 (二)规制的实施 1.官员调配 右布政使“专任清核”,主管全省清理工作,其职责多是督催审核,虽然权责明晰,但欲在短期内成效显著,难免力不从心、效果欠佳。于是,改由道员或推官“设法清查”,主持道或府内的清查工作。如此调配官员,与二者的职掌密切相关。研究指出,道制发展至清初,区域道成为巡抚管辖州县的中间环节,形成巡抚一守巡道一府(或州县)的管理层级,(58)而专务道则成为省级行政部门;(59)其职掌则从监察转为行政,职能已趋向一致,甚至“守巡道在职掌上已无明确分工”。(60)一言以蔽之,区域道(如守巡道)或专务道(如督粮道)在职掌上大都有稽查钱粮之责。而推官之设袭于明制,一般府置推官,其职掌主要为“理刑名”,(61)审核违法之事自是职司所在。 但是,道制本身很复杂,清初各省实情亦不同,规制的具体实践存在很大差异。按“各省督抚按专遴精明廉干道臣或推官一员设法清查”,文意是总督、巡抚、巡按会同遴选一名道员或推官主持清理,别无具体细则。据现有材料查考,河南“遴委分守大梁道右参政王原膴清查开封府属明季宗藩等产”,(62)选任一名道员主持开封府的清查;山东“济南府属遴委济巡道,兖州府属遴委济宁道,东昌府属遴委东昌道,青州府属遴委青州道,莱州府属遴委莱州道,登州府属遴委登州道,就便确查”,(63)即一府辖于一道来展开清查;江西“就近各道总核,各府推官亲诣彼处清查”,(64)即各道员总核、各府推官亲自清查;湖广“(布政司)遵依移会守、巡各道,并檄行各府推官,会同该府就近清查,厘剔遗隐”,(65)即守巡各道员与各府推官共同清查。这四省大抵为各区域道员分别负责,会同下辖府属推官共同主管清理工作。 陕甘则较为特殊,督抚按臣以道员散处各方、各有专责、未便遥制为由,遴选督粮道参政程之璿,督令各府推官实行清查,即由专务道道员一名领衔,督令各府推官实际主持清理。不仅如此,陕甘部分地区行政辖属比较特殊,诸如河西二千里未设推官,临洮府推官又不能兼管;宁夏两河地方,庆阳府推官难以遥摄;兴安州并所属六县不系府辖,难委别府推官兼管。因此,程之璿再请应变之策,分别由甘凉二州同知、宁夏理刑同知、兴安州同知来负责清理河西、宁夏两河地方、兴安州并所属县的清理工作。(66)概而言之,陕甘地区对官员调配作了因地制宜的调整,由督粮道道员领衔,大部分地区由各府推官、小部分地区由州同知或理刑同知来实际清核,这与上述四省的官员调配大有不同。 另者,宗藩、勋戚、叛逆产业的清理似有部门分工。顺治十三年,湖广总督祖泽远称: 臣查藩产隶右布政司清理,严檄催查,已据司详造册题报在案。至勋戚产业,楚属原无此项,节据藩司详覆,无凭查报。惟逆产一项隶按察司专责,随严行清查。(67)可见,在湖广的宗藩、勋戚产业由布政使司清理,而逆产则由按察使司专责清查。而按察使司给总督的覆文中声称: 查得叛逆产业一项,自顺治二三年以及此时,凡经本司衙门审明、奉旨决过者,随即查明造册变价,同各逆妻孥解部矣。至于明季叛犯未经投诚,我朝各逆产业曾经藩司查过,本司当即移会有无底案去后。今准回称:原未奉行,则势必候各府刑官亲查造册赍司,方可汇报,未便草率完事。(68)据此,按察使司已将顺治二年以来结案的叛逆产业查明造册、变价解部,但未曾处理明季叛犯产业,认为已由布政使司清查,行文核实。布政使司回称“原未奉行”,有待各府刑官查实造报,方可汇报。虽云按察使司专责清理逆产,布政使司实际也涉入其中,二者最终将责任落实到刑官即推官身上,此与上述官员调配方式亦相协调。 与右布政使相较,道员或推官的辖区要小得多,清初守巡道员管辖数个州县或一至两个府,(69)而推官一般管辖一府,权责则进一步下放。而专责官员的业绩直接关乎政绩,并会影响到仕途的升迁。这些务实的调配,无疑为清理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2.册籍造报 在清查过程中,精细条款既是工作开展的标尺,又可一定程度上防止因笼统操作而产生的隐匿。它具有追本溯源、人事并重的系统性,依照条目限期文到三月内造册报部,致使地方官的压力甚大。因此,顺治十三年底,多个省份均以地域辽阔、造册繁杂等理由题请展限,清廷对此亦给予一定宽限。(70)这恰好反映各省在认真执行,规制并非一纸虚文。 造报册籍现在虽未见实物,但其所载内容大体以户部的规定为据。例如,河南巡抚亢得时给大梁道的批文说,“废藩勋戚叛逆某某若干,察照部文将总撒分晰明白,不混在一处,此即册式也。”(71)即河南按户部要求将明细、总汇造册明白,定为册式。河南如是,其他省份大抵不会有本质差异。综合档案记述,造册程序一般为州县册汇于府,府册汇于道,道册汇于省,省册送交户部。据江西左布政使范登仕称,省册则应为“一样三本”,以备查考。(72)而在州县、府、道、省之间,除层层造报册籍外,经手官员还须向上司送交甘结或印结,诸如“时估确价、难以再增”甘结(73)、“无遗留”甘结、“无隐匿”印结、“无藩产”印结(74)等,对造报结果负有责任。这种分条造册、有据可查、自负其责的造报程序,无疑加大了清理力度,改善了清理效果。以陕甘为例,康熙《陕西通志》所列新增查出藩勋田产及租银的案例,主要集中于顺治十三年及稍后年份,(75)这显然与清理规制的完善及认真执行密不可分。 3.钱粮考成 清查出的产业经过变价或召佃,价银和租税的征解成为重点,此任务则由府州县正堂官来完成。换言之,限期内的清查工作由道员、推官担纲,而相应钱粮的日常征解则由府州县正堂官负责,此是其职司所在。不过,在严查藩勋逆产时期,相关钱粮的征解以单独核算项目纳入考成,以此凸显其重要性。 顺治十八年三月,湖广巡抚杨茂勋题明十七年份楚省废藩田地应征租银未完各官的名录及未完情形,以十分为率,节次开列。清廷据此加以考成,并按新奉上谕对原不在处分之列的“未完一分者”加以处分,“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其停升转”。(76)显而易见,单独考成藩勋逆产相关钱粮的征解,直接影响到了官员的升迁。其后,经杨茂勋题请,追征完解的官员得以开复,(77)而仍未完解的官员则被清廷勒令继续追征追解,(78)停其升迁。不仅如此,清廷不许地方擅自减免藩勋逆产的赋税及租饷。例如,顺治十八年,户部屡次要求湖广督抚查明应城、孝感、汉阳、黄陂四县顺治十七年缩减之银两,不许擅自减免。(79)这种严格考成,改善了顺治十三年前价银、租饷的拖欠现象,可使清廷有效掌握财政收入,得到清理藩勋逆产的实益。 综上,顺治十二三年,户部主导建立并完善了清理藩勋逆产的规制。首先,细化清查的具体内容,既让地方的清理有的放矢,又杜绝了朦胧操作的可能;其次,以道员、推官专责清理,既不落以前省级官员主持清理而力所不及的窠臼,又避免以州县官清理而过于分散的弊病,加之府州县职司官吏的辅佐,使得清理工作职权分明;再次,钱粮的征解归责于府州县官,并单独从严考成,保证价银、租税流入国家府库,不致重蹈顺治初年“有报部之名而实利尽属他人”的境地。质言之,清理规制的颁行为清理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使之进入有章可循、有制可依的时代。有学者认为,“经过从顺治元年至康熙八年间长达二十五年的严厉清查,明代皇室、藩王、勋戚各类庄田绝大部分,已经基本清查完毕。”(80)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顺治十三年清理规制的颁行有莫大关系。 藩勋逆产的清理是清政权入关伊始就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清理政策,常见政书只载康熙“更名田”诏,对顺治时期几未着墨,从而淡化了后者在制度史上的意义,甚至给人造成顺治朝并无规制的错觉。本文的论述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以往认识上的不足,进而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康熙“更名田”诏是继承和调整了顺治朝的清理政策,继续推行土地赋税民田化,但放弃了“变价”和“征租”这两种增加财政收入的策略。两朝政策一脉相承又有所变化,因此考察前者的演变过程,对理解后者将大有裨益。 收稿日期 2015-01-10 注释: ①陈支平:《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厦门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陈支平:《清代更名田立法及其赋役负担》,收入氏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1-272页;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第39-69页;佐藤文俊:《清初におけろ旧明朝の王府荘田》,收入氏著《明代王府の研究》,研文出版;1999年,第384-407页。 ②如黄六鸿《福惠全书》、王庆云《石渠余纪》等,记述了清代许多重要的典章制度,虽载有“更名田”的内容,但未载顺治时期的规制。 ③清政权一贯没收反叛者的产业,而对藩勋产业则有灵活多变的政策,因此本节所述处置政策的演变主要就后者而言。 ④参见顾诚《南明史》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⑤参见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第39-142页。 ⑥《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 ⑦《清世祖实录》卷13,顺治二年正月辛卯。 ⑧《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甲子。 ⑨《清世祖实录》卷20,顺治二年九月己巳。 ⑩《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壬申。 (11)参见左云鹏《论清代旗地的形成、演变及其性质》,《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 (12)《清世祖实录》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丁未;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四,顺治元年闰六月丁未,《续修四库全书》第36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下栏。按,《东华录》所录文字比《清世祖实录》为简,未述及该道旨意颁行的前因,亦未明言其适用范围为代藩,因此极易误解其为通行全国的政令。 (13)《清世祖实录》卷25,顺治三年四月乙酉。 (14)《清世祖实录》卷23,顺治三年正月乙亥。 (15)《卢钦谷启清查南明勋戚洲场土地事本》,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阁启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151页。按,以下注释内的档案材料均出自该书,只注明页码,不再详注编者、书名、版本。 (16)《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丙寅。 (17)《清世祖实录》卷31,顺治四年三月庚午。 (18)按,圈地令不是处置明代藩勋产业的专项政策,因其关涉藩勋产业的内容甚多,以致从本质上改变了原定的“怀柔”政策。旗地圈占仅指向部分藩勋产业,而赋税民田化政策则指向未被圈占的藩勋土地,二者并非针对同一具体对象、前后相继的政策,而是处理同一问题即清理藩勋产业的不同政策。 (19)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第172页。 (20)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第51页。 (21)《清世祖实录》卷14,顺治二年二月庚辰。 (22)《清世祖实录》卷24,顺治三年二月庚辰。 (23)马兆奎:《请将屯田王田归并民田议》,载琴川居士编:《皇清奏议》卷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4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9页。按,该版本收录正文时,将“马兆煃”作“冯兆煃”,将“请将屯田王田归并民田疏”作“请将屯田王屯归并民田疏”,为刊刻之误,径改。 (24)《祖重光为清查河北明藩遗产事揭帖》,顺治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第204页。 (25)《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房产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第183页。 (26)《祖泽远题清查湖广各处明藩产业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七日,第181页。 (27)《卢钦谷启清查南明勋戚洲场土地事本》,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150-151页。 (28)《车克题清查豫省未报明藩田产事本》,顺治十八年七月初七日,第243页。 (29)《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田产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第183页。 (30)《卢钦谷启清查南明勋戚洲场土地事本》,顺治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151页。 (31)《噶达洪题明藩田产租银开支已有项数难以再动支事本》,顺治十年正月十七日,第155页。 (32)《祖泽远为豁免湖南明藩久荒旨田追价银两事揭帖》,顺治十三年六月初二(收文或朱批时间),第165页。 (33)《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房产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第186页。 (34)《陈极新题清查陕甘等地明藩产业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第169页。 (35)《清圣祖实录》卷27,康熙七年十月丁卯。 (36)《胡全才为清查郧襄等处明藩遗产情形揭帖》,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收文或朱批时间),第167页。 (37)《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房产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第184、186页。 (38)《胡全才为清查郧襄等处明藩遗产情形揭帖》,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收文或朱批时间),第167页。 (39)《张朝瑞为清查湖北明藩产业事揭帖》,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99页。 (40)《车克题山东各州县清查明德、鲁、衡三藩田房产业情形本》,顺治十七年二月初八日,第212页。 (41)《户部题对明宗室遗产之课税应予区分事本》,顺治十年正月十七日,第156页。 (42)《王弘祚题折变青州明藩宫殿城垣事本》,顺治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第226页。 (43)《白如梅题山西明藩房屋拆变情形本》,顺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第245页。 (44)《亢得时为清查河南各州县明藩田房产事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93页。 (45)又如顺治十三年,户部批评山东“有未经变价竟编入民产纳粮”之事,并于稍后责令“未经变价竞编民产者察明输租”,亦表明变价为实现土地赋税民田化的必须环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4辑,第168、178页。 (46)康熙“更名田”诏的基本内容是免价、免租,进一步推行土地赋税民田化。换言之,清廷在制度上已经放弃了通过变价和征租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的策略。 (47)《张朝瑞为清查湖北明藩产业事揭帖》,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98页。 (48)《阿思哈题豫省明藩房地产估价事本》,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第251页。 (49)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第174、181页;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第53、55页。 (50)郭松义指出,造成清理废藩田产进展迟缓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所采取的“变价”或粮租并征(即召佃)政策。见郭松义:《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第51页。 (51)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第172页。 (52)《陈协题明藩田产务须严察起科事本》,顺治八年八月初九日,第151-152页。 (53)《胡全才为清查郧襄等处明藩遗产情形揭帖》,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朱批时间),第166页。 (54)《胡全才为清查郧襄等处明藩遗产情形揭帖》,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朱批时间),第166-167页。 (55)《陈极新题清查陕甘等地明藩产业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第168页。 (56)《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田产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第178页。 (57)《车克题清查河南明藩田产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四日,第178页。 (58)傅林祥:《清康熙六年前守巡道制度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7页。 (59)何朝晖:《明代道制考论》,《燕京学报》新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60)周勇进:《清代地方道制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59、263页。 (61)《明史》卷75《志第五十一·职官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9页。 (62)《亢得时为清查河南各州县明藩田房产事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92页。 (63)《车克题清查山东藩产事展限两月本》,顺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第190页。 (64)《笪重光题清查明藩田产请展限期事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第187页。 (65)《张朝瑞为清查湖北明藩产业事揭帖》,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97页。 (66)《陈极新题清查陕甘等地明藩产业需展限时日本》,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第170页。 (67)《祖泽远题清查湖广各处明藩产业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七日,第180页。 (68)《祖泽远题清查湖广各处明藩产业情形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初七日,第180页。 (69)傅林祥:《清康熙六年前守巡道制度的变迁》,《历史地理》第25辑,第97页。 (70)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中就收录有河南、陕甘、江西、山东等省份请求展限的题本。 (71)《亢得时为清查河南各州县明藩田房产事揭帖》,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192页。 (72)《笪重光题清查明藩田产请展限期事本》,顺治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第187页。 (73)《张朝瑞为清查湖北明藩产业事揭帖》,顺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第198页。 (74)《车克题山东各州县清查明德、鲁、衡三藩田房产业情形本》,顺治十七年二月初八日,第205页。 (75)康熙《陕西通志》卷9《贡赋》,康熙六年刻本,第39b、43a-b、69a-b页。 (76)《车克题严查楚省明藩田地岁征租饷未完各官职名事本》,顺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237页。 (77)《杨茂勋题湖北明藩租饷督催已完事本》,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第248页。 (78)《阿思哈题湖北十七年明藩租饷督催已完事本》,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内阁户科史书),第253页。 (79)《车克题严查楚省明藩田地岁征租饷未完各官职名事本》,顺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第238页;《阿思哈题湖北十七年明藩租饷督催已完事本》,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内阁户科史书),第253页。 (80)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第184页。标签:顺治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