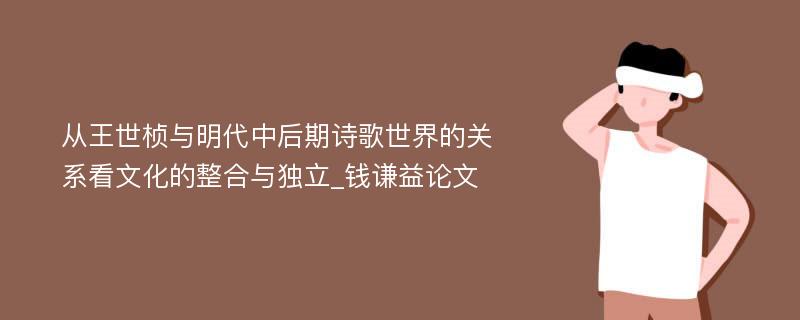
从王世贞与明中后期诗坛之关系看文化的相融与独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后期论文,独立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6)04~0005~07 郭绍虞论明代文学曰:“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1](P528)设坛分砧,标榜风气,充满激烈的门户之争,这即是明代文学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这种文学景观的持久存在固然与明代特殊的政治及社会思潮密切相关,但更为深层的却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争。明遗民张岱云:“五方风气不同,一时诗学之角立不相下。”[2](《叶桐初旅吟诗序》,P541)所言即文化习俗不同,不同地区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诗学。楚人杜濬于易代后“淹留于吴数十年,几忘其为楚,然其诗之卓然自立,仍未失乎楚”。[2](《叶桐初旅吟诗序》,P541)这说明,文化的稳固性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创作,以至于移民异地数十年的杜濬,仍然保留着本土的文学风格。文化自身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与政治权力、经济强势密切相关。费锡璜《国朝诗的序》论清初诗坛三种不同趋势云:“吴越之诗婉而驯,其失也曼弱;楚蜀豫章之诗,勇于用才使气,其失也剽而争;中原之诗雄健平直,其失也板而乏风致。”从地域范畴和大文化圈的背景而言,“吴越之诗”可归入吴,“楚蜀豫章”可并入楚,而“中原之诗”则指以齐为代表的秦晋齐鲁。①明中后期流派纷纭的文人社团大致可分别归属于齐、楚、吴三大地域,诗坛总体呈现出三类不同风格:齐气健、楚风幽、吴声柔。 自明中期始,诗坛的主流趋势便是前、后七子的齐气[3](《丁集》下《王象春》:“才气奔逸,时有齐气”,P654)与公安、竟陵之楚风[4](《杭州赠宋荔裳宪使先生》一:“重开历下盟齐会,一洗江南变楚风”)交互称霸,各藉其强大的文化优势试图覆盖、同化吴声。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角逐之中。即使如此,江南一带,仍然有大批文人不受齐气、楚风所拘囿,一直在强势话语之外保持独立的吴声特色。晚明诗坛实际上是在三种不同地域诗学宗尚的相互抵抗、相互对峙和相互包容中递嬗行进,并一直延续至清初。 晚明山东才士公鼒论明代诗坛:“为君历代选宗工,前称弘正后嘉隆”,[5](《长歌赠邢子愿席上》,P82)“前弘正”即前七子,“后嘉隆”即后七子,公鼒认为明诗可称为“宗”的只有前、后七子。而在文归翰林的明前期,诗坛主流则是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的台阁体。尽管后起的茶陵派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台阁独霸之势,但其大局仍属翰苑,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诗坛格局。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魁的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河南人;徐祯卿,苏州人;边贡,山东人;康海、王九思,陕西人)联袂而起,以河朔贞刚之风横扫诗坛,标举秦汉之文、盛唐之诗,起衰救弊,“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6](《皇明诗选序》,卷首)完全改变了明中期板滞的诗坛局面。从此,雍容倦怠的台阁气象悄然隐退,代之而起的是涛涛而来的北地雄风。“古人之风几遍域中”。[7](P234)其后至嘉、万时期,以谢榛、李攀龙为旗纛的后七子(王世贞、宗臣,江苏人;梁有誉,广东人;徐中行,浙江人;吴国伦,江西人)接续前七子,重扬汉唐之帜,诗风由河朔狂飙之风变为齐鲁雄浑之气。“齐气”兢爽,明代诗坛遂步入生机勃勃的巅峰时期。公鼐《读冯侍讲诗》论七子的诗坛地位云:“迨至嘉靖季,七子争鞬革舟。历下树赤帜,骚坛据上游。”深为七子领袖诗坛而自豪。七子之声光气焰成为嘉、万诗坛主流,此际诗人“无不靡然从风”。[8](卷一七二“归震川集”,P1511)七子诗风炽热的同时,也流露出明显的缺憾。清初湖北大臣熊赐履即理性地总结七子诗文之弊云:“往往以饾飣为能,雕绘为工,填塞典故,不顾其安,如土偶衣文绣,灵气绝无。”[9](熊赐履《经义斋集》,杜濬《变雅堂集·遗集·附录》卷一所引)认为前、后七子的格调诗,正如木偶穿锦著缎,即使外表华丽非常,但缺少鲜活的生命气息。七子复古,以雄压海内之势冲破了台阁体的沉雍板滞,清扫了茶陵之弊,但囿于盛唐,不越雷池,割剥字句,描摹面貌。由于声势浩大,后期公然剽窃,众口一响,“狂易成风,叫呶日甚”,[3](《丁集上》“李按察攀龙”,P429)七子之诗成为千篇一律的盛唐诗,遂遭遇诗坛的全面攻击。“吴人厌其剿袭,颇相訾謷”。[3](《丙集》“黄举人省曾”,P321)追随七子的公鼒也注意到七子复古的明显缺失,“七子以大声壮语,笼罩一世,使情人韵士尽作木强”。[10](王象春《浮来先生诗集序》,卷首)吴下诸生责骂李献吉只一“盗侠耳!”[11](卷一百十七《与李于鳞》) 当风靡百余年的七子格调雄风不能继续担负诗坛的历史使命时,“楚风乘其弊,起而矫之”。[12](卷三《外篇》上,P39)楚风崛起于七子流弊自身不能克服之际,取代“齐气”而成为诗坛新宗向。嘉隆间,诗坛上“与李氏(攀龙)首难者,楚人(袁宏道)也”,[13](《文集》序二《问山亭诗序》,P289)意谓袁氏三兄弟为宗的公安派首先向七子发出责难,他们倡导独舒性灵,悦性自适,形成与七子迥然不同的“楚风”。[14](卷二《叙小修诗》:“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从此“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摩拟涂泽之病”。[3](《丁集中》“袁稽勋宏道”,P567)其后“诗道其张于楚”[15](《珂雪斋近集》卷三《花雪赋引》)的竟陵继起,在抵抗七子的层面上,公安与竟陵联袂携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3](《丁集中》“袁稽勋宏道”,P567)文学主张前后相继的公安三袁与竟陵钟、谭均为楚地作家,他们有意识地以一种对地方文化强烈的自觉体认相号召,以“楚风”抵抗前后七子的诗学宗尚。 公安派扫除了前后七子的模拟对文坛的负面影响,直写胸臆,“抹倒体裁、声调、气象、格力诸说,独辟蹊径”,[12](卷三《外篇》上,P39)“不字字效盛唐”,“不言言法秦汉,而颇能言其意之所欲言”,[15](《淡成集叙》,《珂雪斋集》卷十)变雄迈豪放为清新轻俊。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楚风的诗学贡献:“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致天下耳目于一新”。[8](卷一七二“袁中郎集”)楚风以其全新的面貌迅速得到诗坛的广泛呼应,“钟、谭之体,家传户习”,[3](《丁集中》“谭解元元春”,P573)海内诗人靡然向风,致使以七子后辈自居的云间陈子龙慨叹诗风之变:“汉体昔年称北地,楚风今日满南州”。[16](《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卷十三)楚风以其对性灵的高度重视而君临天下。但北方齐气并未因此消歇,而是与楚风形成对抗之局。施闰章在《与彭禹峰》中描述齐楚诗学相争相持的局面云:“北音噍杀,南响浮靡;历下、竟陵,遂成聚讼”。[17](《文集》卷二十七)钱谦益亦于《赠别胡静夫序》中谓齐气、楚风“旗纛竿立”,[18](卷二十二,《赠别胡静夫序》,P898)各守疆域,互相排挤,各不相容。 在齐、楚诗学交互称霸的时代,江南吴文化受到了巨大冲击,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认定:“徐祯卿、王世贞与李梦阳、李攀龙等人结盟,包含着使南、北文学合流的企望,而袁宏道把‘楚风’引入吴中,则标志着长江中、下游文学的一次交融”。[19](P211)这段文字说明:无论齐气、无论楚风,都试图以自己的文化强势影响并进而同化吴声,都试图将吴声纳入自己的文化领域。 “吴声”不幸遭遇悲剧,正面临着被齐、楚文化所吞没、所消解的危险。吴人钱谦益在《朱云子小集引》中表达对吴文化危机的深切忧虑,云吴声“昔夺于秦,中服于齐,今咻于楚”。[20](卷三十二,《朱云子小集引》,P356)这反映了钱谦益面对齐、楚强大的文化威势而产生的恐惧与焦虑,他为吴文化的处境与前景忧心忡忡。然而其后诗史的发展却证明了:吴声不仅最终并未被齐、楚所同化,而且一直以其显明的地域特色与齐气、楚风并飚诗坛。 对于以柔为显著特征的吴声来说,独立于齐、楚的夹缝之中并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既需要时间的酝酿,也需要吴声精英的诗学调整。台阁、茶陵秉政诗坛之际,吴地吴宽、王鳌等台阁大臣即努力奖掖沈周、蔡羽、史鉴、祝允明、唐寅、文征明等一批吴学后进之士,有意识地在雍滞的台阁之外保持了适情达意的吴声意蕴。当七子诗焰极盛之际,归有光、唐顺之等吴中“唐宋派”独抱唐宋遗集,别立七子之外,毅然与之抗衡,使“吴音”诗文香火未断。即使七子主力徐祯卿身为吴人,在七子中亦未放弃其本土的吴声传统。 朱彝尊论徐祯卿诗学之变曰:“迪功少学六朝,其所著五集,类靡靡之音。及见北地……心倾意写,营垒旌旗,忽焉一变。”[21](卷十,P263)徐祯卿早年为“吴中四子”之一,当他于弘治十八年(1505)释褐紫庭之时,正是京师复古诗学声势浩大之际,乃“深悔其吴歈”,[22]遂与李、何“数子友,相砥砺于辞章,既殚力精思,杰然有立矣”,[23](王守仁《徐昌谷墓志铭》)诗风于焉大变。文震孟《姑苏名贤小纪》云:“于是中原诸子咸推先生主齐盟,名在大梁、信阳间。”[24]可知,徐祯卿当日影响之著若此。 前七子之首李梦阳为扩大诗学阵营试图使徐祯卿完全走向复古,徐亦以高水平的创作最终与北地、信阳鼎足而三,成为七子中坚。即使如此,徐诗仍然柔美清秀,其雄厚大雅的诗歌中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江南文化痕迹,仍未摆脱其固有的文化属性。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并未脱离吴中风习:坚持以情为宗,认为诗歌的表现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格因情立,情随人殊,情永远是文学生成的源头,与复古格调迥然不同。徐诗的总体成就并未拘于盛唐,而是上规陶谢,下摹韦柳,深有寄托,泊然于声华驰逐之外,成为七子之别调。这就是无论诗坛新变如何吴声永远独立于流派纷争之局的重要因由。很多批评家注意到了徐祯卿诗文创作对吴地清美诗风的保留,如朱彝尊《明诗综》即云:“李气雄,何才逸,徐情深”。虽然与李梦阳同调,但徐祯卿中原习气未染,江左流风犹存。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明史·文苑传二》称徐祯卿为“吴中诗人之冠”。 文化的稳固性,使得同为前七子中主粗豪俊逸的李、何与倡导清丽的徐祯卿反复辩难而不相容。对华美清丽文风的钟情,使得徐祯卿与李梦阳在文学观念上始终存在距离。王世贞《黄淳父集序》中“今吴下之士与中原交相诋”之所言即表明吴人与七子在诗学观念上的明显冲突。这种长期论争并不仅仅出于文学的原因,地域、个性等是其中重要因素。因此吴、齐冲突已非仅属一般性的文学观念的冲突,而是北方齐气向江南吴声的逐步渗透和吴声坚持其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地域文化的冲突。徐祯卿后期摆脱了前期创作中的卑弱气格和华丽辞藻,古朴淡雅,颇具复古风格,但仍然清丽情深,并无北方风沙雄浑之气,其早期柔美婉转、重视形式审美文风的吴声痕迹仍十分明显。《明史·文苑传二》言徐祯卿“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故习犹在”即其稳固的文化本性的体现,有意无意间其吴文化属性即会自然流露,因此其诗风仍与李、何相异其趣,与七子诗学的整体追求也不尽相同。虽然创作有所转化,但“故习”——江南“吴声”本色犹存。李梦阳《〈徐迪功集〉序》亦讥其“守而未化,故蹊径存”。[25](卷五十二)钱谦益则认为,徐祯卿诗歌的价值正在于其“未化”的“江左风流”——“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嘎兀之习”。[3](《丙集》“徐博士祯卿”,P301)徐诗所“守”的文化“蹊径”正是钱谦益所推崇的吴文化价值所在,而这也正是当世及后世诗论对其严加苛责之处。王世贞亦认识到徐诗的明显缺憾是缺少骨气,故在《郢垩集序》中云:“稍裁其南之藻辞而立骨”,[11](《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十)认为徐诗如果裁剪其靡丽的江南吴声,那么其诗中风骨就会得以确立。祝允明《梦唐寅徐祯卿》认为徐诗“遑遑访魏汉,北学中离群”,是北方复古诗学中的离群之雁——难以融入北方文化风尚之中。徐诗最终并未被李、何的北方文化所同化,“昌谷虽服膺献吉,然绝自名家,遂成鼎足”。[26](P363)徐祯卿在接受齐气、楚风的同时,吴中华美的才情、风调仍不自觉地带入复古的文学创作中,沈德潜《说诗碎语》之“徐昌谷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润,骨相嵌崟,自独能尊吴体”[27](卷下,P398)的评论正基于此。 吴地尚情的文化特色并给七子复古思潮以一定程度的冲击,使得复古思想有所改变。对李梦阳也产生一定影响,李梦阳晚年在《弘德集序》所提出的“真诗乃在民间”的文化醒悟即源自对吴声传统的反思。 当徐祯卿以吴人身份加盟七子复古文学潮流时,吴中诗人多数仍固守吴声传统,不为格调诗学所牢笼。吴中四名士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创作都具有明显的吴地特征,其诗风仍然保持吴声本色。钱谦益《孙子长诗引》云:“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启)、杨(基),再盛于沈(周)、唐(寅),士多翕清煦鲜,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土风”即吴声,吴文化的柔靡使得他们的创作体现了统一的地域风格,而难以像复古七子及竟陵楚风般卓然而出。在复古诗学中,吴中诗人王樨登挺身而出,以捍卫吴声传统为己任。吴人蔡羽“信心守古,确不可拔”,[3](《丙集》“蔡孔目羽”,P308)吴中皇甫汸、皇甫濂兄弟“当弘正之后,畅迪功之流风,矫北地之结习”。[3](《丁集》上“皇甫佥事汸”,P414)钱谦益即认为吴地诗文,前辈师承有继。弘治、正德、嘉靖时期复古诗学之外,吴声诗学香火未绝。 出乎徐祯卿自己的意料,正是创作中所坚持的吴声,为他赢得极高的诗史声誉。嘉兴名士周筼论徐祯卿的文学影响曰:“李、何专学杜,昌谷兼师盛唐诸家。此后薛君采、蒋子云、王稚钦、高子业、华子潜、皇甫昆弟,皆清婉成音,各极其妙,虽非昌谷流派,而风调实自昌谷启之。”[28](卷三一)周筼认为,徐祯卿藉南北兼宗的努力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范式:既包含了七子盛唐激情诗风,同时也保留着清婉的吴音,从而形成了既同于七子又有别于七子的“昌谷流派”。这一流派全部由吴地文人所组成,崛起于齐气称霸之时。这说明,尽管七子齐气风靡诗坛,但吴文化所孕育的吴学精神却稳固地存在着。不仅如此,由于徐祯卿的文化影响,以至于产生了置于李、何之上的趋势。吴人王世懋即预言:“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废兴,二君必无绝响。”[29](王世懋《艺圃撷余》)千百年之后,李、何的北地雄风将烟消云散,风光不再,而吴地“二君”(徐祯卿、顾璘)诗学必将与史共存。仅仅半个世纪后,这个预言“竟果验焉”。[30](P1730)清初诗坛主盟王士祯即接续了徐祯卿的诗学,不仅其创作容纳了吴声风格,而且诗学观亦深受徐诗影响。《四库全书·二家诗选提要》云:“士祯之诗实沿其(徐祯卿)派”,王士祯亦曾自谓:“更怜《谈艺》是吾师。”[31](P104)王士祯所倡导的“神韵”诗说,昌谷诗学是其源头之一。所以费锡璜《国朝诗的序》即谓:“山左颇染三吴之习”,这说明吴声对齐气的反向影响,齐、吴文化双向碰撞而产生交融。 尽管抵抗前七子的“唐宋派”很快被淹没在后七子的诗学浪潮中,但唐宋派的振臂一呼却证明了吴文化的传统力量。嘉、万时期,后七子接续前七子诗学,重扬汉魏风骨、盛唐气象。《明史·文苑三》谓:“世贞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他折服于何、李的复古诗学,“一扫叔季之风,遂窥正始之途”,“中兴之功,则济南为大”,[11](卷一百四十八《藝苑巵言》五)赞颂李攀龙在嘉靖后期重擎复古大纛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作为前七子诗学的忠实追随者,王世贞几欲横扫天下的诗学努力使其在李攀龙之后成为后七子领袖。《明史》谓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罩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32]即使如此,王世贞的创作仍然充斥着吴音流韵,“自家本色时时露出”,[3](《丁集》中“袁庶子宗道”,P566)其吴声本色终难消解。 王世贞也意识到复古派摹拟的流弊,曾批评李攀龙三首而外,不耐雷同。王穉登《与方子服论诗书》云:“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33](P4812)齐气失之粗豪,南音失之柔弱。对于吴地诗风,王世贞亦常谓之“江左靡靡”、“清淑而柔”、“雅好靡丽争傅色”。这说明,无论对于复古的齐气,还是柔靡的吴声,王世贞都具有清醒的批评意识。他将自己定位于文化拯救者的位置:维护齐气统领诗坛的权威,同时又不拘囿于文化大潮,而是谨慎地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归属。他屡屡称述的“天下之文莫盛于吾吴”,[11](《弇州山人续稿》卷四〇)即体现了其文化归属的自豪感。面对吴文化遭遇的空前危机,王世贞提出南北相“剂”的修正方略:吴地之词藻与北地之气骨、吴地之轻俊细腻与中原之粗豪精深相剂为用,以北方的刚贞豪迈调剂吴地之靡弱轻浮,以齐气之格调羁勒吴声之才情。批评吴下之习与中原齐气“相诋”相责,而称赞吴人徐祯卿和黄淳父能调和齐、吴,“相剂”为用。这不仅说明王世贞遵守自己文化传统的吴人意识,同时也流露了其希望通过一种新的修辞方式概括自己艺术的文化欲望。体现于创作上,他擅长把吴声与齐气交融到其诗文创作中,使得我们今天读他的诗仍然会增长许多文化的灵性与感悟。王世贞的这种诗学努力得到吴人冯时可的鼎力支持,后者认为:吴诗清浅而靡弱,不以二李“剂”之将无能为诗。令人遗憾的是,王世贞“调剂”的尝试和努力最终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晚年的王世贞鉴于格调诗学的粗豪嚣肆,而更倾心于吴诗的婉约清丽,而这也恰恰证明了吴声文化传统的生命活力。更为显著的是,王世贞尽管加盟复古诗学,“毕竟非历下一流人”,[3](《丁集中》“袁庶子宗道”,P566)诗文创作从未脱离其文化归属。在七子诗学风靡的时代,吴人多能谨小慎微地保护吴地文化。领袖人物王世贞如此,而王穉登、钱谦益则公然与齐风抗衡。吴人方子服,诗宗七子,遂遭遇王穉登的责难。钱谦益向以著名学者知名,他对于吴人学北即深表反感,尤其对黄省曾(字勉之)、黄鲁曾(字得之)兄弟之心折北学尤多不满:“国初以来,吴中文学,历有源流。自黄勉之兄弟,心折于北地,降志以从之,而吴中始有北学。”[3](《丁集上》“皇甫佥事涍”,P412)直面谴责“勉之倾向北学”,“识者哂之”。[3](《丙集》“黄举人省曾”,P321)甚而讥刺徐祯卿加盟七子后“有‘邯郸学步’之诮”。[3](《丙集》“徐博士祯卿”,P301)显然,钱谦益的批评在于其强烈的文化情感和地方文化保护意识。 尽管痛责吴人学北的文化背叛,但钱谦益对于吴诗的靡丽浮华亦有所不满,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吴声固有的缺憾,《列朝诗集》中即随处可见其潜在的吴文化批评。但文化的使命感使得钱谦益仍然鼓其余力推扬吴诗、打造吴学精神。他抨击王世贞、冯时可等吴人主张以北郡诗学的格调高古、气骨舒张来调“剂”吴声之弊的选择。钱谦益认为:吴声正在遭遇被齐、楚文化所颠覆和吞噬的空前灾难。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恢复、发扬吴文化精神,有意识地突出吴声传统,成为钱谦益精心编辑《列朝诗集》的主要动机。他在筛选评释“列朝”经典的工作上,努力创立出新的诗学准则。他深信,经由他精心选择而被列入诗集的作品,都将被视为今后的诗学典范。更为重要的是,以诗坛耆宿的影响,《列朝诗集》以吴声数量的绝对优势宣告了新诗学的范畴。它展示了一种文化传统是如何地在其所蕴育的文人身上运作出巨大的生命能量,同时也体现了地域文人是怎样试图改变并影响这个文化传统。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建构出一种在传统和个人之间强大的文化凝聚力,既让读者认识到一个诗人诗风形成的文化因由,同时也说明文化对于塑造文人集体性格和集体文风的重要性,体现了钱谦益对吴文化的竭力回护。是以,《列朝诗集》编纂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向世人展示明诗经典,而且还代表了诗坛宿老的心声:为推广吴声而发起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他试图经营一场弘扬吴文化的伟大事业,并认为自己负有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搜集“故明一代文人之集,就其诗而品骘之”[3](序,卷首)的结果是貌似公平的评论下隐含了对吴声的鼎力推扬。显然,《列朝诗集》证明了钱谦益的文化敏悟。他认定,就文学的影响力和文化的感染力而言,吴诗吴文绝不亚于齐、楚。总体看,其所选列朝诗人,在为之“小传”时的详细和所选吴人之多即是明证,其凸显“吴”文化的诗论不自觉地留下痕迹。 尽管钱谦益屡屡表白编辑《列朝诗集》旨在保存文献而不寓褒贬的目的,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发现其诗学观的地方文化意识的影响。钱谦益叙述明代诗史时夹杂着深重的门户之见,他对前后七子和竟陵诗学的激烈抨击都与其“吾吴”身份意识和吴声地域观念密切相关。也正由于此,《列朝诗集》遭遇其当代及后世的普遍攻击:朱彝尊谓其“多主门户之见”,[34](《跋名迹录》,《曝书亭集》卷四十三,P481)曾燠言其“挟门户之见,而肆其雌黄,南北分歧,是非倒置”,[21](曾燠《静志居诗话序》,P2)四库馆臣则严责其“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黑白混淆,无复公论”。[8](《〈明诗综〉提要》),卷一九〇“集部·总集类五”) 此外,许多吴人从文化的地域性的视角论证吴声存在的合理性。王穉登《与方子服论诗书》述及李梦阳与徐祯卿不同诗风的根源在于:“盖李君之才,产于北郡,其地土厚水深,其民庄重质直,其诗发扬蹈厉。吾吴土风清嘉,民生韶俊,其诗亦冲和蕴藉。政自不能一律齐也。”[33](P4812)他认为,不同地域水土风俗不同,造就了不同气质的人群,人之性格与地域习俗相对应,文化的多元使得文学不可能也没必要归于一统。王世贞《亟野诗集序》“燕、赵之音,相率为悲歌慷慨,秦音则皦劲扬厉,吴音则柔靡清嘉”之评亦基于南北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而致南北文学风貌之不同,同时,他们都表达了文化不必整齐划一的宏观的地域识见。吴声温弱,在其时虽不能振臂高呼,群起响应,不足以掀起抗击齐气、楚风的文学浪潮,但柔丽平静、清丽和婉作为吴文化的精髓,却广泛地体现于文学、绘画、书法等各方面,而后者更引领了晚明文化艺术的众芳争妍,多姿多彩。 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决非轻易地被改变或同化。相对于齐气、楚风,吴声——在此起彼伏的明代诗学潮流中,其声音十分微弱,在齐、楚交互称霸的明中后期诗坛上,几乎被置于文化的边缘,甚至根本未能引起学界的关注——没有谁将吴声作为一种独立的特色文化加以审视。直到清初,诗坛上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齐、楚的孰优孰劣。尽管吴声所经历的“认同”过程至为崎岖,但作为一种长期形成的地域色彩极浓的地方文化,她的恒久存在和对晚明士风的巨大影响却证明了文化潜在的生命力度;吴声的文化影响虽然不逾东南,然而其抵制主流诗学的努力,又证明了吴声传统的文化深度。而齐、楚、吴三种文化相斥相融的命运,说明文化多元的丰富景观。亦唯其多元,明代诗坛方“霞蔚云蒸”。[28](卷二十九) 注释: ①按:费锡璜所谓“中原之诗”指以河南人为主的前七子和以齐鲁人为主的后七子。由于前后七子诗学主张、审美风格相一致,创作上倡导雄浑大雅之气。文章为了论述的连贯清晰,从审美趋向上将前七子的“中原之诗”、河朔之风并归入后七子的“齐气”。标签:钱谦益论文; 吴文化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王世贞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李梦阳论文; 徐祯卿论文; 中原论文; 复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