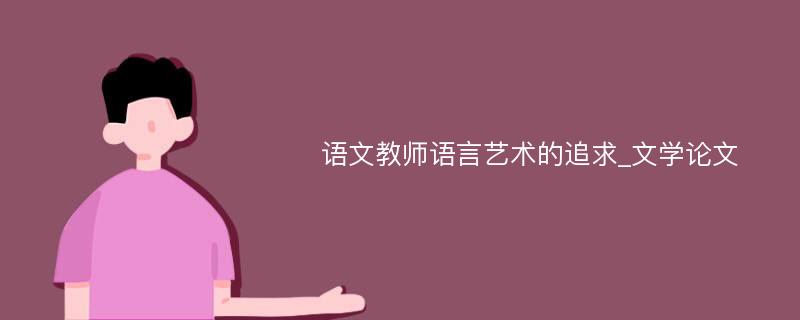
语文教师语言艺术的追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教师论文,语言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语言运用的角度为语文教师定位的话,我想语文教师应该是语言艺术家。记得有人说过,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他的语言应具有诗歌语言的精炼,小说语言的传神,戏剧语言的耐得住咀嚼,学术语言的深沉、丝丝入扣,演说语言的雄辩。这个要求看上去近乎苛刻,却也为我们描绘出语文教师在语言艺术追求方面的美好境界。
一
早年在大学的时候,一位老师回忆闻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楚辞》时的情景:黄昏,幽暗的灯光下,闻先生着了一件黑布长衫,夹着一包书,徐徐走上讲台,放下书包,沉稳地道出:“痛饮酒读《离骚》,方真名士!”整个课堂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大家沉浸于屈原诗歌的慷慨悲凉的境界之中。闻一多是诗人、学者,长于戏剧表演,他以诗人的浓烈的感情,诗歌的语言的精炼,学者的深沉,戏剧的灯光效果、着装、形体动作——肢体语言,成功地营造了悲剧性的氛围。
语文教学承担着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任务,而语文素养是一个人的听说读写诸方面能力的综合表现。说到底,语文学习无不是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学习和操练。细细打量一番吧,从阅读教学层面来看,语文课本里各种类型的课文指涉各种文体,包容了不同时代的众多作家的作品。学习课文,教师主要是借助于自己的语言为手段,破解作品,帮助学生进入作品,进入作家的内心,学习他们是怎样用语言成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解。帮助学生学会如何过滤信息、提炼信息、综合信息、有效地储存信息,从而形成属于自己的语文知识系统。从写作教学层面来看,教师着眼于怎样从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吸取有效信息,梳理加工,提炼主题,找到组合材料的线索,运用合适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就是怎样把自己的心理语言外化,用文字固定下来。
语文教师,一方面用语言作为重要手段去启示引导学生学习语文;一方面也是运用自己艺术化的语言向学生示范。语文教师的教学语言,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的语音、语调、语气、语速,乃至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启发和辩驳的技巧都会在学生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影响学生语言使用能力的形成和发展。
语文教师的语言艺术的使用是智慧,是素养,是灵性,是自我人格精神的体现,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技巧层面上来审视它。
二
语文教师语言艺术水平的提高,似乎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一方面,一些优秀教师语言艺术运用的成功经验,得不到应有的总结、提升和推广;一方面,不少教师不讲究教学语言的使用,波澜不惊,给学生带不来一点惊奇,一点新鲜感。
语文教师教学语言使用的问题,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种是程式化。从课堂起始,指导阅读,启发提问,引发讨论,回答问题,都是一个路数,一样的话语方式。课课如此,除了课文内容的变化以外。比如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并没有一个指向,请大家先把课文看一篇,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提出来;在学生回答问题以后,不管质量高低,对与不对,都是说“很好”“有意思”。而不是从话语方式、语气,表示出教师对于问题的提出或回答者的鼓励和启示。
一种是浅表化。教师的话语是从教学参考书、作品分析的文章中搬下来的,教师只是提供了一些现成的结论。比如学习食指的《相信未来》的第一段: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炉灰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教师依据参考书把“蜘蛛网”“炉台”“灰烬的余烟”“美丽的雪花”之类的词简单地教给学生,还要求学生标记在课本上。如“蜘蛛网”喻指政治黑暗的文革时代,“炉台”喻指作者自己的生活状况,“灰烬的余烟”喻指“生活的艰辛”,“美丽的雪花”喻指“美好的希望”,等等。从知识传授的角度看,似乎没什么错误,但是教师没有引导学生走进作品,没有走进作者的心灵,对学生诗歌欣赏能力的提高没有起到作用。如果想要学生在读诗和心灵上真正有所得益,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真正有所提高,教师必须精心设计话语环境,运用合适的话语方式,要学生自己得出结论。
一种是低幼化或者成人化。也就是不看教学对象的年龄特征、心理特征。比如教学对象已经是初中生了,教师还像和幼儿园、小学生讲课那样,说:“某老师和你们讲”“某老师认为……”再如教师在介绍作品或作者时旁征博引讲了别人的一些评价,不少是从诗话、词话之中来,话语方式是文言,即使是成人,有相当文学素养的,也难一下子弄明白,何况是中学生。这种情况在多媒体教学使用后,显得更为普遍,屏幕上,黑压压一大片,教师读一遍,用古人的话语代替自己的话语。
三
语文教师在教学语言使用上的这些问题,其形成的原因,除了由于对教学语言运用的成功与否与教学效果好坏的关系认识不足以外,还涉及到教师的责任感、教育观念和业务水平等方面。下面逐一予以分析,并且探究解决的办法。
其一,教师的责任感不强,缺乏精益求精的精神。一个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上好每一堂语文课。从话语使用的角度看,上课前,把自己在课堂里要讲的话在自己头脑中过滤一番,一些重要的话语,如启发谈话更要精心设计。
比如语文教育家于漪老师讲朱自清的《春》时,用这样的一段话开场:“我们一提到春啊,眼前就仿佛展现出阳光明媚、东风浩荡、绿满天下的美丽景色!所以古往今来,很多诗人就曾经用彩笔来描绘春天美丽的景色。”这段话,绘声绘色,有景有情,生动形象,一下子把学生从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春日感受引入到朱自清笔下的春。再如有位教师讲鲁迅先生的《雪》,谈到江南雪的特点“滋润、美艳”时。他说“滋润”是暗示雪中饱含着水分,没有被冻结,很湿润,摸上去软绵绵的,说明江南的雪天并不太冷;“美艳”是说在阳光照耀下,雪晶莹发光,这是因为雪里饱含着水分,是由雪的质地所决定的。接下去结合后面的描述来分析,“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信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指出前一个比喻是说,那江南的雪是透露着春的信息的报春的使者。后一个比喻是说,江南的雪像极壮健少女的皮肤,比喻新颖,奇妙,使江南的雪更为形象,几乎有了生命。文章从视觉和触觉、心理感受——联想多方面来写雪,显示出作者对于故乡的怀念之情。这位教师将文本中已经很形象的词语再度予以阐释,使之更具体可感,捉摸出作者的心思。这位讲课者把解词、修辞知识的讲授融化在课文的讲解中,让学生自然地去领略。
其二,教育观念的滞后或认识上的不全面。当前语文教学提倡对话、交流和合作学习,其目的是要通过对话质疑、辩诘,把思考引向深入,它是一种形成和发展学生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有的教师简单地认为,对话就是话语交流,光图表面热闹,形成了你说、我说、大家说的局面,教师就来了个无偏无颇,一味肯定。其实对话理论,不能简单理解。正如英国学者戴维·伯姆所说:“对话是一个多层面的过程,远远超过了传统意义上所指的谈话和交流的范畴。它旨在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探索人类广泛的体验过程,从我们固守的价值与信仰,到人类情感的本质与作用;从我们内心思维过程的模式,到人类记忆的功能;从社会文化的传递,到历史神话传说的继承,乃至于最终涉及到人类大脑每时每瞬构造体验的神经生理学方式。”(《论对话》第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说,对话的本质意义在于探究人类的思维方式,就语文教学而言,就是要通过对话切入文本,消化文本,进入作者的心灵。教师要精心组织对话,一方面,充分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设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一方面,根据教学要求设想怎样引导学生去讨论与课文密切相关的问题,以及怎样把讨论引向深入。下面看一段语文教育家洪宗礼老师讲授《阿Q正传》的课堂实录:
洪宗礼老师不紧不慢地问学生:“明朝末年,有个吊死在煤山上的皇帝,说说看,他是谁?”
“崇祯。”
“怎么写?”洪老师追问。
“‘崇’是‘崇高’的‘崇’,‘祯’是‘礻’旁加个‘忠贞’的‘贞’。”
洪老师板书了“崇祯”二字后,又追问:“你们都知道明朝末年有个崇祯皇帝?”
“都知道。”
“早知道了。”
洪老师忽然幽默地说:“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学的《阿Q正传》里,却又冒出了个‘崇正’(板书:崇正)皇帝来了!同学们看一看课文的第3自然段。”
课文上写着“……穿着崇正皇帝的素”。
奇了,怎么又冒出个“崇正”来了呢?
“会不会是笔误呢?鲁迅先生也是人,不是神,他也难免有笔误……”
“不可能有这样的笔误吧。鲁迅先生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就是第一次笔误了,那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总会发现、纠正的。”
“明朝末年的皇帝是‘崇祯’,这是历史常识,几乎尽人皆知。鲁迅先生不可能把‘崇祯’误写成‘崇正’。”
“会不会是印刷排版中的差误呢?”
“你的意见有两处站不住脚。仅凭猜测来解决问题,如同在沙滩上盖房子,这站不住脚;二是书下注释明确指出,‘崇正’就是‘崇祯’,可见,这不是什么排版的差错。”
“艺术不等于历史。《阿Q正传》中的‘崇正’,不等于历史上的‘崇祯’。”
“艺术真实固然不等于历史真实,但是,艺术真实必须符合历史真实,而不能违背历史真实。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等,都是二者完美结合的典范……”
洪老师面带微笑地插了一句:“能不能从后文用‘柿油党’来代‘自由党’中得到一点启发呢?”
学生举手发言:“我以为,鲁迅先生把‘崇祯’写成‘崇正’,很可能是有深意的。课文里用‘柿油党’去代替‘自由党’,讽刺艺术的效果很好。我想,用‘崇正’来代替‘崇祯’,至少也是对封建帝王的一种讥讽和嘲弄……”
洪老师听着同学们热烈的议论,笑着说:“鲁迅先生为什么要把‘崇祯皇帝’写成‘崇正皇帝’,这个问题,课外可以更深入地去读书研究。现在,我要说的是,像《阿Q正传》这样的名篇名著,它们都是一座座充满奥秘和魅力的艺术殿堂,我们对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课堂里读几遍,问几个问题就能‘一次完成’的,需要我们去反复研读,反复探索。”说着,他转过身,板书了叶圣陶先生的读书名言:一字不宜忽,语语悟其神。
洪宗礼老师从一个极为细微的地方入手,通过谈论让学生领略出鲁迅小说幽默风趣的特色。一层又一层的引导,显示出教师组织对话用心的细密。
其三,教师本身素养方面的缺陷。前面一部分中话及教师教学语言的程式化问题中提到《相信未来》开头部分的教学。如果是一个文学素养较高的教师,可以从介绍作者食指的另一篇代表作《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入手。1968年12月16日作者登上北京去山西汾阳的列车,诗是在颠簸的列车上写的。食指从那时起就开始了多年的知青生活,他自己体验着,也亲眼见到农民们的极端贫困的生活。接下去可以绘声绘色地介绍当时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厨房的布置。让学生从生活中的形象——炉台、烧桔梗留下的灰烬,看诗人是怎样将主观的情思投射到外物上去,从而构成意象,再怎样把意象组合起来,形成诗的意境的。教师可以启发学生注意作者用词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改成直说,该是怎样,并要学生加以比较。比如“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蜘蛛网罩住了炉台是一种生物行为,没有什么感情掺杂在其中,更不是“查封”之类的暴力行动,这些带感情的词语是从作者眼中看出来的。灰烬的余烟缭绕着缈然不散,和人的叹息在节奏上有某些类似之处,作者化视觉形象为听觉形象,写出了陋室的惨淡,诗歌抒情主人公的窘困。但是“我”在这种情景之下,面对极权统治,面对困境,毫不措意。“我”将灰白色的炉灰扒到地上,在它之上用洁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是倾吐自己对令人窒息环境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并没有打算用什么来象征什么。如果设定一些形象作为象征物来对应一些政治概念,怎么能写出诗来?
语文教师教学语言艺术性的高低,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也是教师本身素养的外在表现,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