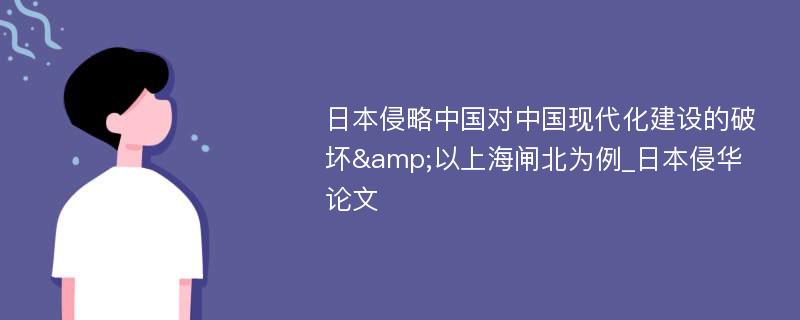
日本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以上海闸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闸北论文,为例论文,现代化建设论文,上海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内战不断、战乱不息的情况下,仍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经济建设。因此在到1937年的十年里,全国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东部的城市化也取得了不小进步。然而,对华觊觎已久的日本,不容中国有片刻发展之余裕。在一·二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两次惨遭日军炮火蹂躏,尤其是闸北,两次淞沪之役均为中日两国鏖战前线,数十年的建设成果顿时化为乌有,所受创伤之重为全市之最,八一三后境内建筑更是十不存九。除上海外,东部其他城市也因日军的轰炸而遭受重创,大量工商业单位被破坏,在随后的占领期间,日军又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本文拟以闸北为例,从战前与战后的巨变来探讨日本侵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破坏。
一、1900—1937年的闸北现代化建设
闸北位于上海北部,其地名与苏州河(旧称吴淞江)上的两座石闸① 息息相关。苏州河系上海与苏、锡等地往来便道,来往船只一直较多,于是“自吴淞江通行小轮,于是新闸、老闸之间,亦见起色”。② 不过,1900年之前,除苏州河北岸一带有些市集外,闸北基本上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然而上海开埠租界发展不可避免地对闸北“荒僻冷落,人迹罕至”③ 的原始面貌产生冲击。上海开埠后,整个城市便以租界(尤其是原英租界部分)为发展源,并沿黄浦江北上,呈纵、横两面拓展。因此,闸北的发展实质上也与上海城市范围向北拓展关系密切。
租界自建立之初便不断进行扩张,到1900年时,闸北东、西两面与租界毗邻,南面隔苏州河也与租界相望,因此实际上三面被租界包围,随时有被侵吞之虞。为了不使闸北被租界侵吞,1900年4月,粤商陈绍昌等联合地方绅商,筹集股款,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拟于新闸浜北二十七保十一图(今铁路上海新客站南)地方建造桥梁,兴筑沿河马路,承办一切事宜”。④ 在得到允许后,他们便在闸北自辟商埠,创办了“闸北工程总局”。之后,闸北在行政沿革上虽屡有变动,但均未对其城市化建设造成太大影响。
交通近代化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前导,⑤ 时人谓“市面与交通有密切之关系”。⑥ 自闸北工程总局始,开辟道路成了建设闸北的首要任务。首先修筑的是东部的南北干道——宝山路,接着又修筑了西部南北走向的干道——新大桥路和新闸桥路。后来,为了将这几条干道连接起来,人们又先后在新大桥路与新闸桥路之间修筑了海昌路,在新闸桥路和宝山路之间修筑了南、北川虹路,在宝山路和北四川路之间修筑了宝兴路。⑦ 这样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闸北道路的系统脉络已基本形成。民国之后,主要是沿宝山路的两侧,修建了宝昌路、中州路、虬江路、宝源路、交通路等马路。这些马路的修筑不但加强了闸北内部区域的交通联系,还基本解决了其内外交通问题。
闸北的吴淞铁路虽开了中国铁路建设之先河,但发展却历经坎坷,⑧ 直到1898年10月才重新步入正轨。1903年,它并入沪宁铁路,并另建新站,取名淞沪车站。1908年底沪宁铁路全线通车,次年7月又在宝山路、界路(今天日东路)西北侧筑沪宁线新上海站。开站伊始,日到发车10对,运送旅客1000多人次。1916年后日接送旅客更达近万人次。⑨ 随着旅客的增加,商店、旅馆、饭店、银行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车站周围不断出现。到1930年,有较大商店86家,其中服务业38家、粮食业11家、鞋帽业11家、家品业7家、烟糖业4家、副食品业9家、百货业2家、饮食业2家,初步形成了“买、带、捎”的消费习俗,而该地区本身也位列闸北四大街市之首。⑩
除铁路交通外,1920年太仓籍旅沪人士洪伯言、项惠卿等兴办全国首条商办长途客运线,随着锡沪公路的竣工,锡沪长途汽车公司等公路运输公司也应运而生。(11) 这些公路交通和铁路交通一起奠定了闸北作为上海“北大门”的交通枢纽地位。
工厂和商店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一条条公路和铁路的周围。甲午战争后,列强取得了在华投资设厂的特权,开始对华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闸北的兴起可谓“正逢其时”。相较于老城厢的南市,闸北如同一张白纸,空地较多,地价便宜,兼有苏州河的水运及沪宁、淞沪铁路的陆运之便,大量资本得以迅速进入闸北,不数年间许多工厂已在闸北的大地上拔地而起了。闸北的工业以轻工业为主,主要有缫丝厂、布厂、碾米厂、制革厂、印刷厂、风琴制造厂、肥皂公司、面粉公司等,多分布在宝山路、新大桥路、新闸桥路、虬江路、新民路、宝通路等处。(12)
大量工厂的出现必然对水电的供应有所要求。1911年9月,为抵制外商势力的渗透,经两江总督张人骏批准,由上海著名绅商李平书、蔡伯浩等人筹办的闸北水电公司竣工。它的营业范围南至租界,北达江湾,东至沙泾港路,西达潭子湾一带,每日最高供水量30万加仑,供应人口10万,电灯500盏,自此解决了闸北工业、企业、居民和附近区域的水电供应。(13) 硬件设施得到了改善,加之外部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闸北的民族资本发展极其迅速,被人誉为“华界工厂发源之大本营”。据统计,到30年代初,闸北有较大工厂256家,为全市的45.23%。行业分布于缫丝、化工、制药、印刷、粮油加工、机器制造、玻璃和搪瓷等20多个领域。(14)
在工业发展的同时,闸北的商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1930年代初,闸北已成为上海华界商业的中心之一。当时,新闸路桥以北一带,日到米船超过百艘,沿街米行、米店接近百家,是上海著名米业北市场所在地。大统路开设各类商店多达50余家,成为闸北四大街市之一,有“闸北南京路”之称。此外,光复路的竹木行,新民路的皮草市场,宝山路一带的饮食服务业等均是全市闻名的。(15)
在众多实业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除上述的闸北水电公司外,便是商务印书馆了。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原址设在江西路德昌里,后随着其业务的不断扩大,1904年在宝山路东侧购地八十余亩,兴建了总务所、印刷所、编译所等等。1924年,厂方又修建了号称“东亚闻名文化宝库”、“亚洲第一图书馆”的东方图书馆(16)。当时,商务印书馆名副其实地是上海乃至全国重要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和最大出版印刷企业。(17) 馆内“各种设备向极完善。其印刷机器之应有尽有,在远东尤无其匹。机器重要者有滚筒机、胶版机、米利机、铝版机、大号自动装钉机、自动切书机、世界大号照相机等,总数达一千二百多架之多”。(18) 商务印书馆机器的种类和质量在远东也首屈一指,印刷技术则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还自行制造各种铅字、铜模、制版、油墨、胶棍、机械以及仪器、标本、文具等教育用品,其提供各地的文化教育用品约占全国总量的75%。(19) 此外,商务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是中国当时中小学教材的主要提供者。从晚清兴办新学到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课程标准,商务版教材均是一再革新,不断再版,风行全国。据统计,从1902年到1930年,商务版的教科书、词典工具书、中外名著、古籍及自办期刊8039种,18708册(20),出版量居全国之首。
随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兴起,闸北各项社会事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并成为上海华界近代文化中心之一。据统计,截止1931年,闸北共办过小学160余所,中学40余所,各类职业教育学校20余所和高等学校10余所。(21) 其中著名的有爱国女学、南洋女子师范学校、市北公学(后改市北中学)、中国体操学校和上海大学等。除学校外,闸北先后有编辑、出版、发行单位74家,出版报刊25种,图书馆6座。有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林记更新舞台等大小剧场、电影院11座。此外,境内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也有所发展。一些慈善团体施诊、施药、施米、施粥、施棺,还创办时疫医院,救治贫民,相继建立了公、私立医院40所。(22)
概括闸北发展的轨迹是交通先行,随之带动工商业兴起,最后是社会事业的勃兴。当时,人们将闸北及与其几乎同时兴起的虹口并称“沪北”。(23)
二、日军对闸北的破坏
两次淞沪抗战,闸北均首当其冲,战争对闸北的破坏严重,使其三十年之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1932年1月29日,日机在发动侵略事变的第二天便对闸北进行狂轰滥炸,并以商务印书馆暗藏十九路军为由,将其炸毁。据《申报》记载:
至(上午)十一时许,商务印书馆总厂竟亦着弹,适落天井内,当即爆烈,继即发火,而当时厂内各工人早已走避。至救火车因在战事区域内,无从施救,乃只得任其延烧。一时火光烛天,照及全市,尤以纸类堆积,延烧更易。片刻间,编辑部即遭波及,所装备之各种印刷机器,全部烧坏,焚余纸灰,飞达数里以外,即本馆左右,均有拾得,可见当时火势之一斑。(24)
这场大火直烧到当日下午五时尚未完全熄灭,而商务总厂房屋在下午三时便已全部倒塌。大火使商务“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25)
商务总厂被炸毁后,中国各界在强烈谴责日本这一野蛮行径的同时,对商务总厂的被毁,无不痛心不已。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1日,坐落在商务总厂对面的东方图书馆突然起火,(26) 大火直至下午二时始被扑灭,其馆藏的大量珍贵图书及中外杂志报章等均被付之一炬。(27)
东方图书馆的前身是涵芬楼,其馆藏的大量珍贵图书是张元济耗费二十多年光阴悉心搜集而得。到1920年代初,“(涵芬楼)所储书籍达数十万册,不当自祕(秘)。乃决议别建书楼,移此藏之,以原备编辑参考之书籍并供社会公众阅览”。(28) 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资十一万余两,在其总厂对面的宝山路建了一座五层的钢骨水泥大厦,取名东方图书馆。(29) 截止1931年,馆中有普通中文书26.8万余册,外国文书东、西文合计8万余册,图表照片5000余种。另有古籍四部善本约3745种,35083册。(30) 全国22省地方志2641种,25682册,其中元本2种,明本139种。全国府厅州县志1753种,占总数2081种的84%。馆藏的中外杂志报章不但种类齐全,很多如荷兰的《通报》、英国的《学报》、德国的《李比希化学杂志》(初版)等均为难得一见的孤本。(31)
当时正值中日双方在闸北酣斗之时,未及对商务总厂的损失进行调查,直到三月上旬,调查工作才告完成。
总厂中第一、第二两印刷所为两层楼,长屋两大排,中有机器数百架,为本馆主要印刷部分,均与房屋同归于尽。第三印刷所为三层大厦,系墨色石印部分,英文排版部分亦在其中,均焚毁无余。第四印刷所为四层大厦,二、三两层置彩印精印机器数十架,上层为全公司总务处所在地,下层为营业部所在地,均付一炬。其他如标本模型制造部、制油墨部,以及三层大厦置有装切机器数十架之装切部等亦无不全毁。
又书籍及纸张等栈房之大厦及所存书籍纸张均焚毁一空,纸灰深可没膝。仪器文具等栈房亦如之。藏版部系三层巨厦,被焚后所藏铜锌铅等版均熔成流质,溢出墙外,凝成片块。他如储电房、自来水塔、木工部、出版科、寄售股等房屋无不烧成瓦砾之场。其残留者仅机器修理部、烧版部及疗病房数处而已。
至于总厂以外之东方图书馆、编译所及其附设之各杂志社函授学社、尚公小学,以及厂外书栈房等,均仅余断壁颓垣与纸灰瓦砾。(32)
商务总厂的经济损失共达1633万银元。(33) 这场浩劫不仅使商务总厂元气大伤,对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也造成了巨大冲击。战前商务的印刷技术领先全国,但经过这场浩劫,它只得将大量印刷业务交给技术水平较低的小厂家承包。东方图书馆被焚前,从事编译工作的专家曾达300人,之后仅剩十名负责审理外稿的编译人员。(34)
一·二八期间,日军在闸北暴虐28天,给闸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包括商务印书馆在内,境内共有103条里弄街坊、数万间房屋被毁;(35) 商号损失4204家,3347.704189万元;工厂损失841家(其中丝业工厂数从77家降至27家,下降了64%),(36) 5199.096932万元;住户损失3777.802012万元;房产损失576.009840万元;学校损失206.846550万元;公团损失126.882602万元;寺庵损失14.530000万元;人员伤亡中,死亡者876人,受伤者469人,失踪者720人,其他17963人。当时全市共损失1.9460636281亿元,闸北一地的损失即达1.3248872125亿元,占了68.08%。(37)
闸北虽遭受了重创,但并未就此衰败下去。《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闸北立刻开始了复兴工作。同年5月21日,铁路即恢复通车,许多被毁的工商企业、医院、学校等也相继重新建设。到1936年,闸北已登记工厂574家,占全市1687家工厂的34.02%。八·一三前夕,境内有大小公、私立医院39所。(38)
然而在八·一三中,经济刚有起色的闸北再次成了日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日军不但利用大炮集中轰击,还派出大批飞机对战略要地进行重点轰炸。从市中心的高处望去,可见闸北整日浓烟遮日,火光冲天,触目惊心。北火车站在日本飞机的反复轰炸下,“到处是累累的战痕,(月台)已经被炸成一堆残缺的砖土,像一个被毁了的大坟墓”。(39) 10月末,日军又对四行仓库周边的蒙古路、满洲路(今晋元路)、国庆路、乌镇路、大统路、新疆路及新民路(今天日中路)一带残存的民房,实行“焦土政策”。经过这次毁坏,从泥城桥一侧向西、向北望去,可一直看到苏州河叉袋角(今长寿路桥周边),真可谓“赤地千里”。同时,日军又向虬江路、宝山路、永兴路及鸿兴路等地区再次投下大批燃烧弹,烈火熊熊彻夜不熄,使闸北又整整“大火三日”。(40) 据统计,八·一三期间,日军共向闸北发起进攻136次,炮轰48次,飞机轰炸98次。(41) 经过80余日的狂轰滥炸,“闸北已成一片焦土,其破坏景状,几不能以笔墨描写,炮弹与炸弹破坏之遗迹,到处皆是,举目四瞩,如地震后之景状”。(42) 全区95%以上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除一处“三层楼”(43) 外,几乎找不到完好如初的建筑。(44) 日军占领闸北后,还派出各小分队在街上挨户搜索、纵火焚烧,打开一座座空屋,置入易燃的化学品,点火烧房,导致闸北到处都有熊熊大火。有时人谓:“日兵三五成群的来往,撬开房屋的门,入内抢劫。……火焰从乌镇路桥一直伸入闸北的内腹,形成一条四五里长的火墙。……火光照着已经烧毁的房屋,看来有如死人的枯骨。”(45) 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旋即组织“清扫班”,每天强迫大批民工将闸北等地物资运回日本,仅钢材就超过10万吨。(46) 一·二八中遭受重创的闸北丝业,八·一三中再遭灭顶性打击,35家工厂中竟被炸毁31家,损失率高达90%,丝车损失6060部,金额达1亿余元。(47)
战前,闸北的繁华地带主要集中在东北、西南两处。一·二八期间,东北部受到重创,八·一三期间日军又集中对西南部进行轰炸,(48) 这就使闸北三十年的建设成就荡然无存。而战争又导致居民的大量逃亡,到1938年初,境内居民竟仅余120户,580余口。(49) 1938年1月30日是农历春节,闸北却是“景象沉寂悲凄,恍若死城”(50)。
三、现代化进程的中断及闸北的沉沦
八·一三期间,日军在闸北施虐长达80天之久,战争的破坏使之元气丧失殆尽。日军占领闸北后,拉起了很多铁丝网,将1300余亩的土地划为军用地,禁止居民进入。(51) 这些措施对本已遭灭顶性打击的闸北经济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
战争使闸北全境几乎变成一片废墟,而居民又十不存九,这使得当时的日伪当局连税收都成问题。因此,1938年后浦东(52) 伪市政公署为博取日人欢心,以图地位巩固,也有所谓恢复闸北繁荣的计划。但一则恢复计划所需经费浩大,而伪市政公署根本是捉襟见肘;二来他们缺乏长久的周详计划,仅是搭盖了一些供灾民居住的小棚而已。当时的《文汇报》即指出这是“缘木求鱼,决难实现”。(53) 要说该计划的唯一成效便是吸引了因“抗战初起遭逢变乱,家室被摧毁于炮火,流离露宿风栖,备受艰辛”(54) 的居民及很多像苏北人这样的“贫苦不堪之辈”(55) 来沪的移民纷纷迁入。
与苏南、浙江和广东等地的人来闸北进行投资所不同,对这些人而言,闸北是他们苟延残喘的藏身之窟。他们纷纷迁入的结果是使闸北涌现出大量的棚户区。大统路在1930年代以前是闸北四大街市之一,素有“闸北南京路”之美称,在兵燹之下成了一片废墟,之后更成了著名的棚户区。其他如番瓜弄等棚户区也均是在这一时期涌现的。战前闸北的大部分街道两侧是三层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56) 1927年时全区已有里坊弄590条(57)。而在两次淞沪抗战后,有388条里坊弄被毁(其中有部分毁后重建再被毁),(58) 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大量棚户的出现。1946年,市参议会将因抗战而未能实现的大上海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将繁华闸北作为大上海之初步计划案。(59) 该计划拟订将浙江北路西藏北路以西、苏州河新疆路以北、京沪铁路以南一带共1.685平方千米为闸北西区,该地区原则上被定为现代化之住宅区域,内分七个邻里单位,所有道路及地段之布置均按照既定计划实行。(60) 参议会同时还规定,“该地区为棚屋禁建区域,嗣后不准搭建棚屋以期顺利推进各项建设”。(61) 而实际上,该地区因战争“繁华屋舍,尽成废墟,大部分土地、经界亦多湮灭。胜利后,所有权人无法管业使用,迭起纠纷。棚户占据日盛,取缔发生困难”。经调查,整个闸北西区有草棚7930间,瓦棚7045间,双层棚屋1970间,而钢骨水泥结构的楼房三层的有两宅,四层仅一宅而已。一方面,大量棚户的存在给拆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仅仅是棚屋的拆迁补偿费便估算了很久;另一方面,内战烽火燃起后,全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力将该计划付诸实施。因此,该计划直到1948年10月末依旧停留在书面上。
与之相对照的是,闸北的棚户蔓延速度极快。到解放前夕,闸北约6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成了随处可见棚屋、草屋、船房及“滚地龙”的贫民窟。据统计,全区100户以上聚居的棚户集中点共120余处,居民约7万户,23万余人,(62) 其西部地区的棚户比例更大,达73.7%。(63) 另一方面,当时闸北共有工厂42家,其中1930年以前所建的有13家,但多一蹶不振;1938年以后新建的有29家,但其中小作坊、小工场便有23家,全区可称得上有规模的企业仅7家。(64) 战时40余所中、小学校被炸毁。到抗战胜利后全区仅剩中学6所(全市121所,占4.9%),小学43所(全市786所,占5.5%)。(65)
昔日“华界自治的典范”成了经济的“下只角”,日军的炮火一方面使闸北的工商企业除小部分内迁或迁往租界外,几乎全部遭毁灭,幸存下来的也被他们组织的清扫班掳掠一空;另一方面,战争不但破坏了支撑闸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使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达十数万之巨,大量人才、资金流入租界,这些恰恰是支撑闸北发展的“软件”。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以致有人讥讽其是一个“光有躯体”的“赤膊区”。(66) 进入90年代,随着上海城市改造的加速,闸北“棚户王国”的面貌已有所改变。现在,闸北又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日本侵略而制造、涌现出来的棚户至今仍能看到。甚至因为此,闸北在上海“木桶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被认为是一根短木条,不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市平均,还阻碍了全市经济的腾飞。
本文为上海市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T0304)成果之一。
注释:
①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人们在今福建路附近的江面上建一闸,此闸后来被称为“老闸”。后因老闸圮坏,雍正十三年(1735年),人们又在距老闸以西三里之处的吴淞江金家湾(今乌镇路桥西侧,大统路附近)再建一座新闸。该闸建设历时两年,于乾隆二年(1737年)始告竣工,被称为“新闸”。闸北得名即因境域在新闸以北,最初被称为“新闸北”。光绪年间,“闸北”始成为人们的习称,代替了原来的“新闸北”。参见花扬:《闸北的由来及其兴起·灾难·重振》,《闸北文史资料》,第四辑,第28页;祝鹏:《上海市沿革地理》,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②姚公鹤著、恽树珏校:《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7页。
③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上海研究论丛》(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④冯梅椿:《全国首创的地方自治闸北市》,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4年第1期,第4、5页。
⑤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⑥姚公鹤著、恽树珏校:《上海闲话》,第37页。
⑦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上海研究论丛》(2),第105页。
⑧这条铁路即淞沪铁路。1866年,英国公使向清政府提议,希望能允许在淞沪之间修筑一条铁路。虽然清政府并未批准该提议,但英商怡和洋行却擅自组织吴淞铁路道路公司,进行修筑。工程从1874年12月开始,到1876年6月30日第一期(苏州河北岸——江湾徐家花园)工程竣工,7月3日正式通车营业。但铁路的修筑一开始便遭到当地乡绅与民众的反对,而清政府更是因为涉及主权问题,一直与英国进行交涉。8月3日,火车在运行时又不慎轧死一名士兵模样的人。这样一来,“乡民大恐,遂于10月24日在南京议明买断(由清政府花费银28.5万两买断),惟火车由英商铁路公司驶行一年”。参见王继杰:《淞沪铁路通车》,信之、潇明主编:《旧上海社会百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上),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17页。
⑨参见长弓:《上海北火车站追记》,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55、56页。
⑩文兵:《沪北商业中心纪实》,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27页。
(11)参见宋峙、张兆熊:《闸北陆上交通史话》,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51页。
(12)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上海研究论丛》(2),第106页。
(13)冯梅椿:《全国首创的地方自治闸北市》,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7页。
(14)上海市闸北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闸北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5)参见《闸北区志》,第3页;郑祖安:《近代闸北的兴衰》,《上海研究论丛》(2),第106、107页;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10—35页。
(16)《闸北区志》,第1248页。
(17)参见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第4页;《闸北区志》,第1240页。
(18)《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第6页。
(19)《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第5页。
(20)《闸北区志》,第1240页。
(21)《闸北区志》,第3页。
(22)《闸北区志》,第3页。
(23)李天纲:《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24)1932年1月30《申报》。
(25)《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第9页。
(26)东方图书馆被焚的说法历来莫衷一是,“有谓原于日本‘浪人’之纵火,有谓原于总厂余烬之延烧”。1932年2月2日《大公报》报道:“东方图书馆今日(一日)又起火,据该馆人员谈,系日人收买无赖纵火。”1932年2月2日《申报》报道:“该馆附近有煤炭店,因日前总厂被焚之余火未熄,至今晨(一日)七时左右,煤炭店忽然起火,无法灌救,以致延及东方图书馆……”但无论哪种说法,东方图书馆的被焚,日军都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参见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东方图书馆纪略》,1933年发行,第7、11页。
(27)不包括事先寄存于金城银行的5000余册善本。
(28)东方图书馆编:《东方图书馆概况》,1926年3月发行,第3页。
(29)《东方图书馆纪略》,第1页。
(30)这其中包括寄存于金城银行的5000余册善本,但未包括原扬州何氏所藏的4万余册善本。参见《东方图书馆纪略》,第6页。
(31)《东方图书馆纪略》,第2—6页。
(32)《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第31、32页。
(33)《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第36页。但另有统计为2033.0504万银元,参见《闸北区志》第1247页。
(34)参见郭太风:《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上海文教新闻事业罪行述评》,《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35)《闸北区志》,第4页。
(36)闸北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藏:《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大事记》。
(37)《闸北区志》,第1272页。
(38)《闸北区志》,第4页。
(39)周鸣钢:《大上海废墟》,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第三部·第三辑),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3辑,据华美出版公司1938年版影印,第106页。
(40)参见夕阳:《“八·一三”日军在闸北罪行纪实》,钟修身、张丽丽主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峥嵘闸北》,第201、202页。
(41)闸北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藏:《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大事记》。
(42)1937年10月30日《申报》。
(43)“三层楼”位于恒丰路、裕通路西侧,建于1930年,共43幢,系当时闸北西南部惟一的三层高建筑,标志性强,建成后附近居民即称之为“三层楼”,而附近也逐渐成为当时闸北的一个繁荣地段。八一三期间,闸北全区建筑均遭不同程度的毁坏,惟有“三层楼”完好无损,后难民在周围废墟上搭建棚屋,“三层楼”于是成了附近一带地域的习称地名,一直延续至今。参见钱以平编:《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44)《闸北区志》,第5页。
(45)王智意:《闸北在燃烧》,朱作同、梅益主编:《上海一日》(第三部·第三辑),民国丛书第三编第93辑,第77、78页。
(46)《闸北区志》,第31页。
(47)闸北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藏:《闸北区志资料长编·大事记》。
(48)参见《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289—298页。
(49)1938年6月26日《文汇报》。
(50)1938年1月31日《文汇报》。
(51)《闸北区志》,第5页。
(52)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及后来的“淞沪督办公署”,皆以南市、闸北、沪西等处交通不便,而将办公地点设于浦东。参见1938年4月14日《文汇报》。
(53)1938年5月2日《文汇报》。
(54)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09—1—1460。
(55)1938年6月26日《文汇报》。
(56)薛理勇:《上海滩地名掌故》,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365页。
(57)《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77页。
(58)参见《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289—298页。
(59)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09—1—660。
(60)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11—641。
(61)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Q109—1—653。
(62)《上海市闸北区地名志》,第78页。
(63)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A4—2—17。
(64)《上海市工商业概况》,1948年。
(65)《闸北文史资料》,第七辑,第41页。
(66)方中圆:《闸北有北》,1998年9月3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