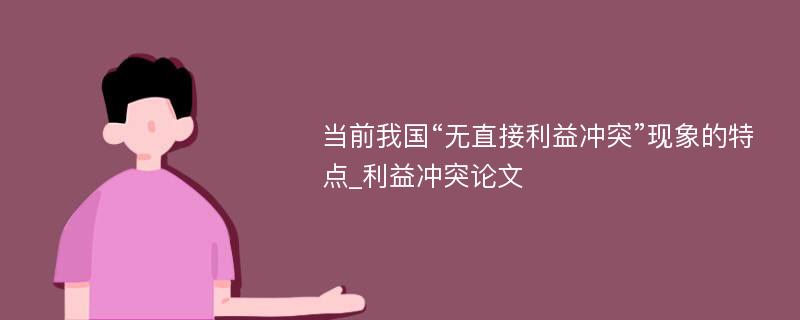
当前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利益冲突论文,特征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刚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决定和部署,主流媒体《瞭望新闻周刊》就在2006年10月17日刊出记者钟玉明、郭奔胜“我国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调查报告,对我国社会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不和谐因素予以披露和探讨,其用意显然是要在舆论层面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互动。报告认为,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迫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出现的冲突。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已随处可见。此文发表之后,诸多媒体便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进行热评深议,这一社会现象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了各方人士的普遍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之所以引起媒体的热评深议和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仅仅在于它早已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更在于它的存在和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导性的话语体系及其所要展开的社会实践,显得格外的不相协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已成为社会冲突的重大病灶,也是当前和谐社会建设所必须突破的障碍,因为它意味着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的下降,意味着社会的不和谐。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能回避包括无直接利益冲突在内的各种社会冲突现象,并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笔者认为,关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特征,可以从3个方面加以概括,并具体表现为9大特征。
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本身来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表现出3个特征:
1.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多与冲突事件本身无关。在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参与者大多和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联,他们之所以参与其中,只是借机发泄一下淤积于心中的不满情绪。这是从“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概念本身的字面含义中,得出的一个比较直观的结论。
2.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多属于拥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源较少的弱势群体。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发现关于拥有资源较多的群体参与到无直接利益冲突之中的相关记录。这是因为拥有资源较多的群体,他们通常拥有常态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或者他们本身直接就是某项政策的制定者。而那些拥有资源较少的个体和群体,恰恰正是因为他们手中的资源匮乏,利益表达渠道堵塞,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甚至受到社会的歧视,基本上没有可靠的办法和能力解决自身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只能“走向社会”,借助于无直接利益冲突这样一种非常态政治参与的途径,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希望以此影响政治过程。
3.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具有了“类意识”或“集团意识”。中国有句俗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俗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国人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但为什么一向素守明哲保身处世哲学的一部分国人,在明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没有受到直接损害的情况下,会卷入到社会冲突的漩涡之中呢?那么,这些卷入社会冲突漩涡的人的行为,是一种瞎搀乎式的行为吗?可以肯定地说,不是。在笔者看来,那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他们之所以会自动卷入到冲突之中,就是因为他们触景生情,感觉到自己曾经经受过、或者可能也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经受类似的不公遭遇,从而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来站队的结果。
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性质上看,它具有三个特征:
1.无直接利益冲突是一种利益冲突。虽然从表面上看,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多与冲突事件本身无关,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仍然是一种导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直接利益冲突强调的仅仅是,社会冲突参与者的利益关系是否“直接”的问题,而不是利益“有无”的问题。美国政治心理学家威廉·F·斯通曾指出,对于政治参与来说,社会利益“是最具有激发力量的一种因素”[1]。因此,尽管国人一向素守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但在关乎自己的利益时,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在无直接利益冲突面前,如果没有利益的关联和驱动,他是不会参与其中的;也因此,无直接利益冲突远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它还带有根本的利益追求的性质。
2.无直接利益冲突表现为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出官民关系出现的恶化与不和谐、不信任趋势。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大多发生在群众与政府公务人员之间,即:群众与党政干部、人民警察、城管等执法人员之间。① 一位网民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发表的留言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官民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说:现在在街上大喊捉小偷没人帮忙,打警察就一大群人过来围观。群众与群众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包括吵架和肢体接触,无故起哄的围观者并不多,只要警察一到场,起哄就马上开始。[2] 再如,有警察明明是正当执法,有人凭空喊一声“警察打人了”,整个局面就立即失控。[3]
3.无直接利益冲突具有利益集团冲突的性质。由于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多或少具有了“类意识”或“集团意识”,因而这种冲突也相应地具有了利益集团冲突的性质。中国人民大学的李强教授即认为,从整体上划分,当前中国主要有四大利益集团,即特殊获利集团、普通获利集团、利益相对受损集团和社会底层集团。据此来分析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冲突,小到网络上的一次对骂,大到群体性事件,往往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4]
从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发展态势上看,它表现出三种趋势:
1.无直接利益冲突具有损害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普遍抱有一种对政府不信任的、甚至是仇视公共权力(“仇官”)的偏激情绪,同时也抱有因不满于社会的贫富分化而生发出的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这种仇官和仇富心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下降,而且也意味着政府执政的民意基础的流失和政府的合法化能力的下降。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仇官和仇富心理具有放大效应和蝴蝶效应,恰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内讧(这里,可借指无直接利益冲突——笔者)虽起于琐细的动机,事情却总是乘势扩大的。细节的牵涉到执政人员者,更容易因轻微的风波而酿成严重的结果。”[5] 如果政府对此置若罔闻,任其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2.无直接利益冲突具有“升级换代”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无直接利益冲突和直接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看,两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一方面,直接利益冲突可能会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培育土壤;另一方面,无直接利益冲突反过来又可能会衍变为直接利益冲突,从而使冲突的范围蔓延、冲突的能级加剧。因此,虽然无直接利益冲突还没有构成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还不足以对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是绝不能无视和放任这种冲突,必须防患于未然,并尽可能地杜绝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换代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否则,一旦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换代为大规模的直接利益冲突,就为时已晚了。
3.无直接利益冲突呈现出泛化的态势。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泛化主要是指情绪化的非理性心态的泛化。这就是说,人们(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在面对某一问题和事件时,动辄采取极端的、不宽容的、不妥协的心态和处理方式,而且这种心态在不断地蔓延,并衍化为一种处理问题的模式。这种情况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钟玉明、郭奔胜的调查报告中就有所反映。例如,在他们的采访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树坚指出,我国民事案件的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双方赌气成分很大,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有些地方征地拆迁、企业转制等较为突出的问题,使各级政府感觉形势不容乐观。江苏省金坛市委副书记张建华形象地比喻说,现在老百姓在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声“倒霉”、起来拍拍灰土继续走路,而是骂“他妈的干部腐败,修的豆腐渣马路”。而在一项社会专项调查中,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虽然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但是反映出当前群众比较严重的情绪化的非理性心态。[6]
总之,不论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研究当前我国出现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升级换代”,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广度和烈度加剧,进而防止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发生,并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积极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研究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时候,关键是要有一个客观而理性的态度,既不能简单地把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定性为是“好”还是“坏”,也不能用障目法把它掩盖起来,或者简单地把它一棍子打死,而是应当把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放在我国以现代化为取向的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应当以辩证的理性的态度、以面向未来的精神来解读改革及其带来的社会变动。只有在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有了正确的态度和认识的时候,人们才会有主动的精神迎接面临的挑战,提出的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对策也才会更加切实有效。
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关于2006年中国社会心态的调查即证实了这一观点。该调查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因为较多的被调查者把干部看作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参见:王俊秀、杨宜音、陈午晴《2006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节选)》,刊于《社会科学报》2007年2月8日。)
标签:利益冲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