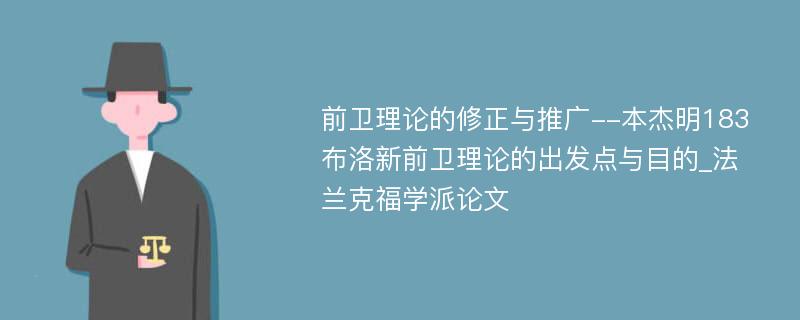
前卫理论的修正与推进——本雅明#183;布赫洛新前卫理论的出发点及其目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理论论文,目的论文,出发点论文,布赫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正如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①一书的翻译者转述阿列西·艾尔雅维奇的话,“《先锋派理论》是当今西方世界讨论先锋派艺术影响最大的一本书”②。面对这样的判断,问题自然会呈现为,既然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其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使得在当代艺术语境中展开布赫洛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从亨廷顿谈文化冲突开始,全球化研究就渐渐成为美国知识界的重要课题。中东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直至今日的叙利亚危机,使得美国知识分子对亚洲和非洲的问题尤其感兴趣,如何建构一个全球化的知识体系已成为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任务。当代艺术史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个知识背景下展开的。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最为矛盾的是,看似处于共时性全球化中的人们却很难了解彼此的当下状况。现时的美国学界正在继现代—后现代之后,对当代性(contemporaneity)和网络文化(network culture)展开研究,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会表现出的是一种即刻现实(immediate reality),在网络文化阶段,“现代和后现代艺术对工业社会同质性(homogeneity)的批评已经被纳入管理理论之中,原来工厂中被异化的工人也已转变为知识型工人。他们工作的灵活性使得他们具有了一定的‘自由’,并且他们作为具有创造性阶级的一员,具有一定自我表现的特权”③。与整体文化转变相应的是,处于网络文化语境下的当代艺术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西方实时变化的学术现状,国内的艺术理论界正开始着手研究其动向,本文对布赫洛的研究也属此类。在这种当代性、全球化的知识话语中,问题应该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艺术批评家如何分析、认知和理论化西方当代艺术现象?在这个问题之下,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Buchloh)④的批评文本便是一个个案。
布赫洛作为美国《十月》杂志的编辑、《艺术论坛》近三十年的重要撰稿者,其对美国和欧洲当代艺术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艺术论坛》和《十月》已经成为美国当代艺术界最为重要的两本杂志,围绕在这两本杂志周围的批评家群体也成为北美当代艺术理论的制造者。以《十月》杂志创始人之一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为核心的批评家及其学生已经成为美国当代艺术史及理论的中坚力量,布赫洛自1977年到达北美后便很快加入了这一核心批评圈。1994年,他以论文《李希特:历史主体之后的绘画》(以下简称《李希特》)在纽约城市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罗莎琳·克劳斯便是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三位教授中的一位。在这之前,布赫洛已经成为《十月》杂志批评家群体的一员,其大部分文章也均发表于该杂志。
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美国当代艺术界通用的几大理论工具,以《十月》杂志为核心的理论家如福斯特(Hal Foster)、布瓦(Yve-Alain Bois)以及克劳斯都比较倾向于前三者。不同的是,布赫洛的德国背景使得他的批评方法区别于来自法国的布瓦和其他美国当代批评家。兴起于德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成为布赫洛的重要批评工具,同时在他的文本中也使用了语言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不足。
布赫洛是比格尔前卫艺术理论在北美视觉艺术领域的推动者和重建者。如果说比格尔是前卫艺术理论的创立者,那么布赫洛则完善了其对前卫艺术的论述,并通过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分析纠正并发展了“新前卫”的概念。
一、标准化与去历史化的“历史前卫”
从布赫洛1984年11月发表的文章《被理论化的前卫》来看,他非但不是较早对《先锋派理论》一书展开讨论的一位学者,而且有些姗姗来迟。但是不可否认,他却是较早在英语世界系统评论比格尔著作、并沿着比格尔的理论框架继续前进的一位学者。1984年比格尔的《先锋派理论》一书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距离它在德国的出版时间已经十年,期间就此书展开的讨论也已结集出版。但正如布赫洛所说:“一本迟来的翻译推动了对60年代晚期美学理论的批评性基础的反思。”⑤
布赫洛对比格尔的批评虽然显得尖刻与犀利,却还是与一般的书评大为不同。西方杂志时常刊登一些对新近出版书刊的评论,它们或是对同行的无条件支持,如2001年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为布赫洛新书所写书评《托付于记忆》显然是一派赞扬之辞;或是作为持不同意见者对书中论点提出质疑,这类批评的作者往往将文章作为口头意见予以发表,之后再无下文。但是对于布赫洛,比格尔的理论自1984年之后就一直没有退场,直至2000年他出版《新前卫与文化工业》一书时,仍然承认比格尔的理论是其之前二十多年北美学术生涯的主要推动力。
布赫洛对比格尔理论的热情含有很强的身份认同感。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二战”期间被迫流亡美国不同的是,布赫洛1977年移居美国完全出于自愿,其中原因之一是他希望走出德国战后高度专断的民族文化身份结构,另一原因则是他强烈感觉到当代艺术批评和欧洲当代美学在当时西德的困境,而北美才是当代艺术的核心地带⑥。实际上从后来的批评事件看来,移居北美并没有缓和布赫洛作为德国人的民族身份感,相反,这使他将这种浓厚的民族身份感释放到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将对法西斯的批判内化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一般,布赫洛将这种民族身份认同感转化为对诸多德国艺术家的个案分析。
1969年布赫洛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1968年的德国学生运动高潮刚刚结束,前后几年自由大学恰恰处于学生运动的核心。西柏林学生运动起因众多,其中一方面源自政府的高压政策与面对法西斯历史时的无能。面对这样的背景,在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学生和公共舆论开始质疑文化和艺术表达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如无处不在的新媒体、文化工业和勃兴的美国绘画市场⑦。面对西德当时的现实环境,布赫洛势必深深卷入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核心内容依然保存在布赫洛的批评文本之中。1977年移居北美不久,他便进入了美国当代艺术批评的核心圈,即以《艺术论坛》和刚成立不久的《十月》杂志为核心的批评家群体。这时的美国当代艺术已经逐渐走出了波普艺术的潮流,极少主义、后极少主义、观念艺术等形式正处在兴盛期;美国批评界也已经历了以格林伯格为主导的形式主义批评向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社会学批评等多元化批评方向的转换,其中罗莎琳·克劳斯就是一位非常关键的学者。这时仅以比格尔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已经不足以分析美国的当代艺术现象,而克劳斯以语言学为工具对前卫艺术进行分析的方法为布赫洛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在1994年完成的毕业论文中,布赫洛一方面强调了比格尔理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赞扬了克劳斯语言学批评方法的有效性。他在对比克劳斯和比格尔理论时主要使用两个关键词:“去历史化”(ahistorical)和“去理论化”(atheoretical),“(与克劳斯相比)比格尔对两种前卫的划分是极为去历史化的,因为他没有成功地辨别,更何况说描述新前卫实践的画面和语言范式的转换;另外,比格尔的模式也是极为去理论化的,因为他并没有从结构上分析新前卫所依存的独特的认识论转向”⑧。比格尔虽然在新前卫的问题上缺乏历史性的思考,但是其对历史前卫的理解确实非常具有历史性。布赫洛也必定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分析李希特的单色绘画时,所做的就是综合克劳斯的语言学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研究李希特的抽象作品。布赫洛对比格尔的批评非常准确,但未免有些强人所难。比格尔使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论证历史前卫的问题,这才是其前卫理论的核心,对新前卫的具体分析和语言学分析方法的使用已不属于比格尔理论的根本任务。再者,比格尔对新前卫的批评并非一无是处,并且在很多方面击中了部分新前卫作品的要害,在这方面,豪·福斯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⑨。
从1984年一篇专论比格尔的书评开始,布赫洛分别在《基本色彩的复现:新前卫的范式重复》(1986)、《李希特》(博士论文,1994)和《新前卫与文化工业》(2000)等几篇文章中重点分析过比格尔的理论。前面提到的1984年的那篇短评重在陈述观点,缺少具体分析,而后面跨度近二十年的文章则可看成是对那篇短评论点的展开。
布赫洛显然是从视觉艺术理论家的角度去评价一个偏向于文学批评的理论,而比格尔则显然是从文学批评家的角度去建构一个与视觉艺术相关的理论,两者之间的错位让彼此产生了不少知识上的冲突,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种学科知识上的冲突使得两者彼此充分受益。比格尔的前卫艺术理论因为布赫洛而在当代视觉艺术领域获得一派生机,布赫洛则因接受比格尔的理论而建构了自己整个学术大厦的框架和关键词。因为比格尔理论的文学背景,使得布赫洛觉得其理论在与视觉对接时总显得捉襟见肘,并略带天真。总结起来,布赫洛对比格尔的批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1.简单地将历史前卫归结为铁板一块的反体制实践;2.比格尔以历史前卫为标准,既盲目否定了19世纪的现代主义又否定了1945年之后的新前卫运动;3.比格尔理论主要使用了来自本雅明和阿多诺两大理论资源,但他既没有微观分析本雅明所论蒙太奇的具体发展情况,也没有明确阿多诺理论强调自律体制的现代主义属性;4.比格尔注重从接受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艺术,把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变成了行政管理者;5.比格尔最后得出的结论在逻辑上不合理,即认为自从试图消解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的艺术实践失败后,任何实践都变得同等有效。
布赫洛对比格尔的批评指出了前卫理论的局限,但正是这些局限性使得比格尔的理论针对历史前卫本身十分有效。将历史前卫归纳为反体制的实践,这是从艺术功能角度去分析达达主义、法国超现实主义、俄国构成主义和苏联生产主义(productivism)后得出的结论。注重接受和功能分析是比格尔前卫理论的重要特征,正是这一独特的研究角度才使得划分前卫和现代主义成为可能,至于布赫洛所指“行政管理者”的比附仅是一种形象性联想而已。
相比于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批评,比格尔对新前卫的盲目否定态度确实是前卫艺术理论的明显缺陷,这一点为布赫洛后来发展前卫艺术理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在《基本色彩的复现》和《李希特》中,布赫洛着重批评了比格尔前卫理论中对新前卫的盲目否定态度。比格尔对新前卫的否定态度依赖于他对前卫起源的认定,于是基于这一认定基础的对新前卫的判断便成为后来批评家攻击的核心标靶。
作为第二次前卫式的与传统决裂的新前卫,成为缺乏意义并允许放进任何意义的表现形式。⑩
新前卫将前卫体制化为艺术,从而否定了前卫的真正意图。(11)
布赫洛仅仅抓住比格尔所使用的词语“第二次”与“真正”(genuinely)来解构前卫理论的基础。“比格尔那原本在其他方面显得或许有效和重要的历史框架,现在却因为这一特点而失败,即对(历史前卫)起源的虚构,并且这一起源不可挽回的具有充分性和真理性”(12)。也是在这一论点基础上,布赫洛认为比格尔将1945年之后的新前卫实践说成是重复和无意义的。在博士论文中,布赫洛对比格尔此观点的批评更为准确到位。他认为“真正的”(genuine)和“意图”(intention)两个词使比格尔落入了本质主义的窠臼(13),也就是说以20世纪初的历史前卫为起点和终点,比格尔既否定了之前的现代主义又否定了之后的新前卫,历史前卫作为一个具有积极价值的运动彻底失败,并已不能挽回。对当代艺术的彻底否定使布赫洛联想起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新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观点,他对当代音乐和电影的激烈批评与彻底拒绝。这种观点也无形中唤起了布赫洛对1968年的记忆,他想极力反思的正是这些形成于60年代末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新左派的某些片面观点。
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一直具有重要的影响,布赫洛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方法的接受和批判贯穿于他的众多批评文本中。因此,他在批评比格尔的本质主义之后,将分析扩展至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内部。他认为,与马克思认为希腊古典艺术无法超越和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抒情诗不再可能一样,比格尔也将一切不符合历史前卫标准的艺术排除在外(14)。但是一旦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布赫洛的观点就显得有些矛盾,他一方面既不认同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观点,又不认同比格尔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但另一方面却在追求一种正确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
比格尔的前卫理论大部分内容源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传统,这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而且还包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性解读。但在涉及对新前卫的观点时,布赫洛便对比格尔理论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属性全部予以否认,转而认为“比格尔既不是一位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又不是一位目前(the present)成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5)。由此可见,布赫洛想要说明的实际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位目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将不得不阐述观念和结构转型后的艺术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强烈悲叹先前范式结构的消失和失效。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首先应该与当代艺术作品单纯的经验主义的事实划清界限”(16)。布赫洛在研究李希特时,正是遵循了他所认为的目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既对艺术现象进行了去经验主义的结构分析,又将结构分析历史化。
二、新前卫的合法性
如果按照比格尔的理论进行推论,“二战”后的新前卫艺术自然失去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其不仅重复历史前卫的艺术手法,而且同化于体制。对新前卫的这种判断固然出自比格尔理论自洽的上下文逻辑,但却为布赫洛这类工作在视觉艺术批评第一线的学者提出了难题。既然新前卫毫无合法性可言,那么他们从事新前卫批评和策划的工作意义何在?于是重述和改进比格尔的前卫理论便成为进一步推进当代艺术批评理论的重要步骤,这不仅因为前卫理论自发表以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因为只有直面前卫理论的尖锐观点,才能再认新前卫批评和创作的合法性。于是布赫洛将比格尔这种极为悲观的历史观转化为积极的历史观,将一种极为本质主义的评判标准去本质主义化。所以,在布赫洛看来,并不能因为历史前卫反抗自律的失败就将其完全抛弃,而是应该将前卫定义为不断寻求新途径去抵抗铺天盖地的文化工业,去重新定义新的文化意义和新的观众群体的一种不断发展的概念。
为了证明新前卫的合法性,布赫洛展开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不断寻找依然延续历史前卫批判性的新前卫艺术,另一方面则在不断细化历史前卫研究的同时,于“历史”与“新”的重复中寻找“新”的独特意义。
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界出现了一系列以反艺术体制为目标的艺术作品和个体艺术家,他们自然成为布赫洛所关注的研究对象。艺术家包括迈克尔·阿舍(Michael Asher)、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马塞尔·布达埃尔(Marcel Broodthaers)、汉斯·哈克(Hans Haacke)、丹·格雷厄姆(Dan Graham)、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这些艺术家的出现很明显证明了比格尔对新前卫艺术的误解。“正是对这些艺术家实践的根本忽视,使得比格尔对两种(前卫)形式的精确划分和对当代艺术的直接藐视让人实在无法接受”(17)。布赫洛对这些艺术家的研究旨在摆脱比格尔这种极端的左派艺术观,发现存在于新前卫作品中微妙复杂的反抗形式,尤其是对物化、文化工业和景观社会的抗议。
除去关注一个个反抗体制的艺术家个体之外,布赫洛试图通过在历史前卫和新前卫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叙事关系来论证新前卫的合法性,《基本色彩的复现》便是最早的一次尝试。他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术语“压抑”(repression)和“拒认”(disavowal)来重新定义历史前卫与新前卫的关系,于是被比格尔划分为历史前卫的罗德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和新前卫的克莱因(Yves Klein)之间的重复关系成为重新定义新旧前卫的典型。
布赫洛对罗德琴科的分析非但没有逃出比格尔对历史前卫的定论和分析方法,反而通过微观考察证明了历史前卫反对资本主义艺术自律体制的正确性。苏联的历史前卫艺术家马列维奇、罗德琴科和李西茨基(El Lissitzky)将绘画缩减到基本色彩的程度,最大可能剔除绘画中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和精神表达元素,使绘画回到最基本的物质层面。他们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一方面“吸引了更多和更为不同的观众”,另一方面“反对社会劳动分工”(18),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绘制单色绘画。布赫洛谈到的以上两点,恰恰是比格尔的接受与功能分析在解释历史前卫作品中的应用。
布赫洛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被比格尔形容为语意衰退的新前卫艺术赋予新的意义。因为在比格尔看来,与罗德琴科等人作品相似的克莱因的作品,已经不再处于192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已经不能再产生出历史前卫那样的意义。面对新旧前卫主观经验形式上的极端类似,布赫洛转而对新前卫采取了语言学上的拯救,正如他在1994年试图将克劳斯的语言结构分析用来分析李希特的单色绘画一般。“现代主义的‘语言’建构了新前卫的讲话者,从而继续重复和修正了他们的‘言语’……(新前卫作品)将意义转移到外围,将它转移为横聚合关系、偶然性和文本的他律结构结合”(19)。通过这种艺术现象到语言学的转换,克莱因看似无意义的作品便具有了产生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新前卫的意义已经不能再从作品本身去寻找,而是要深入到作品和艺术家所处的语境中。
按照布赫洛的这种叙事方法,克莱因的作品就已经不再是历史前卫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历史前卫所造成压抑的拒认,因为克莱因的作品在功能、观众和意图上恰恰与历史前卫相反。克莱因的作品正试图要恢复现代主义的“高雅艺术”(high art)特征,回到自律的艺术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身的合法性。但是在分析新前卫的意义时,布赫洛的判断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他的价值观判断和理论出发点显得相互抵触。从理论出发点来看,他要做的是将新前卫放到战后语境中分析其与历史前卫的根本不同,从而否定比格尔的新旧重复说,那么他对克莱因和俄国前卫的对比分析已十分完满,他认为“源自于现代主义启蒙工程的同样策略已经转而向转型为企业国家(the corporate state)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合适的分配(全然的商品化)形式和文化经验(景观化)”(20)。这个结论也证明了他认为新前卫只能从外部功能才能得到理解的论述。从价值观立场来说,布赫洛虽然认为在企业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正在消除个人经验和精英文化的反抗功能时,克莱因对超验否定性和个人经验的回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同时对克莱因作品的商品拜物教性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里存在的悖论便是布赫洛研究了一个自己在判断上就极为矛盾的新前卫个案,新前卫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完成对李希特的研究,布赫洛才在价值观立场和理论出发点这两者之间达成了一致。面对李希特,他已经不再出现分析克莱因时的那种矛盾心理,而是既肯定了李希特的重复,又赋予了重复以肯定的意义和价值(21)。
从布赫洛的批评实践来看,他并没有通过一篇文章将新前卫理论化,而是通过不同的个案研究,来实现他对比格尔理论的修正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几乎与布赫洛完成博士论文同时,其同事福斯特发表了一篇《新前卫新在何处?》的文章,试图在布赫洛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完整的新旧前卫之间的叙事。这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十月》杂志对杜尚回顾性研究的专刊中,具有浓重的历史总结味道。在文章中,福斯特将布赫洛在1986年提到但是没有深化的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再利用,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建构了从历史前卫到新前卫的叙事,给予新前卫以全然的合法性。
在福斯特建构新前卫叙事的过程中,正如他所说:“要去改善它(比格尔的理论),通过它本身的模糊性将其复杂化——特别是暗示出历史前卫和新前卫之间的时间性互换关系,一种复杂的预期与重构关系。”(22)所以在整个叙事中,比格尔对前卫的两条判断标准被保留下来,一是重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二是反体制。恰如布赫洛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判断新前卫不是对历史前卫的重复、而是对它的拒斥一般,福斯特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但不同的是,他通过转引拉康的延迟行为(deferred action)的观点将这个判断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所以福斯特得出的结论便是,第一次新前卫是对历史前卫的反抗,第二次新前卫则是对第一次新前卫的批判。第一次新前卫,例如劳申伯格,不再寄希望于整合艺术与生活,而是用艺术作品保持艺术与生活间的张力,同时这批前卫艺术家成功地反抗了以弗莱(Roger Fry)和贝尔(Clive Bell)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形式主义批评,以及以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弗雷德(Michael Fried)理论为支撑的纽约画派模式。第二次新前卫,如汉斯·哈克,将历史前卫仅仅宣言式的反体制行为转为一种精细的分析调查模式,并且对第一次新前卫的体制化提出了批评。至此,福斯特认为自己成功地将比格尔的理论合理化了,犹如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
虽然福斯特对比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拯救,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依然是比格尔对新前卫的尖锐批评,甚至福斯特本人也承认,第一次新前卫很快就被体制化了,即便是新前卫没有被体制化,难道新前卫就不存在任何对历史前卫的重复吗?当然,我们依据福斯特的线索可以在纵向上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但是这在横向上却无法区分优秀新前卫和劣等新前卫之间的界限。这一界限的模糊恰恰来自于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使用。由于过分强调无意识的作用,无意识就可以成为模糊一切价值判断标准的借口,要明确这种界限的存在,如布赫洛一样,保持新左派的部分思想精华依然是可取的一种解决办法。
比格尔的理论在布赫洛的接受与修正之下已经完全转变为一种视觉前卫艺术理论,并且在当代获得新的生命力。比格尔提出的历史前卫和新前卫框架也已成为布赫洛艺术史研究及当代艺术批评的基石。布赫洛(包括福斯特)在对比格尔理论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保留了前卫理论最本质的否定和批判特征,只不过前者将这种特征再次延伸到了当代领域,而比格尔则将其固定在了20世纪初的那段历史中。
布赫洛新前卫艺术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对比格尔前卫理论中新前卫“重复”和“无意义”观点的批评。这种批评的目的则是要证明“二战”之后新前卫的合理性。新前卫在转变了的历史语境中,依然发挥着历史前卫的批判和否定作用,准确地说,其不仅继承着历史前卫对自律体制的批判,而且还深刻揭露了工业文化、景观社会的虚假表象和去个体性特征。
注释:
①高建平将“avant-garde”翻译为“先锋”并无不妥,不过,在视觉艺术话语内,“前卫”一词的使用更为普遍,而笔者主要在视觉艺术范围内讨论问题,所以,本文使用“前卫”一词(参见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②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第221页。
③Kazys Vamelis,"The Immediated Now:Network Culture and the Poetics of Reality" (http://varnelis net/network_culture)
④本雅明·布赫洛,美国当代著名批评家,出生于德国,哈佛大学梅隆现代艺术教授。
⑤Benjamin Buchloh,"Theorizing the Avant-Garde",Art in America,Vol.72,No.10(November 1984):19.
⑥Benjamin Buchloo,Neo-Avantgarde and Culture Industry,Cambridge,MA:MIT Press,2001,pp.xvii,xxvii.
⑦见http://www.oxfordartonline.corn/subscriber/article/grove/art/T2094094.
⑧(13)(14)(15)(16)(17)Benjamin Bucbloh,Gerhard Richter:Painting after the Subject of History(纽约城市大学1994年博士论文,未出版)。
⑨豪·福斯特的《新前卫新在何处?》一文在布赫洛基础上再次讨论了比格尔的理论。福斯特认为“如果新前卫这一术语要保留的话,必须在新前卫产生之初就把两种不同的运动区分开来:一方是20世纪50年代初劳申伯格和卡布瓦为代表,另一方以60年代初的布伦和阿舍为代表……(前者)并没有改变艺术体制,却被体制所体制化了”。既然如此,福斯特依然不同意比格尔的盲目否定,而是努力从另一种新角度去理解他们(Hal Foster,"What's Neo about the Neo-Avant-Garde?" October,Vol.70,(Autumn,1994):22)。
⑩(11)译文在中译本基础上进行了改动,中译本见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第135页,第131页。英译本见Peter Bruger,Theory of the Avant-Garde,trans.Michael Shaw,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p.61,p.58。
(12)(18)(19)(20)Benjamin Buchloh,"The Primary Color for the Second Time:A Paradigm Repetition of the Neo-Avant-Garde",October,Vol.37(Summer,1986):42,44,48,52.
(21)布赫洛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李希特进行了详细分析,其中主要区分了李希特单色抽象等看似模仿性的作品与历史前卫的区别,并给予其新的意义。正如他在《新前卫与文化工业》一书前言中写道,“……更为系统的是这些年我对李希特的研究,我集中研究了美学建构记忆经验的能力,它作为极少数的抵抗手段之一在与景观化的总体性作斗争”(Benjamin Buchloh,Neo-Avantgarde and Culture Industry,p.xxv)。
(22)Hal Foster,"What's Neo about the Neo-Avant-Garde?" October,Vol.70(Autumn,1994):14.
标签:法兰克福学派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布赫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本雅明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十月论文; 李希论文; 比格论文; 李希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