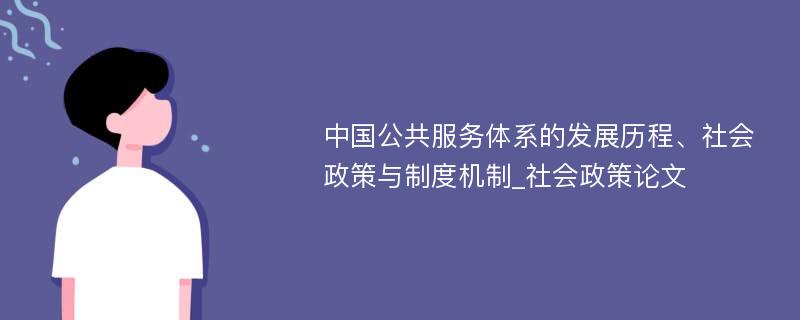
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服务体系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体制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3-0005-1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应地,公共服务能力和供给水平也较之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显著提高。① 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由于追求经济增长成为各级政府的核心任务,相对忽视了其公共服务职能和社会建设投入,加上公共服务体系整体改革和建设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比较突出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问题。2002年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建设等理念与目标的提出,中国进入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新时代,公共服务成为了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中国政府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初步建立起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在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增进国民福利、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如碎片化、差异化、(财权不充分的)属地化、低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及导致投入不足、投入不均的结构瓶颈未有效消解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特别是要着力突破体制性限制与障碍。
一、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历程
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间,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阶段是1978—1994年间,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性使政府较为忽略公共服务供给,同时旧的公共服务体系开始瓦解;第三阶段是1994—2002年间,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政府着手在城市建立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指导下,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更具普遍性和全面性的公共服务体系。②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相对简单、平均主义和国家包办(配给制)的公共服务体系,以适应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制度安排。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在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之上,以城市“单位制福利”和农村“集体福利制度”为主体。一方面,在城市实施“单位制福利”,采取“企业办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各种企事业单位同时兼具生产经营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双重功能,向所有职工免费和同质提供诸如退休工资、公费医疗、基础教育、福利服务、住房分配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在农村实施以小学教育、集体养老和合作医疗为主体的“集体福利制度”,村集体经济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融资和供给主体,国家直接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支持较少。
总体上讲,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服务体系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和均等化,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方面,与较低的经济生产水平相联系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较低和总体短缺,而单一的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又导致了比较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向城市单位职工,农村居民未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类似情况同样存在于城市重工业部门与轻工业部门之间。此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依赖于村集体经济生产能力,不同经济效益的村集体之间的公共服务也存在着相当差距。③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以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持续地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发展路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此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优先地位不断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较多地从个人魅力转向了经济增长,追求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成为了各级政府的中心任务,一种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形成,地方政府日益演变为一种“发展型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积极的角色如招商引资、开发项目等,甚至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政府财政最大化地用于生产性投资甚至充当投资主体。④ 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弱化。改革开放后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总量尽管不断增加,但相比于经济建设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严重偏低。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逐步推动了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双重需要,它具有二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和地方化四个基本特征。
首先,公共服务体系改革沿袭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化思路。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村集体经济基本解体,建立于其上的传统公共服务体系相应瓦解。在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无法继续运作,集体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因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而面临巨大挑战。⑤ 1992年,中央政府开始试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缺少国家财政投入的支持,导致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过低,最终变成了一种个人储蓄养老,因此农民参保积极性并不高,所起到的社会保障功能十分有限。⑥ 1998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陷入了全国性停滞整顿状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名义上由乡镇财政负担,但逐渐以各种名目的税费摊派到农民身上。可以说,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农村几乎处于公共服务供给的“真空”状态。
在城市,计划经济时期的公共服务体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政府开始在城市探索建立新型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首要目标,是从传统的“企业办社会”模式转变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改革,主要面向城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1992年,中央首次提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从原来的“企业保险”转向“社会保险”(由个人、企业和政府按比例共同承担筹资责任),实现社会保险的社会化融资、社会化管理服务。到21世纪初,城市已基本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体系。同时,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革产生的大量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又建立起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主要面向城市正规就业人员,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农民工等游离于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之外。⑦ 在社会福利服务领域,民政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社会福利社会办”的改革思路,希望通过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的参与,解决传统模式下融资渠道单一以及由国家包办带来的效率低下和服务质量差等问题。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但由于缺乏经验,社会化运作的福利服务发展相对滞后,当时主要只是探索了社会化的机构养老服务模式。
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于卫生、教育和住房领域。在住房供给改革方面,实现了从福利分房到货币分房的过渡,确立了商品化住房供给的主体地位,并初步建立起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公积金和经济适用房制度。在卫生和教育发展领域,逐步取消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公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制度,公众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才能享受相关公共服务;公立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质量大大提高。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倾向不断凸显,相关服务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加上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地方化是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又一重要特征,它甚至决定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分权为主题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治理地方事务的自主性、积极性,但也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及其对地方行政部门的控制范围和力度。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在1994年推动了以财政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界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但并没有合理划分相应的事权,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超过了总财政收入的50%,却由地方政府承担了70%的支出责任。由于公共服务采取“属地化”供给,支出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也未能“充分支持地方政府提供这些服务时所需的支出”⑧,导致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难以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特别是乡镇政府几乎无法在农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收入中央集权化与公共服务供给地方化之间的矛盾,还导致地方政府形成“倒逼型”制度外、预算外支出,产生大量“乱收费”问题。在经济先发地区,由于地方财力相对丰厚,往往能够提供相对充足和水平较高的公共服务,这也因此造成了比较显著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区域性差距。
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地方的调控和引导,还围绕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设计了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治理机制⑨。这种政治锦标赛主要以“GDP”等经济指标作为考核标准,导致地方政府往往选择性地履行职能,亦即积极担当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体角色,相对地忽视了其公共服务职能。此外,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少有公共服务的政策和项目出台,地方政府也缺乏社会政策创新和开设公共服务项目的动力。在分税制和政治锦标赛的共同作用下,即便财力丰厚的地方政府也是选择性地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既不过多地投入于公共服务供给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又严格限制着公共服务的享受资格,大部分非本地户籍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和非正规就业人员常常被排除在外。⑩
总体上讲,20世纪80—90年代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实现了从单一供给主体到多元供给主体的转变、从国家免费供给到居民付费享受的转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大大提高,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短缺状态。但由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财权不充分的属地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导致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投入和供给严重不足,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普遍可及性,大部分贫困群体、农村居民、灵活就业人员和转移劳动力处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边缘化地位,造成了城乡间、区域间、群体间比较显著的公共服务差距。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进一步导致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失衡,社会公平状态不断恶化,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需求难以满足,从而对社会稳定和未来发展构成了挑战。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中国进入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的新时代,公共服务成为了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要求,首次界定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并突出强调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此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通过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扩大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构建覆盖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建设廉洁、公正、透明、责任政府,全面增强公共服务能力,有效回应公共服务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11)
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先后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核心目标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旨在实现三个方面或意义上的均等:第一,机会均等,保护全体国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公民权利,这取决于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特别是将城乡居民、弱势群体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第二,投入均等,保证全体国民享有水平均等的公共服务,这取决于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特别是财政投入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第三,结果均等,保证结果大体均等而非绝对平均,这取决于机会均等与投入均等的实现程度。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突出强调要着力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并对“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出专题论述。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专题论述,其中要求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随着发展的民生取向不断强化,中国政府逐步推动了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旨在通过社会政策体系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通过公共服务投入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群体间的公共服务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可及性、公平性和均等化水平,并努力平衡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益与效率目标。
二、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体系
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府将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建设重视不够(12),甚至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容忍不平等的扩大”(13)。改革取消了针对产业工人“从摇篮到墓地”的传统社会福利承诺,但并未成功设计出社会政策以适应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尽管市场化改革提高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福利供给没有明显改善,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催生了新的不平等。(14)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重心实现了“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跨越”,围绕就业、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保障性住房、基本生活保障等方面,集中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其政策重心和财政投入不断向农民工、城乡居民和弱势群体倾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该法将于201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中国社会政策体系建设开始进入全面法制化的新阶段。
1.就业保障与就业服务。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逐渐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包统配和充分就业政策。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已基本实现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的目标,建立起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确立了“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2002年以来,为进一步扩大就业、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特别是解决困难群体、农民工群体和零就业家庭的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公共就业服务的财政投入和供给力度,围绕职业介绍、就业培训、就业援助、创业支持、就业补贴、公益性就业岗位提供等方面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就业政策,并建立起公共部门的三级就业服务平台,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职业介绍与就业培训网络。2007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制定出台。前者提出了“扩大就业,市场就业,平等就业、统筹就业”四项原则,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后者则全面规范了劳动关系,保障了劳动者权益尤其是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并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保护范围。这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公平竞争的就业环境、缩小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背景下各种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就业歧视和工资歧视。
2.义务教育。中国义务教育的筹资和供给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但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财力有限的地方政府越来越难以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支出,这进一步造成了城乡间、区域间义务教育供给的不均衡,特别是在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方面。2003年,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加快普及农村义务教育、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等重大决策,提出在农村地区实施针对贫困学龄人口的“两免一补”(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资助政策。2005年,开始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此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主要由“中央拿大头”。2006年,全国人大通过《义务教育法(修订案)》,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收学杂费,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并将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同时,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硬件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以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学校间的差距。到2008年,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基本实现全免费,城乡间、区域间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程度大大提高,但师资质量和教育质量的不均衡仍比较显著。
3.基本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服务。2003年爆发的“非典”危机,凸显出中国基层公共卫生体系和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脆弱性。回归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建立健全基本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卫生公平,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由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投入城市和农村的基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程度逐步提高。到2010年,中国基本建立起全覆盖的“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人员配置不足、队伍不稳定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2003年,国务院决定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以“大病统筹”为主,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到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7年,国务院又开始仿照“新农合”的运作模式,试点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将全国城镇非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至此,中国建立起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全覆盖。但三项制度独立运行,在筹资水平、补偿比例及政府投入力度上存在着较大差距,特别是“新农合”并没有从整体上削减农民的医疗费用负担。(15)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201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1年度主要工作安排》,提出“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但总体上讲,“新医改”进展缓慢,效果尚不明显。
4.基本养老保障与养老服务。在养老保障方面,2002年以来的主要工作是巩固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正规就业人员的参保覆盖率,并逐步“做实个人账户”,但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城乡居民仍游离于基本养老保障体系之外。在农村,自“老农保”于1998年进入停滞整顿之后,中央政府一直没有新制度出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开始自主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09年9月,国务院决定试点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实行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模式,年满60周岁的农村居民都可以领取到由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相比于“老农保”,“新农保”明确了各级政府的筹资责任,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但基础养老金水平严重偏低,而且全面覆盖速度过于缓慢。近年来,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地推出的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政府也开始着手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在这一时期,中国养老服务业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发展,突破了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以机构养老为主的服务供给模式。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此后,各地的居家养老服务开始迅速发展。
5.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助。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城市贫困问题开始凸显,一些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建立城市最低生活救助制度,并迅速在全国推广。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全面深化,产生了大量下岗职工,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普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标志着这一制度在全国全面建立。此后,上海、广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又开始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2年底,全国有10个省份出台了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方性法规。2007年,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全面普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由于缺少全国统一规范的标准,并且筹资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中央和省级的转移支付相对较少,因此社会救助的总体水平不高,而且城乡间、区域间的救助水平也很不均衡。此外,综合救助制度建设开始缓慢起步,针对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逐步向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专项救助在内的综合救助制度发展。总的来说,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仍停留于保障基本生活层面,福利依赖现象也开始显现,但政府鲜有类似西方“工作福利”的政策改进措施出台。(16)
6.保障性住房。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住房政策改革,确立了商品化住房供给的主体地位(目前住房市场化比例已达到80%),这大大提高了住房供给的效率与质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相对匮乏。(17) 进入21世纪后,房地产行业发展开始升温,商品性住房价格不断上涨,逐渐超出了普通家庭和居民的承受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在不断出台房价调控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性住房供给。2007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首次将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纳入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提出了建立健全以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体系的目标。2009年,国务院进一步提出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发布了有关这一目标的时间表和具体目标。2010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首次将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纳入政府考核问责机制的范围,明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切实履行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职责,并提出了2010年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工作任务。2010年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2011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了2011年建设1000万套各类保障房的目标。目前中国的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正在努力推进,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仍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2002年以来,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得到了健全和完善,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基本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和可及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程度明显提高,特别是扭转了20世纪80—90年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的严重缺失状态。但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和身份碎片化特征,在城乡间、群体间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服务,不但未能实现完全意义的机会均等,还大大限制了投入均等与结果均等的实现程度。
三、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财政保障体制
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根据“放权让利”的改革思路,建立起中央与地方间的“财政包干制”。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财政包干制”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甚至几乎难以保障中央机构的正常运转。由于对地方上缴的税收份额限定得过于刚性(通常是一旦确定,五年不变),因此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央在新增财政收入中的分享比例不断下降。(18)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还承担了各种体制性的大量财政补贴(如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等),因此在税收不断下降的同时,财政赤字却不断扩大。(19) 就公共服务供给而言,由于这一时期地方经济和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地方政府不但维持了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转,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
1994年,中央政府推动了以财政中央集权为目标的分税制改革,重新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配置,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间财政体制。税种被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分设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体系和征管机构,大部分主体税种的收入被划归中央;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防安全费、重点建设费、本级行政管理和本级各项事业费等财政支出,地方政府则承担本级的行政管理费、基础设施建设费、支农支出以及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费的财政支出;此外,开始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分税制改革大大增强了国家的整体财政汲取能力,此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超过经济增长幅度,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特别是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分享比例(保持在50%~60%之间)。但是,分税制改革没有依据财权配置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导致财权不断向上转移、事权不断向下转移,造成了政府间财政的纵向不平衡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中央向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总量逐年增加,但税收返还的绝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先发地区,而转移支付规模又相对较小,且以专项转移支付为主、少有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因此又造成了政府间财政的横向不平衡问题。就公共服务供给而言,分税制改革大大限制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积极性,造成了比较突出的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现象。(20) 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中国的地方财政问题成为了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教育、卫生等国家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21)。
2002年以来,为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体制,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中国政府推动了“民生导向”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
在财税方面,2001年,实施了中央和地方分享所得税收入的改革(收入分享、基数返还、增量分成);2002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2003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60%和40%。2004年,中央政府又开始改革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最初对超基数部分的应退税额实行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负担,但考虑到地区负担不均的问题,2005年后改为92.5∶7.5,由国库统一退还,地方年终专项上缴。2005年,中央又出台了“三奖一补”的财政政策,以激励地方政府积极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此外,2006年又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在事权方面,2003年以来,国务院撤消了许多地方的“经济开发区”,收回了国土资源和矿产资源的直接管理权。2006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更是明确了中央政府投资支持的五个重点领域,即新农村建设、公共服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
从总体上看,2002年以来的局部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划分。实际上,这些改革措施使得中央的财政汲取能力进一步得到稳固,并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2002—2010年间,全国财政收入从1.8万亿元增加到8.3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从1万亿元增加到4.2万亿元,年均增长19.6%,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52%~55%左右。同期,全国财政支出从2.2万亿元增加到8.9万亿元,地方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80%之间。
(二)不断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力度
由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划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地方财力有限和政府间财力不均问题依然突出,因此,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就成为中央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种必然选择。2002年以来,一方面中央政府大大增加了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自2001年实施中央与地方共享所得税改革后,中央政府将所得税收入全部用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建立起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稳定增长机制。此后,转移支付的总体规模迅速增长(主要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倾斜),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比例大大提高。2007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完善了转移支付制度,改进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测算方法,规范了拨付资金的管理程序,强化了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整合力度。
2002—2010年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从2002年的4024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25606.64亿元,年均增长26%左右,远高于同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其中,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从1623亿元提高到12295.73亿元,年均增长28.8%左右,占财政转移支付总量的比例从40%提高到48%;专项转移支付从2401亿元提高到13310.91亿元,年均增长23.8%左右。2010年,中央财政用于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共计6169.7亿元,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24%,占同年上述方面全国总财政支出的23.4%。(22)
(三)积极推进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
在20世纪80年代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建立起一种“市管县”体制。尽管这一体制一度通过“以市带县”而有效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但也逐渐造成了市县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继而严重限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空间。而随后的分税制改革,又造成了财政收入不断向上转移、财政支出不断向下转移的局面,导致了比较严重的县乡财政困难。作为结果,财力拮据的县乡政府难以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且县域间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2002年以来,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中国政府逐步推动了“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省管县”改革肇始于1992年浙江省的“扩权强县”改革,通过将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以及实施“县财省管”、增加县级财政收入的分享比例,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提高公共服务能力。2002年后,广东、辽宁、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也开始了类似改革。鉴于“扩权强县”改革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2006年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管县的体制”作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目标。
就公共服务而言,省管县财政体制由于减少了市一级的管理环节,有利于增加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调配和利用,从而相对地提高了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缩小了省域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目前它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作用并不显著。
(四)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探索建立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
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最直接和最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80—9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两个方面,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所占比例偏低。2002年以来,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下,中国政府一方面逐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比例,另一方面又严格控制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经费的增长规模,但这两项支出费用仍分别保持在总支出的30%和20%左右。同时,各级政府开始探索建立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一些财力相对丰厚的省市县政府承诺“将新增财力的三分之二用于民生”。
2002—2010年间,全国财政支出从2002年的22053.15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89575亿元,年均增长19.1%,其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支出从4670.22亿元增加到26276亿元,年均增长24.1%,高于同期全国财政收支的年均增长率,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1.1%提高到29.3%。特别是2006年实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以来,全国教育经费支出规模迅速增长,从2002年的2644.98亿元提高到2010年的12450亿元,年均增长21.3%,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总支出的比重保持在45%~55%之间。
总体上讲,2002年以来,通过“民生导向”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中国初步建立起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保障体制,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规模大大增加,显著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尽管如此,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偏低,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此外,财政收入中央集权化与公共服务供给地方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仍取决于地方财力,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用有限,由财力差距造成的投入差距依然是制约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因素,在财力相对丰厚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与城乡均等化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3)
四、当代中国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20世纪80—90年代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配给制”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初步形成了一个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供给机制。但是,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责任的实现方式及其具体角色定位并没有得到十分明确和精细的划分,也没有形成一个有机衔接各种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的“复合式供给机制”。2002年以来,随着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逐渐成熟,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方面,明确了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或回归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配给制”,而主要体现为政府担当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项目规划、筹资主体和管理监督角色。另一方面,在肯定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运作的同时,围绕公共服务生产的参与方展开了以“复合式提供”为特色的供给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机制不断成熟,社会组织也获得了空前发展,为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截至2010年12月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民间组织已超过44万家,其中社会团体24.3万家,民办非企业19.5万家,基金会2168家。随着当代中国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多元化,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角色,如直接参与服务提供、反映公众的服务需求、评估服务质量与绩效等。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具有鲜明的国家培育特征,社会组织则在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供给中不断成长。(24) 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有效促进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的形成。
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运作原理,可以概念化为“公共服务生产的二次分工”(25)。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从政府自己生产服务,到服务外包,发动社会和市场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再到复杂的混合式供给,公共服务的参与方之间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分工。第一次分工是将公共服务的规划者和生产者进行分离。服务的规划者一般是政府,在初次分工中,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可以不再担任服务生产者的角色,而是将生产职能划分出去,政府活动范围转为拨付资金、制定政策和监督管理。服务生产者可以自己直接生产服务,生产者除了生产之外,也需要进行监督管理和整合资源。对于生产者自身不能有效生产的服务,则可以通过整合其他服务资源来生产,间接满足服务需求。这一过程也就是“公共服务生产的第二次分工”。在第二次分工中,服务生产者既可以是社会组织、市场中的企业和公民,也可以是政府机构。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总是扮演规划者的角色,它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境扮演不同角色。这种政府主导的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通过竞争机制与合作机制的有机结合以及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的具体功能角色的精细化划分,突破了公共部门直接提供以及简单的市场化或社会化提供的局限,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适应了现实生活中公共服务的混合性和复杂性,而且有效地平衡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益与效率目标。
在社会保障领域,中国政府坚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思路,即实施“社会保险”的社会化运作方式,由国家承担保险基金的最终兜底责任,但在强调个人权利与缴费义务统一的同时,也不断强化政府责任、增加社会保障补贴比例,大大提高了社会保险的享受标准。近年来,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资金缺口和保值增值困难问题不断突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民营化改革的示范作用下,不少论者提出了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的改革建议,但鉴于社会保险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央政府对此始终保持谨慎态度。此外,中国政府也开始借鉴世界银行提出的“三支柱”养老模式,扶持和鼓励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但力度不大,效果也不明显。
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或创新的最大困难,主要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2005年,一份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公开宣布“医改失败”,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失败原因和“新医改战略”的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市场化和商业化,以及政府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不宜引入市场机制,“新医改”应向“公益性”回归,实施“补供方”的公立医疗机构供给模式,并建立健全“全民医保”制度。(26)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失败的原因恰恰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伪市场化”。这种“伪市场化”的实质是“行政化”,表现为公立医疗机构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但组织上仍隶属于行政部门,没有实现法人化和民营化;同时,医疗服务定价受到严厉的行政管制,市场机制没有起到主要作用,公立机构占据供给面的统治性地位,民营机构发展空间小,等等。(27) 正是在“伪市场化”改革、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包括医疗保障补贴不足和公立机构运营补贴不足两方面)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和“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于新医改的方向,这种观点主张采取“补需方”战略,在医疗保障方面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建立“全民医保”制度,并大力增加政府财政补贴;在医疗服务供给方面,采取“有管理的竞争”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实现公立机构的法人化和民营化,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参与竞争,全面推行“政府购买医疗卫生服务”模式。(28)
可以看到,两种观点在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建立“全民医保”制度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冲突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公立化”或“市场化”改革路径之争上。在2009年4月出台的“新医改方案”中,中央政府有意平衡两种不同意见,既指出要“完善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客观反映市场供求情况和生产服务成本变化的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又提出医疗服务“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对于这个“折衷调和”的新医改方案的可能效果,不少“市场派”观察者持质疑态度,批评这种“公立化”趋势实质上在“向计划经济回归”。
事实上,在新医改方案出台的一个月前,陕西省神木县在全国首次推出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由政府担当唯一筹资主体,统一组织所有医疗资源,向全县居民提供几近免费的医疗服务。“神木模式”运行一年多来,社会各界褒贬不一。2010年,“神木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多所高校的社会政策研究专家评定为“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之一。一时间,“神木模式”引人注目。的确,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建立全国性的免费医疗制度并非不可能,但真正实施这一制度后能否避免类似于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制(NHS)的诸多弊端仍是未知之数。也正是基于类似的理由,在“新医改”实施一年多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尽管有了较大提高,但不少观察者仍忧心忡忡于以公立机构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改革所可能产生的经营效率问题。
在我看来,公共服务的“政府主导”不能等同于“政府包办”,回归公共服务的“公益性”更不应等同于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立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强化,但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运作也必须坚持。平衡公共服务的公益与效率目标,实施基于“二次分工”的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失为一种可行且有效的选择。
五、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问题与未来
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一是公共服务仍屈从于经济建设,财政投入比例偏低,总体供给水平不高;二是应急性、二元化和碎片化的社会政策发展,大大限制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性与均等化程度;三是财政收入中央集权化与公共服务供给地方化之间的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地方财力有限、积极性不高依然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主要障碍;四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缺乏制度化和有效的推广机制,复合式供给机制有待完善和扩展,特别是政府规制能力迫切需要提高;五是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缺失,导致供给与需求相对失衡,投入与产出效率较低。这些问题与不足,严重限制了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亟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特别是要着力突破体制性限制与障碍。鉴于从制度建设上完全实现公共服务的平等性和可及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扩大国家福利的供给规模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根本所在,所以,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未来取决于以下领域的改革和建设。
第一,深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成“服务型政府”。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与职能定位,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发展态势。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和职能定位主要由党和国家的发展理念及其具体化的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制所塑造。(29) 在20世纪80—9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以“GDP”等经济指标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干部晋升“锦标赛”,是促成这一时期地方政府逐渐演变为“发展型政府”的主要原因。这种“发展型政府”在行为取向上表现为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在职能定位上表现为经济建设领域的“越位”、“错位”以及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领域的“缺位”。进入21世纪后,随着发展理念的转变,中央政府不断要求各级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然而,在地方政府现实的行为取向和职能定位中,公共服务仍居于经济建设之下。这意味着,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根据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进行“大部制改革”之类的政府机构重组,更需要重新设计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制,也就是建立公共服务的考核指标体系,将其纳入“锦标赛”之中并提高其相对于经济指标的权重。
第二,全面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体系,突破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二元化和碎片化的制度设计。
社会政策体系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基础。2002年以来,尽管中央政府集中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策,但仍缺乏社会政策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宏观战略。一些重要社会政策的出台,常常与突发的偶然性事件(如“非典”)或社会危机密切相关,或者是来自某一社会群体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形成的政策压力,具有强烈的应急性。正是这种应急性特征,进一步导致了社会政策发展的二元化和碎片化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基本社会保障领域,城乡间、群体间、区域间实施不同政策,而且不同政策间、制度间的政府补贴和待遇水平差距较大。由于背离了制度统一原则,近年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再次扩大了社会不平等,而且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分治结构。也就是说,2002年以来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通过碎片化、二元化的制度覆盖方式,在机会均等的意义上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和可及性,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提高投入均等和结果均等意义上的公平性。平等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使所有人都能平等获得“社会通行标准”的公共服务是国家必须履行的一项基本职责。(30) 因此,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首要目标,当是突破现行城乡二元和碎片化的制度设计,构建起一个普遍主义、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实施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政策,并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主调整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积极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全面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
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需要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如果不改变现行政府间的职责分工,就必须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重新确定地方政府的税收分享比例,扩大地方财政的税收资源。如果不改变现行分税制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划分,就必须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重新设计政府间职责分工,由中央政府担当公共服务支出的责任主体。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政策制定、资金筹集和集中管理,并承担大部分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执行的代理机构。考虑到构建城乡一体、全国统一规范的社会政策体系这一目标,在财权划分不变的情况下重新设计中央与地方的职责分工较为可取。
建设“民生导向”的公共财政体制,还必须全面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从财政支出的“存量结构”方面建立制度化、弹性化的公共服务投入增长机制。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各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资源较多地来自于财政收入的“增量”,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两项支出比重依然偏高。
第四,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结构,积极推动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化与社会化改革,大大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与质量,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公共服务供给的总体短缺和效率低下状态。国际经验表明,相比于公共部门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社会化提供在提高效率与质量上更具优势。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应当继续坚持市场化与社会化改革的思路,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结构,即在确立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的作用,不断深化和细化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种参与方尤其是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分工,强化政府对市场机制与伙伴关系的规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供给格局,积极推动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特别是在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必须摒弃“以公立化保障公益性”的错误观念。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往往始于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如果效果比较显著,其他地方政府则开始仿效,最后由中央政府在全国推广和普及。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推广,常常要经历较长的时期,这也是造成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创新上,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地方创新到全国推广历时五年之久,并且期间各地政策五花八门、标准不一,大大增加了制度统一和规范整合的成本。如何使地方创新成功的制度化并在全国较快地推广,如何促进中央与地方在制度创新上的密切配合,是当代中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急需解决的难题之一。
第五,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
尽管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展、供给水平大大提高,但仍与公众实际的公共服务需求之间有着较大差距。从供给面看,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失衡源自于社会政策体系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滞后;从需求面看,则与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密切相关。信息充分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近年来,由于公众利益表达的正式渠道少且作用有限,不但限制了决策信息的有效传输从而影响了公共决策的有效性,还导致非制度化的利益诉求行动如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此外,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模式,也是导致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真实的偏好和需求发生偏差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建立健全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的同时,还须稳步扩大政府公共服务决策与预算编制中的公众参与。
进一步地,当代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注重解决投入不足和投入不均问题,而鲜有关注基于投入—产出效率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既缺少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估和满意度评价机制,也未建立有效的政府自身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目前,“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属于‘投入型’而非‘效率型’”,各地的投入产出相对效率没有明显差异,呈“效率低水平趋同”状态。(31)
总之,要实现人人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政府需要在公共服务的社会政策和体制机制构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重新设计地方政府工作考核评价和干部考核评价体制,以确立公共服务在地方政府职能履行中的核心地位;加快构建普遍主义、城乡一体的社会政策体系,以制度统一实现公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利;重构政府间财政体制和职责分工、全面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积极探索地方创新的制度化推广机制,全面推进复合式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创新,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公益与效率目标平衡;建立健全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以有效回应公众需求、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
(本文系香港中美交流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多视角的观察”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该课题由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特首董建华发起,课题的主要内容是从中美学者的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展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进步成果。感谢本课题的中方召集人俞可平教授和课题组成员王长江、杨光斌、景跃进、王名、林尚立、黄卫平、时和兴、周光辉、何增科、燕继荣教授等在多次内部研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感谢Kenneth Lieberthal,Larry Diamond,Jacques deLisle,Joseph Fewsmith,David M.Lampton,Jean C.Oi,Melanie Manion,Anthony J.Saich,Andrew Walder,Mary Gallagher,Cheng Li和Lynn T.White等教授在2010年10月29-30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国政治发展:中美学者的视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建设性意见,特别感谢Anthony J.Saich对本文的书面和现场评论;感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何子英博士为本文所做的大量工作。)
注释:
① 本文所讨论的“公共服务”主要指社会政策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使用的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于或计算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09年卷)以及中央政府各部门的官方网站。
② Tony Saich,Providing Public Goods in Transitional China,Palgrave MacMillan,2008.
③ Saunders.P.& Shang X Y,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01,35(3),pp.274-289.
④ Joseph Wong,The Adap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East Asia,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04,(4),pp.345-362.
⑤ Mark W.Frazier,China's Pension Reform and Its Discontents,The China Journal,No.51 ,2004,pp.97-114.
⑥ Shih-Jiunn Shi,Left to Market and Family-Again? Id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Pension Policy in China,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06,40(7),pp.791-806.
⑦ Athar Hussain,Social Welfare in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ree Transitions,Nicholas C.Hope,Dennis Tao Yang,Mu Yang Li(ed),How Far Across the River?: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 Christine P.W.Wong、Richard M.Bird:《中国的财政体系:进行中的工作》,见劳伦·勃兰特、托马斯·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⑨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见张军、周黎安编:《为增长而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⑩ Dorothy J.Solinger,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1) 燕继荣:《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再造七项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12) 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见周建明、胡鞍钢、王绍光:《和谐社会构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13) Bjorn A.Gustafsson,Li Shi,Terry Sicular (ed),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2.
(14) Tony Saich,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Palgrave,2001,p.241.
(15) Adam Wagstaff and Magnus Lindelow,Extending 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An Impact Evaluation of China'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9,(28),pp.1-19.
(16) Joe C.B.Leung,The Emergence of Social Assistance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06,(15),pp.188-198.
(17) Catherine Jones Finer (eds),Social Policy Reform in China,Ashgate,2003,Chapter 14,15.
(18) 高培勇编:《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第二章,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19) Yongnian Zheng,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16.
(20) Roy Bahl and Jorge Martinez-Vazquez,Fiscal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T.N.Srinivasan and Jessica Seddon Wallack (ed),Federalism and Economic Reform: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1) World Bank,China: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Finance,a Review of Provincial Expenditures,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2.
(22) 2010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2010年预算案,其执行情况尚未公布。
(23)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007/08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第88-89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
(24) 郁建兴、周俊:《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公民社会》,载《二十一世纪》,2008(2)。
(25) 郁建兴、吴玉霞:《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载《学术月刊》,2009(12)。
(26) 葛延风、贡森:《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27) 顾昕:《走向全民医保》,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8) Karen Eggleston,Li Ling,Meng Qingyue,Magnus Lindelow,Health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a Literature Review,Health Economics,2008(17),pp.149-165.
(29) Susan H.Whiting,Power and Wealth in Rural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0-101.
(30) [英]马歇尔、吉登斯等著,郭忠华、刘训练等编:《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1) 陈昌盛、蔡跃洲:《中国公共服务报告2006:中国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变迁与绩效评估》,第xiii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标签:社会政策论文;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公共服务设施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 服务经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 财政学论文; 基础教育论文; 义务教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