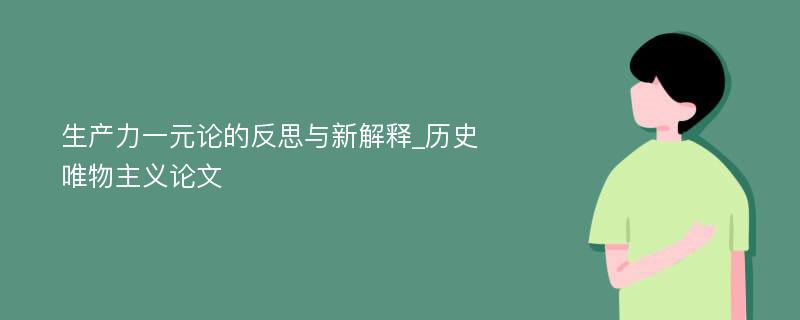
对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反思与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生产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普列汉诺夫是明确提出并系统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原理的第一人,其实质就在于确立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对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一元决定性地位和作用。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其观点的翻版。后世思想家对传统教科书体系、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种种批评、保卫、重建与超越的倾向和立场,无不与普列汉诺夫的阐释相勾连。因此,详尽梳理和准确把握普列汉诺夫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并站在方法论高度予以深入反思,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一元决定:“经济”抑或“生产力”
1.历史观中唯心主义的二律背反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的世界观”,代表了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因而可以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①,也是以往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产物。不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发展,就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他详细考察了18世纪下半期以来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以“感觉论”对抗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功能均是感觉的变形,而感觉则是“周围环境”对人发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思想、感觉和意愿的人乃是其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然而,他们并没有循此思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规律”上来,进而解决究竟是什么东西制约着社会环境的结构以及社会环境的发展有哪些规律的问题,反而认为环境及其一切属性都由人们的意见所创造。这便是有名的“环境决定意见”和“意见支配世界(即社会关系)”的二律背反。
19世纪20年代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和米涅等,开始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止步的地方。法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使他们更加倾向于“环境万能”的思想,并开始从新的观点来观察环境,认为“政治宪法”和“政治制度”产生于“社会环境”,即“人们的公民生活”或“社会本身”,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财产关系”和基于财产关系的“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结构生根于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又取决于所有制的状况。依照普列汉诺夫的理解,这就等于默认了:“为着解释某一国家的政治生活……要一般地研究它的一切财产关系。”②遗憾的是,当进一步讨论“所有制状况”和“财产关系”的起源时,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人的本性”,一方面认为人的本性的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说明,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需要的发展由人的本性的发展来说明,不仅陷入了新的二律背反,而且事实上回避了问题本身。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19世纪前半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着力在历史中寻求“规律性”,而不是像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把人类历史看成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们也没有像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样仅仅看到“财产关系”对于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进一步提问:“为什么正是这些关系,而不是别的任何关系起这样重要的作用呢?”③其答案是:财产关系由农业和工业等“实业”和“生产”决定,人们在财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取决于他们在实业和生产中的地位。这样,他们的分析就率先进到了“物质生产”的层面。尽管如此,他们最终还是没能摆脱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路,而且比后者更为彻底地坚持“意见决定环境”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环境决定意见”的另一面。因为他们发现,要生产就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则决定于生产者的智慧和知识。所以,生产和实业的发展最终由人的智慧或知识的发展决定,知识的发展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因素。他们还认为,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发展又体现着“人的本性”的发展,因此“人类的历史以人类的天性来解释”。可是,“从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人的天性呢?从历史中”。④这样,他们就重蹈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人性决定历史”和“历史决定人性”的二律背反的覆辙。
同样是在19世纪前半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抛弃了人具有固定不变的本性的观点,拒绝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社会现象。他们把社会生活看成是有自己固有规律的必然过程,认为任何事物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因此,没有永恒的东西,一切皆变。但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规律性不过是“绝对理念”自身的辩证运动。无论是人还是社会关系,其本性都以之为依靠才存在的最后基础,就是“概念”或曰“理念”。特定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这理念的实现。每一个民族都在实现自己特殊的理念,而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特殊理念都是绝对理念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历史不过是逻辑的应用,说明某个历史时代,就等于指出它对应于绝对理念逻辑演进的哪一个阶段。普列汉诺夫指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本身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将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人格化为绝对理念的形态,而在这个理念中找寻一切现象的解答,唯心主义这样便引导自己走入死巷。”⑤
黑格尔哲学受到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猛烈批判。鲍威尔兄弟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既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也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不仅把人变成了完全消极被动的东西,而且它本身就是虚幻的。在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不是什么绝对理念,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理性”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力量。没有绝对的理念,没有抽象的理性,只有人们的自我意识,只有有限的、永远变化着的人类理性。普列汉诺夫就此认为,把“人类理性”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动力,用理性自身固有的内在属性来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意味着把人的理性重新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意味着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在新的形态下的复活,也同时意味着重新踏上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走过的“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⑥。
总之,在历史领域,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二律背反”,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思想矛盾使他们最终都投向历史唯心主义的怀抱。只有马克思才从思想的自我矛盾中走出来,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2.马克思对唯心史观二律背反的超越
依普列汉诺夫之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这里获得了“再生”,但这种唯物主义决不是18世纪末法国唯物主义学说的简单重复,它“以唯心主义的一切成就丰富了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辩证的方法,是在现象的发展中,在现象的产生与消灭中来观察现象”,因而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⑦。
鲍威尔兄弟认为,一切重大的历史冲突都不外是观念的冲突。马克思则认为,观念必须符合于“现实的经济利益”,只有理解经济利益,才会获得理解历史发展进程的钥匙。就物质利益而言,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曾经用它来说明特定社会的特定状况,但这只是“意见支配世界这个公式的变形”⑧。因为在他们那里,人们的利益本身也依赖于他们的意见,并且随着这些意见的变化而变化。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把“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确认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和根本,这一见解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事实上的认同,用普列汉诺夫的话说就是:“黑格尔也被迫地承认‘所有权状态’的决定的意义”⑨。马克思将之吸收进来并概括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均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其总和就是所谓的“市民社会”,对它的解剖应当到“经济”中去寻找。
特定社会的经济又依赖于什么呢?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直接地援引“人的本性”来解释。黑格尔则懂得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应当在人的本性之外去寻找,这是他的巨大功绩。尽管如此,由于他错误地在精神的属性中、在绝对理念之逻辑的发展规律中寻找人类历史运动的钥匙,所以又拐弯抹角地复归于人性的观点,因为“正如我们所已经知道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我们思维的逻辑过程的人格化”⑩。青年黑格尔派也没有克服这种错误,他们更是径直用“人”的“精神”和“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此相反,马克思“把人的天性看作是永远地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其原因在人之外”。这是因为,随着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必然要改变其全部生活式样,全部习惯,全部思想式样,全部‘天性’”(11)。同时,如果说生产力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生产中发生的“人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人们的相互联系和关系”。只有在人们的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内部并通过这些联系和关系,才会产生人们对自然界的那些作用。因此,人的本性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生产力的状况对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有决定的影响”(12)。
总之,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的状况,以及跟着它,社会环境的全部性质……不是为绝对精神的属性,不是为人性的性质所决定的,决定它的是‘在自己生活的生产的社会过程’中、即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人们彼此之间必然发生的互相关系”。(13)这一天才发现给予唯心主义历史观以致命打击,并使马克思彻底从“环境”与“观念”,从“人性”与“历史”之间的二律背反中走出来。
3.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与经济唯物主义
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经济唯物主义”。对此,普列汉诺夫指出,第一,在任何一位民粹主义者看来,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者”,就是“主张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有支配意义的人”(14)。然而,认为经济“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人却不止马克思,他也从来没有称呼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第二,“经济唯物主义”是一种“因素论”。人类社会在它那里就像“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律、经济等等——各自从它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社会历史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都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并列平行的力量。历史唯物主义则持不同的观点:“历史的‘因素’是一些纯粹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们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不同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乃是每个一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15)第三,“经济唯物主义”还是一种“折中主义”。它只承认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为“他们借助于著名的‘互相作用’可以对付得了任何问题”(16)。马克思则“坚持以一个原则来解释全部历史过程”,因而属于典型的“一元决定论”。马克思“新的历史理论的任务是在以……经济弦线——即在实际上是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生活的全部总和’。‘弦线’——这只是在这个字的一定的意义上”(17)。
在此,普列汉诺夫把“经济”等同于“生产力”,认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其他一些地方,他又严格地把经济和生产力区分开来。他讲:“按新理论,人类的历史运动是由引导到经济关系变化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任何历史研究的事业不得不从研究某一国度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状态开始。”(18)他还说:“经济本身亦是派生的东西,正如心理一样。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是变化着的:生产力的新的状态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从这里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说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的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19)经济关系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经济本身是从生产力的状况中派生出来的,可见生产力不同于经济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什么“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而是“生产力决定论”。
西方一些学者指责普列汉诺夫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了“工具—技术决定论”(20),其实不然。他曾明确指出:“人对自然的生产作用的过程不仅需要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只是为生产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因此更正确些,不说劳动工具的发展,而是一般地说生产手段、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完全无疑的,在这个发展中最重要的作用正是属于或者至少至今曾是属于劳动工具的。”(21)就是说,劳动工具的作用无论多么重要,也不过是生产资料的一个部分,是物质生产得以进行和生产力得以形成的一个要素。因此,不能用劳动工具的发展代替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而不是劳动工具一元决定论。
二、“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方法论反思
1.“归根到底”与发生学思维方式
虽然说,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在历史观上都陷入了“二律背反”即思想的自我矛盾,但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有各种不同的矛盾”(22)。有些矛盾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毫无裨益,而另一些矛盾则是人类思想向前发展的动力。上述马克思之前的历史观中的矛盾就属于后者,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孕育并降生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是如何从唯心史观的二律背反中走出来的呢?普列汉诺夫认为,第一,在意见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毋庸怀疑的相互作用。然而,“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承认这个互相作用上,因为互相作用远不能给我们解释社会现象。为着理解人类的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人类意见的历史,另一方面,人类在其发展上所经历的那些社会关系的历史;应该要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23)这就是说,停留于意见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充其量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认识;要进到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历史本质的层面,就必须超越意见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观点;为此就需要找到第三种因素,它既不同于人类意见,也不同于社会环境;同时,它既决定着人类意见,也决定着社会环境。第二,18世纪的人们常常说,任何特定民族的“国家制度”都是受这个“民族的风俗”所制约的;也同样常常有人断言,特定民族的风俗受其国家制度的制约。但是,“假如国家制度预先要有那种道德风习,它才能影响它们,那么,显然,促使这些道德风习最初出现的就不是国家制度。对于道德风习,亦应该这样说,假如它们预先要有那种它们要加以影响的国家制度,那么,显然,国家制度就不是它们创造的。为了解脱这笔糊涂账,我们应该找到这样一个历史因素,它既产生这个民族之道德风习又产生它的国家制度,而且这样便产生它们的互相作用的可能”。(24)这就是说,从“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来看,国家制度和民族的风俗相互作用的观点显然是混乱的,说民族的风俗创造了国家制度就不能同时说国家制度也创造了民族的风俗;反之亦然。要彻底摆脱这种混乱状态,也同样需要找到第三种因素,它既产生和创造了相互作用的两种因素,又产生和创造了它们相互作用的可能性本身。第三,推而广之,“互相作用无疑地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之间”,这个观点虽然正确,但能够说明的东西却很少,包括“对互相作用着的力量的产生没有给予任何指明”(25)。只有对社会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产生”问题作出说明,才能从根本上超越相互作用的观点。折中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满足于发现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无法用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些社会力量的“产生”或“起源”问题(26)。
从普列汉诺夫的这些论述来看,他显然看到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区别,并反复强调“不要停留在现象的表面上”,要对现象包括“社会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和说明,以此获得对历史本质的认识。(27)那么,本质究竟是什么?本质与现象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他看来,首先,这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单向关系,因而不同于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其中,本质决定着现象,现象被本质所决定。其次,这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的单向关系,因而有别于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其中,本质创造了现象,现象被本质所创造。本质对现象之所以具有“决定”作用,就是因为本质产生和创造了现象。最后,“本质”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产生”或“起源”问题,探索本质就是解决现象“从何处来”的问题,就是寻找和确认“时间”上“在先”的“本质”。本质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创造现象,就是因为本质在时间上是最早的或最初的存在,没有本质就没有现象。这里,普列汉诺夫所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发生学”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正是凭着这种思维方式,马克思才实现了对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在谈到生产力的一元决定性作用时,普列汉诺夫讲:“互相作用存在于诸民族的国际生活中,同样亦存在于其内部生活中;它是完全自然的和无条件必然的,可是本身说来,它还什么也不能解释。为了了解互相作用,应该弄清互相作用的力量的性质,而这个性质却不能在互相作用这个事实中找得最后的解释,尽管这些性质由于互相作用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地,互相作用的力量的性质,彼此影响的社会有机体的属性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来说明的:即这些有机体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则为它们的生产力的状态决定的。”(28)生产力决定着相互作用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性质,决定着彼此影响着的各个社会机体的性质,因此,生产力对这些社会力量和社会机体具有“最后”的和“归根到底”的解释作用。
我们知道,无论恩格斯还是马克思本人,都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确认过生产力的一元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就讲:“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29)那么,“归根到底”或者说“最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从普列汉诺夫的论述可以看出,“最后”的和“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指的就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对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之所以具有一元决定性作用,就是因为生产力是时间上“最先”、“最早”的存在,其他社会因素和力量都是从生产力中“产生”出来的。认识和把握了生产力,就解决了社会各种因素和力量的“起源”问题,就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普列汉诺夫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政治必须适合于经济,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必须适合于经济和政治,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政治的意义,否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的意义,“马克思没有否认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他只是阐明了它们的起源”(30)。所以,“历史决定论”所要回答和解决的,就是社会各种因素和力量的“起源”问题。
我们看到,普列汉诺夫无时无刻不在惦记和思考着“起源”问题,不仅追问“家庭的起源”,而且追问“财产的起源”和“所有权的起源”;不仅追问“国家的起源”,而且追问“法律的起源”和“艺术的起源”;最后,他还追问“社会环境的起源”和“人的起源”。这样,逼问各种事物的“起源”,梳理各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之间的“先后关系”,就成为普列汉诺夫固定不变的思维方式,也构成其历史观的核心议题和中心任务。
问题是,能否把“决定论”等同于“起源论”?能否把“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归结为“本源”与“派生”的发生学关系?马克思是否借助于发生学思维方式才克服了唯心史观的二律背反?马克思是否在发生学意义上确立生产力之于社会历史的一元决定作用?发生学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历史构图呢?
2.“发生学”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
(1)“起点”处再追问:走向地理环境决定论。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着手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遇到“社会关系发展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决定社会关系的原因是经济。经济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他看来,“马克思……把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由什么原因来决定”(31)。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按照发生学思维方式,我们需要继续对作为社会历史“起点”、具有一元决定作用的生产力进行追问:生产力在创造和决定经济之前,它本身又被什么所创造和决定呢?普列汉诺夫的回答非常明确:“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解决方式首先就是指出地理环境的性质”,“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32)如果说,“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着人对自然的统治的程度”,那么,正是自然界本身使人得到征服自然的手段。因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33)。这样,普列汉诺夫就从“生产力决定论”转向“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招致诸多瓜葛和非议。
普列汉诺夫指出:“制约着思维的运动的情况应该到法国启蒙派找寻过的地方去找。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停留于那个他们所不能超越的‘界限’上了。我们不仅说,人及其一切思想感觉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力图理解这个环境的起源。我们说,环境的属性是为某种在人之外的和至今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原因所决定的。”(34)这个“处在人之外”并且决定着“社会环境”的属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按照普列汉诺夫的逻辑,它“归根到底”是也只能是不同于社会环境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决定着社会环境,进而决定着人、决定着人的全部思想和情感。
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制度“归根到底”也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他说:“人不是孤单地和自然斗争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和自然斗争的是社会人,即按其范围说或大或小的社会联合。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到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不仅如此,地理环境还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地理环境对于更大的社会的命运,对于产生于原始氏族组织废墟之上的国家的命运所加予的决定的影响,不会更小。”(35)
(2)“现实”关系再追问:新的二律背反的建立。按照发生学思维方式,地理环境之于生产力、生产力之于经济、经济之于社会关系,仅仅在“起源”的意义上才具有决定性作用。问题是,这是否同样适合于“产生”,以后的情况呢?地理环境之于生产力、生产力之于经济、经济之于社会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历史往后的发展中是否继续有效呢?
对此,普列汉诺夫在各个层面作了说明:第一,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言,“财产关系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上形成以后,在相当时期内是帮助这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但是后来它又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这就告诉我们,虽然生产力的某种状态是引起某种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的原因,可是这种生产关系一旦作为上述原因的结果而发生以后,它又从自己方面开始影响这种原因了。这样便发生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间的相互影响”。(36)第二,就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而言,一旦“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们的往后发展就按自己本身的内部规律进行,它们的作用,加速或阻滞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人类的历史运动。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了。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于人。可是,因为这样,人对周围的地理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变动不定的了。在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这种关系都和以前不同。……现代辩证唯物主义这样地解决了18世纪启蒙学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解决的矛盾”。(37)第三,就生产力与社会制度而言,“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但是,某种社会关系一旦发生以后,它本身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就给予很大的影响。这样,起初是结果的东西,现在又变成原因了;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之间发生了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带着各种不同的样式”。(38)普列汉诺夫讲得很清楚,只是在“起源”处,地理环境对生产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才成立。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一旦产生,它们与生产力之间就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又使得地理环境只能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环境。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对生产力的作用表现为:它们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它们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依循同样的思路,普列汉诺夫解释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的基础上面既然长成了社会关系、感情和概念的整个上层建筑,而且这个上层建筑起初也是帮助经济的发展,后来又是阻碍经济的发展的,那么,上层建筑和基础之间也就发生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可以拿来解释一切骤然看来似乎是跟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矛盾的现象。”(39)
这样,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如果说马克思超越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二律背反,那么这种超越只是在“起源”的意义上才是成立的。就社会历史在往后的发展中的各种现实关系和情况而言,普列汉诺夫的阐释又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等新的二律背反。
(3)“现实”关系再追问:同义反复与逻辑混乱。普列汉诺夫对发生学思维方式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种种偏弊并非毫无察觉,为避免之,他曾经尝试着立足于物质生产和生产力本身来解决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他说:“劳动工具既然成为生产的对象,那么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用以制造的劳动工具。这是不用任何解释,对任何人都明白的。”(40)实际上,制造劳动工具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不仅仅甚至不主要取决于既有的生产工兵。因此,就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具体关系而言,生产工具决定生产工具是一种片面的认识。他还说:“每个特定的民族,在其历史的每一个特定的阶段上,其生产力之往后的发展是为我们所观察的时期的生产力的状态所决定的。”(41)如果说这是对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概括,那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力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动力的“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抽象,并不存在另外一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力。
发生学思维方式使普列汉诺夫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例如他讲:“据马克思的意见,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头一项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42)没有生产关系的中介,地理环境就不起作用;而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地理环境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普列汉诺夫对地理环境、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概括实在令人费解!
3.马克思对“发生学”思维方式的批驳
由上可见,凭借发生学思维方式,并不足以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事实上,早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马克思就对发生学思维方式作过有力批驳。他说:“现在对单个人讲讲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这就是说,在你身上,两个人的交媾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人。这样,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因此,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43)马克思关注和强调的,是“子为父母生”的运动,而不是“子为父所生”的过程。前者是一种有限的循环,后者则是一种无限的绵延;人的主体地位在前者得到彰显和确认,在后者则终究会被遮蔽和抽象掉。究其原因,恰恰在于后者所采用的是一种发生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所关注的那个无限过程会驱使我们不断进行追问,直到我们提出“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样的问题。但是,生出“第一个人”的肯定不是“人”,同理,生出“整个自然界”的也肯定不是“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因为,既然提出自然界和人的“产生”和“创造”问题,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所以,“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44)对“无限后退式”的发生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尽管仍显得过于思辨和抽象,但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处于思维方式的转型期。通过对“不断向前式”的现实运动的思考和探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创立了“本质抽象”的科学方法并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大厦。
三、在“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之间
1.“本质抽象”与“线性决定”
社会由人组成,历史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因此,人始终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主体”。普列汉诺夫指出:如果“以为‘经济’唯物主义者(此处是借经济唯物主义之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之实。下同。——引者)只应该说到‘生产与交换形式的自己发展’”,似乎“生产形式能够‘自己’发展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呢?这就是人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人们,它怎样能够发展呢?试想,哪里没有人,哪儿亦就没有生产关系。”“把人物和社会生活规律,人们的活动——他们共同生活的内部逻辑对立”起来,是“荒谬”的(45)。生产关系和生产形式不会“自己”或“自动”发展起来,没有人和人的活动,就不会有生产关系和生产形式,就不会有社会历史规律。
同时又必须看到,只有对人的活动、对人的活动的各种构成要素、对活动的人所处其中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科学抽象,才能揭示和把握它们的共同本质和发展规律。以此来看,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无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们都是一种本质抽象。
正是借助于科学抽象,社会历史在我们面前才既不再是康德意义上的“杂多”,也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无规定”,而是得到本质性规整和规律性把握。区别仅在于,施行科学抽象、把握本质和规律,既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也可以选择不同的层面。以此来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抽象不同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抽象,“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抽象又不同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抽象。与此相联系,“经济规律”不同于“政治规律”,“政治规律”又不同于“文化规律”。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说到在人类思想的发展中,或者确切些,在人类的概念和表象的结合中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这点据我们所知,‘经济’唯物主义者之中是没有一个人加以否认的。他们之中谁也没有,例如将商品流通的规律和逻辑的规律同一化。可是这派唯物主义者之中谁也不以为可以在思维的规律中找到人类智慧发展的最后原因、基本推动者。”(46)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逻辑规律就不同于经济发展的规律如商品流通规律。此外,不同时代的思想之间存在的“‘做’与……‘相反的东西’”,即“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是思想发展的独特规律(47)。所以,绝不能用一种本质抽象排斥和取代另一种本质抽象,也不能用一种规律排斥和取代另一种规律。
当然,不同规律、不同本质抽象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例如:“什么是阶级的互相关系呢?这首先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这些关系在社会的政治组织中和在各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得到自己的表现,而这个斗争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推动。在经济基础上必然地建筑着适应于它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48)在此,阶级和阶级斗争不仅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纠结在一起,而且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纠结在一起。下列说法或许不无道理: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都是一种立足于“客体”的本质抽象,而阶级和阶级斗争则是一种立足于“主体”的本质抽象。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总之,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可以说是在“社会形态”层面的一种本质抽象。较之于其他层面——如“经济的社会形态”或“政治的社会形态”或“文化的社会形态”——的本质抽象,它所处的层次最高,抽象的程度也最大。只要提升到社会形态的高度,就必然存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单向决定关系。也只有立足于社会形态的层面,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论才是成立的。
普列汉诺夫认为,并不存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即使承认这种相互作用,我们对社会生活的分析也不能就此止步。这在本质抽象的意义上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失之偏颇的是,他又认为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政治制度影响于经济生活。它们或者促进这个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它”(49)。其实,作用与反作用无非就是一种相互作用,而在本质抽象的意义上,只存在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不存在所谓的多元决定;只存在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的“线性决定”,不存在所谓的“相互决定”;只存在政治必须适合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存在经济必须适合于政治发展的要求。
普列汉诺夫还指出:“我们说过,如果知道了社会的生产力——知道了它的经济结构,因而亦就知道了它的心理。根据这点,可以把这样的思想加在我们头上,即从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状况出发就可以确切地断定它的思想的结构。可是,这不是这样的,因为每个特定时代的思想体系永远是和前一时代的思想体系有密切的——肯定的或否定的——联系。”(50)这就说明,经济决定文化的规律只是社会形态层面的规律,只是揭示了特定社会形态的两个组成部分即经济与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它既没有穷尽经济本身也没有穷尽文化本身的所有本质内涵和发展规律。“这类例子充满于人类思想史上,而所有这些例子证明一件事:为着理解每一个特定的批判时代的‘智慧状态’,为着解释,为什么在这一时代中正是这些学说,而不是另一些学说胜利着,应该预先认识前一时代的智慧状态;应该知道,哪些学说和学派曾在当时统治过。如果没有这一点,则不管我们怎样好地通晓它的经济,也完全不能理解特定时代的智慧状态的。”(51)
作为本质抽象,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需要借助于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理解和把握;但是,它本身又决不是人的头脑的虚构,而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其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力是一个“总的结果”,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应、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则是一种“总的趋势”。马克思就曾明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总的说来,“一般规律”是“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而存在的。既然是总的“结果”和“趋势”,生产力一元决定规律就决不是“预成”的,而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中不断地“生成”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也绝不是什么先验的“目的论”,而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事后”的总结和概括。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存在“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不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只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很难说在时间上是先有经济,随后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最后才是文化的登场。实际上,作为本质抽象,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单向决定关系,不过是构成特定社会形态的“总体关系”,也是对这种总体关系的“总”的“思维把握”。在这一点上,当普列汉诺夫讲“经济统治着政治,生产力的发展……先于人民的政治发展”(52)的时候,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因为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规律是社会形态层面的规律,只有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才能形成并显现出来,所以对于历史当事人来说,它往往作为一种“盲目的必然性”(53)而发挥作用。正像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规律时所说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当事人方面看,“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54)。只有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历史规律才能为我们的认识所把握,从而转化为人的“自觉行为”。
2.“现象具体”与“相互作用”
本质皆是抽象的,现象则总是具体的。从现象具体来看,不存在“生产力”,只存在它的各种要素,如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不存在“生产关系”,只存在它的各种要素,如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和劳动产品的分配权;不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只存在各种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文化要素。必须把生产力和它的各种要素区别开来,否则,就会把生产力看成是某种“具体”存在,从而将之“实体化”。本质抽象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现象具体也有各种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我们可以把人的活动按其本质划分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某个(具体)人的活动不能兼具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人的关系按其本质划分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某个(具体)人不能同时处在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关系之中。
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在本质抽象层面是一种“线性决定”关系,那么在现象具体层面则是它们的各种要素之间在多个层面展开的、极为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经济要素与政治要素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不同的经济要素之间和不同的政治要素之间也会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正如在一切地方一样,我们碰到的是过程,而不是个别的现象,结果反过来成为原因,而原因成了结果”(55)。普列汉诺夫不仅全面考察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且从这种相互作用出发理解和说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国际关系来看,“因为差不多每个社会都受到其邻近社会的影响,所以可以说,对于每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影响其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环境。每个特定的社会从其邻近的社会方面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是永远也不会等于另一个社会在同时所受到的影响的总和。因此,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历史环境,这个历史环境也许——而实际上亦时常有过——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环境很相类似,可是永远也不会和永远也不能和它完全一样。这给社会发展的过程加上异常有力的多样性的因素,而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从我们以前的抽象的观点上看来原是极端刻板的”。例如:在本质抽象层面,“我们说:生产力的发展引导到私有财产的出现,原始共产主义的消逝”;而在现象具体层面,“我们应该说:产生于原始共产主义废墟上的私有财产的性质,由于每个特定的社会之周围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而大不相同”。(56)由于特定社会周围的历史环境自然也会影响该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意识形态的发展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的依赖性”。所以,“当……我们有着彼此异常有力地互相影响着的诸社会的整个体系时,这时候,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的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复杂化起来了,正如它的经济发展在与别的国家不断的商业交换的影响下复杂化起来一样”。(57)可见,尽管从本质抽象层面看,文化必须适应于政治、政治必须适应于经济,然而从现象具体层面看,“这种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58)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是简单的,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则是复杂的和多样的。
以此来看,如果说政治对经济具有促进或者阻碍的所谓“反作用”,那么,这种反作用所处的层面是也只能是现象具体,在实质上从属于政治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同处于本质抽象层面的“决定作用”有质的区别。从现象具体来看,“特定的政治体系之被创造起来就是为着促进生产力的往前发展”;而历史经验表明,“既然特定的政治体系不再适合于生产力的状态,既然它变成了生产力往前发展的障碍,那么它便开始走向没落,最后,被排除掉”。(59)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本质抽象的层面看,就是经济对政治的单向决定规律,就是生产力的一元决定规律。
所以,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线性决定作用与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之间发生的相互作用,并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的两个过程,而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层面或方面。在人的历史活动中,在各种经济、政治和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得以形成和确立。在时间上,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形成相对地要晚于各种具体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展开,因此,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对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具有“发生学”意义的优先性。没有现象具体层面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就不会有本质抽象层面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对于各种具体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又具有“解释学”意义上的优先性。因为,只有借助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我们才能对各种要素的存在和发展给予“社会形态”高度的理解和说明。就各种具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用“发生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不仅某种经济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在时间上先于政治要素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反过来某种政治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如政治变革)也可以在时间上先于经济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如经济增长),由此便形成经济要素与政治要素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普列汉诺夫承认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但却否认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单向决定作用。他一方面讲: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经济和它的心理乃是人们的‘生活的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的同一现象的两方面,在生产中人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态而一定地结合着”。另一方面又讲:“我们说:社会经济和社会心理乃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而马克思本人则说,经济是现实的基础,其上建筑着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60)他显然意识到了自己与马克思之间的矛盾,却又无力解决这种矛盾,原因就在于他不理解,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单向决定作用并不排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种要素之同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从具体要素的相互作用来看,其中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为人的能动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因此,必然性从偶然性中产生,历史的规律性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交换和流通时指出:“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在这个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61)就商品交换作为无数具体的个别行为而言,是偶然性占据统治地位。但正是在这种偶然的和随机的交换行为中,商品交换和流通的一般规律得以确立和形成。就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而言,交换和生产的当事人是难以理解的,他们所能“意识到”的仅仅是“当下”的交换行为。所以,单从总体趋势和必然性来看,人们的个别行为和具体关系显得“虚幻不实”;反之,单从偶然性和随机作用来看,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规律则同样显得“虚幻不实”。实际上,无论是作为本质抽象的一般规律,还是作为现象具体的个别行为,都具有“客观性”,都是一种“事实”。区别在于,前者属于“超验事实”或“本质事实”,后者则属于“经验事实”或“现象事实”。
社会历史越是靠近本质抽象的层面,就越是处于“线性决定”之中;越是靠近社会形态层面的本质抽象,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就越是明显,人的能动性的空间就越小,甚至不再有能动性。与此相反,社会历史越是朝着现象具体的层面延伸,就越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越是朝着个体行为层面的现象具体延伸,人的能动性的空间就越大,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就越是微弱,甚至不再起任何作用。这是因为,越是具体的人和事,就越是具有多重身份和意义,难以用某种单一而固化的标准进行考量;就越是处于多种关系和矛盾之中,难以用某种线性而僵死的框架加以裁衡。故此,“小尺度”事件总显得千奇百怪,往往是“大尺度”规律所难以解释或解释不了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凸现的是也仅仅是生产力在社会形态层面的历史发展规律意义上的“重要性”,它既不排斥在其他层面和其他意义上其他具体要素的重要性,更不排斥“人”之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由是可知,如果说地理环境曾经对历史发展起过决定作用,那么,它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并非两种不同的作用,而是同一种作用在历史发展不同层面的存在。从现象具体层面来看是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在本质抽象层面来看就是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历史越是向前追溯,自然要素、地理环境对于物质生产的作用就越大,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中就越是居于支配地位,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不过是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在历史早期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并不排斥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外在于生产力的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来说等于“无”,离开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也是“无”。
总体而言,普列汉诺夫认识到,一元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既“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论点上”,仅仅承认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也不能像折中主义者那样陷在相互作用中不能自拔,以为“他们借助于著名的‘互相作用’可以对付得了任何问题”(62)。普列汉诺夫没有把“相互作用”与“一元决定作用”简单地对立起来,用历史发展在一个层面的关系去排斥和否定在另一个层面的关系。但问题是,普列汉诺夫对一元决定作用与相互作用所处的两个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虽然已经看到,一元决定作用是一种“本质关系”,而相互作用则是一种“现象关系”;却没能弄明白,生产力一元决定作用的“总趋势”正是在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中形成的,因而是历史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他错误地把它们分割为两个不同“阶段”,在“起源”的意义上理解一元决定作用,相互作用则被置于事后用以解释历史往后发展的情况。这样,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的关系就成了“本源”与“派生”的关系,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就成了“历时性”的“起源决定”,而不是“共时性”的“趋势决定”,本质抽象之于现象具体就具有“发生学”而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先在性。
3.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曾讲:新历史观“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是理论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其作用在于也仅仅在于,“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这些抽象本身”不能离开现实的历史,否则“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也“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否则就不是科学抽象,而是“关于意识的空话”(63)。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用的阐释是极为谨慎的。这是因为,本质离不开现象,抽象离不开具体,历史规律离不开人的现实历史活动。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它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的实现方式和表现形式都不尽相同。如果满足于生产力一元决定的一般结论,就不会理解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像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那样,通过对具体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实证或经验研究来具体展示和说明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64)。在此意义上,辩证地看待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之间的关系,就绝不能用本质层面的研究排斥和否定具体层面的研究,绝不能用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排斥和否定其他历史理论。
但同时,也绝不能以各种具体层面的研究排斥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毕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社会历史总的发展进程的宏观框架,借助于这一框架,我们获得了对审视和评价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极为重要的“历史大视野”。回望人类走过的路,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是不能违背的“总趋势”,是历史进步的客观要求,虽然它并不总是每个具体人物的自觉目的,也不总是每个具体事件的自觉目标。正因为如此,是顺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和破坏它的发展,不仅决定着不同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命运,而且决定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作为一种“解释范式”,虽然不普遍适用于小尺度事件,但对于理解和把握大尺度事件则是不可或缺的。
值得深思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命运多舛,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经济对政治和文化的线性决定论承受着愈来愈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看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最僵化的拥护者”,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决定论”立场并不存在,“自从一开始,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是经济决定论:历史上并非所有的非经济现象都可以从具体经济现象中追溯其来源,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日期是无法确定的”。(65)美国的戴维·哈维则认为,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在当代受到赞赏“差异”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思维方式的挑战,包含了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新左派”放弃了对于作为一种分析范式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任,从而“宣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66)。而无论是卢卡奇的“具体总体”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一体化”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把历史唯物主义从这种所谓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所作的各种努力,尽管这些努力的姿态和称谓各不相同,它们或者是一种“重写”、或者是一种“保卫”,或者是一种“重建”。
问题是,这些旨在超越“一元”和“线性”决定论甚至是超越“决定论”本身的理论蓝图,都毫无例外地在“实体”的意义上理解“生产力”,把生产力与它的具体要素混为一谈;都自觉不自觉地割断了“本质抽象”与“现象具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落入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窠臼,其拯救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成效也可想而知。在谈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时,海德格尔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67)历史唯物主义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它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层面,而不是像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那样停留在历史的表层。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用于“异化”理论未免有些牵强,但与马克思的下列观点却不谋而合:“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任务,而规律所指的便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68)。不仅“规律的实现”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69),而且在各种中介环节和中介过程的作用下,本质和规律往往以各种“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70),由此决定,对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往往是矛盾的。我们既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在面对具体的经济现象时,“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71),也不能像庸俗经济学那样,完全无视经济规律的作用,“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72)。
注释: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4页。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82-584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97页。
④《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99页。
⑤《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63、665页。
⑥《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0-671页。
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69页。
⑧《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5页。
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05页。
⑩《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05页。
(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6、677页。
(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9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05页。
(1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260页。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第294页。
(1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61页。
(1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0、760页。
(1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53-754页。
(19)《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6页。
(20)参见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7页。
(2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5页。
(2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8页。
(2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8页。
(2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577-578页。
(2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95-196页。
(2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1、696页。
(2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3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95-496页。
(3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5页。
(3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63页。
(3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63、165-166页。
(3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65页。
(3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8页。
(3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66、681页。
(3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79页。
(3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66页。
(3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67页。
(39)《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79-180页。
(4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83页。
(4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85页。
(4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70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9-310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0页。
(4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59-760页。在这一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有自相矛盾之嫌。因为,他不仅反对从“人的本性”出发解释历史,而且认为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76页。
(4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7页。
(4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3-735页。
(4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21页。
(49)《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3页。传统教科书体系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阐释与此是完全一致的。
(5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40页。
(5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5页。
(5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4页。
(5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41页。
(5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3、91页,
(5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611页。
(56)《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28-729页。
(5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29、731页。
(5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60页。
(59)《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3-714页。
(6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16、719页。
(6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38页。
(6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736-761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4、74、73页。
(64)参见王峰明:《〈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微观基础》,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1期。
(6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66)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8-441页。
(67)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6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5、250页。
(6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7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0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05页。
(7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标签: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决定论论文; 地理环境决定论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