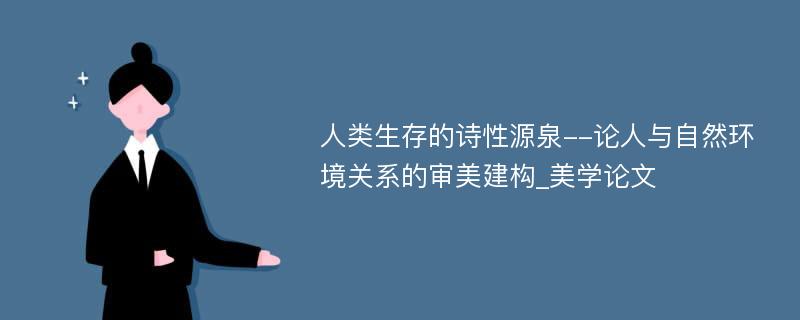
人类生存的诗意之源——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美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环境论文,人与论文,美学论文,诗意论文,之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3-0097-04
一
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曾经格外深情地说:“充满劳绩,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一诗句经海德格尔在他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着力阐释而广为流传,更加引人关注。显然,这诗句所传达的是人类的美好的生存状态,也是人类期望与追求之中的境界。
人类最初的诗意起始于美意识的生成之时(需要特别指出,这里讲的是“诗意”而不是“诗”)。如果说美意识的生成标志着人类开始对于外在世界与人自身的内在世界有了精神意义上的感悟的话(包括非自觉到自觉),那么,“诗意”即是激活于那精神空间的自由的精灵。有了“诗意”,人类生存实践中便有了对于一般生物那种满足本能欲求的超越,同时也便有了情,有了趣,有了灵性,有了富有美的内涵的精神张力,以使人类与其他动物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并拥有了丰富的生存内容。
“诗意”是一个富有美学色彩的概念,令人情牵意动。所谓“诗意地栖居”,是人的生活、生存的诗化。“诗意”的内涵是丰富的,而且是多指向的,但是,笔者以为,其本质是明确的,那就是自由与和谐。自由自在,其乐无穷,这是世上善良人们共有的体验;自然而然,生趣盎然,则往往又是人们生存中滋生诗情画意的根本元素。但人类的生存并不仅止于单向度地依附于自在的自然,或终日满足于欣赏自在的自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还要进行能动的创造性实践,即所谓“充满劳绩”。所以,如何使得人类的实践行为(包括对自然的“人化”)成为充满“诗意”的创造,亦即如何在“充满劳绩”的同时,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出更大的自由空间与和谐境界,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生存实践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人类作为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一个智能物种,本质上就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缘关系。在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这二者之间,有过对立,有过混乱,有过和谐,有过平衡。顺应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生存,是人类的天性;改造自在的自然环境,以求更好地生存,是人类的特性。总而言之,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总是促使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持一种根本性的关系。在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自然界从“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P25),变成了对人类有益的、为人服务的对象。它或者作为人类的生活环境而出现,或者成为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料来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故而,人类在生存实践中必须与自然环境保持和谐,包括在人类发展中对于自在的自然世界的改造,也应当把握适度。
为此,我们特别标举“诗意”,及美学。人类是否可以“诗意”地生存于世,追问到底,则要看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人与人以及人自己的身心之间,是否具有自由和谐的空间,以至是否能够建立起富有审美特质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环境间审美关系的建立,则又是形成“诗意”之质的重要前提或根源。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生成,事实上是从一个重要的角度与层面确证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存关系。把自然环境当作人类的异己的、对立的存在是无益的;而反过来,将自然环境视作纯粹外在于人的被支配对象,甚至以张扬“人的独立性”为由,而去无所顾忌地剥夺自然环境自在的生态机制,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必然造成的共同结果都是人与环境之间失去和谐关系;同时,就人的生存境况而言,无论是受困于自然环境,还是以霸主的身份占有自然环境,都无法进入自由之境(特别是精神世界的自由)。与之相关,生存的危机与美感的失落往往会随之而来。可以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审美关系的确立,能够更内在地反映出人们在特定时空的生存态度、生存处境、生存状态及生存品质。譬如,“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种浪漫的、宏阔的,同时也是富有诗意的情景,是在对于自然风物的描状之中传达出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感。若再深究一步,则可以自然地联想到生活于蓝天白云与茫茫绿野间的牧人们那种自在而浪漫的生存状态——让自然“自在”,自然亦即向人而在,人们可以拥有自由而和谐的空间。
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适相谐,原本就是具有生态学意义的。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明晰地昭示着这样的轨迹:特定时空中的自然环境,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人种,进而产生相应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包括生存意识、生存状态、价值观念、人文关系,等等);反过来,这种文化又作用于滋生它的自然环境,形成相应的富有地域特点与民族特色的人文景观,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特有的美学关系的建立。(我们看到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所存在的审美差异的根源即在于此;而且地域性自然环境差异愈大,彼此间的审美差异也往往愈大。)
二
当我们明确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天缘关系,以及建构美学关系的种种内在依据与可能性之后,现在再来探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环境间的美学关系建构。
应该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所关注的一个最古老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只要生存与发展,则不可无视之。关于这个话题的产生之早,我们只要考虑一番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古老神话传说,便可见出一斑。关于它的永恒,则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天缘关系使然,它是关系人类生存的一切话题的前提。而且,它又往往形成了关于宇宙观、生命观的许多重要哲学命题。
“天人合一”是中国民族美学的最为重要的哲学基础。它既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宇宙精神、生命意识,同时又表达了本民族的审美理想。与之内在相依的“天人同构”观点即认为,人的身心和情感的节奏韵律与自然界运动的节奏韵律是相互感应的同构系统,天“道”与人“道”息息相通,人与自然同呼吸共忧患。所以,在中国人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创造中,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对自然进行认同与驾驭。西方的哲学思想大不同于东方的中国,但是关于自然对人类生存中的意义,在许多西方哲学家的经典论述中,也都指出了自然的美质的重要特性。亚里士多德即认为,自然万物都是以美的形式为目的的。他说:“整个生物界向我们表达着自然的美,每一个生物也各向我们表达着某些自然的美。在自然的最高级的各种创作中,绝没有丝毫的胡乱。殊途而同归,一切都引向一个目的,而自然的创生与组合的目的就是美的形式”。[2](P419)正因为宇宙万物均具有美的资质,因而值得我们不辞辛劳地去进行关注与探究。总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是其最大的哲学命题,而蕴涵其中的美学关系的建立,则同时也便具有了人类生存中的本原性与本体性特质。
从本质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环境是不可分离的。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审美关系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一个人仰卧于柔软的绿草地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遥望着蓝天上自由飘动的白云,往往会美意绵绵。这是人与自然之间最自在最本真的关系。而且,这种审美快感只要当人与自在的自然(大自然)直接感应时就可以获得。由于本质性的关系所决定,关注并关心自然便成为人类追求和谐态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而当代人强调提出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美学建构命题,更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其所针对的主要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严重受损,直至带来人类生存危机的隐伏。显然,这同人与自然间应有的良性的本原关系相违背。关于导致这一问题的突出原因,一个十分趋同的结论是:现代化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负面作用。现代科学理论与理念告诉人们:自然是外在于人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着的,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科学知识、技术力量去有效地认识它、改造它、利用它。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展又鼓舞人们:人能够实现对于自然世界的改造和利用。于是,现代人开始以百倍的自信高居于世界的中心,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人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对大自然进行掠夺性开掘与肆意占有,资源超限损耗,环境日益恶化,逐渐酿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之相关,人们变得心态浮躁,那种本真的自在、自由,从生存状态中远离而去。
人类自恃强胜而形成的与自然的对立,其结果是使人类自身陷于生存的悖论之中。人从自然环境中获得了极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毁坏了人类生存的家园(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海德格尔看到从月球上拍下的地球照片后惊呼:“人类已被连根拔起!”至此,人与自然环境应有的自在而和谐的本原关系失落了,并已危及到生命的完整性。面对如此困境,许多仁人志士在探究济世良方,许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美学!概而言之,其原因至少有三:其一,美学的旨归即在于维护人的完整性,并滋养和保护精神中的自由及生活中的诗意;其二,美学的本质是合于人与自然的本原关系的(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又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其三,美学与文学艺术密切相关,可发挥其导引作用,通过有效地促进文学和艺术的发展而去调节过分物质化、功利化了的现实生存空间,并使人的精神空间得到扩展。马尔库塞曾指出:艺术更贴近于真实的人性与理想的生活,“艺术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做斗争”[3](P257),艺术可以“在增长人类幸福潜能的原则下,重建人类社会和自然界”。[3](P245)
三
人与自然环境建构美学关系的必要性及其积极意义是明晰的,随之而来需要思考的,则是如何建构。这是一个较大的理论问题,而且可以从多方面去加以研究。对此本文不拟作全面展开,而只是有针对性地分析两个比较切近现实的问题,从而探寻构建二者间美学关系的理论启示与现实依据。
第一,如何看待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环境失衡的问题。这要做一点历史性的考察分析。“自然向人生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强调人与自然间密切关系的普遍性。但具体到不同的“时代”,则又有其不同的特点。“原始时代”,自然界对于人类而言具有许多神秘的色彩,人对于大自然既敬畏又看重,是其与生俱来的“内源式调节机制”。所以,他们的生存总体上是建立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初民文化的确趋向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谐共存。尽管原始民族也要改造环境,从自然中获取资源,但很明显,他们中间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模式,能够相对稳定地建立起人口与自然群落之间的平衡关系”。[4](P87)原始神话中有过“借助想象”或“通过想象”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故事,但这种“改造”和“征服”,仅只是为了变害为益、化险为夷,绝无破坏自然和掠夺自然的意图。
“农业时代”,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完全有赖于自然环境。土地、河海、群山、林木等等,是人们生产与生活的来源与根本;风霜雨雪、干湿冷暖等自然气象,对生产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更是农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所不可违的自然秩序。所以,农业时代的人们依然重视与自然界的关系,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都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所谓“自然经济”,其中就包含着对自然的依附性特征。)。这个时代的人们也曾有过改造自然的愿望和行为,但那还是怀着敬重自然的心理,完全以善待自然的态度,通过对某些自然形态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造或调节,使其更有益于农业生产与生活,例如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这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适,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美的境界,以至入诗入画,成为最丰富的艺术资源,农业时代发达的自然抒情诗即是明证。
“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总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人类凭藉自己在科学方面的见识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将人与自然拉开了距离,自然界成为外在于人、供人进行理性审视,并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开发、利用、改造的对象。这样,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境界便渐渐成为遥远的过去。“异常复杂的事物,说到底却又往往如此简单。就是在这样一种观念(指“擅理智,役自然”的观念——引者注)的支配下,在牛顿之后的300年里,人类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00年间,人类凭借自己的理智,凭借自己发明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向自然进军,向自然索取,开发自然,改造自然,一心一意地要为自己在地球上建造起人间天堂。这条道路一直延续到今天,300年的历史,同时又被称作世界‘现代化’的进程。”[5](P5)希图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无限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为人类创造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我们不怀疑这美好的初衷。但300年过去了,人类的生活非但不具有“人间天堂”那般诗情画意,反而接连遭遇自然界的报复,且愈来愈繁,愈来愈重,甚至已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通过上述考察分析,对于现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问题,可以得到这样两点启示:(一)调节科学技术在自然面前的价值取向,变征服、控制、索取,为亲善、调适、维护。就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而论,我们不可能再“回归”到人与自然相谐的“农业时代”,更不会回到“原始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会继续。因此,切实而有效的选择,不应是逃避或遏制科学,而是应置其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视野中,调节其价值取向。(二)调节人自身的生存态度及价值取向。这要从人类历史的生存与发展中领受题旨,认识到人与自然间那种本原关系的深刻含意。依于自然之乡,源于生命之泉,通向永恒之途,复归存在之根。这是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存”的大前提,同时也是在当代生存背景中,人与自然环境间真正确立美学关系的重要前提。
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现代科技所造成的对自然界的破坏,以及导致人类自身陷于生存困境。我们通常认为,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与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从自然力的历史束缚中获得解放。于是,人们便开始了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掠夺和破坏。从这样的因果关系上看,似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科学技术本身。但是,这样的认识是表面化的。
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它之所以成为“双刃剑”,完全在于运用它的人,即人性本身的善恶两重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即认为:“一切力量——也包括进步的科学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在伦理上都是中性的。因使用方法不同,它可以成为善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恶的东西。”[6](P7)从技术发展史上来看,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几乎同时会伴生有“造福”与“为祸”两种性质截然相反的结局。重核裂变被发现后则很快制造出了“原子弹”与“核电站”;人工合成氨技术成功后,同时生产出农业化肥与制作炸弹的炸药;药物合成技术既产生了治病的临床药物,同时又产生了危害生命的海洛因,等等。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问题的出现归因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应该追究人类的本性”[6](P8)。因为无论科学技术怎么发展,说到底它也不过是人类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所以,“技术”方面出现的问题应该追问到“目的”中去。“而作为一种人类行为,‘目的’的确立大抵来自于某种‘欲望’的驱使。”[6](P8)汤因比教授指出:“人类本来是贪欲的存在,因为贪欲是生命特质的一部分”,“贪欲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它是隐藏在人性内部的动物性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是个追求“过剩”的生物物种;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大着的,追求“过剩”的历史。[6](P8)这并非为“工业时代”的人们所特有,900多年前,宋代诗人苏东坡就清醒地看到了这个人类生存中的问题的症结。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之常少,而可悲者常多”。[7](P98)悲剧的根源在于人的无穷的欲望,它可以导致人性的变异与自由的丧失,导致人远离本体故我。而“工业时代”以来,这问题之所以愈来愈突出,正是因为现代人的无尽的物质追求与大量的人口繁衍,是这两个无限的“乘积”借助现代科技力量而铺天盖地地强加于一个土壤、水源、能源等都非常有限的地球之上所造成的。
因此,我们不应当简单地去指责、甚至诅咒技术,而需要设身处地地去反省人类自身,并进行同样是合乎人性需求的积极有效的调适。笔者以为,我们所讲的人与自然环境的美学关系的建构,恰恰就是应该建立在这一十分迫切的现实要求之上的。美学本质特征中的对于直接实用功利目的的超越,对于精神自由的追求,直至对于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其针对性与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真正的实效的取得,仅凭美学理论家的倡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引起世人的共同觉悟与重视。
人类终究还是向往富有诗情画意的生存状态的,但这需要人类为之付出永不休止的努力。其中首先要努力维护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这是实现人类“诗意栖居”的本源。因为只有这种“和谐共存”,人类才可能拥有真正的自然、自在、自由的空间。歌德曾在一首诗中盛赞如此境界:“自然多明媚/向我照耀/太阳多辉煌/原野含笑/……你欣然祝福/膏田沃野/花香馥郁的/大千世界。”[8](P7)这是诗性中的人与自然,或人与自然共同缔构的诗性。为此,就需要特别强调遏制人性中的贪欲,因为它是扼杀“诗性”或“诗意”的罪恶之源,它可以使自然变质、使自由窒息。荷尔德林吟诵“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因为他相信“星光璀璨的夜色,也难与人的纯洁相匹”。陶渊明之所以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情爽意融的和谐之趣,是与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那种不为物累、复归本我的情怀意绪密切相关的。说到底,人与自然环境的美学关系的建构,关键处就是要实现对于人自身的调节,而调节的重心则是要抑贪欲,扬诗性。笔者以为,此可谓当代背景下新的生存理性的自觉!
收稿日期:2002-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