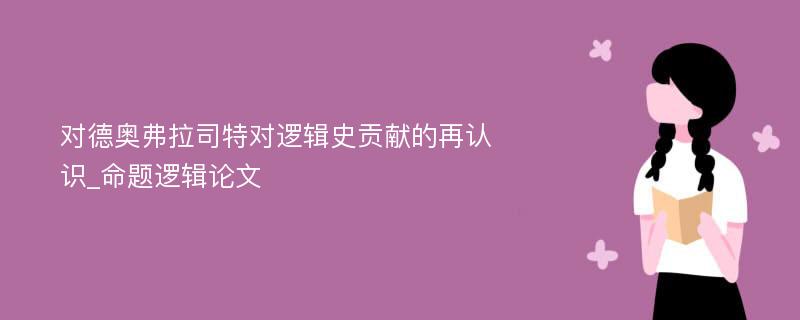
对德奥弗拉斯特在逻辑史上的贡献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史上论文,斯特论文,弗拉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3-0125-04
一
介于构成传统逻辑的两大主流板块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与斯多葛学派命题逻辑之间,逻辑史上曾出现过一个重要的德奥弗拉斯特逻辑学说。德奥弗拉斯特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一位最重要的逻辑学家,也是亚里士多德的直传弟子和朋友,由于在一些逻辑问题上他已超出了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观点,在逻辑史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所以“他成了亚氏以后,斯多葛学派之前最主要的古代形式逻辑家”[1](P140)。概括说来,德奥弗拉斯特在其特定时代给予逻辑的贡献,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他修葺、完善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如在第一格中增补了五个后来属于第四格的式,“为亚里士多德系统中的第四格各式在第一格的各式中找到了一个位置”[2](P39)。他还试图在亚里士多德的模态三段论中增加一些新的思想,并且纠正了亚氏模态学说中的一些错误。二是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从亚氏的类属关系的逻辑体系中跳出来,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依存关系的逻辑体系,由原来的变项之间“是”与“不是”的关系,进而又考察了变项之间“如果,则”以及“或是,或是”等关系,从而将推理形式在亚氏的直言三段论基础上又生发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假言三段论和选言三段论。这种创造性的贡献从本质上发展了人类逻辑,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远比仅从量上修葺、完善亚氏逻辑要意义重大。因此,评价德奥费拉斯特在逻辑史上的贡献,主要是着眼于他富有创造性的这个方面。
二
亚里士多德逻辑无疑是人类逻辑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奉献给人类第一个关于思维形式的系统理论,并且通过发明了符号变项,教会了人类把研究变项之间的逻辑关系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在逻辑中引用符号、字母,即引用变项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上的巨大功绩”[3](P40)。然而,任何始创的学问未必就是尽善尽美的学问,亚里士多德虽然指引世人关注变项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他只是重点教给了一种关系,这就是变项间的类属关系。他眼中的判断,“就是对一事物的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的一个句子”[1](P68)。所谓“肯定”与“否定”,实际就是限定变项之间只能是一种“是”与“不是”的关系,而“是”与“不是”只能表达所联结的变项在外延上有无类属关系。正如他的老师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判断是类与类的关系,或特性属于对象的关系”[1](P40)。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认为“任何一个谓词,必定就或者属于该主词,或者不属于该主词”[1](P69)。“他所关心的问题是‘A是否属于B?’”[3](P97)正是基于把判断中变项间的关系仅仅限定在类属关系的出发点,亚里士多德才建立了关于类的演绎的推理体系。他的三段论实质就是大、中、小词之间类属关系的推演,“客观根据就是事物的最一般关系——类的关系。它适用于一些有类的关系(或可以说概念外延间的关系)的事物”[1](P78)。所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主要是研究变项之间类属关系的学问。
然而,客观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事物的属性是多样的,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就必然是复杂多样的。“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虽然是思维领域的现象,它对于客观事物来说,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它无疑地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客观世界的特定关系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4](P40)。因此,客观世界的特定关系反映到思维中的逻辑形式上面,变项之间关系也就必然是复杂多样的,绝不可能仅一种类属关系就能够穷尽。德奥弗拉斯特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除了继承其师的类属关系学说,又独辟蹊径把视野扩大到变项间的“如果,则”、“或是,或是”等关系,这些被后人称之为假言关系及选言关系的新关系,都体现着变项之间互相依赖、相依而存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客观事物的联系中普遍存在着,比如事物间的条件关系、选择关系、并列关系等。虽然德奥弗拉斯特尚未涉猎尽所有的依存关系,但他能够敏锐地发现逻辑除了研究“A是(不是)B”所呈现的类属关系规律之外,还有“如果A,则B”、“或是A,或是B”等呈现的依存关系规律可以研究,是德奥弗拉斯特的重大创新,也是他对逻辑这门学问的伟大贡献。这一贡献的直接意义应当是,能够让世人领悟到逻辑研究的对象是变项之间的关系,而变项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要想使逻辑理论最大限度地覆盖人类普通思维,就要尽可能多地研究普通思维中的逻辑关系。
但是,长期以来逻辑史学家们并未真正领悟德奥弗拉斯特所做贡献的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曲解了它的意义。或许人们从现代人的角度,早已了解了德奥弗拉斯特身后发生的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于是逆着逻辑发展的历史追溯上去,想当然地认定德奥弗拉斯特创造性的贡献是“最早用这些推理(假言等)扩展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从而奠定了命题逻辑的基础”[5](P35)。“德奥弗拉斯特提出的假言、选言推理形式,已经超出亚里士多德词项逻辑的范围,属于命题逻辑”[6](P95)。把德奥弗拉斯特的创新理论轻易归属到命题逻辑,根据是什么呢?很简单,大家不假思索地认为只要用“如果,则”、“或是,或是”等来联结的变项理所当然只能是命题,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形式,德奥弗拉斯特的推理“显然属于命题逻辑的范围,属于一个全新的逻辑领域,其中的A、B、C这些符号是代表整个命题。看来德奥弗拉斯特是第一个使用命题变项的人”[3](P79)。不难看出,认定德奥弗拉斯特推理中“出现的变项只有命题变项”[1](P146),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而是通过推测得来的。这个推测不外是根据斯多葛学派的逻辑属于命题逻辑,而命题逻辑中的变项都是命题,这些命题变项在斯多葛学派那里是用“如果,则”、“或是,或是”等联结词来联结的。因此,当德奥弗拉斯特也用这些联结词来联结变项时,其变项自然也就是命题,其逻辑理论当然就属于命题逻辑。显然这是一个十分错误的推论。
且不说这种推论的形式多么不符合推理规则,单从事物发展的顺序上看,也是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生存于公元前371至283年的德奥弗拉斯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他身后会有个什么斯多葛学派,更不知道斯多葛学派会搞出一个命题逻辑。截止德奥弗拉斯特生存的年代,他就是属于逻辑发展史的最后一批逻辑学家,他只可能借鉴前人的东西,而不可能将后人的理念注入自己的学问之中。他的逻辑学说就根基而言主要以传承亚氏为主,其次才是创新和发展,不可能突然由词项逻辑一下跳入一个陌生的什么命题逻辑。他推理中的变项仅是变项而已,并没有规定变项的种类一定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果有什么规定的话,按情理他的变项首先应当等同于亚氏的概念变项,也绝不会仅仅是命题变项。因此,正确地理解德奥弗拉斯特的变项,它只不过是特定逻辑形式中根据需要进入分析视野的最基本单位,一种逻辑关系下的最基本单位根据逻辑分析的需要,既可以是概念,也可以是命题,还可以是推理。变项的种类是依逻辑分析的需要而确定的,而不是依逻辑关系的不同来确定的。对于某种逻辑关系而言,很难说它所联结的变项是概念、命题还是推理或多重推理,它就是一个符号而已,这个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单凭某种逻辑关系是无法给出答案的。
在“小张或者小李”中,依存关系“或者”联结的变项都是概念,而在“老王制服了歹徒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中,类属关系“是”联结的变项却都是命题,显然它们跟传统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并非类属关系只能联结概念、依存关系只能联结命题,而是任何逻辑关系都可以联结任何种类的变项。况且,思维形式的生成还有这样的特点,概念经过扩展内涵可以形成命题,命题经过改述逻辑特性可以形成推理。同样,经过一番浓缩和省略处理,推理又可以回到命题,命题也可以回到概念。总之,不同的思维形式经过一番伸缩整合是可以表现为另一种思维形式的。这就是说,变项的表现形式是可以变化的。因此,对德奥弗拉斯特来说,变项的种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变项之间的逻辑关系。从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只关注类属关系,进而发展开来又开拓出依存关系,这才是他的真正用意,从而也才是他为人类逻辑所做贡献的真正意义。
现代人把逻辑分为命题逻辑、词项逻辑和谓词逻辑,是就分析方法而言的。“对命题的不同分析会导致对推理和论证的不同分析,并最终导致不同的逻辑理论。有三种不同的命题分析方法,于是也有三种基本的逻辑类型:命题逻辑、词项逻辑和谓词逻辑”[7](P31)。把单个命题看作不再分析的整体,从而有了命题逻辑;把一个简单命题作主谓式分析,从而有了词项逻辑;把一个简单命题分析为个体词、谓词、量词和联结词等成份,从而有了谓词逻辑。所以,不论把斯多葛逻辑称作“命题逻辑”,还是把亚里士多德逻辑称作“词项逻辑”,都是从分析方法的角度形成的概念,而“类属关系逻辑”和“依存关系逻辑”是从研究对象角度形成的概念,不能把分析方法混同于研究对象,不能理解为“词项逻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命题逻辑”又有另外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分析方法意义上的逻辑与研究对象意义上的逻辑是一种相容关系,而不是全异关系,二者是相互交叉的,不应该将它们对立起来。就研究对象而言,任何形式逻辑都应当是相同的,都是研究思维的逻辑形式的,而逻辑形式又是一定逻辑关系的体现。因此,逻辑关系就是任何分析方法的逻辑共同的研究对象。没有理由说某种分析方法只能研究某种逻辑关系,而不能研究另外的逻辑关系。从理论上说,任何分析方法都应当研究所有的逻辑关系,只有未曾发现的逻辑关系,没有某种分析方法不能研究的逻辑关系。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其特定历史时期主要研究了词项间的类属关系,却不能由此就认为词项逻辑只能研究类属关系,德奥弗拉斯特的发现就证明了词项之间还可以研究依存关系。顺着这样的思路延伸开去,词项之间完全也可以研究人们尚未发现、总结出的其他关系。尽管斯多葛学派受其历史局限性只研究了变项为命题时的依存关系,却不能由此认为只有命题变项才有依存关系,也不能认为研究依存关系是命题逻辑的专利。就是说,概念与概念之间、命题与命题之间、推理与推理之间、以及任意思维形式相互之间,都可以研究任意的逻辑关系。总之,“分析方法”不是“研究对象”,德奥弗拉斯特的逻辑创新主要立意在于指出了逻辑应该研究什么,而不在于用什么方法研究。分析方法是个技术问题,而研究对象是个方向问题,不自觉地将二者混同起来,是逻辑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令人遗憾的过失。
究其根本原因,对德奥弗拉斯特的误解,是由人们始终认为人类逻辑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相互衔接、彼此传承的思维定势造成的。斯多葛学派的逻辑从它诞生直到19世纪末叶,曾经常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贬抑,甚至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斯多葛观念丧失几尽,对于这个学派的逻辑思想已无人问津”[1](P151)。假设此时世人能够趁着这个空白时期,正确理解并延续德奥弗拉斯特的思路,沿着开拓更多逻辑关系的方面走下去,或许发展到今天关于人类普通思维的逻辑将会异常丰满,多彩纷呈了。然而历史没有这样,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数理逻辑的兴起,一些数理逻辑学家又重新看到了斯多葛逻辑的价值,发现了这种理论竟然跟数理逻辑如此投缘,于是“对数理逻辑了解越多的人对斯多葛逻辑的评价越中肯”[1](P152),以致于认为“从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斯多葛派的逻辑成就似乎甚至超过了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领域中作出的贡献”[8](P137)。这样,又把几近消失的斯多葛逻辑重新镶在了逻辑发展历史的长河之中,并且把它定位于上下传承的有机一环,令其为现代数理逻辑充当注脚。依照人们的思维定势,“数理逻辑就是古典形式逻辑在现代的发展,它与形式逻辑本是一家”[9](P50)。就是说,认为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有着同样的研究对象,斯多葛逻辑自然也就成了承前启后的必然阶段。顺理成章,从时间上介于亚氏与斯多葛学派之间的德奥弗拉斯特学说,人们自然从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出发,将其与斯多葛命题逻辑很美观地衔接在一起了。然而事实上,德奥弗拉斯特的本意只是开拓研究对象,并非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涉足什么命题逻辑,那么斯多葛逻辑也就谈不上是在德奥弗拉斯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至少不是在其本意上发展的。
三
看来,有必要对传统的思维定势进行检讨。表面看来,斯多葛逻辑与德奥弗拉斯特研究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关于变项之间的依存关系,只不过前者研究得更多一些、深入些罢了,但就实质来看并非如此。斯多葛学派并非一般地关注依存关系,而是借助某种逻辑关系为工具体现一种“真”、“假”理念。他们眼里的命题是一种体现真假理念的载体,“任何完整的思想由词表达出(某种断定)来,是真的或假的,就是命题”[6](P114)。“不仅简单的句子,就连概念也是真和假的体现者”[8](P141)。他们曾尝试对“真概念”和“假概念”给予解释,但最终还是觉得命题最适宜负载真假理念,所以,“命题的真或假在斯多葛逻辑中是基本的用法”,“主张真或假是和意义即命题有关的,这是斯多葛学派的特色”[3](P106)。既然斯多葛学派认为命题的真假是最基本的,那么为了更方便地传达真假理念,他们把某种逻辑关系所联结的变项定位于命题也就理所当然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多葛逻辑才确立为所谓命题逻辑。可见,斯多葛逻辑实质是一种真假逻辑。至于人类思维到底有哪些逻辑关系需要研究,他们是不关心的,什么逻辑关系能体现真假理念就研究什么,这与德奥弗拉斯特尽可能多地开拓逻辑关系的动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
诚然,任何命题都有真假属性,真假属性是命题共性的东西,斯多葛学派着眼于这种共性形成理论无可厚非。但是,作为逻辑理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探究具体命题孤立意义上的真假问题,只能从此命题与彼命题相互之间的关系上研究真假。就是说,当命题作为变项时,逻辑所研究的真假只能是变项相互关系的真假,也就是逻辑关系意义上的真假。虽然斯多葛学派可以只选择适宜讨论真假的逻辑关系,而放弃其他的逻辑关系,但他不能将真假问题脱离开逻辑关系。事实表明,斯多葛学派初步形成的那些真值表,已经表露出淡化逻辑关系的倾向,变项孤立意义上的真假开始取代了变项相互关系意义上的真假。这种倾向经过现代数理逻辑一番“真值抽象”理论的渲染,愈加显露无遗。如用“如果,则”联结的变项P与q,体现P存在则q必存在,P不存在q可能不存在也可能存在的关系,因此,当说P是真的时,其“真”的内涵包含了P与q都是真的,自然也就包含了q为真的意思;当说q是假的时,其“假”的内涵包含了q与P都是假的,q假包含了P假的意思。但是在所谓真值抽象的意义上,“P真”只是孤立意义上的P自身为真,跟q没有关系,不能传达关于q的任何信息;“q假”也只是孤立意义上的q自身为假,跟P没有关系,不能传达关于P的任何信息。所以,真值抽象的“真”与“假”是变项各自孤立意义下的真与假,而抽象之前的“真”与“假”是变项相互关系意义下的真与假,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相同的语词表达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因此,所谓“真值抽象”的过程,就是混淆或偷换了概念的过程,就是用变项孤立意义上的真假替代偷换了变项相互关系意义上的真假的过程。同样,现代逻辑关于其他真值联结词的解释,都是基于同样的做法产生的。
正是这种割裂了变项间血肉联系的理论,把变项的真假与整个复合命题的真假予以简单的一一对应,由孤立变项的真假即可确定复合命题的真假,由复合命题的真假也可确定孤立变项的真假,从而凭添了一种可演算的性质。然而,在变项之间相互联系的意义下,孤立变项的真假却不能完全确定复合命题的真假,复合命题的真假也不能完全确定孤立命题的真假。虽然孤立变项的真假可以确定复合命题为假,但却不能确定为真。如由P真q假,虽可说P→q是假的,但却不能由P真q真就认定P→q一定是真的,因为当没有确定P与q的关系时,还可能P∧q真或P∨q真或P←→q真或别的什么命题真。虽然复合命题为真时可以确定孤立命题的真假,但复合命题为假时却不能。如P→q为真,则可知P真q真或P假q真或P假q假,但当P←q为假时,却不能确定必然是P真q假;因P→q为假意味着P与q之间不具有“→”关系,而可能是“∧”或“∨”或“←→”或其他关系,而这些关系时未必一定是P真q假。显然,通过割裂变项间关系产生的真值抽象理论,已完全背离了变项处于特定逻辑关系时的真假规律。说到底,这种理论是抽象过度的结果,而过度的抽象无异于新创一种思维模式,为了构造可计算性逻辑系统的需要,现代逻辑将错就错认可了这种新创思维模式。实践表明,这种人造性质的逻辑虽然不能普遍适用人类普通思维,但在某些可计算性思维领域还是很有意义的,斯多葛逻辑之所以受到数理逻辑的青睐,其魅力就在于它显示了这种人造逻辑方向。
当然,斯多葛逻辑乃至数理逻辑并非一开始就明确要把逻辑创造成今天的样子,当初还是试图借用抽象综合的方法,通过抽取命题的真假这种带有共性的属性,在真值意义下构造出一个形式系统,让这个形式系统囊括广泛的逻辑关系,从而企求涉猎比传统逻辑更多的逻辑形式。但是事实证明,从真假角度进行抽象综合的做法是失败的,把普通思维中天然的逻辑关系抽出了,代之以人工规定出来的人造逻辑关系,产生的理论并没有覆盖更广泛的普通思维,倒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逻辑偏向了关于数学思维的人造学问之路。该是冷静地反思一下的时候了,尽管欲使逻辑理论最大限度地覆盖人类思维,既可以借助抽象综合法从质上去概括,也可以采取逐个罗列法从量上去覆盖,但在没有找到新的更好的抽象综合方法之前,不妨还是踏踏实实地遵从德奥弗拉斯特的思路[10](P57),从量上寻找、挖掘更多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充实关于普通思维的逻辑。当然,从量上入手并不排斥借鉴现代逻辑某些先进的分析方法,只是必须明确,分析方法都是为开拓更多的逻辑关系服务的。再不要错误地把德奥弗拉斯特学说同斯多葛逻辑同日而语了,应当明确二者的本质不具有相同的发展方向,既然斯多葛逻辑走了另外的道路,我们应当翻然醒悟,重新找回原来的逻辑,在德奥弗拉斯特思想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地发展关于人类普通思维的天然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