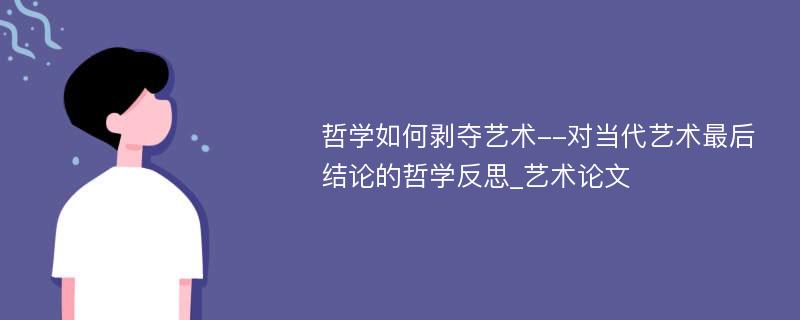
哲学如何剥夺艺术——当代“艺术终结论”的哲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艺术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死亡”、“艺术史结束”、“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呼声,在当代欧美美学界和艺术界越来越高,对中国本土的美学和艺术也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这些“空洞口号”既非艺术家也非纯美学家所创,而是肇始于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的“艺术终结”(the End of Art)的宣称。然而,在这位原创者那里:其一,(艺术)终结(end)≠死亡(death);其二,(艺术史)终结≠结束(stopping)。实际上,丹托“艺术终结”观念的背后隐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一、从黑格尔到丹托的“艺术终结论”
在历史上,提出“艺术终结”的第一人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据考证,这一观念是1828年即黑格尔最后一次在柏林大学讲授美学课的前一年提出来的,后来被其学生霍托(Heinrich Gustar Hotho)编入《美学讲演录》。
在黑格尔那里,将艺术逼向了“终结之途”的是两种东西:一个是思想体系方面的“内在背谬”,这是其所“思”的;另一个则是他所处时代的整体艺术和文化状况,这是其所“感”的。这便构成了双重的张力:一面是“时代与艺术”的张力(市民社会对艺术不利),一面是“艺术与观念”的张力(艺术向观念转化),黑格尔则试图将这两者融会在一起。
从“时代与艺术”的错位来看,黑格尔确认“艺术却已实在不再能达到过去时代和过去民族在艺术中寻找的而且只有在艺术中才能寻找到的那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因此,我们现时代的一般情况是不利于艺术的”(黑格尔,第14页)。黑格尔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是由于与艺术繁荣相抵牾的“现时代”正是黑格尔所说的近代“市民社会”。在这个时代,艺术发展到“喜剧”阶段而最具“散文气息”,市民社会以“偏重理智”的总体趋向对艺术加以禁锢,从而使艺术不再能满足民族“时代精神”的需要。“艺术终结”的逻辑终点,也正是黑格尔“艺术史哲学”的终结之处。
从“艺术向观念”的转化来说,“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黑格尔,第15页)。黑格尔所设定的最高职能,就是要把“精神”从感性现象束缚里解脱出来。照此标准,艺术成为“过去时”是因为它要高蹈于真理的显现之处,艺术必然被逐步扬弃,从而融入更高的宗教阶段。最终,艺术和宗教的真理将被哲学所“凝结与合并”在自身之内。黑格尔“横向”地视哲学为艺术与宗教二者的统一,让哲学成为艺术和宗教的思维之共同概念;“纵向”地把绝对精神的发展安排为从艺术到宗教再到哲学的“三段论”,艺术和宗教在哲学中才发展为最高形式。换言之,“艺术的解体”最初虽融会入宗教里,但最终还是归并在哲学里。哲学吞并了艺术,这是由于“思考和反省已经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了”(黑格尔,第13页)。总之,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观既包含了他对近代市民社会的不满,更是其主体自我意识运作的逻辑结果。可以说,尽管黑格尔美学是由主体性理论构建起来的,但正是主体性不断向上的自我发展,导致了他眼中哲学对艺术地位的直接剥夺,从而最终胀破了其整个美学体系。这也恰恰是黑格尔哲学的“背谬”所在。
在黑格尔宣判“艺术解体”一个半世纪之后,丹托1984年在其《艺术的终结》中重提了这个“历久弥新”的命题,遂被称之为“二次终结论”。然而,二者的基本差异在于,黑格尔所谈的终结是就历史整体而言的,而丹托论及的终结则是单纯指艺术史来说的。
在丹托看来,他也是在“历史地预测艺术的未来”,这同黑格尔不谋而合。正如黑格尔从“大历史”的视角感叹古希腊艺术不复返并洞见到近世艺术的“衰老”一样,丹托思考中的关键词也是“历史”,或者说他关注的最终是艺术与历史的关系。丹托也正是由此出发理解黑格尔的。他认为,黑格尔所说的“辉煌时代”的艺术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而结束的,虽然他本人也并没预言不再有艺术品”(丹托,第77页)。如此看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丹托,都没有认为“艺术从此没有了”,特别是后者反复声明“艺术终结”不同于阐释者所理解的“艺术之死”(参见Lang),而是认为“艺术动力”与“历史动力”之间不再重合。这正是黑格尔给予丹托的“历史性”的启示:艺术与历史的发展不再是同向的,或者说艺术根本失去了“历史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超出了“历史的限度”,从而以一种“后历史的样式继续存在下去”,“但它的存在已不再具有任何历史意义……艺术是否会重新踏上历史之路,或者这种破坏的状态就是它的未来:一种文化之熵。由于艺术的概念从内部耗尽了,即将出现的任何现象都不会有意义”(丹托,第77-78页)。不过,黑格尔所说的“衰老”指的是作为感性显现之理念的式微,而丹托所谓的“耗尽”则意味着当代艺术的发展对传统“艺术”概念的抛弃,艺术已经不能成其为艺术本身了。的确,“在现代艺术史上,熵逐渐成为了主导,以至于现代艺术渐渐地走向了创造力的失败”(Kuspit,p.41)。或者从“唯名论”的角度观之,被冠以“艺术”之“名”的下面的“实在”,被从内部加以消耗直至趋于穷尽,这样,“艺术”概念本身也就被“掏空”了,亦即“名不副实”了。
然而,丹托也并非简单地重复“同一种声音”,因为他是置身于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思潮中来反思艺术的,这便与黑格尔拉开了距离,从而赋予了艺术终结以崭新的意义。在“二次终结”的时代,“杜尚难题”早已成为西方艺术界和理论界的公案。1917年,杜尚在将小便器命名为《喷泉》提交到展览会要求展出的时候,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行为给现代主义内部带来了那么多麻烦,给后现代艺术带来那样丰富的启迪。丹托指出:“杜尚不仅提出何为艺术的问题,还提出了为何某物恰好不像自身时它就是个艺术品的问题……就杜尚而言,他提出的作为艺术品的问题具有真正的哲学形式……因为问题只有提出时,从历史角度说才是可能的。”(丹托,第14页)因而,杜尚所提出的难题也就成为丹托艺术终结论的来源之一,尤其是杜尚摘掉了戴在传统艺术品头上的“光晕”,直接将来自现实生活的物品纳入到艺术系统之中,从而激进地打破了非艺术与艺术的分界,这更是启动了丹托及其后继者们的“艺术终结”观念。
二、杜尚之后“康德美学”的二律背反
先从“杜尚难题”说起。首先出现的问题是,杜尚的《喷泉》这类作品还能给观者以审美上的感受和愉悦吗?换言之,以往(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欣赏艺术而获得并积累的“审美经验”,是否还适合于对杜尚现成品的“观照”呢?我想,大多数的观者都会给出“非审美”的答案。这里,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审美”(aesthetic)。
随后出现的问题是,那么,杜尚的《喷泉》是如何成为艺术的呢?这些本来自于现实生活场景的小便器,是如何被“认可”为艺术序列里面的一员的呢?显然,既然不能从传统的审美视角给出答案,那么就需要用另外的接受方式来对杜尚的现成品加以定位,也就是需要:“判断”。在此,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判断”(judgment)。
现在可以将杜尚同比他早百余年的康德联系起来,因为康德集中精力论述的就是所谓的“审美判断力”(aesthetic judgment)的问题(Kant,XLVⅡ);“审美”与“判断”的合题,也就是德文“Geschmachsureil”(“鉴赏判断”)的问题。按照康德的原意,所谓“判断力”(Urteilskraft)正是略有知性性质又略有理性性质的“津梁”,它可以成为一种沟通理性与感性、必然与自由、有限与无限的有关人类“情”那部分的认识能力。1790年他的《判断力批判》所要探求的正是如何弥合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巨大裂痕,从而寻找快感与不快感的先天原则。这样,“判断力”就成为了跨越沟壑、连通知性与理性的中介桥梁。康德意义上的“规定判断”或“科学判断”总是先有普遍再找特殊,或者按照普遍的模式来“套”特殊的事物。而“审美判断”或“反思判断”的路数刚好相反,是先有特殊再找普遍,它是一种涉及情感判定的人类能力。
可见,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直至杜尚之前的艺术,对它们的鉴赏都可以按照康德的“鉴赏模式”来进行。在这种传统的艺术鉴赏里面,“审美”与“判断”是并行不悖的,乃至是相互交融的,换言之,“审美”就是“判断”,“判断”就是“审美”;在“审美”的同时做出“判断”,在“判断”的时候业已“审美”。“审美”与“判断”在康德那里并不矛盾,而是合一的。
但是,对杜尚的现成品的欣赏却不可能按照康德的既定模式来进行。因为在对《喷泉》之类的作品进行观照时,审美的要素几乎被降到了最低点,一种理性判断的力量逐渐占据了上风。反过来说,当你对这类作品采取判断的态度时,审美也就跑到九霄云外了。这正构成了一种悖论——“审美”与“判断”的悖论。这种悖论就在于:“宣称现成品是艺术的那句话不一定是鉴赏判断,但它仍然宣布了一个审美判断!”(迪弗,第97页)这是语言意义上的悖论,而非语言分析上的悖论。在这一悖论中的对称的对立命题:正题与反题,都可以得到形式上的可靠证明,但相互之间却存在宿命般的冲突。这种杜尚引发的“康德式”的命题就是:
正题:对作品,审美,而不要判断;
反题:对同一作品,判断,但不要审美。
在支持正题的人看来,“只存在审美,但诱惑和享乐尤其不应该判断和被判断,因为艺术的虚构远远超出了批评和评价的范围”;由支持反题的人观之,“只存在判断,但这种判断尤其不应该是鉴赏判断,因为如果是这样,艺术就会在鉴赏中失去其智性的、判断的和意指的功能”。(迪弗,第95页)
进而,如果从语言的角度继续解析,还可以生发出更重要的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这便是康德自己所谓的“鉴赏二律背反的表现”,这种在鉴赏方面表现出来的二律背反被表述为:“(1)正题:鉴赏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这是由于,否则人们就可以对它进行辩论了(亦即通过论证来作出决断)。(2)反题: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概念上的;这是由于,否则就连对此展开争论都不可能了,尽管(这种判断)展现出一些差异……。”(Kant,p.211)当然,康德的这个论证的起点,就是一个短语:“这朵花是美的”,如果更加精炼,就是:“这是美的”。
然而,在杜尚之后,人们对此的解读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里的关键在于一种替换:一种命题上的替换——将“这是美的”转化为“这是艺术”;一种术语上的替换——将“审美判断力”转化为“艺术判断力”,从而导致了另一种康德式的“艺术二律背反”(Antinomy of Art)。如果这种替换成功的话,那么按照对杜尚作品解释而生发出来的启示,可以得出如下的正反两题:
(1)正题:“这是艺术”这句话不基于概念;
(2)反题:“这是艺术”这句话基于概念。
或者,直接转化为更简单的陈述:
正题:艺术不是一个概念;
反题:艺术是一个概念。(迪弗,第99-100页)
因此,如果把“美的”换成了“艺术”,那么杜尚的现成品引发的就是这种“二律背反”。我们再将这种命题的背谬回复到杜尚的艺术语境当中。首先,杜尚是为他的现成品来“命名”的,他的原意就是指着1917年的小便器说:“这是艺术!”这样的表述显然最初是不以概念为基础的,因为杜尚只是将一个个现成品“指成”艺术,就好像点石成金一般。但与此同时,这一表述本身或者说命名本身就是基于概念的,尽管杜尚并没有将“艺术概念”赋予这个物品。因此,关键还在于对“艺术”这个词本身的理解。这里,孳生悖论的根源就在于:“艺术”“这个名称,既涉及一种不可陈述的审美观念,一种不能用逻辑论证的想象观念,也涉及一种不可证明的理性观念,一种不能在感性事物这里得到显现的理性观念”(迪弗,第104页)。这不正是“艺术”自身最深层的悖论吗?一种在欧陆哲学既定框架内永远也无法解决的悖论吗?
由此,再拉伸到“艺术之死”的问题,这就关涉到两种“死亡”:一种是“艺术之实”的死亡,另一种则是“艺术之名”的死亡。我们可以说,当代艺术的死亡更多指的是一种“名称的死亡”,而在“艺术之名”被判死刑之后,“艺术之实”仍继续潜在地绵延着。
三、理论规划:“哲学对艺术的剥夺”
按照丹托的意见,既然艺术“终结”了,那么艺术究竟“终结”在何处呢?答案是终结在哲学。
在此,丹托又回到了黑格尔那里。理念的无限发展和理智化的艺术现实在黑格尔的“艺术解体论”里早就被联成一体,而丹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亦都认定,艺术将终结在“哲学”里面。这样,艺术的“两次终结论”的提出者,皆惊人一致地认定艺术最终要“化入”哲学,或者说,艺术丧失了自身的规定性之后,将会以一种“哲学的形式”出现。在很大意义上,这都不是艺术主动的投降,而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disenfranchisement)。
丹托相信他所谓“艺术终结”,其实是“一种剥夺艺术权利的形式”,“它假定自身的哲学就是艺术所追求的,结果艺术通过最终成为哲学来实现其使命”。(丹托,第102页)所以,丹托在许多地方都在重复一个意思,那就是“艺术已变成哲学,艺术实际上由此完结了”。这里我们不得不回溯到柏拉图那里,因为他才称得上是“哲学与艺术之争”的始作俑者。进而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柏拉图的艺术理论就是他的哲学,由于自古以来的哲学就存在于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言里,哲学本身或许只是对艺术的剥夺——因而把艺术与哲学分开的问题或许能同询问没有艺术的哲学会是怎样的哲学这一问题相提并论。”(丹托,第6-7页)
这便涉及到柏拉图的抨击所具有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建构一种实在从中合乎逻辑地排除了艺术的本体论。第二个阶段力求尽可能地合理解释艺术,以便理性逐渐征服感觉的领域”(丹托,第7页)。丹托在此深刻地洞见到了柏拉图思想的内在罅隙,同时也看到了欧洲哲学史上“哲学与艺术之争”的外在背谬。一方面,柏拉图作为形而上学的政治家,不仅把诗人“驱逐”出了理想国,而且也将艺术逐出了理念领域,从而规避了艺术本体论的建构;但另一方面,他却又要为艺术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将艺术从本体论上转到次要和衍生的实体领域,让人们接受没有艺术位置的世界图景,从而获得一种使艺术避免伤害的“辉煌方式”。这样,哲学史上就出现了两种对待艺术的根本态度:一种是消除艺术对哲学直接“侵犯”的道路,艺术虽然不再有危险但却若隐若现;另一种则是直接将艺术与哲学视为“同一”。丹托认为这便是黑格尔的策略,其实,更为重要的代表应该是谢林,因为只有他将“艺术哲学”作为“哲学工具总论和整个大厦的拱心石”(谢林,第15页)。
由此,丹托推论如下:“所以,把艺术视为哲学变形的历史存在之哲学,指出哲学就是艺术的变形,而这是对黑格尔的理论的巨大反讽:柏拉图抨击的第二部分还原成柏拉图抨击的第一部分,而坚决反对艺术的哲学,最终也坚决反对自身了。”(丹托,第16页)哲学似乎陷入到了自造的“圈套”之中:如果“艺术产生不了什么”并只是哲学的伪装的形式的话,那么“哲学也就产生不了什么”。这样,在丹托所处的现时代,最初攻击艺术的哲学论据的那个结构转而质疑了整个哲学事业。可见,这位哲学家的真正意图仍是“为了哲学的艺术”,而非单纯意义上的“为了艺术的哲学”。
但无论怎样,艺术终结在哲学里面了,或者说,艺术被“哲学化”(philosophization)了。丹托认定,杜尚的启示正在于此:“杜尚作品在艺术之内提出了艺术的哲学性质这个问题,它暗示着艺术已经是形式生动的哲学,而且现在已通过在其中心揭示哲学本质完成了其精神使命。现在可以把任务交给哲学本身了,哲学准备直接和最终地对付其自身的性质问题。”(丹托,第15页)。这样,艺术就终结于自身身份之“哲学化”的自我意识中,但这并不是说需要生产哲学上的纯粹艺术品。艺术哲学的全部必须是艺术。这艺术无论体现什么样的本质,都能用一种真正的定义来表达,具有必要和充足的条件。艺术哲学必须与所有现在的和曾经存在过的艺术都一致。
从现时代的情况来看,艺术无疑已经被哲学所渗透了,使得我们无法将艺术和哲学二者区分开来,也就是把艺术从美学使之陷入的冲突中解脱出来。这样,丹托实际上是在完成柏拉图第二阶段的计划——“永远以哲学取代艺术”!
四、现实归宿:“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
然而,理论的规划总是同现实的归宿发生离异。这意味着,“艺术终结”并不同于“艺术史结束”,丹托对艺术的历史延展有着另一番理解和阐释。
我们发现,丹托实际上深得黑格尔著名三段论的精髓,在一系列艺术史考量里面都对其运用自如:“西方艺术史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段,我们称之为瓦萨利时段与格林伯格时段。两者都是进步主义的。瓦萨利具象性地来诠释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好地‘征服了视觉的表象’。当移动的影像证明比绘画更能描摹现实的时候,关于绘画的叙事就终结了……格林伯格依据艺术条件的鉴别来定义了一种新的叙事,特别是绘画艺术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有哪些差异。”(Danto,1997,p.125)“艺术史的大师的叙事……是一种模仿的时代,随后就是意识形态的时代,再随后就是我们的后历史的时代,在最后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伴随着品质而逝去了。”(同上,p.47)
在此,可以看到丹托心目中艺术史“大叙事”的整体结构。在第一段论述里面,丹托先将艺术史区分为“瓦萨利时段”和“格林伯格时段”两个时段,在第二段论述里面,则继续区分出“模仿的时代”、“意识形态的时代”和“后历史的时代”这三个时代。其实,这出现在同一本书的两种区分是一致的。因为,所谓“瓦萨利时段”也就是“模仿的时代”,所谓“格林伯格时段”就是“意识形态的时代”,它们都是持“进步主义”观念的艺术叙事阶段。关键是今天出现的第三种叙事模式:“后历史的艺术叙事”模式。
如果将艺术发展史归入丹托的“大叙事”结构中的话,可以说,“模仿的时代”大致相当于前现代艺术时期,“意识形态的时代”大致相当于现代主义艺术时期,那么,“后历史的时代”也就大致相当于当下还在延续的后现代艺术时期了。在模仿的时代,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欣赏者都还是按照“具象的原则”来看待艺术的,但随着人们逐渐掌握了相关的规律,特别是运动图像技术的到来,使得艺术的历史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因为,在诸如电影这种有赖于技术的艺术的大发展之下,电影制造幻象的能力已经完全超越了画家的手创,这便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绘画的本质。这样,瓦萨里式的历史持续进入到移动图像,其中,完全的叙事被作为表象的技术后果而组构起来,而后绘画却逐渐走向更哲学化的道路。与此同时,在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之初,也就是在所谓的“格林伯格时段”或“意识形态时代”,19世纪原始艺术对西方艺术界的入侵所带来的挑战,亦同对西方文明之信仰的衰落直接相关,这决定了原本那种“艺术史叙事”的结束。(Danto,1990,pp.340-341)
前两种艺术史叙事模式被丹托视为两条失误的道路:“第一条失误道路,就是通过图像化来紧密地确定艺术。第二条失误道路,就是格林伯格的唯物主义美学。”(Danto,1997,p.107)由此可见,先前的艺术史叙事——瓦萨利时段和格林伯格时段——按照目前理解艺术史的方式,它们没有“以适当的哲学形式”提出关于“艺术本质”的问题。而丹托的潜台词则是:潜在于整体艺术史下面的目标,似乎就是以适当的哲学形式来阐明“什么是艺术的本质”。
这里的关键是第三个阶段的艺术史叙事模式,亦即丹托所谓的“后历史”的艺术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对前两种叙事模式无疑产生了巨大的颠覆,其中最根本的颠覆就在于对“进步主义”的反驳和遗弃。当然,当历史不再是由低向高、逐步上升发展的时候,当历史的不可逆的进化被悬置的时候,当后现代的时间观念走向了零散和碎裂的时候,不得不说丹托也具有某种后现代主义所独具的“反本质主义”的心态。所以,在他看来,现代主义就是一系列“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呈现,哲学家们曾称之为对艺术本质是什么的“具有说服力的定义”,而今却再度受到了质疑。这种质疑显然来自对“现代”的怀疑。现代主义时期在此被视为一种具有“异质性”的时期,它在作为艺术的事物等级当中得以呈现。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丹托发现沃霍尔的艺术说明:任何事物如果成为艺术品,都能与看似好像不是艺术品的东西相匹配,所以,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逐渐模糊了。
在后历史时代,艺术的叙事重点就是要回到艺术本质的问题。丹托认为,“艺术真的是什么与何为艺术的本质的问题”非常重要。“这个问题的形式是:在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东西之间,当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趣味的知觉的时候,如何做出这二者之间的区分?”(同上,p.35)这样,在丹托的视域里,某一叙事之说明被给定时期中艺术史是如何进步的原因,在于它包含了艺术关于什么和什么是叙事的概念。换言之,艺术史的每一叙事都提出了其自身的艺术本质的概念。这样,丹托内心中“艺术史的基本模式”可以图示如下:
前现代时期
现代主义时期
后现代时期
历史阶段 (1300年—1880年) (1880年—1965年)
(1965年至今)
艺术史大师叙事时段
瓦萨里时段
格林伯格时段 没有大师叙事的时段
模仿的时代
意识形态的时代
后历史时代
艺术史时代 (Era of imitmion) (Era of ideology)
(Post-historical Era)
艺术使得自身意识到作
“后模仿的艺术”(post-mimet-
这是“多元文化的艺术”
为“美的艺术”(fine
ic art)从“视觉向内心”转(multicultural art)时代,艺
art)而存在。“模仿的
换,通过一系列的风格,来寻
术的本质被看作是一个对可
艺术的历史趋势
艺术”(mimetic-art)为
求“表现”和“自我探求” 能性开放的领域。这是一个
了更忠实于活生生的可
而非制造错觉。现代主义是 不再有大师叙事的艺术时代,
见经验而努力,乃至要
被宣言所标识的时代,具有 缺少制作艺术的风格而只有
准确地再现视觉经验。
进步和历史必然性的意义。 对风格的借用。
在丹托所描述的当代情境下,从哲学的视角来看,现实中的艺术究竟可能“终结”在何处呢?
本文认为,起码可以给出三种可能的解答(参见刘悦笛,第96-97页)。解答之一:“艺术终结于观念”。这是“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发展道路,传统的“艺术形式”趋于终止,观念倾轧形式而成为艺术的核心。解答之二:“艺术回归到身体”。这是“行为艺术”(Performing Art)还有“身体艺术”(Body Art)的发展走势,就好像是艺术又回到了石器时代那种与身体难分的密切关联当中,从而导致一种“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的出现(参见Shusterman)。解答之三:“艺术回复到自然”。在“大地艺术”(Land Art)的终极指向里,大地艺术家们都普遍相信艺术与自然之间没有严格的界线,应该相互对话,由此达到“艺术的自然化”与“自然的艺术化”。
这三种未来艺术的可能走向,分别持这样的基本观念:“让观念直接成为艺术”、“让人的行为直接成为艺术”、“让自然直接转换为艺术品”。从传统艺术观念来看,这些艺术实践都是将艺术变换为“非艺术”甚至“反艺术”,因为观念、身体、自然都是传统艺术的主要盲区。实际上,这些艺术取向可以归结为一,那就是“艺术与生活同一”。因为艺术家们希望并相信,在生活与艺术相融与同构的时空里,人们才能够幸福地存在。于是,一种崭新的“生活美学”(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s)便逐渐浮出了地平线,呈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当然,关于艺术终结于何处的上述解答,目前只是猜想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艺术总是某种“过去的事物”,艺术的终结也是必然的。这不仅因为艺术总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代被创造的,而且还因为它在历史上执行了一种特殊的功能。因为毕竟“艺术的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它不仅常常要受到样式、材料和技法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内容和功能的制约”(贝尔廷,第316页)。艺术既是“人性之发”,又是“人性之需”。人必然有历史的终结,而艺术只是人的依附物,所以艺术不可能脱离人而有自己独立的命运。
最终的结论只能是:人类的终结之处,就是历史的终结之处,也可能就是艺术的终结之处。
标签:艺术论文; 哲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终结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美学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杜尚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喷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