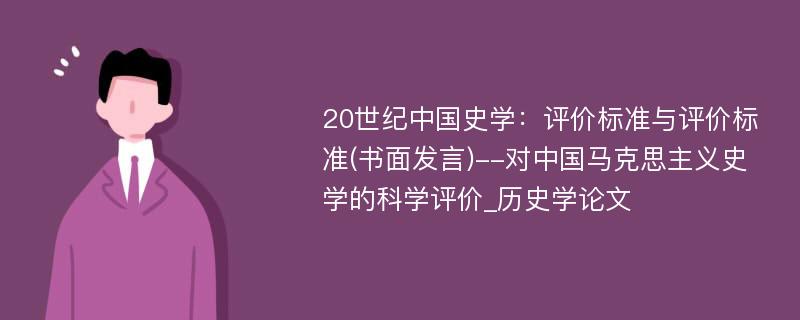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科学地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评价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05-1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版了相当多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信在新的世纪,还会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与同仁共勉。
一、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
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历史学是一门研究过去的学问,它有自身的学科特点。历史学者在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运用史料去揭示和反映过去了的客观的历史实际。历史认识的过程,就是历史学者的主观认识通过史料这个中介反映已经逝去了的“历史”的过程。而历史学者的主观认识又与他所运用的理论、他所掌握的手段和方法密切相关。因此,历史理论是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研究历史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运用史学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有特征,任何历史学都离不开历史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唯物史观有一种理论的自觉罢了。因此,评价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起来。
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史学家区分史学家,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和无产阶级历史学划分历史学的种类,即简单地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个学者、一种学术,是很不科学的。这种作法在20世纪后期的史学总结中得到了纠正。与这种作法相类似,在近几年的史学评论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形式,即动辄就给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划派,什么“史观派”、“唯物史观派”、“史料派”、“考证派”、“实证派”、“阶级观点派”、“历史主义派”等等,划分标准不一样,派别名称也就不同。有的人同时采取几种划分标准,以致一个史学家,一下子加入了几个史学派别。总之,派别是越来越多,让人多不胜记。而派别之间又总是有矛盾、有斗争。一个时期,这个派别得势了,另一个派别就失势了。到了另一个时期,双方的地位又颠倒过来。这种研究史学史的思维方式,说到底是没有摆脱过去片面运用阶级斗争观点研究历史的模式。这种模式过分地强调不同、强调对立,而看不到不同史学家在差异性中的共同性、统一性,自觉不自觉地在揭示了一方面历史事实的同时又掩盖了另一部分历史事实,从而导致论点的片面化和观点的偏狭或偏执。应该说,这是历史研究的大忌,对史学评论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入研究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其产生起,无论是在史观、史料还是治学方法上,都重视借鉴、吸收和批判传统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果。同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也是肯定的;在历史观上,逐步认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胡适与李大钊在思想上有分歧,曾有“问题与主义”之争。这种争论远没有后人所宣扬的那样剑拔弩张。实际上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很多是相互尊重的,并保持较好的个人友谊。《胡适文存》第3集的扉页上写着:“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郭沫若十分推崇王国维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成就,将之比作“崔巍之楼阁”,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所谓“史学范式”概括为重视宏观研究和理论阐释,忽视微观,蔑视考证,给人一种马克思主义史学只会搞“虚”的研究,不能搞“实”的研究之印象。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20年代,李大钊在更新历史学的观念和科学论述史学要义的同时,对考证史实的重要性就一再强调,说:“关于考证个个史实的研究,虽在今日,仍不可忽视。”“历史理论与记述历史,都是一样要紧。”(《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郭沫若在甲骨文、金文研究上成绩卓著,撰写了大量的考释文字,晚年又花费大量精力,搞《管子集校》,这些文字不是“考证”?范文澜著有《文心雕龙注》、《正史考略》、《群经概论》等书,每一部都带有浓厚的考证特色。因此,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重虚不重实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另一方面,有的学者为了拔高考据史学的地位,又把以实证见长的史家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们对理论不屑一顾。事实并不是这样。胡适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胡适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作“考证学派”的精神领袖。但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却说,治史要有三个目的,就是明变、求因和评判。求因和评判不就是过去所说的“释古”吗?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是扎实的考据之作,但又何妨他撰有大量的文化史、学术史、中国通史以及历史研究法之类的著述?
现在,一些研究20世纪史学的朋友,总是津津乐道史学流派及其对立,特别热衷于炒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矛盾。这种研究态度,还不如60多年前学者的雅量。所得认识的客观性、全面性,自然要大打折扣。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应意识形态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主导地位。这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受到政治上“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的确需要认真总结。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也在检讨自己解放前著作中的非历史主义观点。平心而论,在战争的年代里,出现一些非历史观点在所难免,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回护自己的错误。这种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值得称赞的。作为后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承认自己著作中的某些缺点,就否定他们的成就。尽管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少著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们在解放前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公认的,如顾颉刚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评价道:“郭先生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的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书中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100页)。从另一个方面说,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更多地着眼于它的历史地位问题。任何作品,都有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克服这种历史局限性,是时代赋予后人的使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克服,不是简单地否定历史、否定前人,而是一种扬弃,其中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近年,把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所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说成是“假问题”,是一个时髦,其理由主要是:一、这些问题都是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下提出的,语境改变,这些问题本身能否成立都是问题;二、从学术话语看,这些问题都是在西方话语的语境下提出的,是从西方的幻觉出发对东方历史的一种重新编码,与“欧洲中心论”有一定的关系。三、这些问题争论很久,最终也未形成定论。这些理由能否成立也值得怀疑,道理很简单:首先,这些问题都是构筑中国通史系统的基本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问题。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家一直追求用新观点写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的中国通史。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即涉及到这些问题,以后通过进一步学习唯物史观,对这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和条件,因此,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在五六十年代探讨这些问题是必然的。当然,这些问题的讨论规模如此之大,与政治环境有关,但不能说它们就是政治的产物。其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使用相关的词汇。唯物史观确实是产生于西方,但它的理论指导意义并不限于西方。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却不能封闭于世界。中国史学既要研究中国历史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性,也要研究自己的特殊性。30年代重视共同性的研究;40年代又逐渐重视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研究共同性还是特殊性的取向,与社会现实的需要是有关的。但这也不能成为判定一个命题是“假问题”的根据。最后,问题的讨论不一定都会得出结论。这里面既有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史料方面的因素等。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研究重心发生了变化,这些一时难以搞清的问题不再成为热点问题,毫不奇怪。一旦条件具备,或许这些问题会再次成为历史学关注的重点。所以,不能因为现在将它们搁置起来,就说它们是“假问题”。问题的“假”与“不假”,关键看它们是不是历史问题,是不是在历史学上有研究的价值,而没有必要把它们与政治扯得太紧。
把上述问题说成是“假问题”的,往往不是在这些问题上作过精深研究的学者。他们将这些问题判为“死刑”,主要不是依据学理,而是依据这些问题与政治的边缘关系作出的。真正有说服力的论断,还是要靠实实在在的学理的探究。当然,这样做很难,只有上具备多方面的基本功以及平心静气的研究方能至此。而这种扎实的功夫才是当前学术发展所需要的。
三、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科学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史学家总结经验教训,在发展唯物史观和运用唯物史观方面达到了新的水平。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及多卷本《中国通史》、陈旭麓著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田余庆著的《东晋门阀政治》、唐长孺著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都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史观,是学界公认的佳作,展示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需要有科学的态度。根据当前存在的问题,我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应当注意的:
1.一定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不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偏概全、感情用事都是需要尽力避免的。大而空的论断不仅对揭示具体的历史事实无补,就是对总结经验教训也是无益的。
2.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教条主义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史学需要认真清理。但把教条主义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又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和创新。
3.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从大处着眼,要重视分析史学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史学家也是人,彼此之间存在个人矛盾是正常的。学术以外的个人关系不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4.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在基本功上下工夫。事实表明,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易事,只读一些现当代史家的著作不行,还须有古今贯通的学识,因此在史学基本功方面用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3-1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