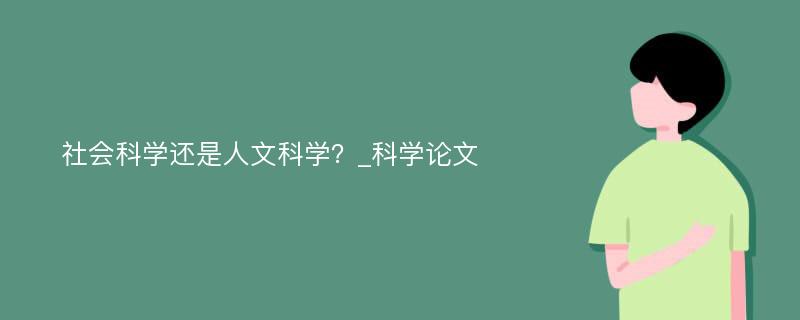
社会科学抑或人文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社会科学”定位,不知有多少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那些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家们为此魂牵梦绕过。他们曾为此唇枪舌战,争执不休,历时达一个世纪之久。若仅就“定位”评说,本无可厚非;但若关乎如何“定位”,问题就变得极为复杂了。
从历史上说,自E·杜克海姆在上世纪后叶为“社会学”在众多真正的以及标榜的“科学的”学科领域中寻求一个“独立的”地位以来,“社会科学”就被不少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视为与“自然科学”并侧齐驱的科学“战马”,它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客观性、非心理干预和经验可验证性等明显特征。这样一种观点被称为“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但另有一种能与此抗衡的、更有影响力的观点,它认为,社会科学关涉人的活动,旨在为人的活动提供意义,因而它应是解释性的而非说明性的。这被称为“解释主义的(或解释学的)社会科学”。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社会科学”中,还重叠交错着方法论上的各种“主义”:行为主义、还原主义、整体主义、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等等,不一而足。
从逻辑上说,“社会科学”原本是对人的个体活动以及社会活动的研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寻求人类活动中的某些规律性(regularities)。但人类活动自身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又使得这种研究的终极理想变得扑朔渺茫:“社会科学”究竟能否寻得这种理想中的“规律性”?或者说,“社会科学”真的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去发现并做出“因果性的说明”吗?
于是,“社会科学”能否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任何想要和正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难题:“社会科学”是否可能?
一九八八年,美国著名的哈泼·柯林斯出版集团公司的子公司“西方视点出版公司”(Westview Press Inc.)在该公司推出的“哲学之维丛书”中出版了一本《社会科学的哲学》,对上述难题和出了富于挑战性的回答。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丹尼尔·M ·豪斯曼教授评价该书“以极其连贯和富于热忱的方式从根本上讨论了社会科学所提出的所有重要的哲学问题”。该书作者亚里山大·罗森伯格是美国乔治亚大学的哲学教授,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研究,并出版了大量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生物学基础以及经济学、数学等研究论著,其中的《数量经济学的政治或报酬递减学》一书获一九九三年度的“拉卡托斯奖”(注:拉卡托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社会科学的哲学》一书经修订补充于一九九五年推出第二版,再次引起轰动。英国柯盖特大学教授李·麦金泰尔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哲学读物》一书的编者之一,他在评价罗森伯格著作时写道:“该书堪称清晰明了、精湛分析之楷模。”
那么,为何这样一本原为美国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选用的学科介绍教材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呢?恐怕关键就在于它紧紧抓住了当前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大哲学问题,并竭力以后继者的姿态对这样的问题给出最新的解答。正如作者坦言,他在书中始终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哲学是社会科学家们无法回避的重大的、根本性的话题,因为他们在各自学科内回答问题时所做的选择迫使他们在哲学问题上无法骑墙。同时,哲学家们总以为自己只关心认识论或形而上学,但罗森伯格指出,社会科学的哲学事实上对他们同等重要,因为这种哲学恰好提出了关涉知识和人类行为的根本问题。
其实,无论是在人类对自我行为的认识发展史上——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哲学——还是在被罗森伯格明确地划归为“社会科学”领地的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交叉产生的学科中,哲学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被遗忘过,而且随时地成为讨论研究的主要依据和参照系统。因为它们关心的都是人的行为活动与心理过程的关系、个体行为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行为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等,而这一切正是哲学家们声称属于他们的“特权领地”,不过,与哲学家不同的是,社会科学家似乎疏于认识个体的心理层面,更倾心社会群体的现实行为及功效,虽然对部分社会科学家来说,这种社会群体的行为只能是或应该是通过个体行为才能达到的。
罗森伯格把社会科学家们在重大哲学问题上的“失误”以及最终导致社会科学未能取得“预期的进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使他们“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先在假设:他们指望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肩负寻找和发现“规律”的使命,并自信以因果解释就可以对社会的未来行为做出“先定式”的“科学预测”。杜克海姆就曾通过对一八五六——一八七八年间欧洲各国自杀人数的统计分析,得出天主教徒的自杀率低于新教徒的自杀率这一结论。后来的社会学家深受启发,竭力模仿此道,梦想由此建成真正“独立”、“自主”的社会学大厦。但个中问题,他们却少于深究。要命的是,这些问题个个都关系着“社会科学是否可能”这一根本。
其一,由单一的个体行为如何能够对社会的整体现象做出判断?换句话说,做出这种判断的理论依据究竟在于个体行为还是在于先定的抽象观念?如果依据个体行为即可对社会现象做出判断,那么,对相同的社会现象就完全可以(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存在迥然不同的判断,我们又何以选择其中之最佳呢?反之,若是依据先定的抽象观念,那么,个体行为岂不成为辩明某种观念的纯粹“佐料”?显然,当社会学家们想要构建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他们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危及大厦基础的两难选择。
其二,依据对过去的和现在的某种特定社会现象的统计分析,我们是否就可以对未来的社会活动做出相应的“预测”?换种问法,社会科学研究真的能够发展某种“规律”吗?通常理解的“规律”一词,不外乎有这样几个主要内涵,即普遍性、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等等。但若据此判定社会科学家们意欲寻求的“规律”,我们却很难在各种社会行为活动中找到符合上述内涵的东西。因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分析,最终都只能适用于呈现此类现象的特定社会,而且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完全相同的社会现象或行为不会复复出现;而所谓的“历史重演”,不过是人们出于某种政治的或其他利益原因对不同社会现象做出的相似或类比的解释。
其三,社会科学家们声称可以通过观察社会行为以及社会活动中个人的作用,达到对社会心理的分析。但所谓的“社会心理”是不可观察的。迄今为止,即使被视为社会学分支的“社会心理学”也不过是凭藉对某些具有类似“家族相似”特征的社会行为和现象的外在分析,而给出对造成这些行为现象之原因的各种解释。至于解释得是否合理,并非取决于是否符合被解释的社会行为,而是取决于接受解释的个体是否感到满足自身的某种需求和目的。这样,问题也就凸现在社会科学家面前:对社会行为和现象的各种解释究竟有没有如同自然科学说明一样的可靠性?
罗森伯格在他的书中对那种试图以自然科学研究为蓝本建构社会科学大厦的构想给予了致命的打击,他提出的疑问当然远不止上述所开列的问题。他要捍卫的是这样一些观念:其一,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是不可比较的,因为它们体现着不同的本体论以及对人类和人类行为的不同看法。特别是,根本不存在某种方法可以把自然主义与解释学、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行为主义与大众心理学结合起来。其二,大众心理学以及所有社会科学方法都是循环论证,是不可验证的。因为我们无法用它们做出精确的预测:我们也没有什么规律可以去确证和修正它们,或者把它们弄得更精确些。这表明,要检验社会科学理论,存在着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双重困难。其三,社会科学依赖于哲学观念不会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而发生改变。哲学是社会科学的根基而不是最后产品。所以结论只能是,社会科学需要哲学,而不是相反。
不过,尽管罗森伯格对社会科学的态度已是立场鲜明,措辞激烈,他还没有从根上铲除社会科学大厦得以建构的所有可能性。他的立场无非是坚持以个体主义的、自然主义的方法重塑社会科学应有的哲学形象。因而,他在书中关心的与其说是社会科学本身是否可能,不如说是社会科学赖于存在的哲学基础如何可能的问题。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罗森伯格用以划定基于哲学理念的社会科学与以自然科学为蓝本的社会科学之界限的标准,关键一条是,后者声称能够对社会现象和行为给出类似自然科学一样的“因果说明”;而前者自知只能给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其实,“说明”(explanation)与“解释”(interpretation )的差异一直被用于刻划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始于狄尔泰的、最终以李凯尔特为集大成者的建造独立的人文(精神)科学的宏大事业,始终把人文解释放在整个被称作“人文科学”的中心。狄尔泰的名言是:“自然为我们所说明;心理(精神)生活为我们所理解。”当代的哈贝马斯更是把“科学说明”逐出人文科学的领地:人文科学不仅应是解释性的,更是批判性的。伽达默尔坦言,“解释”不是要去发现某种“客观的”意义,而是要创造意义。
可以相信,罗森伯格对所有这些都耳熟能详。而难以置信的是,在他的“术语表”中却看不到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界定。当然,在一般的西方文献中两者经常被交替使用。但这种交替又往往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科学”也可以称为“人文科学”。不过,若是依照那些梦想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建构社会科学大厦的理念,社会科学不应属于人文科学,而更近于自然科学。可以说,罗森伯格对这种梦想的破除,恰恰是让社会科学真正回到人文科学的怀抱,把社会科学真正根植于人类的行为活动之中,根植于人类对自身的终极关怀之中。这样,当罗森伯格把“解释”作为社会科学的灵魂时,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应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
在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似乎从未被明确地加以区分界定。在常人眼中,它们是相同的。即使对某些专家学者,他们也极少区分地加以替换使用,以致于引出诸如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同桌研讨却南辕北辙的笑谈。其实,若是以科学的态度,应该承认“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学理上,“人文科学”原本是因其把人的精神活动和行为表现视为研究对象而被看作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不同的研究范畴,虽然这种研究的真正形成远远晚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但在现实中,“人文科学”的这一独特地位却始终被“社会科学”占据着,使得人们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看作合理的存在的对子。不过,若用本文的上述分析稍微推究就不难发现,“社会科学”在这里正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建构社会科学必将使其丧失与自然科学配对的资格;以“解释”为核心的最后结果又只能走向真正的“人文科学”。
围绕为“社会科学”定位问题的争论,经过世纪历程到达罗森伯格,遗留给我们的却仍然是这个初始的问题,而且它变得更为尖锐和迫切:“社会科学”是否真的可能?
(Alexander Rosenberg,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236pp.Second Edition.Dimensions of Philosophy Series.WestviewPress.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