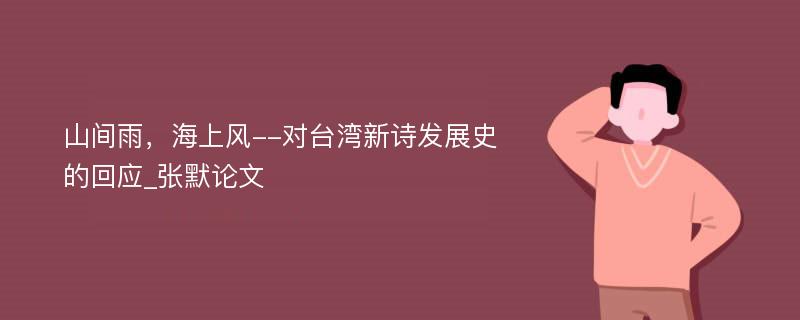
雨过山自绿,风过海自平——关于《台湾新诗发展史》的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台湾论文,发展史论文,过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争鸣篇: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二)
编者按:我刊1995年第1期曾以“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为题,转载《台湾诗学季刊》的争鸣文章,为读者提供海峡两岸诗学交流的信息。1996年3月,《台湾诗学季刊》第14期,又推出“大陆的台湾诗学再检验”专辑,刊登台湾诗评家的10篇文章,对古远清、古继堂、王晋民等人的著作提出批评,随后又在第15期刊出古远清、古继堂等的反批评文章。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就是台湾诗评家之间的意见,也并不一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例如,文治先生在《如果渐成事实》一文中,指责近两年来大陆诗评家评论台湾诗的文章,“通篇只有叫好鼓掌赞美的声音”,“从来不敢或不愿道及台湾诗的缺失”,但在同一期刊登的漫画中,却又讽刺大陆诗评家把台湾诗人“辛辛苦苦炖的肉给狗吃了”。
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开始文学交流只是近10年的事,而且交流的渠道又很不畅通,因此,通过对话和讨论,将有助于化解彼此的敌意,也有助于创作的繁荣。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只是选登批评“二古”的文章和“二古”的反批评文章,今后如有新的文章推出,本刊还将继续转载。
一、学术问题应平等对话
拙著《台湾新诗发展史》自1989年分别由大陆的人民文学文学出版社和台湾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以来,到今已有近八年的时间。它像出生在海峡两岸关系刚刚渡过漫长的黑夜,开始看到黎明的景色;刚刚结束冰封雪埋的冬天开始呈现一点春的绿意时刻的孩子,伴着忽暖忽冷的季风和忽明忽暗的天象,步履坎坷地度过了童年,进入了青少年期。因为它是第一部台湾新诗史;它是出自大陆学者之手的第一部台湾新诗史它是海峡解冻后两岸出版家同时推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它又是本人写的第一部专著。因而它占尽了优势和劣势;它赢来了热烈的掌声,也惹来愤愤的骂声;它带着拓荒的冲刺,也表现出源头的潺弱。然而当我们站立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90年代的峰颠,回首诅咒人类幼年时的野蛮;当我们立在长江下游的滔滔激流,去耻笑源头的所谓“荒唐”,甚至表现出某些未能作源头的嫉妒和嫉恨,那岂不是太没有时务感了吗?那不是一种“偏颇”、“错置”和“不实”吗?是的,人类是要不断前进和发展的,要前进和发展就要回顾和总结。写史就是一种最好的回顾和总结。这种回顾和总结是一种学术,而学术是一种自由地创见、发挥和探讨。就像写诗一样,是诗人心灵的自由表白和描述。所以在创作和学术的园地上,既没有皇帝,也没有管家(有人被称为诗坛“总管”其实是一种戏言,如真的以总管自居,那就有点“十三点”了)。既然是一种心灵的自由表白和论证,那就有优劣和深浅之分,但也仅此而已。这里不存在谁能不能当诗人谁能不能当评论家的问题,只是当优当劣、当好当不好而已。张默先生在《偏颇·错置·不实——古继堂著〈台湾新诗发展史〉初撰笔记》一文中的其他问题,我们将在下面依次展开。这里先就该文的最后一段话开膛破肚,说点看法。该文写道:“其实,治史,并非任何人都可轻易尝试,你是否具有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以上缺一不可。笔者认为古继堂当初的企图心(企图即可,加个“心”字画蛇添足)实在太大,如果把本书定名为《台湾新诗发展史稿》可能较妥,如他一开始即抱定从事《台湾新诗史料汇编》的心情,提供搜集诚实可靠的史料,给某些更具实力宏观的文学史家来治台湾新诗史,懂得自省、藏拙扬优,可能他今天在两岸的声誉就豁然不同了”。这里张默在下意识地行使诗坛“总管”的任务了。这么一小段话中不仅给拙著改了两个书名,而且为我分配了搞“资料汇编”的职务。本人真要叩首感谢张默的悉心关怀了,但又仿佛使人感到有那么一点缺乏自量?著作优劣高下别人可以评说,至于叫什么书名,作者应该从事什么职业,别人是无权说三道四的。正像张默的诗写得不怎么样,和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缺乏学术品格,但别人无权叫他不写诗,不写文章一样。这种作风对张默来说有点习惯性。他曾自以为是地在诗坛弄出许多框框和等级,贴上许多标签,来认定别人的地位,叫人们对号入座。人们熟知的这个“十大”、那个“十大”就是一例。但不知是张默眼睛老花、还是近视,不是弄得不准,就是别人不肯就范,结果弄得不伦不类。有不少台湾作家对我谈起此事,轻蔑地付之一笑。有位诗友就不屑地对我说:张默那算什么,有谁承认他,我和周梦蝶就拒绝他的封赏。张默在该文中公布的治史理论:“宏观的远景,独特的主张,客观的态度,和犀利的笔触”也实在不敢领教。请问这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有什么治史的特点和个性,放在写什么样的文章上不都一样吗?这一招如果录验的话,在张默的手里还不嗖嗖嗖地立马蹦出几部新诗史来?张默在文里还以教官对士兵、先生对学生、主子对奴才的口气教训道:要“懂得自省,藏拙扬优”。是的,谦虚、自省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人人都要重视垂范的。但从张默的语境领悟到,他这只是板起面孔教训别人的。而板起面孔教训别人的人本身是否就违背了这种美德,是否正好是一种不知谦虚自省、不知藏拙扬优的行为?
探讨学术问题,首先要有学术涵养,学术意识,学术氛围。双方起码要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人格和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展开交流和对话,在此,张默首先需要端正学术态度,把自己从居高临下的地位上降下来,降到与对方同一地平线,才能获得学术交流和对话的资格。
二、《台湾新诗发展史》之我观
《台湾新诗发展史》是本人“台湾系列文学史”即《台湾新诗发展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和《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的一部,也是这套书的第一部。它孕育和创作于80年代中期,出版于80年代末期,大陆版稍前,台湾版稍后。本人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动机是完全纯正的。那时只是为了展示中国诗坛和诗歌成就的完整性,让大陆读者知道隔绝在浩瀚海峡那边的,还有祖国一片诗的神奇的土地;还有一大批值得骄傲和尊敬的诗人;还有那么多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美丽的诗篇。并想通过这种展示来探索台湾新诗自身发展演变的状貌和规律性;探索诗与政治、与时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探索台湾新诗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外抗异化吞食,内抗逆流堕落,表现出铁骨铮铮的民族风骨和坚韧不拔的艺术韧力;探索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异同,通过较为深入的思想和艺术分析展示出一个多姿多彩的诗的艺术世界。那时除了与转道海外来大陆的台湾个别诗人有极表面、短暂的接触之外,和台湾各流派各诗社基本上没有接触,因此谈不上受到谁的包围和影响。我的心灵中基本上是一片诗的童话世界。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认我的思想的倾向性。众所周知,本人在学校里受的是系统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教育;大学课堂上接受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教育,批判和排斥的是现代派。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受的哲学训练是肯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的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成了我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并且我始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科学、最可靠的,无法取代的观察和评价事物最犀利的武器。《台湾新诗发展史》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当然也吸收其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由于海峡阻隔,收集资料不易,当该著罄稿后,虽然理论构架,作品论析诸方面较为满意,但对书中的许多资料在无法核对的情况下,缺乏把握,因此总想在送交出版社之前能找不同诗社、不同流派、不同观念和台湾诗人过过目,作些修改更正的工作。因而这部书稿在交给出版社之前,曾交由台湾三个流派,三种截然不同诗观的上十位诗人、学者阅看过。他们都十分热情、认真审读。并且都提出了意见,有的还写了非常详尽的修改方案。1988年9月我会见创世纪诗社一行诗人时,与我太太一起抱去的是四大厚册全部书稿,(不是张默说的一部分书稿)由诸位书上列有专节的诗人分别阅看。他们提出了不少修订意见,虔诚地向他们表示道谢。应该说这部书从准备资料、构思到写作,到千方百计请台湾不同流派诗人、学者审稿等,当时我该作的和能作的,都已作了。因而学术动机是端正的、治学态度是较为严谨的,稿子的修改也是认真的。该书稿虽然还隐伏着不少问题,但它出版之后却获得了热烈的、良好的回响和评价。现摘录数则肯定性的评价如下:
一、江西大学教授陈公仲在《文艺报》1989年9月23日发表评论认为:“这的确是一部有个性有水平有质量的台湾新诗史”,“《台湾新诗发展史》就是建立在对台湾新诗的全面系统,翔实充分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的。甚至可以说,对于新诗的微观剖析才是他之所长,才是这本书最大的成功,才显露出他诗人的气质和灵感,才表现了他情感丰富,处事精细入微的个性特征。不少名篇诗作的评论文字,本身就是一篇篇精美的鉴赏文章。”
二、北京大学教授汪景寿,中山大学教授王剑丛等合著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1991年10月天津教育出版社)一书认为:“《台湾新发展史》问世以来,引起了海内外研究者的瞩目,开创意义显而易见。尤其是对于台湾学界的震动,非同凡响。由远在台湾海峡彼岸,未尝到过台湾的作者,完成此第一部台湾诗史的力作,令人感佩。也不禁为台湾本地学术生态环境感到汗颜,台湾无批评环境,也缺乏有见识有胆量的批评家,以致至今,在我们的学术界和出版界,还没有一部公正客观的新诗史。而这一部大陆诗评家研究台湾新诗发展的学术性著作,也是彼岸学者的台湾新诗定位、为台湾诗人立传的史学专著。出自台湾著名诗人、诗评家李魁贤、文晓村的肺腑之言,具有一定代表性。该著为《台湾新诗发展史》概括的特点是:①善于分析背景;②巧于捕捉特点;③精于鉴赏,道尽诗人心底秘密、被称为“诗的解谜人”;④诗人论诗;文笔优美,充满诗情画意,这是《新诗史》有别于同类史著的独到之处。
三、中南财大教授、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古远清于《诗刊》1990年3月号发表《新颖的史识与独到的史笔》一文认为:“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这是海峡两岸第一部台湾新诗史,也是一部具有创见,无论是在史识还是史笔方面都具有特色的学术专著。……出版后之所以能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本书具有独到的史识,在台湾新诗的归属及如何摆正它的地位问题上,该书澄清了过去比较混乱的看法。……对于“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三大诗社的演变及互相竞争、诗坛内外的重大辩论,作者也没有照抄现成的结论,或根据个人的好恶随意褒贬,而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偏颇。最明显的是长期流传的台湾“现代派”始于纪弦的“现代”诗的说法。作者认为:现代派进入台湾的最早时间不是1949年,而是1935年;现代派在台湾的第一个阵地不是纪弦的《现代诗》诗刊,而是台湾省籍诗人杨炽昌主办的《风车诗刊》。这就将台湾现代派诗的历史回溯了十四年之久,从而恢复了历史的原貌……对台湾现代派的评价,同样没有主观随意性,不以感情代替评价,同时又有自己的是非尺度。这样的史笔,正有利于作者连接处疏浚台湾新诗发展的流程。
四、诗评家、中南民族学院副教授邹建军在《唐山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2期发表《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读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一文中写道“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是一部风力独具的巨著,开拓了中国诗史建设的新局面。一、强烈凸现的主体意识。在材料翔实,态度公正客观的基础上,强烈的主体意识使它到处充满见识。二、诗、论联系中,揭示诗作特征。像古继堂这样充满个人见解、条分缕析地总结和揭示诗的规律,确系少有。让我们掌握新诗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未来新诗的健康发展,这是《台湾新诗发展史》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三、博然的赏诗艺术,高妙的解诗专家。《台湾新诗发展史》是那样深厚与广博,简直是一座天然的自然博物馆,也如蓝天下的大海。这一方面得力于生机勃勃的史笔,一方面源于大量诗歌的独具风彩的鉴赏。触及灵魂与血脉的鉴赏,是以前的文学史著所难以企及的。大量的对妙诗的精解,使《台湾新诗发展史》走向了个性化与主体化。古君不仅是一位具有客观史识的史家,也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与心灵的学者。四、生机勃勃的史笔。《台湾新诗发展史》宏大严整,客观公正,也有《史记》之遗风。它生机盎然,丝毫没有一般学术著作的枯燥乏味,相反,显出博大的风彩。这主要得力于充满个性的生机勃勃的文笔。“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这就是古继堂先生《台湾新诗发展史》成功的奥秘,也许就是他新颖的诗史观照主题概示。它凝集了他十年的心血,历史终将证明它确是一部风力独具的划时代巨著。特别是当中国现代和当代新诗史还未诞生的时候,它的出版更显得独秀孤标。”
五、台湾、海外学者、诗人的评价:台湾的《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立晚报》、《台湾新闻报》、《首都早报》、《台湾立报》、《民生报》等,美国的《华侨日报》等海内外三十多家报刊发表了专题评论和报导。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里不一一摘录介绍。现从各方的大量来信中,选择两封,略加告知:痖弦兄于1989年9月22日来信说:“这书写得非常成功。先生能运用有限的(不易取得)的台湾诗坛资料,把这几十年的诗的发展,理条如此清楚,又加上精辟的评述,令人敬佩。连台湾本地到目前还没有人写出这样的著作哩!”老诗人纪弦于1994年1月16日来信说:“非马兄把书中有关我的部分,第八章影印寄来。我仔细拜读过了之后,对于先生的评论与分析,虽然有些地方不能完全同意,但我必须尊重先生的看法。至于先生对我诗艺之过奖,这一点,我不但接受,而且也已把先生大名列入我的知己者名单中了。”张默于1989年也有一信给我,对拙著作了适切地恳评。那时我异想天开,想征得张默的同意发表那封信,因未收到张默的回信而作罢。拙著究竟怎样,已有众口评说。在数十篇评论文章中,有说特别好的,有说比较好的,也有个别的像张默《偏颇·错置·不实?——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初探笔记》的文章。按照一般竞赛打分办法,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再去掉一个最低分,拙著大约是一个中等以上的分数。自己的孩子,自己心中明白;自己的著作,自己心中有数。看到好话不至于头脑昏昏;听到骂声,也不到于失去自信。树经得住狂风摇晃,是因为它有根;那么山立风前,除了吹散一些云雾和尘埃之外,还会有什么呢?
三、痛苦的回应
拙著《台湾新诗发展史》自1989年出版以来,有两篇较为突出的批评它的文章,均发表在《台湾诗学季刊》上。一篇是游唤的,一篇是张默的。游唤那篇文章,以鲜明的“独台”的观点,集中攻击拙著以“中国为本位”,而不是以“台湾为本位”,是把台湾新诗看作中国新诗的一部分。他的文章是以反面的话语道出了正面的真实;以不同的语调说出了与本人一致的内涵。从反面肯定了拙著的功劳和价值,因此我便没有必要为文批驳,这就是本人面对攻击而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此外,也恐过早发言,封堵言路,听不到更精彩声音。除了张、游二文之外,六、七年前还有几位“台独”观点的年轻学者开过一次座谈会,座谈纪要发表在台湾《民生日报》上。记得其中有吕兴昌、陈明台等。他们集中攻击的,也是《台湾新诗发展史》中的论述爱国主义作品和思潮的内涵。记得吕兴昌在谈到拙著对巫永福《祖国》一诗的分析和评价时说:古继堂一看到“祖国”二字就高兴地要跳了起来。他这话的确符合本人的心境,但他们的观点却不地道,因而本人在《香港文学报》发表文章进行了反驳,《世界日报》转载了该文。不管是吕兴昌、陈明台等的座谈会,还是游唤的文章,都是意料中之事,也不难批驳。意料之外的,是张默的大文。现将该文提出的问题依次回答:
一、关于“诗人分类,张冠李戴”问题。①“方家诗派”之说。此说是受余光中文章的启发。当我阅读了“三方”的作品之后。以为“三方”作品的风格非常接近,余氏之说颇有道理,于是便加以沿用。但“方家诗派”作为一个小的群体,在书中应组构在何处,而大方小方又有时间差别,东谈一家,西谈一家,前叙一家,后叙一家,则显不出这个小小的流派中流派的内涵,而“三方”中方思为长,成就也最高,为“三方”中的灵魂人物,而方思本人、是纪弦“现代派”的最早成员之一,于是就把他们放在“现代派”中叙述。而在这一节中是以叙述方思为主的,其他“二方”只是副叙而已。我想这样安排,并未犯什么大忌。也没有什么“令人不解”之处。
二、关于高准、张香华、朵思三位诗人放入青年诗人群中叙述问题。高准出生于1938年,张香华、朵思出生于1939年。他们70年代初均为30岁刚刚出头的人,而不是张默说的50岁出头。张默为了否定拙著,竟然把他们的年龄虚报20岁,这样作不是过分了点吗?请记住,拙著中写的是70年代的史实,是把他们放在70年代初发生的台湾青年诗人运动的背景中去叙述的。张默的时间表错了。
三、关于对羊令野、罗门、向明、痖弦、叶维廉和创世纪“任意枉下断语”的问题。我不认为是“古继堂枉下断语”而是张默在乱扣帽子。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枉下断语”。“枉下断语”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判断,而本人的判断是件件有据可依的。请问羊令野曾任诗歌队长是不是事实?此事属实,“居高临下的威权”是一种地位势态的形容。当然也可以有别种写法,别种形容法,但怎能够说本人这种写法就是“枉下断语”呢?请问在《创世纪》遭到挟击时,洛夫是不是“首当其冲”,洛夫是不是台湾现代派的名人,这里何为“枉”,张默对现代派的理解极为狭小,认为只有纪弦成立的现代派才叫现代派。岂不知西方的许多文学流派都统称现代派,其中也包括超现实主义。请问罗门是否曾被张默封为“十大诗人”。沿用张默自己的断语,也叫“枉下断语”吗?那首先“枉下断语”不正是张默吗?向明是台湾现代派中一位“中国化”的诗人。是本人的断语,但这断语张默用什么来推翻呢?没能推翻就说别人是“枉下断语”,那不是明明在“枉下断语”吗?“创世纪”是不是“代表国民党军中诗人的倾向”,有没有较浓的政治色彩?“战斗诗特辑”是要拓展毫无政治色彩诗的素材吗?《创世纪》的发刊词《创世纪的路向》一文中三条主张的第三条:“彻底肃清赤色黄色流毒”也不含政治色彩吗?至于“创世纪为国民党服役”,则是张默慌乱中的自我中伤,查遍拙著也没有这句话。那么“纯属大胆虚妄的猜测”看来也扣不到古氏的头上,而是张默自我惊惧情况下的语无伦次和口不择言。关于把洛夫、向明、痖弦、叶维廉、罗门一律划归为现代派诗人,确属乱扣帽子。请查一查拙著121页开列的“以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名单中,除了罗门之外,似乎没有洛夫、向明、痖弦、叶维廉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分别在“创世纪”和“蓝星”的同仁名单中。张默为什么要无中生有混淆视听呢?张默还煞有介事地说:“古氏当初如在行文中说他们的诗风有现代主义的倾向倒无不可,可惜他对“派”与“主义”之别不察,终因一字之差,而意义相距千里矣。”张默以为在这一点上他牢牢地站住了脚,因而不无得意地在语尾加了“矣”字。不过且慢得意。在辞义学上“派”是指人群,而“主义”是指主张。流派和诗社是有区别的。文学实践中一个流派可以包含许多诗社,台湾就是如此。通常人们把创世纪、现代和蓝星称为台湾现代派的三大诗社,就这个意思。因而洛夫、罗门、向明、痖弦、叶维廉虽然不是一个诗社,但却是一个诗歌流派——现代派。看来不是本人“相距千里矣”,而是张默错说了“千里矣!”综上所述,“张冠李戴”的不是古氏,正好是张默本人。
这里需要对“政治”多说两句。政治有好有坏,国民党也今昔有别。人们今日对这两个词的理解与往日也大不相同。蒋经国的国民党是搞政治的,但他搞的政治中有许多是好的,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坚持一个中国、大兴富民之道,开放两岸探亲等。所以不要一听说政治就紧张;不要一听说国民党就不安。如今是所有热爱中国的人闭结起来反对“台独”,其中当然包括所有主张祖国统一的国民党人。时代不同了,如今谁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所有政治,谁也不会不论三七二十一地反对整个国民党,何况写史只是一种总结和回顾,无需有什么顾虑。
二、关于“评价诗人标准,南辕北辙”。①“对蓝星诗社的介绍,作者采用罗门的《蓝星的光痕》的说法”。张默此人既爱主观武断,又爱多疑猜测。本人年初曾致信张默,对他赠送《新诗三百首》一书表示感谢。除了谢意外,还略谈及对该书的粗略印象。其中不指名地谈到有的诗人辛辛苦苦经营了一辈子,榜上无名,可能人们会感到不服不公。张默即来信猜测说,“我知道你指的是谁”。其实这是自作聪明,我指的是许许多多榜上无名的两岸有成就有的诗人。我看到这种猜测感到好笑。不过从这一猜测中已经透露出张默对我那无心之言是很在意的,而且慎重思索过的,结果他猜错了。这里张默又在猜测了。我用的是罗门的材料。这一次没有完全猜错,罗门《蓝星的光痕》一文的确是我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但本人还有其他参照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的使用,是经过我的判断的。张默在引用本人的话时,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作法。本人在拙著的181页的那段话是这样写的:“后来由于覃子豪的去世,钟鼎文的退出,余光中、夏菁、吴望尧、黄用等人的出洋,蓝星诗社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从1964年到1984年的20年时间里,由罗门和蓉子夫妇在自己的灯屋里,维系着蓝星一颗微微跳动的心。每逢同仁返台,由罗门夫妇作东,在灯屋里聚餐议论社务。所以在后20年的艰苦岁月里,罗门和蓉子成了蓝星诗社不死的灵魂。”张默把前因后果都去掉了,引用的话语如下:“从1964(少了个‘年’字)~1984年,罗门、蓉子(这里抽掉了几句关键话语,未用省略号)成为蓝星诗社不死的灵魂。”把作者的原话任意加以掐头、断中、去尾后重新组合,再用引号括起来当原话使用,这作法或许是张默在著作史上的独创。最起码可以看出,不是作者缺乏正规的文法训练,就是别有用心的组接。在这样组接了之后,再来说覃子豪、余光中的作用,对读者构成了欺骗。请问覃子豪已经去世,怎会再对蓝星发挥作用,余光中已经出洋,能够精心地主持蓝星社务吗?据我所知,1980年8月蓝星的死而复活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余光中就未能参加。怎么能够说“以后历次改组复刊,大多由余光中主导。”张默似乎比蓝星诗社的社长罗门对蓝星的事还清楚。难道不令人怀疑张默在这里不是又一次自作聪明吗?更不应该的是,张默借否定拙作之机,捎带着对罗门也进行了攻击。他写道:“综览罗门最大的长处,是把个人的资料洋洋洒洒,一点一滴,装订成册,一字排开,为他将来个人的纪念馆作准备,至于为诗坛诗社服务,那不是他的第一志愿。”把个人的资料积累起来,传给后代,启迪世人,也是为社会为诗坛作贡献嘛!难道罗门作错了吗?能为诗坛社会服务就好,怎么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把它当作第一志愿呢?张默是把对诗坛对社会服务当作第一志愿吗?对别人不适当的挖苦,恰恰是对自己的一种暴露。
②关于“对诗人个别(这话十分别扭)评论标准不一,有些诗人零缺点(这话别扭),有些诗人缺点一大堆。”张默例举了本人对余光中、叶维廉、赵天仪、李敏勇的评价后概括道“仅举以上数例,足以了解古继堂对诗人评价的判定,南辕北辙。某些十分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视觉里反而缺点一箩筐,反之某些平庸的诗人则较少发现其缺失,笔者以上铁的论证是否主观,请有识的诗学史家和读者明鉴。”读了张默大文的每一个字,没有发现张默对我对余光中、叶维廉、赵天仪、李敏勇的评价有丝毫的反驳性论证。更不要说“铁”的论证了。大概什么叫“论证”张默还没有弄清楚。论证就是要引用大量的论据,把你反对的东西驳倒,证明自己有理。张默错把引用自己反对的东西当作了自己的“论证”,(因为文中只看到张默引用我的话)。不过从他引用本人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意思。他引用本人评余光中和叶维廉的话,都是谈缺点的话,引用本人评赵天仪和李敏勇的评论,都是谈优点的话。于是“某些十分杰出的诗人,在他的视觉里反而缺点一箩筐。”指的是余光中和叶维廉。“某些平庸的诗人则较少发现其缺点”指的是赵天仪和李敏勇。那么张默用了什么论据来论证余光中、叶维廉杰出,没有;张默又用了什么论据来证实赵天仪和李敏勇平庸,也没有。既然这两者都没有,你又用什么来推倒我对他们的评价呢!又怎么证明你这“杰出”和“平庸”的认定是对的呢?就凭有的缺点“一箩筐”有的缺点等于零吗?这种判断问题的方法不是太形式主义、太机械化、表面化了吗?还用得着“请有识的诗学史家和读者来明鉴”吗?自己心中应该有数。这里“南辕北辙”的仍然是张默。
三、关于“全书校勘粗疏、错误百出。”这一点是事实。正像张默所说,错误之处还不止张默举出的。这种错误的出现分几种情况。一种是由台湾的原始资料来的,由于无法核对和核对极为困难,而造成的。一种是本人粗枝大叶弄错了的。一种当时海峡两岸交流刚刚开始,台湾的排字工人不识大陆的简体字,在简繁改变中弄错了的,这种情况占的数量最多。当本人拿到样书后,通读了一遍,搞了一个正误校勘表,这个表上校正62个错误字、词,但张默举出的有些还不在其中。这里要十分感谢张默的细心和坦诚。此书有再版机会,张默此功要汇入书中。在此再表感谢!
在本文结束时,再多讲几句话:年纪渐老,骨质疏松,自己主动跳水,或是被挑战一方拉着下水,都极易发生粉碎性骨折。除奉劝老年的挑战者别轻易作这样的文字跳水之外,本人一般将不再作这样疲劳性、消耗性的应战。
1996年5月16日子北京西郊寒舍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第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