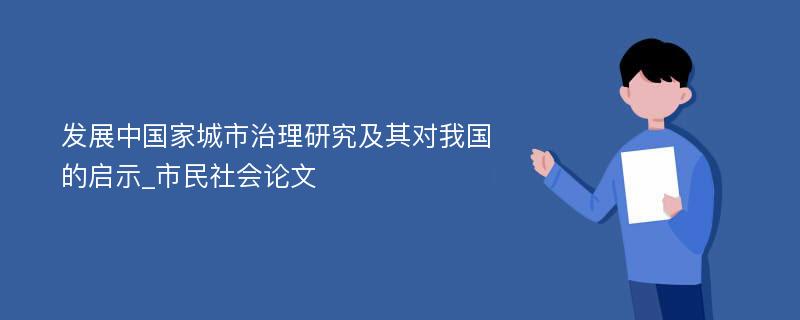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城市管治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启发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C931:C912:F293 文献标识码 A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Davoudi,1995)。在现代社会,最佳的和可持续的管理系统往往是多维、分散、网络型以及多样性的(Asian Development Bank,1997)。考虑到社会的每个要素都有各种权力,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可为促进政府、公司、社团、个人行为对生产要素控制、分配、流通的影响起关键作用(Christian,1996)。本文主要探索发展中国家城市管治研究,尤其注重南亚、西非、东非、南非和拉丁美洲城市管治的最新发展,以便我们能在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管治模式的基础上研究我国的城市管治体制及运行模式。
1 城市管治研究的背景
有关管治的研究,开始于1980年代晚期,1990年代形成研究主流。这里就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我国城市管治研究的背景作简单介绍。
1.1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管治研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由传统的福特主义(Fordism)和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转向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和“劳保”国家(Workfare State)。后工业社会的生产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使得世界经济生产方式的空间特性,既强调跨越边界、区际差异,也强调控制和协调(Davoudi,1995),这表现在全球、地区、国家、区域、城市等各个层面。另一方面,世界城市化的趋势正在加快,尤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更是如此。总之,城市经济正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据此,构建一个既有公平、公开,又具竞争力的城市管治(Governance)和协调系统,对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最佳的管理和控制往往不是集中的,而是多元、分散、网络型以及多样性的,既涉及中央、又涉及地方、也涉及非政府组织(NGO)等多层次的权力协调,其中政府、公司、社团、个人行为对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控制、分配、流通的影响起十分关键的作用。
1.2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管治研究
全球城市研究机构(The Global Urban Research Initiative,GURI)在1991-1993年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评估,在诸如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方法论、城市管治、地方机构和地方政府、城市立法、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环境、性别研究以及儿童的作用等研究热点中,遴选出城市管治、全球化、城市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城市贫困、城市财政和经济、城市社会结构作为近期GURI的六个主题。1995年墨西哥的GURI网络会议通过投票将城市管治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研究的中心主题。近几年来,该组织在圣地亚哥(智利)、墨西哥、里约热内卢(巴西)、达卡(孟加拉)、孟买(印度)、马尼拉(菲律宾)、珠海、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约翰内斯堡(南非)、阿比让(象牙海岸)、伊巴丹(尼日利亚)和突尼斯分别召开会议由地方学者、决策人、地方和国家政府代表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共同就城市管冶主题进行研究(Stren,1995)。
1.3 中国的城市管治研究
在中国,过去20年的改革扩大了城市自主权。城市政府从中获得相当的独立发展资源,已有能力为市民和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尽管中国在许多方面市场经济的机制已经开始运作,但城市管治中旧计划经济体制仍然盛行,政治—行政中心的地位对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仍起关键的作用,各城市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和等级也就显得至关重要。现行的城市行政体系在国家资源分配和事权分享方面,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存在很大的差别。在过去20年中,已有300多个县改为县级市,许多城市的行政界线发生变化,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城市化地区城市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变化关键主要在于控制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向,而这种行为是有悖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城市行政级别设置相当臃肿,阻碍了中国城市的有效管理,也妨碍更广泛的公众参与管治。在这种状况下,“市长是一个积极的充满开拓精神的企业家”(Wang,1994),需要一种新型的城市管治结构运作。然而,迄今这方面系统性的工作做得非常有限(Huang,2000)。在发展中国家,相关的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正受到重视,中国相关的研究刚刚开始(注:2000年5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次城市管治学术研讨会。)。
2 城市管治框架的变化
西方国家的城市管治框架是建立在管理理论之上的。西方第一代管理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物本管理。当时的管理理论学家认为,人是经济人,是经济动物,只要满足人对金钱和物质的需求,就能调动其积极性。基于这种认识,管理理论注重实行物本管理,其特点是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把人当做工具、物来管理,对人实行物质刺激和金钱激励。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应用,社会生产率的大大提高,以及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各种各样的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相继出现。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物本管理提出批评,随之而来,西方第二代管理理论产生。该理论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人本管理。这种管理理论有三种表现形式:人群关系学(注:管理学家梅奥经过多种调查研究和实验认为,工人获得集体的承认和安全比物质刺激更为重要。影响工人积极性的还有工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工人社会地位低下,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发挥不出来。据此,梅奥提出以“社会人”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群关系学”。)、行为科学(注:20世纪40年代,“人群关系学”导致“行为科学”的产生,行为科学主张协调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激发人的内在动力,促进人们自觉自愿发挥出力量来达到组织目标。该理论重视人的因素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重视人的外在关系行为)和“以人为本”理论(注:20世纪80年代美日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不安和关心,因而导致美日比较管理研究的开展。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管理模式的背后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对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认为企业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组织,人不单纯是创造财富的工具,人是企业最大的资本、资产、资源和财富,是企业的主体。据此,管理应该采取“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方式。)。在现代西方,对人的创造能力的关注日益增长。作为人的最高需要的自我实现正成为西方人追求的重要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是挖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和智力,把人塑造成“能力人”。据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智力因素,培养和发挥人的工作能力,营造一个能发挥创适能力的环境,成为新一代管理理论的重点。基于这样的思路,以“能力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能本管理发展成为西方第三代管理理论。“经济人”、“社会人”和“能力人”塑造也就成为西方国家的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
基于上述管理理论框架,联合国人居中心报告是这样定义管治的:管治作为一种可认识的概念,它是存在于正规的行政当局和政府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权力总称。在许多范式中,管治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管治强调“过程”,强调决策建立在许多不同层面的复杂关系之上(Unchs,2000)。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管治基本上是涉及城市地区不同机构层——地方政府、市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关系的性质、质量和目标的总和。这些关系又分解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结构和规则等诸多方面(McCarney,1996)。研究方法一般通过系统的流态、系统机制和系统目标进行,将经济、社会、生态等可持续发展,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综合包融在内的整体管治概念。也就是说,城市管治涉及中央、地方和非政府组织多层次的权力协调,其中政府、公司、社团、个人行为对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信息、知识等生产要素控制、分配、流通的影响都是研究的内容(Brenner,1999)。
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机构——全球城市研究机构(GURI)网络的参与者(注:参与者一半是社会学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规划师,仅有很少的政治学家,因此,城市管治的研究一开始就特别注重邀请地方政府官员和公共行政管理专家的参与。),通过第一轮的研究,是这样定义城市管治的:管治(Governance)不同于政府(Government),它涉及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执法者和守法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政府和可控性(Governability)的关系(McCarney,1995)。此外,发展中国家不同地方的专家对城市管治也有不同的理解。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区的专家认为,城市管治的概念应该是在推进城市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地方政策层次上。中国珠海市的市长认为,城市管治就是政治能力和政策措施的结合,使城市更有效地运作(Wang,1995)。大多数非洲研究者认为,城市管治应该强调城市政府与社区的关系。
近期发展中国家城市管治的中心议题放在地方层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遍缺乏可持续性和有效率的地方城市政府,小城镇服务设施严重不足,暴力事件经常发生,贫困和失业面扩展很快,地方财政赤字严重,私营企业部门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联合抗缴房租和物业管理费用的倾向。很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将管治的理念引入到城市地方政府的层面上来。
自“城市管治”确定为发展中国家城市研究的中心主题以来,一些问题正成为讨论和研究的热点,诸如:(1)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及其对地方政府的作用;(2)社会运动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再现;(3)新机构、新政治关系和新结构;(4)有关有效政府类型的研究等等。
3 分散化及其对地方政府的作用
在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分散化的政策。尽管这一时期分散化的目标通常是“发展”,而不是政治或财政方面的分散。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分散化趋势进入第二波。这时候的分散化已与民主化进程相伴随,并受到强有力的财政体系支持。经过这两轮的分散化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处于基层的农村和城市地方政府较1960年代已经失去太多的权利和自治力(Stren,1995)。
3.1 分散化类型
分散化存在两种类型,即:国家权利分散化和城市内的分散化。
(1) 国家权利分散化
在印度,按照宪法,尽管城市政府自19世纪末就保持有广泛的地方职能和税收权力,但是国家在地方政府之上具有额外的权力。这一时期,用于城市再开发和城市扩展自筹资金的城市改造基金(city improvement trusts)得以建立,在所有印度大城市都建立城市开发部,其职责是将城市规划、法规、房地产开发、住房和公共设施统一起来。如果城市政府一旦是民主化的,那么中央政府就有权力中止或解散城市政府(Sivaramakrishnan,2000)。直到1990年中期,大约50%的城市政府是由中央政府指定的行政长官负责的。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这种状况直到1992年城市地方政府和农村地方政府两个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才得到改善。在城市地方政府法修正案中规定,城市政府从终止到大选组成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城市政府必须参与解除贫困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城市政府的财政计划与中央政府脱钩。这次宪法修正案是印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瞄准了加强民主化和分散化,给城市政府带来了职能和财政关系方面的秩序(Stren,1995)。
(2) 城市内的分散化
城市政府需求、法律、财政和其它行政权力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下层政府。加尔各达市通过法规建立由15个行政区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由行政区选出的议员成为该自治委员会委员。自治委员会的职责是指导或控制市长——议会制度运转。城市自治委员会由城市人口和土地规模决定。
3.2 分散化的影响
(1) 对政府权力的影响
在大的联邦国家,分散化促进了城市政府权力的巩固。巴西在1988年通过了新宪法,巴西利亚进入一个新的民主时期。以前是国家对这个城市承担责任,现在是由选出的市长和议会对城市负责,一些重要的方面如公共服务管理、土地管理和地方税除外。按照1988年新宪法,市政府按照组织法有权利重组市政府结构,而且都是建立在市民社会参与很强的城市规划不同代表实体间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市议会扩大了不同组织参与政治和规划的机构的能力,并从中产生城市理事会,赋予它协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意见的功能。巴西50个大城市的市组织法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功能(Coelho and Diniz,1995)。近年来,比较富裕的城市政府已经将重心转向解决城市贫困的社会政策制定和设计,尤其注重教育和健康领域。过去这些国家关注的领域现在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能。
(2) 对政府效率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的分散化过程,城市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显得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增加相应功能以提高政府效率成为关注的中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城市地方政府开始注意资源的流动性功能。在孟加拉国,中央政府任命了一个地方政府结构评估委员会(Local Government Structure Review Commission) "inter alia",对分配中央政府的基金给地方政府时作出评估和推荐,由公务员、专家和城市政府代表组成的国家基金委员会一次次评估将基金分配到不同层面的地方政府(Islam and Khan,1995),这类基金约占城市总税收的1/3。然而,尽管如此,这种体系和过程运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城市政府效率低下。
4 社会运动和市民社会再现
4.1 民主化进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全球许多军人政府纷纷还政于民,与东欧、前苏联、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一起,形成了全球民主化进程的第三波(Huntington,1991)。西非法语区国家是受这种分散化和民主化影响的最好的例子。这种国家层面上的民主化也意味着地方政府民主化和责任感的增强。
4.2 城市社会运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拉丁美洲,人们为了改善生活状况,一个多阶层组成的地方层次的协调活动非常普遍,被称为“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
在东南亚,非政府组织(NGOs)和人民组织(POs)在消除城市贫困的开放政治空间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与拉丁美洲的“城市社会运动”相平行发展的。由于亚洲城市政府日益递减的提供城市基本服务的能力,流动在社区机构中的地方社团正好填补这方面的空白(Porio,1995)。然而,这些非政府组织(NGOs)和人民组织(POs)的阶级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其中许多活动带有中产阶级的色彩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4.3 市民社会再现
民主化和城市社会运劫的直接结果就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再现。由于要求结束军人政府和一党制政府的民主化进程,一个由律师、教师和新闻记者等多元社会群体组成的协会推进了国民大会召开和宪法的修订,使得中央政府层的民主化很快扩展到地方政府层面,也推动了分散化的过程,促进了由传统的律师、职业协会、劳工组织、学生和妇女群体、地方和区域发展协会、新政党、社会和慈善组织、公共和私营企业等组成的更加活跃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这些新的社会角色在地方城市政府层面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非洲,南非可能是市民社会中机构网络最发育的国家。据初步估计,南非有不少于54000个非政府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相当活跃(Swilling,1994)。它们从提供技术咨询的服务组织到为低收入社区无偿服务,从环境保护到跨阶级、种族和地方分割的互信建立和冲突解决等,应有尽有。它们在南非城市政府层面上发挥非常主体的作用。这种做法目前已经开始影响整个南部非洲和英语区的非洲国家。
接近市民。加尔各达城市自治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要拉近市民与选举代表的距离,解决许多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比如地方性道路、路灯、下水道和邻里公园等。
5 城市政府职能重组
在1980年代,分散化运动影响了大都市的管理,提出了管理结构的改革。在南美洲,市民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发育良好的。在这一地区,新城市经济具有“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倾向(注:传统的城市工人阶级严重失业。)和“非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倾向(注:就业机会向国际性的文化和信息部门转移。),在一些地方的城市已经滋生社会不满的情绪。人们通过投票希望要一个“好的政府”帮助度过难关。在印度,建立市长——议会制度。这一制度具有将集体领导概念引入城市管治中的创新意义。市长由5年任期的议会选举,副市长和另外小于10名政府内阁成员由市长任命。这种市长——议会制度被认为是政治行政机构和负责任的政府。中央政府特派员作为内阁秘书和行政机关职员工作,并且对市长负责。议会在地方议会主席领导之下。城市司法委员会主席由反对党领导担任。这样一来,市长、行政长官和中央政府特派员组成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政党也能很好的支持这种市长——议会制度。这种制度尽管市长需要与相关成员分享权力和责任,但是由于副市长和另外小于10名政府内阁成员由市长任命,因此也导致了一个强市长管治体系。在西非法语区国家,几个大都市进行政府重组和政区重划,建立大都市议会,推选分区的大都市议会代表;实行分区税制,对低经济增长区减少税收,提供更多的服务。城市管治注重机构组织效率、决策过程、政策形成与实施、信息循环以及政府与管治的关系(Attahi,2000)。
另一方面,城市管理引进民主化理念。例如,开普顿在经济上是南非最好的城市之一,尽管它的传统制造业,尤其服装和纺织,近10年有所衰退,但信息、知识和服务部门增长较快。然而,这个城市20%的人口生活在国家最低贫困线以下(155美元),50%是受健康和失业威胁的脆弱人群,70%的社区青年男性都是帮派成员,人均犯罪率也是南非最高的城市(Pieterse,2000)。针对这样的状况,开普顿逐步建立起城市管治框架。首先,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民主的地方政府选举,将开普顿大都市区的39个地方当局和19个行政区,建立由6个自治的地方政府和一个“弱”的大都市当局的双层次的大都市政府系统。其次,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将发展目标锁定为提高全球竞争力、消除贫困、财政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好的城市管治。第三,通过“城市组织法(the Municipal Structures Act)”规范城市管治模式,公布“开普顿市民公约(Citizen's Charter for Cape Town)促进市民参与城市管理,推进政府决策走向公司化模式。
6 城市贫困的整治
最近几年来,有迹象表明,在市民社会内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新地方城市政府或新机构已经出现,它在国际和国内分散化和民主化机构的支持下,共同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这些新进展,其中包括中国城市市长的作用、巴西的《城市组织法》以及南非的地方协商会议等都令人鼓舞。
在拉丁美洲国家,也许涉及到城市贫困的城市管治创新是将其纳入城市社会政策的范畴。自从20世纪80年代实行城市政府机构调整以来,“社会补贴(Social Compensation)”计划已经在许多国家实行。这些计划的目的——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城市层面的——都是帮助贫困的农民、边缘化的工人以及受经济萧条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弱势社会群体。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政策”与亚洲和非洲有明显的不同。哥伦比亚、中美洲国家和墨西哥等把“社会补贴”设计成“救助基金”,同时这个计划不仅面对贫困问题,而且试图建立一条国家与贫困人口之间的管道(Duhua and Schteingart,1995)。据统计,到1992年,用于该项计划的经费已经达到政府总投资预算的17.6%,其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政府选举顺利,国家政治气氛融洽。墨西哥正试图将这项计划写进地方法规之中。总之,社会政策的创新计划对于改善地方社区的生活状况将具有长期的影响。
哈尔法尼在“东非城市贫困与城市管治”一文中提出了有关城市政府机构改革的引人注目的方法(Halfani,1995)。首先,他不是直接针对政府机构或行政组织进行讨论,而是发展了“多元化政治制度(regime of multiplicity)”的思想。就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城市贫困反常状况,哈尔法尼认为适应城市变化的趋势改组城市政府机构非常必要。城市政府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法律和规章制度赋予的地位和权力,具有收缴各种税费和规费的权力,对中央政府有很强的磁力。其次,城市的发展也受到来自一个区域物质、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非政府组织和基层社区组织事实上是“市民社会角色”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内罗比,有80多个这类组织为棚户区(informal settlement)减少贫困、提供服务和发展经济实体而工作。其它如建立辩护团、合法诊所、民事诉讼以及妇女保护网络等与国际捐赠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在政治框架内就有效地消除城市贫困开展工作。第三,非正规经济(the informal sector)也很重要。它对增加贫困阶层收入,减少贫困程度起到缓解的作用。要发展非正规经济,这涉及到住房(安居)和土地管理、小企业、城市农业、商业贸易和摊贩(vending)、服务供给水平以及流动信用控制等诸多政策的改革和配套。
拉丁美洲城市在生活方面最严重的问题是社会不平等,城市功能区发生破碎化,城市社会结构走向社会分隔。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富人区实行会员制物业管理制度,形成一个又一个小的类似西方城市中的犹太人区或少数民族居住区(ghettos),城市的破碎化加速;另一方面,据统计,大约5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棚户区的违章建筑内(Hardoy),这些地区呈水平蔓延,浪费大量土地,基本服务设施缺乏,非法用电、用水,交通和健康服务以及法律保护等基本社区服务严重短缺,洪水和火灾危机四伏,犯罪现象严重,有些已沦落为对社会无用、又无法摆脱自身贫困状况的底层社会社区。如果农村地区继续维持对劳动力需求逐渐降低的局面,向城市移民流的压力不会减轻。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大都市区不仅成为一个失控的发展区,而且也成为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地区。针对拉丁美洲国家城市的现状,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进行城市管治,概括起来,主要是:(1)通过基础设施改善营造新的公共空间。例如旨在改善交通、供水、卫生和垃圾收集等基本服务的里约热内卢的城市改善计划(Favel Barrio)和加拉加斯(Caracas)的棚户区改造计划等,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家具翻新、文化事件、住房外装修、增加旅游点和创造更安全的环境等措施提高老城区的生活质量和吸引潜力。(2)加强流动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公共交通系统方面。首先提高公共交通的质量。因为如果公共交通的质量太低,必然迫使中等收入的家庭使用家庭汽车,使利用公共交通的人数急剧下降,对增强城市流动性极为不利。其次改善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地铁等的方便连接,扩大可达性范围。
7 城市规划与管理
7.1 国家城市体系发展策略
近50年来,拉丁美洲的城市人口的自然和机械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尤其是90个主要的大、中城市或国家首都。例如,阿根廷1991年人口统计显示,国家城市体系发生较大的改变。事实上,这种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变化的主要特征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市区(RMBA)的城市首位度下降,较大的城市,尤其是南美大草原省的省会城市增长最快。研究也表明,19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各省会城市的发展并成为省内移民的目的地,使得跨省区趋向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市区的移民流开始递减(Jordi Borja,2000)。从整个拉丁美洲看,城市化还在加速,但新城市化人口的生活标准较低。拉丁美洲这一时期的中等城市成为城市体系增长的主体,主要在于它们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经济发展与人口分布的关系。由于这类城市基础薄弱,扩展太快,已经造成居住拥挤、服务和基础设施不配套等城市问题。在空间上,由于城市经济基础变化,传统产业发生危机,工业和基础设施重新布局,导致城市结构的重构,城市人口密度出现严重不平衡,中心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弱化。
7.2 城市群协调发展
在印度,由于大都市区一般都是跨政府的实体,其人口一般超过100万,由2~3次级行政区组成。在这个大都市区设立大都市规划委员会(MPC),负责编制大都市规划纲要,主要包括大都市区的空间规划、水及其它自然资源分享、基础设施协调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这个规划纲要上报中央政府,以便政府部门间的协调。
7.3 适应新经济的发展管理
经济全球化使城市围绕一些“专门区”发展,诸如技术区、商务区、世界贸易中心或电讯中心等,这些区一般都是不同时期按城市外“飞地”形式发展的,与中心城市间协调较差。此外,城市发展的新活力是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如商务、写字楼、旅游、文化包装、会展中心等。这些城市要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一般都在尽可能低的价钱“卖”或推销自己,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和商机,塑造城市的现代形象。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忘记了一个城市可能提供的最好产品是城市本身。城市的这种“飞地”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没有必要的竞争。新经济,无论它的规模如何,给了当代城市将技术、活动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机会。营造新的有效的城市功能就成为当代城市适应新经济的挑战进行城市发展管理的必然选择,它们是:基本城市服务功能、外向型高质量基础设施(尤其机场和通讯)、最优化的电讯水平、城市中心和各类中心区的可达性改善等,特别是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成为提高全球化和网络中城市竞争力的具体体现。
7.4 可持续城市的建设
拉丁美洲城市正面临一系列大气污染问题(尤其智利的圣地亚哥和墨西哥),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来自工业和生活污水对河流的污染也相当的严重。蒙得维的亚(乌拉圭首都)为了恢复城市周围环境、生态和景观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如尽可能地恢复溪流、扩展已有的公园或布局更多的生态公园、生活污水处理以及农村地区的环境与生态保护等。
7.5 降低城市不安全感和减少城市暴力
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被玷污,人们的生活质量必然下降,也很难吸引投资者和旅游者光顾。因此,针对老城市中心、商业街、开敞市场、大型购物中心制定专门的振兴计划,并精心策划文化包装,增加吸引力,从而达到降低城市不安全感和减少城市暴力的目的。城市居住区按照社会空间分隔模型布置,中心区为低收入家庭区,中高收入家庭在城市外围或郊区,棚户区或违章建筑社区实施封闭隔离政策,增加对医疗、教育和基本服务的投入,缓解因社会分割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程度。
7.6 编制城市战略规划和项目管理
拉丁美洲城市战略规划和项目管理非常流行,主要在于这类规划与管理有利于城市环境改善,能够为公共或私营部门提供发展信息,便于社会分隔的融合,以及推进市民的参与。
8 关于中国城市管治的启发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到重新组合和流动。然而,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仍然主导城市政府的管理,这不仅仅表现在市场经济氛围不浓的内地城市,而且在沿海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密集地区也是如此。中国城市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资本、劳动力、技术向少数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重复建设已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分配和福利政策滞后,社会极化和新贫困化现象已经产生;等等。尤其中国大城市的边缘区(郊区)正在快速发展,它们是城市发展的向心力量(如外来人口、外资)、离心力量(如城市工业和人口的外迁)和乡村自我发展力量汇集的地方。城市边缘区也是目前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诸如有大量外资投入,快速的变动,小而分散的地方政府、缺乏基础设施、缺乏规划、环境恶化和大量的社会问题等。
由于中国受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影响,总是习惯于分别从城市或乡村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习惯于单纯从政府加强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对城市边缘区的管理基本上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其次,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同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基础相比,中国的城市发展基于三个独特的平台:(1)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2)5000年的中国文化(集权、儒学、薄弱的公民社会)传统;和(3)长期且强有力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比如,江苏省苏南地区城市经济的市场分额已达到90%以上,但是城市管理的方式仍沿袭绝大部分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导致城市管理效率不高。
解决上述问题,传统的途径是通过频繁变更行政区的等级,达到控制城市及区域的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及流动方向,从而实现适应不同等级行政区管理权限的膨胀与制约。然而,加入WTO,中国城市的管理正面临结构性的转变,城市政府需要更多地成为协调者,调动其它组织,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共同协同工作,这就特别需要加强管治的力度。据此,以行政区权限、行政区等级变更标准为主线研究不同层次行政区间的运行机制、利益冲突、协调模式对提高中国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的管理效率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可能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管治模式找到新的切入点。
【收稿日期】 2001-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