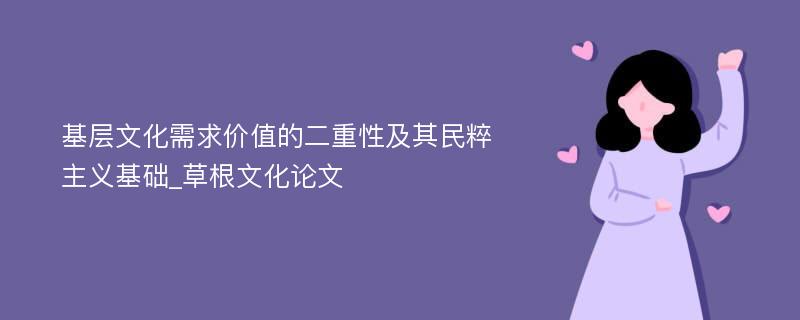
草根文化诉求的价值两面性及其民粹主义根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根基论文,草根论文,主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草根文化概念的流行及其缘起
目前在中国,“草根文化”还主要是一个都市大众娱乐领域的概念。
早在19世纪,“草根”一词随美国的淘金狂潮而流行,并在后来以其比喻义被引进了社会学领域。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因为主要借鉴、依托的是苏俄文化和文学的思想资源,所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底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间”等概念,成为相关内涵的正统术语。“草根”和“草根文化”虽然在美国作为“准学术概念”使用的历史颇为悠久,在中国却长时期内并未流行。直到近年,缘于电视和网络传播平台中种种娱乐化、互动化现象的出现,“草根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使用频率,才陡然频繁起来。
大致2005年以来,借助电视、网络等新型的传播平台,都市大众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甚至在过去不敢摆上“台面”的现象和“事件”。其中此起彼伏火爆一时的,包括“超女”、 “快男”、“选秀”;“芙蓉姐姐”、“二月丫头”;《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和《潘冬子参赛记》等“恶搞”;郭德纲相声、“梨花体诗”、博客写作;乃至“百家讲坛”,等等。这种种现象相互间的内在差异极大,但都呈现出“全民”自由参与、自主狂欢的特征。于是一时之间,网络爆红、媒体热炒、众口笑传、学界争辩,竟呈现出似乎将构成文化新格局的态势。
实际上,这些现象和事件的话语主体并非所谓的“全民”。从“超女”、“快男”、“选秀”、“恶搞”、“芙蓉姐姐”、“二月丫头”的表演主体,到郭德刚相声、“梨花体诗”乃至“百家讲坛”的接受主体,再到媒体的热炒者及其主要关注者,基本都是我们惯常所称的新型都市“小资”阶层,以及响应、迎合乃至依附这一群落的精神心理倾向的“外围群众”。他们在现在的大小城市里人数众多,却身处既定的社会文化体制外难获均等机会,同时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又富于“另类”意识和青春期叛逆倾向。这一群落核心的心理诉求,是渴望否认体制文化特权的合法性,获得文化参与的乐趣与自我表现的快感,并通过这种“快乐”的参与,进一步获取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优势状态。新科技支持自由的网络和视觉化的电视传播平台,则为他们心理企图的达成,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公共空间。相关的运作机制和传播平台为了“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为了以此为突破口寻求“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也不遗余力地上下其手,助推这些现象。不过,从具体表现来看,不管是“超女”、“快男”,还是郭德刚相声、胡戈“恶搞”,更多的其实是以一种娱乐化、脱口秀式的形态,以在传统的审美规范和社会影响形成模式中多半是“出位”姿态,来展示“真我”与“个性”,构成感觉的狂欢与情绪的宣泄,其中呈现的,主要是一种感官化、欲望化的精神生存境界。而且,这种娱乐现象的参与者本身,也多半具有浓烈的商业意识,往往在新媒体一举成名获得声誉之后,就会马上置抵抗“精英”或“主流”文化、展示自我生命灵性与神采的“成名”姿态于不顾,被商业文化“收买”和“招安”了。因此,总体看来,当前都市的种种大众娱乐现象,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不择手段追求“眼球效应”、“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道路,是社会转型、多元文化并峙的时代环境中青春期文化与商业文化合谋的产物。
从民族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这种种现象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往往由体制文化和精英文化全盘主宰的审美惯性、明星模式乃至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也包含着以种种“无厘头”的方式,敏锐、辛辣地对精英文化和社会现实的热点现象中出现的弊端进行嘲弄与亵渎、将其消解和狂欢化的功效;其中还隐含着构建同主流、精英文化相抗衡的公共话语空间的民主意识。但与此同时,它们在具体内涵方面,往往既缺乏深层次审美活动的感动因素,也缺乏主体精神沉静的磨炼、过滤、提升和坚定的理性观念的支持,所以,虽然影响巨大,实际上却基本属于较为粗疏的快感型审美层次,缺乏真正沉实的精神文化内涵。即使是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也不过是将某些学术文化界甚至并不前沿的研究成果传奇化或通俗化,本身实际上并不具备时代文化高度的创新性。而且,这种种现象在颠覆传统、恣意狂欢的张狂姿态背后,还显示出诸多的道德式微、底线伦理匮乏的话语倾向。而这些倾向与特征,是与成熟文化的精致性、深厚性与建设性,无疑是相抵触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们所构成的不过是一种“亚文化”形态的、内蕴芜杂、精神和思想含量稀薄的娱乐生态。
正因为表现形态相当火爆热闹而实际上只属于一种“亚文化”形态,它们更渴望获得一个在时代文化整体格局中能够独立自主的“名分”和“说法”,来作为在文化理论与精神心理层面的支撑。而且,早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世俗化、娱乐化文化思潮刚刚萌芽,就遭到了精英文化痛心疾首的批判。当时,这种价值立场就因缺乏相应的理论武器,而难以与精英文化的猛烈攻势和高亢姿态相抗衡,而只能以“生活无罪”的辩解和“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姿态,来勉强加以抵挡。结果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庄严与威压下,它们总显得低人一等,难以理直气壮。如今,各种类似现象更为蓬勃地兴起,具体表现往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寻求“名分”和“说法”、予以“正名”的心理诉求,就变得更加必要和紧迫了。
正是借助这样的时代文化契机,“草根”和“草根文化”的概念被重新发现和引进,“草根英雄”、“草根偶像”、“草根艺术”、“草根的狂欢”等语词,被频繁地使用和传播起来。
二、草根文化概念的价值两面性及当前大众娱乐的本相
其实,“草根”和“草根文化”只是一个比喻性的学术概念,内涵具有一定的含糊性。当前大众娱乐界对于草根文化概念的“中国式”引用,则基本上只强化和使用了这一概念的部分内涵,却忽略乃至有意遮蔽了其另一方面的特性。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草根”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使用过。所谓“草民”、“草寇”、“草台班子”等等,都只是一种日常话语。而美国“草根”一词的最初流行,则源于19世纪的淘金狂潮中山脉土壤的表层草根生长茂盛之处则下面蕴藏着黄金的传说。后来,“草根”以及关于“草根”的这一传说,被“捆绑”在一起引入了社会学领域,而获得了以“基层民众”为中心的思想内涵及其价值阐释。因此,“草根”的概念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以遍地小草平凡朴素却生生不息的生态,形象地显示出基层民众身处弱势却拥有广大的共命运者、蓬勃的生机、顽强的生命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气息;其次还以“草根”的本原性、基础性和草根茂盛则地下必有黄金的传说,显示出一种虽然身世卑微却具有存在合理性、正义天然性和前途不可限量性的价值判断,言说者由自矜、自诩而至桀骜不驯的情感心理,也自然而然地隐含其中。
“草根”一词积淀的这种概念内涵和价值倾向,恰好有效地满足了当前中国都市娱乐文化确立文化话语权的学术图谋,而且能够成为他们一种亚文化生质的情感表达。整个社会普遍谋求和谐、公平的时代语境和学术界底层、民间乃至“人民性”理论的思想累积,也为这样一种文化内涵的概念摆上“台面”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这样,诸多的都市大众娱乐现象以“草根”、“草根文化”及其正面含义为标识和旗帜,也就是顺理成章而且势所必然的事情了。
但我们如果从学术角度、以客体实际容纳的全部内涵为对象进行考察,则可以发现,所谓的草根和草根文化实际上还存在着被人们所忽略的另一方面的特征。
我们不妨首先对草根的概念略加文化语义学的分析。从这一角度看,草根的本原性、生命力固然值得称道,但这本身其实并不能保证它成长的茁壮性;草根下面埋藏着黄金的传说,也不等于说它本身就是黄金;对所谓“自由自在的生机”也要区别而论,自由自在地藏垢纳污同样是一种自由自在。这就说明,草根的概念其实并不具有正面价值的必然性。再从文化整体格局的角度看,大众文化确实可能潜藏着发展成为时代文化高峰的因素与契机。在中国文学史上,从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词、曲等文学体裁,到“三国”、“水浒”、“西游”等具体作品,都起源于民间。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本身又往往是一种瑕瑜互见的、粗糙原始的文化形态,真正成为一个时代文化精华登上大雅之堂的,多半是以之为基础,经精英文化浸润、修正、提炼和升华的产物。从诗词最高成就的代表性作品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最终集大成文本,无不如此。即使是往往被当作民歌、民间文艺代表的《诗经》、“汉乐府”等,即使排除采诗官修正润色的可能,因为当时的王朝或者诸侯国宫廷之外皆称“民间”,所以从常理推断,它们实际上也许是过于广大的“社会公共空间”中的“著名作家”、精英分子的创造,而非真正基层、“草根”民众的“手笔”。就像《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乃至新世纪文坛的《檀香刑》等作品使用了民间文艺的形式,当将来也许作者不可考时,如果有人真以为它们是基层人物、“草根英雄”的产物,那除了想当然就是被学界为表述方便创造的说法所蒙蔽导致的“误读”。因此,以为只要占有“草根”、“民间”的身份就具有文化价值的天然优越性,其实是一种误解。大众文化的大量产物,都往往因为内容的单薄、浑浊,形式的稚拙、粗疏,只能处于自娱自乐、自生自灭的境地,只略具对于真正的文化创造的借鉴价值,本身在整个时代的文化格局中不可能拥有重大和长久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对于草根文化,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把量的扩张、庞大天然地转换成质的纯熟和完美。当前大众娱乐领域的诸多现象,即使显示的是草根文化的正值和优质,也应作如是观。更何况因为商业诉求和整个社会文化品质的滑坡,当今的种种娱乐现象中实际上包含着大量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诟病的弊端,诸如电视“选秀”节目的雷同低俗,芙蓉姐姐的卖弄风情,“梨花体诗”的浅薄,“恶搞”的张狂,等等,其中包含着太多属于“泡沫”和“垃圾”的成分。当前大众娱乐的现实所体现的草根文化的负面品质,绝不可能因为多了个“根”的标榜就能“正名”,从而理直气壮地跻身时代文化精华的行列,和高雅文化分庭抗礼了。
当前的学术界对于大众娱乐现实的两种不同态度均存在着值得引起重视的局限。草根文化的推崇者们往往空泛地强化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却忽略了草根文化必然存在的负面特质,忽略了其合理性背后同时包含的肤浅与粗疏,以至在具体操作层面掩盖乃至纵容着大众娱乐现实潜藏的文化病灶,甚至标榜的是其正值、优质,实际上真正展开的却是其负面的价值内涵。批评者则往往就事论事,着重关注其严肃精神内涵和纯正审美品质的匮乏,以及对于精英传统利益和主流价值规范的冲击与损害,却未能从草根文化本质的高度,来透视其两面性和当前负面特性泛滥的现实,所以批评起来总显得缺乏透彻性、前瞻性,缺乏釜底抽薪的功效。两种学术立场和姿态及其相互间已经较长时间的僵持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种理论建构的单薄、自闭、专横与盲目的自大,具有巨大的学术文化危害性。
国外诸多的文化理念传播到中国,往往都会产生一种蜕化变质的现象,即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当前大众娱乐领域的草根文化现象也是如此。所以,深刻地辨析中国式的草根文化理念的价值两面性及其现实本相,对其宽容但不盲目地认同,更不缺乏分析地、无条件地推崇,才是真正具有学理深度与历史眼光的价值立场。
三、草根文化诉求隐含的民粹主义倾向
更深一层从思想文化史的高度看,大众娱乐现象的草根文化诉求中,还显示出一种民粹主义的思想价值倾向。
民粹主义其实也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态,是源于人类现代化过程中发达与落后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其矛盾和问题所形成的一种回应。从社会思潮角度看,民粹主义一方面强调民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肯定民众的首创精神,把民众的愿望、需要、情绪当作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从重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角度看,当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忽视乃至抹杀精英人物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作用,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而且常常通过对大众的普遍动员,而对全部群众实施高度集中的操纵和控制。所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更基本的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和极端民主主义立场,即极端地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合法性的最终和唯一的来源,对普通大众在特定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性的共识也盲目顺从,并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
文化民粹主义的根本特征,则是无保留地视普通百姓为积极的快乐追求者,全盘信任他们的判断的合理性。即使百姓对邪异的个体与个性、性、丑闻、暴力、运动和娱乐等方面的兴趣,甚至其中表现的是人性的低俗品质、负面特质与卑污内涵,如果以一种生动的、有特性的语言和形式表现出来,也往往被文化民粹主义用一种理解与重视日常的意义、理解与重视普通百姓的趣味与快乐的姿态,来加以解释并使之合理化。其中隐含着这样一种理论假设,即如果某种东西是流行的,那么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必定是健全的。而且,它往往源于对精英和主流文化传统和现实某些方面的失望,而以一种对立的姿态,不加分析地指斥一切精英文化的平庸、苍白与虚伪、委琐,并试图从根本上孤立精英文化,否定文化精英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有意遮蔽、淹没在底层和为底层而工作的精英的努力。一种狭隘、极端、盲目乃至非理性选择的精神特征,就由此显现出来。
所以总体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往往具有两面性,对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来说,它也许是福音,但也很可能是一种祸害。
民粹主义的危险面主要产生于社会转型期。因为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的基本现实,以及随处可见的掠夺、腐败、僵化、蜕变等等特殊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欲望泛滥、道德失范、心理失重等等精神弊病,往往也会寻求文化的选择和表达。当前中国式的草根文化话语诉求,就正是都市多元文化并置、“小资”阶层寻求文化出路与理论话语权的产物,是一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民粹主义。文化民粹主义的诸多内涵,甚至其诸多的负面特征,在中国式的草根文化现实中,都已相当充分地表露出来。关于这一问题前面已有所述,此处不再赘言。其实,草根文化的民粹主义倾向其来有自,自我标榜“草根美国”的美国草根文化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罗斯·佩罗(Ross Berot),就号称为代表“众多百万富翁的民粹主义者”。所以,源于这种理念形成的中国式草根文化成为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实际上毫不奇怪。
与传统民粹主义相比,这种现代都市民粹主义的不同之处表现在,往往着意强调现时代的诸如电脑等高科技、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快速通讯手段、普及的高等教育、文化同质等后现代语境的技术和文化条件的新特征、独特性,从而在经济和技术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会对公众显示出一种迷惑与蛊惑性。但恰恰因为技术条件所造成的公共交流平台的畅通和公共意见传达的自由,使这种文化民粹主义制造自我的“高峰”处于唾手可得的状态,结果制造出来的“草根英雄”、“草根偶像”,往往只是招摇过市却转瞬即光彩黯淡的文化明星,只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和整体意志的代言人,本身很难说拥有真正高品位的审美素质和深层次的精神境界;它的产品也多半是大众世俗性趣味和欲望的表征,很难说具有真正的艺术分量和精神水准。而且,文化民粹主义的操纵者还往往会以商业、经济利益为显在和隐含的目的,采用各种策略来对民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而都市民粹主义被别有用心的商业文化利用,由某些商业寡头借以操纵大众,成为其商业利益专制独裁的手段,也是常见之事。当前中国的信息传播平台由内容选择的快乐、欲望化,逐步走向各种保健、丰胸、美容、整形乃至性暗示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的发展趋势,就是其中典型的例证。所以,现代都市的文化民粹主义貌似时尚、激进,实质上隐含的往往是低俗与势利,长此以往,必然有损于国家形象的高尚美好和民族文化的健康纯正,对于基层民众自身长远的文化利益与文化发展,同样有害无益。这正是当前的草根文化发展值得严重关注乃至警惕的根本点之所在。
虽然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于大众娱乐文化需求的满足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意识与草根情怀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但在确立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发展方向时,我们必须切实地把握各种文化现象的精神实质,在承认其生长的同时,也高度警惕其价值的两面性,并随时注意有效地阻止其两面性之间的蜕变,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时代文化的健全发展与民族精神素质的提升。对于当前的大众娱乐现象及其草根文化诉求,我们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立场与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