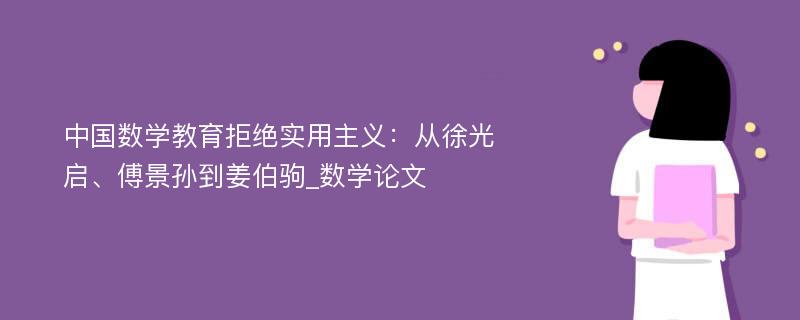
中国数学教育拒绝实用主义——从徐光启、傅种孙到姜伯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数学论文,傅种孙到姜伯驹论文,徐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辛亥革命以来的100年,乃是中国追赶西方文明的100年.数学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先学日本,辗转引进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继之崇尚欧美,包括美国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曾全面学习苏联(一个数学超级大国)的经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更是全方位地引进欧美数学教育理念.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既具有悠久的数学教育文化积淀,又能全方位地从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的国外数学教育里吸取营养.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中国数学教育博采众长,择善而从,逐渐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尤其在对待“几何学论证演绎体系”的态度上,形成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可以说,从明末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到民国时期数学教育界的代表人物傅种孙,乃至21世纪初对课程改革提出质疑与批评的姜伯驹,在几何学教学的认识上是一脉相承的.20世纪以来中国数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和抵制了杜威的数学教育的主张,和这一传统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中国的学校数学课程并非基于中国古代数学,而是重起炉灶全盘从西方引进的.对于西方的数学理性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是全盘接受,从未加以抵制. 开启这一传统的是徐光启.他在《几何原本序》中谈了自己对古希腊理性精神的感悟:“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他还说:“(此书)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1]对于一种由域外传入的学科,17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能有这样深刻的评论,难能可贵.这种理念流传后世,融入了中华文化,以至成为中国数学教育的一块基石. 清代中期以来,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进一步和西方传入的数学联姻.事实上,戴震、阮元等自己就是算学家.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重实证,讲究逻辑推理,因而贴近数学.中国学术界崇尚“严谨治学”的文化氛围,恰与西方数学要求严密逻辑推理的理念相吻合.著名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在《中国数学史》中评论说: “到乾隆中叶,经学家提出了汉学这个名目和宋学对抗,他们用分析、归纳的逻辑方法研究十三经中不容易解释的问题,后来,又将他们的考证方法用到史部和子部书籍研究中去.研究经书和史书都要掌握些数学知识,所以古典数学为乾嘉学派所重视.”[2] 明末清初的中国学者,同样重视西方数学和数学教育.留日归来的王国维,于1901年5月在上海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并亲自翻译立花铣三郎著的《教育学》[3]和藤泽利喜太郎著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①.这表明清末中国文化学者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以上笔者约略地叙述了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数学的认识.此后,现代中国的数学教育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并与后来传入的杜威教育学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1919年,杜威来中国访问,足迹遍及14个省市.杜威的哲学和教育主张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潮流相一致,因而受到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普遍欢迎.早在1919年秋天,由数学教育家俞子夷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实验开始试行设计教学法,此后,中国学者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实践杜威的教育理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实验学校更直接被命名为“杜威学校”,影响之大,超乎寻常.[4] 杜威的学生——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H.Kilpat-rick)提出“设计教学法”,帕克赫斯特(H.H.Parkhurst)倡导“道尔顿制”,华虚朋(C.W.Washburne)则有“文纳特卡制”等具体的教学模式.帕克赫斯特、克伯屈、华虚朋本人还先后于1925年7月、1927年3月和1931年2月访问中国,宣传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方法.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法案”,推动了设计教学法在中国教育界尤其是在小学教育界的传播和实验.杜威的一些学生还先后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开办了一些实验学校.杜威对这些实验学校也很感兴趣.[5]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实验,在小学阶段得到一定的成效.俞子夷的著作《新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在理论上受杜威、桑代克、克伯屈以及赫尔巴特和陶行知的影响,但是,在中学阶段,尤其是几何教学方面,杜威及其学生的学说则遭受冷遇.事实上,中国教育家对杜威教育思想也并非全盘接收.中学的教学实验曾经坚定地抵制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做法. 我国教育家廖世承,对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道尔顿制进行了实验研究.他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的消极作用加以揭示.廖世承据此实验写成的《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一书,最后的结论是: 优点方面,道尔顿制较能适应学生个性;教员可以因此经常与学生接触;劣等学生可多得指导的机会;大多数学生因之而增加自动的能力.缺点是费时;不经济;练习簿先后交免不了抄袭;懒惰者不易督促.困难在于因学生学程前后参差不齐,有时牵动太多,不免增加教师与办事人员的困难;教师特别费力、费时.在对实验班和比较班两组学生成绩的看法上,大多数教师认为差别不大.最后,实验结果表明,道尔顿制和通常采用的班级授课制的实际效果不相上下.道尔顿制的特色“在自由与合作”,但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很难实行,“班级教学虽然有缺点,但也有它的特色”.[6] 这一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也成为我国教育实验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报告显示了杜威的进步教育理论虽然在重视儿童的学习主体,提倡贴近社会生活的学习活动方面,应有可取之处,但是在教学层面并不成功.1926年以后,中国的道尔顿制实验热潮急速衰退,名噪一时的道尔顿实验,连带设计教学法从此偃旗息鼓.[7] 1920年至1930年间的中国数学教育界,坚持自徐光启以来的传统,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划清界限.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全盘排斥充满理性精神的古希腊数学.杜威和他的学生们只认可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费数学”,明确否认学习“几何学”“代数学”的必要性. 克伯屈(W.H.Kilpatrick)原是一位数学教师,后来投入杜威门下.他在20世纪20年代曾有两段十分雷人的话:“就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类型而言,数学害大于利.现有中学的代数学和几何学的学习不应继续下去.”“我们过去教的代数和几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克伯屈在中国演讲中甚至明确地说:“有许多科目,例如代数、几何、论理学学科,若不是为了升学起见,完全无用.宜选用适合中国国情的课程.”[8] 这种排斥几何学的观点,与徐光启当年的认识南辕北辙,自然受到中国数学教育界的抵制. 傅种孙先生(1898—1962)是民国时期中国数学教育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位数学家,1922年翻译出版了罗素的《罗素算理哲学》(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接着,又在1924年翻译出版了形式主义数学哲学创始人D.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1862—1943)的名著《几何原理》(今译《几何基础》).1929年,他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本书他都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足资楷模的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著的《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该书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四版.采用该书的教师都说用起来有事半功倍之效.20世纪20年代初,傅种孙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兼课.钱学森回忆说:“听傅(种孙)老师讲几何课,使我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严谨科学.”[9]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对数学教育的歧视,也受到我国著名数学家陈建功的批评与调侃.陈建功先生亲自编写过许多中学数学教材.他在著名的论文《二十世纪的数学教育》中这样评论美国的数学教育: 哥仑比亚大学教育学教授司内屯竟这样说:“‘消费者的数学’——算术的一部分——自然人人所必需不可以省略,但是中学校的代数和几何,未必人人所必需,不必作为正科,应改为随意科(选修课).至于数学的陶冶价值,几乎无穷小”……我们于此可以断言:美国数学教育的特色,是在培养“小市民性”.美国的数学教科书,是富于小市民的实用性和学习心理的色彩.所以美国没有一本数学教科书是数学专门的人写的,著者大多是教育工作者或是心理学者.[10] 仔细寻味我们可知,这些把数学仅仅用于消费性商业、为小市民服务的错误主张,正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念所派生出来的.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位司内屯教授认为数学的陶冶价值(指以理性精神陶冶培育学生)是“无穷小”,但那正是徐光启、傅种孙和陈建功等广大中国数学教育工作者所要坚持的.二者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 杜威本人有一段话直接谈到数学教学,他写道: “在学校里,学生思维训练失败的最大原因,也许在于不能保证像在校外实际生活那样,有可以引起思维的经验的情境.一个教师看到学生做小数乘法时,计算程序是对的,但结果却错了.例如一个学生的答数是320.16元,另一个说是32.016元,第三个学生说是3.2016元.这表明,学生虽然会计算,但并没有思考.因为他们思考一下,就不会对数目的理解相差这么大.于是,教师派学生到一家木材行去买学校手工场所需的木材,预先和商人约好让他们计算货价.数字的运算和教科书里的相同,但小数点全都没有弄错.这是因为情景本身引起学生的思考,限定了他对木材价值数目的理解.因此,教科书的习题需要一个情景.”[11] 杜威的这番论述,所涉及的数学是“小数”,属于消费数学范围.即便是这样切合日常生活的数学,也非要“从做中学”,把“数学完全寓于生活之中”,这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典型体现.按照杜威的说法,有了买木材的情景就可以让学生不出错,但是这能否保证学生在其他场合也不出错呢?情境创设不是万能的.抽象的数字计算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程序化的操作.学生由于没有掌握抽象的“小数运算的算法法则”,才会把小数点的位置弄错.对于重算法的中国数学教育工作者来说,杜威的教育学说是无法接受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数学教育经历过许多曲折.第一次折腾是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面提出的口号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然是“革命”,就要全盘否定此前的教育体系.于是,把学校办到工厂、农村中去,以劳动代替学习.“破除师道尊严”,鼓励由学生编教材.否定知识的系统性,主张从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中进行教学.这时的数学教育,出现了“公社数学”“车间数学”等名目.学生在生产劳动中学习数学,几何证明等理性思维内容全部废弃.到了1959年,学校的教学秩序遭到全面破坏,学生的学习成绩全面下降,不得不停止“实验”,恢复基本的教学秩序.时隔数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重复1958年“教育革命”的错误,而且变本加厉,破坏得更加厉害.几番折腾,几多教训.所谓“教育革命”,表面上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旗号,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和杜威的教育主张十分相像:破除师道尊严,以学生为中心;否定知识传授,以参加生产劳动的“活动”为中心;批判书本知识的系统性,走出校门以社会活动为中心.这不正是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教育图景吗? 时序进入21世纪,一场新的教育改革拉开了帷幕.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率先公布,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先声.数学教育的“中国道路”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次数学课程改革突出的成就之一是课程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年呼吁未果的概率统计进入教材,新标准将它作为和代数、几何并列的学习领域推出;方程思想、坐标方法以直观的形式渗入小学内容;初中阶段加强了函数概念的教学;算法进入高中数学,曾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学以后又被扫地出门的微积分和向量,重归高中数学课堂.这些改变,适应了信息时代的数学需求,也是许多数学教育工作者多年来追求的成果,其成就将会载入史册. 但是,这次改革对几何学的处理却引起了激烈的论争.2005年,姜伯驹等几位数学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对此进行质询.姜伯驹认为: “新课标”全面否定了我国中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大大淡化了数学中的推理证明,代之以“贴近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使生活和数学融为一体”.甚至连“平面几何”这个词都不见了,只许说“空间与图形”;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这样的基本定理也不要求讲证明,有的教材就代之以所谓说理,让学生用剪刀将三个角进行拼接实验.不鼓励学生问为什么,不讲证明,数学课就失去了灵魂. 其实,数学上很多概念并不是完全可以实验出来的.比如“三角形内角相加是180度”,你真用尺子去量,可能会有误差,也许就得不到这个180度.现在这些概念都不讲了,只让学生认识一个具体的角,这还是数学吗? 平面几何中很多概念看似很简单,但是不把它讲清楚不行.一是要让学生认识图形,另一个是让学生从简单入手,逐步深入,学会怎样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最简单的东西,往往也是最本质、最基本的东西,通过对简单的把握,建立思维体系,通过推理,得出的结果往往是惊人的.这就是数学思维,是科学精神,是我们要着力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很多人说:“平面几何是对人生很重要的一课.”对这一点,科技界是有共识的.[12] 这一段论述,与徐光启当年对《几何原本》的赞赏,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和钱学森听傅种孙讲授平面几何课的严谨性,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也不妨认为,这是在新时期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否定“形式陶冶”论调的批判.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课程改革,不仅是内容的变更,更突出的是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变化.这次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注重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 但是,为了实现“触及问题的改革才是真改革”的预想,此次改革没有采取“继承优良传统、扬弃旧有积弊”的方针,而是把此前的教育传统定位为“教师中心”、“学科中心”、“知识本位”、“目中无人”和“机械记忆”等等,进行全面的否定和批判.从教育史的角度看,这是向赫尔巴特技术主义教育理论开战,向杜威进步主义学说靠拢. 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刚一公布,就引发了激烈争论.在中国数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召开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工作者的座谈会上,发言者对这份文件的许多方面进行批评,除了对大幅度削减平面几何内容表示强烈的异议之外,更对新课程标准中否定中国数学教育界许多行之有效的共识表示质疑.例如,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的“数学双基教学”、“教师主导作用”、“启发式教学”和“数学三大能力”等等全部被删除.这样一来,学生中心、活动中心的影子隐约可见. 教育部随后组织了以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为首的修订小组,对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进行修订,修订持续了八年之久,到2011年底才公布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保留了本次课程改革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各方面的批评意见,纠正了一些“矫枉过正”的提法,恢复并发展了一些优秀的传统.例如,重提“教师主导作用”“启发式教学”等,将“双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发展为“四基”(增加基本数学活动经验和数学思想方法).这一修订,完成了一个新阶段的提升. 杜威教育思想虽然对于革除教师注入式讲授的教育弊端,关注学生主动学习,建立课堂中师生的民主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其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忽视知识的系统性,否定数学提升学生思维品质的重大价值,无法成为中国数学教育的指导思想.晚近以来,有些学者认为,杜威的教育思想是21世纪以来的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历史证明,就数学教育而言,这是做不到的. ①连载于1901—1902年的《教育世界》杂志.标签:数学论文; 数学教育论文; 徐光启论文; 杜威论文; 数学中国论文; 数学文化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姜伯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