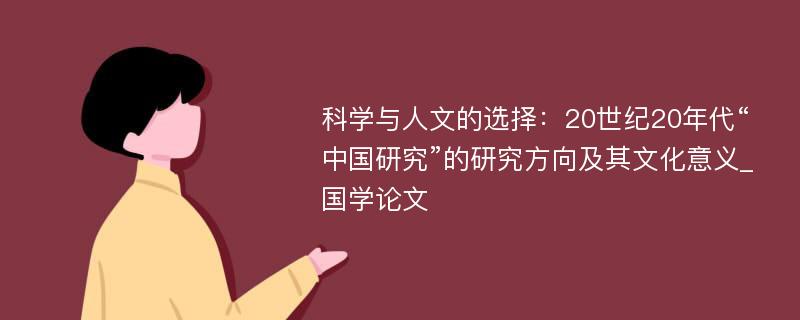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抉择——1920年代的“国学”研究取向及其文化意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国学论文,人文论文,意味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9-0112-06 “国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但“国学”这一命名出现于晚清时代,确实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作为具有现代意味的“民族学术”,“国学”与晚清以前的“旧学”“古学”“儒学”“经学”“君学”,以及“汉学/宋学(理学)”等传统所固有的学术称谓相较,其内涵外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一种较为宽泛的纵向历史维度看,“国学”研究实际上曾历经过章(太炎)刘(师培)“国粹”(20世纪初期)、北京大学“国学门”及清华研究院(1920年代)、无锡“国专”(1930年代)及海外“新儒家”(1990年代至今)这样四个主要的演化阶段,而在不同的阶段,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位是有其潜在的差别的。当然,如果没有不同阶段的那些前辈学人的持续探讨,被我们视为“民族学术”的“国学”事实上也是无法真正被确立起来的。 一、1920年代的“国学”研究境遇 “国学”一语自章太炎和刘师培首倡,经由黄节、邓实等人所主持的《国粹学报》的张大,最终才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但早期那些力倡“国学”的学人们,对于“国学”这一范畴的定位其实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也是造成后世出现多重向度纷争的核心原因之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学”初萌时期的多向度探索也为后世学人的深化与拓展埋下了宝贵的种子。比如,早期“国学”中“民族”意识的获得虽然主要是针对满清而来,但这种“族群(自我)认同意识”的建立,却为后世“东/西”学术思想的分界(或者说与西方的“Sinology”的自觉对应)奠定了基础;此外,早期“国学”研究中对于先秦“诸子学”的复活及对佛学的引入,既打破了儒家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为后世在接纳西式学术体制的基础上建构现代形态的学科规范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国粹”时期的“国学”虽然视一切中国古典的思想传统为“粹”,但与科举时代日趋狭隘的“君学”“经学”及“理学”相比,在思想导向与学术界域等方面已经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了。 “国学”真正得以确立当归功于蔡元培、胡适等人对于“西学”的借镜。1923年,由胡适等人发起了“整理国故”运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并有《国学季刊》创刊,国学研究开始以科学的名义转向对于中国既有国故的全面整理。其整理研究的利器则是胡适所强调的以“科学”为前提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事实上,在北大“国学门”成立之前,以“国学”之名组织起来的各式讲堂学馆都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数量,除了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的国学讲习会(1906)以外,其他比较知名的还有章门弟子马裕藻发起的杭州国学会(1911)、廖平和宋育仁等主持的成都国学馆(1912)、陈尔锡与吕学沅等组织的国学扶危社(1914)、倪羲抱等人的国学昌明社(1915)、唐文治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以及南社同人的国学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当然,从总体上看,这类名目繁多的“国学”研究大都并没有突破以“小学”(朴学)为方法、以“经学”为根基、间以诸子学为辅助的传统学术的一般架构;偶有对西学持开明态度者,其对西式的治学精神也多半不甚了然。也许正是因为这类研究仍带有明显的旧学痕迹,而新一代的学人又正急切地希望彻底摆脱旧学的暮气,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由胡适、顾颉刚等人所倡导的以“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的运动甫一出现即应者云集,一时之间成为中国学界的翘楚。 循北大之例,东南大学国学院(1923)、清华国学研究院(1925)、厦门大学国学院(1925)及中山大学历史与语言研究所(1928)等也相继成立。与清季民初的各式讲堂学馆有所不同,诞生于1920年代的这些国学研究院所已经彻底摆脱了旧式“学塾”的知识传承形态,而初步具有了类似于法国的法兰西学院或英国皇家学会等学院式特征的现代学术专门研究机构的雏形。①而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处身这类研究机构的学人多数都有留学外洋的背景,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西式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广泛认可与接纳才真正突破了章、刘时代的“旧学”印记,进而使得“现代民族学术”的最终确立成为了可能。 如果对1920年代出现的各个研究院所细加辨析的话,就不难发现,新式的研究机构虽然都是在现代大学建制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但它们各自的研究取向却不尽相同。后继的厦大及中山大学的研究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北大“整理国故”路向的分流(其人员和机构设置大多出自北大),而由东南大学的吴宓转职主持的清华研究院所呈现出来的研究风格又与北大一支迥异。倘若加上这个时期由章、刘等清季学人所传承下来的“国学”一派的话,则1920年代的“国学”实际上已成鼎足三立的局面。冯友兰先生曾将晚清民初的学术大体分为“信古、疑古及释古”三种主要的趋势,他认为:“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即要消灭;……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②冯先生对于三个渐次推进阶段的划分虽曾引来过各种争议,但就1920年代中国学界整体的学术格局来看,此一划分还是有其道理的。王瑶先生也曾分析说:“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做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王瑶先生甚至以此希望确立一个有独立风格的“清华学派”。③ 具体而言,北大一路的“整理国故”与清华以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等为主的研究取向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以“疑古”和“释古”论,“疑古”重在“辨伪存真”,所以对科学的精神及实证的方法有特别的强调;“释古”并未放弃或否定考证的重要,但其目的却是在“证实/证伪”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资源予以全新的解释,以使传统本身能够得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清华的《研究院章程》已明确指出:“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始终;在国民,则与一国相始终;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始终。”所以,在面对中西学术既有资源之时,“学者必致其曲,复观其通,然后足当指导社会昌明文化之任。”④负责主持清华国学院具体工作的吴宓,在1925年学院开学之日的演讲中则进一步解释说:“(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惟兹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⑤吴宓对“国学”的这种兼顾中西而又着眼当下的定位,其实正是他在《学衡》时期思想的延续。相比于“疑古”一路严谨的科学取向,“释古”的目的在选择上其实显示出了明显的人文色彩。以《红楼梦》研究为例,王国维从中悟出了人生的“哲理”,吴宓看到了汉语的优雅与古典艺术的精妙,胡适则对曹雪芹的生平史迹更感兴趣。“科学”在求客观,其目标是确定最终的可靠“原则”(即“规范/法”);“人文”在求践行(知行相合),化传统资源为今日之鉴用。比之“古史辨”派的“古史层累说”,梁启超的“进化史学”与“抒情传统”、王国维的“悲剧论”与“境界说”、陈寅恪的“不古不今”之论及“了解之同情”说等,确实显示出了更多的人生气息。 二、“国学”:在知识与人生之间 当然,并不是说,“疑古”与“释古”所标志的就是截然两分的“科学”与“人文”两种路向,而只是说,在两者的选择上,其各自应该是有所侧重的。实际上,“科学”与“人文”一直是西方世界推进其自身文化的两个核心支点,只不过从18世纪以后,特别是在20世纪,“科学”的一翼日渐占据了主流,以宗教、道德等为内质的“人文”取向终至隐退了而已。余英时先生曾分析认为:“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个别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这显然是因为自然科学如物理所创获的知识不但具有普遍性、准确性、稳定性,而且它的方法也十分严格。人文研究见贤思齐是很自然的,尽管这一效颦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失败远多于成功,但整体来看,20世纪的人文研究一直在科学典范的引诱之下游移徘徊,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⑥科学所追求的是一种可靠的纯粹知识,因为只有足可实证的知识才能彻底打破现代人对于传统的种种迷信,也因此才有可能在“重估一切价值”的基础上,“再造”全新的“文明”。有着这种思路作为先导,胡适等人才特别选择了“赛先生”“德先生”和“费小姐”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号。而这其中,真正的核心支撑其实是“赛先生”,因为只有它才是合逻辑地推衍出“德先生”(以民主求法制)和“费小姐”(依法理求人权)等一系列现代观念的前提。1920年代前期的“文言白话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及“科玄论战”等,几乎无一不隐藏着“赛先生”的影子。 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需要引起注意,那就是胡适和吴宓等人的留美背景,因为这是形成后来北大和清华各自不同的学术理路的关键思想资源。 胡适于1910年留美,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实用主义,1917年归国。吴宓于1917年入弗吉尼亚大学,次年转入哈佛,追随白璧德,开始遵奉新人文主义,1921年归国就职于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次年与梅光迪、柳诒徵等一起创办了《学衡》杂志,1925年入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学衡》一派的梅光迪留美(1911)及转入哈佛大学(1915)都比吴宓要早,其研习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最为深切,陈寅恪和汤用彤入哈佛则稍晚(分别为1918年和1919年)。详细清理这段过程,主要是为了说明,在20世纪之初的1910年代,中国刚刚经历过了摧毁王朝体制以重建现代民主的共和体制的关节点上;而此一时期的美国,也正处于需要彻底地摆脱原有的“欧式”阴影以建立全新的美国精神与美国文化的当口上——是沿袭和继承欧洲的文化传统还是反叛欧洲以建构新的思想文化模式,已经成为了在日益膨胀的经济自信刺激下勇于探索的美国人所普遍面临的问题。此种境遇之下,“固守”和“重建”就成了某种无可回避的必然选择。 胡适留美之际,正值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依照詹姆斯的说法,“实用主义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个哲学方法。作为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假设宇宙是不连续演化的,人只是其中若干成分的一种。作为一种方法,实用主义是归纳的、科学的、非绝对主义的,它的基本原则是:把某个观念放到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中,观察其效果,最终验证这个观念的真伪。任何观念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被视为是‘真’的。此外,随着将来科学发现的增多,我们还应该有所准备,在必要时修改整个思想结构。对实用主义来说,人们的信仰实际上是行动的准则,这些信仰必须由它们的实际效果来检验,这个原则是实用主义理论的关键。”⑦作为詹姆斯思想的忠实继承者,杜威借助其对实用主义更加“工具化”的阐发和推广,把曾经被欧洲人奉为圣典的形而上学从几乎高不可及的玄学象牙塔中拉了出来,实用主义自此使哲学从先验领域退回到经验的世界,变成了可用于解决人类社会实际问题的工具。转过来看,吴宓和梅光迪等人留学美国的时候,并非对风靡一时的实用主义一无所知。而他们之所以初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即心生向往,除了有个性气质及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从白璧德的思想中看到了某种在不摧毁和不彻底否定传统的基础上使“传统”与“当下”对接的希望和可能:因为白璧德虽继承的是欧洲的人文传统,却并没有拘泥于其间,而是在针对以卢梭式的自然倾向上的人道主义及以培根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化的人道主义展开批判的基础上生发出了一种新的人文主义思想。“在白璧德看来,卢梭的浪漫主义理想实际上是在无限制地放任人的个体欲望,其对于普遍原则的否定最终将导致享乐主义的极度张扬与人类道德的彻底堕落,而培根所强调的借助科学与知识来获得人类幸福的所谓‘进步’途径,同样会因为其对物性法则(Law of thing)的刻意追求而完全丧失人的法则(Law of man)所规定的人类幸福的实质性精神内涵。正是在完全忽视‘人的法则’的培根主义者,以及将法则与自身性情相互混淆的卢梭主义者的支配下,人类的‘自由’才变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观念的空壳。白璧德在此无疑清楚地点明了现代人真正所处的‘异化’境况——既可能因为无限的放纵而成为‘自然人’式的‘非人’,也可能因为迷信‘科学’而成为‘物化’的‘非人’。”⑧比较而言,白璧德的思考比杜威要深刻得多。不过,既然以实证为前提的科学可以帮助人们重建更为合理的社会,对于习惯在所有事情上都希望有所尝试的进取好胜的美国人来说,实用主义当然要比新人文主义显得切近而实在。特别是在自由经济面临周期性转换的时节,人们更愿意相信实用主义也许是一剂有效的良方。如王晴佳所分析的那样:“1929年经济大衰退,使得人们对于新人文主义的精英主义态度,不再有什么兴趣了。他们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学说和理论,而新人文主义则过于阳春白雪、过于理想主义了。与之相对,杜威的乐观主义、科学主义则显得更为切合实际。因此,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社会和学界的影响,也由于那时的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而受损。”⑨“柏拉图曾构想了一个哲学家统治的共和国;而杜威则构想了一个在教育的帮助下,人人都成为哲学家的共和国。或许他们都过于乐观地认为哲学家不仅有理性,讲道德,而且还富于社会责任感。”⑩这也许正是胡适的理想所在,但在吴宓等人看来,胡适恰恰正在把已经出现在美国的文化危机几乎完整地搬到了中国。 有了这样一重思想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曾经上演过的杜威与白璧德之间的较量,到了中国本土,又会在新文化运动一派与《学衡》派之间重现一回了。《学衡》同人绝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保守”,甚至与其指为“保守”,毋宁说他们其实是过于“超前”了。白璧德在巴黎访学期间经由法国汉学家们的译介,曾有限地接触过《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及东方的佛学思想,白氏也确实明确地表示过对于孔、孟思想的心仪,但这些都绝非吴宓等人借祖宗文化聊以自傲因而倾心白璧德的真正原因。白璧德提倡古今文化在传承上的延续性,却并不刻意执守古典文化的优越性;同时,白璧德倡导新人文主义也主要是针对以技术化的“科学”训练来规范美国教育体制终将导致人的思维的机械化倾向而来的。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在“科学”意识已经畅行无阻的今天,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真正的问题之所在。事实上,在白璧德之前,英国的安诺德即曾激烈抨击过现代文明对于传统文化及道德伦理的肆意破坏和摧毁。毋庸置疑,现代文明比之传统,确实是一种进步,但完全割裂其与传统的有机联系,恐怕也并非最佳的选择。儒家文化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确实被强化成了为专制统治提供意识形态合法依据的工具,它也因此被确定为“君学”“经学”或“理学”;但根植于儒家文化深层的以“内省”为核心的“人文”(道德自觉)意识却并没有断绝。“国学”的倡导不是在恢复其意识形态意味,而恰恰是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尝试回归传统文化中真正的人文蕴涵,更不用说其对诸子学及佛学等思想的接纳所透露出来的自由思想及人生境界意味了。就此而言,《学衡》之所谓“昌明国粹”,绝无指一切传统为“粹”的意思,而正是在希望发掘出传统中属于“粹”的部分,使之在融化新知的基础上重新发挥其道德制衡的有效功能。这也许才是《学衡》一派的真正的意图,吴宓无疑是希望将这一意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付诸实践。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以四大导师为主的清华国学研究确实更富有道德坚守的内省式的人文色彩,这与北大“整理国故”一路的“科学”基调也确有明显差异。在1928年北大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整合学术资源之时,傅斯年虽曾刻意强调“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1)而由“《学衡》/清华/中研院”一路沿袭下来的对于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坚守也始终未曾中断,陈寅恪及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刘述先、余英时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代代学人在不同向度上的深切思考即是最好的明证。 1920年代由北大和清华所代表的“国学”研究,基本奠定了后世“科学”与“人文”的路向选择及其形成协同并进的学术格局的可能。但遗憾的是,出于五四以来激烈颠覆传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倾向等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一曾经的分歧似乎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而在今天却又重新成为了我们建构现代中国学术所必须面对的鸿沟。 三、“会通”:“执两用中”与文化汇流 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学术,余英时曾有过一个评价,他认为:“‘五四’以后的二十年间,中国曾有过一个人文研究的传统,所取得的成绩至今尚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普遍尊重。但读者不要误会这里所用的‘传统’两个字。研究传统是在不断成长和发展之中的,甚至往往发生所谓‘革命性’的变动。章炳麟、王国维等上承乾、嘉学统,然而最后更新了这个传统。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五四’一代学人的身上。……无论文化心态是激进、温和或保守,他们都体现了推陈出新的共同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虽处在思想极端冲突的时代,最后都能使个人的心态和人文生态之间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人文心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必然存在着紧张,其程度因人而异。但这种紧张如果调节到恰到好处(也因人而异),反而可以为个人的创造力提供充分发挥的机会。这是我所谓‘动态平衡’的确切涵义。”(12)事实确实如此,当西式的科学意识完全浸入、渗透并主宰了国学研究的总体架构时,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固有的人文取向就会不可避免地与西学的科学意识发生冲突和错位,这也正是“中/西”问题最终总是会转化为“古/今”问题的核心原因。 中国自进入现代以来,其实一直都在“融入世界”与“文化守成”之间徘徊,其在思维形式上也主要显示为“中/西”“古/今”“传统/现代”“落后/进步”等样态的二元结构范型。由此,如何突破二元对立模式,以寻求二元互补的可能的新路径就成了众多中国学人反复探索的焦点问题。事实上,援外来文化之力以求传统文化的新路,一直是中国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秘诀。陈寅恪就曾分析认为:“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注解四书五经,名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传宗,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13)“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特殊耳。盖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叛,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14)从这个意义上讲,由吴宓等人借助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所展开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位,确实有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全新的价值。 白璧德曾受到过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一点无可否认。比如,他对“内制力(Frein vital or Inner chack)”“适度律(Law of measure)”及“君子儒(Confucion gentleman-scholar)”等的推崇,其意味与儒家的“克己”“中庸”以养成“君子”的思想几无差别。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白璧德的立足点仍然是西方式的,也就是说,即使他试图将培根的所谓“知识即是力量”重新拉回到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即是美德”的人文主义路上去,他也并不排斥“科学”本身。同样的道理,白氏倡导人文主义,却并不主张走向卢梭式的自然天性的道路。换言之,真正在白璧德思想中起核心支撑作用的仍然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建立起来的“理性”,只不过,在白璧德那里,理性的功能主要显示为对于“极端科学”和“极端感性”的合理节制而已;或者说,他其实是在希望兼顾“科学”与“人文”的同时,能够促使这两者协同并进。这也许才是吴宓、梅光迪等人所获得的真正的新的启发。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讲,以儒家为中心的思想没有发展出“科学”的一翼,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缺乏了对于“原则”的无条件服从这一重要的维度,由此也很容易使所谓“中庸”被单一地转化成为“无所执守”“和合为贵”,甚至“世故”“圆滑”。“科学”与“人文”能够形成现代西方文明的两翼,其根源就在于,“科学”培植起来的是一种“法(规范)”的意识,它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了相对可靠因而可以得到公共领域所普遍认可的“一般原则”——这既是一种不可逾越的底线,同时也是促使人性本身去恶趋善的保障。只不过当这一原则被推进到极致,以至于成为了钳制甚至扭曲人性的工具时,“人文”层面的反弹才会骤然爆发。所以我们看到,在白璧德的所有争辩中都无可避免地透露出了激烈抗争的偏执色彩,但彻底地以人文主义取代科学主义却也绝非白氏的本意。 与白氏的抗辩非常类似,发生在新文化阵营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也同样充满了偏执的气息,这就很容易造成视《学衡》一派为极端保守的错误印象。事实上,我们其实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学衡》同人的取向与林(纾)、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清季遗老一辈的“国学”意识已经完全不可同语了。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助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启发,对传统儒家的“中庸”理念给予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这就是对“执两用中”的“会通”意识的刻意强调:既执“中/西”之“两”,又兼顾“古/今”之“两”,彼此交汇以形成文化互融。如吴宓所言:“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宗教、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中西实可古今而下,两两比例。中国之儒,即西国之希腊哲学,中国之佛,即西国之耶教。特浸渍普通,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觉耳。”(15)这既是白璧德调和“科学”与“人文”两端的理想设计,同时也是对1920年代“杜威,胡适”式的单极化“科学”取向的有效制衡。对于正处建设时期的现代中国学术来说,这确实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大而言之,现今的西方世界对于单一技术主义倾向的警惕及对其自身现代性问题的深入反思,以及中国当下在大力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境遇等等,“执两”而“用中”的“会通”构想又何尝不是一条值得尝试探索的路径呢?东西方“古典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以及中国学界对国学问题的重新审视,其间所透露的也正是对于如何协调“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深切思考。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及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1994年)等。 ②罗根泽编:《古史辨(六)·冯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③王瑶:《我的欣慰与期待》,《文艺报》1988年12月6日。 ④《研究院章程·缘起》,原载《清华周刊》1925年10月20日,第360期,收入徐耕葆:《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75-176页。 ⑤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开学日演说词)》,原载《清华周刊》1925年9月18日,第351期,收入徐耕葆编选《会通派如是说·吴宓集》,第173-174页。 ⑥[美]余英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九州学林》2003年秋季创刊号。 ⑦⑩[美]罗德·霍顿、赫伯特·爱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房炜、孟昭庆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88、202页。 ⑧贺昌盛:《想象的互塑——中美叙事文学因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1页。 ⑨王晴佳:《白璧德与“学衡派”:一个学术文化史的比较研究》,(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2年6月,第37期。 (1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1928年10月。 (12)[美]余英时:《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九州学林》2003年秋季创刊号。 (13)(14)(15)吴宓:《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1919年8月31日,1919年12月14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2页,第58-59页,第45、103页。标签:国学论文; 人文论文; 科学论文; 胡适论文; 1920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实用主义论文; 吴宓论文; 学衡论文; 北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