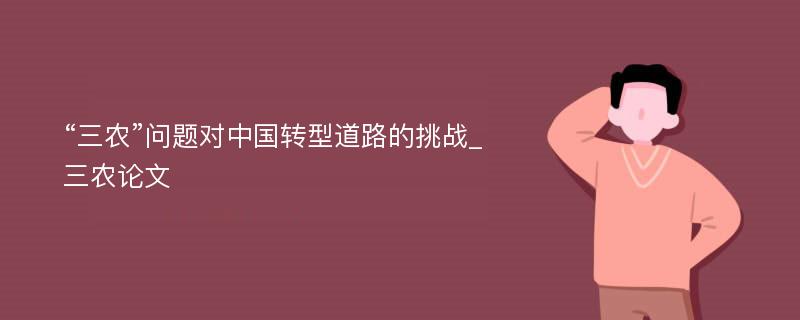
“三农”问题挑战中国转型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农”何以成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一定程度的城乡差别也是合理的,甚至被认为是城市部门进而整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在中国,城乡差别似乎到了分化的程度,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这表明总的说来城乡差别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除了1959-1961年3年农业危机期间)城乡差距是相当稳定的。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例基本上围绕着2.5倍之间平稳运行,而人均收入比率在1962年以后几乎稳定在2.3倍上下。与此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距在波动中呈发散趋势。从名义收入差距看,改革初期,城乡差距出现一个迅速下降的时期,在1983年达到建国以来的谷底:1.82倍。城乡差距在8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拉大,1994年上升到2.86倍。在1995-1997年间出现了近20年来的唯一的一次短暂缓解,但在1997年后又出现了显著的持续恶化态势,城乡差距以迅速上升的姿态挺进了新世纪,并在2002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值:3.11倍。可以说,现在既是建国以来农产品供应最充裕的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为严重的时期。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城乡差距是罕见的,并不是经济发展中普遍出现的现象。我所收集的36个国家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计划经济国家,城乡收入比率大都低于1.5倍,明显不同于我国2-3之间波动的情形。而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为到3倍以上并呈进一步分化趋势,这可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根据世界发展的一般经验,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阶段,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
二、中国转轨路径是城乡分化的根源
对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考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二元结构严重,且波动较大,并未呈现出逐步缓解的趋势,特别是1996年来反而有加重的态势,这同城乡收入差距的分化趋势是一致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差距的直接原因,这一由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w·刘易斯提出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但如前所述,中国的城乡差距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的一般程度,已达到了分化的程度。
当然,这可以部分地由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的发展中大国来解释,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这一结论可在与印度和巴西的比较中得出。中国全社会的基尼系数很高,而城乡差距贡献了其中的近60%,成为导致整个社会出现分化趋势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中国大城市中并没有出现过度拥挤、大量失业以及遍布城市边缘的贫民窟,而这些问题在孟买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是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化与农村而不是城市过分拥挤并存的现实,表明城乡之间一直以来存在着某种超市场机制的隔离障碍。这种判断让我们把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与中国特殊的转轨路径联系起来。
根据林毅夫等人的理论,我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是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需要。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建国以后,新中国领导人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确立并推行了一条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历经长期战乱和落后挨打之后,新中国的现代工业几乎是一片空白,要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面临资金原始积累和粮食原料的来源保障,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这些条件只能来自农业部门。要从农业顺利地汲取剩余,就需要相应的政策安排相配套,这一政策安排就是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另一方面,重工业的资金密集程度高,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因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意味着牺牲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控制劳动力从农村流出,同时保证城市居民充分就业以及避免其他福利的外溢,户籍制度应运而生。1958年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户口管理制度,以法律形式严格控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由于能够有效地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城市体制之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福利诸如全面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幼托、养老等制度也就可以随之建立了。这样,在此一系列制度安排下,从经济恢复后的1952年到改革之前的1978年城乡差距一直保持在2.4-3.2之间的高位上,除了3年农业危机时期外,差距值相当稳定。
在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随经济发展得到应有的缓解。转型在一般意义上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而对于中国,转型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在迅速推广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农业产量得以空前增加,农民收入有了显著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前期一度也得到明显的缩小,由1979年的2.66倍下降到1983年的1.82倍。然而,改革的重心很快就转移向了城市,但为汲取农业剩余以及限制农村人口的传统政策在渐进式改革中保留下来。农业早先的制度创新潜能很快就受限于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农产品价值的实现也受到城乡结构失衡的制约,先后两次出现卖粮难,农民增产不增收,城乡差距在城市现代部门的迅速发展中进一步拉大。
从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市场化改革得到不断推进,经济发展迅速,但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随之缓解,甚至还略有强化的趋势,这样,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就是必然的了。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虽然在总体上在1995年就已达62-80%,但实际上,市场化主要是在城乡内部并行推进,而城乡之间的隔离并未得到相应的消除,通过人口流动拉平城乡差距的市场机制功能大打折扣。增量的市场化改革似乎在城乡内部同时增长,但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成为存量部分而改动很小,因此城乡分离政策是中国转型中最大的计划体制堡垒,也导致了严重的城乡分化问题。可以说,城乡分化态势是中国渐进式转型道路限制了城乡二元经济正常转换的结果。
三、“三农”问题挑战中国转型路径
中国渐进式的转型虽然缺乏主流理论的支持,但到目前为止,事实却证明了它的成功性。与苏东巨变后的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的长期混乱和停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1978-2002年均增长率为8%)。这显然与提倡激进式道路的新古典学者的预测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并不就此认为自己的理论失效,而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特有的初始条件,是转型前超强的城乡二元结构能量释放的自然结构,与中国所实行的渐进式道路是不相干的,因而中国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他们的估算表明,来自农业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构成了TFP在1979-1993时期增长率的37-54%,在1984-1993年时期占到TFP增长的45-100%,而这一效应只占美国(1979-1969年)TFP增长的13%,这说明中国转型经济增长得自于初始经济结构的特殊。
近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进而认为,中国渐进式转轨的长期成本是高昂的,因为二元体制会在发展中制度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会使继续推进转轨的努力归于失败或丧失了进一步转轨的动力来源。对后进国家而言,存在某种“后发劣势”,因为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进国家应首先应进行宪政转轨,从根本上实行民主的制度安排,为经济的长期增长提供有效率的制度保障。而对于实行渐进式转轨的国家而言,短期内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但会使双轨并行的体制制度化,其转轨的长期成本将远远大于激进式道路。
对照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体制甚至宪政制度的改革,我们有理由再次怀疑新古典学者的判断。然而,就我们所关注城乡差距问题来说,它似平与我国转轨难度有互相强化的趋势。城乡差距直接缘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应该说,这在经济发展中是一个普遍而且是必然的现象,但我们认为,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诱发城乡分化。中国城乡差距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也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不相适应,超强的城乡二元结构只能归因于政策因素人为地强化作用。
城乡差距拉大诱发并强化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城乡二元经济的持续累积了城乡比例失调的矛盾;由于城乡间的体制分割,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部门膨胀,城市化道路任重道远;产业结构严重失调;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诱发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并导致一段较长时期的经济紧缩;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分层日趋严重;贫困问题难以通过扶持途径从根本上解决,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障碍;新兴科技和信息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使三农日趋边缘化;农业竞争力低下,WTO的巨大冲击指日可待。
由于我国渐进式的转型路径,分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存量保留下了的城乡间计划体制和制度落差造成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城乡二元转换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城乡差距得到人为强化,三农问题由此产生,并演化出一系列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足以对中国的转型路径提出挑战,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求。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调整,转型导致的问题要由经济的进一步转型加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城市部门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的条件下,重构城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