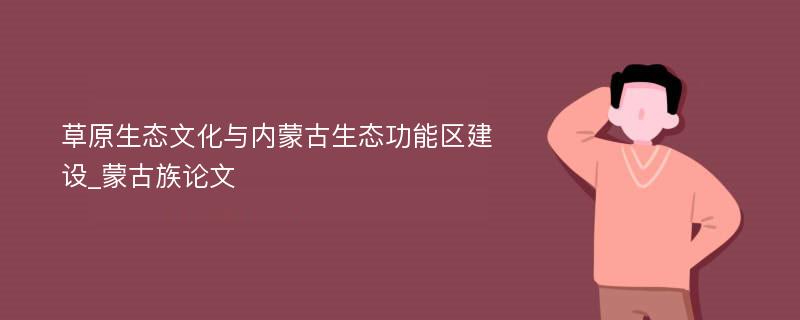
草原生态文化与内蒙古生态功能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内蒙古论文,文化与论文,草原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祖国北部边陲,横跨“三北”,东西长2 400多公里,南北宽1 700多公里,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1](P3)是祖国北疆生态系统的前沿阵地。内蒙古自治区一直以其临近京津、横跨“三北”的重要地理位置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在我国的生态安全大局中占据格外突出地位。内蒙古是我国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目前内蒙古荒漠化的面积已占全区土地面积56%,在全区88个旗县中,有67个旗县存在着土地荒漠化问题。[2](P16)因此,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防止草场退化与土地荒漠化,已成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环境治理的首要任务。
关于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问题,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大都从法律角度、制度层面、科技层面和提高群众对保护环境认知程度方面加以论述,且著述颇丰。但从文化的视角,从继承、弘扬草原文化精神元素的角度,探讨生态文化在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目前学术界不多见。
草原文化是人类社会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草原文化具有整体性、伦理性和实践性特征,其思想体系中渗透着关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共同繁荣的博大思想精神。尤其是草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在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环境方面,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草原生态文化的核心元素
1、“以人为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蒙古族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北方广袤的大草原上。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载体。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如蒙古族、鄂温克、鄂伦春等)很早就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这种自然崇拜实质是与游牧业相适应的大生态观。这种大生态系统观念,是游牧业对自然和谐统一的对象关系及其对象化活动方式的必然产物。其中包含着把自然生态环境当作自己生存本源的合理内核。反映了古代蒙古族珍爱自然、保护环境的价值取向。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价值观念体现在古代蒙古族的全部生产生活过程之中。
蒙古高原的地形分布大致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其间分布着各类草原,如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戈壁滩等。由于该地区草原分布广,各地所处的地形、气候、土壤、水分条件和草的营养成分差异很大,所以,蒙古牧民在草甸草原主要以饲养牛及肉毛兼用的细毛羊、半细毛羊为主;典型草原以饲养牛和马为主;荒漠草原以饲养肉脂兼用的粗毛羊、裘皮羊和绒毛山羊为主;戈壁荒滩以饲养耐干旱的骆驼为主。[3](P50)从蒙古族饲养牲畜的种类看,蒙古族的先民们很早就懂得“因地制宜”的生产经营方式。
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进化,成为生态系统中的最高层次,成为食物链中的最高层次,始终扮演着调节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蒙古牧民是蒙古草原生态系统的主要调节者和管理者,因此,蒙古族的牧业经济特点和生产方式,反映了他们对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认知程度,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是如何调节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草原生态系统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选择“掠夺”式的牧业发展模式,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的实际出发,把人、畜、草有机地结合起来,其行为后果是保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现出蒙古族自古以来就能够遵循自然发展规律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合理地利用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一面。
2、经济发展与“草、畜、水”三要素的有机结合。
古老的蒙古民族,不仅懂得怎样遵循自然规律,而且懂得怎样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在牧业生产中,珍爱草原,“取之有道”,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又不损害自然。
草,是牲畜的粮食。古代蒙古族为了保护草场,避免草场载畜量过高,严格划分草场使用权,实行游效(实质是轮牧)。成吉思汗时期,“把全体人民按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万户和九十五个千户……封建领主世袭占有自己的领地及其居民”[4](P9)“各千户所辖百姓不许变动,离开自己所属的千户、百户、十户跑到别单位者,被处死,接受他的人也要受到严厉的处罚”[5](P362)。这实质上就是对草场进行了严格的划分。每个封地里的人,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从事牧业生产,逐水草而居,实行轮牧。夏季有夏季的牧场,冬季有冬季的牧场。一年中多次迁徙、两次搬迁,而且均有固定的时间、路线和目的地。禁止在一处过度放牧,给草场一个自然恢复的过程。这种划分草场使用权和进行游牧的方式,从主观上讲,是统治阶级为了便于对劳动人民进行有效地统治和剥削。而这种制度化、法制化的牧业生产经营方式之所以一直延续至今,不仅仅在于法律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整体蒙古族在生态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因为这种生产方式能有效地避免因乱牧和过度放牧而导致的草场退化、沙化的局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草场的作用。
畜,是牧人生存之本,为了使草畜平衡必须加强对牲畜的管理。古代蒙古族十分善于根据不同的牲畜的特点选择不同的牧养方法,不仅有赶牧、领牧、天牧,而且对病弱牲畜还要进行适当的圈养、饲养等等。他们还以“套海”的方式来计算牲畜的数量,并给牲畜打上印记,当牲畜走失时也很容易在邻近的牧场找到,或被邻近的牧场主人驱赶回来。严格禁止牲畜“过境”乱啃、乱食。并掌握了一整套饲养牲畜的交配、阉割、育羔、治病、饮水等方法,适当控制牲畜和种群的数量。避免草场载畜量过高,形成对草场破坏的局面。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畜、草都不可或缺的。很早以前蒙古族就懂得保护水源的重要性。比如,蒙古族传统取火燃料是牛粪、马粪。每到夏季,他们总是把大量的牛马粪收集起来,和成粪饼晒干,储存起来,以备冬季取暖之需。粪饼热量高,污染小,不易熄灭,而且燃烧时间长,其燃烧效果可以和木炭相媲美。蒙古族使用牛粪作燃料,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之需;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大量粪便覆压草场,影响草的生长;同时,也避免了夏季雨水冲刷,把粪便冲入河流,污染水源。真可谓是一举三得。在古代蒙古族札撒(法律)中规定:“禁止在河中洗澡、洗手,或者用金银器皿汲水,也不得在原野上晒洗过的衣服……他(察合台汗)不宽恕一个哪怕稍有违反它的人,当他看见这个人在水中洗身时,出自他的愤怒火焰,他想把这个人焚骨扬灰”[6](P241)。从表层次上看,这是生活习俗的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是对水的自然崇拜,但从深层次上却起到了保护水源的作用。
从古代蒙古族的牧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来看,蒙古族合理而有效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把牧业经济中的三要素:水、草、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经济活动不仅在一定生态系统中进行,而且以其中的生态资源作为劳动资料或劳动对象,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人本身也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生命物质一样,时刻不能脱离生态系统,所不同的是,人不是简单地、消极地适应环境,而是积极能动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生态系统中,“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生存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7](P517)因此,自觉地遵循自然规律,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发展内蒙古地区经济的前提。就这一点讲,蒙古族先民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不是单纯地为了自身的生存而盲目地、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恶意”索取,而是把牧业经济发展和保护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满足了人的需要,又保护了自然环境、保持了生态平衡,获得了人与自然的“双赢”。古代蒙古族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3、保护草场要有严格的法律。
12世纪蒙古族崛起后,随着人、畜数量的增加,给草场承载能力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草原的保护与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成吉思汗时期,就把破坏生态环境作为“国禁”,如:在狩猎时禁止猎杀幼崽,不得乱砍树木,“凡破坏牧场者,受惩罚……遗火焚草者,诛其家”[8](P443)。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年)屡下诏令,“禁牧地纵火”,并派人到缺水草原凿井,扩大牧场。由郭守敬主持修建了内蒙古历史上第一座牧业用水渠——铁幡竿渠。虽然在元代前后,内蒙古地区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了草原耕植,但主要分布在与汉族接邻的地区,零星分布,且规模较小,对畜牧业没有构成影响。到18世纪中叶,内蒙古草原还基本保持着原始的自然形态。
古代蒙古族生产、生活之中包含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使得蒙古草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蒙古牧民也世世代代在蒙古草原上生息繁衍。而这种生态伦理观念的形成,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古代蒙古族制定的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禁忌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这种良性互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和支持。
二、发挥草原文化在内蒙古生态功能区建设中的作用
1、强化舆论引导功能,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蒙古族世世代代以游牧为生,习惯于逐水草而居。要改变这种粗放式经营方式,变“天然牧养”为“圈养”,变“游牧”为“定居”,无疑会使蒙古族生产、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对蒙古族传统生活方式与心理适应提出了重大挑战。古代蒙古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具有明显的适应性、实用性、合理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稳定性、传承性特征,这种生态伦理文化至今仍然植根于蒙古族的价值取向中,这就为退耕还林还草、封山育草,保护修复蒙古生态功能区,提供了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支持。蒙古族先民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传承了辉煌的草原生态文化,草原生态文化中的自然观是一种内在的回归自然、追求朴素的生态伦理观。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下,草原自然环境长期以来得以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清水、净土。蒙古族草原生态文化的自然观既符合当代人热爱优美环境,渴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又为内蒙古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修复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所以大力弘扬草原生态文化,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积极营造经济发展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舆论环境,落实“科学发展观”,这对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2、坚持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大背景下,蒙古牧民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保护与修复草原生态环境,以草原为依托,发展现代牧业经济,走集约型牧业经济发展道路,利用草原风光和民族风情发展草原旅游经济、兴办沙漠产业,让广大牧民在保护治理环境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发展特色经济,才能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只要措施得当,大力弘扬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蒙古牧民还是很容易接受的。尤其是在今天内蒙古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必须发挥广大牧民的主观能动性。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不仅要从物质层面上加大环境投资力度,也要从文化层面上弘扬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使各民族充分认识到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例如:随着市场对鲜奶需求的增加和内蒙古乳业的发展,内蒙古奶牛发展前景广阔。因此,因地制宜,减羊增牛,是今后牧业经济发展中的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3、加强法制建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是核心。因此,有些地方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盲目地追求经济发展指标,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下,置生态环境于不顾,造成森林惨遭毁灭、草原退化、水源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而各民族优秀的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在经济利益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面对已经严重退化了的内蒙古大草原,蒙古牧民只能靠悠扬的歌声抒发他们对昔日美丽大草原的依恋之情,蒙古族的许多歌曲都反映了这一点,一方面表现了蒙古族对美丽大草原的眷恋之情,另一方面,他们也试图用歌声唤起人们要珍爱草原,保护环境的传统意识。所以,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用法制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4、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生态环境建设与提高广大牧民的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价值说到底是客体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和关于人的理论为基础的,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牧民群众是发展的价值主体,不断满足广大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和实现农牧民的全面发展,是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的根本目的。和谐社会一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这就要求我们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解决好内蒙古农牧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作为生态功能区建设的目标,把广大农牧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价值导向。只有积极发挥广大农牧民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更好地实现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的宏伟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护修复内蒙古生态功能区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需要。全面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努力实现祖国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
标签:蒙古族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修复论文; 草原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