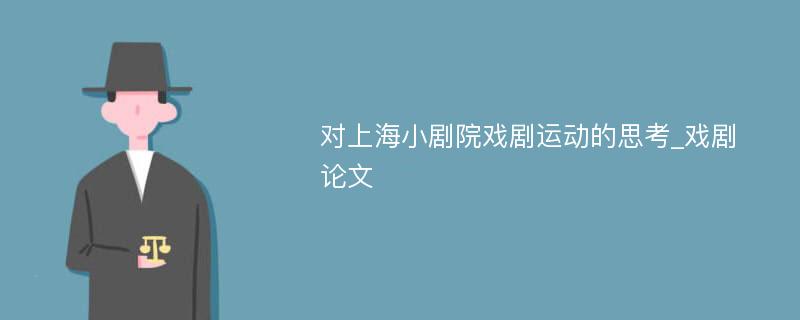
关于上海小剧场戏剧运动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戏剧论文,小剧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种文化艺术,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在其主流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伴随着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非主流支脉。尽管中国话剧在起源时最先受到的是浪漫主义的熏染,后来在相当长的历史岁月中又是写实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但在九十年的戏剧长河中,相对于主流话剧艺术来说,探索从未停止过。如早期的“爱美剧”和抗战时期由田汉改编自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媚娘故事,后又由陈鲤庭、崔嵬进一步中国化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及“工农剧社”的“兰衫团”用不同的色彩代表不同人物,用人物造型代表机器、车马、景物的尝试等等。但这些都没有成为戏剧运动。真正成为一种戏剧运动的中国话剧的小剧场戏剧,则是发生在中国八十年代的历史时期。正是这个小剧场戏剧,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写下了可贵的篇章,成为中国话剧运动中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然而,小剧场戏剧却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艺术概念。无论是小剧场戏剧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因为它的多义或难以界定而显得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即小剧场戏剧的观演关系打破镜框舞台的限制而呈现三面观众或中心舞台或更为融合的形式。否则,只要是反传统或先锋前卫的戏剧就是小剧场戏剧,那么,西方本世纪初就出现的达达派戏剧、法国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和二十年代盛行于前苏联的构成主义戏剧,等等,早该是开了小剧场戏剧的先河了,然而却不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只要是在前面所述的观演关系中,就可以演出各种风格、题材的小剧场戏剧,它们也许演于改造过的剧场、楼厅、排练厅,也许演于教室、咖啡馆、各种休息室、仓库,……
实验一:《母亲的歌》突破镜框舞台口的尝试
1982年,中国戏剧界出了两件事,一件是北京的秋季上演了有小剧场戏剧色彩的《绝对信号》;一件是上海的冬季上演了“中心舞台”的《母亲的歌》。
胡伟民,这位极富有创新精神的杰出导演,在排演《母亲的歌》时,刻意不在剧场,而是把青年话剧团的排练厅改造成“中心舞台”。戏本身并非警世之作,只是讲了一个将军的遗孀教育子女如何对待人生的故事。剧中演员和观众的交流已不是“楚河汉界”,而是近在咫尺的沟通。那清晰的泪水,牵动人心的欷嘘,无不让观众动容。
十五年之后,当我们重新回首这段戏剧往事时,深深感到该剧的历史价值主要不在于艺术上的得失,而在于它勇敢地打破了多少年来横亘在演员和观众之间的镜框舞台口,营造了新型的观演关系。
1759年,当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在法兰西喜剧院把喜欢在舞台两侧看戏的观众赶下台,〔1 〕从而展开了世界各地剧场把观众赶下台的“运动”。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世界戏剧史上的这种运动扫除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观众在舞台上看戏的传统,而是从此在演员和观众之间人为地造成了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将戏剧表演崇高化、神秘化和幻觉化,直至戏剧舞台演绎成自然主义。但是,物极必反,六十年代,西方戏剧界异军突起,很多先锋前卫的戏剧团体已不再满足于在镜框舞台上营造,纷纷突破舞台口,开创他们认为合适的表演空间和观演关系。六十年代的日本也涌现出铃木忠志等人的小剧场戏剧运动。然而在中国,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现小剧场戏剧的端倪。即便如此,对于当时还穿着“蓝制服”、“中山装”的中国戏剧来说,超前的胡伟民不幸“曲高和寡”,观众对演员就在身边表演多数显得茫然。理论界也缺乏心理准备,以至于本应该轰动的演出反响却寥寥,这不能不说是憾事。
实验二:内容走向前卫的《屋里的猫头鹰》
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戏剧界终于出现了一部让观众兴奋的戏。这就是由云南归来的青年戏剧家张献创作,由青年话剧团在排练厅演出的《屋里的猫头鹰》。观众激动的原因首先是戏剧大环境的变化。文革浩劫后的中国文化经过“十年生聚”渐渐恢复了元气,不仅修复了传统,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国际间广泛的文化交流,新观点、新思维之风也真正吹进了戏剧界。无论是戏剧家,还是观众,都出现了追求新戏剧观念的群落。其次,这只“猫头鹰”从内容到展现的确具有对传统戏剧的反叛性,因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神秘和新奇。在这台戏中,空空因为性无能只好用催眠术欺骗妻子沙沙,沙沙由于潜意识中的情欲,在梦境中构想了一个年轻的猎人康康。空空不甘心失去目标,闯入沙沙的梦中与康康决斗……。这时,深林里的猫头鹰因为没有雄性濒临绝种,于是全部飞出深林,飞进城里,飞进每一户人家。剧作者排除事件的表象,深入到精神意识中将生命的本原进行变形和陌生化,不强调主题,只表现朦胧的意念;剧中人物没有特定的年龄、职业和社会地位,只代表象征层次上的社会属性;人物交流大都充满神秘感、冷漠感。观众进场前被命令首先在一间空屋里集中,由演出向导讲述有关看戏的注意事项,然后发给每人一件猫头鹰面具和一件黑色斗篷,并一再叮嘱大家看戏时必须戴上面具。此剧应邀参加1989年“南京全国小剧场戏剧汇演”,由于参演的其它剧目大多数是传统类的“小剧场戏剧”,所以,它的演出即刻成为汇演的热点并引起强烈的反响。
此剧演出的意义有两点引起我们的注意:其一,此剧在结构、内容、表述上具有的先锋性在当时的中国剧坛是罕见的。其二,观众穿斗篷戴面具观看演出,还被鼓动到台上去“殴打”剧中人沙沙,这已是名副其实的观众参与。因而,此剧在中国小剧场戏剧中是一次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尝试。
可惜的是,这样的小剧场戏剧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一定的前卫戏剧群体中才能产生,然而,这样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张献的另两部先锋戏剧除《时装街》得以演出外,《巴士上的孩子们》只能在“剧本朗读会”上朗读一部分情节而了事。
《屋里的猫头鹰》使上海的小剧场戏剧红火了一阵子,但很快转入了低谷,因为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长期来由计划经济哺育的“计划型戏剧”一直仰仗着“计划型”供需关系,以低票价、低收益和缺乏热情的观众维持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当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阶段,常规戏剧一下子晕头转向,在它羽翼下的小剧场戏剧必然步履维艰。虽然戏剧家们坚持不懈,相继排演了《明日就要出山》、《金棕榈酒吧的楼上楼下》,《爱情书简》和《皆大欢喜》等各具特色和艺术价值的剧目,受到观众的欢迎,为小剧场戏剧艺术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但总体来说,没能使小剧场戏剧走出困境。
实验三:从《留守女士》到《情人》,小剧场戏剧闯入商海
剧作家乐美勤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创作的大型剧目《留守女士》会被青话看走了眼,又被人艺如获至宝地做为小剧场戏剧演出。导演俞洛生删削枝蔓,突出“家”的情结,以话剧明星奚美娟和吕凉出演男女主人公。票价第一次提到十元一张。是撞大运还是独具慧眼,反正剧场里“情景交融”、戏票提前月余订空。看到“小剧场”“下海”初战告捷,小剧场戏剧家们跃跃欲试。92年下半年,青话小剧场又开始启动。这次他们选中了英国荒诞派戏剧大师哈罗得·品特的《情人》。在宣传上,他们打出了“未成年人不宜”的欲擒故纵的旗号。在排演上尽量将这出晦涩的荒诞剧演绎得通俗化,竭力迎合观众口味。虽然这些手段未必符合原剧的初衷,但却创造了上海小剧场戏剧的奇迹。剧组不仅在上海场场爆棚,还在全国巡回演出三十余个城市,创下三百场的演出记录,并出访新加坡,投资仅几千,收益二十余万。于是,圈外人也纷纷看好“小剧场”。“上海浦东万丰房地产开发经营总公司”、“上海市演艺总公司”和“上海文艺记者沙龙”联手在“兰馨”大戏院推出意大利现代剧目《开放夫妻》;不久,人艺又和“牧羊神”合作排演了《美国来的妻子》;青话也排演了由四十多个电话组成,一人主演的《大西洋电话》;“现代人剧社”又相继排演了《黑色蜜月》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戏剧家加谬的《鼠疫》,都不同程度地努力于演出市场的开拓,在小剧场戏剧商业化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思考一:难以突破的镜框舞台
每一种戏剧样式都应该有自己的艺术特征。虽然小剧场戏剧由于其性质复杂而让人们莫衷一是,但还是有一些大致相同的共同点。日本演剧评论家扇田昭彦将小剧场戏剧归纳为七点:1.演技的变革;2.剧本结构的转变;3.观众参与;4.改革剧场构造;5.反剧场性;6.非剧团性;7.作为戏剧运动的重新崛起。〔2〕这些观点虽不乏争议之处, 但其主要精神是不错的。如果用这些特征比照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小剧场戏剧,基本上都可达标且有些边缘戏剧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如果比照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小剧场戏剧,明显感到大相径庭。
小剧场戏剧存在的意义首先体现在对演出空间的重构。其中的特点之一就是舍弃镜框舞台口,对演区和观众区重新布局。如果仍然在传统的镜框舞台上演出,即便剧场再小,也只能称为“剧场小”,而不是“小剧场”。纵观上海的小剧场戏剧,虽然有些戏对演区和观众区进行了重构,突破了传统的镜框舞台口,如《母亲的歌》、《留守女士》、《美国来的妻子》、《陪读夫人》等,很多名为小剧场的戏剧仍然沿用传统镜框舞台的观演关系,只是因为演区小,观众少而已。在这样的舞台上,导演和舞台美术家仍然用唯美的方式解释和图解戏剧环境,其舞台表现语汇与传统舞台几乎没什么两样。这显然是一种误区。然而,虽然有些戏剧采取了“中心舞台”或三面观众或演员和观众互相融合的方式,但仍然用传统的结构表现传统的故事。在这些“小剧场戏剧”中物理空间的镜框舞台口也许不存在了,但心理空间中仍然有着抹不掉的镜框舞台口,仍然存在着“第四堵墙”。实际上是在新型的演出空间中表演着传统的老一套的戏剧。虽然在有些演出中,导演和演员刻意进入观众中表演,也设计出一些手段鼓励观众参与剧情,但大都收效不大。究其原因,固然和中国观众缺乏勇气不擅长表现自我有关,但更多的原因则在于戏剧结构和情节本身。可见,突破镜框舞台口,并不象在物理空间中那么容易,尤其是要突破戏剧家心中的镜框舞台口就更为艰难了。但唯其如此,小剧场戏剧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探索。
思考二:表演更需要探索
几乎在所有的上海小剧场戏剧中,演员的表演仍旧采用传统的方式,只不过在程度上存在一些或是偏向再现或是偏向表现而已。由于观众近在咫尺,很多小剧场戏剧为避免大剧场表演的“舞台腔”,纷纷缩小动作幅度,放低台词的响度,尽力表演得自然,就象生活中一样。因而,很多演员借鉴影视表演,采取“低调”、“无痕迹”方式,这对于传统故事情节的戏剧也许是合适的。然而,也有相当多演员过分注重“生活化”,过分追求自然,以至于走向自然主义的表演,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当然,用传统的表演方式表演小剧场戏剧也未尝不可,而且,不可否认,传统的表演方法同样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由传统表演方法也确曾创造出很多深受观众欢迎的戏剧作品,不过,人们要问,小剧场戏剧只能这样表演或者只有这样一种表演方式吗?
事实上,海外的很多边缘戏剧大都采用非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最负盛名的波兰贫困戏剧领导人格罗托夫斯基在训练演员时采用近乎杂技的手段,以求“躯体的延伸性达到极限的地步,就跟印度的卡塔加利舞演员所作的那样,‘纯粹的冲动’才能从无意识的最深层里被解脱出来”。此外,他们“还把东西方的戏剧程式糅合在一起,目的就在于使观众置于新的戏剧体验之中”。〔3〕1961年, 彼德·舒曼从德国把“面包与木偶剧团”带到了纽约,演出时采用了由脚踩高跷、面戴巨大假面具的演员装扮的高大木偶,十分引人注目。按照彼德·舒曼的说法,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使世界叫人看上去一目了然”。〔4 〕美国的“开放剧团”更具有实验色彩,表演方法有点象瑜珈冥想,全团通力合作,运用音响和动作,而不是运用语言探索幻想和梦境的“感情领域”。〔5 〕而日本铃木忠志的剧团则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了某些能剧和歌舞伎的手法,然而又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把注意力提炼、集中在被现代表演技巧所忽视的传统戏剧的动作和肉体素质上,铃木解释说:“它始于脚也终于脚”。尽管铃木的观念基本上是日本式的,但已渐渐成为对美国及其它国家的演员极富意义的一种训练技巧。〔6 〕虽然西方边缘戏剧或小剧场戏剧的表演方法不一定适用于我们的小剧场戏剧,但多样化的表演方式和表演美学也应是小剧场戏剧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
思考三:呼唤非专业小剧场戏剧家群体
著名戏剧家徐晓钟教授和胡妙胜教授曾著文认为,从事小剧场戏剧事业的成员,应具有一种称之为“斯杜基亚精神”的精神或大体上可以叫作“发烧友精神”。〔7 〕这就指出了小剧场戏剧家应该是非专业或业余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东西方戏剧史上很多有创见的戏剧群体,大都是由非专业的倡导发起进行业余的或非赢利的演出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上海小剧场戏剧几乎清一色都是由专业话剧院团的“正规军”操办的。即便是“现代人剧社”等民间戏剧组织,其成员也都来自专业团体,并且是松散的,在艺术观念和制作及演员来源上与“正规军”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有时就等于“正规军”。这样一来,上海小剧场戏剧便无不打上了“专业”的烙印。于是,在小剧场戏剧的观念、剧目选择、排演方法上,必然与海外的小剧场戏剧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必然要较多考虑观众的要求,文化市场的动向和商业上的得失以及社会效益,而较少考虑小剧场戏剧本身的艺术规律和探索。如此,上海的小剧场戏剧必然少了实验性而多了传统性,少了探索性而多了赢利性,成了大剧场戏剧的附庸和戏剧市场化的一种手段。
不过, 要说上海从未有过非专业性质的小剧场戏剧却也不尽然。 1986年就曾有过热情的大学生刘擎、陶骏等人组织了“白蝙蝠实验剧社”, 他们将莎士比亚的某些戏剧人物重新组构演出了《莎翁独白》; 90年左右,又有一批美术界、文学界的青年在上海美术馆举行了《最后的晚餐》的演出。他们一行十二人穿上只露出两只眼睛的白色连帽袍,在用大量白布围成的甬道中鱼贯前行到一长台前,在众目睽睽下,在四周的自然音响中,将各自面前的一听可口可乐喝完。据他们自己称,这是一次行为艺术展。其实,它已经包含了戏剧所要求的基本要素:有空间,有演员,有观众,有情节……。因而,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实验戏剧演出,这和海外的一些边缘戏剧何其相似乃尔。只是他们也许是一时冲动,没有继续坚持他们的实验,从而湮没于历史的岁月中了。
结语
这样说,也许对上海小剧场戏剧过于苛求了,也许采取与海外小剧场戏剧横向比较的方法本身就是不恰当的,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有着自己的根和民族性。本文的初衷是籍此寻找中国或上海小剧场戏剧的历史定位和艺术特点。因为,上海小剧场戏剧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历史所形成的。上海小剧场戏剧运动毕竟走过了十五年的坎坷历程,创造排演了值得我们引以为荣的戏剧作品,为上海的戏剧振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上海小剧场戏剧是在自己民族的土壤上对戏剧的本质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上海小剧场戏剧家们已经走出或正在走出传统镜框舞台,今后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和风格从事和开拓上海的小剧场戏剧事业。
可是,众所周知,戏剧起源于原始的祭典或舞蹈,那时的表演者和欣赏者是融为一体的,无所谓表演和参与之分。由于文明的进步、戏剧的发展,演员和观众才进行了分离,在舞台上看戏的观众才被赶下舞台,镜框舞台才成为传统戏剧和现代戏剧之间的鸿沟,那么,今天的小剧场戏剧家们积极努力摆脱镜框舞台口,去寻找更加自由的戏剧空间,以寻求观演的共享和彼此的融合,这对于戏剧来说,是意味着出走,还是回归呢?
注释:
〔1〕吴光耀《西方演剧史论稿》P543.
〔2〕《戏剧艺术》1996·2·P76.
〔3〕〔4〕〔5〕J·L ·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二)》P232、P242、P244。
〔6〕〔7〕《戏剧艺术》1996·4·P58—P59、1994·1·P3—P5.
标签:戏剧论文; 戏剧影视文学论文; 剧场论文; 留守女士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