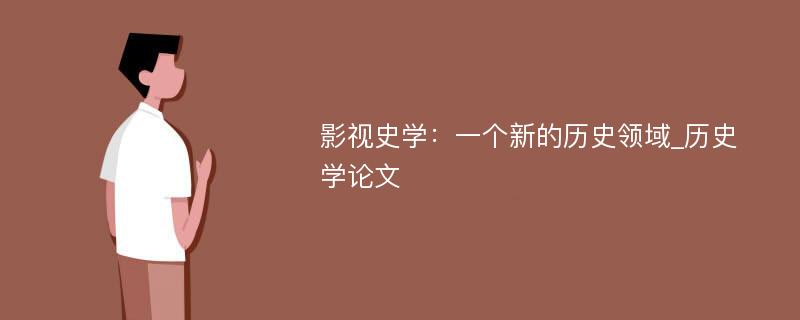
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新领域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时代转变与回旋的速度之快的确令人目迷五色,应接不暇。在这种社会转型与文化演变的时代,历史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由于这种古老学科与现当代各种新兴学科的“交叉”与“嫁接”,产生并繁衍了许多史学新品种与新门类。“影视史学”就是当代史学大家族中的一个新生儿。
1
提出“影视史学”这一概念,是晚近以来的事。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发表《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一文称:所谓“影视史学”,是指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而“书写史学”则是指以书写的论述所传达的历史。[①a]在这里,怀特教授杜撰了一个新名词:“影视史学”(Historiophoty)。此后,结合讨论《谁杀了肯尼迪》(JFK)和《返乡第二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这二部影片,在颇为严肃的美国史学权威刊物《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争论遂起。不管怎样,影视史学的问题终由附庸而蔚成大气,及至跨进了历史学的殿堂。
这种讨论也在美国之外激起了回音。在台湾学术界,中兴大学周梁楷教授首先对此作出了反应,他写的论文《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于1992年发表,从史学理论中的历史因果关系和西方史学嬗变的学科视界,对影视史学的若干方面作出了很生动而又透彻的解析。[②a]翌年,他又撰《辛德勒选民:评史匹柏的影视叙述和历史观点》。他认为,在影片《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List)中,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史匹柏,Steven Spie Lberg)执意用黑白影片(只有在片头和片尾各有一小节彩片),传达出一段往事,亦即揭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残酷杀害犹太人的一段历史的真相,其影像视觉的效果可能远超过任何书写的历史。[③a]
在大陆史学界,尽管《美国历史评论》之类刊物并不难觅,尽管像《谁杀了肯尼迪》和《辛德勒名单》等类影片也可见到,但对影视史学却鲜有反应。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它是一个新概念,一个不见于传统史学世袭领地的新概念,一个反映现当代西方史学乃至国际史学变革的新概念。
在这里,笔者想以1995年秋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两部参展的国产影片,即《红樱桃》(Red Cherries)和《人约黄昏》(Evening Liaison)作为个案分析的例证,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讨论影视史学,陈述若干我的肤浅的认识。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是历史剧情片(Historical Drama Film)与史学之间的关系。《红樱桃》和《人约黄昏》所反映的不是当代正在发生的现实生活,而是与历史有关,可以称之为历史剧情片,前者所要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往事,后者所要表现的是30年代的上海。但是,这两部影片的制作者各以自己的视角与理解,通过影视语言,演绎与传达出一种新的文化意念与历史意识,足以令人回味,并使观众陷入了深深的历史思考之中。
《红樱桃》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则催人泪下的故事:1940年,有一批中共后代被送往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本片女主角楚楚和罗小蛮也在其中。苏德战争突然爆发了,战争破坏了孩子们的平静生活,战争也夺去了许许多多亲人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历尽痛苦与磨难,楚楚更不幸落入德寇魔爪,她从绝食反抗到被迫纹身,这个中国女孩经受了种种难以忍受的悲哀与屈辱。在逆境中,楚楚、罗小蛮等中国少年,与苏联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以惊人的毅力和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父辈们身上的优秀品质与人格力量。当人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楚楚却无法因胜利而弥合她心灵上的伤痕,影片结尾留下了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影片的字幕最后告诉我们,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女主角的原型于50年代归国,直至1990年才病逝。
影片《红樱桃》以其视觉具象的魅力,既展示战争对人类肉体的消殁,如:德军追逐一个未成年孩子张卡尔,把他逼进一个土坑,敌人举枪对他扫射,画面上看到的是这可怜孩子的颤抖的身子与恐惧的双眼,交替重叠,令人窒息的恐惧感犹如狂风席卷着张卡尔,也席卷着每个观众的心灵;又如:当德军头目戏侮学生、遭到女教师制止后,便猝不及防地拔枪射杀她,只见画面上是脑浆迸溅、双目圆睁的令人惊怖的镜头。但影片更以视觉具象,在揭示战争对人类肉体摧残的同时,让观众进一步去感受战争对人类所造成的难以洗劫的精神创伤:当楚楚逃过枪杀、免除肉体毁灭的灾难之后,而法西斯头目冯·迪特里希将军却要在她身上纹上纳粹标志,楚楚再次跌入了苦难的深渊,一种比肉体毁灭更难以忍受的精神虐杀的深渊。当那只黑得刺目的凶恶的苍鹰和腥红的纳粹标志深深地烙在这位中国女孩身上的时候,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创伤也深深地烙在每一个观众的心上。这与大导演史匹柏执导的《辛德勒名单》中,毒杀犹太人的场景,是各有千秋的。对此,日本电影剧作家协会会长铃木尚之评论道,影片中的纹身镜头在神圣刺激中体现出残酷,少女背部的图案与画面色彩,交融出了无限的张力。正如该片导演叶大鹰所说:“所有这些场景,都是用书写语言和文字难以取代的。”影片《红樱桃》主要不是从正面表现战争的场景,表现战争的残忍与对人类的摧残,而是侧重通过多组画面与图像交错,有声有色地昭示了战争中人的心灵感受和战争对人的心灵摧残,它所留给观众的历史思考,在某些方面,确要胜过一些陈述二战与揭露纳粹暴行的书写史学的历史作品。这正是《红樱桃》的成功之处,也是它的胜人一筹之处。
《人约黄昏》与《红樱桃》的故事其背景不同,它所要描述的是一则凄迷的人“鬼”相恋的奇情故事:30年代的上海,某一个深秋之夜,一名记者在一家烟铺,与一位神秘的黑衣女子邂逅相遇,这名男子对她一见倾心,而那女子冷艳幻异,行踪无定,扑朔迷离,且自称是“鬼”。记者为情所迷,追逐不舍。在对女子身份及身世的猜测和追寻过程中,记者不经意地触及了这位神秘的黑衣女子一些鲜为人知与触目惊心的往事。原来此女子乃是当时上海某一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成员,暗杀之风盛行于该组织内部,于是演绎出一段情仇交织的故事。那女子最后带着对人世尘缘的悔悟,倏然消逝,永远离开了与她相爱的记者。而他仍痴心不改,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黄昏,再次来到了那爿烟店,以期盼重现最初的奇遇。
电影《人约黄昏》的制作者借助一则人“鬼”相恋的故事,意在展示风云激荡下的近代中国的一幕,力图“重现”30年代的上海:有着上一世纪欧美风格的大厦鳞次栉比,“弹街路”,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行驶在闹市区,黄包车上坐着穿西装的先生与穿旗袍的小姐,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煤球炉中那浓烈的烟味从弄堂里飘来,沪语方言与沪上小吃,era牌香烟……时光倒转,一切恍然如在梦中,似乎重又回到了当年。影片导演陈逸飞是个画家,他尤其注重环境氛围的营建与图像画面的造型,着意描述一个发生在30年代上海的故事,从而让观众生发出诸多游离于《人约黄昏》故事之外的思考。遥看30年代的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人们不禁要问:饱经西方文明的冲击与苦难屈辱,它做出了多大的反应?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所发生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离异与回归,是对往昔生活的无情抛弃?还是对域外文明的全盘吸收?面对这个东方大都会文明的畸形繁荣,在古老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它又怎样被历史推上了前沿,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东方大邑?如此等等,难以尽说,聊复尔耳。
从这两部影片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影视史学的特征及其相对于书写史学的优越性:其一,影视史学比书写史学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具有某种“摄人心魄”的震撼力。正如怀特在1988年那篇著名的文章里就指出的那样,“电影(或电视)的确比书写的论述更能呈现某些历史现象,例如:风光景致、周遭气氛以及繁杂多变的冲突、战争、群众、情绪等等。”这里的“更能”是因为影视史学借助于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因而比书写史学显得更生动、更形象、更清晰,因而也就更具感染力与震撼力,因而也就有难以忘怀的魅力。
其二,一部优秀影片或经典之作,往往拥有比书写史学更为广泛的受众阶层。影片《人约黄昏》在上海公开放映的那几天,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去“人约黄昏”了,且看:有人喜欢片中那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有人想回到孩提时代,到旧上海去寻梦;有人欣赏它那精美的画面与高雅的艺术品位;有人从表面的复仇故事中寻求一种处世真谛与人生哲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红樱桃》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视角,以最动人的方式和表现手法,对观众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震撼力,女主角的出色表演,以及影片中所展示的俄罗斯美丽的风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打破了“叫好不叫座,叫座不叫好”的尴尬局面,而是真正做到了专家叫好于前,观众也叫座于后。
由此可见,一部为广大观众所称道的影片,它的受众者可与一部畅销的流行小说相媲美,而影视史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一旦这种小说被摄成影片,更是如虎添翼,在坊间广布,如据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小说原作《飘》(Gone with the Wind)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成了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片,历映不衰,传布于全世界,至今仍吸引着千万个“佳人迷”。一旦当流行小说与影视互相联姻的时候,它的受众面之广不可估量,在这方面,书写史学是不能望其项背的。
最后,因为有如上两点,故影视史学的影响要远胜于书写史学,《红樱桃》与《人约黄昏》所引起的广阔的社会层面上的热烈反响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种影响既是直接的又是潜在的,既是表层的又是深层的,既是现实的又是长久的。我想,凡是看过这两部影片的人,也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的。
2
影视史学这一新概念,从它的出现之日起,就构成了对传统的书写史学的挑战。其肇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急剧转换的年代,人们需要一个了解、认识与思考的过程,这就在变化的时代性转换与人的认识之间产生了“时间差”。当上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家还沉湎于档案馆,从灰尘扑面的文献中爬梳史料的时候,1895年电影发明了,从此,人类开始从静态的文字文化进入动态的图像文化。这是一种可供观赏的视觉文化,从最早的无声片到当代最流行的vcd镭射光碟电影,人们跨入了一个不受时空限制交换情报的多媒体时代,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新天地。从文字文化进入这种形式的图像文化,其意义及对人类深远的影响也许并不亚于从远古时代的结绳记事到文字的发明。对于这一重大的文化转型,许多人是准备不足的,当历史学家仍以往昔的史学观念与方法来观察影视史学这一新学科时,两者的巨大落差与失衡是可以想见的,历史学的滞后性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
其次,从表现形式来看,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的明显区别在于传达的媒体的不同:书写史学依赖书写文字以反映历史,而影视史学则是影视技术与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产物,它借助现代影像与音响技术以表现往事。由于影视史学引入了影像与音响,这种视听思维的文化,改变了人们长期来使用的文字训练与文字语言的线性思维的平面模式,正如论者所云,“它的直捷性,它的具象性,它的能指与所指的同一性是文字语言无法比拟的。”[①b]由这种媒体革命而带来的深刻变化,对习惯于用书写形式来研究历史的传统史学,不啻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再次,随着从文字文化进入图像文化,用之于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怀特指出:“现代的史家必须自觉,分析视觉影像时的‘解读’方法和研读书写的档案是截然不同的。”他同时又说,“选择以视觉影像传达历史事件、人物及某些过程的那一刻,也就决定了一套‘词汇’、‘文法’和‘句法’”。显而易见的是,影视史学所使用的“词汇”、“文法”和“句法”是与书写史学大异其趣的,由此会引起史学方法论上的革新。譬如对史料,传统史学认为,只有官方的档案文献才是最珍贵的史料,凭借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就可以写出信史。现在不同了,图像史料便可以列入史料的范畴,video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历史研究者也是可以凭借这些材料,丰富我们对某一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总体了解与认识的。以此生发开去,这种在方法论上的变革,将会对史学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
最后,影视史学的出现,也促进了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根据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说的“重新定位”,大体可包括如下一些内容:如历史学家在如何阐明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与史料的关系等方面,有一个观念的更新与再建的问题;在历史研究的范围方面,他们发觉应当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把19世纪传统史学所不屑一顾的许多方面列入史学研究的对象,以本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史学”(Publie History)为例,在那里,史学研究的范围从协助制定政府决策到文化资源的管理,再到婚嫁、娱乐、饮食、衣着等,史学简直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一如万花筒般的现代影视节目那样;在史学方法方面,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开展,为史学变革找到了突破口,尤其是它推动了历史学家研究技术、手段与方法的革新。影视革命是现代技术革命的直接成果之一,这一成果对史学革新,尤其是方法上的革新,同史学研究借助计算机一样,都将会产生革命性的结果,有着难以估量的意义。
以上从影视史学的出现说到了它对书写史学的挑战,涉及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然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从而无所畏惧地迎接来自现实的挑战,并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②b]倘此论不谬,在我看来,历史学不管是通过书写的方式,还是借助影像视觉的手段,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都是有其相通之处与共同点的。因此,无论是《红樱桃》还是《辛德勒名单》,与繁多的用书写形式的二战史作品一样,都可以唤起人们对往事的回忆,重新认识与评价历史,以作为现实的借鉴与走向未来的启示。
在此,有一点需要提出来讨论,即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所承载讯息的可靠性,或传达的真实性的问题。首先,这里有一个史学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弄清,历史作品(包括书写的历史著作与历史影视片)能否复原历史,亦即如19世纪法国大史学家米什列所说的,历史是过去的复活。此论实在是自欺欺人,即使有人真心这样想,也只可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梦幻。客观的历史是不能复原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或历史影视片所要反映的往事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两者之间永远是一条渐近线。影片《人约黄昏》的编导们,力求要“重视”30年代的上海,但它所表现的与30年代上海的实际,只能是一条渐近线。无怪乎一些批评家说当今重现旧上海题材的失误,批评张艺谋拍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虚假性,说:外婆桥?似乎没摇到。[①c]为什么电影艺术家花了那么多的心血,要“重现”旧上海的努力却遭到了如此的命运,看来制作者与影评家都要在这一点上取得共识,即:真正意义上的“重现”是不可能的。
况且,在这一点上,书写史学也具有同样的局限性。怀特说得好:“其实,任何历史作品不论是视觉或书写的,都无法将有意陈述的事件或场景,完完整整的或者其中的一大半传真出来;甚至于连历史上任何小事件也无法全盘重现。每件书写的和影视的历史作品都一样,必须经过浓缩、移位、象征、修饰的过程。”历史学家的努力只能接近这条渐近线,而永远不可能达到它。
毋庸置疑,历史影视片如《辛德勒名单》或有其真实原型的《红樱桃》等,当然会给虚构和想象留有广阔的天地。但问题是,制作者要表现某一时代的历史,就必须在占有大量材料与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地弄清影视片所要反映的特定时代的历史,乃至各种具体的细节。影片《红樱桃》的制作过程正是这样:叶大鹰在采访中,最初被中共后代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经历所感动,继而在参观俄罗斯的二战纪念馆时,又被馆中展列的人皮纹身图案所震惊,终于找到了演绎这动人心魄故事的切入点。叶大鹰导演说:在影片中,我表现的是我作为中国人心灵的真实,影片依据一个真实的背景,故事的所有细节都来自于真实的采访,所有的细节都有它蘸着血和泪的真实的依据,如影片中那位德国将军穿的制服就是一件真品。[②c]。
当然,我们说《红樱桃》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这种真实不是海市蜃楼式的幻影,而是蕴含在编导者所刻意营造与提炼的艺术真实之中。这并不是说,影片中所描述的人物与场景,是一种对生活原型的复制;恰恰相反,《红樱桃》所要表现的人物及其社会情境,都是典型化了的,它不是历史上的人与事的简单再现,而是编导赋予这一题材以新的艺术生命,从而创造出了高于历史原型的艺术典型,这也正是影视史学所特具魅力的地方。因而评论一部历史剧情片的真实性与虚假性,是看其在特定的时空中所表现的是否符合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亦即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倘能正确地被传达出来。并被观众所辨识和认可,这就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感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感。因而影视史学所追求的艺术真实性与书写史学所追求的历史真实性,在揭示与认识世界的本质及其真实性的问题上,是相一致的。其实,要求历史影视片完全逼真,就像影片《红樱桃》中要求所有德军都穿上当年的服装,这实在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总之,历史剧情片中的人物是可以也应当被典型化了的,它与历史上的人物原型是有区别的,这是不容混淆的两个概念。从影片《红樱桃》所营造的时代氛围、所刻划的典型人物、所展示的对战争与人性的共识,我们以为它都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3
从以上所述论的情况来看,史学变革的新时代确实来临了,影视史学这一新名词的正式出现及其传延,说明影视史学的时代也的确来临了。
影视史学是繁杂的史学大家族的新成员,这个新生儿如果从19世纪末电影发明之日起,迄今也不过一个世纪罢了。在电影发展史上的默片时代,它还不曾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历史学家开始正视影片与历史的关系,是到了二战后,确切地说,影视史学获得历史学家的注意是在60年代。此时,从普通民众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人物与解释历史事件的风气日浓,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在1966年发表《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①d]一文之后,“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便成了学界一个专用名词,并与传统的“自上而下看的历史学”亦即“精英史学”相抗衡。在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下,通过影视所传达的历史意念开始受到了专业史家的真正关注。特别是到了70年代下半叶,西方史学又发生了一次新的转向,这次转向基于这样的背景:战后西方新史学从50年代勃兴至70年代上半叶达到了它的全盛期。但正当新史学家高视阔步的时候,新史学也产生了某些流弊,如新史学家为了寻求“结构”与“深层”的历史,于是历史著作中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与环境气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见了,历史学变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②d];历史著作中充满的大量数学公式、数据、图表等,不仅在专业史家中鲜有反应,而且更失去了大众社会的广大的读者群。西方新史学家所崇尚的分析性的史学著作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于是从70年代下半叶开始,叙事性的史学著作又开始复兴,英国史家劳伦斯·斯通在1979年当叙事史兴起的时候,就撰文《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断言“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③d]不管斯通的见解是否有些片面,但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叙事体史书在整个80年代重又得到了历史学家的青睐。这一学术背景与时代氛围,对以叙述性为专长的影视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影视史学的勃兴,的确是与西方史学中重新复兴的叙事式的文化走向相呼应的,这里就牵涉到历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的这一历久不息的争论,克莱奥到底姓什么呢?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历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被由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矛盾困扰着,有人说,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也有人说,历史是艺术,一种只能凭想象才能成功的艺术,于是从近代,尤其是19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对此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辩,[④d]两种意见,各执一端。对这一与生俱来的关于历史学性质的争论,也许永远不会止息。不过,在我看来,以下一位历史学家对它的概括是很精彩的,也是可取的,他说的是:“理想的历史学,应该既有科学性,又有文学性;应该既作结构的分析,又作事件的叙述;应该既是总体的宏观研究,又是具体的微观研究,总之,应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完全的结合。”[⑤d]
对影视史学来说,它确实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摆在影视制作者面前是双重的工作:一是确立宗旨,寻觅主题,这是与历史学家历史研究过程中寻求真理与考证方法应具科学性属于同样的性质;另一是将主题通过影视手段表现出来,这一过程主要是艺术性的,它需要借助虚构与想象等艺术手段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与历史学家如何陈述往事有其相通之处。论者云,历史学不仅需要抽象思维,寻找规律,同时也需要形象思维,需要把活生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等跃然纸上,历史学的这一特点不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是不会改变的[⑥d]影视史学作为现代影视技术与古老的历史学科相交融、相嫁接的产物,它可以充当这两者(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的桥梁。当然,影视史学主要是以直观的艺术性的手法传达我们对历史的见解,但它也可以通过声音或旁白等手段来作出分析性的评述,它不应也没有必要排斥抽象的分析性的方法,因此主张影视史学并非必定要否定书写史学,两者应当互补而不是排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所指出的:“历史研究正朝着众多的方向发展……一度互不关联和易于驾驭的领域和问题彼此交融,失去了界限,层出不穷……各条道路纵横交错,各种身份难解难分,史学研究的范围日益深广”[①e],融合了影视与史学两者之长的影视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它的发展不正是对贝林之论所作出的一条最好注解吗?
由此再稍稍引发开去,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我以为,历史学大体可以分为“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②e]自古以来,“精英史学”为当权者所驾驭,如西方的传统史学着力要表现的是政治事件和显要人物,书写史学是为这一宗旨服务的;大众史学多以口舌相传的形式流行于坊间,以中国古代的大众史学而论,那些视觉感极强的画像、砖石、壁画、画册,那些声情并茂的俗讲、变文、词文、说话、鼓词和戏曲,那些富有影响力的口头传闻、话本、小说等等,都可以归列其中。[③e]在西方,自荷马时代以来的民间行吟歌手所保留的口述历史以及其他诸多的形式,也包涵了很丰富的大众史学的内容,在此不容详述。在这里,我需要说的是,目下西方学界流行的影视史学,正是大众史学在当代的一种最新表现。它们在史学的发展史上,不管是彼此对立还是互相渗透,就实现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与功能而言,则都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本义,其实,它们应当是并行不悖且应相互取长补短的。
当今中国大陆学界专业史家多不屑于承担大众史学的传播工作,而把它拱手让位于文学艺术家,不是有大陆五位颇负盛名的小说作家被武则天“一网打尽”,其中四位就是专为张艺谋执导的影片《武则天》而写作,这种大众史学的非史家化现象与史家的非大众史学化现象,我以为总是不正常的。书写史学家与其等待影片《武则天》上映后说三道四,批评它如何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还不如拿起你的笔,投身到影视史学这一史学的新领域中来,而不只是满足于充当“顾问”而已。影视史学确是很年轻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但我们相信,它将拥有广阔的前景与无限的生命力,在影视时代生长的一代又一代人需要这种新的学问,亦即那种在休闲娱乐之中传播历史故事及其所负载历史意念的新学科。的确,今天的历史学家需要用新的眼光、新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史学与影视之间的关系,促进它们的结合,促进影视史学的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未来社会中更充分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必将促进历史学家与历史学自身的变化,乃至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别开生面的新文化景观。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注释:
①a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5(December 1988),PP.1193-1199.
②a 周梁楷:《银幕中的历史因果关系:以〈谁杀了肯尼迪〉和〈返乡第二春〉为讨论对象》,载台湾《当代》月刊第74期(1992年6月)。
③a 载台湾《当代》月刊第96期(1994年4月),第47页。
①b 邦雄:《失衡的图像》,载《当代电视》第69期(1995年2月),第41页。
②b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①c 见陈思和《外婆桥?似乎没摇到——从一个失败的例子看旧上海题材的虚假性》,载《电影新作》1995年第5期。
②c 见叶大鹰关于《红樱桃》的后话,载《上海电视》(周刊),1995年第47期。
①d E·P·汤普逊:《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E.P.Thompson,History from Below),《时代杂志文学副刊》,1966年4月7日。
②d 法国当代史家勒·罗瓦·拉杜里语,转见《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0页。
③d 载《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85期(1979年11月)。
④d 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增订版,第43~51页。
⑤d 陈启能:《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⑥d 参见刘爽《历史学功能的动态结构——兼论历史学的科学性及其与艺术的关系》,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1月。
①e 载《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8页。
②e 对于历史学的这种分类,诸说不一,如有“应用历史学”与“基础历史学”之分,见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1986年;又有“通俗史学”与“正规史学”之分,见彭卫《中国古代通俗史学初探》,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历史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又有“通俗性史学”与“学术性史学”之分,见美国史家格尔达·勒纳《历史学的必要性与职业史学家》,载《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③e 见前引彭卫文,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