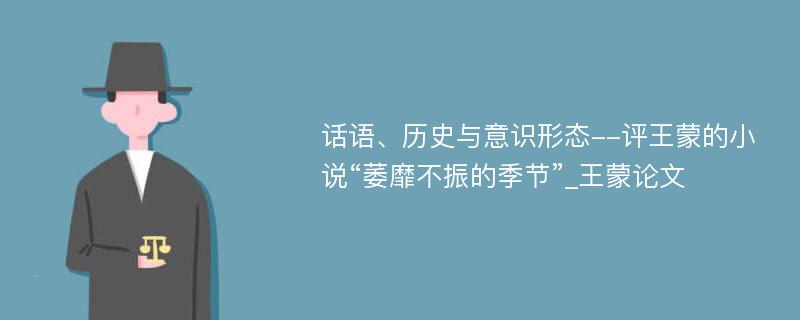
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评王蒙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失态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长篇小说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长篇小说,在《大家》创刊号上,作家王蒙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短篇小说是真正的艺术。长篇小说也是艺术,但尤其不是艺术,是非艺术,是人生,是历史,是阴阳金木水火土,是灵肉心肝脾胃肾,是宇宙万物。”这段话,无疑是具有丰富的长中短篇小说创作经验的王蒙的肺腑之言,是他在数十年创作生涯中悟到的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精粹之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段话语理解为王蒙基本的长篇小说观。在这样的前提下,解读王蒙的长篇新作《失态的季节》(载《当代》1994年第3期),我们即可对王蒙以上的论述产生更真切也更为直观的理解和顿悟,在笔者看来,《失态的季节》正是这样一部较全面完整地体现了王蒙的长篇小说观的具象文本,但是这个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王蒙在这部长篇的创作过程中忽视了艺术技巧的运用,忽视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层面,而是要强调地说明,虽然在这个文本中王蒙仍然在诸如作品的叙述结构叙述语言等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上有其匠心独运之处。但是支撑整部长篇成功的主要因素却是如王蒙所言的那些非艺术的东西。是作家对人生的独到而深刻的领悟与认识,是作家对历史所进行的细密的考察和深刻的观照与反思,是作家通过对钱文萧连甲们在“失态的季节”中的种种生态与心态的描摹和再现,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丧失的悲悯和对人类命运的体悟与探寻。
《失态的季节》是王蒙“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二部,是一部既与《恋爱的季节》有某种内在的情节与精神联系,同时却又相对独立成篇的长篇小说。如果说《恋爱的季节》是饱经人世沦桑后的王蒙对已拉开了相当时空距离的建国初期生活所作的极富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冷静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思想中所根深蒂固的一种“五十年代情结”的话(参见拙作《爱情、历史与“五十年代情绪”》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5期),那么《失态的季节》则是王蒙自己刻骨铭心的“右派”生活的一次充满理性与反思色彩的全面观照与审视,在其中凸现的乃是作家面对那段特殊生活经历时的一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以及处于九十年代这一历史语境中的作家对那段历史所进行的极为冷静的返顾与思考。应该说,对王蒙这一批“右派”作家而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突如其来的历史风暴是极难忘怀的。本来风华正茂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忽然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革命者就变成了反革命者,人生位置的前后反差之大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而“右派”分子下放农村后所饱尝的那种肉体和精神方面的非人遭遇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可以想见,这样一段奇特的凄惨的人生遭际肯定会在作家的内心深处留下很难愈合或者干脆就是不可能合的心理创伤。对于作家这一种特殊的职业者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段非人的经历遭际则可以被视为生活的一种馈赠,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题材来源,一个永远的表现对象。换言之,王蒙的这种奇特的人生体验乃是作家相当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自“文革”结束起始,迄今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了,其间表现“右派”生活的作家作品可谓多也,窃以为,其中影响最巨者当首推张贤亮与从维熙。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凤泪眼》等,均是新时期曾名噪一时的小说名作。然而,细究张贤亮从维熙的上述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浪漫化”倾向。所谓“浪漫化”倾向,乃指作家创作的本来意图是以真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展示那段惨痛的“右派”生活图景,但在具体的话语操作过程中,或许是由于作家无意识中的某种“自怜”“自视甚高”的情结的作用,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了人为的矫饰,对他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的拔高,这样做的结果就导致了主人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并进而减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与艺术表现力量。比如张贤亮的那位著名人物章永,虽然是一位落难的“右派”知识分子,但却总是能得到象马缨花、黄香久这样圣母般温柔可人的社会底层女子的倾心恋慕与真心爱抚,得到一种真诚的情爱补偿。这样的情节设计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公子落难,佳人相救”的文学原型的一种再现。
同样的道理,从维熙笔下被羁押在狱的葛翎为了扎制花圈悼念周总理,竟登梯攀墙摘玉兰花,终于被枪杀在墙下的英雄主义行为(《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索泓一如同章永磷一样的不断遭逢的艳遇,在笔者看来,都是具有明显的“浪漫化”倾向的情节设计。在对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的人生遭际进行人为矫饰的同时,张贤亮从维熙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些主人公们的精神境界进行了人为拔高。于是,身处逆境中的章水,便忧国忧民,反复研读《资本论》,便在潜意识里与孔子、马克思等先哲们进行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对话,便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潜隐心理期待着未来某一日在大会堂开会时发现的辉煌感。而身陷囹圄的葛翎则可以以赢弱的身躯迎拒老反革命分子马玉麟和流氓头子俞大龙的挑衅,以机敏和睿智同靠造反起家的“人狼”章龙喜巧妙周旋,凛然一副不失革命本色的老共产党员的崇高气概。窃以为,这样的情节设计乃是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的主人公的结果,同时也是作家意识中一种尚未彻底清除的“英雄主义”人物观作祟的结果。当张贤亮从维熙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上述“浪漫化”的倾向强行赋予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的时候,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处置方式必然会给他们自己的作品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损害。在笔者看来,这种损害首先表现为作品真实性的弱化,章永磷索泓一式的艳遇的出现,就使得本来冷酷凄惨无比的“右派”生活莫名地具备了某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莫明地笼罩上了一层美丽动人实质却虚幻至极的七彩光环,因而也就在无形之中淡化了作品的悲剧意义,弱化了对实在的“右派”生活的原生活进行艺术再现的真实程度。其次,这种损害还表现在对人物的思想与精神深度的挖掘上,当作家过份偏爱自己笔下的人物的时候,这种偏爱所导致的“偏见”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遮蔽作家的艺术视野,并对作品本来应具有的对人性历史的深层透视形成某种妨害。可以想见,王蒙对张贤亮从维熙等作家的“右派”小说所存在的上述“浪漫化”倾向是有所洞悉有所觉悟的,而且我们也不难在他自己的《布礼》、《蝴蝶》等涉及表现“右派”生活的小说中发现上述“浪漫化”痕迹的存在。王蒙不满足于在原有的基础上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他在竭力地寻找一种更恰切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自己立足于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对那段沉重历史的整合性的全面思考。笔者认为,《失态的季节》就是这样一部突破了“文革”结束以来所有“右派”小说创作模式的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完全打破了人为矫饰与拔高的那种“浪漫化”的表现方式,相当逼真地重现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原始风貌,重现了在那场历史风暴的突袭下,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失态”情形,在审判历史的同时也对这些知识分子内在精神世界进行了严厉的毫不容情的自审,因而在艺术表现的力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一个时期的“右派”小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失态的季节》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作家对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历史风暴所进行的历史性反思与艺术性表现的最高成就。
通过对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恋爱的季节》的解读,基本上可以确认,以艺术的方式书写“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展示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表现他们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乃是作家最主要的创作题旨所在。笔者认为《失态的季节》的艺术成就首先就体现在作家以戏拟性极强的叙述话语完成了对那段特殊的历史原貌的状态性重现,并在这重现历史原貌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失态”二字逼真传神地对身处当时历史语境中的“右派”知识分子们的生理与精神状态作了相当精妙准确的概括、把握与传达。在《失态的季节》中,我们不再能发现章永磷索泓一式的艳遇、葛翎式的斗争以及章永磷式深沉的哲理思考,充斥于全篇的首先是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面临历史风暴时的惶惑与恐惧,不解与张慌失措。(同时,也正是在对作品中人物的种种“失态”状态的呈现中,王蒙开台了他对人物的精神领域的深层挖掘,并在这挖掘的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并最终完成了对他笔下人物灵魂的不失严厉最后又宽怒了的拷问与自审)。他们本来刚刚从“恋爱的季节”中走出,本来还或者是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钱文),或者是满腹经纶指点江山的青年理论家(萧连甲),或者是颐指气使踌躇满志的某儿童文学刊物主编(郑仿)。但那场历史风暴的突袭,却无情地把他们卷出了都市,卷到了紧邻着繁华之地的穷乡僻壤——北京郊区的权家店,开始了漫长难熬的下放劳动与自我改造过程。而导致他们获罪的具体的原因都是些什么呢?对于钱文而言,是与儿童文学作家廖琼琼在欧美同学会一起吃了一次西餐,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被批判揭发过若干次,但在讨论是否把他定成“右派”时,当时的部门负责人陆洁生书记曾坚决不同意把他划成“右派”分子,但曲风明却以钱文吃西餐为证据坚持把他划成了“右派”,而“这件事对于他的命运所起的重大作用,直到二十二年以后,在一切都时过境迁之后,钱文才听说”。萧连甲获罪的原因是他不识时务地纠正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上的若干错字和错词。而郑仿则是因为他一直倡议组织一个儿童文学研究会被划成“右派”的:“他的组织儿童文学研究会的活动被定性为摆脱党的领导,企图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革命罪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钱文萧连甲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一种没有丝毫精神准备的情形下,被强行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成为“右派”分子下放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这些知识分子本能的反应自然只能是神经紧张惶恐不安,只能是生理与精神的“失态”了。于是钱文感觉到“雨声变成了怪笑,这笑声不便稀奇而且持续不断永无休止的可能”、“雨声不再象是笑了。雨声象是催促和呐喊。像是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哇啦哇啦哇啦,淅沥淅沥淅沥,滴答滴答滴答,斗啊斗啊斗啊,打啊打啊打啊……他简直无地自容,他在雨里。”雨声的听觉变异说明钱文内心深处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产生一种难以排解的极度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的进一步发展竟然导致了钱文生理上的短暂的“失语度”的发作:“发生了最惊人的事情:他失去了声音。他张开了嘴。他的嘴哆嗦,下巴哆嗦,眼睛乱眨磨。一点儿没有声音。”以到于事后许多年,“钱文回想起这件事仍然羞愧万分。他简直成了白痴。他究竟是要什么呢?他要向茶叶庄交代他自己也完全莫明其妙的问题么?……”而鲁若则“抓着自己的头发,他的脸上是一片空虚。这实在是最最可怕的面孔。不是损伤,不是疾病,不是恐惧也不是丑陋,而只是被彻底地抽走了灵魂的什么也没有……甚至死人的面孔都比这样的面孔正常和安宁。”至于萧连甲,当他最终折服于曲风明之后则“无法不感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强奸犯。他在终于板上钉钉地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从而从党内人民内部清洗出来以后,仍然念念不忘这个妙喻,见人就讲这个妙喻,”在如此“失态”的情形下,置身于历史洪流的裹挟中无力主宰自己命运无法看清历史真相的这些知识分子们剩下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只能由不自觉逐渐演变为自觉地开展对他人和对自己莫须有罪行的无休无止的反复批判与检讨。在这种强大异常的精神压力的逼迫下,这些“右派”知识分子们“觉得不知为什么此身非己有,此刻非己所有,快乐非己所有,转眼间只能有批判批判认罪认罪劳动劳动了。”久而久之,这样的一种检讨与批判竟然变成了他们的一种思维惯性与生存习性:“却原来,写揭发材料也是能上瘾的,居然写得痛快了起来,他(萧连甲)体验到一种批判别人整别人,硬是把别人分析成反革命的快感,咬牙切齿而又痛快淋漓。”多么瘆人的细节!多么可怕的人类本能的攻击欲望!由对这场政治运动所持的不理解与抗拒态度,一转而为对这场运动的接受,并且在对运动的参与中产生快感,这种变化就充分地说明这政治运动对钱文萧连甲这些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扭曲达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精神被扭曲的结果是进一步导致了在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自虐与更严重的他虐行为的出现,导致了受难者之间的种种令人惨不忍睹的互相倾轧互相欺辱的丑恶现象的产生。典型如这批“右派”中唯一的女性章婉婉,在钱文未到之前,她本来是这里的“右派”们当中处理最轻的一个,但没想到钱文比她还轻,竟然一级也没有降,对此现状她“好长时间如吃进了一只苍蝇”一样地难以忍受。于是她不仅反感钱文的诗人身分,而且反感钱文的日常行为举止,甚至于钱文与叶东菊夫妻频繁的通信也令她难以接受:“尤其是当她得知钱文是一个策划过刺杀毛主席的大特务的女儿之后,一股强烈的阶级仇恨更是倏地熊熊燃烧起来。她只觉得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便开始了对钱文不遗余力的攻击。但更使读者难以接受则是章婉婉令人发指的自虐行为,在她的丈夫秦经世也被揪出来之后,她居然残忍地“拒绝了秦经世与她享受夫妻生活的快乐的要求,她咬牙切齿地强调,帽子没有摘以前,什么都不要再想了。”更有甚者,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次休假机会的时候,“她主动要求来一个女干部搜查她的内衣内裤与私处,大家说这么早怎么可以去叫醒谁呢?于是她表示,不经过彻底的搜查她宁可放弃休假。”然而,具有他虐与自虐倾向的却不止是章婉婉一人,比如钱文也曾经在半夜里点起灯对自己进行大搜查,连自己的表他都难以断定“是不是自己的表呢?会不会洪嘉的表也是这个牌子这个型号的呢?他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这块表一定是他的而绝对不可能是洪嘉的呢?”人人自虐的结果是“右派”们的集体性自虐:“象《国际歌》里唱得那: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啊,如今是——一旦把我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当写到他们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情绪特别饱满时,叙述者产生这样的疑问:“真弄不明白他们是真心爱唱这首歌?是用高唱‘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来表示他们的低头认罪,向人民投降,向党缴械?是一唱就升华起来,只感受到了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豪情忘记了自己的可耻身份?抑或这也是一种奇特的发泄,一种自虐的痛快淋漓?”然而,无论自虐也罢,他虐也罢,这些“右派”知识分子最终是逃脱不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一种人生怪圈的制约,这是一个如同“第二十二条军规”一样不可超脱的人生怪圈,于是,钱文萧连甲们置身于这样的人生怪圈中就只能无奈地任自我的精神在沉沦下坠中挣扎了。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他们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在批判别人与批判自己时所操持的貌似强大实则空洞无物无具体所指的话语工具:“人们全都调动起语言的潜能,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刀我一剑,真是把费可犁千刀万剐了个体无完肤无地自容语无伦次丑态毕露稀哩哗啦散了架。”在此处,话语已经丧失了它本有的指涉功能,而仅仅成为作品中人物的一种近乎本能的生理反映,成为他们生存活动的基本表征之一。对于钱文萧连甲们而言,只要一参加批判会,那就意味着将这程式化了话语反复地重新操练一番,无论被批判者是杜冲,还是郑仿,亦或是其他别的什么人,话语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表达方式都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都只是在无实在意义的语言平面上所进行的平行滑动而已。本来,话语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有其具本所指关涉物的一种工具,表达语言的主体应该是具有个人独立自由意志的个体的人。换言之,应该是人说话,人借助话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不应该是话语自立于人这一主体之外,而借助于人实现它自身的目的。但《失态的季节》中的实际情形却是话语凌驾于人物之上,人物反而变成了话语实现其自身目的一种工具,总之一句话,作为抵达外在客体有效工具的话语异化了操持它的主体——人物,使人物反过来被异化为一种丧失了独立自由意志的工具。然而,当话语异化了操持它的主体——人物的时候,它自身也就陷入了某种空前被动的困境之中,而变成一种游戏活动:“(他们)得到语言撞击也得到了语言的游戏。在权家店这个偏僻又匮乏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批评会,应该说大家得到了某种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满足。”但是,不论文本中的话语对人物的异化达到了何种强烈的程度,它的真正的创造与操持者却也只能是作品的实际写作者,是作家王蒙,是王蒙以他卓尔超群的艺术智慧创作了《失态的季节》,制造了语言的迷宫,是他赋予自己小说中的叙述话语以巨大的功能去吞噬他笔下人物的主体精神的。
那么,王蒙为何要运用上述的叙事式来完成他的《失态的季节》这部长篇新作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分析解决的核心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王蒙之所以要设计运用这样的叙述话语来讲述钱文萧连甲这些“右派”知识分子的“失态”故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首先要通过这种戏仿性极强的叙述话语逼真地重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众所周知,建国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即是对上层建筑的超乎寻常的重视,却是社会表层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是指在政治冲突中统治阶级的一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回避不利于它统治的事实时所形成的对万事万物的看法。”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色彩的愈来愈强化,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到五十年代末反“右派”政治运动开始时,这种夸张强化意识形态领域内斗争的重要性已经强调到了一种很不适当的地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右派”斗争本身即是意识形态被空前强化的过程的一个必然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妨把当时的社会称之为“意识形态化了的中国社会。”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偏重于理论务虚,或者说偏重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话语力量的。因此,当时社会的一大根本性的表征就可以说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喧哗与杂陈。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逼真地重现当时的历史氛围,王蒙在写作时就必须通过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戏拟性模仿来达到对五六十年代之交时期社会状态的真实展示。正因为如此,解读《失态的季节》时,我们才会在作家似乎别具魔力的叙述话语的指示引领下,必领神会地进入那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与作品中的人物一道亲身体验一番那逝去已久的梦魔般的痛苦生活。我们认为,王蒙之所以没有象张贤亮从维熙那样出现明显的“浪漫化”倾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话语还原。与王蒙的话语还原相比较,张贤亮从维熙的叙述话语则很明显地带有八十年代的政治理性色彩,运用这样的叙述话语当然很难逼真地重现当时生活的原生状态。而当我们把意识形态话语的喧哗与杂陈理解为那段历史的根本性特征的时候,同时也就可以把王蒙小说中异化人物主体功能的那些戏拟性很强的话语理解为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某种象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失态的季节》中的叙述话语以其巨大的功能对人物主体精神的吞噬,就可以被理解为历史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对人性的一种扭曲与摧残。正是在“历史”主体以“话语”的名义对人性的这种扭曲摧残的过程中,我们才可以在文本中聆听到人性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一种根本性的冲突,才可以感觉到作家王蒙对他笔下诸人物的那种博大的悲悯心理的存在,才可以感觉到王蒙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以及对人类存在之谜深切的关注与探寻。
然而《失态的季节》中的叙述话语所承担的并不仅仅是逼真地重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氛围的功能。当我们把这种话语命名为戏仿话语的时候,同时也就暗示了上述叙述话语还具有另一个层面上的表现功能,这就是指它的反讽功能。所谓反讽,乃是多元视境下的产物,专指一种“在常规认识背景和框架中还显得合情合理的现象,一旦变更了认识背景和认识角度。原有的秩序中确定的因果联系会突然出现明显的悖逆和漏洞,正确的变为荒谬,神圣的变为可笑,反讽便由此诞生。”(见吴文薇《当代小说中的反讽》,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1期)反讽的第一种类型乃是言语反讽,主要是指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态度对照所形成的反讽,这一类言语反讽在《失态的季节》中几乎俯拾皆是,比如,当萧连甲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大家也应应付付地表了一下态。反正都说他死的不对,如果认为他死得好那还得了!为什么要死呢,形势一片大好愈来愈好,认真改造前途一片光明愈来愈光明。”在这段叙述话语中,我们即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言语反讽的存在。本来隐含作者(真实作者)如同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对萧连甲的自杀是充满同情与悲悯心理的,而且还不乏一种兔死狐悲式的伤感,但叙述者在叙述时偏偏采用了一种无动于衷的叙述态度,而且对萧连甲的自杀进行了一番貌似公正的评判,在这里,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态度的反差越大,我们便愈是从中读出与叙述者相反的意思来,文本也就愈具有反讽意味。另一类反讽则可称之为总体性情境反讽,这时小说的人物所面临的是那些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是一种不可摆脱的两难困境与人生怪圈。关于本文中人物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与人生怪圈的存在,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所涉略,比如交代不交代与面部标准表情的问题。这样一种两难困境乃是当时“右派”知识分子的普遍存在状况,在这个层次上反讽就具备了某种整体性象征特征。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而是针对一时代和某一情势下的整个的特定的现实……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反讽概念》)我们认为,《失态的季节》中的反讽就是指向历史时期的整个社会现实的。在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中,作家王蒙正是通过对具有极明显的反讽功能的戏仿性叙述话语的成功运用,完成了对那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并最终在重视那段沉重的历史的同时对那种以意识形态话语为基本表征的荒唐历史也进行了彻底的强有力的消解。到小说的结尾处,王蒙写到了历史对闵秀梅的残酷无情的捉弄,当作家不无戏谑的以“她哭什么呢?也许只是哭她的曾经乌黑的头发?”为这部长篇小说作结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能对这部作品的反讽性特征产生更为真切理解与认识么?
最后应该提到的是王蒙那种戏谑的充满伤感气息的然而同时却又是抒情的优美的叙述风度。窃以为,王蒙对语言的揣摸运用已经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阅读他的小说(当然包括《失态的季节》),首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乃是他那如庄子般行云流水汪洋恣肆的语言表现才能。且不说作品所具有的深刻题旨,仅仅浏览欣赏一下作品纯粹的语言外观,就可以给读者带来无穷无尽的美感享受审美愉悦。所惜篇幅有限,对王蒙小说语言风度的分析只能留待另文完成了。
标签:王蒙论文; 小说论文; 历史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张贤亮论文; 从维熙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萧连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