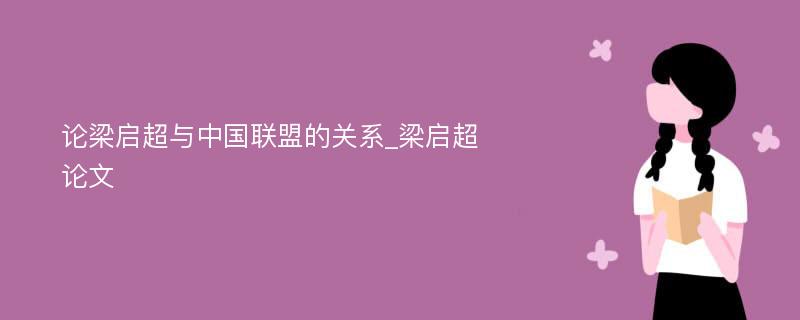
盟友与对手之间:梁启超与中国同盟会关系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同盟会论文,盟友论文,对手论文,关系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3—0080—06
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华民族危机的加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两种新兴势力:一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其政党组织为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晚年又改组为国民党。另一种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势力,“戊戌变法”前称维新派,变法失败后在海外组织起保皇会,后更名为国民宪政会。在一段时期内,同盟会所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与保皇会所开展的保皇、立宪活动并行于世、相伴而生。两者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同盟者,既彼此排斥又相互影响。同盟会的建立、发展和演变过程与保皇会领袖梁启超的保皇、立宪及民初政党政治活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过程,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作为同盟者,他们却各自选择了不同道路;作为政治对手,实际上双方又在不约而同地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共同对付封建主义,并试图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关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学界论述不多,本文拟就该问题作一探讨。
一、从尝试合作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相继亡命日本。在日期间,梁启超对变法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并阅读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及日人译注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著作,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及国家政治学说有更深刻的理解。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影响下,梁启超开始从保皇转向革命。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为孙中山与康、梁的接近与合作提供了契机。
对于康梁,孙中山曾满怀倾慕,一直希望同力救国。1892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借行医宣传革命时,曾向康有为表示过合作意愿,未果。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办农学会时,曾力邀康梁加入,又遭拒。后复请梁启超出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终未成功。变法失败后,当双方都成了“天涯沦落人”时,双方的接近与合作才出现新的转机。孙中山通过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平山周等前往康有为处表示合作意愿,康有为遂派陈少白、梁启超出席由孙中山安排的秘密会谈。梁启超对孙中山早有好感,孙中山更是引梁为“同志”,希图“同商大事”。① 于是两人“往还日密, 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固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② 拟推孙为会长,梁任副会长。梁还联合康门十三弟子起草《上南海先生书》,痛言清政府腐败至极,“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甚至明确劝乃师“息影林泉,自娱晚景”,③ 由他们出来做事。 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变化和与革命派联合的企图,自然有违康有为的意志和保皇会的宗旨,更与康氏所坚决主张的君主立宪政体背道而驰,且有忘恩负义、不忠不仁的“罪名”。当得知梁启超等弟子倡言革命、倾心共和的消息时,康有为先是痛责,继而婉劝,严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公开发表两封长信:《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意在说明中国不可行革命的理由。梁启超难违师命,遂于1899年12月31日抵达檀香山。至此,两派联合的努力功亏一篑。
梁启超的檀香山之行是保皇与革命两派关系变化的一个转折点。此行,对保皇、革命两派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这是因为梁不同于康,其“办事宗旨,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就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④ 在檀岛期间,梁启超依然徘徊在保皇与革命之间。在他自己看来,打着“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旗帜以争取华侨支持,他日与孙中山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
梁启超滞留檀香山长达半年。在这半年中,梁启超到处集会演讲,联络各界人士,筹款募捐,广大华侨仍踊跃捐资、慷慨解囊,使梁募集到近九万余元的捐款。更甚者,梁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使众多不明真相的兴中会员纷纷加入保皇会。由于梁的影响,檀岛“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之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⑤ 梁启超自己也说:“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中山旧党。”⑥ 檀岛效应波及港、澳、南洋,继之美、加,引发一股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样,兴中会在海外华侨中辛苦打下的基础眼见着被保皇会蚕食殆尽。是年夏,孙中山写信斥责梁启超背信弃义,谓之:“含(舍)革命复保皇,犹不足责;至遇保皇者而言保皇,遇革命者而又与言革命,以致遁为此名实反对之说,诘尔之宗旨安在?”⑦
“武装勤王”失败后,梁启超取道南洋,在澳大利亚呆了8个月,次年5月返回日本。所到之处,在当地华侨,尤其是华侨青年中,梁启超几成为崇拜的偶像。1902年元旦,《新民丛报》创刊。从《清议报》到《时务报》,数年间,梁启超以报纸为武器,积极宣传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译介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无情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和清廷的腐败、卖国行径,热情宣传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民主自由思想,其思想和言论对于国人的思想启蒙,对于推动维新运动的开展,唤醒国人的救亡意识,开启民智、维新民德等,产生了积极持久的影响。应当说,数年间,梁启超在启蒙和救国上的激进言行曾极大地冲击、启迪、洗礼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这正好弥补了孙中山革命党人的不足。当然,我们同时又不难发现,梁启超大倡“破坏”、“革命”,却不鼓吹“流血之破坏”即法国式的大革命,而是主张实行日本“不流血之破坏”的明治维新,这就表明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割舍与根除内心深处的改良主义思想。
为彻底划清革命反满与保皇臣清之界限以争取广大华侨,1903年至1904年兴中会与保皇会展开了激烈论战。1903年孙中山回到檀香山,首先将保皇派控制的机关报《大同日报》改为革命派党报,并发表了《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同时,大量散发邹容的《革命军》,在希炉和火奴鲁鲁连续召开大会,倡言革命,驳斥保皇谬论。为打败保皇派,孙中山由檀岛转往美国,到处演讲宣传革命,建议致公党进行“全美会员总注册”,制定《致公党重订新章要义》,改组致公党。孙中山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皇党梁贼在此之时,极为兴盛,今已渐渐冷淡矣”。⑧ 其他各地论战相继取得胜利,侨商纷纷倒戈, 与康有为和保皇会断交。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兴中会曾试图与梁启超合作,是因为“爱重其才”,并期望借其舆论先锋的力量助一臂之力。然而在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上思想上始终游离在革命与保皇之间,致使保皇会与兴中会力量此消彼长,兴中会组织曾几乎遭致瓦解。但正是通过与梁启超和保皇会的艰苦斗争,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革命纲领才逐步完善成熟,中华革命党和致公党都将誓辞更改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就为兴中会团结和领导其他革命团体,建立中国同盟会奠定了阶级、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与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
如果说《清议报》专事对清廷的批判,那么《新民丛报》则已转向大力传播民主、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观念,大量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梁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撰写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主义》、《论自由》等多篇脍炙人口的名著。《新民丛报》受社会之欢迎,连梁启超也感意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曾说:“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以前此《时务》,尚有过之无不及也。”⑨ 其影响之广, 仅国内就有97个发行点,遍布49个县市,即使在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人们也在争相传阅《新民丛报》。不少青年深受其影响,开始反思中国的现状,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客观上讲,梁启超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作好了一定的舆论准备,这种“种豆得瓜”的效应,也是梁启超始料未及的。
1905年8月,孙中山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 组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同盟会的诞生和成长为领导全国革命运动中心,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几乎与此同时,在190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也出现了一浪胜似一浪的要求实行资产阶级立宪的呼声。日俄战争结束,其结局引起朝野震惊和深思。几年前戊戌维新派未竟的变法要求和君主立宪的希望,此时又在中国的工商界、教育界和立宪强国派官僚的心中燃起,他们以为从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此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活跃起来,立宪团体纷纷出现。立宪派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力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在内外压力下,清政府被迫于1905年7月宣布“预备立宪”。次年9月,颁发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1905年以后,中国既出现了“革命风潮,一日千丈”的形势,同时又涌动着资产阶级立宪运动的热潮。听到仿行立宪的诏书发布消息,梁启超既欣喜若狂,又潸然感叹“今日局面,革命当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尽全力与之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⑩ 为此,康梁将“保皇会”更名为“国民宪政会”,以适应立宪活动的需要。梁启超又另组政闻社以“改造政府”,又派徐佛苏等人回国联合杨度、熊希龄等人着手组织政党。20世纪初的形势,把革命派与改良派推上了冰碳水火的位置。
梁启超等立宪派以《新民丛报》为擂台,孙中山等革命党以《民报》为阵地,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论战。双方论战的焦点在于: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民族革命);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政治革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社会革命)等等。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仅见的,其结果无论如何都将给清政府敲响丧钟。
通过《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激烈论战,孙中山和革命党批判和清除改良派君主立宪主义的影响,夺取了舆论先声,从前一切对清皇室、贵族及其政府不满或失望的人们,都或先或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汇集到全国性的反满革命的潮流中来,革命排满思想大受欢迎。当时身在国内求学的高一涵后来也回忆道:“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11) 梁启超论战之所以败,非败在其改良主张。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应当承认,“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两者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变革者,都属于社会革命派的范畴,都是资产阶级的勇敢的先驱。
这一时期,梁启超是立宪运动的灵魂,他为中国未来的国会所设计的建设蓝图,一直成为立宪派的梦想和行动的指南。但颟顸的清政府在千呼万唤中抛出的第一个责任内阁竟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一成立便宣布“干线铁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又把粤汉、川汉铁路利权卖给英、美、德、法的四国银行。其出卖民族利益、“劫收”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倒行逆施,在满汉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终于把立宪派推向了另一边。川、鄂、湘、粤四省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梁启超连发文章,一为四川民众保路作歌,再为声讨政府之罪,三为大清摧梏拉朽。其中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一文中,他明确地提出了推翻清政府的政治主张。
席卷全国的保路风潮果如梁启超预言的那样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梁启超开出的所谓立宪“良药”与政治实践,和革命党人的一次次武装暴动与牺牲,都在证明清末民初国内各派的政治诉求集中在两条道路两个前途上,在清王朝的丧钟敲响前都在试图作最后的一搏。但是,统治者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农民的自发反抗不足以倾覆清政府,立宪派不敢尝试以暴力夺取政权,官僚阶层更谈不上主动倡义,唯有革命党人,高张革命大旗,誓将倾覆清廷,创建民国,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主导力量。
三、既是政治对手又不约而同地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南北“和议”的方式而结束,清朝皇帝被逼退位,南北方形式上完成了“统一”。这样,“革命党人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而袁世凯却得到了临时大总统的‘名器’”。(12)
为防止袁世凯日后专制自为,孙中山在辞职前向临时参议院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奠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新总统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这些条件终不能阻止袁世凯反对民主、扼杀共和的行径。在孙中山和黄兴醉心办实业之后,宋教仁实际成为改组同盟会的主持者。他希望以同盟会为基础组织政党,夺取国会多数议席,组织责任内阁,钳制袁世凯权力,以防君主专制的变相复辟。1912年8月国民党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但全部党务工作实际上由宋教仁负责。
时事逼人,康有为梁启超该何去何从?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梁启超根据国内急遽变化的形势,立即制定出“和袁,尉革,逼满服汉”的行动方针。其目标就是要利用袁世凯的实力,抚慰南方革命党人,从而操纵局势,“乘此而建奇功”。这是一个顺应形势发展的策略转变,符合康、梁一派的实际。他们在海外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内始终没有立足之地,欲有所作为,还得利用袁世凯,笼络革命党,周旋于诸强之间。
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也有意拉笼梁启超,频频邀梁回国参政。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真出乎他的意料。(13)
从对手到联手,从相仇到相互利用,梁启超与袁世凯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过程。戊戌政变前他与袁世凯曾是变法的盟友,政变后是仇敌,这时又走到一起。同党友人罗惇曧评价说,梁之所以联络袁世凯,是使其不为我敌,反为我用。“吾党与之联合,当在不即不离之间,断无委身其中之道理”。(14) 而且,经过对袁世凯之解剖分析,梁启超虽也深知“其头脑与今世之国家观念绝对不能兼容”,但袁“确在中国有一种大势力,确为中国现时一大人物”,“有政治才能之人物”,如若尽力“补助之”,“将现今大势、政治公理灌输其脑中”,使袁脱胎换骨,成为一“开明君主”,替国家做些事情,即建设一“善而强”的中央政府,则国家将“更新百度”,立宪之梦也不远了。(15) 梁启超企图通过自己组织的进步党来组阁,用法律的途径帮助袁世凯逐步地把中国引入立宪政治的轨道,从而最终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
梁启超敏锐地认识到清末民初蔚然成风的政党政治已经转入相互竞争、互为角逐的态势。围绕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的召开,社会各种政团形成了四个较大的政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关于中国宪政“国权”与“民权”孰轻孰重孰先孰后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两大根本对立的阵营:一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原同盟会系统的激进派政党国民党。素有“议会迷”之称的宋教仁实际上成为党魁,政党的革命精神已大为减色,妥协性明显增强。但国民党始终积极主张和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公开标榜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其进步性自不待言。另一是以原立宪派为主、包括部分旧官僚、地方绅士及部分旧革命党人在内的保守派政党,强调国权,拥护政府,倡导渐进与改良,得到了袁世凯的鼎力支持和慷慨资助,其妥协性显而易见。
以党派斗争观察,两大阵营都希望结束专制,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然而保守派三党旗帜鲜明地维护总统制,国民党则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双方展开直接的较量与对抗在所难免。为了与国民党抗衡,1913年,梁启超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联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组成进步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则为九人理事之首。从政纲源泉来看,梁启超则为该党的精神领袖,进步党的大计方针无不依据梁启超的“国权主义”和政党政治主张,梁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党魁。
“二次革命”爆发后,进步党极力为袁世凯制造的宋案和违法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辩护,并支持袁发动战争,消灭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军事力量。1914年初,袁世凯相继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进步党开始有限度地抵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它首先要求袁世凯务于年内召集国会、以民选机关制定宪法和继续采用内阁制,并严厉谴责袁世凯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假总统政治之名,行独裁政治之实。它批驳袁世凯的尊孔复旧违背世界潮流和中国民心。它还坚决抵制袁世凯解散政党的阴谋。1915年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化以后,进步党发生严重分化。王印川等人公开声明赞成帝制,梁启超、蔡锷等人则联合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温和派和唐继尧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武力反对洪宪帝制。历史可鉴,进步党起了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
护国战争结束后,进步党分化为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案研究会及以孙洪伊为首的倾向国民党的韬园系。为了控制国会,昔日国会中的国民党与进步党积极筹组新政团,最后演变成国民党的“商榷系”(“丙辰俱乐部”、“客庐系”、“韬园系”三政团合并)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宪法案研究会”与“宪法研究同志会”合并),继续在国会中明争暗斗。
1917年,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问题,段祺瑞与黎元洪之间爆发了“府院之争”,康有为、张勋文武“二圣”便乘机又拥立溥仪复辟帝制。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毅然站在段祺瑞一边,梁启超不仅为段起草了讨伐张勋通电,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反对复辟电》。7月5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梁启超躬入段祺瑞军帐,任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赞。此时,孙中山也在上海召集同志,通电南下护法。12日,段所部攻入北京,辫子军溃不成军,慌作鸟兽散。讨伐张勋,维护民国,梁启超和研究系功不可没。
历史再次重演,梁启超随段归来,其研究系人在段新内阁中受到重用,九名阁员中就占了六席,从而达到了研究系参政的巅峰。梁启超与同仁采取“入阁主义”,旨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变成一党之专制恶果”。(16) 很显然,梁启超此番入阁,仍然与当年跟袁世凯携手合作的宗旨与目标毫无二致。可是,段祺瑞并不这么想,他公开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17) 他以“参战”之名,用大宗的借款组建所谓的“参战军”,步步扩大皖系势力,推行其反动的“武力统一”政策。段之倒行逆施遭到了国民党和南方各省的激烈反对,纷纷举起护法旗帜。中国随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军阀割据时代。
当然,历史不应忘记,在中国近代化的发展进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犹如两列奔驰的火车,虽然途径之所常常“杂于虎豹蛇蝎”之中,乘客们为求生时有互相水火,但从不曾逆转,向往着民主政治的站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失去政权之后进行的斗争。和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进行的斗争一样,都是在为整个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而斗争。而梁启超却总以一股救世的毅力和挥之不去的政治浪漫,一搏再搏。对一位曾经联袁拥袁、对袁一直抱有幻想和规劝之心的梁启超,树起反袁的旗帜,“敢为天下先”,无疑需要莫大的责任、勇气和胆魄。如其所言:“余确是老于亡命之经验家,然宁可亡命,也不愿苟活于此浊恶之空气中!”(18) “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命去干这一次不可!”(19) 对梁启超的爱国、 救国之精神与信念,后人不可不敬。
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革命进行下去,国民党得以新生。梁启超则全然身退,从此息影学林,遍释群经诸史,独步杏坛,春风桃李三千人。
梁启超与同盟会关系之嬗变,反映了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同时折射出具有爱国救国思想与理想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杂的政治革命形势面前做出的痛苦而又艰难的历史抉择。
收稿日期:2005—12—08
注释:
①⑧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240页。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32页。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⑤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3页。
⑥ 《梁任公先生年芦长编初稿》上册(油印本),1936年版,第124页。
⑦ 《民报》1900年8月2日,第5号。
⑨⑩(13)(14)(19)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2,391,651—653,589,721页。
(11)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
(12) 谢俊美:《上海南北和议与辛亥革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15)(1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14,143页。
(16) 《申报》1917年7月30日。
(17) 《民国大新闻报》1917年7月22日。
标签:梁启超论文; 康有为论文; 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袁世凯论文; 民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