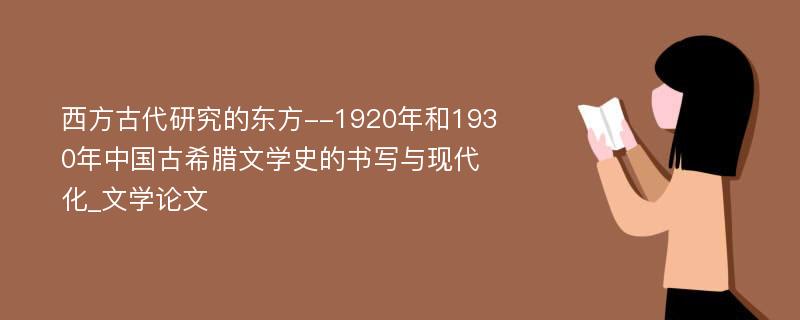
“西方古学”的东方面相——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古希腊文学史写作与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希腊论文,面相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1)-04-0100-13
在1920-1930年代中国人写作的西方文学史中,对古希腊文学的描述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部分。与普通的国别文学史不同,古希腊文学以其时代久远的神秘感和无可比拟的原创性成就凌驾于民族文学之上,成为欧洲文化共同体的源头性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它整合地代表了西方的“古典文学”。而对它的反应,也能镜像式地折射出国人在面对异质文明时的根本态度。古希腊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是“西方的”和“古典的”(非现代的),这意味着关注和研究希腊文学,虽然可以树立言说者在西方文学方面的权威地位,但在急于融入欧美主导的现代性社会秩序的五四知识分子那里,又是一件很难赢得掌声的事情。另一方面,研究者又反而有可能获得一个分离与差异化的视角,对文学现代性保持一定的反思与批判距离。
本文将主要以这个时期中国人写的两部以希腊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作为研究对象,即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吴宓的《希腊文学史》。① 在现代中国,古希腊文学生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学科是学者个人阐释的结果,1920-193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激变年代,文学的“观念”还未被一统化,我们不难从当时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中找到浓厚的原创性和个人立场,这些立场从根本上都基于研究者对本土问题的灵活参与意识。在不断的转述中,“希腊”这一对象变成了不同层面上现代性理念的表意工具。而对古希腊文学史写作观念中所蕴涵的多重意向的分析,使我们在象征层面上介入了西方古典文学是如何被本土化为中国现代性方案这一问题。
一、“文艺复兴”与现代西方文明危机
周作人、吴宓等人重视古希腊文学,与他们心目中对“古典文化”的感情支持密不可分。希腊文明之所以在五四时期获得特殊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其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古学”的大盛给了中国知识分子无限遐想的空间,类比之下,他们觉得古典文化完全有可能被激活后重返现代生活。在中国,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发展了一种尖锐的对比性的论式,通过文明等级的划分,将“古学”强化为应然的。而希腊之后的欧洲文学史,就是一部希腊之美的精神如何与其对立面作斗争的历史。
周作人称中世纪时为黑暗时代,“非复希腊罗马时哲学,能研求真理者之比矣”[1:113]。吴宓也在对清华学生的谈话中说:“此时,西洋文明之弊病,已传染及于吾国。欲医西洋传来之病,只好用西洋药。古典精神,即西洋药也。”[2]正是在这些对比论式中,西方现代文明的内在危机被暴露出来,希腊“古学”作为西方文明内部的他者,迫使一直以学习西方为要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回答下述两个问题:首先是如何避免西洋文明造成的泛滥无节制的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和对自然的索取?其次是这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说,这一论式是和对西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密切相关的。
在这个思考背景下,中国出现了“文艺复兴”话语,中国知识界论及“文艺复兴”并不始自周、吴等人,1905年创刊的《国粹学报》就有邓实将周秦诸子和希腊学派作并列比较。② 梁启超、章太炎都提及过“古学复兴”,后更有胡适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集《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正如罗志田指出的,此时的“复兴”更多带有“面向未来”而非“温故知新”的倾向。③ 至1920-1930年代,“文艺复兴”之说重又被提起,而且不再是泛化的理想,也有具体的内容填实,其指向也更带“温故知新”意味。在建构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吴宓和周作人虽然同样求诸于希腊,寄希望于“复兴”,但二者对文化价值秩序的设计却是不同的。吴宓试图将现代民族重新纳入到文化的大传统(儒教)中,但是儒教显然不可能为处在多元世界格局中的国家和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提供一个被广泛接纳的统一叙事。为解决“古学”的现代性问题,吴宓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首先,他效法其师白璧德,将不同文化的精英分子(孔子、亚里斯多德、佛陀、耶稣)跨时空地聚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抽象的精神道德共同体,这一超文明的世界主义语境使“传统”超越了狭隘民族性,对于身处多元世界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吴宓又否认这一道德共同体的宗教性质,认为其建基于个人的道德良知之上,“以自我之方法,表阐人类公性之精华”[3],而非外在的教理,形成所谓“完美的个人主义”,通过这样的意涵转化,便能与现代个人社会相契合。
较之吴宓,周作人并不泛化地谈论整体文化,他重视的是具有“个体的和包罗万象的感受”(巴赫金语)的“异教思想”,以及民间文学等与主流道德相悖的小传统。他在《欧洲文学史》中说:
中古时希伯来思想,虽凌驾一切,而异教精神(Paganism),出于本能,蕴蓄于人心者,亦终不因之中绝。一与事会,娵复萌发……游学之士(Clerici Vagi),身在教会,而所作浪游之歌(Carmina Vagarum),则纵情诗酒,多侧艳之辞,殆纯为异教思想。及东罗马亡,古学西行,于是向者久伏思逞之人心,乃借古代文明,悉发其蕴,则所谓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也[1:144]。
周作人认为文艺复兴是恢复古希腊的“尚美主情”的自由心性,落脚点始终是放在被普遍道德伦理压抑的感性生命体验之上,是作为“记忆”被主流价值压抑的“侧艳之辞”。这不仅可以创造性地阐释现代非神性的世俗民本社会,而且通过发掘文艺复兴这一精神资源,能想象性地获得复数的而非单一的、包容的而非权威的民族文化内涵。
作为和启蒙相辅相成却又显然有不同言说维度的语式,“文艺复兴”之所以在1920-1930年代的中国被强调,其中包含了双重动机:一方面,作为相对抽象的希腊“美之精神”的历史性展开,将原先只在模糊的古代空间中存在、几乎与“现代”无涉的希腊文明转换为时间上的绵延存在——后人并不仅仅生活在自己的语境里,传统对它们而言仍然可以成为内在的能动力量;反过来说也一样,传统在不同的历史世界中不断变化,唯有落实在当下才能得到理解,这对面临传统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中国无疑是可资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依靠文字的深层感召力促成社会的变革,这种焦灼的危机意识制约了知识分子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他们没有闲暇去慢慢检讨遇到的每种思想体系的文化内涵。而希腊文学的“爱美”、“中和”、“现世”等特质,更多地指向以个体精神状态为中心的人文世界,将长期受冷落的希腊文学纳入视野,也可视为中国现代性方案的自我调整。
二、《希腊文学史》:科学方法的道德视野
对于吴宓而言,对希腊的接受始终是附着在对中国的历史处境的思考上来进行的。事实上,他的问题意识来自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各国,应该采取何种文化模式才能确保族群的生存。当道德问题与救亡保种的命令联结起来之后,文化类型的选择就负载了巨大的使命。之所以求于希腊文明,是因为一方面希腊文明中的某些成分(主要是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主义和知识论)对培养中国现代国民的道德品格大有裨益,且和“中国国粹相近”,能增加对本土文明的信心;另一方面,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连同其优点与弊端,都可以在希腊文明中找到渊源,“单就研究希腊文学史而论亦为各种文学史之根本,故研究希腊历史实可以作全史之借鉴与参考。”[2]
出于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立场,吴宓对现代社会亵玩经典持批判态度,在一种要回到更高级文明的责任感的驱使下,他特别注重学理本身的完善和内部的严密性,这为他的文学史提供了一种科学化的现场感。或许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在举国皆言西学而实际只知道“问题戏剧”、“写实主义”等“西洋之疮痂狗粪”[4:152]之时,西学的真知却隐遁无踪。他提出要窥得文学创造的门径,要做到对传统毫无错讹的理解,为此付出的艰苦的科学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即“(一)宜虚心;(二)宜时时苦心练习;(三)宜遍习各种文体,而后专精一、二种;(四)宜从摹仿入手。作文者所必经历的之三阶级:一曰摹仿,二曰融化,三曰创造。由一至二,由二至三,无能逾越者也……”[5]等一系列的适当途径。他在《希腊文学史》的“附识”中系统阐发了他的文学史写作观念:
文学史之于文学也,犹地图之于地理也,必先知山川之大势,疆域之区画,然后一城一镇之关系可得而言。必先读文学史,而后作者、书、诗、文之旨意及其优劣可得而论。故吾人研究西洋文学,当以读欧洲各国文学史为入手之第一步。此不容疑者也。近年国人盛谈西洋文学,然皆零星片段之工夫,无先事统观全局之意。故于其所介绍者,则推尊至极,不免轻重倒置,得失淆乱,拉杂纷纭,茫无头绪。而读书之人,不曰我只欲知浪漫派之作品,则曰我只欲读小说,其他则不愿闻之,而不知如此从事,不惟得小失大,抑且事倍功半,殊可惜也。欲救此弊,则宜速编著欧洲文学史[6]。
吴宓认为研究文学史必须要有“博学”、“通识”、“辨体”、“均材”、“确评”五种资格,这五种资格无一不指向文本意义的永恒不变。《希腊文学史》中“附识”的用辞充满了“标准”、“真知”等断语:“凡欲述一国之文学史,必须先将此国此时代之文学典籍,悉行读过。而关于此国此时代之政教风俗、典章制度等之记述,亦须浏览涉猎,真知灼见,了然于胸,然后下笔始不同捕风捉影、向壁虚造也”,“凡文学史于一人一书一事,皆须下论断。此其论断之词。必审慎精确,公平允当,决不可以一己之爱憎为褒贬。且论一人一书一事,须著其精神而揭其要旨。”[6]他理想中的文学史写作,是无可更改的“唯一”文学史。
树立如此高的目标,导致他的《希腊文学史》只写了荷马和希霄德,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实在无法做到像他那样详尽考证和深入讨论。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的讲演中说:“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7:174],他的诸多论述确实有科学主义背景。他写到荷马时,不厌其烦地列举“晚近学者研究之结果”,并对每一说法甄别考订,引述历代权威学者对史诗的从语言、结构到观念的评论,最后还要与中国文学中的三国演义、封神榜、弹词等作比较。至少在理论上,吴宓希望他的文学史在形式上,从总体观念到细枝末节,包容描述对象的全部风貌。
然而,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并未让他像胡适或顾颉刚那样走向疑古,吴宓从未满足于将文学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说清即可,而是力图证明,科学方法的目的恰恰是要揭示出传统的源头性价值,他毫不怀疑那些考证和事实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合理秩序。文学史用科学实证成分摒弃各种不实之词(如对荷马和希霄德进行诗歌竞赛的辩驳),同时又保留了形而上学的需求。这一双重化的要求使其论述看起来有些自我抵牾,但是在吴宓那里却并不成为问题。吴宓的逻辑是,科学的工具性和科学的精神态度是区别开的,要是只注重具体学科知识问题,就会成为毫无关怀、琐碎无聊的“考据家”,而科学精神则连接着人的心灵,科学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全面周密地认识问题提供了基本条件,它的终极指向一定是发现作为智慧之源的价值秩序。一旦秩序树立起来,我们就可以不被那些故作惊人之语的外道邪说蛊惑。他提及的作为科学精神对立面的“粗浅”、“谬误”、“眩惑”、“模糊”、“舍本逐末”等等,显然同时又是道德上的精神疾病。这就意味着,吴宓“科学方法”范畴中蕴含了强烈的非物质向度,抽象为一种精神。他的《希腊文学史》中所有的实证成分涉及的都不仅是认知的问题,更是他形而上学体系的一种佐证,他总是从这些科学论述中寻找他需要的东西。
吴宓花大段篇幅讨论了“荷马问题”,即历来研究者对荷马是否确为史诗作者的怀疑,如德人拉赫曼(karl Lachmann)将《伊利亚特》切分为18篇短歌,认为是一些彼此无联系的作者不同时期所作,后人汇集这些散乱的断章而成整体。但在广泛引述拉赫曼及武鲁夫、哈曼、尼采、Robert Wood等人的疑古言论之前,他就宣判了这些言论的死刑:
推此问题之所由起,盖因十八世纪之末及十九世纪之上半叶,为浪漫主义大行之时。时人结鹜为新奇,喜为不经之论,一反前人成案,藉此为鸣高。又溺为天才Original Genius之说,谓凡惨淡经营、完整精密之说,必非佳品……此乃当时之风气,而以此施之荷马,异说遂生。至十九世纪中,人多用所谓科学方法者治文学,遂常不免割裂挑剔,破碎支离,及吹毛求疵,强作解事之病。且言语文字之学发达。治荷马者,肆为寻章摘句,以一声一字之微,遽断荷马史诗此段与彼段为一人之作,而某句与某节则另出一人之手,繁分缕析,不可究诘。故各家之说,及其争辩之陈迹,若详述之,徒乱人意,无多裨益[8]。
吴宓表示,相比“新派”,自己更愿意附和“旧派”如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布查(S.H.Butcher)的言论,要是荷马史诗真是出自多人之手的话,又怎样解释“全书结构完整细密”、“有一种特殊之精神之感情弥漫全书,前后浑然一致”[8]这些问题呢?如果一口气读下来,会趋向旧说,要是纠缠枝节,会趋向新说,此乃方法问题;诗人文士会趋向旧说,而考据家会趋向新说,此乃人性问题。
要是仅仅对西方文学的具体流派和作家感兴趣,吴宓也许会写出一本类似于王力的《希腊文学》的文学史,但他重视的显然不仅是具体的文学史知识,而且是这些知识能否通向某种合理的道德体验。在这方面,他将对西方文学的意义申说内在地转换成了中国传统的“诗教”观。一种基于教化的、精神性的东西笼罩了吴宓,较之不带偏见的具体知识,对于文学的精神品质的考虑显得更为重要。由此看来,吴宓将荷马史诗置于预设的道德秩序中理解,也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引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荷马史诗的道德观念的评价说,荷马史诗写家室骨肉之亲,合群奉公之义,善恶得其正报。敬神重祀,尊古崇法,若无节制将受到神的惩罚。正是这种内含的伦理使之有巨大的影响力,从而为人们提供价值与意义的源泉以及行为准则。
三、《欧洲文学史》:“杂”的趣味
在诸种希腊文学史中,茅盾的《希腊文学ABC》最具现代化的“文学史”样式。茅盾的文学分期,注重体制的统一和时间的接续,这一充满逻辑性的规范化文学史写作法,对后代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希腊文学被预设为准备期、高峰期和衰落期,好像荷马前后时代的所有元素都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伟大的雅典文学做铺垫,而在希腊文学的鼎盛之时,一些微小的变化又预示了必然的衰亡。作品的特定风格和具体文学派别的流变都暗示着更大的单位——阶段和时期——的变迁。在这个进程中,文学史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个别的细胞和整体的质量相互依赖,茅盾将那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个别作品联系成整体性的逻辑单位,并且只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个人的创作才能被赋予意义。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文学史沿着“时代、民族精神和写实性”[9:47]的本质主义道路走向了具体化和客观化。
现代文学史叙事中对“必然性”的要求,习惯于将一时期文学中的文学现象联接为互为象征的系统,并显示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这不言而喻地会产生压迫性的叙事者,使读者置于被传道和训谕的位置。周作人一直对西方文论中文学的“超功利”之说感兴趣,并据此批评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自觉不自觉地,他对有可能“载道”的圣贤之书或宏大文类,始终有抵触的态度。在《灯下读书论》中他引用英国陀生的话说:“希腊国民看到许多哲学者的升降,但总是只抓住他们世袭的宗教。柏拉图与亚利士多德,什诺与伊壁鸠鲁的学说,在希腊人民上面,正如没有这一回事一般。但是荷马与以前时代的多神教却是活着。”[10:36]具体到《欧洲文学史》,里面虽然写了史诗、悲剧和哲学等后世公认的希腊文学的最主要成就,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写了各式各样琐碎的“杂”文体,如拟曲、牧歌和讽刺对话等,周作人日后对这些很难进入现代文学史的文学形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谈到拟曲时说:
Mimos亦云Mimiambos,今称拟曲。源盖出于宗教仪式,与喜剧同……然后世则列之玩物,失其本意矣。Mimos初盖类于巫师,后渐转变,止存模拟之动作。更无祈求之意,遂流为诙谐戏谑……由是herodas始复闻于世。其曲皆用跛体(Kholiambos),故文辞不能与Theokritis比美,而实写人生,至极微妙。第一章之媒媪,第三章之塾师,皆跃跃有生气,虽相去二千余年,而读其文者,乃觉今古人情相去不远[1:44-45]。
周作人特别看重拟曲的原因有二:1,虽然拟曲在起源上含有宗教目的,不过随后就变成了无目的的“玩物”,只剩下了“诙谐戏谑”——这恰恰是周作人认为可贵的琐屑之事。透过拟曲的戏谑,我们看到的只是普通人物平常的欢愉和苦恼,也即他反复强调的“人情”。2,他喜欢拟曲和他对中国的游戏文章、日本的俳文,乃至英国的essay的兴趣一脉相承,这些文学样式都是“俗中不失雅”,且“要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去办差”[11:428]。值得注意的是,“自己的话”其实并非口语,而是有“蕴藉而诙诡的趣味”的“美文”。美文中的语言从根本上说是书面语,只是打上了个人风格的印记,亦即周作人说的“趣味”。趣味这个词在周作人那里有丰富的涵义,多与幽默、反讽等考究的文字表达有关。“在去伪存真中运用所有真正所具的个人价值,是‘趣味’的根本主张,换一句话说,‘趣味’是个性的延展。”[12:84]拟曲的好处,也因为其在文字表达上能引起人特别的兴致:
第十五章名Adonizusai记二中流妇人至亚历山大府观Adonis之祭,诙谐美妙,两至其极,为拟曲杰作,法国至演为剧。尤最者为第二章,Simaitha见弃于Delphis,因对月诃禁,招其故欢。文真而美,悲哀而诙诡,深入人心,令不能忘也[1:43-44]。
除了拟曲作家,《欧洲文学史》里说到其他作家时也强调了他们在文体和结构上的表现,“Theoktitos(315-270 B.C.)亦撰诗铭十三章,然以牧歌(Eidyllion)著闻……唯所歌亦不尽关牧事,因称Eidyllia为小图画。描写物色,以及人事,诗中有画,论者或以是与浮世绘(Genre)相比。”[1:43]这种对语言的执着使美文成为不透明的记号,而非“道”的直接载体,借用柄谷行人的话,即是对现代文学“声音中心主义”的无意识抵制。
要是从文类角度来分析《欧洲文学史》的话,书中的“希腊文学”部分均按文体分类,计10章:1,起源;2,史诗;3,歌;4,悲剧;5,喜剧;6,文;7,哲学;8,杂诗歌;9,杂文;10,结论。周作人对自己这部著作评价是:“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13:333]话虽如此,周作人个人的文化理念和趣味仍然在这部书稿中得到凸显。他说自己的文学史是“杂合”、“杂凑”的,但私心里他自己未必觉得这一定是缺点,“杂”意味着趣味的广泛和不拘一格,不轻易将文学史现象归入到事先划定的“现代”文学史叙事陈套中去。
“诗歌”被分为“歌”和“杂诗歌”,散文被分为“文”、“哲学”和“杂文”,这是周作人独创的分类法。在茅盾的《希腊文学ABC》中,他主张文类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所以诗歌的历程是:荷马时代及之前的短歌、婚歌、哀歌、凯歌→共和政体建立后的挽歌、讽刺诗、墓铭、谐歌和抒情诗→诗歌时代衰落和散文时代到来(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但到了周作人那里,上述文学类型的时代性却不会固定于一处,而是循环往复地流动着。例如,他对“歌”和“杂诗歌”的区分,第一卷第三章“歌”包含了挽歌、讽刺诗和抒情诗,而第一卷第八章“杂诗歌”的特质是:
三世纪后,希腊诗歌,更无巨制。时世变易,亦不复有英雄盛事。是供赞颂,人人所见,止现实之人世。若过去之光荣,早成幻景。故史诗凯歌,遂绝嗣响焉。Apollonius作Argonautika,虽独庚坠绪,而不为世所赏。盛行于世者,乃为短歌(Elegos)与诗铭(Epigramma)。二者起源本古,至是弥益发达,臻于美善,为后世模范[1:42-44]。
从周作人的叙述看来,似乎写“现实之人世”、以俗语写人情之常是杂诗歌的不同之处。不过说到俗语,“歌”中的讽刺诗就是“诙谐调笑之诗,其体近于常言”,并非杂诗歌所独有。实际上,这里的“短歌”即第三章说的“挽歌”,两者均是“Elegos”,诗铭就是墓铭,也是古已有之。所以没有办法说是文体发生了新老更替的进步;很多时候看上去完全不一样的文类不过是同一种类型发生了丰富的变化造成的。“歌”中的各个类型和“杂诗歌”中的各个类型既有区别,又紧密地联系,甚至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混杂在一起。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里对“诗歌”和“散文”等常见文学类型的定义总给人不清晰的感觉,是因为他不像茅盾那样将时代和某种代表性的文类挂钩,周作人关注的不是文体在形式上的统一和时间上的接续,而是空间的展开和风格的多样。
对于“文”也是如此,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里写了各种各样的散文,如在“文”中有历史、演说词,在“哲学”中有哲学论文,“杂文”中有学术著作、历史、地志、小说等,但到底什么是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呢?周作人似乎并不觉得这是重要的问题。或者说,这里并没有对散文究竟为何的本质化规定,它是在各种类型的关系之间被呈现出来的。作品总是具体而微的,很难将其完美地归纳为一个类型之中。如“杂文”章提到的Kebes,同柏拉图一样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其人“仿Platon作答问三章。其一曰《图册》(Pinax),言游Kronos庙,睹一木榜,上有画图,莫详其谊,有老者为之解说,盖以行道喻人生。”[1:50]柏拉图的论著是“哲学”,而Kebes仍可视为哲学问答录的作品为什么却是“杂文”呢?其区别之细微,普通读者恐怕难以省察。柏拉图的哲学也同样不是纯粹的——“年二十,始从Socrates游,前后八年。以问答体作文八篇,然非以讲学,盖拟曲(Mimos)之一类。”[1:41]此外,周作人没有将小说看成独立的形式,而是归入杂文,这是敏锐地看到了当时的小说不是独立发展的,“其初多述古人逸事,借作谈助,与故事(Logoi)同。后或渐改面目,凭空造作,不必实指其人,遂由别史而成小说。盖小说缘起,在于神话,始乃教典。转为传说,言英雄事迹,诵之可知史诗,亦可以供娱乐。后信念渐移,则化为童话(Marchen)。”[1:50-51]周作人列出一些小说,如Lukianos(琉善)的《信史》,指出这类小说与混合了哲学对话和喜剧的文体有强烈的姻亲关系,同时还借鉴了希罗多德体裁。这种不追求清晰明了、不把复杂的文学个体化约为简单的概念符号、较大程度地还原其文学史本相的做法,是周作人博雅的见识和注重个人体验的文学观念决定的。
四、“美”的形而上学神话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无情批判遗产中的古典趣味为前提的,所以重建趣味的工作就不可能直接用本土资源说明本土资源,而必须采用迂回的方式。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许多人在情感上认同历史中形成的人文传统,而在理智上又认可西方的价值观。这一历史与价值的悖论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危机”。将西方的人文传统打捞出来,展示这种价值的超时空特质,以增强对待自己的传统文明时的自信力,是缓解认同危机可以想象到的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希腊的“美”的形而上学在中国语境中的历史性展开加以论说。
在周作人等人对希腊文学的界定中,“美”几乎成为一种先天的文明理想,其作为西方“古学”的基本特质具有价值源泉、伦理法则和艺术风格的多重含义,是纷纭变化的文学史中最终要复兴的东西。《欧洲文学史》中第一卷“希腊文学”的“结论”部分说:“英国Fredrick Robertson论希腊思想,立四要义,曰:一无闲之奋斗,二现世主义,三美之崇拜,四人神之崇拜。今得合之为二,曰美之宗教,曰现世思想。”[1:55]后来他又加上一条“中和之性”作为希腊民族的“第三性”,“盖其民族具中和之性,以放逸为大戒。行藏无不准此,因亦见于艺文。故其文学,有悲哀恐怖之情,而无凶残之景。”[1:56-57]
周作人树立的“现世”、“爱美”与“中和”的精神贯穿了希腊在中国的形象。其实,这三种精神有其内在一致,就是对超越功利追求的“美”的向往。因为“现世”的范畴并非表面看起来的世俗生活,而是想象中的生活状态——“希腊人有一种热烈的求生的欲望。它不是只求苟延残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充实的生活”;“中和”也不仅是行为方式,还可被视为美学形式上的标准——“其在美术,尤以安闲著称。如雕刻之像,多静而少动。即表动作,亦至微末,多将事而非既事,皆足以见一斑”[14:10]。进一步说,希腊文学之“美”作为周作人创作体系中的一个源初象征,经过他想象性地展开,就不能仅被看作是审美主义的感性体验,而至少包括了三层含义:其一,它是“无目的”的“艺术”,只是一种“满足要求”的结果,成为了宗教与社会运动平行的另外一极,对于处于现实重压下的中国人有“祓除”之效;再次,这一“美”的追求也可以被理解成关乎伦理道德的人生态度,它和传统中国人“植物性”一般的好吃懒做有着截然的区别,是积极的、充满个性的;最后,“美”是文明进化的结果,将古代传递下来的丑陋分子逐渐美化,使之能符合理想。他举Gorgon为例,最初的形象十分狰狞,但经过美化之后,面目变得可爱,作成了悲痛的女人的像。所以,美“于文化进化至有关系”[15:64]。
在周作人这里,对希腊文学的推崇已经超越了他个人的兴趣,被强化为一种理想范型,也是文学进化的鹄的。或者说,他对文学根本概念,就是依附在希腊这个对象上表达的。希腊文学非常符合他对“文学”本身的定义,即“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的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16:2]如此一来,“希腊”从它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被剥离了出来,成为了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公式。在这点上,周作人充分显示了他对待希腊文学浪漫主义式的价值态度,他将这些文明秉性放在希腊文学的“结论”部分加以申说,起到的效果是将希腊文学整体浪漫化。在这一极端理想主义的背景下,甚至中国文学也需要由希腊来定义。例如,在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说到文学起源的问题时他援引希腊文学来维护自己的观点:“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以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便可以知道其他一切。”[16:11]明显地将希腊文学作普泛化的处理。
周作人的浪漫观点在国内学人之间不乏共识。吴宓的《希腊文学史》显示出充沛的人文气质:“希腊人富美术之心,故其所造作之神多美丽之形,美丽之意。他教之神,多牛鬼蛇神,奇丑凶怪,其来则飞砂走石,食肉吮血,又于地狱中刀山剑树逞其刑威。希腊之神,如此类者,绝无仅有。”[8]王力的《希腊文学》中的说法也有样学样:“希腊人的特点在乎善于欣赏美丽的形式,尤其是欣赏人体美。当他们离开了亚洲之后,他们就渐渐把他们的神形成了美男子或美女子。”[17:12]缪凤林《希腊之精神》认为希腊精神分为四种:“入世”、“谐和”、“中节”和“理智”,除了“理智”之外,基本就是周作人说法的翻版。
中国知识分子将“美”的文学理想投射于其中,使希腊文学成为一个超级能指符码。这一操作方式,一方面自然是秉承了温克尔曼(J.J.Winckelmann)和罗伯逊(Fredrick Robertson)等西方学者对希腊的理想化言说趋向;另一方面,希腊文学年代久远,且文化成就不容置疑,再加上作为“文艺复兴”的精神资源这一金字招牌,使之对后来的任何一种文明方式都能保持足够的优越性和批判权,成为普遍性的解构资源。由于这种近乎神话的力量,当现代中国的民族文化需要言说自己时——无论是主动质疑西方的现代性方案还是进行文化自卫——竟可以诉诸希腊这个想象性的起源,通过论证西方现代文明违背了自己的价值源头,达到对本土文化身份的迂回确认,难怪周作人把希腊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民族性的一块建基之石。
因此,尽管对希腊文学的审美特质的描述是高度理想化的,但其本身却是一种历史之中的文化冲动,与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的内在矛盾密切相关。周作人、吴宓、缪凤林等人均在希腊和中国文化之间发展出了一种比较的视点,认为双方在中庸、现世、谐和等方面相去不远,而都与现代西方文明相抵触。在这里,希腊和中国成了同一符号分裂出的两面,希腊文化被想象性地转化为现代中国民族性的意义之源泉,它跨时空地确证了中国文明,使民族精神在世界主义语境中获得了合法性。在周作人那里,与希腊人相比,中国人“缺少求生的意志”、“对于生命没有热爱”,但在这表面的痛诋之下,却不难读出对中国应有的民族性的渴念;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我们“应该”拥有而暂未拥有的文化形态。而对于吴宓来说,荷马史诗弥漫着“特殊之精神之感情”,亚里斯多德则代表着后代西方文明早已丧失的“中庸”,可惜的是,希腊哲学家“尊理智之无上,而同时又欲保有谦卑之德,其事必不能行也”[18],造成了西方文明的自我分裂,反而需要孔子这位“道德意志之完人”来救援,神话式的希腊就这样悄然过渡到神话式的中国。无论如何,作为能指的希腊的“美”的神话都是“中国”这个更大能指符号自身滑动的创设,所指着一种“非西方”地自我现代化的可能性。
与西方彻底拒绝社会日常逻辑、“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相比,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将美的无功利性作为社会启蒙的一部分,即使是思虑较深的周作人,对“美”的考量仍然含有强烈的社会学和伦理意义。他们所针对的,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而忽视精神价值的问题,这里有的是文化自立的欲求,以及对已经失去的民族伦理性的期盼。最终在“美”中,体现出作为“神髓”的国族主义——民族不仅在经济政治的显在层面上“富强”,更要成为富于内在想象力和生命的“文化民族”。不妨说,五四学者对希腊文学史的论说是以特殊的方式参与到了中国的现代性争论之中,所有对“现代”的期望和失望,都反映在文学模式的选择上。他们赞颂的不只是希腊文明之馀光,也是作为“神话”中国民族精神的现代复苏。
注释:
① 这两部著作的最初版本是,周作人:《欧洲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吴宓:《希腊文学史》,《学衡》杂志第13、14期连载。
② 参见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7期,1905年10月。
③ 参见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85页。
标签:文学论文; 1930年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古希腊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欧洲文学史论文; 文化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性论文; 读书论文; 周作人论文; 吴宓论文; 古中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