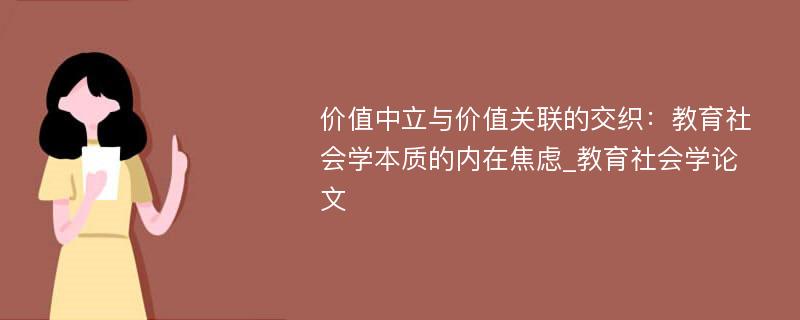
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一个内在焦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社会学论文,焦虑论文,学科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其发展需要不断对自身学科要素(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方法论)进行反思。这即便不说是教育学社会学界同仁的共识,至少也可视为大多数同仁不会反对的取向。对于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大致有两条路径(尽管二者不是截然分开的):一是与其他学科进行比较与鉴别,以凸显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与学科视角,可称之为“外部的反思”,这比较常见;二是“反求诸己”式的反思,以扪心自问,教育社会学在同其他学科比较时所声称的那些学科属性与学科特色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本文所欲尝试的即是后一种反思。
笔者认为,这种反思的关键或要领恰在于“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这一对社会学中的经典命题。可以说,正是这一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题,从根本上牵掣乃至决定了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论“是何、如何、奈何”等一系列的观点呈现与理论交锋。进言之,在关于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三种观点(简称“三论”)中,“事实学科论”奉行事实判断,摈弃价值判断;“规范学科论”强调社会学知识在教育实践中的直接运用以及对教育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则在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间调和、折中抑或摇摆。检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尤其是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不难发现一个大致从“规范论”到“事实论”再到“事实与规范兼有论”的波浪起伏的运动轨迹。
一、教育社会学从“规范论”到“事实论”再到“事实与规范兼有论”的变迁
正如其基础学科社会学的发端不过是对因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1],因而从一开始,与社会学家就怀着“改变世界的希望”去理解世界一样,教育社会学在其“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学科性质取向往往也是‘阐明规范’(系‘规范学科论’),美国是这样,日本是这样,我国也是这样。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重建的起始阶段,也同样如此”[2]。譬如,美国的沃德于1883年在《社会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教育社会学”这一概念,并专论了教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认为教育在促进人类进步、建设美好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源于此,以改进教育实践为直接目的的“规范性教育社会学”,如“服务于教师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Teacher)、“服务于教育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Education)及“教育问题的社会学”(Sociology for Educational Problem)占据了二战以前教育社会学的主流地位。[3]
由于受二战后日本社会对于教育培养“民主人格”之期待以及当时美国教育社会学尚处于“规范性教育社会学”阶段的双重影响,日本教育社会学在其初创阶段(1945-1954年)的主导学术取向也是注重用社会学成果来解决教育实际问题,为培养“民主人格”的实践服务。[4]我国的情况更是如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社会学先驱性人物陶孟和、雷通群都把运用社会学知识改良教育作为教育社会学之要务。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的情况来看,由于受教育社会学隶属“一级学科”教育学的学科建制、教育社会学从业人员多来自教育学而非社会学的学术背景、“学以致用”的心理期待以及研究者本身的社会位置等多重因素的交错影响,“规范学科论”就不只是在重建初始阶段占有主导地位,而且至今强劲势头不减,并大有在与“事实学科论”的争锋中呈现“由守转攻”的态势,而“事实学科论”则浮现“且战且退”的迹象。
也正如其基础学科社会学在初创之际就存在倾向事实分析的“科学社会学”与热心价值参与的“改革社会学”一样,[5]教育社会学在诞生不久就存在着“事实学科论”对“规范学科论”的抗争,直至取而代之成为主流。譬如在美国,安吉尔于1928年首次提出与“Educational Sociology”(“规范学科论”)相对的“Sociology of Education”(“事实学科论”)这一概念,后经1932年沃勒“Sociology of Teaching”一书以及1949年布鲁克弗“Sociology of Education:A Definition”一文的问世,直到大势所趋之下创刊于1927年的“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杂志最终在1963年易名为“Sociology of Education”之际,“Educational Sociology”(“规范学科论”)这一研究范式“终于退缩一隅”。[6]30年后在中国,吴康宁在其《教育社会学》(1998)一书中明确提出“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的观点,最终实现了教育学与教育社会学之“母子关系”的重新厘定。[7]
这里需明确三点。第一,能够成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社会学只能是Sociology of Education(“事实学科论”)而非Educational Sociology(“规范学科论”)。第二,尽管作为独立学科的教育社会学产生于社会学与教育学之后,但它并不是这两门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不是“交叉学科”,而是社会学用于“教育领域”而不是“教育学”后的产物,所以,教育社会学成为教育学的“母学科”是教育社会学给予教育学以理论滋养而不是相反,这与教育学产生于教育社会学之前并不矛盾[8]。第三,“事实学科论”之所以能够取代“规范学科论”成为主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规范性教育社会学实为教育学之变种,其致命缺陷便在于将教育社会学与教育学混为一谈,从而在实际上取消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独立地位,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历史业已表明,正是在规范性教育社会学占主流地位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科形成时期,美国教育社会学领域几无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9]这注定了其日后的式微,并对我国教育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警示作用。
正如其基础学科社会学在当代日益呈现奉行价值中立的“专业社会学”与负载社会关怀“公共社会学”相融合态势一样,当代教育社会学大有“事实学科论”与“规范学科论”握手言和的迹象。如美国学者巴兰坦便竭力主张,“今天的教育社会学家需要双管齐下,即一部分人从事客观研究,另一部分人则与学校人员一起去转化与完善已有的科学发现”;日本第二代教育社会学家清水义弘明确主张,在“事实学科”还是“规范学科”的问题上,“教育社会学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皆需”;日本第三代教育社会学家柴野昌山认为,“教育社会学并不只停留于对教育事实的如实记述、分析与说明,它同时也是预言教育应有状况,并为达于这一状况而做准备的一种教育科学”。[10]
与“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在美、日等国虽存在但并不占主流的情况不同,在我国,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这一学科性质取向在实际研究操作中有颇多贯彻,在理论探讨上亦有不少共鸣,且似有逐渐增强之态势。仅就理论探讨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边际学科论”[11]与“边缘学科论”[12],到本世纪初提出的“综合学科论”(教育社会学乃交叉、边缘学科)[13]、“(社会学的一门)具体学科+(教育学的一门)子学科论”[14]及“边缘+基础学科论”[15]等观点,万变不离其宗,均可视为“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的变异体或改良式。教育社会学学者张人杰十年前就曾隐约表达,[16]新近更是明确提出:我国教育社会学主流取向应当“重新作出抉择”,“现在看来,将‘事实与规范兼有论’列为应有的一种主流取向似更合适”[17]。
这里并不是要哀怜“事实学科论”在与“规范学科论”的争锋中且战且退,而是要迂回追问: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究竟能否弃守“事实学科论”?“事实学科论”本身又是否可能?如若弃守,或者,如其本身不可能,教育社会学又将安身立命于何处?
二、事实学科论:教育社会学不能弃守的“学术底线”
面对教育社会学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必须厘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独特性究竟是什么?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维和认为,与其他学科相比,教育社会学独特之处在于它是通过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来研究教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18]实际上,将探讨“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这种观点在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曾得到高度认同,在学科恢复期尤为明显。[19]这也是迄今为止相当多学人在判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简称“关系说”。
问题是,正如非教育社会学学者劳凯声所言,所有与教育有关的学科的理论体系不外乎“起始于两个基本问题,即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和教育与个人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两个基本问题又可以分解为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与文化、教育与个人的社会化、教育与身心发展阶段、教育与个性特征的关系等一系列更为具体的问题”[20]。这样看来,“关系说”至少面临两个障碍:第一,“教育与社会关系”本身是个矛盾用语,因为教育本身亦是社会之组成部分,它要表达的无非是作为一种社会要素或现象的教育同其他社会要素或现象(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第二,也是至关重要的,“关系说”并未切中要害,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等学科不都是关涉教育与社会(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方面等)的关系的吗?或许正是基于“关系说”这种未及肯綮的模糊界说的印象,教育学者潘懋元批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尚不明确,从而与教育学及其各门分支学科颇多重复”[21]。
这种笼统的或者易于让人笼统理解的“关系说”并不足以凸显教育社会学的学科特性,教育社会学的“门牌号码”究竟何在呢?张人杰在其新作《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探索中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22]一文中推举(重申)吴康宁提出的“社会学层面说”为判定标准或原则,认为它更直截了当,且更概念化:“教育社会学虽然与其他教育学科同样研究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但它只研究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的社会学层面”[23]。张人杰同时还提出,实施这一原则乃是教育社会学的“当务之急”,认为《课程社会学研究》[24]一书堪称实施这一原则的范例。张人杰就此反思自己早年撰写的“教育社会学”词条时说,“对于研究对象部分因未强调‘社会学层面’这一要害而有失之过宽之虑”。
紧接着要追问的是,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的“社会学层面”如何体现?或者,“具有社会学意味”的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如何彰显?就此问题,笔者不赞同不少学者要么就研究对象来讨论研究对象,要么割裂研究对象与方法论的关系来讨论研究对象,抑或主张研究对象决定研究方法论的致思路径;而主张研究对象必须与方法论关联起来探讨,进一步说就是要由方法论决定(确保)研究对象,再进一步说,笔者主张的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纯粹主义”。正如教育社会学学者胡宗仁所说,“研究方法的定位和取舍(方法论)几乎成了教育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社会学层面)的主要标志”。[25]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正因秉持了事实判断的方法论而具有了一种吴康宁所提出的独特的“学科之眼”,并由此有了“社会层面”的研究对象。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的“社会学层面”,是由其研究方法论——摈弃价值判断、奉行事实判断,以及由这种方法论主导的“事实学科论”——来确保并体现的。吴康宁提出的“社会学层面”研究对象说,与其同时提出的“价值中立”方法论说、“事实学科性质论”以及相应的“学科关系观”(教育社会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而非相反)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6]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或内核,就是“摈弃价值判断、奉行事实判断”的研究方法论,其他部分均依循于此并由此决定、确保。这样,诸如在认可“社会学层面”研究对象说的同时又否定“事实学科论”而主张“事实与规范兼有论”(或“交叉学科论”),甚至主张教育学为教育社会学的基础学科这种“学科关系观”之类的做法,就不仅是对“社会学层面”研究对象说的割裂,同时这类做法本身也存在无法圆通的矛盾与内在的“短路”。舍去“事实学科论”的保障,是无所谓“社会学层面”研究对象说的,具有“社会学意味”的教育现象或教育问题也是无以凸显的。
说到底,教育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至少是作为一门区别于教育学的教育社会学,那么,在其学科性质的识别上似乎不存在“选择”的余地,而必须坚守一条吴康宁所提出的“学术底线”:就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本身而言,其本职任务只有一个,即揭示事实,这就是教育社会学区别于教育学的一条学术底线;只有这种“本职工作”,才能确保教育社会学为教育学阐明教育实践规范提供社会学依据的基本任务;否则,倘若教育社会学既揭示教育事实也阐明教育实践规范,那就变成了“不务正业”,并通过这种“不务正业”而使自身同教育学的关系变得混乱不堪,这既是“失职”,更会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它作为教育学之基础性学科而存在的合法性理由。[27]恐怕这就是为什么“规范学科论”或者“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在教育社会学比较成熟的国家不能占据主流地位的根底所在,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虽然现实的学术实践和高校的人才培养大多经由教育学出身的学者和教育学院(系、所)来进行,却几无学者明确表示自己是持‘教育学分支学科说’”[28](规范学科论)的赧颜所系。
照此说来,在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上似乎不存在选择的问题,因为“规范学科论”径直把教育社会学等同于教育学而使教育社会学失去了自立的合理性与存在的合法性,而“事实与规范兼有论”则将教育社会学同教育学的关系变得混乱不堪,并最终也把教育社会学混同于教育学。那么,由“价值中立”确保而命悬一线的“事实学科论”忧堪何处呢?
三、教育社会学“价值中立”何以可能
教育社会学“价值中立”涉及所谓“休谟问题”,它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一是认识论或逻辑学上的“归纳问题”或“因果问题”;二是伦理学或价值论上的“是—应该”问题或“事实—价值”问题。[29]就“事实—价值”问题而言,使休谟“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在以往的道德哲学体系中,普遍存在一种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动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联系动词(实为情态动词)的价值命题的跃迁,“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30]当初,休谟只是提出必须对由“是”或“不是”跃迁为“应该”或“不应该”这种新的关系加以“论述和说明”,后人却抓住这一点并联想到他在认识论或逻辑学上的关于归纳方法的见解,命名了所谓“休谟问题”,并津津乐道至今的是诸如“事实与价值二分”、“‘是’推不出‘应该’”之类的命题。而休谟本人,仅仅在其《人性论》第三卷第一章第一节最后的一则附论中,提出这个使其“大吃一惊”并自诩为“可以和牛顿在物理学中的发现相媲美”的“发现”后,“再未对此发现或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释与探究”,这使得“后人对休谟是否真的认为这一问题很重要产生了怀疑”[31]。或许,对于休谟而言,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休谟并未反对而只是吃惊“是”或“不是”向“应该”或“不应该”的跃迁,他留下一串意味悠长的吊诡就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不应该’联系起来的”;“从‘是’或‘不是’跃迁到‘应该’或‘不应该’需要证明”,而这又看似不可能。
换个思路,休谟又何尝不是在预示:原本就没有纯粹的脱离事实的价值,更没有纯粹的脱离价值的事实。想想看,世间再没有比表达价值倾向或做“价值判断”(不管是个人兴趣还是社会关怀更容易的事情了。山林中的野兔就知道母兔子好、大灰狼坏,草原上的狮子更懂得用尿液作为领地的界标。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但人比兽更多情,更多价值判断。人的语言里更多的是情态动词(“应该”之类)而不是连系动词(“是”之类),而且人最喜欢用情态动词取代连系动词,还会“话里有话”地用连系动词表达情态动词。在人眼里,在人言中,万水千山亦总是有情。不客气地说,人这个类就是个“情”种。寰宇之内,只有人这种动物穿衣,可人穿衣除了御寒这个自然(客观)需要之外,不是为了“让人看”就是为了“不让人看”,仅有的三个原由中,“情”居其二。
难怪德国哲学大师卡西尔对“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说“不”,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动物(Animal Symbolicum)”(这本身也是个价值判断),并特地征引埃皮克蒂塔的话说:“使人扰乱和惊骇的,不是物,而是人对物的意见和幻想。”[32]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当代欧陆人文哲学家孜孜以求的,就是把语言(也就是思维形式和生存形式)从英美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理性语法主义中解放出来。对于中国,似不用作此解放,“中国传统文化发展道路的最基本特征,确实就在于它从来不注重发展语言的逻辑功能和形式化特征,而且有意无意地总在淡化它、弱化它”,从而也就“更容易丰富词语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由此,“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正是把所谓‘先于逻辑的’那一面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了”。[33]
基于这些特征,中国的非拼音文字及其语言表达,更容易富含价值意蕴。字、词、句及建基其上的新闻报道、科学研究等无不如此。譬如“孬”、“囚”、“嬲”之类,只需一字,价值韵味便跃然纸上。又如“钢笔:一种有贮存墨水的装置,写字时墨水流到笔尖”[34]之类的词典释义,看似客观的事实描述,实为价值判断,这说的分明是“好钢笔”,“坏钢笔”是不会流墨水的。词典、产品说明书中诸如此类的定义和说明,所给出的其实都是一种“不能不包含价值因素”的“功能性概念”[35],如一个具有X型功能的事物的概念不能脱离一个好X的概念而独立地被界定,如“钢琴”等乐器、“眼睛”等器官不能脱离“好钢琴”、“好眼睛”而被界定,甚至“钢琴”、“眼睛”等的原初含义就是由“好钢琴”、“好眼睛”来赋予的。总之,描述事实、评价价值均由同一人类语言符号系统或概念系统来承担,纯粹描述事实的“价值中立”的语言符号系统或概念体系是不存在的;事实认定中有价值渗透,价值评定中亦有事实认定。[36]
但是,教育社会学者又在追求价值中立或以之自居。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是教育社会学中一对致命的张力,同时也是一个解不开的结。为此,教育社会学研究者试图上下求索,却又难免自我矛盾:究竟如何弥合“社会学层面”研究对象说与“事实与规范兼有论”之间的“短路”?究竟怎样才能在“担当社会责任”的同时奉行学人的“事实判断”?究竟怎样才能克服像“迷信的科学”一样的“个人化的社会事实”[37]这一“术语谬误”的荒诞?
也许,社会学的奠基者韦伯和涂尔干对此早有所料并挖好了陷阱,韦伯是“价值中立”原则的倡导者,但同时也是“价值关联”的拥护者,他强调价值关联只是涉及研究课题的选择,而不是对研究对象的解释;[38]涂尔干在“进行完全客观的分析”前面悄然加了“力求”一词[39]。他们把困难和焦虑甩给了我等:选题要“价值关联”、研究过程要“价值中立”,韦伯的这种捆绑,是要告诉我们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吗?涂尔干的“力求”是什么意思?大差不差还是稀里糊涂?更要紧的,就算教育社会学研究能够做到百分之百的“客观”和“价值中立”,这就能够成为它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标志吗?“社会学碰上的许多困难,恰恰是因为我们总是想把它搞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科学。”[40]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可是,不这样的话,不就成了一种“作为借口的教育社会学”[41]了吗?相应的,所有的学科不都成了“作为一种借口的××学”了吗?追问到此,焦虑变成了恐惧。
那么,本文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笔者只能这样回答:首先,教育社会学研究无论如何也绕不开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换言之,没有纯粹的脱离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也没有纯粹的脱离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这是第一个事实判断。如此,那种绝对的“事实学科论”或绝对的“规范学科论”就显露合理性危机因而不宜再主张了。这是我的第一个事实判断背后的价值判断。其次,从纯学术及学科自立的角度讲,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必须是、也只能是“事实学科论”(那种“事实与规范兼有的学科论”因此也显露合理性危机,因而也不宜再主张了),但这不可能,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宿命式的焦虑,简列为:“事实学科论:必须+不可能=焦虑”。这是第二个事实判断。这第二个事实判断背后的价值关切,就是作为一名教育社会学从业者的笔者的焦虑,以及笔者对方家赐教的期待。
四、结语
本文原拟只呈现由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而产生的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判识的焦虑,但就此脱稿未免沉重。迟疑再三之际,拜读到张人杰新作《教育社会学研究对象探索中需要澄清的三个问题》,文中关于“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是难以将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所谓“‘价值中立’只是一种虚假现象,想使研究更具‘客观性的’的‘事实论’事实上不能成立;同一逻辑的分析也适用于‘规范论’”,因此,“将‘事实与规范’列为应有的一种主流取向似更合适”[42]的观点,既让我暗喜“于我心有戚戚焉”,又催我进步,试图解开这个源于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交织的死结。思索再三,古人关于《易经》的思想(所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浮现脑海,似感茅塞顿开,解铃还需系铃人!于是,我再次扭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交织”这个牛鼻子,得出在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之主流取向抉择上的“一个或所有”式结果。
其一,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没有纯粹的脱离价值判断的事实判断,亦没有纯粹的脱离事实判断的价值判断”(用张人杰的话说就是“‘事实论’事实上不能成立;同一逻辑的分析也适用于‘规范论’”),这本身就是个“事实判断”。根据这一“事实判断”,在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上,就不存在“选择”的问题,更谈不上在“三论”中“抉择”何者为“主流”的问题。全部的理由就在于只剩下“无可奈何”的“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这一个结果。既然所有的结果都是“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何谈主流?此谓“所有”式结果。
其二,阴阳相对,彼此互生。从与上述“事实判断”相对的“价值判断”(学术品位要纯正,学科要自立)来说,笔者主张,在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追求上应该是“事实学科论”,而不是把“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列为“应有的”一种主流取向。这是因为,一方面,“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无可奈何的结果,倘若变消极的结果为主动的追求,后果将如迄今为止的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史所一再表明的那样,必将因把教育社会学混同于教育学而危及教育社会的学科自立;另一方面,理想总是高于现实,既然是“价值判断”,既然要谈主流“取向”,往往就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取向”未必要求完全实现亦未必能够彻底达到,但至少应该导向应该去的“方向”,走在通向目标的“路上”。所谓“法乎其上,得乎其中”,不可能有纯粹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有彻底的“事实学科论”,但在向着“事实学科论”目标迈进的方向与道路上,需要保持“尽量的”价值中立和“最接近的”事实学科论的态度,而这至少有利于同危及教育社会学学科自立的“规范学科论”保持必要的张力。倘要“法乎其中”,列“事实与规范兼有学科论”为“应有的”主流“取向”,则只能“得乎其下”,进一步助长“规范学科论”广泛流布,从而在实际上取消了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社会学,此谓“一个”式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