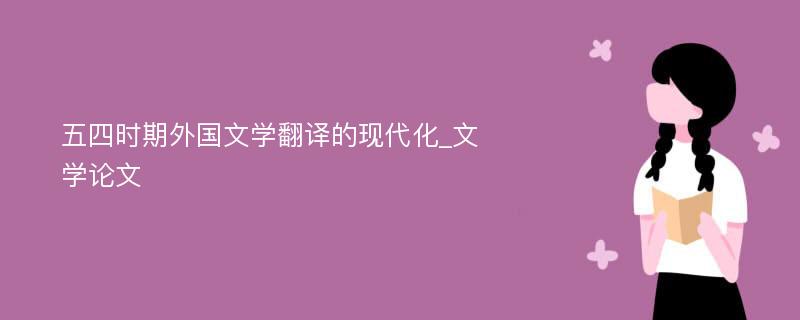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外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4)04-0050-06 五四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异常丰富,翻译思想异常活跃,与晚清的翻译一起构成继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之后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翻译高潮。无论在翻译的规模、组织、范围,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五四时期都可以看作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这一时期的翻译不但前承了佛经翻译的严肃庄重、科技翻译的丰富多样,而且后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第四次西学引进的高潮,为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举足轻重,关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不能不谈到现代性的问题。 一、区分三种现代性 现代性是指“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特点”,就起源而论,“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经济层面的范例,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政治层面的范例,从德国开始的宗教改革和法国为核心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思想意识层面的基础,以伽利略、哥白尼、牛顿、达尔文为代表的学院性科技提供了理性思维和工具动力”(张法,2002:4~5)。我们将此称为启蒙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 审美现代性则恰恰相反,它以非理性为核心。工业革命将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科技进步、商业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都市化特征,人类物质生活的舒适、富足与精神生活的匮乏、危机形成了鲜明对照。科学主义的长足发展,使得人也成为技术和工业支配的对象。物极必反,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对人的过度钳制导致了非理性倾向的出现。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根源。可以说,审美现代性是基于对启蒙现代性的消极反抗、批判和否定,审美现代性中浸透着焦虑、感伤、无奈等情绪。卡列尼斯库从文学艺术现象总结出现代性的五个方面,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派、媚俗风、后现代主义(张法,2002:6)。 翻译现代性是在翻译中表现出的现代性,包括翻译职业自身以及翻译对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表现、传达,涉及对现代性的理解、介绍、传播以及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现代化的影响。王德威在论述晚清小说翻译时,对晚清翻译的现代性从叙事模式、文体特质、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以《文明小史》、《新中国未来记》和《新石头记》为典型例证,认为人们滥用、挪用翻译使其在晚清成为一种“文明”的现代职业;译介了一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方法;套用西方科幻小说的模式进行中国历险奇想,并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进行新知识改造(王德威,1998:103)。到了五四时期,科幻小说等被当作娱乐闲书遭到漠视,翻译成为一种严肃的工作,直译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滥用、滥译的现象减少了,但是在翻译中对西方思想文化的选择、接受、挪用、转化却是不可避免的。 二、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宏观体现 从宏观上讲,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以及人为的翻译现代化趋向上。 首先,对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清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就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但被文学界视为“小道”的小说便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梁启超的论述为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革新传统的小说观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地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新文化倡导者们虽然和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但他们和近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将思想启蒙和政治救亡的希望寄托在文学上,“以思想家去做文学家”(刘纳,1987:29)。文学和文学翻译在晚清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而有所改变,新文化倡导者们反对“文以载道”,并不是要戒除文学及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而是反对“道”的具体内容,即儒家所言之道。因而他们倡导的新文学同样是“载道”的文学,只不过“道”的内容发生了改变。新文学所载之道就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自由和平等的思想。鲁迅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讲:“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鲁迅,1982:512)。陈独秀则援引西洋文学家的例子,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陈独秀,1993:159)。因而,从新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这一点而言,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与晚清维新改良派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文学翻译仍然是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同时也真正实现了对文学自身的“启蒙”。五四时期正因为“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的互动,才建构起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王嘉良,2004:96)。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科学知识的宣传,对旧伦理道德的反对,对“人”的发现无不是通过“翻译”西方启蒙思想实现的。 其次,通过对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译介,对中国的现代文学进行启蒙,使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化。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诞生、成长和发展的。五四时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多兼为作家,这使得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方式变得错综复杂。由于引进外来文学的急迫性,五四时期译者所熟悉语种的集中性以及受整体翻译倾向的影响,五四时期对外来文学的输入方式除了直接翻译之外,还大量存在转译(当时称作重译)现象。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引进新的文学类别,改造中国原有的文学类别,丰富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总体看来,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诗运动 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表现出的气魄,是对中国传统诗歌全方位的变革,以至于梁实秋称:“新诗,实际上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胡适的《尝试集》“表示了一个新的诗的观念。胡先生对于新诗的功绩,我以为不仅是提倡以白话为工具,他还大胆地提示出一个新的做诗的方向。新诗与中国传统旧诗之不同处,不仅在文字方面,诗的艺术整个变了”(梁实秋,1985:141)。梁实秋对新诗的描述,充分说明了新诗运动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大。中国近体诗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字数、行数等要求,新诗运动对近体诗的形式结构进行了“暴徒式的破坏”。格律诗向自由诗转变,诗的叙事成分增强了,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等,诗与非诗的界限逐渐模糊,相对于严格限制格律与字数的近体诗而言,白话新诗出现了“非诗化”倾向。白话化、散文化是新诗翻译与创作的主要特征。同时,起源于中国古诗的意象经由庞德的翻译名噪美国,又戏剧化地通过胡适等知识分子的翻译引进来影响了中国的新诗。 (2)戏剧改革 中国在20世纪初成立了多个戏剧社团。这些戏剧社团的成立促进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他们借鉴西洋戏剧,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早期话剧的探索。他们把自己实践探索的新文学样式称之为“文明戏”,表明其与传统戏剧的不同。五四时期,文明戏与传统戏剧一起遭到新文学家们的批判。与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观点相一致,五四干将主张借助西洋戏剧来建立中国的新戏剧。胡适、傅斯年、钱玄同、欧阳予倩等对新剧理论的论证,始终是和对外国剧本的翻译、本国的实践活动相伴而行的。翻译剧本的数量逐渐增加,1917年翻译剧本1册,1918年1册,1920年2册,1921年9册,1922年10册,1923年20册,1924年10册,1925年14册,1926年12册,1927年19册(田禽,1946)。西方戏剧经过文明戏阶段和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与实践,最终在中国落户,形成了新的戏剧文学,有了从事话剧的队伍和团体。 (3)题材借鉴 五四时期的作家在创作中大量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五四时期,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呼声很高,易卜生及其力作之一《玩偶之家》便进入了中国现代作家的视野,成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易卜生创作现实主义戏剧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开创的“社会问题剧”成就和影响很大,并在中国引起了“问题文学”的创作高潮。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胡适于1918年创作了独幕剧《终身大事》,这是中国现代最早创作的话剧剧本。郭沫若的《卓文君》取材于历史,但并不拘泥于史实和封建阶级对卓文君的诋毁,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重新给予定位。另有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都成功地塑造了娜拉般勇于为争取自由平等地位而斗争、不惜离家出走的女性形象,被称为娜拉剧。另外,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王昭君》、《聂荌》等,也都是以追求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剧目,反映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成长的影响。 再次,这一时期出现了人为地推动和加速翻译现代化的趋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新文化人与林纾之间关于翻译的论战。林纾的翻译虽然删削改易现象不少,但将林纾作为旧派人物的代表进行批判却是言过其实的。林纾从事小说翻译本身就能标识一种开放的心态,林纾的翻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也不能说没有贡献。但是新文化人为了加速翻译趋向的转变,为了表明新与旧的誓不两立,将林纾作为人为的靶子进行攻击。这是五四时期激进主义和惟“目的”是图的结果。五四人具有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导致了有时在学术上不是实事求是地考虑真理是非问题(王元化,1998:74)。五四人对林纾的批判正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以及新文化人对启蒙理性的主动选择,通过译介西方文学而启蒙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现代文学仍然是以弘扬理性精神为主的文学。西方以非理性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在中国也有所译介,但其气势远不能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比,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要小得多。郁达夫、李金发等具有西方现代主义创作倾向的作家在文坛中处于边缘地位。因而,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性”。 三、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微观体现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翻译方法的变化、理论自觉意识的增强、对译者要求的提高和译本选择的变化上。 1.从豪杰译到直译 晚清是“豪杰译”盛行的时期,将西方文学作品改为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删节心理和景物描写、在译文中夹杂作者的评论与解释、追求译笔优美雅驯而改变原文的风格,这些现象在晚清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中俯拾即是。究其原因,还是译者自身的国学修养、对读者接受程度的关注、当时的总体翻译倾向和翻译目的的制约等因素战胜了译者尊重原文的本能,翻译与创作的界限不断模糊化,出现了译即作、作即译的现象。后期坚定提倡直译的鲁迅和周作人,他们的早期作品《斯巴达之魂》、《孤儿记》等都是半译半作。 到了五四时期,直译成为外国文学翻译的主要方法。直译的流行,得益于傅斯年、周作人等的推广,也得益于梁启超、胡适、贺麟、杨世骥等的著述。这些论述无形中扩大了直译的影响。然而,直译在当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的界定,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因人而异。关于直译的讨论,主要涉及字词和句法,这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是吻合的。 直译在五四成为主要的翻译方法,主要是针对和区别于晚清的“豪杰译”对原文随意删削改易。因而与其用意译概括晚清的翻译,不如使用变译或变体的概念。五四译者关于翻译方法的论述表明,直译与意译在他们的实践与理论中并非不可通约。艾伟在1929年关于直译意译的调查问卷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吾人所征求的十四答案中,即无人主张绝对的直译,而主张意译者,又因有绝对的直译始倡相对的意译。故此两派与折中派并无不相容之处”(艾伟,1984:168)。 2.翻译理论自觉意识增强 晚清译者在言说与实践方面的矛盾,与那个时代的译者缺乏理论自觉不无关系。他们对翻译理论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阶段,并没有要发展翻译理论来宏观规约、微观指导翻译实践的意识和欲求。他们关于翻译应该忠实的言说可以说是出于译者的本能,但这难以抗拒特定的翻译目的、本土传统文化势力和伦理观念等因素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排斥力,因而他们在言说与实践层面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晚清的译者并没有认识到或者说并不承认他们在言说与实践层面的矛盾。 文学翻译方法从晚清以“豪杰译”为主到直译成为主流,这不仅仅体现了翻译方法的转变,也体现了译者对翻译本质的重新认识。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理论自觉意识不断加强,以往的翻译理论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反响,新的翻译理论开始迭出。对以往翻译理论的认识,包括梁启超、胡适对佛经翻译的理论总结与归纳,也包括对晚清文学翻译实践的反思,对严复“信达雅”说的态度及其阐发。同时,国外的翻译理论也开始向国内译介,如Tytler的三原则。 这一时期,郭沫若提出在直译、意译外,应有“风韵译”;茅盾提出“神韵”与“神似”说,开启了翻译中美学问题的研究,是以后“神似”说的萌芽。“风韵”与“神韵”的提出有其语境,那就是直译的盛行。直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否保存原作的语言特征,意译关注的是译文能够流畅。可以说,直译、意译关注的都是语言层面,这绝非文学艺术的全部。事实上,原文作者的文风、笔法,原文的体裁及其特征等都不是直译、意译所能完全涵盖的,尤其在诗歌翻译中。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郭沫若表示在直译、意译之外,还应当有“风韵译”,茅盾提出宁可失去直译的形貌也要保留“神韵”。 3.对译者的要求提高 晚清时期,由于国门刚刚被迫打开,人们对西方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对外语的熟稔程度不高,所以西译中述、对译的翻译形式十分常见。“西译中述”在1895年之前曾经占据一定的翻译地位,并在克服和跨越文化障碍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译”的模式与“西译中述”类似,但其述与译的工作都由中国人担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林纾的翻译。 五四时期随着翻译的蓬勃发展,外语人才的增多,对译者的要求较之晚清时期已经大大提高了。从郑振铎、茅盾、郭沫若与郁达夫等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对译者的要求已经涉及:(1)语言能力,包括对外文理解能力和对本族语的驾驭能力;(2)文学修养,包括对原作风格、精神的判断力和敏感度以及用本族语言将其再现的能力;(3)创造力,文学翻译绝非简单的文字转换活动,需要译者具有创造力;(4)职业道德,文学翻译虽然要求译者有创造力,但决不能流于放纵(这种职业道德当然是基于传统的翻译观念而言的),如钱钟书所说,“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功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5)对于原著有一定的研究,包括对作者的研究,对所述事物的了解等;(6)接受新思想的开放心态。可以看出,对译者的要求涉及多个方面,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 4.译本选择的变化 从晚清到五四,翻译选目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国别来说,晚清的主要选择有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国、德国。就作家来说,晚清译者所青睐的是柯南道尔、哈葛德、凡尔纳、大仲马和押川春浪等。就文类来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等普遍受到晚清译者和读者的欢迎。就篇目来说,晚清作家主要翻译长篇小说,这与那个时代的译者和读者阅读域外小说的“内容”或“情节”的期待有关(陈平原,1998:42~44)。 到了五四时期,译者对译本的选择从各个层面都发生了变化。俄国的文学作品译介入中国的数量一路攀升,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法国、德国、英国、印度、日本的文学作品也深受青睐。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绝对数量远远小于俄、法、德、英等国家。就作家而言,托尔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泰戈尔等作家深受欢迎。就文类而言,五四译者选择的主要是严肃的社会小说,包括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对小说教育功用的强调使得小说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改善,从“小道”一跃而进入大雅之堂。晚清的新小说家意欲将小说推举上“雅”的宝座,最终又不得不借助域外新异的通俗小说,这两者实难得到统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真正实现了由俗向雅的转变,是在五四作家与译者的手中完成的(陈平原,1998:95~100)。 四、结语 区分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翻译现代性,缕析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体现,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翻译现代性具有人为造就的趋向。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现代性的人为趋向主要表现为:直译成为主要的方法,欧化语体文是主要的翻译语言,译本选择倾向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翻译风尚的这些转变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不是译者自然选择的结果。五四主将上演双簧戏将林纾作为批判的靶子,并通过胡适的确认和罗家伦、傅斯年的应和,使得林纾很快落败,其所代表的“删译、改译、选材零散没有系统”的翻译迅速退潮(任淑坤,2013:123),翻译的现代性迅速显现。 (2)五四外国文学翻译对思想启蒙和审美情趣的重视,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时间差。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发生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勃兴时期,按理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入中国有时间上的便利性。然而,经过译介,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却是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式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在译本选择上更青睐具有共鸣和抗争精神的弱国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归根结底,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共同存在于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之中。 (3)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与晚清时期的翻译活动有传承关系。并非如印象所示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全盘否定和摒弃晚清通过译介外国文学学习西方的器物、思想乃至政治制度的传统。相反,译介的社会功用在五四外国文学翻译中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只是通过翻译的现代性特征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情趣,从而掩盖了其对社会功用的重视而已。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在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中总是相伴而生的。标签:文学论文; 现代性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晚清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