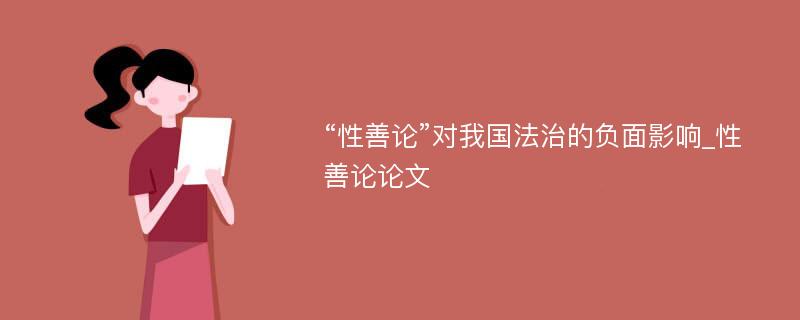
“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法治论文,消极论文,性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的法治以防恶为逻辑起点,以保障个体权利为归宿。公法之设,在于防范公共权力的滥用;私法之设,一方面是为了抵御公共权力对社会个体权利的侵犯,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社会个体权利的滥用。贯穿西方法治的一条主线是对人性和权力的不信任。即:人的本性是恶的,权力更加恶,是恶的平方。法治就是从防恶开始的。西方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即已产生,中经中世纪基督教“原罪说”的深化,至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则集大成。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对人的本性和权力持不信任态度的,他们所设计的,沿用至今的法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人性和权力不信任的产物。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人自古至今大都对人性和权力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虽然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曾出现过儒家性善论和法家性恶论两种不同的学说,但自从采用法家学说的秦王朝十五年而亡之后,再也没有人敢蹈亡秦之迹去信奉力倡性恶论的法家学说。西汉中期,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说”,力倡性善论的儒家思想成为法定的指导思想。中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佛、道三教的融合,至宋代理学产生,性善论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信仰。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就是在宋代问世的,这本小册子开始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性善论”从此几乎是家喻户晓。
性善论作为中国人普遍信奉的一种价值观念,曾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例如,性善论使中国人对人性持乐观态度,所以,当代中国刑法规定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对罪犯做到仁至义尽,同时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罪犯改造制度,相信绝大多数犯罪分子经过改造,可以幡然醒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些规定和制度显然是与性善论有关的。
但是,勿庸讳言的是,性善论也给中国的法治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偏激一点地说,性善论误尽了中国法治。
一、“性善论”导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崇拜,忽视了对最高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约束,极不利于以控制国家公共权力运行、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滥用的现代公法的建立或健全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权力是恶的平方,而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外化。西方人从以恶制恶,以毒攻毒的目的出发,很早就建立了权力制约机制,而中国总是试图找到一个不会腐败的、永远善良的权力,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虽有一定的权力制约机制,但始终对最高权力缺乏专门的、有力的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是有一定的分权制衡机制的。例如,隋唐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制度,宰相的权力由三省分掌,分工明确而相互制约,中书省大体上属于决策机构,门下省大体上属于审核机构,如无意见,则副署(签字)亦加盖“中书门下之印”,直接发往执行机构——尚书省执行;如有个别不当之处,门下省在进行涂改修正后发还中书省重新起草;如发现有原则性错误,门下省可以拒绝签署,驳回中书省。门下省虽有此等权力,但是没有具体执行权。
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分工制约,确有防范权力滥用的作用,但对最高权力——皇权的监督却存在空白点。皇权始终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放弃,不可制约,三省的长官是皇帝随时可以任免的,虽然古代的相权对皇权有制约,但以皇帝的开明、容忍为条件。
中国古代的司法权亦有一定的分权制衡机制,例如,清代的司法机关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组成,刑部掌审判,大理寺掌审核,督察院掌监察,合称“三法司”。从司法实践来看,三个机关之间确实起到了相互制约的作用。但是对握有最高司法权的皇权,三法司没有任何制约功能,死刑、重大疑难案件都需奏请皇帝决定。
中国古代老百姓的一般心理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国古代的监督制度是只监督臣民,不监督皇帝,分权制度也是只分大臣的权,不分皇帝的权。中国古人认为皇权之外的权力都有可能腐败,而皇权是例外,皇权是最后的善的权力。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主要是近现代民主法治理论的产物,但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能说毫无关系,也带有性善论的某些痕迹(尽管这不是当前政治体制的主要价值观念基础)。
仔细分析一下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可以发现,我们是承认司法权不受制约将会产生权力滥用弊端的,所以,我们设立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四个机关共同行使(广义的)司法权,让它们相互制约。即便如此,我们对司法权还是不放心,又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他们的监督职责。我们也承认行政权不受制约将会产生腐败弊端的,所以我们通过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使司法权制约行政权,同时还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但是,我们虽然承认司法权和行政权不受制约容易产生腐败,可我们却没有思考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会不会产生腐败?从理论上来说,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无论如何也不会腐败,人民代表大会怎会自己残害人民?如果仅仅从理论上看问题,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法院、检察院、政府都不会产生权力滥用。因为法院是人民法院,检察院是人民检察院,政府是人民政府,怎会发生人民司法机关和人民政府去残害人民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承认权力具有自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是一条法则、一种规律的话,我们就必须承认,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受制约会腐败,同样,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不受制约也会腐败。
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早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所证明。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先生在其所著《论依法法国》一书中提出,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在不少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正确,实际上是违法的监督。仅据一个省的材料,有以下种种情况:一是对具体案件作出直接具体的处理决定;二是对终审案件提出具体的建议和要求;三是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四是对尚未生效的判决要求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处理;五是对生效判决要求暂缓执行。这种种在监督名义下代替法院审判工作的违法事例,在全国并不少见,不仅基层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属机构也有。这样实际上在法院之上,又有一个审判机关了,在最高法院之上,又有一个更高的审判机关了。这是不符合宪法的。中共中央曾专门发了文件对此类问题进行纠正。但是,干扰与反干扰,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过程中是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必须在斗争中实现依法治国。(注:郑天翔:《确保依法独立审判·独立检察》,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9月28日第三版。)
尽管一些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本位主义的狭隘观念影响下,会做出违法监督的事情。但目前我们却没有一套预防各级人大滥用权力的法定制约体制和机制。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人内心深处确信世界上肯定存在一个不会腐败、永远慈善的权力。
当然,笔者这里虽然指出了人大的权力不受制约也会腐败,我们从体制、机制方面要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主张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制约的模式、途径从来就不是单一的,更不是只有三权分立一种。并不是西方人才具有权力制约的智慧,东方人只能拾西方人的牙慧。这一点不是本文论述的主题,所以就不再展开了。
二、性善论导致了中国深入开掘内心资源的内倾文化的产生,法官的审判活动不是依照法定程序层层展开,而是依照法官的神秘的内心体验和直觉感悟而进行,不利于现代程序法、证据法的建立与健全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善的源头在上帝,如果不借助上帝的意志而单凭人类自身的修养是无法实现社会公正的。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到司法领域,就表现为:单纯依靠法官实现实体公正是很难的。实现公正的实质是人类向外认识上帝、回归上帝的一种过程,因此,司法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程序的公正。
中国人认为人性是善的,善的源头在人的内心里,毋需凭借外力而单凭人类自身的修养即可实现社会公正,这种价值观念反映到司法领域,就表现为:只要法官的素质是好的,毋需什么程序,法官经过自己内心体验、直觉,即可明察秋毫,裁断是非。中国人企盼的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则无关紧要。
因此,有学者把西方的法律文化视为程序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视为实体文化。
在中国古代,法官的审判活动不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而是依靠内心体验、直觉来进行。首见于《周礼》,后载于《唐律》的“五听”规定,法官要“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眊然)。”“五听”依据被告的表情和心理状态来判断其是不是罪犯,有正确的一面。但它毕竟不是建立在客观调查取证和举证、质证等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法官的内心体验、直觉基础上。如果把直觉感悟作为一种参考性材料,而进一步去予以勘验、取证、举证、质证,那就符合了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辩证认识论原则。但在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恰巧不是这样,法官经过“五听”,就主观地认定被告是不是罪犯。如果主观地认定被告是罪犯,法官就不再去勘验、取证、举证、质证,而是进行刑讯逼供,直到“供认不讳”为止。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说道:“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行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申了,大呼青天。……这种程序在现代眼光中,会感到没有道理;但是在乡土社会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否则为什么这类记载,包公案、施公案等等能成了传统的畅销书呢?”(注: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55页。)
中国人把善的源头归诸人的内心,所以古代的法官非常看重被告的口供,因为“言为心声”,口供是内心意思的表露,是善与恶的显露,口供当然就成了证据之王。为了得到口供,不惜采用严刑拷打手段。因此,一定的刑讯逼供在古代是合法的。南北朝的“测罚”、“立测”,唐朝的“拷讯”等都是法定的刑讯制度。这些刑讯制度一是规定法官有权刑讯逼供,二是规定进行刑讯逼供要有一定的限度。其指导思想是:如果被告能够忍受拷掠,就说明他的内心是善的,是无罪的。
不难看出,性善论导致中国人向内心寻找善源,寻找的方法又是神秘的内心体验和直觉感悟,因而极不利于现代程序法的培育。同样,中国人循着“言为心声”的思路,认为通过口供才能鉴别一个人内心的善恶,遂视口供为证据之王,这就压抑了现代证据学的培育。当今中国的诉讼法、证据法相对落后,很难说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念没有关系。更令人关注的是,目前现行的不甚完善的程序法由于人们程序观念的淡薄,也未得到很好的实施。(注:有资料显示,较之实体违法,程序违法构成了司法机关职务违法行为的主要方面。例如,山东法院系统在1998年的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检查了45万起案件,查出有明显问题的案件3818起。其中实体处理上有问题的仅960件,占25%,程序方面存在问题的却多达2458件,占63%,其他问题约400件,占12%。)
三、性善论导致了中国人把人视为“义务人”,而不是“权利人”,获取利益的途径不是争取权利,而是期求人人无私奉献,“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价值观念着力培育的是“圣人”,是超功利的崇高的道德精神。虽有合理的一面,但强调过度,则会与权利神圣、为权利而斗争的现代民法精神相抵触,因而不利于现代民法在中国的生根、开花和结果。
西方人认为人性是恶的,基本上是自私自利的,因此,期求别人发善心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既然是贪婪自私的,因此,我们就不能轻率、盲目地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因为你的无私奉献,正中自私自利之徒的下怀,成全了别人的特权,满足了别人的贪欲。西方人的思路是:自己该得的东西不要放弃,不该得的东西不要窃取。古罗马人对“正义”的理解就是如此。循着这种思路,西方培育了以民法为基础的法律文化,民法把人视为权利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即集中地表现了这一点),权利有三重含义,一是权利是做人的资格,没有权利就不是人,因而作为一个人必须誓死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权利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防范,要求国家非经法律许可不得剥夺一个人的权利;三是权利是社会个体之间的一种相互防范,规定一个人的某一权利,就是对其他人设定了一个义务,捍卫自己权利的同时要尊重别人的权利。
中国人与此不同。性善论的价值观念容易使中国人认为政府是可爱的,不会做坏事,每一个人都是天生的善良,也不会做恶。“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因此,一个人不必防范政府,毋需提防别人。我们的唯一职责就是无私奉献,“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人人都肯无私奉献,每个人的利益要求都在他人的奉献中实现了。西方人在斗争中求利益,中国人则是在奉献中求利益。这种价值观念势必导致把人视为义务人,把争取、捍卫权利视为羞耻之事,《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一般人也一概把捍卫权利、合法地成名成家等观念当作错误思想来批判。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权利为核心的现代民法的培育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性善论把人视为义务人,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权利的漠视,不知道权利为何物,迄今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缺陷;不知道权利是权力的基础,迄今亦是许多政府官员的不足。而权利虚无主义、义务本位等,都与中国人笃信人性本善密切相关。
四、西方文化的主流认为人性本恶,并非西方人生来就喜欢性恶;中国文化的主流力主人性本善,亦非中国人天生地喜欢性善。两者不同的原因在于西方经济结构的主流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结构长期以来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
我们可以假设,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西方人和中国人肯定都认为人性是善的。因为这一时期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压迫,氏族部落中的成员平等友爱,全无私心杂念,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根本看不到人性本恶的表现。但到了奴隶社会,古希腊和罗马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品货币关系无情地斩断了人们的氏族血缘纽带,把原来温情脉脉的宗族人际关系赤裸裸地还原为利益、利害关系。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更彻底地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更彻底地破坏了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更彻底地崭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市场经济)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市场经济)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西方的人际关系经过古代的商品经济和近代的市场经济的洗礼,血缘关系、友情关系、地缘关系等全都淡化了,人性本恶的价值观念就由此而生了。
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从未得到很好的发育,因此,宗法血缘关系长期未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冲击。在广大的农村,人们聚住以族、祭祀以族、生产以族、庆贺以族、械斗以族、丧葬以族。温情脉脉的宗族血缘关系掩盖、缓和了赤裸裸的剥削压迫关系,使中国人全然地相信“血浓于水”、“好大一个家”、“五百年前是一家”等,国家是家庭、家族的放大。人性本善的观念就是在商品货币关系不发达、宗族血缘关系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产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把社会成员有计划地安排在“单位”里,实行统包统配,如同一个慈祥的父母。人与人和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不象市场经济社会那样凸显利益竞争性,“人性本善”的价值观念不易轻易退去。
然而,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如今,中国终于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它必将对传统的人际关系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造。中国未来的人际关系既不同于过去自然经济下的宗族伦理关系和计划经济下的“单位同志关系”,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因此,中国将会产生一种新的对人性的见解,这一新的人性见解又将创设一种新的法治观念(因为法学是人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