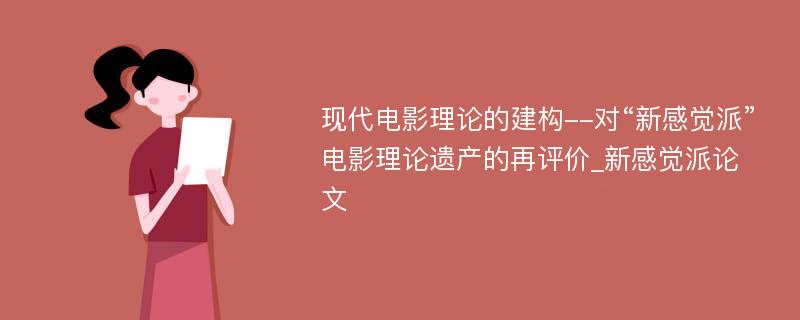
现代电影理论的建构——重新评价“新感觉派”电影论的理论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电影论文,遗产论文,新感觉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1)02-0016-07
一、歧义视野中的“新感觉派”电影论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理论与批评实践中,曾经开展了一场历时三年之久(1933-1935年)的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论争。这场论争是由“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穆时英、黄嘉谟和江兼霞等为主将的“软性电影”论者发起的,挑战和反拨以夏衍、王尘无、鲁思和唐纳等为骨干的“硬性电影”论者,提出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本质特征等命题,与左翼电影人进行了一次关于电影为何存在的辩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硬性电影”的理论和批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追述和阐释,然而,“软性电影”理论和批评一直被遮蔽在绝大多数电影史“宏大叙事”的阴影中。“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后,在“国家危急存亡”、“民族意识日益高涨”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下,难免地,电影史学家会把这场论争置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集团斗争的视阈中,“软性电影”往往作为缺席者接受历史话语的否定审判。根据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评判:软性电影论者宣扬、追捧的“软绵绵的东西”,是“企图杀害‘新生’的中国电影的生命的”,他们主张“制作荒唐淫乐的软性影片”。[1]近年李道新在其《中国电影文化史》中仍坚持认为,软性电影的实质“是为了反对和扼杀所谓‘内容偏重主义’的新生电影”。[2]历史的话语始终站在“硬性电影”这一边。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面前,两者是“围剿”与“反围剿”、“进步”与“反动”的对立双方。
近年来,有一些文章抛开政治视角,从电影本体的立场出发来重新审视这场论争,对“软性电影”基本持肯定判词,同时承认它的不合时宜性。李今女士认为:“软性电影论者的产品,在今天淡化了意识形态之后的文艺观点看来,正属于所谓大众文化模式的几种典型的类型。他们所提倡拍摄的电影,正具有着一种适应着商品规律和城市市民生活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但在当时面临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左翼影评人对他们继续展开的批判,无疑也具有着历史的合理性。”[3]在对“软性电影”重新检视后,钟情于“新感觉派”研究的黄献文进一步指出:“软性论者这时打起纯艺术的旗帜,要求电影与时代保持距离,主张电影躲到艺术的象牙塔里,可以想见其观点是多么地不合时宜。……但是他们尊重艺术的规律,探讨艺术创作应遵循的原则,重视艺术形式的创造,无疑应予以肯定。”[4]以上观点都旨在从电影艺术本身出发树立“软性电影”的正面形象,只不过在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代大背景的笼罩下,“软性电影”论者的先锋论断前途黯淡。
更有许多学者避开这场充满硝烟的“软硬论战”之历史文化语境,渐趋对“软性电影”理论进行正面的重新定位和价值重估。李少白先生在《〈中国电影艺术史〉提纲补叙》中对刘呐鸥和黄嘉谟的电影理论做了提要,并认为:“刘呐鸥的这些理论,撇开它攻击新兴电影的背景目的,就理论本身而言,在当时来说也还是有相当的理论价值的。”[5]郦苏元教授在《中国现代电影理论史》中开辟专节对“软性电影”作了论述,并认为:“‘软性电影’论是中国电影历史上一个复杂的理论现象,需要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并联系过去的历史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它。”[6]胡克教授在《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主要对刘呐鸥的电影观作了论述,并将软性电影理论列为1931-1937年的“三种电影理论共存格局”之一。[7]这些研究都是从“软性电影”论者的电影理论本身出发,撇开意识形态的影响,寻求其理论的价值旨归。
在今天的语境之下,我们倾向于不把以上分歧性的评价看成是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是看成由于学术上出发点或方法论不同而产生的评价错位:一者是从历史和批评的角度出发,一者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根据美国电影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在《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观点,“理论家们总是抽象地处理电影问题的”,“电影理论对电影进行共性研究,而电影批评则从事于个别影片或若干组影片的特质研究”。[8]换言之,历史和批评针对具体电影现象(如作品、作者、思潮等)发言,除了电影艺术的因素,还必然涉及和具体电影现象相关的社会、政治、种族、性别等层面。而电影理论针对一般电影艺术规律发言,其标准可以是抽象的、纯美学的、形而上的。落实到对“新感觉派”电影遗产的评价上,前者自然会把它联系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后者则往往会超越它所涉及的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主张把“新感觉派”的遗产分成理论和批评两个方面(把批评和理论分开来),对其理论上的贡献予以合理的肯定,对其批评上的错误予以揭示。这样才能较为全面地照顾到这一历史现象的复杂性。
基于以上立场,我们认为“新感觉派”的批评是一种“有理论”的批评,但是却是一种没有历史意识的批评。他们也许是仰仗“理论”意识的强势话语而有意拒斥“历史”意识的自觉介入。但是不管他们本意如何,其结果是他们的理论(颇为讽刺和带有报复性地)长期被历史所拒斥。或许,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之时,我们有可能重新评价“软性电影”的理论遗产。
本文试图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阅“新感觉派”文人散见于民国时期各刊物中的电影理论文章,尤其得益于康来新、许秦蓁编的《刘呐鸥全集》(包括文学集、日记集(上,下)、理论集、电影集和影像集),这一学术关注填补了刘呐鸥全部文艺事业历程描述的空缺,还有严家炎、李今编的《穆时英全集》。本文通过梳理、细读“新感觉派”文人在论战内外的电影理论和批评的文字,观照“新感觉派”文人的电影活动轨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他们是否有自身的电影理论体系?他们与中国“宏大”电影理论是一种什么关系?他们的理论书写的文化渊源是什么?他们是否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有独到的建树?期望以此揭示其可能存在的理论价值。
二、“新感觉派”文人的现代电影理论体系
1910-1920年代的中国早期传统电影理论执着于电影与戏剧、文学、美术等息息相关的“影戏观”,崇尚以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为出发点的电影观念,这种美学体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电影理论的主导倾向,[9]代表了中国的“宏大”电影理论的叙事话语。可以说,中国传统电影理论基本把电影定位在“为人生”、“为社会”的艺术,没有从“为艺术”而电影这一理念出发对电影的特质进行深入探究,这一文化图景直到“新感觉派”文人的以探索电影本质特征为出发点的现代电影理论建构后才得以重新描绘。
(一)刘呐鸥:“机械的要素”
中国“新感觉派”文人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文艺界首先是以作家的文化身份立足的,他们的中坚分子主要有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这些作家因为在政治观、艺术观以及对外来影响的态度基本相近,开创了“新感觉派”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特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感觉派”文人都谙熟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各种技巧,在作品的题材、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深受电影的影响,用簇新的形式书写了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景观,创造了小说创作的新类型。作为中国“新感觉派”文学的开创者,刘呐鸥(1905-1940)的一生波谲云诡,但始终与文学和电影结缘。从刘呐鸥在当时各刊物上发表的电影理论文章可以看出他对电影这门艺术已深得其中三昧,形成了一道专业电影人的经验光谱。1928年10月至11月刘呐鸥以“葛莫美”和“梦舟”为笔名在《无轨列车》第4期至第5期上发表了一组名之曰“影戏漫想”的电影理论文章,包括《影戏·艺术》、《电影和诗》、《电影和女性美》、《银幕的贡献》、《影戏和演剧》五篇文章。目前,“影戏漫想”这组文章尚未得到学界的关注,而我们从这组诗性电影文字发现,刘呐鸥正是在此间亮出了他革命性的电影理论观念。在1930-1935年间,刘呐鸥在各期刊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系列电影理论文章:《俄法的影戏理论》、《影片艺术论》、《Ecranesque》、《中国电影描写的深度问题》、《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的电影作者》、《关于作者的态度》、《电影节奏简论》、《电影形式美的探求》、《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其译著有安海姆的《艺术电影论》。在这些文章里,刘呐鸥提出了诸多以电影的机械特性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具体探讨了电影的本质特性,分析了电影独特的表现手法,强调电影作为一门独立艺术的独特魅力,建构了一套纯电影理论、纯视觉艺术理论的观念和体系。
从电影的物质特性和具体的镜头出发关注电影本体是刘呐鸥所有电影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电影的“机械的要素”这一核心美学概念来区别电影与戏剧、文学、绘画、美术等的不同,把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进行审美观照。“表现绘画艺术人们只用了几种颜色,几根画笔,而表现影戏艺术,人们却用了许多机械器具和化学的精制品是事实。这是说影戏里多了些机械的要素。然而正为了这机械的要素的关系,影戏才做了艺术界的革命儿。”[10]刘呐鸥从物质性出发力推电影在艺术界的地位。在《影戏和演剧》 一文中,刘呐鸥进一步强调了电影的“机械的要素”命题,提倡声音是电影进行物质性革命的重要表现。“影戏应该有影戏的特质”,“影戏本来就是机械的艺术,所以就是因此再加上了许多机械的要素。我们不但不应该否定这两种革命的发生,而且应该希望它向这方面大大地发展”。[11]刘呐鸥在有声电影的艺术攀援历程中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而且,正是电影具有的“机械的要素”使得电影能够达到其它艺术所不能达到的技术特性。在《电影和诗》小文中,刘呐鸥感言“影戏是有文学所不到的天地的。它有许多表现方法:有close-up(特写——笔者注,下同),有fadeout(化出),fade in(化入),有double crauk(crank),有higo(high)speed(慢动作),有flash(闪回)……利用着他们这些技巧要使诗的世界有了形象不是很容易的吗?”[12]刘呐鸥在提出电影这门艺术一些独特表现手法的同时,指出了其能有如此的表现魅力在于它本身具有的机械特性。
基于对于电影机械特性的领悟,刘呐鸥在《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一文中提出“非文学的,非演剧的,非绘画的艺术”,所以他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更关注的是电影如何利用这些机械特性去表现主题内容。正是从这样的美学观照出发,刘呐鸥深入阐释了“节奏”、“镜头”、“摄影角度”、“织接(Montage)”等代表电影艺术生命力的美学概念,剖析了电影的内部本体结构。关于“节奏”,刘呐鸥感同身受于现代都市生活的高速度化,认为电影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之所以能够在现代艺术中占着“绝对地支配着”的地位,就因为“它克服了时间”,于是“电影的造型”便代替了一切“静的造型”。掌握好电影的节奏感是电影的归宿所在,毕竟“把现代用视觉的手段组织成为有节奏的东西”是电影的成功标志之一。刘呐鸥熟谙电影的语言系统和电影人常用的表意技术,在《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影片艺术论》中对“不绝地变换着的”观点和作为影片的生命的要素“织接(Montage)”这两个重要美学概念的内涵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所谓“不绝地变换着的”观点即摄影机的位置角度。“影片是对照,highlight(强调)和影的记录,这里面的千变万化尽由光源的位置和Camera angle(摄影机角度)的关系决定。”刘呐鸥从分析摄影机的位置角度出发,阐发了摄影机的功能,通过它的推移、升降等可以形成多样可变的镜头语言。“织接”即蒙太奇,“如果用织接的魔力把这些四角长方形的各片的头尾连接而统归在一个有秩序的统一的节奏之中,这一连的软片便成为有个性的活泼泼的东西”。蒙太奇作为电影独特的创作思维和叙述方式,刘呐鸥对此艺术技巧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二)穆时英:形式本体论
穆时英(1912-1940)作为“中国新感觉派的圣手”,似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中国文化界的天际,即使是生命短暂,也努力在现代电影理论的建构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承袭刘呐鸥开创的“视觉冰激凌”的电影审美观之路,在1933-1937年间发表的理论及批评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电影的散步”系列理论文章,包括(《性感与神秘主义》、《才能演员与风格演员》、《魅力的解剖学》、《文艺电影》、《主题·焦点·尾巴》、《电影的真实与象征》、《电影的两方——印象批评与技术批评》和《劳莱与哈代》等八篇)、《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当今电影批评检讨》、《Montage论》等。在这些理论文章中,穆时英紧紧围绕电影技术的特性是什么这一问题来把握电影的本体,形成了专业化、体系化的Montage理论,并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艺术快感论”。
首先,穆时英认为,作为“第八艺术”的电影,它的存在是摄影机的存在,“它和别种艺术底不同,只是工具的不同,文学作品借文字,绘画借颜料,雕刻借石膏,音乐借音符和乐器,电影则借胶片,演员,摄影师,导演及脚本所共同构成的画面以表现作者的情绪”。[13]169这些包括机械特性在内的各要素,是电影技术特性的具体构成,是电影的形式所在。穆时英还在其他文章中多处阐述电影的形式大于内容的内涵,“电影艺术存在于它的形式上,而不是存在于它的内容上,只有形式是把电影和别的艺术区别开来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相当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物质可以脱离精神的存在”。[13]230显然,穆时英提倡的形式是可以脱离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内容存在的终极目的也是要化为形式以镜头来展现出来,所以,在叩问内容与形式关系的时候,穆时英走的是形式至上一路。基于对“电影特征到底在哪里”这一命题的追问,穆时英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电影的主要特征是以摄影机和Montage为主题的造型艺术这一点上”。[13]241所以,分析电影是怎样用摄影机和Montage来塑造银幕成了电影批评的立足点。
其次,在“电影的散步”系列组文里,穆时英从解构女明星的魅力、演员的类型、电影的主题、真实性与象征性到电影批评的两种不同形态等,对电影理论和批评进行了漫谈。其中《魅力解剖学》一文专门讨论了好莱坞女明星的魅力是如何通过电影的技巧表现出来的问题。“把某一部分的情绪,感觉的特征加以强调,便需要高度的表现艺术,需要摄影、化妆、衣服样式、道具、布景,甚至于导演和Montage 的协助。……魅力的形成,摄影机和化妆术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摄影机的角度可以使嘉宝成为一个讨厌的老巫婆,或者成为神秘的女王。普通全身的大写对于女明星最有利的镜头是三十度左右的仰角。这样拍出来的画面上的黛德丽便会有了谜样的风姿长睫毛,眼成为半闭的,眉梢弯向鬓角,嘴像稍会闭着一点。腮像陷了下去那样的空虚。”[13]182-183可以看出,穆时英从电影的技术特性出发,发掘了电影中女性美存在的理由。在《文艺电影》一文中,区分了电影与文学的不同,“文学是平面的,而电影是立体的;文学是诉于心脏的,而电影是诉于视觉的”。[13]184作为视觉的艺术,穆时英提出用纯电影的手法来表现作品,才能让观者的视觉受到陌生化的冲击,从而产生视觉的快感体验。
最后,在“软硬电影”论争结束两年后,即1937年,穆时英在香港的《朝野公论》上连载了长达一万八千多字的理论文章《MONTAGE 论》,到蒙太奇中去寻求电影的特性成了穆时英后期潜心研究电影理论的方向。遗憾的是,至今学界似乎对这篇理论长文无人问津。这篇文章首先提出Montage是电影艺术的基础,对Montage的三个原则(运动和动作底分解与再建、细部底强调、时间与空间底集中)做了理论联系实例的解读。接着对摄影机的位置和角度、画面剪辑、节奏、音响等技术层面进行了理论探究,形成了完整的蒙太奇理论。
三、“新感觉派”文人的理论书写渊源和价值旨归
20世纪初,欧风美雨东渐,大量西方文化思想和物质文明被引进中国。电影作为从西方传进来的一种“舶来品”,长驱直入到上海这个半殖民地后便掌握着电影工业的放映特权,顺利地进入中国观众的“期待视野”。“新感觉派”文人都是西方电影的追捧者,认为“最能够性格地描写着机械文明的社会的环境的,就是电影”。“新感觉派”文人投身于世界性的文化盛宴,深受诉求娱乐化、商业化的好莱坞式影片的洗礼。同时,刘呐鸥持续不断地潜心于译介西方先进电影理论,从西方电影理论中寻找到支撑自己理论的灵感。他曾经翻译过著名的电影理论家安海姆的著作《艺术电影论》,在上海《晨报·每日电影》上连载了三个月之久,其中主要涉及了电影的“立体在平面上的投影”、“隐射与实体”、“影片底深度感觉地减少”、“空间与时间的连续性底缺乏”、“非视觉的感觉世界底失灭”、“电影底制作——当作艺术手段的开麦拉与画面”、“空间深度减少之艺术的利用”等关于电影艺术特性和技巧的重要问题。他还对苏联电影理论家普多夫金和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观点也进行了纯本体理论意义上的推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译介的同时,西方电影理论以“镜头”、“蒙太奇”、“节奏”等接近电影本体的审美理念渗透到刘呐鸥自身的电影理论建构中,他以电影的机械特性为立足点,以节奏、蒙太奇等美学概念为基础,从各个侧面表达了自己对于电影审美特性的认识,指出了中国电影理论的现代路径。而穆时英更是欧美电影理论的追随者,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他直接援引安海姆的电影观念来佐证自己的论点。如在阐明内容与形式的区别时,穆时英直接援引安海姆对内容与形式性质的理解,来支撑电影之所以成为艺术,关键在于它的形式的完满这一电影观;另一方面,从他的《MONTAGE论》的篇目结构来看,分为“电影艺术的基础”、“分解与再建”、“细部底强调”、“时间与空间底集中”等八方面的内容,与安海姆的《艺术电影论》存在着很多重合处。
需要指出的是,“新感觉派”文人在接受、移植西方电影理论的过程中生发出了自己的创新之处。西方电影理论更多偏重影像的认知心理学。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堡发表了《电影剧:一次心理学研究》,首次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研究电影,他通过分析人眼的视像滞留等生理特点,强调电影依赖观众而存在,之后在安海姆、米特里等西方早期电影理论学者的关注和参与下,对观影的视知觉心理进行了探讨。而新感觉派电影论在观众的审美经验和审美心理学上有更独到的阐发,“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是“软性电影论”的核心表述,他们强调电影的视觉快感,成为今日消费文化语境下电影接受美学的先声。
胡克在《中国电影理论史评》中对“新感觉派”文人对于中国电影理论和批评的贡献的评述极其精到,认为他们“把一种‘纯电影’的观念带入中国,与强调意识形态性的理论观念形成对照”,“是中国比较全面接触西方实验性电影理论的一次机会,填补了一项空白,也是中西电影观念的一次碰撞”,同时“弥补了中国电影观念重视商业电影观念的缺失”,“属于具有相当的美学意义的电影理论态度,他的‘思路逐渐离开具体的社会因素’,去‘探求电影的抽象本性’”。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中西方文化语境的时空维度中,“新感觉派”文人对中国电影该何去何从做出了不同于左翼电影人的回答。“新感觉派”文人走的是西方的电影理论一路,即对电影本体论的研究是以具体的镜头和影像为对象,强调艺术的纯粹性,建构了“纯电影”、“纯视觉”的中国现代电影理论新体系。打破了长期以来电影理论界以“影戏的”、“社会的”电影观垄断的局面,从新的视角探讨电影艺术的内部结构和客观规律,完成了电影理论从现实主义范型向现代主义范型的转向,开创了多元对话的新格局,推动了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性转变。虽然,这一转变只是昙花一现,“社会的”、“教育的”美学体系依然主导着中国的电影理论界。作为历史的一个断裂,“新感觉派”文人无论在电影观念上,还是在电影理论方法上,都提供了一种值得我们今天予以更大重视的理论价值。
标签:新感觉派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电影理论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蒙太奇论文; 刘呐鸥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