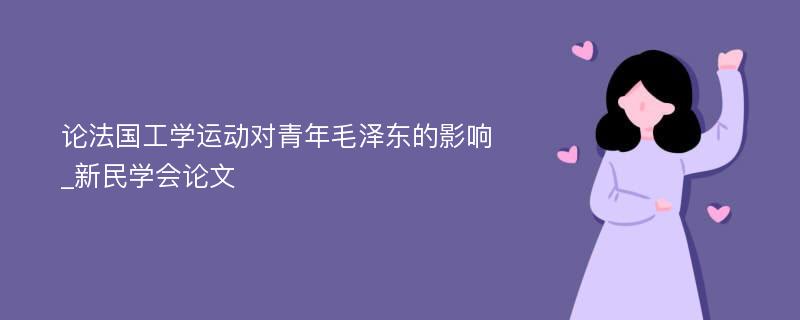
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勤工俭学论文,青年论文,留法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03)03-0023-04
1918年8月,为了筹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到达北京。此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发展,在对各种学说、主义的纵横比较,反复探求中,在国内和赴法留学人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作为一个年青的马克思主义者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一、在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中,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国的第一步
(一)留法勤工俭学为毛泽东等提供了“向外发展”的机遇
新民学会刚成立时,会员首先面临的是“毕业后往何处去”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当他们决定,向外发展,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之际,1918年6月下旬,传来北京正在倡导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毛泽东立即同何叔衡、肖子升、肖三、周世钊、蔡和森、李维汉等新民学会会员讨论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当时,湖南政局动荡不安,学生几至无学可求。新民学会的会员和省城学校许多进步青年渴望到外面去发展;不少家境贫寒的学子对这一消息更是欢欣鼓舞。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刚毕业的毛泽东及新民学会会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向外发展的契机;为毛泽东走出湖南,走向全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二)为筹备勤工俭学工作第一次到达北京
1918年8月,为了筹备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到达北京。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不足,勤工俭学的人员不能马上离京赴法,招来不少怨言。毛泽东一边先把大家安顿下来,一边找人想办法。他与蔡和森等8人挤在三间狭小的房子里,人多炕窄,只能骈足而卧,合盖一床棉被。毛泽东说这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生活得很清苦。毛泽东在杨昌济协助下,几经与蔡元培、李石曾联系,为暂时滞留在北京的湖南青年举办预备班。由于来得人多,并且北京的房租等生活费用较高,于是将预备班分设在北京、保定和蠡县三地。预备班的功课主要是法文,其次是为准备进工厂而设的制图、数学等科。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刚刚创议,为解决经费不足等问题,毛泽东建议先在北京开始勤工俭学。经他接洽,为大家在长辛店铁路工厂谋得半工半读的机会,每月挣三元钱伙食费,暂时解决了经济困难。
由于毛泽东、蔡和森等的积极组织,到达北京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人数达四五十人,居全国之首,得到组织勤工俭学负责人的赞赏。为使勤工俭学工作顺利开展,毛泽东起草了一个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主要内容为:勤工俭学的意义;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初步学会法文,以减少在法的语言障碍;先派少数人到法国去预先布置等。华法教育会同意这个计划,并同意经新民学会讨论和推荐的肖子升作为先行人员赴法。为帮助肖筹集旅费,安顿家庭以及准备行李等,毛泽东四处忙碌奔走。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当年10月16日在给祖父、叔祖父的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
(三)为送别赴法留学人员三赴上海
1919年春天,湖南准备留法勤工俭学青年结束了半年预备班的学习,准备启程出国。3月12日,毛泽东为了给这批青年做赴法的准备,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于17日、31日两次送别了赴法的肖子升等人。7月初,他同何叔衡、熊楚雄等,在长沙送别徐特立等18人经武汉、上海赴法。12月中旬,毛泽东又从武汉绕道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等送行。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第三次到达上海,8日同新民学会会员肖三等旅沪新民学会会员,为欢送即将赴法的陈赞周等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召开送别会。11日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人赴法。在上海期间,毛泽东为筹集勤工俭学及组织革命活动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这笔经费为毛泽东帮了大忙。
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以及此后发动湖南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创办《湘江评论》等活动,毛泽东频繁奔波于京、湘、沪之间。他在谈到这一段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2](P72-73)在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迈出了从湖南走向全国的第一步。这期间,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充分展示了卓越的组织、领导水平以及社交等方面的能力,为尔后领导湖南和全国更大规模的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在组织勤工俭学过程中,接触了北大思想界诸多名流、学者和种种主义、思潮,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在北大广泛接触各类人物,涉猎各种主义
在京组织勤工俭学期间,毛泽东为解决生计、落脚问题,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充分利用和李大钊一起工作的方便条件,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最早地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接触马克思主义。他时常向李大钊请教,并参加李大钊组织的学生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刚刚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大钊又是中国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人。李大钊的言论和行动自然更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使他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P131-132)在京期间,毛泽东还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从此架起了毛泽东与陈独秀直接交往的桥梁。
当时,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各种思潮、学术空前活跃。毛泽东是个渴望知识、追求真理的青年,他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主义学说。毛泽东又极富参与意识,参加了北大的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并旁听课程。还参加了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参加了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演讲团”。这一切,都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还广泛结识名流学者,与不少进步知识青年进行交往。他或登门拜访,或通过湘籍教授、学生引荐,认识、结交了许多名流学者。他曾多次拜访黎锦熙、邵飘萍等,向他们请教留学、治学、办报等问题;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并且与梁漱溟、周作人、徐宝璜等人有所交往;还和康白情一起议论新诗。同时,他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接触了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物。他曾倾向邵飘萍的自由主义,一度受到胡适实验主义和周作人的新村主义影响,还同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过无政府主义。这些名流学者新颖的思想,深邃的学问和其本人所具有的特殊魅力,曾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满足感。在这种独特文化氛围的感染下,毛泽东眼界大开,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
(二)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中形成了自己的留学理论
毛泽东在组织勤工俭学过程中,最终改变了原有的出国打算,对“出洋”有了新的认识,形成自己独特的“出洋”理论。
1、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毛泽东认为:“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3](P339)他强调,“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1](P54-55)他提倡自学、共同讨论,开办自修大学,强调博学。为了改造社会,他主张组织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团体,以便共同讨论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方法,讨论方法怎样实践,以便将来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避免那种个人冥想和“人自为战”的弊病。[1](P53)
2、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在北京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想虽然还来不及消化,但却引起青年毛泽东对研究国情的热情。因此,在送走赴法青年后,他毅然决定暂时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1920年2月,他在致信陶毅时提出,用一二年的时间,将古今中外学术大纲弄个清楚,作为出洋考察的工具。3月14日,又写长信给周士钊,对不出国解释说:“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他认为暂时留在国内搞研究而不出国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得到较多的知识量。第二,世界文明分类东西,我们应该先研究过本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我们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与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再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他还坦率地告诉友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若有工夫能将所提取的东西编成一本书更好。[1](P54-55)1921年1月1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时,毛泽东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毛泽东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拯救祖国、振兴中华,首先就要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开始把社会改造同了解本国国情紧密联系起来。他暂时不去欧洲留学,把时间更多地花在中国,研究中国地盘内的情形。刚刚走出校门,毛泽东的实践活动就带上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强烈的责任感。
3、留学的地点,由重视留法转而重视留俄。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实践中,毛泽东的思想还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越来越赞扬十月革命,向往社会主义。他热烈称颂苏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劳农政府,为“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4]1919年7月21日他撰文《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提出,只有步俄国的“后尘实行社会大革命”,各国人民才能求得自由独立和彻底解放。因此,出国勤工俭学的地点也由法国转而为俄国。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表示,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并说:“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3月毛泽东再次强调说,“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1](P54-55)8月22日,长沙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等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9月毛泽东授意张文亮给陈独秀写信,请他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9月15日,毛泽东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会议公推毛泽东为书记干事,驻会接洽一切。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1](P63-65)毛泽东出国、留俄等设想,由于随后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使他无法脱身,都没有实现。然而,这一时期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在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三)比较、试验各种学说流派,探求改造中国的出路
送走留法青年后,毛泽东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将了解国情、学习各种学问、主义同改造中国紧密联系起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领导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亲拟传单,动员青年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主编《湘江评论》;与湖南进步分子一道进行驱张斗争;酝酿发动湖南自治运动。但这时,毛泽东对各种主义、学说尚未形成明确的态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尚有待确立。
这时的毛泽东,正经历着对刚刚接触的种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比较和选择的阶段。他曾经是“新村”试验的积极分子,第二次去北京期间,他在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后,还计划在湖南组建类似的组织。毛泽东在北大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回到长沙后,无政府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影响着他。毛泽东尚未放弃和平改革的意愿,认为,“较为温和的”,主张“和乐亲善、共臻盛世”的克鲁泡特金派,比之“很激烈的”,主张“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马克思派“意思更广,更深远”。[3]因而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实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毛泽东还曾受到过胡适点滴改良观的影响,把实验主义当作改造社会的指导思想。他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制订章程时,列举144个问题,要求“先从研究入手”,“解决如斯之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向往社会主义,一方面又对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尚未割舍;一方面热烈赞颂十月革命,一方面又主张“忠告运动”、“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改良主义。但是,青年毛泽东是个不懈的探索者,不但好学不倦,而且注重在实践中纵横比较,从中探求改造中国的出路。
三、在对各种主义、学说孜孜以求的探索中,在国内和留法人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迅速完成世界观的转变
(一)出国留学与国内探索,互相交流、互助互益
为了充分利用在法国留学会员的学习成果,并使这些成果尽快运用于国内,毛泽东等在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要求法国会友和在国内一样,定期集会,组织座谈,互相交换、切磋学习成果。蔡和森等先期到达法国后,如饥似渴地学习,“猛看猛译”,翻译出几十种革命书刊,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俄国道路,尤其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有较深刻的认识。1920年7月5日,新民学会留法会友在法国蒙达尼举行会议,在用什么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上出现争论。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肖子升等人则主张实行改良的方法。会议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等,请他们发表意见。
毛泽东大约在11月份看到这两封信。这时他正好在抛弃实行湖南自治的幻想,思想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世界观正处于由改良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彻底转变中。蔡和森的来信,对这一转变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和在法诸会友写了一封长信,坚决支持蔡和森的全部意见,对关于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和俄国道路的主张,尤其“表示深切的赞同”。对于肖子升等人改良主义的方法,“不表同意”。他尖锐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认为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能有的。毛泽东得出结论是: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信中总结自己对于各种主义反复对比探求得出的新观点,说: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P74)毛泽东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影响下,在国内探求、试验、比较各种学说、主义,与赴法留学的蔡和森等殊途同归,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较早接受和坚决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人。
1921年1月1日,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会议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蒙达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结果:第一个问题,到会18人中14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第二个问题,毛泽东等12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2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1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3人弃权。第三个问题,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主的革命团体。在巴黎留学和在长沙探求学问的两地新民学会会员互相交流,互助互益,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在对各种主义的比较、选择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时的毛泽东,对于社会上流行着的各种主义,究竟信仰哪一种,尚在比较选择中。他在北京组织驱张活动期间,同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努力搜寻当时还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较大地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1920年5月毛泽东因欢送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和宜传驱张运动到达上海后,专程到《新青年》编辑部,拜访正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同他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对正在进行思想转变关键时期的毛泽东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P131-132)
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一些信件上写下提要或按语。他在一封讨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信件上写道:“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开始了质的飞跃。湖南自治运动由于湖南军阀的破坏、镇压而告失败后,促使他彻底醒悟。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到:企图利用或依赖封建军阀实行“人民自治”,无异与虎谋皮,他们“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是永世做不到的”。通过湖南自治运动,毛泽东“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1920年11月25日他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他认为,中国革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P71)
湖南自治运动的流产,苏维埃俄国的胜利发展,使毛泽东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启示:依靠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等难以挽救中国,只有寄希望于社会主义才是出路。他得出结论说,看来用老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走俄国人的路,从而认定“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1](P74)。从而与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试验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完成了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上海、巴黎两方面影响,使毛泽东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赴法留学的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毛泽东等早一点,学得也深一些,因此在他们之间共同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信件往来中,无疑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关于建党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入党条件上的原则区别等,并具体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和意见。蔡和森肯定中国不但将有自己的二月革命,而且将有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寄希望于毛泽东能按照列宁的榜样,领导中国的十月革命。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初,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几封最重要的通信,着重地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并达到了完全的一致。毛泽东复信表示:蔡和森9月16日的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信中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知蔡和森,关于建党一事陈独秀等正在进行,并称赞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版的《共产党》“旗帜鲜明”。[1](P80-81)蔡和森的来信,加速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诞生的步伐。1921年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新年大会上,毛泽东与何叔衡等不仅决定以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且毅然作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1](P77-79)这时的新民学会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事实上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湖南小组了。
与蔡和森、毛泽东酝酿建党的同时,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陈独秀从组织新民学会、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才华和能力,并对他寄予厚望。因此,陈独秀一开始就把长沙和其他各地一起列入建党计划。[7](P471)陈独秀不仅给毛泽东寄去青年团团章,还寄去《共产党》月刊,其中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并表示要去亲自参加湖南青年团的成立会议。于是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等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奔赴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组织勤工俭学开始,仅仅三年时间,毛泽东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南北奔走,上下求索,在对各种主义、学说孜孜以求的探索中,在国内和留法人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下,迅速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作为一个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打下了成为一代伟人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3-02-15
标签:新民学会论文; 李大钊论文; 蔡和森论文; 陈独秀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20年论文; 社会主义改造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湘江评论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