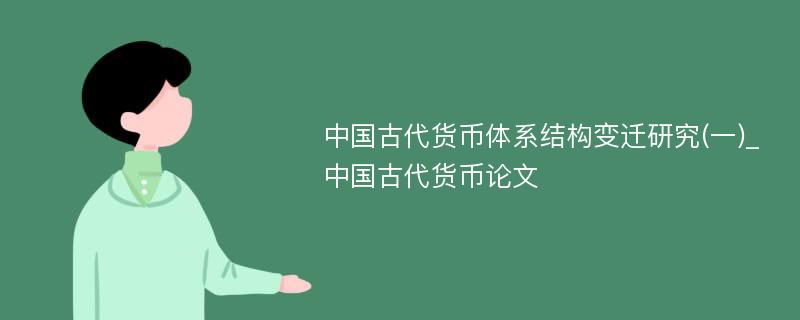
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研究(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货币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货币经济在中国出现很早,并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在对古代货币状况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货币体系、货币结构有过十分重大的变化,中国货币史上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对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研究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货币体系,指的是两种或更多的货币组成的有规律的货币整体;货币结构,指的是构成货币体系的具体货币种类及相互间的关系。货币体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内部结构因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动。货币体系和货币结构的变化,对货币体系本身,对商品流通,对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都有着程度不等的影响。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发达,其间不乏货币体系完整,货币结构正常的时期。大体说来,秦汉时由黄金、铜钱组成的货币体系和明清时由白银、铜钱组成的货币体系是完整的,其结构也是正常的。自东汉末期至明中叶一千二百多年里货币体系出现缺环,货币结构不完整、不正常。在这段不短的时期,由于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出观了问题,引起货币的急剧波动。在近十三个世纪里货币的波动情况是复杂的,波动程度也不一样,研究者见仁见智,提出各自的看法,但却未涉及货币体系和货币结构,一些问题的解释使人觉得不那么妥当,还有一些货币问题则没有进行过研究。本文拟从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发展变化的分析研究入手,解释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的一些问题。
一、对货币体系的认识
由于至今未见对货币体系的研究成果,所以货币体系是否存在的问题需要说明。
我们对货币体系及结构的认识从理论和史实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又分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两部分,马克思的货币理论集中叙述,古代思想家的观点将在后几节和史实结合论述。
马克思对货币体系问题进行过探究和分析。马克思对货币体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在开始货币的分析研究时曾着重说明“在以下的研究中要把握住,我们所谈的只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如信用货币。”〔1〕这表明,我们所要研究的中国古代货币体系、货币结构,属于马克思分析研究的范围。
马克思对货币体系的分析研究是从对铸币的论述开始的。马克思认为,铸币在流通中会受到磨损、“它在尘世奔波中磨来磨去,日益失去自己的含量。它因使用而损耗。”〔2〕从而铸币金属的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逐渐出现差异。“在流通速度不变时,铸币流通得越久,或者在同一时间内它流通得越活跃,它作为铸币的存在就越是同它的金银的存在脱节。……其他物因为同外界接触而失掉了自己的观念性,而铸币却因为实践反而观念化,变成了它的金体或银体的纯粹虚幻的存在。”〔3〕铸币逐渐成为其金属含量的象征,“这样,由于流通过程本身,所有的金铸币或多或少地变成了白己的实体的单纯符号成象征。……由于金变成了它自己的象征,又不能当作自己的象征来用,所以它在自己磨损得最快的范围内,即在买和卖以最小规模不断重新进行的范围内,取得了一种同它的金存在脱离的象征性的存在即银存在或铜存在。在全部货币中总有一定部分(显然不是同一些金块)在这个范围内当作铸币来流通。这一部分金就被银记号或铜记号所代替了。”〔4〕处于流通的铸币本身的特性允许不止一种币材的多种铸币同时存在,“因此,如果说能够作为价值尺度,因而作为货币在一国之内发生作用的只有一种特殊商品,那末、当作铸币来用的除金外可以有几种商品。”〔5〕为了保持铸币的相对稳定性,“因此,在一切流通发达的国家中,由于货币流通本身的必要性,不得不使银记号和铜记号不论损失多少金属仍具有铸币资格。”〔6〕这样,作为流通货币的铸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特性使流通山多种货币的并存成为必要和可能。在论述了铸币,说明在流通过程中将出现多种铸币之后,马克思又论述了非流通状态的货币。非流通货币表现为“货币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三种运动形态.用于贮藏、支付和平衡国际贸易差额。三种运动形态都体现了完全货币的基本职能。〔7〕处于非流通状态的货币既有铸币形式.也有非铸币形式即抛弃了形状和官方印记的无差别条块形态的货币。从马克思对流通状态和非流通状态的论述可以看出货币的种类是很多的。
多种类的货币并非一盘散沙,随意组合,它们的存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表现出货币的客观规律,它们是按照货币规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的。有规律的货币组合是多样的,分层次的,如流通状态货币和非流通状态货币就是其中一种,本文所要探讨的货币体系也是遵循客观规律的货币组合方式之一。
在论述了处于流通的铸币后,马克思提出了“辅币”和“货币”概念并论述了其发展演变过程。马克思指出:“用银铜等金属记号作的辅币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价值较低的金属过去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例如银在英国、铜在古罗马共和国、瑞典和苏格兰等地,直到流通过程把它们降为轴币和贵金属代替它们为止。”〔8〕铸币在流通中发展演变的结果是“辅币”和相对应的“货币”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较低的金属在流通中降为辅币。相对应的由贵金属充任的不被称为“主币”而是被称为“货币”。马克思这样考虑是严谨而审慎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所研究的是”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那些货币形式.而不是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那些货币形式。”近世货币学所提出的,属于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货币形式的,有主币辅币之说。近世货币学所说的主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辅币没有主币的这种能力,处于从属地位,主辅币相互之间并不相权,而只是主币权辅币。古代货币,即从商品交换直接产生出来的货币形式并非如此。拿中国古代货币来说,在货币体系完整时,不管是秦汉的黄金和铜钱,还是明清的白银和铜钱,都各自具有无限的法偿能力,彼此相权。把古代货币的这种构成称之为“主、辅币”不恰当,所以马克思用了“货币”一词和辅币相对应。这里需要说明,马克思在货币理论研究中使用的“货币”一词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全部货币的指称,另一层是指和铸币不同的非流通的货币形态.在货币研究中要注意区分。〔9〕
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了“辅币”和“货币”,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也就是形成了一个体系,我们将之称为货币体系。由“货币”和“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的形成原因,马克思是这样解释的:“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各个国家都觉得用银计算比用铜计算方便,用金计算又比用银计算方便。随着国家日益富裕,国家就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10〕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促使货币体系形成,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又决定着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商品流通情况是由贵金属充任的“货币”和由贱金属充任的“辅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形成的根本原因,商品经济的具体情况也极大地影响着货币体系的发展演变。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我们知道,在还没有达到生产过程较高阶段的古代,货币体系的存在是可能的;在相应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货币体系的形成则是必然的。下面我们依此从货币体系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古代货币史。
二、货币体系的形成
西周以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货币使用也不普遍,到了春秋战国,货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论述就从春秋战国开始。
春秋战国是一个急剧动荡变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地权逐渐松动,“田里不鬻”的局面逐渐为土地私有所代替,以地权凝固的公有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解体,“工商食官”制也被打破,经济空前发展,商品经济有了长足进步。在这种基础上,货币日益活跃.齐刀、赵布、秦圜钱流通领域日益扩大,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长江流域,楚国的郢爱和蚁鼻钱也在中国货币总体中占了一席之地。虽然在诸候纷争的局面下货币无法统一,完整的货币体系还不能全面地建立起来,但史料表明,由两种以至更多种不同币材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已为当时的思想家认识到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系统而又扼要地论述到货币体系的思想家是单旗。单旗.史称单穆公,是周景王的卿士,他在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提出了货币子母相权论。他说:“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货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为潢汗也。……夺之资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11〕史载这是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时提出的,从其议论可以看出,他不是简单地反对铸大钱,而是反对周景王“废轻而作重”。单旗提出了轻重概念,认为轻重两种货币应该并存,“权轻重以振救民”,而且依时而变异,“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如果货币过重,使民“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一旦这样做,使轻重币子母相权,并行不悖,就可以“民皆得焉”,“小大利之”。单旗所说的轻重,是指货币对商品的不同比价,并不是指货币本身的轻重,也就是并非后世出现的虚价大钱。《管子》言:“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12〕“粟重则黄金轻,黄金重则粟轻,两者不衡立。”〔13〕就说明了这一点。单旗认为要根据社会需要发行轻、重两种货币,从而构成了货币体系,如果“废轻而作重”,货币体系便被破坏了。用现在的话来说,单旗反对的是周景王对货币体系的破坏,他论证了货币体系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所以说,单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由轻重两种货币组成货币体系的理论的思想家。
单旗所处时代是春秋末期,在那个时候商品经济已经以空前的态势发展起来,“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自然需要“使价值较低的金属变成辅币,使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贱金属充任的辅币用于零星小额交易,贵金属充任的货币用于大额交易,在商品经济处于上升的时候,是需要的。到了战国,商品经济发展态势进一步扩大,对由两种以上不同币材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的货币体系的需要也进一步加强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对此也有反映。《管子》中多次提到货币体系,《管子·国蓄》写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以平天下也。”这是提出珠玉、黄金和铜钱三种货币构成货币体系。至于“黄金、刀币,民主通施也。”〔14〕“黄金、刀币者,民之通货也。”〔15〕则是把货币分为黄金、铜钱两等,组成轻重不等的货币体系。
先秦的货币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割据性,无法形成统一的完整货币体系。六国灭亡后,货币也统一了,秦王朝把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为上币,以镒计,属称量货币;铜钱为下币,是重如其文的“半两”铜铸币。这样,由国家法令规定,“价值较低的金属”铜变成了“辅币”,“价值较高的金属”黄金则变成了“货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完整货币体系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当然,秦的货币制只不过是春秋战国空前发达的货币经济的制度化。
秦祚不永,两汉代之而兴,刘汉王朝革除了秦的不少弊政,两等货币构成的货币体系则保留下来,只是根据社会认为秦半两钱过重的情况,“多作轻以行之”,具体措施是“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16〕放开铸币权的结果是劣币充斥,物价上涨,“米至石万钱”,〔17〕西汉政府不得不着手稳定货币。从吕后至武帝,七十多年中九次调整铜铸币的法定重量,最后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由中央政府垄断铸币权,发行五铢钱,货币得以稳定下来。
西汉政府整顿稳定货币的着眼点主要是铜钱,目的在于把铜钱的法定重量从不适宜的半两降下来,以适应经济的需要,作轻以行之。对作为上币的黄金也有改作,但仅是在称量单位上调整,改镒为斤。在汉代(新莽除外),从法令上说,以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没有改变。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经济持续发展,商品流通日益兴盛,形成我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由贵金属黄金和贱金属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就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它是完整的、结构也是正常的。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演变中虽有波折,但这个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存在下去,直至东汉末。
三、货币体系的破坏
秦汉时期形成的完整货币体系是稳定的。两汉之间的新莽曾对货币作了四次大改变,废弃了原有的简明适用的货币体系,代之以泥古不化的币制。王莽四次币制改革的根本缺陷在于过于繁杂,改变太快太频,使人无以适从。仔细看一下可以发现,王莽币制改革中第一次泉刀制,第二次的大小泉制,第三次五光十色的宝货制,第四次的泉布制,都有着货币体系的含义。王莽灭亡后不久,东汉政府就又恢复了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这说明简明适用的货币体系是合理和稳定的。
经过长期演变,到公元二世纪末,原有货币体系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进而对货币自身并通过货币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影响。
货币体系的这一次结构变化是长期而渐进的,较具体的时间可以探究到东汉末期,到那个时候,原有的货币结构,也就是由黄金充任的货币及由铜钱充任的辅币之间的原有关系已发生了变化。具体情况是黄金退出了货币行列,这一来,秦汉时形成的货币体系解体了。
秦汉时期形成的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经历了两汉,维持了数百年时间,黄金和铜钱之间的相权比价基本稳定,大体保持在黄金一斤兑一万铜钱的水平。黄金在两汉主要用于赏赐、捐税征收、赎罪费、贿赂等的支付上,也用于货币贮藏和平衡国际但易差额的世界货币方面。〔18〕西汉时期黄金使用次数多,数量也大,到了东汉黄金的使用次数和数量从史料看比西汉有较大减少。到东汉结束,黄金基本上退出了货币行列。黄金在经历了汉代后退出货币行列的原因和具体过程经专家学者多年探究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也不拟探索。这里需要认识到的是,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使秦代正式形成的货币体系发生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由黄金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就这样缺了不可缺的一环。
货币体系的结构变化对货币本身的影响是重大的,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各种情况的变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逆转,从而援和和减弱了货币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
四、商品经济低潮时期的货币体系
东汉之后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是复杂的,就对经济的直接影响来看,主要因素是世族和均田制。
世族的兴起经历了较长时期。汉代是豪强地主、世族地主的形成时期。到东汉末,世族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力量,左右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世族的兴盛标志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深刻改变,这一系列变化的核心是土地私有制的衰落,土地私有制是在秦汉得以确立的。土地私有制衰落,地权日益凝固,减少了用于交换的土地数量,均田制在北魏的颁行及隋统一后向南方的推广进一步从法令上强使土地退出了商品行列。地权凝固不仅使商品总额中少了土地这一大块,同时也对商品生产产生消极影响;遍布南北的世族庄园趋向于“闭门成市”的自给自足经济,这一切,导致了自东汉末到唐中叶商品经济的回落。加之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长期战争破坏了黄河流域的繁荣,而长江流域一方面开发程度尚低,一方面战争也不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现实使“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的增加”这一促使货币体系形成的因素急剧逆转。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是货币体系形成、维持和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商品经济的衰落则使货币体系的维持和发展失去了基础。这样,虽然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使已然形成的货币体系缺了不可少的一环,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势头出现逆转,自然经济代之而起成为经济的主要体现,社会经济对完整货币体系的需求降低,所以货币体系重大结构变化的影响在自东汉末至两税法颁行这段时期延缓、减弱了下来。
在魏晋至唐中叶约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经济总的趋势是衰落,相应的是自然经济抬头,实物交易盛行。但在特定时期的局部地区,以及如唐前期全国范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商品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商品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有所表现。
西晋覆亡后中国进入了战乱不已,南北对峙的时期,总的来说经济受到极大破坏,但具体看南北有所不同。一般说,北方战乱在次数和烈度方面超过了南方,相对而言南方较为稳定和平。南北朝形成后黄河流域也稳定了下来,但北魏颁行的均田制从法令上限制了土地买卖,对商品经济的制约很大,而南方则出现几次稳定、繁荣时期,如“元嘉之治”、“永明之治”,梁武帝治下也有数十年的和平繁荣,南方的开发在这一时期有较大进展。南北相比,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北方,货币体系的存在、维持在南方具备了一定条件,有所表现。
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部分实物进而填补空缺,其中较著者是粮食和绢布。刘宋时周朗论政,涉及货币问题:“今且听市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周朗认为“如此,则垦田日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人死必息”〔19〕。他把铜钱的使用范围限制于千钱以内的小额交易,千钱以上的大额交易则使用粮食、绢布等实物。在这里不难看出货币体系的影子,尽管粮食绢布等实物不是合适的币材。南朝另一个表现货币体系的是“短陌”现象,萧梁时尤为突出,相较之下,北方尚未见类似记载。关于“短陌”问题将另文探讨,这里就不展开了。
货币体系中由于黄金退出而导致的结构缺环在相应的条件下有弥补的需要,这在南北朝特别是南朝有所表现,到了隋和唐前期这种需要就更明显了。在隋和唐前期,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即推广到全国的均田制和世族影响依然存在,商品经济还只是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但毕竟出现了较长时期大范围的稳定和繁荣,特别是唐前期一个多世纪里政局基本稳定,经济繁荣,使填补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需要加强。社会经济的需要促使绢帛加入货币行列,和铜钱一起流通,形成“钱帛兼行”。绢帛作为货币,用途是广泛的,既用于大额交易,也用于零星小额交易。但绢帛的自然属性使之作为交换媒介难以尺寸分裂,主要以匹计,这使得绢帛更适用于大额交易,同时黄金退出后形成的结构缺环也是用于大额交易的“货币”。这样,“钱帛兼行”的局面大致是绢帛充任“货币”,以补货币结构的缺环,铜钱还是主要作为“辅币”在零星小额交易中起作用。这一点,从政府法令中也可以看出,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十月六日敕:“货物兼通,将以利用,……自今以后,所在庄宅口马交易,并先用绢布、绫、罗、丝纬等,其余市价至一千以上,亦令钱物兼用,违者科罪。”〔20〕明确规定了绢帛等纺织品主要用于大额交易。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钱荒”已困扰社会,唐政府要求交易中使用绢帛时亦明确说:“公私交易十贯钱已上,即须兼用疋段。”〔21〕按此法令,十贯以下(是时物价较之开元年间已大幅度上涨)的小额交易是不要求用绢帛的。唐代政府法令所规定的,和刘宋时周朗的见解有相似之处。绢帛在充作货币时主要是用来填补黄金退出后货币体系所缺“货币”一环的,这所缺一环本应由价值较高的金属充任。以上迹象说明,在两税法之前的六个世纪中,尽管商品经济发展处于低潮,但社会经济对货币体系的需求还是有所表现。
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在东汉末至唐中叶的六个世纪中由于商品经济的低落而被延缓和减弱了,在这段不短的时期,始终没有“价值较高的金属变成货币”,以填补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空缺,绢帛等实物弥缝其间,一定程度起到代替贵金属的作用,但绢帛等实物的自然属性并不适于作币材,绢帛和铜钱构成的货币体系结构不正常。这样,经过六个世纪,黄金退出所造成的货币结构缺环实际上依然存在,一旦商品经济重新获得发展,货币结构缺环对货币自身及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影响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以两税法的颁行为转折,货币体系结构缺环的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各个方面。
五、两税法后货币体系受到的压力
经过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之后,在东汉末期开始,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低谷。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世族的兴起,二是均田制的颁行和推广。在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持续开发,尽管局部地区在某些时期稳定繁荣,甚至在唐前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出现全国范围的和平稳定,这些条件都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受世族和均田制两大因素制约,商品经济始终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这一局面,到唐代中叶有了根本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是世族最兴盛的时期,同时世族的各种弊端也就是在这期间迅速膨胀,世族的力量全面趋于下降。隋唐行科举,废除九品正制之后,失去活力、素质日渐降低的世族丧失了做官特权,进一步衰落。到了唐代中期,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世族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已如强弩之末。均田制自北魏太和年间以来之所以屡废屡兴,在于多次战乱造就众多无主旷土以供给授,一旦出现长期和平,无主旷土和新垦土地供不上给授日益增多的人口,均田制就无法维持了。如北宋刘恕所言:“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22〕至唐中叶,统一、稳定、和平局面延续了一百多年,人口增长很快,已无足够的无主土地按均田制的法定数字给授,加之土地买卖突破均田禁令日益盛行,“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23〕禁止土地买卖的均田制逐渐被侵蚀,且无法按法令如数授田,趋于瓦解。唐政府为解决财政税收问题,承认了现实,于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行了两税法。这样,到唐中叶,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世族和均田制,或衰微或结束,从此,“商品经济否极泰来,又向前发展了。”〔24〕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唐中叶起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两税法的颁行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的重新确立,这一变化,从两个方面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按照法令土地可以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衰落了的世族已没有力量象在魏晋南北朝那样把土地长期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地权凝固。在农业社会,进入流通的土地是价值很高的商品,这就大幅度增加了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另一方面,经过长期开发,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南方经济已有长足进步,南方的产业结构变化也已经开始,经济作物普遍种植,这也大幅度增加流通中的商品价值总额。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唐代和秦汉时期相比,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质上是一样的,但在量上看,由于南方的开发,耕地面积唐代比秦汉时有较大提高,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就决定了唐中期以后的土地商品量要比秦汉时期大。从第二个方面考虑,南方多丘陵山地,纬度低,水面也较广,水热条件远远优于北方,很适宜茶叶,桑、漆、蔗、药材、果木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其在农业中比重的增大,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土地自由买卖和南方的开发相结合,有利于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户、半专业户产生及扩大生产规模,因为种植经济作物对技术要求较高,土地自由买卖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专业户、半专业户扩大生产提供了便利。专业户种植的经济作物除少量供自己消费外,大部分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李埏教授指出,在秦汉商品经济第一个高峰时期,执商品界牛耳的是盐铁酒酤,到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进入第二个高峰,情况有很大变化,由于南方的开发及经济作物大量种植,大量绢、茶、漆、蔗等进入商品流通,其中绢和茶不仅和盐一道成为最大宗商品,而且还越过国境,输往域外。〔25〕这决定了土地以外的商品量,唐中期以后也要比秦汉时期大得多。综合言之,同样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由于南方的开发,唐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秦汉时期。商品经济“这次发展的势头是那样强而有力,甚至唐未五代的军阀混战也未能使这逆转。”〔26〕从唐中叶起,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高峰,“这个高峰,比第一个高峰更高。”〔27〕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货币。
除上述两大方面外,商品经济影响下的货币本身变化也增大了货币所受压力。两税法以前,货币行列中长期有绢帛这一实物,而且在相当程度上绢帛代替贵金属起“货币”作用。绢帛的自然属性并不适宜作货币,唐政府屡次用法令强调绢帛的货币地位说明在日常商品交换中绢帛的货币作用在减弱。在商品经济受某些因素制约而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时,绢帛的货币地位还能维持,一旦商品经济摆脱了限制重新兴盛起来,商品交换对货币的属性要求也随之提高,绢帛就无法在货币行列中呆下去了。两税法颁行后,绢帛逐渐退出货币行列重新还原为普通商品,“钱帛兼行”瓦解。一种曾在相当程度上起过和辅币相权的“货币”作用的实物退出了货币行列,它不仅不能充任其他商品的交换媒介,而且反过来要货币充当自己的交换媒介,成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增加”的一个因素。这一增一减,无疑加大了对货币的压力。
货币及货币体系的存在和发展情况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两税法颁行后,以土地重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为契机,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骤然大幅度增加,并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保持了向上的势头。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对货币及货币体系的需求有相当可观的持续的增长,而黄金退出货币行列后造成的货币体系结构缺环还没有补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快陷入窘境。
商品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压力,货币体系重新形成的势头,在两税法颁行后明显加大,“钱荒”是其表现。两税法颁行以前,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长期物价上涨,钱轻物重。两税法颁行后不久,虽然唐中央政府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止,但很快出现钱重物轻的现象,流通中的货币日益感到不足,形成了“钱荒”。
“钱荒”主要表现为流通中铜不足,时人所议论的也多是就铜钱论铜钱。这是因为自黄金退出货币行列之后,始终没有贵金属能够加入货币体系,起到和辅币相权的“货币”的作用,绢帛一度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两税法后也已逐渐退出,只剩下铜钱唱独角戏,起主要流通媒介的作用。流通媒介的不足,自然具体而形象地表现在铜钱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钱荒”的延续,很多迹象表明,货币的不是不仅仅是铜钱的不足,商品经济日益繁荣所形成的对货币的压力很快就体现在货币体系上。(未完待续)
标签:中国古代货币论文; 铜钱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货币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均田制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