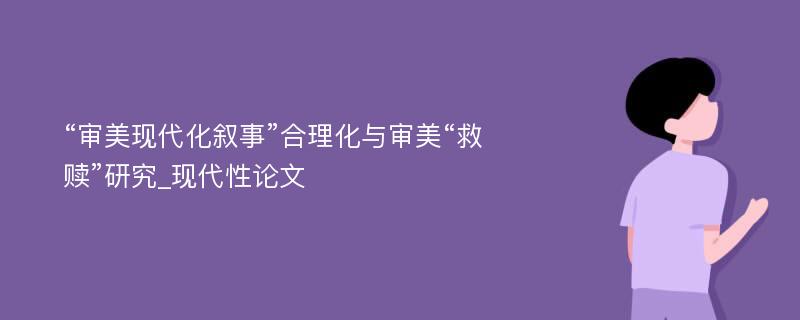
“审美现代性的叙事”研究——合理化与审美“救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化与论文,救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的话:作为宏大叙事,现代性可谓无所不包。举凡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均可收入其内加以辨析审视。作为小叙事,审美现代性则专指与现代艺术活动密切相关的问题。编排在这里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以现代性的大叙事为背景,又把焦点集中于审美现代性的小叙事,分别讨论三个有趣的问题。《合理化与审美“救赎”》以现代性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为题,围绕着他著名的“合理化”命题展开,着重分析了在现代合理化进程中审美所承担的独特功能,进而深入剖析了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意义,以及作为审美现代性表征的艺术自主性的复杂意义。《先锋派的两个现代面相》以20世纪独特的先锋派艺术为研究对象,作者集中笔力分析了先锋派的商品和技术这个层面,透过先锋派理论的解析,揭示了先锋派在现代文化中所呈现出来的复杂面相,由此揭橥了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艺术体制与纯美学的去魅》一文,通过对艺术这一现代体制的考察,质疑了纯美学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论断,从而强调现代艺术乃是受制于象征价值和文化资本体制运作的根本特征。这三篇文章理论角度不同,各自结论也不尽相同,它们构成了一个对话语境,促使我们进一步思索审美现代性问题。
一、合理化与现代性的困境
合理化作为韦伯全部社会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是理解韦伯社会学主题的一个中心概念。正如德朗蒂所概括的那样:在韦伯的社会学里,至关重要的概念即合理化的观念。现代性带来的正是合理化过程在宗教、经济、法律和科层制等领域中逐步展开的进程(注:德朗蒂:《社会理论的基础:起源与流变》,见布莱恩·特纳编,李康译《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对于韦伯而言,首先是由宗教改革开始走向世俗化的宗教伦理,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力量并成为现代性进程的关节点。在他看来,开始于16世纪初的欧洲宗教改革,倡导的是一种对于世俗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为此,一方面宗教伦理借助一种合理化的手段对世俗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自律要求,力图以此强化对世俗的掌控;另一方面为了获得世俗的成功,这种合理化的手段也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决定性的发展。最初逃避尘世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由此开始把自己的规矩条理渗透到生活的常规之中,把它塑造成一种尘世中的生活。然而这种生活对于宗教而言却是灾难性的。因为一方面,宗教伦理越是具有影响力,也就越是因为自身的出世本质,与世俗的要求处在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之中;另一方面,宗教伦理通过其合理化进程而获得巨大的世俗约束力的同时,也促使经济、政治,直至审美与性爱等领域在合理化之路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存在合理性,并开始对宗教所提供的各种所谓理性规范提出了质疑。
这种质疑首先集中表现在文化领域的价值分化之中。这种分化不仅是宗教与世俗的一系列张力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更是西方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领域一方面摆脱宗教的束缚,获得了世俗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又在这一过程中各自获得了区别于其他领域的自主性。这意味着原本在那个宗教—形而上学的世界中统摄一切的文化力量,如今已经分崩离析。而代表着这种文化力量的宗教伦理所提供的文化价值,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了。
与此同时,文化的合理化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分化还只是合理化进程中表现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表现在具体的世俗社会生活之中的合理化现象。韦伯所理解的排斥宗教的颠覆性力量也同样来自于此。正如哈贝马斯所分析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的合理化形式。韦伯一方面关注的是世界观的合理化;另一方面关注的则是沿着宗教合理化的道路逐渐形成的现代意识结构在制度上的体现,也就是关注文化合理化向社会合理化的转换(注: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借助宗教伦理的力量获得最初的发展权之后,也在社会合理化进程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直接推动力。
但是这样一个合理化世界必然来临的事实,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人们可以欢呼雀跃地跨越传统,走向现代。韦伯通过其敏锐的观察,为我们揭示出了这一事实背后所暗含的激烈冲突。在他看来,这种冲突首先表现在:伴随着文化合理化而来的价值领域的不断分化,传统的宗教—形而上学世界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彻底失去了整合一切的神圣性。它为这个世界所提供的意义从此在价值领域的四分五裂中遭到了支解。价值分化因此不仅造成了宗教的衰落,还将现代社会带入到一个“诸神纷争”的意义混乱的时代之中。这正是个体必须面对的现代性的基本困境之一。
另一方面,在各种理性秩序之间还存在着第二种冲突,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61页。) 之间的冲突。韦伯最终对现代社会进程所作的基本诊断,是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目的理性对现代生活的全面征服。
在齐美尔看来,目的为手段所遮蔽是现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人类的愿望越来越容易陷身于手段的迷宫,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的目标最终沉入地平线下(注:齐美尔著,顾仁明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页。)。当韦伯指出“行为越是严格地让目的合乎理性,就越是对既定的情况作出相似的反应,因而就产生行为和态度的相同性、规律性和持续性”(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6、61页。) 时,他其实也就意识到了这种所谓目的合乎理性行为的工具性本质,意识到了现代社会已经通过一种世俗生活的社会合理化,将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然而就是这种工具理性,却在社会合理化的过程中成为现代性的基本推动力,成为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理性原则。社会合理化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的“科层化”因为一种非人格化和专业化精神而成为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在这种体制中,个体寻找不到自己的未来,也用不着寻找自己的未来。这意味着,对个体而言自由在这个世界中也成为多余物。
这样,文化合理化的过程带来了意义的丧失;社会合理化的过程又带来了自由的丧失;工具理性大获全胜并成为指导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韦伯为我们展示的这个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社会生活,构成了现代性的最基本内容,并成为现代西方学者一直苦苦思考的热点问题之一。齐美尔通过对客观文化的分析作出了类似的诊断,并提供了一个“距离”概念作为对抗它的可能方案。而对于韦伯来说,人无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中都应当有价值地生活,应当始终有一个为他或她的行动提供意义的庇护神。既然曾经为人们的行动提供意义的宗教伦理已经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那么谁又能在宗教伦理倒下的阴影里站出来对抗这个世界的冷漠和无情呢?韦伯由此实际上已经将问题转入到:在这样一个启蒙的现代性占主导地位的合理化世界中,如何寻找到一种可以体现文化意义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阻止或至少是减少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恶果?
二、审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
此时我们再回到价值领域分化的讨论中,才能够理解韦伯为我们描述的“诸神纷争”境况中的乐观因素:文化合理化所带来的价值领域分化虽然导致了意义的混乱,却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意义的彻底丧失。因为在这里,仍然存在着拒绝工具理性主宰一切的力量,它们借助于韦伯所揭示出来的另一种理性——价值理性,获得了完全不同于工具理性世界的存在方式。换句话说,在宗教伦理没落的地方,仍然保留了分化的事实所带来的更多可能性。就是在这个地方,韦伯特别注意到了艺术(审美)的力量,作出了这样的判断:在生活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艺术正越来越变成一个掌握了独立价值的世界。无论怎样解释,它确实承担起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从而将人们从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从越来越沉重的理论的与实践的理性主义的压力下拯救出来(注:H.H.Gerth & C.W.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342.)。用魏尔默的话说则是:“这个现代世界已不断地揭示了它可以动员一些反抗力量来反对作为合理化过程的启蒙形式。我们也许应把德国浪漫主义包括在内,但也包括黑格尔、尼采、青年马克思、阿多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大多数现代艺术。”(注:转引自周宪《现代性的张力》,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这意味着,现代性在其社会合理化过程中所发展出来的一个工具理性的世界,并不是现代性的全部内容。在这个世界之外仍然存在着另一种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一种由文化合理化及其价值领域的分化而带来的价值理性力量。价值理性以其对行为的固有价值的无条件追求而与工具理性处于无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它能够与工具理性始终保持一种对抗性的关系。韦伯的社会学主题所包含的美学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从审美现代性的立场出发,我们看到,当宗教与世俗的张力因为前者的衰退而自然消解,当传统不得不走向现代之后,和解并没有伴随着现代性的进程而出现;相反,一种来自于现代性内部的新的冲突又重新构成了新的张力。简单地说,如果前一种张力是由宗教伦理对世俗的规范性力量与世俗自身的合理化力量所构成的;那么后一种张力则是由合理化之后的工具理性社会与同样来自现代性自身的合理化进程的文化质疑所构成的。
尽管韦伯并没有使用过审美现代性这一术语,但他所表达的却正是审美现代性的精髓所在。可以说,自从审美现代性生成之日起,它就一直与这个工具理性世界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状态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对立既是审美现代性必要的存在方式,更是它推动现代性进程的动力所在。它同启蒙的现代性所构成的矛盾性,将现代性变成一个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的未完成的过程。如鲍曼所言:现代性的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注:鲍曼著,邵迎生译《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页。)。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也准确地把握了这一张力中两种现代性的激烈对抗(注: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页。)。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与以价值理性为依据、以现代艺术为核心内容的审美现代性,构成了这种张力的两极。
由此可见,如果说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全部悲观看法最终都指向了工具理性对现代生活的无边侵蚀,那么他在这种悲观之外,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从这种侵蚀中解救出来的诸多可能性。他在艺术那里看到了希望,并保持某种谨慎的乐观。
从韦伯的社会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构成前者对后者之工具理性的反抗,这种反抗正是人们阻止或至少是减少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恶果的希望所在。审美现代性从自己的角度看到了弗莱所指出的那个将现代人困囿其中的“幻觉的牢房”(注:弗莱著,盛宁译《现代百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因此重要的是首先要意识到它是一种幻觉,是一个牢房。对于审美现代性而言,这意味着,它的现代视野与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启蒙现代性判然有别。
如果说宗教与世俗的分离来自于合理化进程中的一种无可调解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宗教的衰落,那么同样作为合理化进程中一个基本事实的现代文化与其社会之间的分化,则来自于一种自觉的反抗意识。它意味着只有在启蒙现代性之外提供一种颠覆性的力量,才能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以避免这个社会彻底沦为工具理性的囚牢,或者至少,可以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提供一种世俗救赎的可能性。韦伯由此出发,看到了艺术所具有的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由此引出了一个以审美为核心的现代救赎方案。
三、从艺术自主性到审美救赎
我们知道,在一个宗教统摄一切的传统社会中,艺术的存在依据并不是完全由其自身就能获得的。从目的或功能上看,它是完全融合进了被称为“宗教”的社会体制之中,作为一种宗教的崇拜物而存在的。这意味着在宗教艺术中,既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艺术家,也不存在独立自主的观众或读者,更不存在自主独立的艺术及艺术观。因此在韦伯看来,在传统或前现代的艺术中,艺术的内在逻辑一直是混乱的,因为形式总是从属于内容的:艺术技巧的独立发展永远依附于宗教伦理和救赎的目的(注:沃林著,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6、115页。)。但是同时,艺术与宗教伦理之间也存在着紧张,亦即宗教所要求艺术表现的内容与艺术自身的感性形式之间始终存在着张力。因为后者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地超越宗教寓意本身的要求不仅随时随地都在折磨着艺术自身,也同样在不断地威胁着宗教的存在。对于合理化进程中的新教伦理而言,严重的问题是,艺术的这种要求在合理化的进程中已经不断表现出了摆脱宗教束缚的巨大潜能。
韦伯以音乐为例,认为完全理性和谐的音乐,只是在西方才真正出现过。其合理化,首先是在音乐内部。一方面表现在乐理层面,通过理论重构达到音乐的系统化,借此将神秘的而深不可测的美感经验予以知识化,这就是一种美感经验的“祛魅”过程(注:陈介玄:《韦伯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69页。)。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乐器方面。乐器的技术发展本身,体现了艺术在其表现形式上的合理化程度。伴随着艺术自身的理论与表现技法的不断合理化,宗教在艺术那里不断地遭到了祛魅。宗教那些曾经对于艺术而言的神圣权威,则在这一祛魅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威慑力。而这一切,也正是艺术走向自主性与自身合法化的最初体现。
这些理论的、技法的不断合理化,却并不是艺术自身合理化的核心要素。因为艺术的合理化,最终是要依据文化合理化的价值理性原则展开的。也正是在这里,韦伯准确地指出:“某种特别‘先进’的技术的运用,对于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没有哪怕一点儿揭示。……新的技术手段的发展首先只是意味着分化的增长,并且仅仅提供了在强化价值意义上增加艺术‘财富’的可能性。”(注:韦伯著,韩水法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进一步说,艺术的技术手段的丰富不过是推动价值领域分化的一个积极因素,体现艺术价值的内在尺度却只能在价值理性那里才能找到。这一尺度在哈贝马斯那里得到了更明确的说明:文化的现代性的特征在于,原先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中所表现的本质理性被分离成三个自主的领域——科学、道德和艺术。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注:Jürgen Habermas,Modernity-An Incomplete Project,In Hal Foster ed.,The Anti-Aesthetic: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Seattle,Washington:Bay Press,1995,pp.8—9.)。在这里,哈贝马斯既说明了文化的分化事实,又揭示出文化的不同领域各自不同的游戏规则。对于艺术而言,它只需要依据审美—表现理性就足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价值世界。这意味着,艺术再也不必依附于宗教而存在。这也正是韦伯所要强调的:艺术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一种世俗的救赎功能,恰恰就在于它已经在生活的理智化和合理化的发展条件下越来越变成一个掌握了独立价值的世界。
所谓审美—表现理性,作为现代艺术的内在法则,也只有放在韦伯关于两种理性的讨论中才能得到更清楚的理解。韦伯将审美纳入到价值理性的框架之中予以说明,实际上暗示了这样一种关于艺术的理念:艺术通过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宗教同样不可证明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在工具理性的视野里,艺术这样一种以感性愉悦表现出来的价值理性存在,必然成为试图颠覆这个世界的力量。艺术在合理化过程中所遵循的审美—表现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文化的其他价值领域的最大区别也就在于:它以一种极其明显的感性愉悦而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颠覆性和反叛性,更有可能将人们从工具理性的规训世界中解救出来。换句话说,当现代艺术借助于对纯粹感性形式的强调开始表达自我时,它也就成为将身处工具理性“铁笼”中的现代人解救出来的出发点。
可以说,韦伯之所以对艺术寄以厚望,一方面在于他通过对价值领域分化事实的揭示,看到了现代艺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域,已经获得了释放其潜能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意识到了艺术的感性形式背后所潜藏的价值理性内涵。
从审美现代性的视野加以考察的话,关于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具有某种审美救赎功能的讨论,既不是从韦伯才刚刚开始的,也不是在他那儿得到最充分表达的。但是,韦伯的美学意义却在于,他第一次清楚地指出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分化事实,并对艺术在现代性进程中的独立地位给予了理论上的确证,从而揭示出了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所具有的自身合法性与现实可能性。韦伯之后,关于审美救赎价值的讨论虽然繁多,但基本上都在这里汲取了有益的理论营养。这其中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代理论家的美学理论中。
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那里,关于审美救赎有着更为系统的阐述。恰如沃林所概括的,比起韦伯来,在阿多诺的美学中,艺术在某种更加强烈的意义上变成了救赎的工具。作为和谐生活的某种预示,它起着强制性的乌托邦作用。对他而言,只有艺术才能够提供把令人苦恼的社会整体重新引导到和谐的道路上去的前景(注:沃林著,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6、115页。)。他抓住工具理性及其同一性表现对现代社会展开了深入批判,进而提出了审美乌托邦的理念,是在更激进的立场上回应了韦伯的文化社会学所暗含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对于马尔库塞而言,问题是相似的。尽管他对韦伯持一种更明显的批评态度,但是在他借助于“新感性”概念反抗物化世界控制的企图中,除了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之外,显然还包含了韦伯关于现代社会“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判断,也包含了艺术获得自主性之后的合法性及其感性形式所具备的救赎功能问题。
韦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特别显著地表现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考察中。他对于韦伯合理化理论的批判继承尤为突出,而他将艺术放在审美—表现理性这一维度加以说明,也正是沿着韦伯的思路,对审美救赎的可能性所作的进一步具体说明。现代艺术凭借这一理性结构获得了足够的自主性的同时,也就有可能获得一种世俗救赎的文化力量。作为建构其交往理性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也在更切实的背景中得到了深入的讨论。
事实上,无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于韦伯持怎样的批评态度,在他们所关注的审美乌托邦问题中,都无法完全摆脱韦伯的理论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韦伯,对现代艺术的审美救赎——再进一步说也是审美现代性——的探讨注定是不完整的。如沃林所言,无论如何,韦伯都将一项专门的救赎功能归之于现代世界中的艺术,对于有文化教养的人们来说,艺术超越宗教而成为生活之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某个独一无二的领域(注:沃林著,张国清译《文化批评的观念》,商务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6、115页。)。正是这个领域,为人们面对现代性的困境获得世俗的“救赎”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韦伯的社会学主题所包含的美学价值,也因为他的这一洞见而显得弥足珍贵,有必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