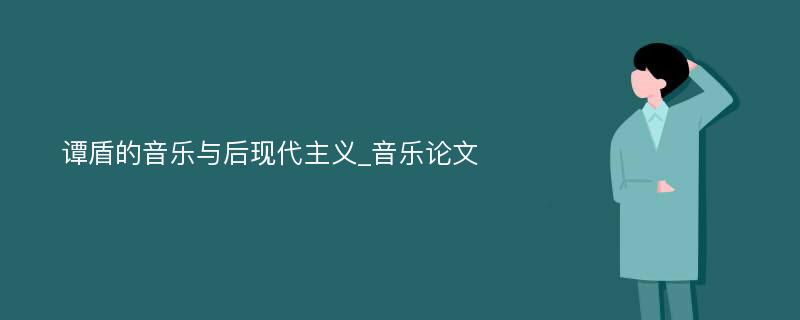
谭盾音乐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追求简单,要感兴趣的观念是构成。不太注重局部的技法,也不注重“东方”或者“西方”或者表面的民族性。我是想从自己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出发,试图在较为综合的文化语言中找到自己。[①]
——谭盾
引言
谭盾,作为一个深受当代世界文化影响的作曲家,他的音乐[②],尤其是其近作,“追求简单”、“构成”,创造出了一种“综合的文化语言”,从而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注脚。
80年代初,谭盾音乐就暴露出后现代端倪。这就是《复、缚、负——室内乐团及人声》、《弦乐队慢板:自画像》(均1982)等作品中“自然之声”的体现。80年代中期,“谭盾民族器乐作品音乐会”(1985)中所渗透的某些观念以及“谭盾交响作品音乐会”(1985)中《道极》(《乐队与三种音色的间奏》)的“反文化”也表明了谭盾音乐向后现代主义的倾斜。1986年,谭盾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音乐艺术博士学位。初到美国的谭盾,为适应其学院派风格,创作了三部涉及序列原则的作品——《第三交响曲》(1987)、《戏韵——小提琴协奏曲》(1987/94)以及《为弦乐四重奏所作的八种颜色》(1986—1988)。1989年,谭盾创作了歌剧《九歌——为四位独唱演员、合唱队、舞蹈而作》。正是从这部作品开始,谭盾不再遵循哥伦比亚那种学院派范式,“宣布十二音音乐已经死了”[③],而最终走向后现代主义。进入90年代,谭盾音乐的后现代主义取向更为显而易见。他的“乐队剧场”系列——《乐队剧场Ⅰ:埙——为十一个埙及乐队而作》(1990)、《乐队剧场Ⅱ:Re——为观众、两个指挥及乐队而作》(1993)、《乐队剧场Ⅲ:红色——为声像装置、摇滚乐队及交响乐队而作》(1995),《交响曲:死与火——与画家保罗·克利的对话》(1992),室内乐《圆——为四个三重奏、指挥、观众而作》(1992),“实验音乐”——陶乐《静土》(1991)、水乐《序、破、急》(1992)、纸乐《金瓶梅》(1992),歌剧《鬼戏——为弦乐四重奏、琵琶及铁、水、纸、石头及演奏员的人声而作》(1994)[④]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他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一般认为,谭盾音乐体现出了两个极端。一方面,谭盾把音乐作为纯粹的“声音”艺术,从而对“声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最终因大量“自然之声”的充斥而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另一方面,谭盾又把音乐视为一种不能脱离其戏剧传统的艺术,故而在舞台上实施了“乐队剧场”等及一系列现代“祭祀”,并在“现场观众”的“参与”的“游戏”中逐渐走向“行动艺术”。这些都隐隐向人们昭示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艺术”。也正是在这种后现代信条的驱使下,谭盾音乐打破了“现存的语言习俗”,进而表现出了面对现代主义的“反文化”——“深度模式的拆除”。由于谭盾音乐在“人”与“自然”之间选择了“自然”,以致丧失音乐的“主体性原则”,表现出了所谓“主体的死亡”。此外,谭盾音乐还通过“二元对立”的设置而造成了文本意义的分解”;通过“引用”、“拼贴”以及“构成”实现了“文化兼容”。不仅如此,谭盾音乐也走出了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塔,而力图“满足社会的需要”、注重“市场性”,从而被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如果这些都是事实,那么谭盾音乐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现代主义。
尽管谭盾曾说:“不能用既有的所有概念来衡量我的作品。”[⑤]但在这里,笔者仍要套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把谭盾音乐视为一种后现代主义。这或许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谭盾本人恐怕也更要表示反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以作曲家为中心的批评模式早已开始松动了,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批评意识及鲜明的理论背景,而任何音乐现象也只不过是理论的注脚。
深度模式的拆除
后现代艺术所体现出来的一切品格,都可以用“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一言蔽之。当然,这里“反文化”已不再是6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场运动,而是广义的“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就是现代主义。“反文化”也就在于拆除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即视艺术为“游戏”,打破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并把一些曾被排除在传统审美规范之外的东西搬进的艺术殿堂。谭盾音乐之所以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就在于它实现了这种意义上“反文化”,并在拆除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过程中展示了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平面感”。
(1)“深度模式的拆除”在于“近距离” 谭盾音乐也具有这种拉近艺术与生活距离的后现代取向。这就在于,谭盾音乐通过凸现那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⑥],强调了生活自身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从而体现出了“近距离”。从“祭祀歌剧”《九歌》到作为“祭祀交响乐”的“乐队剧场”,再到体现“行动艺术”、“多媒体艺术”的《鬼戏》,谭盾所制造的一系列“祭祀仪式”都体现出了这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因而不同程度地观照了楚祭祀仪式的原貌或西南傩戏的原型,即所谓“远古仪式叙事模式或规则程序的复现”[⑦],体现出了“近距离”。此外,谭盾音乐因注重“艺术家与观众的交流”也拉近了艺术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如《乐队剧场Ⅱ》就在“现场观众”的“行动、参与”中,打破了“乐队与听众之间的隔阂”[⑧],填平了艺术与受众之间的鸿沟。这就是造成“近距离”的一种方式。再者,谭盾的“无声”与凯奇的“无声”在性质上并无两样,仿佛都在表明,“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音乐。”[⑨]这无疑也是一种“近距离”。的确,谭盾音乐中的“无声”,也象《4′33″》一样,使人想起凯奇所崇拜的社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大玻璃》(亦称《被单身汉剥光了衣服的新娘》,作于1915—1923)[⑩]。《鬼戏》中“乐器、自然声音的乐器:包括水、石头、铁、还有纸”所设计成的“装置艺术”及《乐队剧场Ⅲ》中的“声象装置”,与和凯奇素有交情的劳生伯格(Rauschenberg)等后现代艺术家的“波普艺术”一样,具有“反文化”的“近距离”取向。总之,谭盾音乐在体现那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的过程中,表达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艺术”的后现代观念,打破了现代主义与生活之间的那种“距离感”。
“近距离”使谭盾音乐表现出与80年代“新潮音乐”的不同。首先,“近距离”使谭盾音乐打破了“新潮音乐”的那种认识论。“新潮音乐”曾在“反传统”和“另起炉灶”中使艺术对象和艺术方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由过去对现实生活进行机械地“反映”转向对人类社会进行深刻的“反思”;由过去对民族民间风情作形象的“描绘”转向对民族民间文化精神作内在的“表现”;由过去对中国近代革命史进行真实的“再现”转向对人类的历史及未来进行哲理性的“思辩”。这种“转向”表明,“新潮”作为一种现代主义,仍具有一种基于认识论的深度。然而,谭盾音乐却打破了被作为哲学基础的认识论,随之也拆除了基于这种认识论的深度。尽管它在艺术对象上仍体现出这种“转向”,但从艺术方法上看,谭盾又似乎在这种“近距离”中重新选择了“反映”、“描绘”和“再现”,并反对艺术及美学对生活的证明与反思。或者说,在谭盾的艺术方法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中心地位已被剥夺,而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本体论哲学取向。其次,“近距离”也使谭盾音乐丧失了“新潮音乐”所捍卫的那种“本体位置”。十年前,我们曾经欣慰地看到,谭盾象众多“新潮”作曲家一样,通过打破“从属论”,使音乐在一种批判意识中取得其“本体位置”,体现出新时期“文的自觉”。但90年代的谭盾,却在“近距离”中频频推出“乐队剧场”、“行动艺术”、“多媒体艺术”等后现代话语以体现其“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从而使他的音乐被“异化”为“综合艺术”,最终脱离其“本体位置”。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超越,即拆除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
(2)“深度模式的拆除”在于“大众化” 后现代艺术力图打通“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隔阂,而具有“大众化”取向。谭盾音乐的这种取向也显而易见,这就是在体现其“先锋性”时追求其“大众化”。在与克诺斯弦乐四重奏团(Kronos Quartet)合作《鬼戏》的过程中,这种取向就显露无遗——既“要广大的听众特别喜欢”,但又要有“挑战性”,要“很现代”[①①]。《鬼戏》正是在这种“现代”的取向中显现出了其“通俗性”,即所谓“大众化”。《乐队剧场Ⅲ》也在“摇滚乐队”和“交响乐队”的结合中使“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归于失效。“大众化”还在于谭盾音乐具有将音乐直接诉诸听众感官的取向,即力图使听众(不仅限于那种具有“音乐的耳朵”的听众)在他的那种音响游戏中直接介入音乐,而不再象现代主义者那样,总寄希望于听众去关注音乐中那种音与音之间的逻辑关系。总之,谭盾音乐所兼顾的“市场性”、“流行性”、“艺术家与观众结合的可行性”,都属于这种“大众化”取向,都是对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拆除。
(3)“深度模式的拆除”在于“反审美” “反审美”即对理性的亵渎。谭盾音乐中那种非理性的“酒神精神”,正是这种“反审美”的前提。谭盾音乐总给人一种狰狞诡趣、光怪陆离的气氛,一种原始的迷狂,一种缺乏理智的宣泄。而“反审美”就在这种迷狂和宣泄中得以实现。如《道极》(中部,b.83—96)那种干涩、粗糙的人声(Voice),在乐队的衬托下,发出力度为三个“f”的叫喊。这种叫喊,如同“巫”(巫师)的“装神弄鬼”及“道”(道士)的“画符打醮”,具有“反审美”品格。在《乐队剧场Ⅱ》中,当“人声”发出“Hong”及“Hongmi la ga yi go”时(b.15—28),其“反审美”也就显露无遗。在《死与火》的“间奏5:土巫”和“间奏6:酒狂”中,那种“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宣泄,也无疑是“反审美”的范例。《鬼戏》中的“反审美”则是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十九种语言Fuck的纪念碑——钢琴、人声、低音提琴三重奏》(Memorial Nineteen Fuck,1993),作为“一部严肃的作品”,把十九个国家或地区类似“操你妈”的这种“脏话”搬上舞台,其对于理性的亵渎,不言而喻。谭盾曾说“Fuck”是他从历史责任感出发所找到的一个点[①②]。这部作品正是用这种充满“摇滚精神”的“Fuck”,表现出了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种种“不满”和“怨恨”[①③]而成为一种“政治波普”。这不仅在于对所谓“高雅艺术”提出挑战,而且也极大消解了现代主义那种对于历史、社会的“深度感”。这种把对于历史及社会的关注,表现为一种充满“反审美”精神的“Fuck”,就使“历史”、“社会”这类具有“深度”的话题立即获得一种“平面感”。这正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那种反普遍性、整体性的内涵,也正体现出后现代主义者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折》中所说的那种“卑琐性”[①④]。纸乐《金瓶梅》中,谭盾把“欲望和爱”作为“人与社会更深层次的平衡点”[①⑤]并以“卑琐”方式予以体现。这种“反审美”色彩,与《金瓶梅》原著中那种以“人欲”反“天理”的挑战性是一致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上述后现代主义“卑琐性”。这种“卑琐性”,也正是后现代主义拆除现代主义“深度模式”的典型行为。
二 主体意识的消失
后现代主义在拆除现代主义“深度模式”时,也消除了那种作为现代主义主旨的“主体意识”。这就在于,后现代主义通过拆除其“表层深度”而拆除了“心理深度”,进而使“主体”从“文本”中退了出去,即所谓“主体死亡”。从 理论上来说,这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首要特征是反主客二分,反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继尼采的‘上帝死亡’的口号之后,提出了‘主体死亡’、‘人已死亡’的口号”,而“人就是‘世界的成分’,人与世界万物融化在一起,彼此不可须臾分离,也可以说人融化在世界万物之中”。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主体死亡”的真实含义。后现代主义这种人与自然的一体观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是“相似或相通的”[①⑥]。谭盾音乐,作为一种“从自己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出发”而创作的音乐,无论是诠释道家文化精神还是表现楚祭祀文化精神,都充分体出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也正是由于这种“天人合一”的存在,谭盾音乐已不再象现代主义音乐那样,以表现“主体意识”为己任,而体现出“主体死亡”,进而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死亡”论紧紧抱为一团。具体地说,谭盾音乐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消失,或曰“主体死亡”,就在于“音乐主体性”的消解。所谓“音乐的主体性”,就在于把音乐表现主体内心世界、感情生活作为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不难发现,谭盾音乐大多都消解了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性”。
(1)谭盾音乐脱离了音乐作为“主情艺术”的本质 谭盾的确不同于那种以“第一人称”说话的现代主义者。在他看来,那种炽烈的“情感化”已不再具有魅力,而“声音”对于生活的直接摹仿或者对于感官的刺激则更有意义。因此,他曾对早期作品中的那种“主观”进行了反省:“《离骚》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主观了。”[①⑦]由此可见,在谭盾那里,追求“客观”比表现内心世界、感情生活更重要。那么,这种“客观”是什么呢?这种“客观”就在于“声音”本身以及受众对于“声音”的反应。所以,谭盾将“声音”对受众感官直观刺激作为音乐的主旨,而不需要受众在音乐的感染下产生一些高深莫测的情感升华,即以对生命快感的追求替代深度的内心体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所谓“主体的零散化”的表现。谭盾音乐正是在这种对于“客观”的追求中,打破了“声音”作为内心情感表达这一传统审美原则,以致使其音乐脱离了音乐作为“主情艺术”的本质。尽管谭盾恪守人文主义传统,表明他与约翰·凯奇的不同,而象萧斯塔科维奇一样,注重“内心灵魂”的表现,但是,他因为他所说的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正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因而在注重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主体死亡”。从这里,我们也已隐隐约约地看到,谭看似乎更接近阿多诺所批评的那个追求“客观”、拒绝“表现”、最终丧失其主体性而与表现主义的“灵魂的呐喊”者勋伯格相对立的斯特拉文斯基[①⑧]。当然,谭盾主要还不是受斯特拉文斯基那种“原始主义”的影响,而主要与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相关。也正是因为这种道家精神的存在,谭盾音乐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那种以“自然的人”否定“社会的人”的趋向,那种把世界盾成“物”与“物”的世界(而不是“人”与“物”的世界)的世界观。尽管他说他的音乐都是写“人”的,但其中的“人”,毕竟大多是“自然的人”,由于被过分强调其“自然”的一面而“异化”为“物”了。总之,在“人”与“自然”之间,谭盾音乐过多强调了“自然”——这不仅在于“自然之声”,而且还包括那种“软弱的人性”——人对生命快感的需求。这些都表明,谭盾把音乐从作为“情感”的艺术转移到了纯粹作为“声音”的艺术,如同众多的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将艺术对于文化、历史及社会的理解和把握寄托于“平面化”的感官刺激之中。这正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后现代主义反“主客二分”、“反主体性”的体现,即所谓“主体死亡”。
(2)谭盾音乐丧失了“主体价值”和“主体地位” 谭盾音乐也正是在追求“天人合一”境界中丧失了音乐的“主体价值”和“主体地位”。“天人合一”的实现首先在于体现“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而要体现这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就必需后现代主义的“行动、参与”。而这种“行动、参与”,正是谭盾音乐丧失了其“主体价值”和“主体地位”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行动、参与”需要表演人员及“现场观众”的“直觉把握”。而正是在这种对他人的“直觉把握”的依赖之中,谭盾音乐中本来就淡化了的“主体意识”进一步消解了。尤其是在那种“多媒体艺术”的实现过程中,那种“直觉把握”所带来的“不定性”就使“文本”与“文本”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更大的“差异”。尽管谭盾音乐中“所有的东西都是被安排的”,也尽管一些段落的记谱就象一个关于表演的说明书,但其中“不定性”的因素处处可见,因而给表演者留下了极大的即兴发挥的余地。因此,这种“差异”也在所难免,而“文本”中那种淡漠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这种“差异”中进一步淡化了。此外,一些“文本”与其结果之间的“差异”也在受制于演出场地的过程中进一步拉大,因而“主体意识”就让位于客观实际了。例如,在北京音乐厅这种“一个十九世纪的构造”里演出《鬼戏》,谭盾也只好屈就了。这种“差异”正是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之所在。从这里就不难发现,谭盾虽早已从意识形态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取得其“主体价值”和“主体地位”,但又在这种后现代主义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所要求的“行动、参与”及“近距离”中,进而丧失作曲家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位置”——“文本”对于音乐的规定性。
总之,在后现代语境中,谭盾音乐,一方面,因为过于强调音乐作为“声音”艺术的“本体性”,偏爱“自然之声”,而忽视了音乐作为“主情艺术”表现内心情感的本质,进而在对“声音”把“把玩”中消解了音乐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谭盾音乐又在极大程度上偏离了音乐的“本体性”,由于体现那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在走向“多媒体艺术”的“异化”中丧失了其“主体意识”。不难发现,这两种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的消失,都与谭盾所“最熟悉的文化背景”有关。这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所带来的“主体”萎缩症,使谭盾音乐在表现人与自然关系时偏向了自然,而忽视了“人”这个“主体”。也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存在,使谭盾音乐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消失与后现代主义那种“反主体性”而导致的“主体死亡”产生了内在的联系。
当然,谭盾音乐中的“主体死亡”与前面所说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认识论而选择本体论也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弗·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的那种“风格”的丧失,也是导致谭盾音乐“主体”消解的原因之一。关于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意识的消失,在此暂置之不论。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所导致的主体意识的消失,它都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主义者那种“寻找自我”的艺术理想,从而使音乐成为一种失去“主体性”灵魂的躯壳。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谭盾音乐已打破了“新潮音乐”那种“注重自己的感受”、“追求自我意识的完美”、“为艺术而艺术”为契机的“主体性”,而陷入后现代主义那种使“主体死亡”的泥沼之中。如果说现代主义使音乐直接诉诸内心情感,将艺术对象从客体转向主体,从外在观察转向内心体验,从情节性表达转向情感性表达,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线,使音乐回到其原始状态而成为一种“近距离”的“摹仿”,弃其“表情性”和“表现性”,进而丧失其“主体意识”。谭盾音乐无疑也将这种“后现代性”暴露无遗。蔡仲德先生曾说,谭盾“虽然否定了机械反映论,却对音乐的主体性原则认识不足,在探索与创新过程中未能牢牢地把握、鲜明地突出人的主体地位”[①⑨]。这是一个恰如其份的评价。
三 文本意义的分解
后现代艺术家往往在“文本”中设置一种“二元对立”,并在陈述过程中,展示“对立”的“二元”之间的“矛盾”,但最终在“二元对立”中不战自溃,从而分解了其“文本意义”。谭盾音乐中也存在着这种“二元对立”,并在容忍“矛盾性”的过程中分解了其“文本意义”。勿庸置疑,谭盾音乐中那种“文化与文化的对位”——“古典与民间”、“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民族”的“并存”,正是这种“二元对立”。就传统意义而言,“古典”与“民间”、“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矛盾”的解决显得尤为重要,以致成为中国大陆作曲家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但是,谭盾并不象这些作曲家那样,致力于解决这种“二元对立”,进而实现“二元”之间的“融合”,而是通过所谓“对位”的方式,展示出一种“多元文化”的并存。所以,谭盾音乐最终既不在于“古典”,又不在于“民间”,既不完全属于“现代”,也不完全属于“传统”,既无所谓“世界”,也无所谓“民族”,其“文本意义”,就在一种“大杂烩”(collage)式的“并置”中分解了。《鬼戏》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巴赫的赋格曲主题、中国民歌《小白菜》、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国和尚的道白,就构成了这种“古典与民间”、“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民族”之间的“二元对立”。由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存在和不予解决,这部作品的“文本意义”,就在“二元”之间那种与生俱来的“矛盾性”中分解了。《死与火》也在多方面与《鬼戏》保持同一流向。这部作品的“文本意义”也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矛盾性”中分解了。如,这部作品的第三部分“死”与“火”,竖琴上奏出了天使般的和声,象是对“死”的超越,其它声部却发出了“死”的哀鸣、展示出了“死”的恐惧和“死”的痛苦。这就使“文本章义”在对“死”的超越和对“死”的恐惧的“二元对立”中分解了。重要的是,“死”与“火”本身就是一种“二元对立”。“死”即“死亡”、“绝望”,而“火”则象征着“生命”、“希望”。面对这种“死”与“生”之间的“二元对立”,谭盾并没有采用传统“文本”中那种“凤凰涅槃”的方式,超越于“生”、“死”,而是将“死”与“生”(“火”)作为一种“对立”,并置之不予解决。最终,《死与火》既不表现出对死亡的超越,也没有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求,其“文本意义”就分解了。正因为如此,整个作品也就成为了一种没有“所指”的“能指”。这种“二元对立”的设置及“文本意义”的分解,正是现代主义所谓“无中心”和“矛盾性”,即所谓“解构”。
四 语言习俗的打破
后现代主义还在于超越一切既有的、“现存的语言习俗”。在总体的后现代语境中,后现代艺术家一方面继续现代主义者的“反传统”和“另起炉灶”,另一方面,他们又重新拾起那些被现代主义者所抛弃的东西,并用新的观念重新进行组合而形成与“现存语言习俗”所不同的语言。谭盾音乐,也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打破“现存的语言习俗”。谭盾曾说:“实际上,欧洲过去三、四百年以来的音乐传统,和本世纪二次大战以前的传统,包括无调性的音乐传统,这个东西造成了一个假象。所谓假象,就是说,现代音乐的形态和语言只能在这个范围里去寻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剧性的事情。”[②⑩]因此,谭盾既打破了近现代的音乐传统,又超时空地把视角指向了更为古老的传统。这包括:
(1)“序列主义”的反动 谭盾音乐不仅摒弃了他曾操作过的“序列主义”,而对现代主义大师们创用的种种“体系化”的音乐语言(如巴托克的“调式半音体系”,兴德米特的“二部写作技法”等)也似乎置若罔闻。总的取向是,谭盾不再注重“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音与音之间的(音高)关系和逻辑,更不再去设计那种结构主义的“乐音体系”,转而关注“声音”的色彩及其变化,进而操作起以“解构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不定性音乐”(Indeterminate Music)——通过“直觉把握”实现音乐的“即兴性”或“偶然性”。《乐队剧场Ⅱ》对于“现场观众”的依赖,就表明这种音乐存在着“直觉音乐”(Intuitive Music),或者干脆称之为“现场演奏音乐”(Live Perfermance Music)的因素。这种“不定性”或者“偶然性”就使得谭盾的一些作品在“文本”与“实际音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一些作品干脆成为一个“事件”、一种“行为”,而不具备其永恒不变的价值。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结构主义逻辑下“文本”对于音乐的规定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打破“语言习俗”的表现,也正是对于“新潮音乐”的反动。
(2)“观众艺术”的端倪 谭盾曾说,“作曲到最后都是比观念”[②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技术的资源终究要被作曲家耗尽,而观念扩充则是无止境的。这正是谭盾音乐中“观念艺术”倾向产生的契机之一。谭盾音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音乐作为的“本体性”,而在音乐的“异化”中表现出了对“多媒体艺术”的兴趣。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中“观念艺术”(Conceptual Art)的取向。谭盾音乐中的那些“行动、参与”,其主旨就在于向人们推广他关于音乐的“观念”,而不在于表达别的什么。此外,从谭盾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谭盾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从“观念”出发的取向也是勿庸置疑的。总而言之,这种“观念艺术”的取向,在极大程度上,超越了音乐的本体意义,无疑也可视为打破现存“语言习俗”的表现之一。如果说“新潮音乐”打破了过去那种“主题先行论”,那么谭盾音乐却又以种种“观念艺术”的倾向,重新回到了与“主题先行论”有相似之处的“从观念出发”,这也是对“新潮”的超越。
(3)“语言环链”的断裂 谭盾在谈及《鬼戏》的时候说,在音与音的关系上,即“单音的构造、音的合作的构造”,其“来源”及“音乐的平衡”都来自他“对自然音响的分析”[②②]。这就表明,这部作品中的和声及织体,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自然音响的把握而无视既有的音乐逻辑。其实,谭盾音乐,尤其是其近作,大多都存在这种“语言环链”的断裂。在和声语言上,谭盾音乐不仅不具备传统的和声逻辑,而且也置现代和声风格于不顾。在曲式结构上,谭盾不少采用以音色为主要结构力因素的“段分曲式”。如《死与火》,尽管作曲家本人说它是“没有乐段与乐段的间接的,是连贯的”,也尽管其中包含一个七音的“主题”[②③],但它仍象是“肖像”、“自画像”及“死与火”以不同“间奏”的“联缀”,或者是不同“作品”[②④]的“联缀”。这正是所谓“文本”的“零散化”。总之,在这部作品中,传统曲式的那种“结构力”已经消解了。谭盾音乐中的调性,也常常是来自他对于“声音”的考虑,也无关乎传统的调性思维。这种“语言环链”的断裂,所给人正是后现代那种历史意识消失后的“断裂感”,一种“非连续性的”的“时间观”,即所谓“符号环链的断裂”——“零散化”、“无中心”的体现。
(4)“感觉方式”的革命 “感觉方式”的革命,作为后现代主义“反文化”的基本取向之一,在谭盾音乐也有其表现。这种“反文化”的“激进主义”就在于向人们那种作为传统音乐审美机能的听觉发起了挑战。如《鬼戏》中的“行为艺术”,使音乐成为一种并非完全依赖于听觉的艺术;其“自然之声”,也使人们在音乐审美过程中,从乐音之间的逻辑关系解放出来,而进入一种以“声音”的品质、模式为视点的“感觉方式”。这种“感觉方式”的革命,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那种与传统哲学的“超越性”相对立的“内在性”的体现。这种“内在性”就是“极力反对超时空的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人只需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即所谓终极真理是虚幻的”[②⑤]。这也是谭盾音乐打破既有、现存的“语言习俗”的一种表现。总之,谭盾音乐打破了“新潮音乐”的技法风格,而向人们推出了一系列后现代主义话语。这表明,谭盾早已脱离了“新潮”作曲家们所热衷的那种现代主义语境。
五 文化兼容的实现
后现代主义一方面从“反文化”出发,对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实现一种所谓“文化兼容”(acculturation)。这种“文化兼容”,在文化取向上,打破文化的“地域性”(即民族文化立场上的“本位主义”,如“欧洲中心论”)或者说“地域”对于文化的制约,从而实现超民族、超时空的多元文化的并存;在风格、语言上的“多元主义”,实现“自由的风格”和“风格的自由”。即后现代主义的“重构”(reconstructive),即“综合”。留学美国后的谭盾,更多地受到了“纽约那多种风格、多种文化,没有形态的熏陶”[②⑥],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这种“综合”症。他所说的这种“多种风格、多种文化”及“没有形态”,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特征,正是谭盾实现“文化兼容”的文化背景。谭盾曾说,他“更感兴趣的观念是构成”,“试图在较为综合的文化语言中找到自己”。这种“构成”的观念,似乎正是哈桑所说的那种“构成主义”[②⑦],而“综合的文化语言”正是美国艺术理论家金·莱文在《告别现代主义》中所说的“风格的自由和自由风格”[②⑧]或哈桑所说“种类混杂”。我们说,谭盾音乐实现了这种“文化兼容”,这主要在于:
(1)“文化与文化的对位” 在文化取向上,谭盾音乐实现了所谓“文化与文化的对位”。谭盾曾说:“未来的音乐,我们现AI写作的音乐,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且音乐的传统一定应该包括全世界各种语言的传统。”[②⑨]这正是他打破“地域性”,“跨越国家文化”的观念之所在。在《死与火》和《鬼戏》中,谭盾正是“从自己最熟悉的文化背景出发”(主要是楚祭祀文化),并在后现代语境中,打破了“地域文化”的局限性,通过“综合的文化语言”,实现了这种“文化与文化的对位”。荷兰学者高文厚在谈到《死与火》时曾说:“这个作品中的马勒、巴托克、萧斯塔科维奇、梅西安和巴赫的音乐片段使一些评论家称这个作品是一个‘文化兼容’的作品。”[③⑩]的确,这部作品,作为“与保罗·克利的对话”,处处都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文化与文化的对位”。其中第二部分“自画像”——以楚文化为背景的文化语言——与作为具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第一部分“肖像”和第三部分“死与火”,就“构成”了“文化与文化的对位”。可见,“对话”即“对位”。在《鬼戏》中,这种“文化与文化的对位”则在巴赫音乐、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国民歌《小白菜》及“和尚的道白”之间得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位”实为一种“并置”,一种所谓“拼盘杂烩”(pastiche)式的组合,而不是那种天衣无缝的“融合”。这种“拼盘杂烩”,正是后现代主义的那种“矛盾性”、“复杂性”、“包容性”所能容忍的。
(2)“向传统回归” 在风格和语言上,谭盾音乐表现出了“向传统回归”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谭盾音乐中的那种原始戏剧意识,作为一种古老的音乐传统就是“向传统回归”的表现之一。《鬼戏》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中国或古希腊那种古老祭祀仪式中的音乐传统、中国西南傩戏音乐传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鬼戏》,谭盾说:“我希望我写作这个东西能够包含欧洲三、四百年以前的东西,我对两千年以前、一千年以前,或者中世纪以前的音乐传统可能会更感兴趣。我觉得,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音乐的传统,我们学得太少。”[③①]这无疑就是后现代主义那种“返回原始和怀旧”的取向。正是科勒所说的“超越现代主义的一系列企图”、“各种被现代主义所‘摒充不顾’的艺术风格的‘再生’”[③②]。
(3)“引用”和“拼贴” 在作曲技法上,谭盾音乐也显示出了后现代主义作曲家所常用的那种“引用”(Quotation)和“拼贴”(Collage)。在《死与火》中,谭盾就运用了这种技法。例如,在“间奏7:巴赫”中,谭盾就“引用”了6首巴赫赋格曲的主题,然后将它们复调式地“拼贴”在一起,形成一种多主题的“对位”。在第二部分“自画像”中,谭盾还较完整地“引用”了他于1982年创作的《弦乐队慢板:自画像》。在《鬼戏》中,这种“拼贴”和“引用”就更为明显。这就在于,这部作品“引用”了巴赫的音乐主题,中国民歌《小白菜》甚至他本人在13岁时所写的《拖拉机进山村》的主题,并把它们“拼贴”在一起。这种“引用”和“拼贴”,作为一种音乐技法,与传统的运用某个主题进行创作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而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普遍存在的那种“喜剧性戏拟”(parody)保持同一流向。总之,关于谭盾音乐中的这种“文化兼容”,我们可用金·莱文所说的那段话作结:“后现代主义不是纯粹的。它引用、纯化、重复过去的东西。它的方法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它是风格的自由和自由风格的。它充满怀疑,但不否定任何东西,它容忍模糊性、矛盾性、复杂性和不连贯性。”[③③]
余言
谭盾音乐具有“后现代性”,并不表明谭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后现代主义作曲家。但对于谭盾来说,这种“后现代性”比他的那种“楚文化”背景显得更为明显。这种“后现代性”,作为谭盾突破“地域文化”的一种结果,正是谭盾音乐得以走向世界乐坛,参与国际交流的一个契机。
从1994年1月9日“谭盾交响作品音乐会”,到1996年3月14日谭盾《鬼戏》在北京的上演,两年多来,谭盾音乐在大陆知识界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对于谭盾音乐,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从这些看法中,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总体的印象,这就是,人们的观念(也包括笔者的观念)尚滞后于谭盾音乐以致造成误读。赞扬者如此,批评者亦如此。基本趋势是,人们似乎没有看到作为“新潮”的谭盾与作为“后新潮”的谭盾究竟有哪些不同。人们在赞扬谭盾的音乐时,似乎仍然把他看作为一个“新潮”作曲家。比如说,在涉及谭盾音乐的“创新”意识时,人们仍然是从“新潮”对于“左”的反叛意义上去肯定谭盾的,而没有看到谭盾音乐中的“创新”,已不再是那种政治批判,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文化批判还包括对于“新潮”的反动。又如,谭盾关于“艺术家与观众结合的可行性”的探索,也被一些人认为是,“新潮”终于开始考虑“听众”了。其实,这只不过是谭盾音乐拆除“深度模式”后的一种必然结果。还如,谭盾音乐中的那种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古典与民间的结合,也被人们理解为我们过去所崇尚的那种水乳交溶的“融合”,说谭盾在“中西文化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结合点”[③④],甚至被看成为了“1+1+1+…+1=1”的“融合”,故而大唱赞歌。实际上,谭盾只不过在实施一种“文化与文化的对位”,那种“容忍模糊性、矛盾性、复杂性和不连贯性”的“并置”(即“1+1+1+…+1”仍等于“1+1+1+…+1”)。再如,人们在赞扬谭盾音乐具有“历史使命感”时,也未能真正发现谭盾关注“历史使命”的方式与“新潮”作曲家有什么不同。在批评者那里,谭盾音乐也同样被误读。如,那种“观念艺术”取向被等同于那种“主题先行”;那种“引用”和“拼贴”,也被等同于我们过去的那种“贴标签”,说这是“简单化、图解化、标签式”的,是“肤浅的”[③⑤]。谭盾对“巫文化”等某些精神现象采取了一种后现代“近距离”的观照,这也引起了人们的“人/鬼”之辩。总之,在人们看来,谭盾仍是一个代表“新潮”的现代主义作曲家。其实,谭盾近来在北京发表的作品,表明谭盾音乐已经走向了后现代主义。因此,评价谭盾音乐,首先必须看清其中的那种“后现代性”。也就是说,与其赞扬或批评谭盾音乐,不如去赞扬或批评这种“主义”。整体而言,谭盾音乐中的那种“后现代性”,在极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审美理想,以致超越了人们可接受的界面。它不仅砸碎了古典的审美理想,而且也打破了人们对于“新潮”表示接受的极限。一些受众曾对“新潮”啧有烦言,今天又对谭盾音乐嗤之以鼻,这表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真正找到它的立足点,而变本加厉的后现代主义也同样没有摆脱受冷落的命运。但本文认为,谭盾音乐所引起的“轰动效应”,表明谭盾音乐在中国大陆已经大获全胜。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全球化”了的文化思潮,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已得到延伸。那么就会有人要反问,中国大陆能够产生后现代主义吗?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作出了答复,他在论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时说:“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今天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即‘前现代’阶段。然而,后工业信息社会的天体力学、量子物理学、电子技术、计算机工艺、外层空间的开发等各种高科技的发展,加之新闻媒介的不断更新,大大缩小了人为的时空界限,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社会也不免带上了一些‘后现代’色彩,或曰‘准后现代’。在这样一种类似西方后现代的氛围下,除去翻译和新闻媒介的直接作用外,人们不难通过各种渠道呼吸到后现代社会的气息,这无疑为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社会,特别是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渗透和传播,造成了某种适度的氛围。”[③⑥]这表明,后现代主义虽然是西方“后工业时代”的产物,但今天它毕竟“全球化”了,以致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成为可能。其实,新时期大陆文艺中每一个领域都打破了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不可能性”[③⑦]。
的确,正是在这位论者所说的前提下,中国大陆滋生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即所谓“后新潮”。早在新时期中国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就伴随着现代主义一同来到了中国大陆,并开始在文学、美术、戏剧、电影等领域中留下了它的足迹。首先,在80年代的小说中,后现代主义就显而易见。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曲》就正是后现代主义那种“不确定性”和“无选择技法”的一种变形;莫言《红高梁》和《红蝗》等小说中的“反文化”特征及“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无疑也具有强烈的“后现代性”。90年代,一大批后随者如余华、苏童、王朔等人的小说,则更是变本加厉,把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企图表现得淋漓尽致[③⑧]。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生代”诗歌也在“打倒北岛”的呼声中染上了后现代色彩[③⑨]。美术界的“后现代”现象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触目惊心。从“86厦门达达”到北京的“观念21艺术展现”,再到1989年春节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劳生伯格式的“反文化”、“波普艺术”或“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艺术”的倾向也显而易见。90年代“新生代”画家的“近距离”[④⑩]也正是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新时期中国大陆音乐中的后现代主义景观也是不可忽视的。谭盾早期作品(如《复·缚·负》,《道极》等)就显露出向后现代主义的靠近。瞿小松的《Mong Dong》(1984)及《文明之忧》(1988)等作品也充分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综合”及其“文化兼容”。赵晓生的“新浪漫主义合力论”(《希望之神》,1986)及根据图谱的“现场演奏音乐”(如1989年的《啸雪》、《生命之力》等)也是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表现。朱践耳的“结合”和“多元化”及一些中老年作曲家在技法风格上的多元化取向,也都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端倪。90年代的谭盾,在“纽约那多种风格、多种文化”及“没有形态”的熏陶下,其后现代指向更是显而易见。1995年10月“北京·上海·香港音乐联展”中的“新生代”作曲家的部分音乐(如崔权的《弦体》及邹航、缪宁博的《人民大众高兴之时》等),也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音乐中的重要表现。总之,中国大陆音乐中既存在着那种以“解构”(Deconstruction)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又存在着那种以“重构”(Reconstrution)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
对于这种登台已久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面对,必须正视。这是因为,对于当下中国音乐文化而言,后现代主义可能比现代主义更具有合理性。如那种“文化兼容”或“多元共生”取向,或许就能克服蕴含在现代主义中的那种“激进主义”,这包括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代表的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更为接近一些。等等。当然,我们更需要的是那种“重构”的后现代主义而不是那种“解构”的后现代主义。
[编辑部收到本文日期:1996年5月10日]
注释:
① 见《世界的回眸——漫谈20世纪音乐的大众欣赏》,载《音乐爱好者》1994年第1期。
② 谭盾是一个多产作曲家。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近年来谭盾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作品。根据谭盾最近提供的《谭盾作品目录、简介》,本文所涉及的作品仅为《目录》中总数的三分之一。笔者所收集到的音响和总谱还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故本文中的“谭盾音乐”,实为“谭盾的部分音乐”,即主要为在大陆传播过的作品。
③ 见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中国大陆新音乐(3):多元主义的时代》(Mainland China's New Music (3):The Age of Pluralism)载《磬》第5期(CHIME NEWSLETTER,NO.5,SPRING,1992),第78—134(荷兰,莱顿大学)。
④ 关于谭盾作品的体裁形式、创作年代、标题文字、标志方法,本文以《谭盾作品目录、简介》为准。如《鬼戏》作为“歌剧”而不作“弦乐四重奏”。
⑤ 据谭盾1995年3月13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学录音。
⑥ 在谭盾看来的,音乐一方面是“声音”的艺术,另一方面,又是不可能脱离其戏剧传统的艺术。这里的“声音”是一种“全声音”意义上的“声音”,其“戏剧传统”就在于原始音乐(“原始生命文化形态”中的音乐)那种“歌、乐、舞”合一的艺术特征。这二者是可以统一的,这就是,“戏剧传统”的体现有赖于“全声音”的实现,或通过实现“全声音”体现其“戏剧传统”。本文把谭盾这种通过“全声音”体现“戏剧传统”的艺术观称为“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或称“音乐的原始戏剧意识”。这种“原始音乐的戏剧意识”就带来了谭盾音乐那种对于生活的摹仿,同时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之间浑然一体的倾向。
⑦ 见韩钟恩《绞断母语环琏之后……能否继续文化颠覆?——“新潮”·“新潮”之后·“后新潮”断想》,载《今日先锋》第2辑(总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北京),第43—61页。
⑧ 见梁茂春《Re的交响——谭盾<乐队剧场Ⅱ:Re>的分析》,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二期。
⑨ 《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Cage”条。
⑩ 参见汪申申《论<4′33″>的价值取向与审美效应》一文,载《黄钟》1989年第2期。
①① 同⑤
①② 根据1996年3月15日“谭盾《鬼戏》座谈会”的原始录音。
①③ 同①②
①④ 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月版,第127页。
①⑤ 见激光唱片《纸乐——选自舞台纸祭<金、瓶、梅>》的封套中谭盾关于这部作品的说明。美国Pamassus唱片公司出版,唱片号为CD81801。
①⑥ 见张世英《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载《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北京大学名教授演讲录》,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8页。
①⑦ 见《现代音乐对话录》,载《人民音乐》1986年第6期。
①⑧ 见于润洋《对一种社会学派音乐哲学的考察(上)——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一书的解读和评论》,载《中国音乐学》1995年第1期。
①⑨ 蔡仲德《音乐创新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从谭盾作品音乐会说起》,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②⑩ 同⑤
②① 根据1994年1月10日“谭盾交响音乐会座谈会”的原始录音。
②② 同⑤
②③ 同②①
②④ 谭盾曾称这个作品中的各个“段落”为“作品”。同②①。
②⑤ 同①⑥,见第63—64页。
②⑥ 见谭盾、严力《对话录》,载《爱乐·音乐与音响》丛刊第二辑。
②⑦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34页。
②⑧ 转引自史建《共生·多元·传统——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思考》,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5期。
②⑨ 同⑤
③⑩ 同③
③① 同⑤
③② 转引自王宁《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载《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③③ 同②⑧
③④ 同②①
③⑤ 根据1996年3月15日“谭盾《鬼戏》座谈会”的原始录音。
③⑥ 见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03页。
③⑦ 佛克马在《后现代主义的诸种不可能性》(Postmodernism Impossibilities)中“不可能性”之一就是后现代主义被中国接受的“不可能性”。参见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第119页。
③⑧ 见王宁《多元共生的时代》第四章“先锋小说:走向后现代主义”。
③⑨ 参见陈晋《当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的有关章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④⑩ 见尹吉男《独自叩门——近观中国当代艺术》之“新生代·近距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