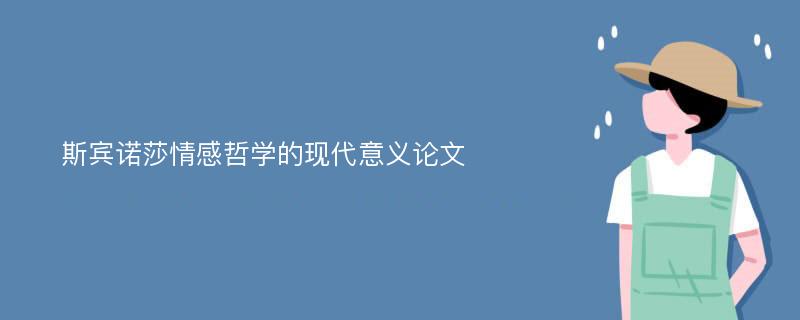
斯宾诺莎情感哲学的现代意义
崔露什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提要: 斯宾诺莎情感哲学是西方现当代情感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其思想启发自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瓜塔里(Felix Guattari)、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 Hardt)等人,引起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情感转向”,西方当代情感哲学研究随之兴起。斯宾诺莎情感哲学现代性启发是提供了“本质主义一元论”的视角,他证明了一个本质上同一的世界,进而更好地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德勒兹将之命名为“强度的世界”,并称其为“伟大的发现”。然而,西方当代情感哲学并未沿着这一维度延伸,只是借用“情状”(affection)、“情动”(affect)、“努力”(conatus)等新概念进行结构上的拆分和细化,将情感研究更多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学科内进行量化分析,忽略对其本体论价值和人文维度的探究。对斯宾诺莎情感哲学本体论的重新解读,能够挖掘这一新视角与现代性理论的关联,以及它对当代情感哲学的价值指向。
关键词: 斯宾诺莎;情感;情状;一元论;“自因说”
以斯宾诺莎情感动力论为基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 )延伸出以“力量—欲望—爱(vis-cupiditas-amor)”为根本的生产矩阵,并应用到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将人类未来的行为、劳动、生产、创造等建立在“本质主义情感动力论”基础上,创造出由情感自发产生的“情感劳动”或“活劳动”(affectivelabor)理论,超越了传统马克思劳动学说。简单来讲,斯宾诺莎情感本体论贯穿其整个哲学体系,要想发掘斯宾诺莎情感理论对现当代情感哲学的启蒙性,必须以理清其本体论基础为前提。斯宾诺莎哲学本体论可概括为“本质主义一元论”,即实体只有一个,且世间万物的本质与实体的本质是相同的,有限事物(即“分殊”affection)是对实体本质力量的表现。其次,斯宾诺莎首创了“自因说”,从理论上彻底打破笛卡儿二元论思想的逻辑基础,将人类“情感”归属于对实体本质力量的表现,其内在原因也来自实体本身。而情感与本体的直接通连性,为现当代情感哲学研究打开了“新视角”,也是最具启发的部分。
一、 本质主义“一元论”与传统“二元论”的对峙
实体概念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基础,他的本体论、认识论、情感论、伦理学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实体概念古已有之,早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有专门的定义,他认为实体是既不能用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1]97。而其他诸如性质、数量、关系等概念,则都属于实体之中,不能独立存在,它们都被称为实体的“偶性”。后来,这一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在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这种表述十分常见,例如乔瑟夫·阿尔波(Josoph Albo)就曾表示:“凡存在的事物首先分为两类,即存在于自身内的事物和存在于他物内的事物。”[2]62近代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沿用这一方法认识事物,他说:“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东西。真正说来,除了上帝没有什么别的能相应于这种作为绝对自我保存的存在物的描述,因为我们察觉到没有其他的被创造的事物能够无须他的能力的保持而存在。”[3]20可见,在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实体是指存在于自身内的事物,一切其他事物都存在于实体内,即存在于他物内。斯宾诺莎对实体概念的界定就基本沿用传统哲学的总体思路,所以他将实体界定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4]1
然而,斯宾诺莎对传统哲学实体观有所超越,一方面,他取消了亚里士多德从现象界的具体事物中抽象出实体概念的做法,而是将实体作为最高的绝对存在。另一方面,斯宾诺莎在肯定笛卡尔将实体与上帝等同,并将实体作为一切事物的制动因的同时,对笛卡儿将“思想”与“广延”看作两个相互独立、互无关系的实体的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就引出斯宾诺莎与笛卡尔之间关于实体一元还是二元的著名争论。斯宾诺莎认为,实体只能有一个,即绝对存在的上帝,也就是自然整体。而思想与广延是实体无限多属性中可以被理智认知的属性,思想与广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关系,只是分别表示实体的两种不同呈现样态,因此,两个属性相互关联且共同出于一个实体之中。斯宾诺莎与笛卡尔在实体一元和二元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情感”概念的界定,以及它的属性和特质。前者在实体一元论基础上,将情感统一于身体与心灵的共同运动之中;后者在实体二元论基础上,却将情感分别与身体和心灵产生关联,从而在心灵对情感的支配能力上,只能依靠一个抽象的“自由意志”,对其存在的证明也较难自圆其说。
具体来看,斯宾诺莎将情感界定为:“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4]97这个定义将情感建立在一种“活动力量”的流变基础上,亦即遵循实体一元论的逻辑。斯宾诺莎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事物属性或表现的样态纷繁复杂,就界定它们从属于不同的实体,因为属性是“由知性看来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4]1。也就是说,由于人类的理智不能直接认识实体事物,只能通过属性来认识。因此,实体、属性、分殊(样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实体通过属性表现其本质的力量[4]9-11;实体内部有无限多属性存在,但是能够被人类认识的只有“思想”和“广延”两种属性,而且二者本质上也与实体是同一的,只不过以两种不同方式表现而已。洪汉鼎先生曾将斯宾诺莎的这一思想比喻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他说斯宾诺莎的心灵和物体,就如同手心和手背同是一只手的两面;这两面虽不能相互作用,但能同时发生变化,它们的秩序和联系是一样的[5]247-248②。这个比喻十分生动,它基本涵盖了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的主要特点。
综上可知,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维度的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聚焦于具体的行业或企业进行分析。由此,本文针对商业银行这一特殊金融服务行业,采用包含时间序列与截面两个维度的面板数据进行建模分析。
斯宾诺莎最后总结道,“纵然两个属性可以设想为确有区分,也就是说,这个属性无须借助那个属性,而我们也不能因此便说它们是两个存在或两个实体”[4]8,这一结论显然是针对笛卡儿的实体二元论思想。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思想,一方面承认属性与属性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例如“身体”的属性与“思想”的属性就不能互为因果[6]43,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因此之故就将二者决然地分割开来,因为如果这样,在谈论人的心灵指导身体行动,以及理性控制情感等问题时,便会产生笛卡儿式的难题和困境,最终陷入对神秘晦涩的事物的讨论。例如,笛卡尔将“身体”与“心灵”两种属性完全分割开来,他在《哲学原理》第一部分命题65说道:“我们如果认为思想的各种情状(如理解、想象、回忆、意欲等)和广袤的各种情状(如形相、各部分的位置及其运动)只是它们所寓属的事物的情状,则我们也会把它们理解得最为清楚。同样,我们如果只存想移动,而不求知道能产生它的那种能量(不过在适当地点,我要解释这一层),则我们也可以了解清楚运动本身。”由此可见,笛卡儿将思想与广延认为是极为不同的两种事物,人的思想要想得到清楚明晰的观念,必须不考虑任何广延上的因素;同样,要想清楚明晰地考察广延上的物质属性,必然不能考虑人类心灵方面的因素。为了证明他的论点的真实可靠性,笛卡儿列举了这样的例子,他说:“我们关于痛苦本身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这种偏见也发生于我们一切别的感觉中,甚至存在于发痒和痛苦的感觉中。因为我们一向虽然不爱相信,在我们身外,有一些和发痒和痛苦相似的物象存在,可是我们也不以为它们只是在心中或我们知觉中存在,而是以为它们是在手、足或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中存在的。”(笛卡尔《哲学原理》第一部分命题67)由此可见,笛卡尔认为我们心灵的感觉对象不是身体或广延中存在的事物,而是某种与发痒或痛苦“相似的物象的存在”,因此人的心灵和身体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相互对应的关系,它们各自在独立的系统中存在和运行,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但是笛卡尔也非常清楚人类身体的行动有时必须在心灵的指导下进行,所以他将这一关系的调和寄托于连接心灵与身体的那个“相似物象”的存在,这就是他所说的心灵与脑髓的某一部分——“松果腺”。关于这一观点笛卡尔在《心灵的情感》一书中进行了讨论,也就是他在命题65中所提到的那个“适当的地方”。然而“松果腺”的出现并没有真正调解身体与心灵的根本分裂,反倒显得是在用神秘的东西解释晦涩的东西,本身是缺乏说服力的。
首先,就相同点来说,斯宾诺莎与笛卡尔都承认实体是区别于一切事物的独立存在,并且属性是由“知性”看来构成实体本质的东西。比如笛卡儿在《哲学原理》中定义道:“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需要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3]20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也表示,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需借助于他物的概念”[4]1,以及“一个实体不能为另一个实体所产生”等[4]4。可见,他们对于实体的绝对存在性、独立性和唯一性是持有相同态度的。此外,他们对于属性是构成实体本质的事物,或属性是知性认识实体的途径这一观点也是基本相同的。笛卡儿认为:“我们原来所以能发现出实体来,却不仅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自存的东西,因为‘存在’自身是不容易被我们所观察到的。不过我们却容易根据实体的任何属性来发现实体,我们的发现就凭借于这样一个公共意念,就是:任何属性或性质,都不能不有一个东西作为依托。因为,我们既看到有一些属性存在,我们就推断说,这些属性所依附的事物或实体也必然存在。”[3]20而斯宾诺莎也认为,只有通过对属性的认识,我们才能够认识和确定实体:“属性,我理解为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4]1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 nSLN转移与阳性SLN数目(Z=-1.991,P=0.047)、原发肿瘤直径(Z=-1.991,P=0.047)以及神经/脉管等淋巴结外浸润(χ2=5.630,P=0.018)情况有关;与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激素受体状态、是否多个病灶、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以及Ki67表达状况无关。见表1。
其次,就实体是“唯一”的存在,还是实体是“多种形式”的存在这一问题,斯宾诺莎与笛卡尔产生了巨大分歧,核心点在于他们如何界定实体的内在本性与特质,而这一问题表现出来的核心逻辑是,实体是否是可以“分割”的,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斯宾诺莎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看出其哲学中系统论的思想倾向。
一方面,在笛卡尔看来,尽管实体是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独立存在,但真正意义上能满足此条件的,只有“上帝”。他说:“何谓实体,这个名词在于用上帝和被造物时,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设想有一个绝对独立的实体,那就是上帝。而且我们知道,一切别的事物所以能存在,只是借助于上帝的加被。实体并不是在同一意义下(借用经院中惯用的术语)应用于上帝和万物的。”[3]20由此可见,笛卡尔的“实体”实际上指两种不同属性和特质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们会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和存在方式。比如在存在的原因方面,二者就有根本区别,“上帝”这一实体是不需要借助其他原因而存在的,但是“被造物”的实体却需要借助上帝的被加,以上帝作为存在的原因。这就造成了“实体”概念在内容上的分裂,以及它的内部原则和逻辑体系不能统一的局面,以至于后来他再想连接两个实体的关系时,难以寻求一个统一的法则或理论,而只能借助另一个神秘的“存在者”将二者弥合,但其效果颇有叠床架屋之嫌。
可以说,斯宾诺莎的整个哲学都体现了世界或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系统性”和“联系性”,即他是站在一个“通体为一”的视角上看待一切变化中的事物,因此尽管现象界有各种不同形态,但其本质并无区别。这也使他的情感理论渗透了这一思想逻辑,即不论人类的情感表现出何种纷繁复杂的样态,其本质都是对自然力量的不同程度的表现。然而,情感作为一种多变的有限样态,如何传递或表现绝对无限的“实体”或“自然”力量呢?也就是“有限”与“无限”之间如何产生逻辑上的“因果性”以及“联动性”呢?这一点在西方学界曾引发广泛而激烈地讨论,其核心点在于论证事物的“因果性”。值得注意的是,斯宾诺莎对因果关系的讨论并非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本质为一”的思想之上,某种意义上与中国道家的“道通为一”有相似性。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传统哲学常将斯宾诺莎思想视为反传统、叛逆、异端的原因,这一反叛极具现代性启发,西方当代情感转向的根本逆转是重新发现和探索这一本质主义的“同一性”和“因果性”,而斯宾诺莎首创的“自因说”是当代情感理论的核心内置逻辑。
另一方面,笛卡儿之所以对实体进行这样的划分,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属性”概念的理解。笛卡儿认为“每一个实体都有一种主要的属性,构成它的本性或本质,而为别的性质所依托。”[3]20这里面“主要的属性”实际上指的是属性呈现出来的某种突出“特质”或“特点”。西方学者米歇尔·德拉·卢卡(Michael Della Rocca)认为,笛卡儿哲学中的实体观念,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实体的性质和它能够拥有的特点”[6]38。的确,笛卡儿自己也为此做出了解释,他说:“我们如不在这个观念中混杂任何虚构的东西,只注意对它的观念中所包括的那些特质,只注意我们明知属于绝对完美的‘造物者’本性的那些特质,那么,我们对于上帝,对于不被创造的、独立的思想实体,也可以得到一个明白清晰的实体。”[3]21由此可见,笛卡儿哲学中的实体,只是在“观念”中捕捉“那些特质”,他所谓不在这个观念中混杂任何“虚构的东西”,实际上是指那些“不主要的属性”或“次级主要的属性”。但如果我们继续深究下去,如何能够区分“主要属性”和“不主要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界限是什么,是否有清楚明细的界限呢?对这一问题,笛卡儿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斯宾诺莎的实体一元论的逻辑合理性。
二、一元论的“内在系统性”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笛卡儿以“主要属性”为区分所形成的实体观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概念性的存在,即它更多地代表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不是现实中实际的存在东西。而斯宾诺莎在这方面却有着突出的进步,他的实体不是一个只在抽象概念中存在的名词,而是一个在现实中存在的真实事物,斯宾诺莎贯之以“自然”(nature)之名,实际上是将实体的本体性地位下降到现实存在的生活世界层面上,而这样的转化赋予了实体更多“现实性”的含义。
为了更好地说明世界本质的内在联系性和系统性,斯宾诺莎在《神、人幸福简论》中列举了一个例子,生动阐释了“实体”(自然)与“有限个体”之间的因果关系。他说,要想让某个房间有光,我需要点燃一支蜡烛,让它照亮房间;或者推开一扇窗,让阳光充满房间。但是,点蜡烛和开窗这两个动作本身并不产生光,而只是为光可以照亮或进入房间打好了基础[7]165。因此,一切有限个体虽然遵循因果联系,但能够让这一切发生的却是将“实体”(自然)的本质转化为有限事物的那个瞬间或条件。下面我以“人类”的存在为例,作为一个有限存在的个人张三,他存在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他父母的生育,但事实上他父母的生育只是让他在现实中“存在”的条件和原因,正如那个“点蜡烛”或“开窗”的动作。因此,父母的生育将张三这个人的本质带出场,张三在某个“个体”的样态中表现“实体”(自然)的属性,而实体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和规律。
苗族人民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可以说是顺其自然。当地婚庆大典时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的家人亲戚均会盛装出席,特别是新娘的服饰更为整齐,由于苗族银饰的整体性特征,新娘一般会同时佩戴银凤冠、银项圈、银披肩、银钻花腰链、银脚环等。举办大型活动时也是如此,居民们也会穿上特色的服装,戴上苗族银饰以示隆重。这些活动也无形中促进了苗族银饰的流传以及其锻造艺术的传承。
实体现实性的第二个方面是对“整体”与“部分”关系问题的解释,它透露出一种整体的系统论思想。首先,斯宾诺莎认为“部分”与“整体”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物,而仅仅是“思想存在物”[7]151-152,即思想的样式。整体与部分只在人的思维之中存在差异,除此以外没有差别。所以,实体与属性并非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将它们彼此分裂开来。其次,斯宾诺莎对这一观点给出了解释,他认为人类之所以倾向于认为事物是可分的,是因为我们对“量”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是将它理解为抽象的或表面的量,这乃是我们想象的产物,例如就水作为水而言,这处也有,那处也有,其部分彼此分离,则我们认为水是可分的。而第二种是作为实体的量,即它仅仅从理智中产生,例如就水作为有形的实体而言,便不能认为它是可分的,因为它既不可分离,又不可分割[4]16。 所以,属性作为一种可以被知性认识和衡量的“量”时是可分的,而作为实体的本质属性则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斯宾诺莎系统论思想的倾向。
鉴于此,斯宾诺莎针对笛卡尔哲学二元论思想展开辩论,他认为笛卡尔将身体与心灵当作两个互无关联的实体,导致后来在他讨论人类“情感统一性”问题时,不能自圆其说。斯宾诺莎批判道,“他(笛卡儿)把心灵与身体看得如此不同,弄到不论对于心身的结合,还是对于心灵自身,都说不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不得不追溯到全宇宙的原因,亦即追溯到上帝”[4]238,而且,虽然笛卡儿最终指出了人心能够获得绝对力量来控制情感的途径,但是“(这)除了表示他的伟大的机智外,并不足以表示别的”[4]96。为理清一元论哲学与二元论哲学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冲突,介绍笛卡儿实体二元论的思想,进而表明一元论思想对于解释和理解情感问题的优越性及其重要作用。
那段时日雨季绵长,我每天都痛苦地活在胡思乱想中。既有不甘心,不甘心就此与叶子错过;也有自卑,面对优秀的叶子和她对另一半的高标准配置望而却步了。时光就这样在神思恍惚中飞逝,再往前走,我便会濒临堕落的边缘。
三、情感表现的“自因性”
斯宾诺莎对“自因”的界定是:“自因(causa sui),我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即包含存在,或者它的本质只能设想为存在着。”[4]1自因性是实体概念的一个重要特性,因为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里,实体只能有一个,一切属性和样态在实体内而没有本质上的区分。换句话说,除这一个实体外,没有另一个实体可以产生它,实体只能自己产生自己,是自己的原因,而一切存在于实体内部的事物都以实体为因。这就将实体以及一切事物都统一在了一个关系体中。斯宾诺莎哲学中讨论的所有概念如“有限样态”“分殊”“观念”“个体”“情感”等都遵循这套关系系统,恩格斯曾经高度赞赏斯宾诺莎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实体是自身的原因,把相互作用明显地表现出来了”[5]250,270。的确,实体的“自因说”使得实体具有了主动性和能动性,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情感本身也作为实体的表现,不再是一个抽象、僵死、孤立的实体概念,而是将实体的力量表现为个体生命力,并且层层外化为情感状态的过程。
从词源上来看,“自因”这个词在他那个时代甚至之前的几个世纪就出现了,最早大概来自于柏拉图的“εαυτòχιουν”[8]144,但当时这个概念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事物无缘无故地被自己产生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斯宾诺莎并未将这个概念用在一般事物中,例如他在解释“欲望”的时候说:“当我们说欲望是自由的,这正如我们说,这个或那个欲望是其自身的原因,这就等于说,在欲望存在之前,它就已经使自己存在了,而这是荒谬的、绝不可能的”,以及他在论及事物的自由时也表示:“没有任何事物当其存在时就会自身具有一个能使自己毁灭的原因,或者当其不存在时就会自身具有一个能使自己产生的原因。”[7]239,265斯宾诺莎只是在解释整个自然的开端时才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只有“实体”(神)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它的本性决定它必然存在。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实体的自因来自它的圆满性和实在性,他说:“实体所具有的圆满性不是靠外因得来的,所以它的存在只是基于它自己的本性;因此实体的存在,无非是它的本质。可见圆满性不但不取消一物的存在,反倒是肯定它的存在。而没有圆满性正足以否定一物的存在;所以我们深信不疑的存在,除了绝对无限、绝对圆满的存在的神之外,没有别的东西了。”[4]11
中职生是一个特殊群体,与其他学生相比,中职生素质稍差,大部分学生理论学习热情不高,缺乏钻研精神,学习动机、目标不明确,学习习惯不佳,效率低下,成绩差,厌学、自卑、叛逆几乎成了中职生的普遍特征。如果不能在课堂上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其极易表现出一系列课堂问题行为。我们针对中职生课堂问题行为进行调查。调查对象是兰州大学护士学校学生,主要采取分层抽样方式抽取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8份,回收率为96%。
“自因说”为斯宾诺莎哲学建立起了一套统一的因果联系,即实体是一切属性和分殊的原因,同时它引起有限样态之间的因果联系。奥利·科伊斯蒂宁(Olli Koistinen)曾对比斯宾诺莎与笛卡尔的哲学,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容易建立起因果联系的序列。因为在笛卡尔哲学中,他不承认不同个体间具有相互连续的因果序列,原因是个体之间不具有共同的属性,因此它们之间不传递任何关系,是孤立的个体。而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由于无限多的属性在无限多的方式下表现一个实体,所以同类属性之间的分殊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它们可以相互影响,产生一系列的关系[8]61-62。的确,在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实体、属性、分殊在定义上虽然各异,但在逻辑上却彼此相联,因为它们同属于共同的实体。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便是:“从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无限多的事物在无限多的方式下都必定推得出来。”[4]17-18这里面“神的本性的必然性”指的是,神的本质必然包含存在这一“自因性”;“无限多的事物”是指具有形态的“样式”和“分殊”,即有限的个体事物;而“无限多的方式”则是指神在表达其本质时的方式,即通过“属性”(思想、广延)及其“分殊”等样态进行表现。由于它们都在一个实体内,所以这些方式便可构建一个完整的内在因果联系链条。
3.1 加强GDM产妇的围产期健康教育 GDM产妇对自身患DM的风险及DM所带来的危害的认知会影响其产后血糖复查行为。GDM产妇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否认或低估自己患DM的危险会阻碍血糖复查,这与Van等[8]研究的系统评价结果一致。产妇知道自己的易感性,由于害怕永久的血糖监测和胰岛素注射会在今后更加注意血糖相关的问题[9]。因此,医护人员在进行围产期健康教育时要评估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帮助GDM孕产妇正确认识GDM与DM的关系,了解产后血糖恢复的过程、发生血糖异常的风险及DM的危害,从而促进其进行产后血糖复查[10]。
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才狼吞虎咽,城市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奇又陌生的,他兴奋地望着那些高楼大厦和电子屏,仿佛看到了新世界。那一次他发挥得很好,得了一等奖后县里还专门派人把奖状和奖品带到学校,其实也不是特别大的奖品,就是一块电子手表,估计也才几十块钱,但他把手表握得紧紧的,仿佛拿到了宝物一样。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实体的“无限性”和“圆满性”如何来影响有限个体的“分殊”或“样态”,实体又是如何传递它的“自因性”呢?斯宾诺莎给出这样的逻辑:“每个个体事物或者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事物,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而且这一个原因也非经另一个有限的且有一定的存在的原因决定它存在和动作,便不能存在,也不能有所动作;如此类推,以至无穷。”[4]25也就是说,有限个体的原因只能是另一个有限个体,而不能是无限的存在等等,而以此类处到最源头的那个有限个体又从哪里获得原因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比较赞同奥利·科伊斯蒂宁的观点,他认为神要想成为有限事物的原因,需要借助于“其他”有限个体作为原因引起这些个体的运动[8]68。换句话说,必须将神(实体)的存在转化为“某种有限个体(即分殊)”,才能将神的原因传递出去。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神(实体)是它的直接产物的绝对的最近因(causa proxima),而不是自类中的最近因[4]27。这里面“由神直接产生的事物”可以理解为普遍的法则或真理,它们实际上不容易被人类获知,而且不论人类是否能够认识它们,它们都作为自然的真理永远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类”属性中的有限事物,必须通过间接的手段才能获得存在的根本原因,否则有限事物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因果联系。斯宾诺莎的“实体”具有更多现代性含义,它实际上指的就是“自然”,而这个自然并非传统古典哲学那样是在神性统照下的自然观,而是将“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相统一的自然观[9],其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更具现代哲学的特质。
斯宾诺莎实体的现实性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主张实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属性不是独立于实体的任何存在,也不是对实体的任何抽象表述,而是属性本身就是实体,只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实体而已。产生这一论调的原因在于,斯宾诺莎将实体看做自然整体,而“自然”与其属性是无法被分裂开的,所以实体与属性也不能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东西。属性唯一的特点在于它是由“知性”看来构成实体本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属性是一种可以被“知性”建构或认识的事物,或者说它是“知性”为了认识上的方便,而将对象进行分割的逻辑方式。所以,就属性是构成实体本质来讲,属性与实体实际上是同一的;而就属性的存在性质来讲,它更容易被知性把握,所以它只是“看起来”构成实体本质,但实际上它“就是”实体的本质。可见他的实体观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存在物,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物”。
因此,通过对实体“自因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的情感也有“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之区分,情感产生的“直接原因”或“物质基础”,来自于实体的“本质力量”,“外在世界”或“外在对象”只是引起情感的“间接原因”或“偶然事件”,是触发或激起本质力量在身体与心灵结构中运动变化的机制。西方当代情感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现了“情感”与“世界本源”的内在联系性,及其蕴含的本质生产力与创造力。
四、“情状”与“主动情感”的研究价值
西方当代情感理论的根本逆转是对“情状”(affectio/affection)概念的发现与讨论,这一概念斯宾诺莎哲学中被多次使用,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与功能。Affectio实际上是指介于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一种中介结构,其关系可简单表述为:主体——情状(身体情状与心灵情状)——外在世界。这一新结构对当代哲学对情感的解读有两点重要启发,一方面,它打破了传统情感哲学将情感视作“主体”与“外在世界”的直接互动产生的旧有观念,即认为导致主体产生或形成情感的对象是一个“外在事物”或“外在对象”,而使主体产生欲望、愉快或痛苦的原因也来自这个外在事物。这种陈旧观点让我们在处理情感的复杂问题时,总是不能自圆其说,引发不必要的争论,例如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为何会产生不同情感,或同一主体对不同对象为何产生相同或相似情感等。新的情感结构让我们认识到,主体与外在对象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结构“情状”,它既具有主体的结构属性,同时又包含外在对象的结构属性,并且不断地将外在世界对主体影响的结构变化纳入到主体自身的结构生成中,因此主体情感的形成及其复杂性与中介结构“情状”的属性及结构有更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这一新结构打破了传统情感哲学“身心二分”的旧有观念,传统情感理论受二元论影响,倾向于将“感性”与“理性”截然对立起来,从而认为情感的控制可以通过“理性”来实现,“理性”如果受到“情感”等感性因素的影响就会失去其力量等。实际上,我们通过经验就可以证实,出于理性的某种观念或意识,很难克制或控制由身体引发的情感状态,同时,情感的体验有时也会增加理性的理解与体悟能力。而新的情感结构告诉我们,身体的情状与心灵的情状本质上是同一的,任何身体的变化都伴随着心灵的变动,而心灵的变动也影响着身体的变化,感性与理性在这一点上是具有统一性的。因此,关于“情感”概念的界定,斯宾诺莎给出的定义极具现代意义,他说:“我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感触的观念同时亦伴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伦理学》第三部分界说三)可以看出“情感”(affectus/affect)概念建立在身体的“情状”基础之上,身体的情状可以引起和促进身体活动力量的增减变化,同时心灵对这些感触的观念也同时发生变化。换句话说,情感就是身体活动力量的表现,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感性(身体)活动,也不是单纯的理性(心灵)活动,而是二者相互协调增减的综合运动。
那么,“主体—情状—情感”这一结构关系包含着怎样的逻辑呢?这就需要我们理清“情状”的本质特点以及“情感”的多种表现类别。就“情状”来看,它是主体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情感形成的动力基础。其拉丁语为affectio,在经院哲学中它表示一种构成“本质”的“属性”,并且是“处于正在变化中的状况”[10]149-150。斯宾诺莎在原有经院哲学赋予它的意义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含义,affectio不仅有形而上的特性,它还是构成人的身体与心灵本质的一种独特属性。一方面,情状是一种“物质存在”或“广延存在”,它是人类的身体对外在世界的“感触”,或者说外在世界对身体影响下产生的“变化状态”。另一方面,情状还是一种“思想存在物”,是人类认识事物所捕捉到的“特点”或“特质”,它把“思维的样式”呈现给心灵,方便心灵形成观念进行思考。最后,身体的情状与心灵的情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从其哲学本体论体系来看,实体只有一个,且身体与心灵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只是对实体本质力量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在此基础上,人类“情感”的诸多表现形式和类别也都随之被给予。首先,情感的最初表现形式是“冲动”“欲望”“快乐”与“痛苦”,它们都以“一定程度”表现人的身体活动力量。不同的是,“冲动”与“欲望”与人的身体活动力量(即生命力)关系最为“直接”和“亲近”,是身体基于本能的活动呈现,且尚未被心灵明确意识到,很难进行言说,因此是一种生物性或本能性的情感,斯宾诺莎将它们界定为“情绪”或“激情”(passio/passion)。“欲望”则是身体的冲动被心灵感知且具有了“意向性”,是一种综合的情绪。而“快乐”与“痛苦”则是具有明确意向性的两种不同维度的情感,即痛苦是身体力量的减弱伴随着观念的负向发展,快乐则是身体力量的增强伴随着观念的正向发展。可见,欲望是冲动在思想意识层面的进步,而快乐与痛苦则是具有方向性的欲望表现。斯宾诺莎将这些基本情绪的关系表述为:“所谓人的本质的情感乃是泛指本质的任何状态而言……所以欲望一字,我认为是指人的一切努力、本能、冲动、意愿等情绪,这些情绪随人的身体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常常是互相反对的,而人却被它们拖拽着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不知道他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前进。”[4]150-151由此可见,人类的自然属性具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随“情状”的力量变化而变化,如果说人类本质是以某种方式表现自然的力量,那么情感本身也就是一种“中性的”或“自然的”存在物,并无好坏善恶之分,在属性上与“理性”并无高低之分。
接下来,最应引起当代情感研究关注的是情感“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它体现了情感作为人的本质属性,先天具有“进化性”“过程性”“生成性”“开放性”等结构特点,这一特点使情感在当代研究中更具人文价值。在斯宾诺莎看来,情感应分为“主动情感”(actio/action)与“被动情感”(或“激情”),因为:“对于情感中的任何一个情状,如果我们能够为它的正确原因,那么我便认为它是一个主动的情感,反之,则是一个被动的情感。”[4]97换句话说,“主动情感”是情感发展的最高阶段,它是理性通过身体的情状进行了体认后得到的情感,是出自理性的情感,引导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而“被动情感”是情感发展的低级阶段,它较少地接受理性对其指导与操控,任由身体的情状随外界事物的变化和影响而变动,受制于此阶段的人常处于矛盾或不幸之中,难以得到身心的平静。所以,斯宾诺莎主张我们应尽可能充分地对“被动情感”认识、理解与反思,在此基础上对它进行修正,从而形成“相对主动”的情感。而这时的主动情感是出于理性并超越理性的情感,因此其本身更具“行动能力”和“驾驭能力”。
这一思想对西方现当代情感哲学以及情感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勒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情动理论”,引领了西方情感哲学的当代转向,20世纪美国学者克拉夫(Patricia T.Clough)在《情感转向:对社会性的理论化》一书中断言,人文学、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了“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情感”作为众多学科和跨学科间的一个话语分析焦点,其重要性已逐渐显现出来了,而这一转向的理论资源则来自斯宾诺莎的情感理论[11]1。当代情感哲学与传统情感哲学相比,其最大特点与新意是对“情状”与“情感”概念进行区分,这一要点最先由德勒兹提出,他在一次关于斯宾诺莎情感哲学的课程中强调,如果我们不区分“情状”与“情感”两个概念,则是“灾难性的”,因为“情状”概念并非仅仅是哲学家发明的一个名词,而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感觉的方式”。而这一新的感觉方式就是主体在感知外在事物时,情感形成于“主体本质力量”(生命力)及其“情状”(对主体力量的表现)的活动结构当中,因此人的“情感”与世界本源之“力量”是相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西方哲学界出现了情感向“本体论”回归的发展趋势。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安东尼奥·奈格里,他在《大同世界》中宣称“爱是一个本体论事件”,“存在(Being)由爱构成”,并且“爱是共同性生产和主体性生产的过程”,由此构建出了“实体力量-爱-生产力”新的劳动创造理论。可以说,现实社会中的工作劳动、思想革命、文艺创作等,都以这一矩阵为根本“生产力”,它将人类的生产从原来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可以说,斯宾诺莎的情感理论为西方现当代情感研究带来了一次“逆转”,他通过在本体论上确立“一元论”和“自因说”的逻辑基础,从而打通实体的本质力量与有形事物的根本相通,这一逻辑上的疏通为人类的“生产力量”增添了一个新范畴,即“情感”或“爱”,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劳动生产和艺术创作,才是真正具有人文主义革命思想的自由产品。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Abraham Wolfson.The Philosophy of Spinoza[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3]笛卡儿.哲学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4]斯宾诺莎.伦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洪汉鼎.斯宾诺莎伦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6]Michael Della Rocca.Spinoza[M].London: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8.
[7]斯宾诺莎.神、人及其幸福简论[M].洪汉鼎,孙祖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Olli Koistinen.Causation in Spinoza.Spinoza’s Metaphysical Themes[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9]曹孟勤,徐磊.论自然的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的辩证统一[J].河北学刊,2018(5).
[10]Wiep van Bunge,Henri Krop.The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pinoza[M].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
[11]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and Jean Halley,The Affective Turn:Theorizing the Social[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
中图分类号: B5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 2019) 03-012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情感哲学的起源、发展与应用研究”(18CZX045);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创新团队成果。
作者简介: 崔露什(1984—),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跃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