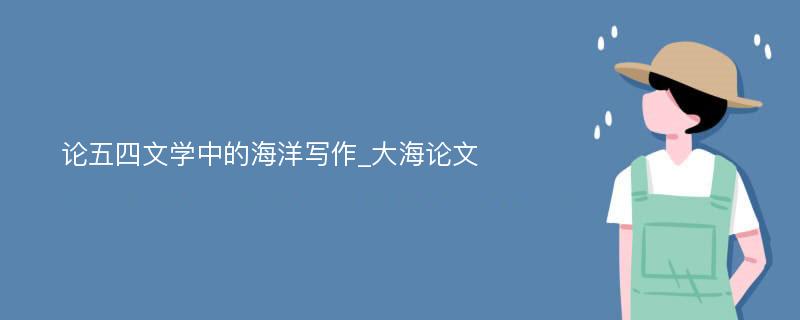
略论“五四”文学中的海洋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洋论文,五四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中国,“海”是环绕中土神州、渺茫难征的边缘“他者”,是覆挂在文明中心四围、浩荡无涯的“无知之幕”,是“蓬莱仙怪”和“镜花奇缘”幻变的想象之域。晚清时期“风从海上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击碎了天朝中心的凝定幻觉,在世界图景的急剧变动之中,开始孕育一种现代性的深刻变革。这时期《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勾勒了新的世界地理版图,“只身东海挟风雷”①的人生志途给了国人真实的海洋经历,并有了“茫茫烟水着浮生”②的新型人生体验。然而,“海洋”作为一个承载着现代意识、世界想象和生命觉悟的特殊意象大量涌入中国文学,深刻变构了现代中国人文化想象和世界感知的深层图景,并且持续生发出一种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则应当始于“五四”。正是在“五四”文学中,这激情一代站在中国和世界交接线上的那种临界感受,那种向着新世界发言的自信而焦虑的冲动,那种情感丰溢到漫出的欣悦而迷乱的状态,使得“大海”脱出了旧的物象之限,成为宏大的时代精神对应和建构的对象,成为某种生命理想投射的焦点和文化精神生发的广域。郭沫若、冰心、庐隐、徐志摩、许地山、郁达夫、杨振声乃至鲁迅等人,这时对于“海洋”形貌各异的书写,在深层意义上共同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一种丰富而多维的“共名”。
可以说,海洋是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契机,是文明转型的方向,是现代意识建构的向度。现代中国人面向海洋构想和形塑了新的自我:一个充满现代感受和世界意识的主体。如果忽略现代中国的海洋精神,忽视现代文学中关于海洋的斑斓言说,就不可能拼合出现代中国完整的精神图景,不能真正释解这一场文明转型的内在密码,而长期以来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的海洋文学缺乏全面关注,或者仅限于对个别作家笔下的海洋意象作些阐释,或者将海洋作为一种边缘的文学景观加以理解,这就需要重新读解现代文学中的海洋书写,并从中探寻其精神生发的内涵和意识变迁的轨迹。
一、新自然:现代理想投射中的“大海”建构
在古代中国,“海”与“河湖江流”同是天地万物之一员,古人在“东临碣石,以观沧海”③或“海上聊一望,船舶天际飞”④之际收览海天,游目骋怀,“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⑤而觉“万物万情”。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⑥,或者“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⑦,在凝神移情之间,体会“万物归怀”、“天地同一”的生命感觉。此刻,“山海自成天理”,天地万物自身具足,观海即泛览万象,即悟理情叹,具足的天地是具足的“人”的外化。这是古典的自然,需剔除过分机心独运的“自我”,而将“自我”融汇于天地之中。面对大海,即使其苍茫无涯偶或带来一瞬间的迷惑和忧思,如“岛间应有国,波外恐无天”⑧,但不足以扰动自然的内在秩序和生命自足的感受。
“五四”正是这种古典自然模式的终结。随着“西风”从海上大规模涌入,古典自然秩序的内在稳定感坍塌了,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地理观念被颠覆了。更为内在的变化是,中国古诗中那种物我浑融的自然裂碎了,代之而起的是“新自然”。“五四”是一个肯定自我、高扬主体价值的时代,在自我发现的热烈情绪中,这一代普遍相信个人应该在历史过程中扮演具有决创力的角色,为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而贡献其力量。正如普实克所说:“在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便是主观成分普遍存在。这似乎与作者人格自传统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并逐渐凸显于作品中有关。”⑨自我的发现从根本上解构了古典自然,在主观价值构造的眼光下呈现出来的是“新自然”,自然万象正是在新的自我意识的烛照下被重新编码、书写,获得新的意义和位置。“海”也正是在这个语境下,获得了发现的意义,它不再是与“江河湖泊”类同的一员,而是在整个“新自然”的构建中获得凸显的位置、时代精神的建构对象、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深处的一个情结。
在这一时期等待进入“新文学”并接受价值重估的众多自然物象中,“海洋”无疑具有某种优先权。这固然因为它似乎标示着现代中国文明的走向,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它所挟带的现代西方文化资源。拜伦、普希金、海涅、雪莱等西方诗魂已在晚清传播了摩罗诗人的伟名,在“五四”一代人心中更是浪漫精神的化身,他们面向着大海的吟咏,塑造了理想的人格姿态。当《恰罗德-哈尔德游记》中的叛逆青年欢叫:“又到了海上!又一次以海为家!我欢迎你,欢迎你,吼叫的波浪”;当海涅在熠熠闪烁的波浪里看到传奇的色彩、童年的梦幻而咏赞:“我向你致意,你这大海,亘古永存”;当雪莱吟唱着“月儿在吻着海波,波浪也相互拥抱”,怀抱“爱的哲学”长眠在海浪中;当汹涌的波涛展现着“自由的元素”,等待着、召唤着普希金那被束缚的灵魂。当这些激情言说涌入“五四”精神世界中,其所挟带的力量展现了一个新的“大海”,也召唤着在新自然面前与之相应的赋形的力量。
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在新的价值重估、文化列序过程中,海洋会占据一个凸显的位置,几乎天然地成为“五四”精神的旨归,成为时代意识的建构对象。在这一时期的海洋书写中,郭沫若显然居于特殊的地位,在他的诗里,迎面而来的是极具冲击力的大海:“我眼前来了滚滚的波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⑩这是充满颠覆力、狂躁的、急切要求涌入诗人内宇宙的大海。这个大海带来了新生的体验,“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太阳礼赞》);(11)带来了无限的感受,“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万籁共鸣的symphony”(《笔立山头展望》);(12)带来了生命的冲动:“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晨安》)(13)在这些诗里,自我与大海之间不是凝神观照式的识见,不是陌然无关的主客邂逅,而是充满生命自主的发现,是一次狂热的命名,是新生的自我欲将热烈的理念赋予对象,并从理想化建构的对象中反过来确验自我。
如果说,在“五四”文学中,郭沫若以他的发现和歌咏建构了一个充满力与美的大海、一个无限生命和自由涌动的大海、一个“惠特曼一样的太平洋”,那么冰心则以充满女性温情的爱与美的诉说,呈现出“大海”另一理想的面相。冰心在《往事二》中记述了寄给父亲的一封信:“我已受了一回风浪的试探。为着要报告父亲,我在海风中,最高层上,坐到中夜。海已证明了我确是父亲的女儿。”(14)对这个在海滨长大的海军世家女孩来说,“寻海”就内蕴着“寻父”的意义,也是追寻那“山巅水涯独来独往”的童年。由此就不难理解冰心“海的女儿”的自我认同,不难体会她在诉说大海时情不自禁喃喃自语的孩气话。冰心赋予大海一种可依恋的品质、一种宽博而永恒的爱,“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春水·一○五》)。(15)在冰心动情诉说海的那些文字里,她往往一往情深地模拟儿童口吻:“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会说。”(《往事一》之十四)这种“五四”式的童心发现,意在创造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创造出适合童心尺度的单纯的自然。于是一个冰心式的“满蕴着母爱的温柔”的大海诞生了,这是大海的另一理想面相,纯净、深美、宽博,是爱的哲学的化身,也是雪莱、泰戈尔以及安徒生那一脉意绪的衍化。
“五四”的两位作家徐志摩和庐隐分别在其作品《海韵》和《海滨故人》里,让主人公(向往自由的女郎)徜徉在海滨,大海的起伏象征了一种自由的远景,海洋带来了新生活的气息。此后新女性和大海的组合在新文学里几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传统,典型的一例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在海边出场的一幕,借助于大海强大的表征功能,这部小说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一次“五四”式的个人浪漫传奇的演绎。另一作家许地山则赋予大海以宗教性的悲悯人生的象征意味,《缀网劳蛛》中的尚洁遭受不公正的污蔑和遗弃之后,感受到“人生就同人海采珠一样,整天冒险入海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没有”。可是人生不息,就如同无涯的波浪不止,一度一度地踊跃掀动。被无尽的波浪磨拭过的尚洁终于悟到“我已找到许多失掉的珠子了!那些灵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探求那么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颗了”(16)。灵海寻珠所象征的人生体悟,此后变幻出没在戴望舒《寻梦者》、卞之琳《白螺壳》等诗中。深邃、神秘、包容的大海构成一种终极性的召唤,召唤怀着理想的人们去探求人生的真谛。
这些海洋书写就建构起了新文学中“大海”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两个自然物象由于寄蕴了现代中国共同的宏大理想和集体想象,而得到突显的“待遇”,这就是“太阳”和“大海”。又唯有“大海”所负载的新生、无限、自由、爱与美等“五四”式自由个体的现代理想基本上未被改换,因而成为知识分子隐秘的文化情结和精神资源。延续至198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17)这种“大写的海”的模式基本上没有遭遇质疑,“大海”成为具有深度内涵和理想意义的符码,成为召唤生命朝向和价值信念的文化秘咒。它启迪了中国人对大海所象征的广阔世界的全新想象,现代中国向外仰视、希冀探寻的深层海洋意识,以及不断突破固有文化框架不息追求的海洋精神,而“五四文学”的话语建构与精神实践正是一个源发。
二、异时空:“世界图景”的崭新体验
杨振声的小说《玉君》讲述的是滨海渔家的生活,其中记述了出洋归来的林一存的一个幻梦,“仿佛是在埃及的东岸,赤圆的落日,如夜火一般,照得沙漠都通红。从天边的椰树间,跑出一群野人来,飞隼一般的快,直扑到我面前来捉我……”(18)在那些细致的写实场景间,这个梦突兀地嵌入一幅“异时空”的图景,从太平洋这壁到埃及东岸,世界仿佛作为一幅可折叠的风景,以逼真的视觉意味而跃现出来……
自近代通海以来,许多国人已表达过海洋带来的新异体验,如黄遵宪《八月十五日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其中既有“一舟而外无寸地,上者青天下黑水”的浑茫景象,又有“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19)的时空错置感。如果说,此时的黄遵宪置身在新的全球性海洋体验中,更多的是“倚栏不寐心憧憧”的困惑感受,那么在“五四”文学中,这种无所置身的感觉逐渐消退,相较之下一种更具发现意识、主体的“看”的自信姿态便渐趋成熟了。
在“五四”文学中,杨振声的滨海渔家小说可谓较早地展现了海边实景,在其最早的小说《渔家》里,海——那个春雨连绵的海——还给人以模糊、虚写的感觉,而在《玉君》中则以加强的写实逼真地展现海的景观。有傍晚的海:“此时宏大的晚日,刚落在绛色的云里,把水面、海岛、船上的白帆、水上的白鸥、人面的颜色都映得鲜红”;有夜的海:“海面起一层银雾,远山近岛,都在迷离隐现中。四维清空,万籁无声,只有荡漾的波纹对月闪烁”;有狂风中的海:“看呀!那墨色的乌云从海上冒出来,遮盖了半天,快起大风啦!”(20)在自觉的写实意识下,对滨海实景所作的逼真描摹,使海的风景作为现实的细节获得呈现,这本身就体现了作者意图驱散笼罩在神秘海上的“无知之幕”的启蒙意识。海作为可视的风景,被纳入作者主观理性的视景之中,这似乎是纯客观的自然摹写,但其实包含着主体努力的意图。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所说:“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很明显是在风景中确立起来的。因为写实主义所描写的虽然是风景以及作为风景的平凡的人,但这样的风景并非伊始就存在于外部的,而须通过发现才得以存在。”(21)
如果说杨振声的海是滨海外望之风景,那么冰心则试图在笔下绘出一幅大海的肖像。“海是蓝色灰色的。蓝色灰色含着庄严淡远的意味”,“海是动的,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着崖石,更欣然的溅跃了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海上的朝霞晚霞,天上水里反映到不止红白紫黄这几个颜色。而海上的沙鸥,白胸翠羽,轻盈的漂浮在浪花之上”。(22)作者发展着透视的能力,摹画出大海多彩的面影,随着这幅面影渐趋丰富,大海也越来越显亲切。在《寄小读者》里冰心记述了自己的海上旅程,由东海滨而扶桑而横跨太平洋至北美的慰冰,沿途海上景观组成一条世界的风景线,通过作者的视景被欣赏、感知。由此,陌生世界的异在感被克服,在亲切的讲述中,作者所要传达给小读者的,显然不仅仅是白话文字之美,也是一种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通过摹画海洋而展开的这一幅世界图景,是“五四”一代眼中的新世界,它具有真实感,可信可感,可理解,也是可进入的。在温和的视景中,原本笼罩在神秘大海之上的未知之幕逐渐被祛除,被陌生大海阻隔的异在世界也逐渐显出崭新的面貌。
海洋对“五四”一代来说是新世界的表征,也是进入世界的通途。而对海洋的凝视,这个“看”的姿态则有着让新世界显形,并在主体意识中凝聚成一种可被认识和把握的图景的意义。这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图像”,即世界作为图像被置于主体面前,“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23)。所以在《玉君》中林一存梦境里浮现的那幅奇异的埃及东岸的幻象,其实正体现了“五四”时期现代新意识的特征,即作为图像的世界不再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在现时空的人凭借想象可以自由跨越到异时空之中。这种现代新意识与海洋体验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在海洋面前,任何障碍都显得局促和暂时,它动荡不息又不断更新,不断触发人们对新异时空的想象。在凝望大海的时刻,处于启蒙状态的主体很容易赋予视觉的新异体验以超越意义。在他们的目光里,内蕴着崭新的精神投力,几乎强迫性地逼使世界呈现新的意义,同时获得自我和世界共同更新的临界状态的兴奋,这在“五四”另一些充满激情的海洋书写中表现得尤为热烈。
在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中,一个载来新世界的大海坦陈在山巅观者的视景中,“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与弯弯的海岸、黑沉沉的海湾、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烟筒盛开的黑牡丹,组成一幅现代文明图景,铺展在观海者的脚下。这个观者将大海裁取为令人震撼的“风景的断片”,这构成了一种发现,即大海雄壮的威力承载着工业巨轮而表征着新世界的到来。面对新时空的畅想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中更显奔放,诗人想象自身摆脱了具体时空的拘囿,自由置身于两大洋相撞的地球极边,“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诗人强烈的主观开启了一片异时空中的风景,这虚构的壮美海景,正如柄谷行人所说是“从前人们没有看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没有勇气去看的风景”(24),此刻却无比雄辩地展现在新生主体的视景中,在怒海狂涛中开启了一个迥异于日常经验的异时空。这是一种典型的“五四”式的精神体验,即面向未来在虚拟的临界点上,感受新世界的激情。郭沫若《太阳礼赞》也传达了这种新生体验,“青沉沉的大海,波涛汹涌着,潮向东方/光芒万丈地,将要出现了哟——新生的太阳”。在这幅壮阔的海上日出图景中,整个未来的世界在产诞的瞬间被目击,光芒万丈的波涛所推起的视觉冲力,热烈涌向那“背立在大海边头紧觑着”的诗人。在那一刻,诗人体验到“时间开始了”的瞬间、拥有崭新意义的世界景观突然爆现的狂喜。
“海上日出”作为“五四”作家所倾心表现的景观,其意义在于展示了世界图景在一刹那间的更新,当恢弘的新异视景在被压缩的瞬间爆现之际,那种世界和自我更新的激越体验宛如一场庄严仪式,而大海内蕴的价值指向和世界意义则使其成为这场仪式最理想的舞台。富有“五四”精神的青年巴金,在归国海轮上描述了印度洋的日出:“太阳慢慢透出重围,出现在天空,把一片片云染成紫色或者红色。这时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这不是伟大的奇观么?”(25)这是新主体对世界的展望。在这幕视景中,海洋及其象征的整个世界在主体的召唤中,以期望的方式出现了。“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这自我与世界一致的体验,彻底驱散了黄遵宪的焦虑。当海洋从混沌未名而变为充满自信的视景时,也就通过视觉的方式实现了一次新世界的命名。徐志摩在《泰山日出》中,也将山巅的云海拟想为大海,“云海也活了;眠熟了的兽形涛澜,又回复了伟大的呼啸,昂头摇尾地向着我们朝露染青的馒形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在……”呼啸、冲洗、震荡,只有想象的大海才具有激浊扬新、内爆出一个崭新时空的伟力。“在霞采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26)在那昂扬的推力下,主体视景中的激情体验被爆炸性地生发为一种世界精神,此刻,世界被洞彻为一种光明的新景观,一切障限、阻隔在主体的灿烂视景中都告消弭,普世融合的欢彻在生命的潮声里澎湃激荡。
这种创世纪式的激情体验,在鲁迅的《补天》中也罕见地以瑰丽奇崛的一幕呈出,“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27)。海幻化成一幅奇艳光明的视景,被目睹为新世界产诞的温床,似乎唯有大海才能确验这种创世纪的想象,才能应和一个时代对新世界的唤起,才能成为异时空进现的恢弘象征。身临其境般地目睹和体验创世纪的爱与美,这本身即是多么奇崛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所开启的“异时空”,需要寻找一个物象的载体,而大海——“五四”的大海正是这崭新精神的凝结物和象征物。
三、“动”的海洋:浪漫“自我”的生命表达
冰心曾这样表白她的海洋体验:“海是动的,山是静的;海是活泼的,山是呆板的。昼长人静的时候,天气又热,凝神望着青山,一片黑郁郁的连绵不动,如同病牛一般。而海呢,你看她没有一刻静止!从天边微波粼粼的直卷到岸边,触到崖石,更欣然的溅跃起来,开了灿然万朵的银花!”(28)“海是动的”,那不确定和未凝固的动态是美的,是自然的呼吸、生命的表征,这表现了“五四”一代直白的向往,也是内在自我的一种生命表达。
“动与静”的对比,以此来分野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文明是“五四”流行的观念,李大钊即言:“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29)“动”是这个时代对外部世界的洞察和理解,既指物理世界所发生的客观运行,更是世界潮流方生未歇的起伏变化,它勾勒出簇新的世界景象,也包含了对于世界本质的把握。在动的永恒节律里,传统的凝神静观的那个世界被打破了,万物贞定、天地纯宁的想象图景被置换了,而“海洋”作为变化的物理世界和起伏的世界潮流的最理想的双关象征,几乎天然地成为“动”的精神的表征。在“五四”文学中,波涛、海浪、潮头这些动感形态,几乎脱出海的本体,获得大力的书写。在郭沫若著名的《凤凰更生歌》中,开场即咏叹“听潮涨了,听潮涨了,死了的光明更生了/春潮涨了,春潮涨了,死了的宇宙更生了”。(30)这是“动”的精神的赞歌,动的宇宙载来了光明和更生,于是世界不复是静观默想中的凝定图景,而是万物在动,在动中相互抵近、接受、更新、拥抱。“汪洋的海水在我脚下舞蹈,高伸出无数的臂膀待把太阳拥抱”(《新阳关三叠》)(31),此刻的海洋充溢着泛神论式的激情,在生命动力中腾跃,伸出新生的触手,把握着宇宙的意志。
“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32)这宣言式的声音表现了郭沫若所理解的“动”的精神,即万物皆动,而自我是动的精神的本源,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在这种泛神论式的世界图式中,自我和自然万汇相融合,自我充溢于万物之中,赋予其行动的冲动。这是“五四”“动”的精神的深层一面。“动”不仅是外在的物质运动,更是内在自我的生命节律,是新生自我的精神萌动和情感扩张,是簇新的生命感受。这种内在自我意识的充溢和外化,表现出这一时期新的世界观:世界不再是由固有秩序所统驭的,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可以扮演一个具决创力的角色,为创造一个整体文化及文明而贡献其力”(33)。这个新的自我是浪漫的,他们相信精神性的因素是世界上扬的原因,内在主体赋予外部世界以动力,自我的生命决创开辟历史的通路,而将自我的内在视野传递给世界正是写作的意义。因而“五四”文学便具备一种自我表达的积极形态,对于大海的动的精神的表现,正是这个浪漫自我高涨的生命意识的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有其公开为时代精神分享的一面,也有更个人性的专属个体情感、梦想与欲念的一面。
在郭沫若的诗里,除了白昼灿烂踊跃的大海,还书写了月光下的海洋。离开太阳的光明普照,他似乎感觉到海的另一番律动,“海已安眠了。/远望去,只看见白茫茫一片幽光。/听不见丝毫的涛声波语”(《夜步十里松原》)。(34)夜的寂寥,触动了诗人内向的敏锐,“我的一枝枝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如果说白昼的海带来的是时代的震惊感受和外向体验,那么夜的海则是属于自我的,充满独一份的自我感受的幽微和隐秘,“海水渊清/沉默着断绝声哗……一种寂寥的幽音/好像要充满那莹洁的寰空/我的身心/好像是——融化着在”(《岸上·其一》)。(35)这是一种隐在的动,自我的感觉几乎不可察觉地扩展到宇宙之中,这泛神论式的生命体验,表现了郭沫若深层的浪漫想象,即自我与自然的合一,而“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36)。如果说这一个自我其情感是内敛的,意识是含蓄的,那么在极端的情绪下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会使得自我表现出更具个体性的精神气质,“我已成疯狂的海洋/你却是冷静的月光!/明明在我的心中,/却又高高挂在天上,/我不息地伸手抓拿,/却只生出悲哀的空响”(《瓶》)。(37)这里令人惊骇的是,自我完全摆脱了理智的常规,与海洋这庞大的存在实现了精神同体,其间已密合到不需要隐喻和象征,不需要一切过渡的说明,自我张扬着强烈的欲求和非理性的冲动,以意念的力量瞬间从这个本体跃为那个本体,化身为海洋——宇宙最恢弘不息的运动。这确是“五四”一代最狂热的海洋书写,这一个海洋已不再是与生命意志无关的静观的古典大海,也不再是外在于自我的物化存在,而是浪漫自我的直接投映,是拆除一切理性藩篱之后的生命意志的奔流,是“动”的精神在宇宙间的激情冲涌。
这一时期对海洋“动”的精神的抒写,生发出一种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弥漫在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时期的海洋书写中。艾青曾这么写道,“你也爱那白浪么——/它会啮啃岩石/更会残忍地折断船橹/撕碎布帆/没有一刻静止”(《浪》);(38)蔡其矫亦写道,“永无止息地运动,/应是大自然有形的呼吸,/一切都因你而生动,/波浪啊!没有你,天空和大海多么单调/……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39)舒婷也这么说,“大海变幻的生活/生活汹涌的海洋”(《致大海》)。(40)从20世纪30年代的艾青到60年代的蔡其矫、80年代的舒婷,从涌动不息的海洋中发现崭新的自然精神,与常变常新的自我想象和激情自由的生命表达相融合,展现了对不受遏制的自我和无限可能的生活的向往。这清晰地表现了现代“动”的精神的生发,一种自由意志、激情自我和世界精神相结合而生的新精神,正汇入现代中国文化气质的深层,构成着生发不息的充满力量的潮流。
[收稿日期]2012-10-03
注释:
①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6页。
②苏曼殊:《七绝: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苏曼殊小说诗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③曹操:《观沧海》,《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页。
④贯休:《南海晚望》,《全唐诗》卷834,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⑤王羲之:《兰亭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
⑥张九龄:《望月怀远》,《全唐诗》卷48。
⑦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全唐诗》卷21。
⑧周繇:《望海》,《全唐诗》卷635。
⑨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⑩郭沫若:《女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11)(12)(13)郭沫若:《女神》,第94、64、60页。
(14)冰心:《冰心全集》第二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70页。
(15)冰心:《冰心全集》第一卷,第46页。
(16)许地山:《缀网劳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17)在1980年代出现了一个书写大海的热潮,如王蒙《海的梦》、舒婷《致大海》、刘再复《读沧海》等,表现了挣脱禁锢奔向新生,重新体认“五四”理想的意义。
(18)(20)杨振声:《玉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39、47页。
(19)黄遵宪:《黄遵宪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8页。
(2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页。
(22)冰心:《冰心全集》第一卷,第98页。
(23)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9页。
(24)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52页。
(25)巴金:《海上的日出》,《中华散文·巴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26)徐志摩:《徐志摩散文集》,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27)鲁迅:《故事新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4页。
(28)冰心:《冰心全集》第三卷,第69页。
(29)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5页。
(30)(31)郭沫若:《女神》,第39、97页。
(32)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上海:《创造周报》2号,1923年5月。
(33)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4)(35)郭沫若:《女神》,第92、140页。
(36)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上海:天下书店,1948年,第3页。
(37)郭沫若:《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6页。
(38)艾青:《艾青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1页。
(39)蔡其矫:《蔡其矫诗歌回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40)舒婷:《舒婷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标签:大海论文; 文学论文; 海洋论文; 艺术论文; 郭沫若论文; 全唐诗论文; 新世界论文; 风景论文; 异时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