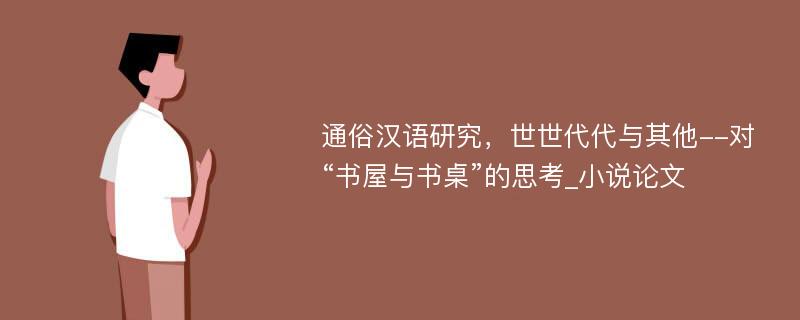
大众国学、世代累作及其他——读《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场论文,案头论文,大众论文,国学论文,世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133-05
关于说唱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古代的杂著中已有零星谈及。像《唐会要》卷四所载韦绶“好谐戏,兼通人间小说”,讲到了一人而兼两者,但这“小说”可能还不是指小说文本。明代以后,如《七修类稿》说“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国初瞿存斋过汴梁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云云,以及陶辅《花影集》卷四《瞿吉翟善歌》说“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稗官小说,演唱古今”,《野获编》说郭勋“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者,……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等等,都讲到了说唱与通俗小说文本之间的关系。不过,诸如此类,只是不自觉地点到而已。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笹川种郎、狩野直喜、盐谷温等撰写中国小说史时,就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了“说话”与小说文本的关系,且专门拈出了一个“诨词小说”的名目,指的是“当时流行的说话底书物”。[1](P406)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改称“诨词小说”为“话本”,认为这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再由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胡士莹等学者多方探讨,说唱与通俗小说的关系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研究实绩。但总体而论,个体的、单向的、表面的撰述居多,尚无一部系统的、双向的、深入的研究专著。有之,则当自纪德君的《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①始。纪德君的这部著作,从唐五代的俗讲、转变讲起,系统地考察了各代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的双向互动关系,力图从中把握它们各自的一些重要艺术特征的生成与演变的规律,材料详赡,新意迭出。毫无疑问,这部著作的出版将推进明清小说和民间说唱的研究,更加完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史与民间说唱文学史的建构,同时,也将引起我们对当代一些文学艺术问题的思考。就我个人而言,拜读之后,有以下三点感触。
第一是关于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问题。这是从小说文本的角度来看的。纪德君的这部著作很容易引发我们对于中国小说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的重视与思考。
中国小说是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这种特点是什么?怎样形成的?对此,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小说的民族特点也应该是由多种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但说话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是举足轻重的。正是在说话等说唱艺术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通俗小说大都有一种“说书体”的味道,塑造的人物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着重通过动作的描写来刻画某种比较单纯而强烈的性格特征;故事情节有模式化、兼容性的倾向,追求传奇性,多采用缀段性和直线化的结构模式;语言明快、刚健,正文中不时用“正是”、“但见”、“怎见得”、“端的是”、“有诗为证”等话头引入诗词韵语来写景绘人,或赞颂打斗等场面;小说的作者犹如说话人那样常常跳出来用“看官听说”等语插入大段议论,爱憎分明,不嫌其烦;再加上分章节、列回目,正文前有“入话”,回前附有诗词,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等程式;诸如此类,自有特色。假如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种特色有粗有精,有劣有优,不可全盘接受,也不可一笔抹杀。比如,就中国小说爱好刻画某种比较单纯而强烈的性格特征来说,人们常常将它视为“类型化”,似乎比突出个性化的性格特征低一等。其实大不然。《三国》、《水浒》中的许多人物被指为“类型化”,但刘备、关羽、赵云、鲁智深、武松等形象“千古若活”,一种单纯、强烈、和谐的美也能震撼人心。近20多年来,小说创作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多变、立体化等等,追求所谓“个性”,可是到现在,恕我孤陋寡闻,不知有几个形象能真正立起来,活在百姓的心中?再从某些形式来看,有的可能比较机械,但有的稍加改造后也有它的妙处,比如分章列回,回目对仗,尽管有的写得很漂亮,但千篇一律,毕竟比较呆板,现在改造后,记得我小时候读的颇有民族风貌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小说中的一些现代的回目,也觉得很精彩,既能点出一回的中心,又有巨大的吸引力吊起你阅读的胃口,何陋之有?
可是这类富有民族风格的表现特点与表现形式,在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被顺畅地继承下来。小说的民族传统的承传第一次遭遇阻扼是来自“五四”前后新文学家们对于“旧形式”的猛烈批判。假如在此之前的晚清的“小说界革命”只是革小说内容的命,在艺术形式上并未认真顾及,甚至还有意维护旧形式的话,那么“五四”前后新文学家们就向旧形式猛烈开火了。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就认为,从晚清“小说界革命”后的《官场现形记》到民初的《广陵潮》、《留东外史》等,都是“旧小说”,因为它们都是用的“旧思想、旧形式”。他特别强调:“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用说书的章回体,对偶的题目,这就是一种极大的束缚。……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2]后来,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将小说分成“新”、“旧”两派时,所指“旧派”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源出于旧章回体小说”,描写方法“完全逃不出《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等几部老小说的范围”。他们都将矛头指向与“说书体”有密切关系的传统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标举的新派的“前进之路”又是什么呢?即是“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2]所以有人说,当时新旧之别,“差不多以中西二字为代名词”,“所谓新的,是指新体或欧化式的小说;一班所谓旧的,是指吾国固有的小说”。[3](P136)他们争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是:继承传统还是首先西化?这场争论的结果是,新派占据了统治地位,中国小说的传统的继承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虽然还不能说导致与传统的“断裂”,但确实使以后小说界的主流话语是“洋”的而不是“中”的了。到4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50-60年代,不断有人一再强调要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但看来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文革”以后,西风烈,不亚于“五四”时期,一些人在全球化潮流中一切向西看;另一些人则反其道而行之,打出了“国学”的旗号。可是在“国学”的旗号下,一些人走的路却越走越窄,“国学”就成了“儒学”,成了“尊孔读经”。很少有人看到存在两种不同的“国学”:一种是官府的、精英的国学,另一种是大众的、通俗的国学。《西厢记》、《琵琶记》为什么不是“经典”?《水浒传》、《红楼梦》为什么不能成为“国学”?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离不开通俗的、民间的文化的。我们不应该一味跟着清末民初打出“国学”旗号的人的屁股后面走,新时代的国学应该既是精英的,也是大众的。国学的大众化不仅是将精英国学通俗化,而更重要的是国学本身要包容与重视大众的国学。假如连讲国学的人都看不到中国古代富有民族风格的小说等也是国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要继承与发扬中国小说的民族精神还能有望吗?轻视中国小说艺术民族的、大众的传统的路已经走得够长了。我们应该相信: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大众的,才是民族的。我们的小说应该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21世纪怎样使中国的小说更有一些中国的特点、民族的风味,看来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办到的事呢。
第二是关于小说创作的“世代累作”问题。这是从创作成书的角度来看的。纪德君的这部著作在谈民间说唱与小说的关系时,自然谈到了一些小说是文人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问题。这就使我想起了他曾经对“世代累积”的说法有过不同的意见,以致引起了一些争论。②
本来,人们对以明代“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长篇小说,一般都看作是“个人创作”。如《忠义水浒传》,在明代或著录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或署名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署了两个人的名字;后来像鲁迅、郑振铎等人也强调了小说的成书深受民间说唱等艺术的影响,胡适甚至说《三国志演义》是“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作品”、《水浒传》是“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但即使到20世纪以后,一般还是将《三国》、《水浒》最后归结为个人创作,更没有“集体创作”的提法。1954年,潘开沛在《光明日报》8月29日的“文学遗产”栏中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了一个“集体创作”说。他认为,这部小说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期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大约从此以后,这个“集体创作”说逐步影响到其他通俗长篇小说的作者与成书问题的看法,像1960年出版的、文革前惟一的一部《中国小说史稿》就很有代表性地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产生过程”“很相象”:“基本故事先在民间长期流传,然后由一个或几个作家在人民集体创作的基础上加以再创造而成书。”但是,这个“集体创作”毕竟是有“在同一时间”与“不同时期”之别,而且在古代小说的实际创作中,“在同一时间”内的“集体创作”恐怕很少,多数是在“不同时期”内的几代人的“集体创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朔方先生于1981年提出了一个“世代累积”说,马上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同。在一段时间内,我也是很赞赏这个“世代累积”说的。可是在前几年,一些学者陆续对“世代累积”说提出了疑问,包括德君也撰写了专文。之后,我又陆续看到与听到了徐先生的一些学生的辨析文章与有关言说。我很钦羡徐先生有这样一些很好的学生。
应该说,对于《三国》、《水浒》一类小说的成书过程的认识,从“个人创作”说到“集体创作”说再到“世代累积”说,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逐步符合实际情况的过程。徐先生敏锐地提出了“世代累积”说,功不可没。但是,平心而论,这个提法还是有改善的余地。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看来不仅仅是双方集中争论的是否轻视或削弱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的问题。徐先生在行文中虽然也顾及到了写定者,但要强调“世代累积”,就难免要偏重于“集体”一方,且假如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提法来看,最后毕竟落脚在“集体创作”上而摒弃了“个人”。除此之外,我觉得“世代累积”中的“累积”两字用得是否妥当,也值得讨论。这两个字,分开来讲,是重叠、聚集的意思;合起来看,就是重复、连续、不断地聚集。但是,如《三国》、《水浒》之类成书前,在说唱及其他形式的同一主干题材的故事演变过程中,决不是某些零星题材的简单相加与机械拼凑,而始终是沿着某一主干题材而既有所累积,也有所删改,是一个能动地艺术加工与不断创造的过程。这正如纪德君在本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国志演义》就将先前《三国志平话》中一眼即可识其荒谬的地方,如司马仲相断案、刘关张太行山落草、刘备从黄鹤楼私遁、刘渊灭晋立汉,以及张飞独破黄巾的故事等等,统统予以删改或剔除,罗贯中是根据他的历史观、道德观与艺术观来重新加以写定的。《三国志演义》是这样,《三国志平话》也是这样。在某个基本故事、主干题材演变过程中,每一次成品都不是简单的累积,而是一种创造。所以整个世代演变的过程,不是累积,而是累作,是累创。“世代累积”说的可贵之处是将原来的“集体创作”说中的笼而统之的“集体”两字变成一个纵向的、历史的、流动的过程,但却丢掉了“集体创作”说中的“创作”的灵魂。当然,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提法,还是将“世代累积”与“集体创作”连在一起的。这样,粗看起来,中间明明还有“创作”两字,似乎并没有无视“创作”之意。但仔细推敲,将“世代累积”与“集体创作”两个矛盾的词组一连起来,实际上就是用简单、机械的“累积”否定了“创作”。因为所谓“累积”型的“创作”,就是这个“创作”只是“累积”罢了,那还谈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提法,在修补潘开沛的“集体创作”说时不慎留下了漏洞。今天,假如将“世代累积”改成“世代累作”,或许更贴切一些,后面也用不着再拖一个“集体创作”的尾巴了。而且,“世代累作”的提法,还可能避免忽略、否定最后写定者功绩的嫌疑,而是肯定了演变过程中每一阶段性的实绩都是一种“创作”,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成果。《三国》、《水浒》就是一种“世代累作”型的作品,它们的最后完成,还当归功于个人。
“世代累积”说还有一个泛化的问题,将作品中容有前代题材、甚至前人思想的,都说成是“世代累积”,那就没有边际了,可以将任何作品都可归入“世代累积”了。因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积淀着祖宗的东西。当然,徐先生还没有这样无限扩大,但已经开启了泛化的口子。这特别表现在他对《金瓶梅》成书过程的看法上。对于《金瓶梅》中引用了许多前人的作品、前后情节有矛盾、显示了民间说唱语言文化特色等等,是否可以说就是“集体创作”、乃至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呢?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谈过,这里不想重复了。在这里,最关键的一个判别的标准即是,有一个基本故事与主干题材而经过世代不断加工的作品,才可以称得上是世代累作或所谓“世代累积”;本无一个基本故事与主干题材在一定时间内流传过的,而是由作者在一时间内根据自己的构思而“镶嵌”了一些前人作品中的故事或人物在内的作品,只能归之于个人的创作。《金瓶梅》就是不同于《三国》、《水浒》,是属于后者,是一时“镶嵌”而不是世代“累积”。它在成书前,没有经过一个重复、不断地积聚与加工的过程。近见有人又将《金瓶梅》的“镶嵌”说成是“隐性”累积,这无非也是玩弄一些名词,为泛化“世代累积”的说法又寻找一个借口而已。
第三是关于小说经典的大众传播问题。这是从成书后传播的角度来看的。纪德君的这部著作是双向的研究,既论述了民间说唱对通俗小说成书的影响,又反过来探讨了小说对民间说唱繁荣与发展的推动,而小说在民间说唱的搬演中,又扩大了影响,深入了人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放手改编文学名著成为大众文化产品,很有启发。
一部文学名著的生命力来自广大读者的认识与欣赏。而读者的欣赏趣味,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变迁,以及文化形式的多样化而不断有所变化的。因此,适时地将文学名著改编为当下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将有助于不断地唤起大众对这部名著的记忆和热情,得到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广大读者的认可、接受和欣赏,使一部作品的生命历久常新。在这里必须杜绝保守的态度,慎谈忠实于原著。实际上,每一次改编都是渗透着当代的精神,不可能复制原本。只要新改编的作品的主要倾向是有助于人类进步、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哪怕是有某种“曲解”、引申,或抓住一点写,或换个角度说的“二度创作”,去诠解当代生活,亲近时人感情,也应当欢迎而不是排斥。
近年来,电影、电视、动漫等一些大众的传媒形式,具有极大的普及性,用它们所改编的小说名著,在传播古代小说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应当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而不是用消极的角度去计较。比如,就小说《西游记》而言,在中国,前几年也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这基本上是根据原作来演绎的。当时也受了大众的普遍欢迎,但这不是说有此一家,就不能再开分店了;别人再搞新的,就指斥为野狐禅了。事实上,人家也不买这个账。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就拍摄了一部《大话西游》,借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唐僧、牛魔王、白骨精等形象,凭空捏合了一些新人,非常搞笑地重编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也使一些年轻人为之倾倒。在日本,对拍摄《西游记》也有很大的热情。在上世纪80年代拍过《西游记》不久,前两年日本富士电视又开始放映的连续剧《西游记》仍然在日本引起轰动。可是这部电视让我们中国人看来,多数会觉得怪怪的,怎的让唐代的人物穿上了现代日本人印象中的中国人该穿的旗袍,让唐僧的师父像日本和尚那样生儿育女,穿着日本的服饰,戴着高高的帽子。特别是,这部《西游记》让唐僧变成了一个穿着洁白的袈裟、带着哀怨的眼神的靓丽女性,且与爱徒孙悟空相爱着……。有的中国的网民就忍不住说,假如原作者吴承恩看了“如此糟蹋他的作品,只怕也会吐血身亡了”。但我觉得,它毕竟面对的是日本的、现代的观众,只要它与原作的精神还有相通之处,其主题又是积极的,研究者就要有一种理解与宽容的态度。据这部电视的“剧情介绍”说:“这是中国明代的小说。孙悟空、沙悟净、猪八戒追随三藏法师为了追寻维护世界和平的经书出发前去天竺。途中,师徒四人击退了袭击他们的妖怪。这个描述作为人最重要的莫过于伙伴的故事,不管在哪个时代都一直让人着迷。”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吗?这里所说的一些基本的人类精神,不也是与原作有相通之处吗?无独有偶,韩国出了一部名为《幻想西游记》的动漫也很红火。在这里,孙悟空是被一个新冒出的乐神杰特弹钢琴弹得头痛,无法还手,被压在五指山下。另一个新造的公主美娜成为本剧的第一号灵魂,变得不听话的悟空就是怕美娜的禁咒之笛。在这里,唐僧尽管成了武艺高强的法师,但也被女性化得分不清是和尚还是尼姑,孙悟空的筋斗变成超级滑板,丢下了金箍棒改用了双截棍,猪八戒戴着墨镜,在石油村外做大王,……一路想颠覆《西游记》的传统,用西洋化、现代化来调适现代青年的口味,但无论如何还是像原《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那样,这部《幻想西游记》的主要人物还是离不开唐僧师徒四人,孙悟空的性格还是与原作相近,猪八戒还是那样好色贪财,……说到底,它还是从《西游记》而来。当人们在兴致勃勃地游玩《幻想西游记》迷宫之时,也就是原本《西游记》再显魅力之日。当然,这些大众文化产品,与正宗的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我们也应该承认它们与原作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们也应该用开放的、现实的、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然,在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大众化的过程中,要防止低俗化,乃至是色情化、暴力化,这往往是在大众传播潮流中会泛起的一些泡沫。
以上是我由纪德君的这部著作所引起的一些感想,也是我心里郁积了很久的话,看来有点借题发挥,其实这些或许正是这部著作的现实价值之所在。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我从来不反对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但我更欣赏能对现实中正在思索的一些问题多少带来一点启示的研究。
注释:
①《在书场与案头之间——民间说唱与古代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纪德君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版。
②参见纪德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周明初《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释疑——与纪德君教授商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纪德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再思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