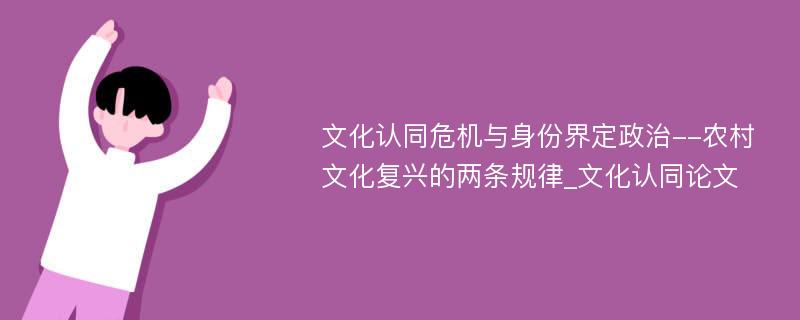
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身份界定的政治学——乡村文化复兴的二律背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政治学论文,乡村论文,危机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1-0054-09
问题的提出:摇摆的极端化
对于近世中国,如果想快速地勾勒出其全貌的话,她似乎是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并在这两极中间不停地摇摆,即在左和右、新和旧、现代和传统、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复辟、城市和乡村、拆除和建设等的对立概念之间摇摆,这个有着长久稳定历史的文明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整体性的文化认同以及厘定对立的边界,并促使其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地造就出与自己差异分殊的对象性存在。余英时先生曾经称此为发生在20世纪的“中国的极端化”(radicalization of China)①,但是在我看来,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摇摆的极端化”。
可以说,这样一种摇摆的极端化构成了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参照体系,所有的新现象以及所有的新主张都不可能脱离开这样的一种极端化,那就是在不断地从一个极端摆动到另外一个极端,并且最终构成了康德哲学中最为核心的二律背反②,也就是文化的改造与保护各自的表述与自圆其说。这一点又特别集中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以及以“复兴”为手段的村民对自己文化的保护上面。
这种摇摆的根源或许不在于传统社会的整体性,而在于引入了现代性观念之后,对与现代性相对立的概念和假设的彻底抛弃。在此意义上,乡村文化最初的界定就是“迷信”与“落后”,它本身是在与城市的“科学”与“先进”这一强烈反差映照下而得到界定,并进而得到区分的。这种区分背后的逻辑发展跟现代性的成长密不可分,特别是由于现代性观念在中国近代的全面引入,原来城市和乡村之间以“文”和“野”来做区分的整体论宇宙观模式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界定乡村社会存在与运转的理念,强调的是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之间的对立,而不是相互的依赖,这样的一种两极化的社会区隔方式还特别在1949年以后的户口制度中得到了制度化的实践。
原来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同样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实际生活的场景,而是被界定为一个地点,尽管在这里蕴涵着丰富的民俗、潜藏着纷繁的文化,但它们却是旧时代的“遗存”,是“活化石”,而依照现代与进步理性,它们又是最需要加以改造的地方。文明城市的保护与乡村陋俗的改造成为两分的而不是整体的宇宙观的表达,这种两分的宇宙观一下子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建筑、庙宇、政治与经济制度、人的观念,当然还有作为整体的文化,并在保护与摧毁之间不断地摇摆,很难静止在一个点上,由此而将这个世界“摇摆的极端化”不断地复制又不断地重演,似乎所有文化认同的危机都从这种摇摆中显露出来。
文化认同:危机的由来
对于个体而言,自我认同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期,并影响到其成长的方向。对于社会而言,文化认同在特定的时期也会出现危机,这种危机隐含着新的社会重组的可能性。个体认同的危机往往是跟随着对于自我概念的界定的变化而出现的,“我是谁”一直是困扰着个体克服这一认同危机的提问方式。但对于一个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的产生是建立在共同意识的营造上面的,这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界定。如果说传统社会里,身份的界定依靠的是神话的逻辑,那么在现代社会中这样的身份界定更多的是仰赖于理性的逻辑,这种理性不单单是在安排差异,同时它还使这差异有了单向度的进化顺序上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差异转化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等级分殊。
在我曾经调查过的河北赵县范庄,原本是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龙牌会,因为其身份的重新界定而成为一种新认同的营造,那就是将龙牌的会头之间的认同不断放大而成为整个民族的认同,依循着这一龙牌认同而建立起来的原本没有名称的各家轮流“侍奉”龙牌的地方性信仰,现在不仅有了“龙祖殿”和“赵县龙文化博物馆”——两个不同但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事物的名字,而且还有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庙宇,并借助各种宣传渠道将其表征为一个民族的发祥地。地方性信仰不断升级,不单单是地方上以及外来知识分子相互“合作”的“功劳”,也有地方社会对于“龙”文化认同的被动接受和主动再造。因为,在我这里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摇摆的极端化”的整体发展脉络中,一方界定身份,一方没有任何选择地接受这种界定,这实际成为了现代文化认同营造的基本逻辑,而能够维持这种认同的合法性基础或者理性基础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进步”与“现代”的观念。但是,依照康德的二律背反原则,文化认同的营造一定伴随着文化危机而出现,二者并行不悖,各自在自己存在的意义上获得了一种合理解释。
实际上,中国在晚清皇权政治解体以后,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认同的危机,随后才有民族认同的危机,以及为应对这种危机而出现的大规模的文化认同的营造,由此中国文化或者说西方人眼中的汉学才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构成要件而得到不断的建构。但是,这样的建构本身却是潜伏着一种认同的危机,因为它本身也在画地为牢地排斥着不是这文化认同框架下的文化认同的意识。曾经有过的“文”和“野”之间宇宙观观念上的区分,被直接转化成为城市与乡村之间文化发展进程上的对立与差异。因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城市就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充斥和弥漫着风俗和习惯之所。这样的区隔也特别为早期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的调查实践所强化。比如,妙峰山进香这样原本具有强烈民间信仰色彩的仪式活动被重新书写而纳入到民俗学家特别的分类、观察和书写的视野之中去。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也成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兴趣点,并将其看成是恒定不变的历史遗存。所有这些都在有意或者无意地帮助现代民族国家去构想自己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以及民族性格的差异。
这明显地体现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分类之中, 比如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差不多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典范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在其调查项目中,能够跟今天我们所说的乡村文化密切联系的大概有三部分内容,那就是第八章“乡村娱乐”、第九章的“乡村的风俗与习惯”以及第十章的“信仰”。对于如何有此三部分的分类,当时的研究者一定有其特别的社会学方法上的考虑,但是至少今天看来,这样的分类有意无意地适应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以及文化与野蛮这样的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对比分类的基本预设。我们也会特别地留意到,原来富含一种乡村文化自我认同的婚礼、丧礼以及认识理性都被重新加以界定,进而转述成为一种不附加任何文化意义的乡村风俗与习惯,并将这些说成是一些客观发生的“事件”和在进步论者眼中的“迷信”。由此“婚礼”变成了“婚事”,“丧礼”变成了“丧事”,同时地方性的自然发生的朴素的认识逻辑被界定为“迷信”,这些转述最后又都成为了现代主义者可以理解的跟现代、城市以及文明相对立的传统、乡村以及野蛮。单就迷信而言,《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有一节提到了“关于农事的迷信”,其中被列为第一条的迷信是这样的:
元旦泡豆 在除夕日农家把秫秸一节,用刀劈开两半,在每半个秫秸里边,隔相当的距离,挖十二个小坑,每个小坑里放一小白豆。作好以后,仍把两半的秫秸合在一起,用绳束好,不要白豆落出。然后就把它投在水缸里,到了元旦的早晨,从水缸取出来看。由秫秸的一头数,第一个小坑里的豆,算是正月。第二个小坑里的豆,算是二月。如此类推,一直到十二月。那个小坑里的豆儿被水泡胀,那个月的雨水就大。那个坑里的豆没被水泡胀,那个月的雨水就小。③
这样一种农事活动,对当地人而言就是他们做出判断和选择的最直接的方法,对这方法的“灵验”,他们并不怀疑,因为这种“泡豆”和天气预测之间的关联和效度才是他们朴素的或者直觉的认知观念,原来曾经为西方的认识论所忽视,今天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④。在进步论者将一切不同于现代科学的东西标定为迷信的地方,他们自己实际也是在对科学投以极大的迷信,因为,对于受过现代教育的精英分子而言,“相信科学”才是他们朴素的认识论。
实际上,针对于当地人的这种“迷信”行为,如果我们借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 (Lucien Lévy-Bruhl)的语汇,这应该是不同于现代人的思考习惯的一种理性,是另类的,但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⑤。这样的一种本来对于当地人而言富含意义的文化认同,却被包括学者在内的现代主义者归类和界定为现代科学的对立面,即迷信,在这里,迈向现代的努力是以彻底地抛弃既有的思考和生活方式为根本目标的。这种彻底的抛弃实际上是在瓦解既存的文化认同,但是又无法根本地让人接受一套新的离当地人的生活极为遥远的现代国家所发明出来的集体认同。而强制推行这样集体认同的结果便只能是使得差异的政治学得到了不断的复制和繁荣。
身份界定:差异的政治学
依据康德的二律背反,我们总是在制造着差异。因为我们在界定事物的时候,这界定本身就是在造就着一种范围,而范围之内与范围之外之间便着实构成了一种差异。当我们界定新的事物时,不属于这新事物的就被分离出去构成这新事物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差异成为今天政治学最为直接的治理对象,可以说构建和固化差异便成为当今社会政治学最肯用力之所在。
单就乡村社会而言,这种差异界定的政治学直接地体现在对于“农民”身份的界定上。这方面当以孔麦隆(Myron L.Cohen)对于农民身份认同的转变的文献研究最为经典。在孔麦隆看来,近代中国对于“农民”的界定是建立在整体的文化与政治发明的基础之上,这种文化和政治发明不是融合的而是区分的,也就是帝国体系崩溃以后所涌现出来的文化认同上的危机,进而转变成为了一种没有文化认同感的文化差异,这差异体现在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知识分子与公共性以及知识分子整体与国家之间的差异上面。此时原来中性的“农产”(farmers)概念就自然地转变成为含有道德意义的“农民”(peasants)概念。与此同时,不断生发出来的概念上的转变还有从“传统”转变成为“封建”,或者借用从日本传入的“迷信”这一翻译,并且,使用这些词汇在当时几乎是成为了一种时髦,并且也是能够成为一个“现代人”的标志性语汇,而这些语汇首先就是从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中间首先获得传播的⑥。
近代中国许多两极化的想象都跟知识分子的参与密不可分。作为过去的传统以及作为现在的现代成为构建此类想像的基本范式,并通过各种社会传播途径而对乡村社会的整体意识造成极大的影响。在范庄,造就出龙牌跟龙文化以及跟中华民族的联系的显然不是信仰龙牌的村民自己,而是能够联系内外、沟通上下的地方知识分子。在此种勾连的文化实践中,一种强迫的认同得到了实质性的灌输,个体认同的龙牌的灵验由此也就转变成为了“这是龙文化的故乡”的意识再造。因为作为当地人,他们可能并没有可以用来辩驳的根据来抗拒这种多少带有强迫性的认同,因为这种认同本身有其理性上的依据,那就是历史谱系的建构,而对此应该是无法证实,也无法推翻的。但是在这种建构中,乡村成为了知识分子想像现代都市生活反面情形的最理想的参照系。
两极化的想象也是使社会实践得以实施的基本推动力。作为我们的“这里”,是被塑造成为代表着“富裕”、“城市”以及“文明”地方:而“那里”则是“贫穷”、“农村”以及“野蛮”的同义词⑦。这种极端化的想像进一步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差异,并且赋予了这种差异以道德的意涵。比如“这里”都是高等的,是文化的中心;而“那里”都是低等的,是文化的沙漠。而全部乡村文化的改造的合法性基础也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差不多凝固化了的对于这种人造的差异的想像之上。如果说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城市生活的影响是一种外部的殖民的话,这个过程清楚地在杨念群对于民国时期北京市传统的出生与死亡的仪式如何受到美国社区卫生改良观念的影响而发生转变的研究之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⑧,那么,中国城市文明观念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则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内部殖民。一次次地把“文明”观念带入乡村,如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1949年以后一系列的对于乡村社会的改造,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种内部殖民的心态上面,试图以城市文化、精英文化、士大夫的价值观、经济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来改变乡村的面貌⑨。比如,在河北乡村,许多家产的大门上都曾经钉有“十星级文明户”的标牌⑩,这“十星”隐含着的城市文明的强制性是极为明显的。当一块“十星级文明户”的牌子由村委会的干部钉到农民的家产大门上的时候,权力支配的政治学便已经在悄然地发生了。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身份界定,是由国家所给出的对于“穷乡僻壤”的居民生活状况以及未来转化目标的界定,当然根本还是一种对于差异的界定,问题是这样的改造和界定永远不可能得到终结,因为这种界定的初衷恰是要营造出差异,尽管表面上体现出来的是未来的城市与乡村文明的融合。在这个意义上,差异与融合再一次构成了康德意义上的二律背反。
在近代中国,对于乡村的界定以及随之而起的无数次的改造中,发生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由蒋介石和宋美龄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历史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特别是这一运动本身对于乡村文化的改造的后效更没有什么严肃的评价。当然,关于这一问题并不是本文主要的关注点,但值得提醒的一点是,这样的由上而下的改造中国人整体性格的运动,其起因以及实际运作的模式都跟后来的乡村改造运动,甚至是1980年代的农村小康建设的运动极为相似,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十星级文明户”的标牌,在那个时代里则是开展“挨户评定等级”,然后是“贴签门首”。在一份对那个时代福建的“新生活运动”的口述史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意志如何对于基层社会发生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长久效果。在这份《福建的“新生活运动”》的回忆文章中,一位实际参加者回顾了他在前后10年的“新生活运动”中所亲历的作为基层社会文化与风俗的蜕变过程(11)。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属于城乡基层生活方式的风俗习惯被这一运动重新界定为“社会不良风气”而加以改良,并通过一系列的“禁止”和“提倡”而加以实施。在下页的表1中,我们看到了对婚礼和丧礼,洗浴习俗、服饰、民间信仰活动、饮食卫生以及时间观念的改造,这些几乎涉及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在这一系列的禁止与提倡的活动中,国家的意志以及社会精英的意识形态下达到基层社会,从城市“陋俗”的改良为始,而以乡村社会风俗的改造为终。这一过程一方面体现了现代国家有意推行的国民一体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一体化背后的城乡差异,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是精英文化与庶民文化之间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经过现代话语的反复诉说而产生并予以了实质化。
乡村文化复兴:回到问题的原点
似乎只有明白了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才能够使我们清楚地理解今天可能的乡村文化复兴的根本意义是在哪里。而且,也许最为根本的问题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问题,而是谁在使乡村文化成为了一个讨论的话题,成为一个相对于“旧”而言的“新”事物。
如果我们单单听到“复兴”的话语而无法听到本来就没有什么声音的生活原本,那么这种“复兴”充其量也只能够是一种当下的展现,新的复兴可能会随之即来。这是文化传递中出现的问题,上一代的文化经由怎样的途径传递下去,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型。并且复兴的基础是文化表征的再创造,乡村文化复兴的认识论基础是新的表征的涌现和传递以及一些人的大脑认知受到了这些新的表征的“传染”(12)。因此,从外来者看来的乡村文化的复兴,就其核心机制而言,根本是文化表征的创造与传递的过程。也就是依循着从个体表征到集体表征再到个体表征的文化传递的链条。这样的文化解释的模式可以让我们摆脱既有的文化解释理论的空泛的解释,而回到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使解释落实在个体认知的根基上面。
表1 福建“新生活运动”10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事件摘要
年份月份 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事件
1934 4 举行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8 禁止台籍浪民开赌花会,并革除婚丧寿宴浪费
9 开始取缔奇装异服
10 调查福建停柩,并实行分期清葬,禁止男女浴堂同座
1 禁止麻疯患者在外行乞
12 禁止中小学生蓄发
1935 1 厉行集会守时运动
2 焚禁春宫及裸体照片
4 举办省会规矩运动;规定妓女佩戴桃花章;禁止妇女烫发
5 严禁本市迎神赛会
1936 6 禁止学生乘车上学以纠惰风。禁止男女评话员对口说书
7 纠正妇女烫发及裸腿
……
9 取缔额外小帐,禁止浴堂假借餐间名义实行男女同座
1937 6 发动全省大学生暑期到农村服务
9 组织乡村宣传队深入乡村宣传
……
1938 4 举行短装运动示范游行
8 劝导永安居民人畜隔离
9 发动年历换算运动
1939 4 禁止内地民间停尸陋俗
5 公布禁止抽烟范围,包括汽车、戏院、会场、行路、山林等五项
……
1940 6 宣传禁烟禁毒
12 发动各级分、支会提取普度迷信费以救济出征军人家属,慰劳伤兵
1941 3 推广各业使用消毒锅
1942 6 禁止裸体水浴
1943 4 发动守时运动,整饬社会风气(禁止男女浴堂同座、麻疯患者行乞、迷
信迎丧)
5 厉行卫生宣传。举行游泳、龙舟比赛
资料来源:参见王宜祜、萨福简《福建的“新生活运动”》,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1986年版(第十二辑),第177-186页。
能够代表乡村文化复兴的乡村庙会的繁盛跟诸多因素都有关联,但是最核心的是新的表征可以得到创造,这表征可能是观念、故事或者是符号。拿我调查过的河北李村的张爷庙复兴过程为例,其所依靠的就是张爷托梦给一位村民,或者神附体到这位村民身上,最后这位村民再把这样的观念表征“传染”给了村里其他的人,由此村庙以及后来的庙会才得以复兴起来。在李村西北的常信村,其庙宇的恢复依旧是靠水祠娘娘的托梦,不是托梦给本村的村民,而是托梦给了邻近范庄村的一位村民,这位村民又从自己家藏的《后汉书》中找到了一段有关“王莽赶刘秀”的历史记载,并将其中的一个故事跟常信村里人信奉的水祠娘娘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范庄龙牌会的发展历程也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从私下里的一家一户的供奉,到后来有外来的地方和国家学者的参与,并将新发明出来的意义或者文化表征,也就是让龙牌跟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龙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跟上古史传说中的“勾龙”的神话谱系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保护,同时也是正面的获得国家认可的便利途径,因而村民受到此种表征的“传染”程度也就最为剧烈(13)。
不过,在这些村落中,最为广泛地受到传染的表征应该是村民对于毛泽东画像的位置安排上。就我多年调查记录来看,毛泽东画像被悬挂在庙会过会的醮棚里最早应该是范庄龙牌庙会。先是把毛泽东画像悬挂在看护醮棚的侧殿里供奉,后来又被安排到后殿里,现在则是摆在龙祖殿右手的窗户上。常信村的情况似乎更为有意思,2002年的庙会上,毛泽东画像被悬挂在最前面的殿中,而他们供奉的正神娘娘却位居其后。而在李村,这种表达更具有工具性,因为有一年地方政府强行拆庙的原因是庙会上毛泽东的画像被压在了写着“张爷庙”三个字的牌匾下。而在同一个村的冯家老母庙,2005年过会时,毛泽东画像是和老母画像并排放在一起的,而2006年刚刚过去的庙会上,老母会的毛泽东画像是被摆放在了一进院落门口的土地神的位置上。而在我2005年春天访问过的李村东南二十余里的大夫庄高峰大队的“观音堂”庙会上,毛泽东画像是被放置在了负责庙会组织的会头所在的房间里。
这里我想强调,对毛泽东画像的摆放形式,特别将其摆放在庙宇中加以供奉,显然是一个全新的文化表征的发明,并且,相比其他的发明而言,其更为具有表征的传染性,差不多是在10年不到的光景里,这个区域的乡村已经是逢庙必有毛泽东画像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画像作为合法性象征所具有的两种意义,其一是作为保护,因为在村民的眼中他是以“大神”的身份而受到敬拜的;其二是作为竞争,毛泽东画像本身可以构成对其他文化表征的掩盖和遮蔽,在常信村、李村和范庄,这一点都表现得极为明显。在这一点上,文化终究是一种竞赛,竞赛的基础就是文化表征的传染能力。在范庄由地方和国家学者共同营造出来的勾龙的传说使龙牌信仰者自己的声音受到了实质性的遮蔽,但是信仰者本身似乎并不甘心于此种“缺席”的境遇,而是很快地将毛泽东画像放在殿中,将其当作他们所信奉的神谱中的一员来加以膜拜。
但是,在此种文化表征的创造过程中,根本体现出来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显然跟国家作为外来力量对于地方性文化活动的直接干预密不可分。这种干预实际上是借助地方的和国家的学者,地方精英以及负责地方文化事业的各级干部而共同营造的。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对乡村文化的改造,这种改造是在适应现代国家的文明与进步的主旨,这种主旨所隐含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极端化地抛弃地方村民长久以来保留下来的地方性的文化和娱乐形式,并将其平和地转变成为国家认同所许可的文化表达形式。比如,范庄新建立起来的“龙祖殿”,它实际上是发明的产物,是从原来的由二十几家会头之间年度性地轮流实施供奉责任的龙牌会,转变成为了由上述外来力量加以干预而新发明出来的“龙文化博物馆”。
与此同时,国家则是通过给庙上“户口”的办法在给予村庙一种界定,由这种界定,国家视角的合法与非法得到了区分。“户口”实际上就是“经营许可证”,并由县里的民政局颁发。凡是有了“户口”的村庙,据说就可以大张旗鼓地开展各类的庙会庆典活动,而且可以从村里批拨土地搭建庙宇,而没有“户口”的村庙则只能时时担心会有上面的人来强行拆庙,而要再从村里划拨土地翻盖新庙那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但是,申请庙宇的户口实际上是非常烦琐甚至是不大可能的过程。比如常信村在为自己村里的水祠娘娘庙申请正式的户口时,几乎动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源,有前面提到的传统的神附体,也有现代的关系运作,比如邀请县文化馆的干部为他们的村庙撰写《赵县常信水祠娘娘庙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文本(14),还学着范庄的样子将中央、省以及县里的知识分子邀请到村里参加他们一年一度在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举办的庙会庆典,去附近的各大庙会上散发娘娘庙庙会活动的传单,并且在没有得到户口之前,村里已经答应批拨一亩半的土地给娘娘庙盖房子,即便是这样,到今天户口也没有申办下来。
但是,国家所要求的村庙活动的户口制确实为有能力沟通村内和村外的地方精英施展他们的活动能力搭建了一个舞台。由此,以个体认知为基础的村庙的灵验就被转变化成为了一种公共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是潜伏着危机的地方性认同,并且也与国家实行的差异的政治学相去甚远,但却不能不说这是文化的复兴,因为新的文化表征借此可以得到传递或者我所谓的“传染”(15)。
结语:无法超越的左和右
建立在理性和进步观念基础之上的现代性的极端性没有为“宽容”和“中和”留下一丝一毫的空间,留下的只是对于过去、传统以及另类文化的彻底的、极端的抛弃。这样一种观念在前后相差半个世纪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与这种粗暴的处理传统和过去的做法有些不同的应该算是早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我们今天知识分子和公共舆论对于乡村文化和社会改造的态度和实践。
当同情乡村文化的社会改良者们有意将“贫弱病苦”的标签安插在农民身上之后,村民自己的文化创造力就变得日益不重要了,改变他们的文化成为了最为直接的社会行动的动力。不论是扶贫还是社会救济,根本的还是将乡村的文化看成是根源于“落后”和“不文明”,因而需要得到改造。这样的社会改良者可以是地方的学者、国家的学者以及地方的精英,他们共同接受的是极端政治的既定预设,并将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不同于城市与现代文明的情形都归结为落后与迷信。当然,今天也出现了新的形式,那就是从一味的改造转变成为了一味的保护,一下子乡村文化的全部的东西都成为了值得保留下来的历史和传统。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许多的乡村庙会开始热心于申办国家级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范庄的龙牌会已经成功地申请成为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说彻底地否定是建立在对于过去和传统的无端的鄙视上面,那么完全的保护则是由新的知识精英和地方精英共同发动的对于过去和传统的盲目的崇拜。这样做根本都没有给村民自己的文化选择留有任何的余地,村民依旧在那里烧香求菩萨。
这应该算是一种对于乡村文化改造的再一次回潮,其借助的是对文化破坏和摧毁的文化的复兴和保护,但是这种复兴和保护应该不是农民自己在做,而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代理人在做。回顾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历程,在上述两种极端的政治中间持续不断地存在着的是两种交替出现的社会干预形态,我们可以借用吉登斯的概括称之为“左”和“右”这样两种。在中国的语境中,对于这样两种政治态度的更为直接和实际的对应或许是“拆”和“建”这两种,他们构成实践场域中的两种社会改良态度。“拆”是武断的不加筛选地抛弃陈旧的东西,而“建”则是在优良的“传统”与“糟粕”之间进行选择,仔细地看护和保留甚至是重新发明优良的传统,而在这个过程中,陈旧的糟粕自然通过社会遗忘的机制而得到了抛弃(16)。后者实际依旧是依据一种极端政治,不过是在文化的伪装之下、在学术发现的权威之下来开展工作,这些活动借用人类学家费边 (Johannes Fabian)的话就是,使当地人特别是当地的没有掌握权力的人发不出声音,人为地造就一种“缺席者”的局面(17)。
现代中国对于乡村文化不仅仅是控制的历史,而且还是改造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其合法性的依据是极端化的对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以及文明与野蛮之间差异的想像。借助这种想像而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看似全新的对于乡村社会以及文化还有他们生活方式的改造。陈翰笙先生曾经不无讽刺地批评过民国时期山西省主席阎锡山的乡村改造的“新方案”,他的批评是借用阎锡山的代言人对《大公报》记者无奈地说出来的一番话来进行表达的:
我们已确定了一个计划。现在,人们害怕贯彻这一计划,而共产党说它完全是欺骗人民的方法。我们认为,共产党在鼓吹极端手段,而只有采取我们的计划才能避免流血。即使到那时预计仍有一些动乱。实际上,贯彻新政策的时机尚未到来;但我们将在有必要避免流血的时刻实行这一政策。……我们的农业新方案就像一列破损的火车,人们不敢乘坐,而赤色分子声称它是开不动的。我确信,如果我们要行动的话,我们将首先推动这列火车。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知道它到底能不能开动。不管怎样,我们已完全准备好了。(18)
实际上,在我们一开始接受了现代性的理性之时起,就已经命定地是要在现实与改造之间不停的摇摆。改造的结果不是使既有的乡村文化成为一片“废墟”,便是会激起进一步的抵抗而使既有的文化受到重创和摧残。那位阎锡山的代言人所提出的“破损的火车”的比喻应该是无奈但却是准确无误的。实际上更进一步的比喻还可以提出来,那就是“破损的轨道”。借用费孝通先生的看法,我们的乡村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存在,它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样两条轨道将村庄与外面的世界联系在一起(19)。自上而下的轨道是指国家对乡村社会和文化的控制,这条轨道自明清时代以来已经得到了精致化的修筑,并在民国以后的民族国家建设框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应该说对这条轨道已经是利用得很充裕了。但是,另外一条自下而上的轨道则是指乡民自己组织、自己修缮起来的通向外界的轨道,这条轨道由于国家控制力量的加强,反而使其很长时间没有更多地发挥作用了,几乎处于闲置状态之中。车体破损一点似乎还可以忍受,但是,如果轨道长久闲置,无人照看,那么一旦启用起来,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发生。
由于过度强调单方面对乡村文化的改造,文化认同的危机由此不断地生发出来。极端的对立和差异的想像以及身份的界定又使由下而上的对这种认同产生了怀疑以及不信任。一方面排斥乡村,另一方面又试图改造乡村,一系列的对立在近代中国得到了不断的发明和创造,各自成为对立和背反,无法调和,结果二律背反地走在摇摆的极端主义的道路上。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乡村文化的复兴是处在了“不可能”的境遇中,最终的结果只能体现出不能超越左和右的恰如钟摆一样的“拆”与“建”的循环往复。这也许是现代性的悲哀,而不是乡村文化自身的悲哀。
收稿日期:2006-06-20
注释:
①Ying-shih Yu,"The Radicalization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Daedalus:China in Transformation.Spring 1993,125-150.
②借用哲学家梯利(Frank Thilly)对康德的解释,我们的理性有这样的倾向性,那就是要么是把一切现象归结到“终极和至高无上的境地”,要么就是无所凭依,陷入“无条件的境地”。但是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我们构成宇宙的观念,都使自己陷于各种对立中”,此类命题都属于诡辩之列,无法得到证实,也无法被推翻,一种是根基于理性的必然,而另外对立的一种也能够为自己找出实际无可辩驳和必然的根据。这样的一种状态便构成了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葛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页。
③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版,第395页。
④Pascal Boyer,"Cognitive Track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How Evolved Intuitive Ontology Governs Cultural Transmiss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99,100(4):876-889.
⑤Lucien Lévy-Bruhl,The 'Soul' of the Primitive.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65.
⑥Myron L.Cohen,"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Chinese 'Peasant'",Daedalus:China in Transformation.Spring 1993.125-150.1993,pp.155.
⑦有关“这里”与“那里”关系的分析是来自于费边(Johannes Fabian)的对于时间的讨论,参阅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140页,特别是第133页插图。
⑧杨念群:《“兰安生模式”与民国初年北京生死控制空间的转换》,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⑨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十星级文明户”是指要满足下面的十项指标:勤劳致富、遵纪守法、计划生育、敬老爱幼、家庭和睦、学用科技、学文重教、义务奉献、讲究卫生、移风易俗。但实际的评选并不严格按此标准,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11)王宜祜、萨福简:《福建的“新生活运动”》,载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 1986年皈(第12辑),第171-186页。
(12)赵旭东:《表征与文化解释的观念》,载《社会理论学报》2005年第2期。
(13)赵旭东:《民俗的易感染性》,载《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14)此文本由退休的县文化馆馆长张焕瑞撰述,文中他强调几点,一是由皇帝敕封;二是建庙时间最久,是在刘秀即位(公元25)后不会超过公元30年曾下旨建造“昭济圣后庙”,这是州志记载,并认为这就是“水祠娘娘庙”。如果这样,那建庙时间就有1970年历史。三是供奉真名实姓的赵州本地人,就是传说中搭救过刘秀性命的常信村村民贾亚菇;最后强调“宏扬济困扶危的精神美德”。
(15)参阅赵旭东《民俗的易感染性》,第5-28页。
(16)赵旭东:《拆北京:记忆与遗忘》,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7)Johannes Fabian,Anthropology with an Attitude.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77.
(18)陈翰笙:《中国“模范省”的乐土》,载汪熙、杨小佛《陈翰笙文集》1985年版,第99-10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36/1985年版,第109页。
(19)参见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
标签:文化认同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迷信活动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二律背反论文; 身份认同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