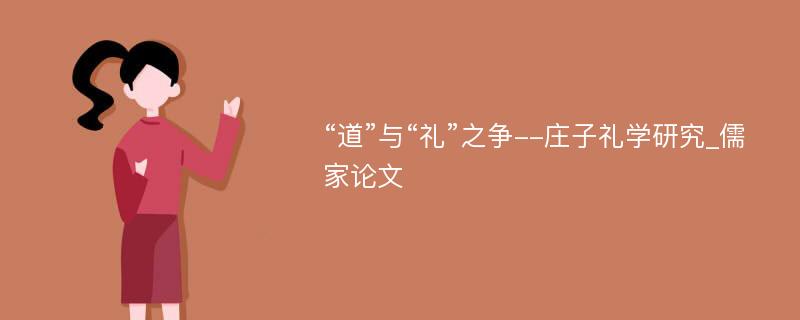
“道”、“礼”之辩——庄子礼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庄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
一、以道批礼:礼是乱之源
道家以道为宇宙的本原和最高主宰,视道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列道为治理天下的唯一准则。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章),即是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则,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庄子提出以道观天下的主张,也是要求君天下者循道无为,做到“无欲”、“无为”、“渊静”(《庄子·天地》)。基于此,道家站在道和“道治”的立场批评礼和礼治。老子曾从道的高度、无为的视角考察道治与德(仁义)治、礼治的差别,得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三十八章)的结论,指责礼是一切祸乱的根源。庄子沿袭老子的致思路径,假借黄帝之口,通过从不同视角解说道、德、仁、义、礼的不同特征,解释老子上述“失道而后德”诸语,全面否定礼的价值:“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庄子·知北游》)。庄子的意思是,道(德)神圣广大,无处不在,又无形无象,无为自然,其特征超出感官认知层面;礼与仁义均是道的对立者,均属“有为”范畴,其形式化、表面化特征所包藏的是人性人情的异化。道是先于人而存在的自在之物,在道与人之间,道主宰人,道治因此有其逻辑依据;礼和仁义乃人为的制造物,在礼与人、仁义与人之间,人掌管礼和仁义,礼治和德治因而缺少理论前提,特别是缺乏本原性根据。在政治层面,道是理想的为政之道,其价值是完美的、绝对的,礼不具备道的绝对价值,也不具备仁义的相对价值,其价值指向是完全负面的——既伪饰、遮蔽乃至损毁道,又破坏道治下的美好社会,乃“乱之首”。
对于礼是社会乱而不治的罪魁祸首,庄子作了详细的分析说明。他认为礼乐仁义产生之前的“至德之世”系大道流行的理想时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此时,统治者(君王)遵道无为,被统治者(民众)逍遥自由,二者均处于自然状态,人性因之真实自然。就人的社会存在来说,社会中有君有民却无君与民的等级区分,有人生“至德”却无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划分。在此境况下,人们素朴纯真,无知无欲,不分彼此你我。就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来说,人与禽兽同居共存,和睦相处。在此情形下,自然万物处于原生状态,山河大地没有人为痕迹,动植物随意生长不受干扰。简言之,“道治”的政治效果便是至德之世的呈现,至德之世即是人我为一、天(自然)人和谐的人生境界和生活世界。可是,这样的理想社会形态却被礼乐和仁义破坏。如果说仁义的产生造成“天下始疑”,使人民因迷惑而由纯朴走向虚伪,那么,礼乐的产生造成“天下始分”,使人民因等级名分的出现而由人我同一状态走向彼此分离对立状态。更为可悲的是,所谓的圣人竟然将礼乐仁义看作为政之至道,以礼乐仁义治天下,企图用礼乐“匡天下之形,”限定人的言行举止,用仁义“慰天下之心”(《庄子·马蹄》),约束人的思想意识,从而由内外两面控制人的思想和行为。其直接的政治结果是人人弃却真性以放纵和满足物欲,从而导致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并进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局面。为此,庄子判定礼治是治天下的下策,称“礼法数度,形名比详”是“治之末”(《庄子·天道》)。
与道家不同,儒家面临无道乱世,尤其推重礼的正名分、序君臣、治百官等政治价值,美化礼治下的三代为王道盛世。对此,庄子一方面在其关于“至德之世”的描述中,揭露礼的正名分、序君臣所造成的人的等级化以及由人的等级化而产生的人的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的分别和对抗,社会结构在有序的表象下潜藏着的深层危机;另一方面运用其虚构的所谓玄古之时为君者“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庄子·天地》),来说明道不仅仅具有三代之礼的政治功能,而且有益无害,道治优越于礼治。因为“道治”即是以道为准绳来审视君王以及君臣关系、百官职能,从道的维度对待自然万物,也就是说,把道视作确定君臣职分、百官类别和管理自然万物的根本准则;道治的直接效果是包括君臣、百官在内的所有人仅有职业上的分工而无等级上的尊卑贵贱的分别,万物顺其本性和需求自由发展而免遭人类以及任何外力的压迫,能妥善处理好君臣关系,划分好百官职能,协调好人和自然的关系。
二、由礼批儒:儒家崇礼的错误
儒家迷恋先王之道(礼),推崇礼治;道家则标举道,崇尚“道治”。庄子在批评礼和礼治的同时,不得不对儒家的守礼尊礼思想作出回应。在庄子看来,无论三代礼治是否合理,儒家的崇礼观念和复礼主张都是荒唐而有害的。
首先,庄子指出,就算三代之礼具有合法性,三代礼治有其政治价值,这种价值也是暂时的、特殊的,它只适用于时间层面的三代时期与历史层面的三代社会,并不具有超越时空规定的永恒的、普遍的价值。儒家越过夏、商、周这特定的历史时空,设定礼为万世不易之则,其实是将礼的特定作用普遍化并加以无限放大,从而最终将其神化。客观地说,礼在三代乃天下之治道,应被尊崇;在三代之后的今天已一无所用,应被弃置一边,更何况三代之后礼乐已坏。
其次,从历史上看,三皇五帝均以礼义法度为治道,这是三皇五帝为政之道之“同”。但是,这种“同”的根本在于三皇五帝为政天下的政治目标是天下之“治”,而不是为政之道本身的前后相同,也就是说,三皇五帝关于礼义法度的相同选择皆是治天下所必需而已。所以,三皇五帝各自赋予了礼义法度以一定的新的内容,从而使他们所用的礼义法度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这是三皇五帝为政之道之“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皇五帝的治道各不相同,有着差异性和特殊性。这表明,“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天运》)。既然三皇五帝以礼义法度为治道是顺应时世变化的结果,礼义法度的涵义的更换也是顺应时世变化的结果,那么,治道本身同样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常更常新。而儒家墨守三代之礼,尤其是其中的周礼,恰恰同治道的常更常新的内在要求相悖,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古”与“今”、“周”与“鲁”不仅标志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序列和前后更替,还表征古代社会与当今社会、周朝(西周)与鲁国之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质的差异性。儒家只看到社会在时间层面上的前进,以及这种前进的连续性、继承性,看不到社会在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层面上的阵痛和剧变,不懂得“水行”用舟、“陆行”用车,治周用周道(礼)、治鲁则应用鲁之道,更不懂得周道(礼)如同车和舟一样有其适用范围与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在完全不同于三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企图恢复礼治,“行周于鲁”,无异于“推舟于陆”(《庄子·天运》),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儒家坚信六经是先王之道(礼)的承载者,希图通过研究包括《礼》、《乐》在内的六经来破解先王之道,所谓“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同上)。对此,庄子借用老子之口批驳了儒家的观点:“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同上)!这是说,六经与先王之道(礼)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但是,六经不是先王之道,六经也不具备承载先王之道的功能。因为六经和先王之道的关系如同足迹和鞋子之间的关系,鞋子决定足迹,足迹却不能代表鞋子;先王之道决定六经内容,六经所记却不一定是先王之道的真实内涵。这样,即使三代之礼像儒家所说的那样完美伟大,人们在礼乐崩坏的今天也不可能真正认识和掌握它,它将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为政之道永远消逝于历史深处,后人是无法将其还原的。
以上表明,礼即使有其功用和价值,也是历史的、特定的,而社会和治世之道则是发展的、变化的,因此儒家的崇礼情结、复礼主张及其理论和心理基础——静态思维模式与形而上学方法,都是错误的。
三、以道解礼(礼仪):礼仪的道家化
礼从本质方面可以划分为政治之礼、道德之礼和风俗习惯之礼等,就其构成要素来说,包括礼制、礼仪和礼器等。其中,礼仪主要属于礼的形式。庄子从道的高度揭露的危害社会之礼以及庄子批评的儒家所崇奉的礼,从总体上讲主要是政治之礼,即作为政治制度的礼。关于礼仪,庄子虽直接批评其使人注重外在形式和处世技巧,丧失人性的纯真与自然,“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但他更多地是从道的角度解构之,赋予其全新的内容,从而实现礼仪本质的道家化。即一方面从礼仪的反面解读礼,抽去礼仪的固有内容——仪式规则,使礼仪有其名无其实;另一方面,从道以及得道者的视角诠解礼,加入礼仪所没有的内容,使礼仪具有道或者得道者的某些属性。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的道家化实际上是礼仪的消解。
庄子本人精通礼仪,他曾借颜回之口解为臣之礼曰:“擎跽曲拳,人臣之礼也”(《庄子·人间世》),指出执笏、长跪、鞠躬是臣子上朝觐见君王的礼节;他自己解礼仪之礼曰:“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庄子·在宥》),指出礼节仪式由一套繁多的节度规矩所构成。可是,由于庄子对礼仪之礼持否定态度,这使他在阐述自己的礼仪观时,完全将其道家化,彻底削夺了礼仪的“形式化”特征。
庄子认为形式化的礼仪乃虚假的、低层次的礼仪,真正的礼仪、最高层次的礼仪是无“形式”的礼仪,或者说在“形式”的意义上是无礼仪,即没有任何礼节形式;真正的、最高层次的礼仪不是对于礼的实践者行礼时的外在行为的规范式表达,而是自我所达到的人我不分、彼此合一的精神状态。关于这一点,他是通过考察日常生活世界里风俗习惯之礼的礼仪——人际交往中所必须遵循的形式化法则,并由“蹍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这一具体事例或者说经验事实推导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即是“至礼有不人”(《庄子·庚桑楚》)——最高的礼节指人我无所分别,不把他人当作“他人”。庄子的意思是,一个人踩了别人的脚,如果所踩的是陌生人的脚,向对方道歉并解释原因、责备自己,这属礼仪;如果所踩的是兄长的脚,喊出表示粗心、表示怜爱的声音,也属礼仪;如果所踩的是父母的脚,没有道歉的语言,没有怜爱的声音,更合乎礼仪。因为人己关系越亲密,礼仪便越简单,礼仪所表达的内容越真切,礼仪也因此越真实。人我不分境界下的礼仪是礼仪的极至——脱去形式规则的礼仪,达至礼仪极至的礼仪(至礼)是人我不分境界的标志。由此可知,最真实、最高级的礼仪没有形式,没有形式的形式是礼仪的真正形式;最真实、最高级的礼仪指视人若己时的彼此的心灵感应,人我同一时我的内在的、超越形式的精神和情感状态。换言之,礼(礼仪)不是规矩人情、限制人为的一系列规范,而是人性的自然流淌,人生的逍遥境界。
丧礼是凶礼之一,丧礼礼仪指哀悼和安葬死者的礼节仪式,其中包括初终、小殓、大殓、下葬等程序以及哭泣、吊丧等复杂的环节。庄子认为这种礼节仪式乃“世俗之所为”,即人为制造出来的,不足以表达人们源于自然、出于天然的真性真情,反而局限了真性真情的自然流露。因此,庄子借渔父之口说:“处丧以哀,无问其礼”(《庄子·渔父》),主张在情、礼(礼仪)之间任情越礼。在批评丧礼之外,庄子着力于丧礼的道家化。庄子心目中的丧礼排斥任何特定形式,即是说,即使这种丧礼有形式的话,形式也是不确定的或者说多样的;庄子心目中的丧礼礼仪是表达生者对死者的真实情感以及生者面对死者时的内心感受的方式和手段。换言之,表达生者处丧时的情感体验、情感表现和心灵感悟的最佳途径与方式即是丧礼,它没有特定规矩和仪式,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或需要制作和采用不同的丧礼礼仪。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借孟子反、子琴张与子贡的对话具体阐述了上述看法。据《大宗师》载,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超然物外,与道同体。“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孟子反和子琴张“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这是说,丧礼并非如常人所理解的吊丧啼哭之类仪节,丧礼所表达的甚至也不是亲人的哀悲苦痛之情和友人的祭奠死者及慰问其家属的友善与怜悯之情,它是生者直面死者之“死”而沉思和体悟生命现象、生命本质,以及生者与死者进行精神对话和灵魂沟通的样式与方法。相对于常人所熟知的所谓丧礼中的“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踊”(《礼记·丧大记》)之类的仪式来说,真正的丧礼礼仪未尝不可以含有“歌”,只要“歌”所寄托的是生者的“真意”,所包含的是丧礼的“真意”。这样,丧礼超越了形式化的障碍,既可以说是无形式规定,也可以说是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规定。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由批评丧礼时的否定丧礼、任情越礼,转向解构丧礼时的肯定丧礼。不过,这里所肯定的丧礼是业已道家化、精神化的丧礼,而不是三代以来的丧礼。
礼仪无形式规定,丧礼无形式限制。在丧礼没有特定形式规限的前提下,丧礼的实践便无原则可言。针对儒家固守三代丧礼礼仪、强调丧礼实施中的诸多条条框框,庄子提出三代丧礼的实践原则是“简”——简化繁杂的仪式规定。可是,“简”的极限便是“无”——繁杂仪式的无限制的简化、删除,其最后的结果则是三代丧礼中所有仪规的消失。这样,三代丧礼就走向自己的反面——道家无仪则规限的精神层面的丧礼。关于丧礼之“简”,庄子是通过孔子与颜回的问对来述说的:鲁国的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颜回怀疑其“无其实而得其名”,并请教孔子。孔子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庄子·大宗师》)!这无非是从丧礼实践的维度再次说明道家的丧礼超越了具体的、固定的仪式,超越了道德的、情感的界域,是得道者面临他人之死时彻悟生死、顺物自然的精神状态。
吉礼主要是祭祀之礼。斋是举行祭礼前祭祀者清洁身心以示诚敬的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不饮酒、不吃荤等。庄子借孔子之口,通过孔子与颜回问答的形式将斋诠解为“心斋”,以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敬祖求神的祭祀之斋,并从认知角度,准确地说,从心斋的功能的角度将心斋道家化为得道途径和得道境界:“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这是说,心斋是放弃耳与心的认识功能,超脱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使心灵保持绝对空虚的状态,是心灵在绝对空虚境况下体悟和接纳绝对空虚之道的状态,是心灵与道合一情形下人生的最高境界——得道状态。
总而言之,庄子以道解礼(礼仪),用道的无形、超验、无为等属性以及得道者逍遥自由、顺性存真等特征解读礼(礼仪),从而解构三代礼仪,使礼仪道家化。道家化的礼仪已是不具备三代礼仪任何本质特征的超形式化礼仪,其基本的特质是精神性的。如果说三代礼仪是有形有则的“实”的存在,那么,道家化的礼仪则是无形无则的“虚”的感受。
除却上述礼仪的道家化以外,庄子还以道解乐,致使乐道家化。我们知道,广义的礼包括乐,庄子批评礼、解构礼(礼仪)必然批评乐、解构乐。庄子单独批评乐的地方并不多,只是指责“钟鼓之音,羽旄之容”之类人为造作之乐是“乐之末”(《庄子·天道》)。庄子以为真正的乐绝非人为的人间之乐,而是天籁之音——自然的音乐;真正的乐也非有形有声的感性存在,而是“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庄子·天运》)的超越感知且充塞无限时空的神秘性存在。此处,庄子用道之自然性、超越性来解构和解释乐,破除了三代之乐的形式性和等级性,已将乐“道化”。
四、以礼解道:道中有礼、道为礼源
庄子批评礼、解构礼(礼仪),并且否定儒家守礼尊礼思想。但是,庄子毕竟生活在礼乐文化衰而不亡的战国中期,承受着礼乐文化的浸染,毕竟出入过儒、墨、法、名诸家,无法完全排拒儒家礼学的影响。所以,在批判礼的同时,庄子又不自觉地接受了三代之礼与儒家礼学的正面影响,对礼有所肯定。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庄子在其道中容纳了礼的部分内容;其二,道由批判礼的理论武器变而为礼的本原与根据,道甚至失去其原有本质而变为类似于礼的某种存在;其三,庄子肯定儒家的神圣之“命”与世俗之“义”,并将其“礼”化,从而证明礼对于人类的至上价值。
庄子之道指自然之道(天道)。针对儒、墨诸派动辄言“道”,庄子告诫人们分辨道家之道与儒墨之道的区别。他说:“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庄子·在宥》),指出道家与儒家、墨家虽然都言道,但是,道家之道与儒墨之道的本质和内涵截然相反、根本对立。道家之道是以无为为特质的天道,儒墨之道是以有为为特质的人道。令人惊讶的是,庄子偶尔也将道理解为天道和人道的集合体,把原本属于人道范围的礼吸入其中。例如,庄子由认识之维阐述道时即是如此。他说:“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庄子·天道)),从关于道的诸多内容的认知次序的角度阐明道包括天道和人道两部分,由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等构成,其中,天、道德属天道范畴,仁义、礼(分守、形名、因任)、智(原省、是非)、法(赏罚)属人道范畴。这意味着,礼从道的反面、道的对立者转而为道的组成部分、道的基本内容之一。好在庄子言“明大道”时,先明天和道德,后明仁义、礼、智、法,即是说,先明天道,后明人道,意在申明大道之中天道为主、人道为次,天道为本、人道为末,从而列礼于天道之下;大道中的天道是“治之道”,大道中的人道是“治之具”(同上),排除了作为人道之一种或者说人道之组成部分的礼的治世之道的地位,坚守了道家的道治立场。这表明,即便道中有礼,礼也处于次要地位;即便治天下时使用礼,礼也只是治天下的手段之一而已。
道中有礼,道(天道)本礼末,从逻辑上讲蕴含着道是礼的根源和依据。庄子恰是沿着此种逻辑进路往下走的。不仅如此,他甚至由道中有礼、道是礼的根源进而滑向道即是礼——用礼的某些属性来界定道的本质。这时,庄子之道便从天道堕落为人道。《庄子·天道》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万物化作,萌区有状,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矣,而有尊卑先后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庙尚亲,朝廷尚尊,乡党尚齿,行事尚贤,大道之序也。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哉!”这里,庄子认为天与地在空间位置方面的上下关系,春夏与秋冬在时间方面的先后次序,万物在生长过程中所呈现的盛衰变化等自然现象,所表现的即是尊卑主从关系,道即是以尊卑先后的等级秩序为本质的道。宗法血缘亲疏、爵位高下、尊卑长幼之分、贤与不肖之别等构成礼的核心内容的等级序列,被纳入道的本性之中,变成道的秩序。这种失却自然、无为等本质特征的道(自然之道)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礼的化身。沿着天道(道)决定人道(礼乐仁义之类)的思维路径,庄子由天道有着尊卑先后之序的等级之道,推论人道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长幼、男女、夫妇间尊卑秩序、主从关系的等级之道(礼)。这就是说,人道的等级属性取决于、根源于天道的等级属性。如此,礼来源于道,道是礼的本原,原来的道、礼对立转化为道为礼源。这里,庄子在证明礼的形上根源是道之后,还认为具体的礼乐制度是圣人制作的结果,圣人作礼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取象”于天地的尊卑先后。即是说,圣人是礼制的制作主体,自然现象和自然之道(天道)乃礼乐制度的“原本”,礼乐制度则是自然现象和自然之道的“摹本”。
天命和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命是预定人生种种情状的超人间力量,义是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的人间之“路”,顺命行义是人生别无选择的选择。庄子凭借孔子之口,通过肯定、放大命和义的价值,提升其为人生的根本法则,同时把命和义界限在礼的范围内等手段,证明礼在“人间世”的至上意义:“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庄子·人间世》)这表明,庄子把命、义二者看作控制人的形下生存状况的绝对力量,并把这种绝对力量客观化为不可超越的人生戒律;还把礼所规定的子之事亲和臣之事君以及事亲之孝和事君之忠分别注入命、义之中,使命与义呈显礼的特征,使遵命循义质变为践行臣子之礼——尽孝尽忠。这样,庄子肯定命、义即是肯定礼,鼓吹命、义在人生实践中的至上地位就是宣扬礼对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绝对价值。庄子视界中的天下之“大戒”与其说是命和义,不如说即是礼。
综上所述可知,庄子礼学开始于对三代之礼的政治批判,同时对三代之礼的政治价值又有所肯认。庄子礼学的复杂内容是庄子持守道家立场又受三代礼治和儒家礼学浸染的产物。庄子礼学的复杂性反映了庄学源头的复杂性,折射了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各种哲学思潮和政治理论间既相互对立又彼此融合的复杂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