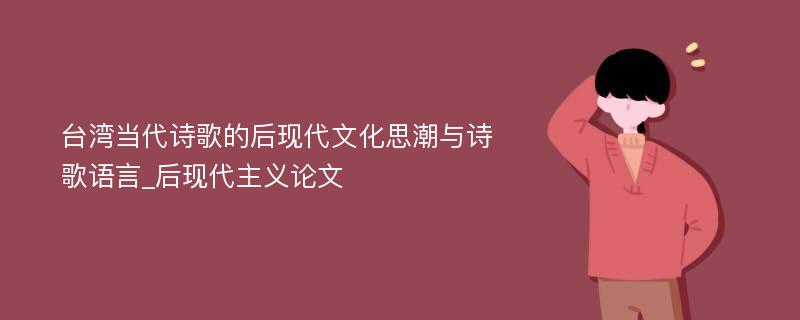
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及诗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当代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34X(2012)04-0005-10
前言:后现代思潮在台湾
后现代主义以“后”字区别并连结现代主义,表现对现代主义的权宜性反思。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本身没有强烈的主体性,而其内涵甚至倾向自我消解。就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来界定后现代主义,因而无法精确勾勒出后现代主义的轮廓。然而当论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显著意义是断代,远大于做为“主义”的思想、风潮或美学趋向,隐藏的意义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势不两立。[1]
事实上,台湾现代诗史中的后现代有两种不同的意涵:时间上的后现代及美学上的后现代。时间上的后现代,指向1980年代以后;美学上的后现代,其哲学内涵重于拼贴的形式,而于1980年以前诗作中就已见蛛丝马迹。然而评论者谈到台湾的后现代诗,多半局限在1980年代以后,甚至1987年解严以后的作品,更以时间上的后现代笼罩美学上的后现代,为后现代诗定下简易而化约的标签;而那些被窄化、僵化、条列化的后现代主义诗作特质,与贴了标签的后现代主义诗人,可能会歪曲未来的诗史。
后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兴发。初始,外文系学者的引介起了定调式的效应。其后各领域的学者蜂拥而至,台湾文学界迅速陷入后现代主义的迷障,几乎形成以“后现代主义时期”为文学史断代的共识。而“何谓后现代”,也就以条列式的准则成为“台湾后现代诗”的基本标签。另外,经过中文翻译的后现代,在精神上蕴含了思维活动的曲折而显得繁复多姿。目前在台湾广为学者援用的两种“后现代”为孟樊与简政珍的界定。孟樊在《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中定义了台湾后现代主义诗的特征:
1.文类界线的泯灭;
2.后设语言的嵌入;
3.博议的拼贴与整合;
4.意符的游戏;
5.事件的即兴演出;
6.图象诗与字体的形式实验;
7.谐拟的大量引用。[2]
简政珍则以为后现代的精神是:
1.批判和反思并存;
2.与内在的自省辩证的后现代与政治的关系;
3.模仿与揶揄同时展现的谐拟;
4.外在纪实的档与内在形式自觉的拉扯;
5.对大众文化的不得不承认与感叹式的批判;
6.未定性的美学空间。如朦胧性、多重性、随意性、嬉戏性、反叛性、断裂性、解构性;
7.播撒、消散、相互嬉戏、相互依存的不定性与内在性;
8.自我反思与自我探问的哲学层次;
9.多重意义的可能性。[3]
正因为后现代主义已在台湾的文艺领域中,经由学者、文化工作者或作家以不乏创意的方式去推衍、扩散其历史效应,即使已知台湾版的后现代主义代表的是一个简化的图腾,评论者应做而可做的,仍是从较细致的作品诠释来演绎这个既成的历史脉络,而不再是将其对照于现代主义,找出其“特征”。台湾版的后现代主义,在现代诗这个领域,出于急切进入诗史的心态,以对号入座的方式,圈定“后现代主义诗人与诗作”的名单,及设定“后现代主义诗作”的特质;而这些既定的诗人、诗作与“后现代诗的特质”,不但未必完全为“后现代”,甚至在精读与诠释之后,展现的是“反后现代”的一面,反而未被标签化的诗人,某些作品的某些方面相当的“后现代”。[4]
居于台湾“主流”位置的后现代论述,以简化的标签横扫文学界与文化界,昌言文类泯灭、意义崩解、游戏当道、解构至上,造成1980年代之后,文学创作者向边缘靠拢的风潮。王德威曾以“拥挤的边缘”讥讽这个“以边缘为主体”的后现代现象。透过文化及文学、美学、哲学翻译的后现代思维,在台湾演绎的具现有形式与内涵分离的现象。在形式上,一眼可见的后现代,未必富含后现代的精神;而具备后现代精神的创作,未必符合评论家的准绳。
后现代诗的盾牌:形式的游戏
文字的拼贴和表面上的文字游戏,是最被符号化、盾牌化的“后现代诗特征”,也是最不值一笑的特征。曾几何时,诗人们为形式游戏躺上供桌的盛况已不再;搁浅在所谓“后现代诗”的沙滩上的,却是充满视觉庆贺的牺牲品。
焦桐称呼诗人的创新实验为“前卫诗”,如视觉诗、语言诗,其创作策略体现在听觉与视觉的戏耍上。[5]而孟樊界义台湾后现代主义诗的特征的其中几项,如意符的游戏、事件的即兴演出、图象诗与字体的形式实验,等等,从诗作最表像的结构与形式样态,而非语言使用,看出了台湾在后现代社会中,文学语言市场化、庸俗化,以及诗人消费语言的状况。在这样的后现代诗表现下,浮华的诗名,市场利益,阅读群众立即的掌声则凌驾于诗人之上,诗人已经与掮客无异。以视觉上的形式游戏做诗,破碎的主体性几乎不再可能凝聚艺术创作的野心与理想以扩张创作的自我,反而使得各种徒具形式游戏的诗歌实验滑向平凡而顺手的机械式复制,以不精准、条件反射式、无限能动的形式舞弊,呈现各种包装过而符合机械化制程的作品。
首开后现代形式游戏之风,并以之为号召的诗人为罗青及林耀德。[6]罗青的《一封关于诀别的诀别书》,在诗的正文、附录与“又及”中,不断对同一个意义做后设衍述;而《多次观沧海之后再观沧海》则表现单义的反复辩证,在诗行中一再显示与原意互相推展的衍生意,从“平平坦坦的大海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到“平平坦坦的大海之上/果然浑然自然的是什么都没有”,语意在海的实存与否推展。罗青的这两首诗,以不断向后推衍的意义制造语言回路,以待读者赋义,是符合机械标签的后现代诗雏形。其后林耀德以《线性思考计划书》一诗做为实践后现代主义的宣言。[7]《线性思考计划书》以组诗形式展现经过设计的解构蓝图。从“现象学的实证”、“读者反应理论的反刍”、“西南德意志学派的说词”、“语言学的看法”、“解构主义的理论”这些子题与四个子题中的“间奏”,为叙事者的后现代诗观做了论诗诗式的宣告。“间奏”颠覆了子题之间的“线性思考”,绾合后现代精神中的“反”,实验性很强。而其的《薪传》更具备台湾版后现代诗的轮廓。《薪传》用连连看的形式把诗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并列与拼贴的对照中显现正反相即的矛盾与纠结,可视为行动游戏诗的先声。类似的技巧后来在夏宇的《连连看》、陈克华的《井》、刘克襄的《金安城小传》中出现,成为典型的后现代诗形式复制。在无限的复制前,夏宇的《连连看》的新意毋庸置疑:
宝蓝
挖
着
无邪的
铅字
□□
方法
笑 手电筒
鼓 人行道
五楼
自由
磁铁
信封
图钉
夏宇是台湾女性诗人中的后现代地标。从1984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备忘录》开始,即以特有的机智与敏锐而广受瞩目。包括后来的《腹语术》、《摩擦·无以名状》、《Salsa》、《粉红色噪音》、《这只斑马》、《那只斑马》,夏宇在台湾出版的每一本诗集,诗作不断被传诵讨论与模仿。夏宇最好的作品是好在直截了当而惊鸿一瞥的比喻,比如《上邪》、《野餐》、《鱼罐头》、《爱情》、《疲于抒情后的抒情方式》;而不是实验性特别显著的语言游戏,像《在阵雨之间》、《降灵会Ⅲ》、《其它》。夏宇诗的后现代景致,表现在把天差地别的两种事物并列做喻而不在于日常景象的并置,例如以蛀牙比喻爱情而有:“拔掉了还/疼//一种/空/洞的疼”;[8]以爱情与昙花比喻青春痘而有:“开了/迅即凋落/在鼻子上/比昙花短/比爱情长”,[9]“蛀牙”与“青春痘”做为意指的中介,展现说话者冰冰凉凉的语调及不假思索的客观性,这是夏宇诗语言的特点。
视觉上的庆贺属于一时的新奇。作品形式上的实验性越强,被复制以后的阅读惊喜就越少。许多看起来像自由指涉的谜题般诗作,起初总以记号的无限衍义,颠覆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例如鸿鸿的《超然幻觉的总说明》、林彧的《空格密语》、陈昱成《开往□□的列车》、焦桐为考生所仿做的一系列考卷,等等。这类诗作没有固定连结与固定答案,意符与意指的关连不再绝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超文本文学的相关创作如动态文字与影像、超级链接设计等元素的加入,扩张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也更易传统的阅读方式,开启有别于平面文本的想象;[10]李顺兴、须文蔚、米罗·卡索在超文本的创作上都曾着力过。[11]如米罗·卡索的超文本诗《钟摆》,诗行如钟摆般可左右摇晃,[12]使读者主动参与创作。因为文本的意义是靠着读者来完成的,互动游戏诗在网络媒介下更显多元,代橘的超级链接诗:《超情书》即是一个例子。[13]但是阅读的焦点与乐趣已经从文字转向游戏,故而这类文字上的互动游戏诗,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游戏是否新鲜好玩,已不在文字本身。诗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及透过文字所能彰显的对人生的感受力,也不再是读者所能期待。
这类放烟火式的视觉庆贺,在诗心贲发的瞬间或可提供趣味性的阅读,然而一时的兴头过后,形式上的文字迷宫最容易让人厌倦。当然稍微有心的诗人,在玩这类游戏的同时,可以镶嵌至少表像的现实或历史背景而增添假深度。向阳在2005年出版的诗集《乱》中,《发现□□》、《メ与○的是非题》、《咬舌诗》、《囚——戏作图象诗》等诗,即属于流风所及的文字实验。[14]以《一首被撕裂的诗》为例:
一六四五年掉在扬州、嘉定
汉人的头,直到一九一一年
满清末帝也没有向他们道歉
夜空把□□□□□□
黑是此际□□□□□
星星也□□□□□
由着风□□□□□□□
黎明□□□
□2010□夕阳□□□□
□□唯一□□□
□遮住了□□
□雨敲打□□□□
□2011□带上床了
□□的声音
□□的眼睛
□□尚未到来
一九四七年响遍台湾的枪声
直到一九八九年春
还作着恶梦。[15]
此诗五段,第一段书写明清之交满族与汉族的族群位移,与第五段书写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际的政权移转呼应,二至四段皆以符号□穿插,形成待填补的语意。向阳以切割的语言对应被切割的历史,形塑“被撕裂的诗”;但是二至四段的□与文字间的数量是个经过巧思布局的提示而非罅隙,比对之后可结合为语意完整的句子。其游戏规则为:第二段特定句次中的□等于第三段及第四段该句□数目的总和,而顺序将第二段到第四段的同位句黏合起来,即为完整的一个句子。例如第二段的第一句:“夜空把□□□□□□”,□的数目为6,就是第三段第一句:“□夕阳□□□□”和第四段第一句:“□带上床了”的□数目总和;于是这一句可还原为:“夜空把夕阳带上床了”。如此依序把“撕裂”的句子拼凑出全貌,即可还原为:“夜空把夕阳带上床了/黑是此际唯一的声音/星星也遮住了眼睛/由着风雨敲打尚未到来/黎明的大门”。[16]留下的空格经过暗示而还原为诗行原本的样貌,就可发现这种刻意的撕裂与刻意的补丁一样,凸显二至四段重复了三次的文字;倘若没有□的遮掩,而直接呈现中间重复的三段,则那三段凸显的是音乐性上的意义。而当此诗删其重而以诗人创作之初的原貌面世,诗行变成:“一六四五年掉在扬州、嘉定/汉人的头,直到一九一一年/满清末帝也没有向他们道歉//夜空把夕阳带上床了/黑是此际唯一的声音/星星也遮住了眼睛/由着风雨敲打尚未到来/黎明的大门//一九四七年响遍台湾的枪声/直到一九八九年春/还作着恶梦”,更可发现填空游戏对于此诗不可更易之主题没有转圜语义的任何作用。这首诗的主体意识强烈,而且以暗喻为表现方式,意指鲜明确切,缺乏后现代艺术的意象流动性。要不是以“意符的游戏”与“即兴的演出”为盾牌,其语言的指涉及意义的延伸具有相当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与“后现代”沾不上一点边。[17]
其它各类的行动与观念游戏可视为这种填空游戏的衍申,广告也充斥着置入性的后现代形式游戏。2006年组成的“玩诗合作社”,在当年元旦的《苹果日报》刊登十则分类广告,如许赫《诚征小弟——许赫帮》、刘哲廷《空屋先生售屋广告》等等,都运用了意符游戏的手法,使得广告披上一层如诗的外衣。
文字被其它艺术媒介取代,而仍以诗为名,在后现代的时间版图上攫取读者的眼睛,有一个堂皇的名字叫做“跨界越位”。跨界、越位、跳梁,在某个层面上意义相通。所谓跨界越位,指的不是楚河汉界的截然划分,而是坐享齐人之福,在文字与非文字之间来去自如地染指,而又指望获得文字这一边的读者青睐,具有相当大的投机性。更重要的是,从跨界越位元的作品来看,往往并非先谨守文字的本位再求越位;而通常是守不住本位,或不知何谓本位,而用跨界越位当做和稀泥的口实,给读者看的是一把又一把自己都说不清的胡涂帐,“朦胧就是美”。跨界越位后的诗人,从没忘记自己的诗人身份,然而表现出比其它诗人对文字成为媒介的更大期待与热情。跨界越位的诗作展演,在台湾现代诗史上的意义是资料上、文献上的,和许多现代诗的活动、诗社的成立一样,可看做“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它在现代诗美学上的功过,以史为鉴,就数百年的中国文学史来臆测,或许只有有效期限在百年内的现代文学史才可能稍微带上一笔。“生活中何处不是诗呢?”这种似是而非的话语仍叫许多读者闭嘴。[18]
图象诗的形式与技巧,近年常被纳入对后现代诗作的讨论。台湾讨论图象诗较早的文章:张汉良的《论台湾的具体诗》,认为图象诗不无可取,但是该文更重要的主张在于,大多数的图象诗都是“陈腐的图形安排”。其后,袁鹤翔对于图象诗的看法为:“西方语言缺乏图形性,故西诗必须从字距结构安排与意象字的结合来造成形、声、意的综合效果。……相反地,中国文字本来就具有图形性,形、声、意俱在文字之中,故不须依赖形式上‘故意’的安排来达到预期的效果。……刻意在形式上追求西化的诗句,常常有东施效颦的恶果。”[19]简政珍则认为:“台湾许多号称后现代诗的形式游戏,其实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反而偏向现代主义的精神。那些片段的文本,以零散的意义和破碎的叙述,在刻意的留白、扭曲的文字、交杂的文字与图象,以及拼贴的外形中,寻找潜在的统一感以支撑崩毁的现实价值,停留在外表看得见的模式里,展现卷标式、皮相式的后现代主义诗作。此所以在台湾后现代诗的时空里,‘意义’往往被粗糙地宣布为虚无。”[20]
在台湾现代诗的发展中,图象诗对于文字透过形、音、义而仍难以展现的静地有一种乡愁,其形式游戏的上乘作品,最多以令人惊喜的想象力停留在意象涌动的刹那,缺乏对幽微人生面向的观察。图象诗对于台湾前行代诗人只不过是偶一为之,带着表像现代性的文字实验,如詹冰、林亨泰;到了战后第一世代,即1947至1960年出生的诗人手中,图象诗大量出现,也被同一世代的学者型诗人封为后现代诗潮下的独特景观。碧果、萧萧、罗青、白灵、向阳、焦桐、陈黎、林建隆、夏宇、丘缓、鸿鸿,等,都曾致力于图象诗,陈黎独树一帜的自我复制更是无人可出其右。且以罗青为例。罗青著有诗集:《吃西瓜的方法》、《神州豪侠传》、《捉贼记》、《水稻之歌》、《录像诗学》等。萧萧以为,罗青在《录像诗学》之前的诗作,“最原始的本质是嬉戏”;[21]而1989年出版的《录像诗学》,论者又多将之引为后现代诗形式游戏的例证,则罗青诗作中的游戏特质几成共识。然而比起许多诗人,罗青诗的游戏特质主要在于自我调侃与嘲弄,因而始终如一地贯串着轻盈的调性。其《葫芦歌》以形式游戏堆砌葫芦的图象而剥除意指,论者认为是“理念先行”的写法。[22]罗青运用“依样画葫芦”、“葫芦里卖什么药”的谚语,以文字绘制葫芦图形而为深用其义,游戏本身就达到了阅读与创作的目的。
对于现代诗学而言,后现代诗的视觉庆贺似乎增添了诗体建设的诸多风景,可供学者及评论家写文章品头论足,故应欣见其发展盛况而不宜予以断然扬弃或否定;然而当诗人以任意的游戏博得声名,复以浅薄的内涵与机械化的形式成为一时之诗潮,读者有必要认真思索它对诗教的影响。尤其一个诗人在具有相当诗名之后,还能安然以嬉游、好玩为借口来制作图象诗,对文字的敬意以及创造的能量就很令人质疑。一个具有盛名的诗人弃深刻的文字世界不顾而径自玩文字游戏,是江郎才尽的前兆。倘若许多读者满足于这样的文字游戏而无所警觉,表示这个社会的文学教养出了严重的问题。
后现代诗的精神:辩证性的思维
后现代诗的精神为辩证性的思维方式,例如因为矛盾而起,对权威、信条、现象、自我、史观的反思、质疑,以及谐拟。启示式的绝望这是后现代诗最重要的精神,也是最被诗评家忽视的后现代元素。就表现而言,启示式的绝望经常展现于语调的悲喜剧内涵,以诗行中潜藏的翻转、意象的嬉戏与流动、空隙与缝隙的牵连等处,而呈现后现代文化情境中的当代性。
简政珍、杨小滨、陈克华的诗,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可看出诗人以传统诗行进行语言的自我消解及语意的断层之特质,他们打破台湾后现代诗在形式或外表上的僵化标签,从内涵上是表现后现代。尤其是简政珍和杨小滨的诗,由于布满语意的缝隙与断层,诗人的自我经常跌落到叙述的断层和破碎的意象中,表现一种当下、瞬间、变异、流动、充满危机、随立随扫的存在情境,透显多重的后现代视野。
在《穿越阳光地带》、《景色与情节》、《为女太阳干杯》这三本杨小滨的个人诗集中,贯串着戏耍、翻转、质疑、谐拟的基调。在《幽灵主义写作》一文中,杨小滨以“幽灵与幽灵的对话”、“一个说唱的幽灵的表达”,描述创作的心理过程,[23]从“幽灵”的自况,足见杨小滨体认:意义之发声,出于意义之瘖哑。可以说,在场与不在场的对话、自我质疑与批判的语言风格,以及奔飞的意象、游走的意义,使得杨小滨的作品焦点落在符征而非符旨。他借着与言自我欺骗,超越怀疑论,而与读者共同创作、共享语言嬉游的欢愉。
表像的语言嬉戏虽是杨小滨诗作的调性,值得注意的是,诗行常在是与否的论证中演进,充斥着各种反转、倒置、颠覆、否定的力量,在语言和意象中宣示“不是”的美学。例如《如果一朵花》的前三段:
如果一朵花提前到来
你不要慌乱。
如果一朵花怀着鬼魅的芳香,如果
她是你昔日的情人/如果它痛击着春天!
仅有一次的花朵,枯萎之前就已跳走
如果它扔在工地上
让一个路过的酒鬼踢开了它![24]
又如《软钉子主义》:
刺到肉里的,未必是爱情。
从心灵的窗户眺望到的,
也可能铺满灰尘。
对一只鞋底的蟑螂发呆
只能解释为
意外发生得太晚。
而光着脚走路,啊,脚尖的
夜曲,在冰凉月色下
戛然而止。[25]
《书签》:
你打开一本尘封已久的书
夹在书签的位置。
它不愿意离开,它死死地
抓住这个字
一个句号。
枯萎的手,书页上的化石
等待另一只手的掌声。[26]
花与情人、钉子与爱情、手与书签在这三首诗中的关联,形成主词及述词、符旨及符征、特定意涵及多重意涵互相纠葛的现象,平添许多阅读趣味。《如果一朵花》将情人比喻为花,但又从味道、开花的状态等各方面否定了它:“怀着鬼魅的芳香”、“痛击着春天”、“扔在工地上/让一个路过的酒鬼踢开了它”,然而这样的花却又是“仅有一次”,诗行就在肯定与否定的辩证中进行。《软钉子主义》以“鞋底的蟑螂”与“冰凉月色下走路的光脚”比喻爱情之碰壁尤其饶富意味。鞋子温暖的环境容易招睐蟑螂,蟑螂跑入鞋子里,而被穿鞋的脚踩死,尸体留在鞋子里没有清出来,可知鞋子的主人不知道鞋子里死了一只蟑螂,故而踩死它很可能出于无心,然而鞋子本来不是为蟑螂设计的居住环境,蟑螂跑到鞋子里,无异于自寻死路。诗行先以“无心的意外”比喻感情中无意受到的创伤,但不停驻在顾影自怜的层面做进一步的发挥,反而接着以“有心的尝试”下了“冰凉月色下走路的光脚”之喻,藉意象说明美丽、切肤、沁凉而短暂的体验,“夜曲”“戛然而止”。蟑螂与光脚这两个比喻一正一反,跳脱一般诗作对爱情制式化的单调颂扬,一边进行对既定认知体系的瓦解,一边重新铭记再现,语言充满活力。
《为女太阳干杯》第一辑的诸多诗作可视为杨小滨的后现代创作,如与书名同题的《为女太阳干杯》:
不过,当太阳蹲下来嘘嘘的时候,
我才发现她是女的。
她从一清早就活泼异常。树梢上跳跳,窗户上舔舔,有如
一个刚出教养所的少年犯。
她浑身发烫。她好像在找水喝。我递给她一杯男兵啤:“你发烧了,降降温吧。”
她反手掐住我脖子不放:“别废话,那你先喝了这口。”一边吮吸我,一边吐出昨夜的黑。
“好,那我们干了这杯。”
瞬间,她把大海一口吸干,醉倒在地平在线:“世界软软的,真拿他没办法。”[27]
基于对太阳的人格想象,《为女太阳干杯》设计了自律与乖张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一方面呈现不安、狂躁、直觉、激情、无限能动的形象,一方面又有干在的规律与习性,因而这两种表面悖反的个性又都符合大自然现象,而为诗人包装过后的嬉戏性。就后现代的意绪而言,此诗有几处值得注意。其一,作为一个符号,“太阳”一词并非固定在某个象征意义上,而有较为繁复的展现。它颠覆神话传说中对太阳的性别,与崇高、令天下瞻仰的特质。其二,诗中顽皮、撒泼、不按牌理出牌的“女太阳”架设为整首诗的指设系统,仍同时受惠于活泼的符号与稳定的象征系统,并非于两者择其一而弃其一。所以读者看到“吮吸大地并吐出昨夜的黑”那样的磅礴象征,又看到“反手掐住脖子不放”那样与自然现象逸轨的表现。其三,由诗题而来的阅读期待,“太阳”是主词,据以衍伸的其它指谓是述语;但是诗从“不过”一词开始,隐去前此的叙述,而其后的描绘又异于一般人对太阳的认知,于是因性别与既定印象的翻转而主词及述语整个反转,变成相对性的指谓。其四,在诗行的行进中,与“女太阳”相关的语汇和语法彼此干扰又互相连结,例如形容太阳像“刚出教养所的少年犯”的奔放、无羁、不受管教意义下,有人管得动的意涵,与“瞬间把大海一口吸干”那种统领一切、无人凌驾其上的象征的不相容;以及“浑身发烫”与“醉倒在地平在线”那种对霞光与太阳热力的牵连,因而“太阳”的特定含意在多重意涵的诗行中绵延繁衍,诗行一边分裂,一边维持原有的意义。其五,《为女太阳干杯》以太阳为仿真建构的客体,根据的不是“太阳具有什么意义”的“普世真理”,而是“太阳做为地球最大的光源及热量”的逼真感。诗行一边力求逼真,一边很敏锐地体会及模拟逼真可能的断裂。因此“女太阳”这个意象一再浮动,诗行在论证中演进,充满吊诡的趣味。
杨小滨的诗很显著的特性,在于将现有的掌控,包括自然现象的认知、常理逻辑的了解,以及既有的真理或谎言的定位,全都翻转倒错,积极摧毁再现的次序。他以充满严肃的意涵倒置是非的表像,意象的符征不断浮动而为扬弃原先较固定的符旨,文本的途径一边维持原有的位置又一边分裂,仿真的对象在符号网络上辗转延生,诗中充斥戏耍的痕迹。
后现代诗作透显的启示式的绝望追求的是实际而非再现的真实,诗行的语意常因而在反转后接续。在这方面,简政珍最能转化后现代的精神,以意象及思维的正面动力展现诗美学的形貌。简政珍在台湾出版的《季节过后》、《纸上风云》、《爆竹翻脸》、《历史的骚味》、《浮生记事》、《意象风景》、《失乐园》、《放逐与口水的年代》,一贯的诗风是在传统的诗行形式中蕴蓄对现实人生的解构及批评,把后现代的多重视野结合于意象的环炼与换喻的逸轨,从实质与内涵呈现后现代精神而不以玩弄文字游戏为依归。例如《二○○一年》:
那人调戏语言
使股市投资人以为蛇的尾巴是一条长虹
他把设计过的五官张贴在旗帜下
麦克风顿时壮怀激烈了起来
而我们能支付的
是一张张撕碎的报纸
清晨就准备以空肚子
面对马路的坑洞和迎风招展的塑料袋
很多心情倒挂成十字路口的交通号志
煞车惊呼后,随口一地的
槟榔汁取代血的见证
以口水取代泪水
以笑声指点那些躲避晨光的数字
那人在楼顶上挥舞色彩错置的旌旗
忘掉信鸽已被截断归程
远方斑鸠旋律悠扬的啼声[28]
此诗对当下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但并不全然肯定或全然否定,而以兼容悲情与喜剧等不同心理模式的话语样态,反思并模拟政治的复杂情境,进而质疑某些既定的常理。诗的开头以不屑的语调带出仿真的主要对象:“那人”。“长虹”与“长红”以谐音戏拟五彩缤纷而未必乐观的经济面向。“旗帜下设计过的五官”与“顿时壮怀激烈的麦克风”两个动态意象,讽刺“那人”所隐喻的政客。“而我们能支付的/是一张张撕碎的报纸”,写选民的:1.无法支付而又不得不支付;2.明知受骗而又无奈的激愤情绪。“刹车惊呼”、“心情倒挂成十字路口的交通号志”、“随口一地的槟榔汁”、“以口水取代泪水”等四个意象,以揶揄的语言稀释而非强化哭笑不得的政治现实。“以笑声指点那些躲避晨光的数字”呼应股市的假长红与撕碎的报纸那两句,显见政客透过媒体光明正大的作弊与民众了然于心的一致唾弃。诗末“在楼顶上挥舞色彩错置的旌旗”的“那人”指的实际意涵为豢养信鸽的一般民众,意义上虽不同于此诗一开始的“那人”,但是在同一个指谓下,民众因养鸽子而在黄昏时分打开鸽笼、在屋顶上挥舞旗帜引导鸽子的寻常现象,成为对此诗所讽喻的政客:“那人”的谐拟,于是“放鸽子”所模拟的客体与动作本身即富于吊诡。最后,以“斑鸠旋律悠扬的啼声”写“忘掉信鸽已被截断归程”,声音之可闻而不可见,则从“斑鸠”与“信鸽”的相似,意味两者的截然不同,进一步延伸两者所暗示的意涵:假使“鸽子”为和平的象征,那么与之相类的“斑鸠”则在意义上暗示了假和平。由此,此诗以谐音的“长虹”写股市的假“长红”、两个“那人”从意义上同样挥舞旗帜的养鸽者写翻云覆雨的政客,及从啼声的相似,以“斑鸠”的假和平写鸽子所象征的已不再的和平,皆从比喻的正向活动中,显露了反向的属性,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借着“像”的比喻意味“不像”的事实。
又如简政珍《四点钟的约会》:
四点钟的时候
妳将拨弄这一条街道的风沙
妳将加速交通号志的闪烁
我们心中累积的微尘
四点钟的时候
妳将带着遮蔽时间的面具
让我看不到快速移动的日影
让我逐渐老花的视野里
看到你春光乍现的
几根白发[29]
此诗以自然的意象流动,写一个凝视者与一个被凝视者、一个动作中的人与一个静止中的人,经由预设的视觉流程与心眼投射,在生活情境中展现的幽默。诗中人以静态的凝视者角度,观看穿梭于表像下的空间与象征意义上的时间的“妳”,而透见“妳”和“我”在岁月中的各种情感丰姿。“拨弄”和“抖落”以嬉戏的语音写出“妳”的动态,它们实际上的语意是快步时衣裙撩动的样貌。既是“约会”,迎向“我”的“妳”在通常理解下应该是轻盈缓步,而“我”应该充满期盼;“拨弄”和“抖落”一则不着痕迹地写出“妳”的疾行、仓促,与“我”的促狭、客观,再则用主动语态取代被动语态,翻转了受制于交通号志、被风沙拨弄的“妳”,语言在嬉戏中埋下了严肃而悲喜兼具的伏笔,暗示时间之不留情面以及或多或少“妳”的心绪动荡,由之延伸以“妳”、“我”两人潜伏在诗行内,平淡、日常而积累的相处,故不同于牛郎织女式或年轻爱侣式的“约会”。诗题“四点钟的约会”因而在诗行的行进中渐次赋予惯性而非偶发、已知而非惊喜的内涵:在诗中人定点浮动的印象中,“妳”在“我们”的“四点钟的约会”时,总在过马路,所以才有“妳将加速交通号志的闪烁”这样的句子。“可想而知”的未来式出以诗中人调侃的代言体,借着对“妳”的预想,写出“我”对“我们”既定关系的感慨以及未来的期望:“妳将抖落/我们心中累积的微尘”。让风“抖落”而非自己主动“清扫”,可知“微尘”累积之随时随地、不知不觉、无可奈何、清扫不及。而既然“扬弃灰尘”是诗中人自己的愿望,却写成一心一意过马路的“妳”“让风抖落”的习惯动作;“妳”虽非主动,不意间却完成了“我”的愿望。“我”的意识在如此的诗语言中获得矛盾的位阶,语调中暗藏了接受现实的不得不然;而“妳”也不再如诗题“四点钟的约会”表面的固定符旨,停留在“被约会的对象”中,而是呈现瞬间展现的符征风采。诗行接下来聚焦在时间的刻痕。“妳将带着遮蔽时间的面具/让我看不到快速移动的日影”,面具不可能遮蔽光线移动,因而不论“面具”所指为何,重点在从“快速移动的日影”引出休止句:“让我逐渐老花的视野里/看到你春光乍现的/几根白发”,特别是“春光乍现”一词。也就是“妳将带着遮蔽时间的面具”一句的作用为虚起而实接,让“快速移动的日影”结合情境铺陈中的“眼花”与实际上诗中人的“老花”,让诗中人睁着眼睛作一个斑斓的梦。“老花”与“白发”指向“约会”的两人的青春不再,使得“四点钟的约会”继续保持诗行语境中的谐谑之意;而“春光乍现”则再度展现流动的符征,把语义从乍见约会对象的惊喜转向约会对象在日影翻动中白发乍现的惊心。“春光乍现”一词的语言裂缝,一方面制造诗行转进中的语言缝隙而产生阅读的韵致,另一方面化时光流逝的苦涩为诙谐的浅笑,令浪漫意义下的“约会”呈现一种美学的偏移,保持意义封口的开放性。故而此诗可谓展现后现代诗作的典型视野。
以上简政珍的两个诗例,从空隙中的美学与意象的流动两方面体现后现代诗作的精义。尤其放在解严后的台湾,在乱象迸发、威权陨落、宗教欠缺说服力的后现代文化状况中,简政珍的诗创作基于既定的现实意义,以客体的逼真度为摹写基础而促使结构衔接进展,意象跨出理念的框架后,进一步以自己的风采,和浮动中和其它的物象产生奇诡的连结,虚实互映,常理逸轨,语调舒缓,与人生的情境牵连,在语言的缝隙中营造诗义的可能性而引发深一层的玄思。
简政珍和杨小滨透过诗行,以富于理想性的自我调侃与谐拟,对存在、现状、信条等等不断诘问。这种对自我的反思、质疑,以及若隐若现的辩证性,呈现台湾后现代诗的内在要素。
结语:歧义的美德
在台湾当代诗的后现代文化思潮中,后现代的“后”同时具备“现代主义之后”及“对现代主义的反动”两种意涵。权宜性的“后”字,极贴切地表述了后现代思维中的解构精神:既解构外于自我的一切,也趋向自我消解。语意的缝隙或断层在后现代的诗作中因而是最该被看重的元素,即使符合某些既定卷标的文字游戏也应和后现代的表像。在意象的边界,从未交锋的事物突然相遇,意义以播散而非消灭造成多方向的逸轨或折返,于是意象界面两端的不平衡感,将文字的趣味推进一层深度。常理逸轨、符征流动,诗作在内涵上从绷紧的状态中放松,以游击的身影声东击西、避重就轻,调侃现实、凸显人生的荒谬。故而后现代诗以歧义为美德,但非以歧义遮掩想象及内涵的欠缺。
后现代诗的语言嬉戏追逐的不是终点,而是过程;是不时的移动,而非定点的执着;是离开地面的瞬间凝注,而非飘在天空的恒常挪移。台湾当代诗中真正的后现代作品,即使不乏嬉戏的语音,然而诗行中的当代感、理想性与空无指涉,使得诗的功能趋向宗教。检视台湾从1980年代起,经由文化翻译者、批评家与诗人切磋、角力,最后达成共识或共谋的后现代形式标签,更令人欣喜的是标签贴不住的后现代堂奥。
①陈大为即认为:“‘后现代’一词,对台湾文学史的最大意义在:断代。”见其《台湾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评议和演练——评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陈大为:《风格的炼成》(台北:万卷楼,2009),页165—178。
②孟樊:《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台北:扬智,2003)。
③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149—150。
④陈大为说,台湾的“后学”大兴,凸显诗史的命名意识:“台湾(外文)学界将‘后现代’视为前卫艺术与思想的旗帜,部分新锐作家视之为引领风骚的标签,前仆后继地投奔到后现代旗下,按照后现代的美学特质——拼贴、嬉戏、谐拟、不确定、零散化、平面化、图象化——来创作,然后急迫地等待后现代学者来‘册封’或‘冠名’。”见陈大为:《中国当代诗史的后现代论述》,《国文学报》,第43期(2008年6月),页177—198。
⑤见焦桐:《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台北:时报,1998),页64。
⑥罗青的《观海》和《一封关于诀别诀别书》曾以“后现代诗两首”为题,在《中外文学》刊出。此二诗皆收于罗青:《录像诗学》(台北:书林,1988),页254—257。
⑦林耀德:《都市终端机》(台北:书林,1988)。
⑧夏宇:《爱情》,《备忘录》(自印,1984),页17。
⑨夏宇:《疲于抒情后的抒情方式》,《备忘录》(自印,1984),页38。
⑩相关讨论可参见须文蔚:《网络诗创作的破与立》,《创世纪诗刊》,第117期(1998年12月),页80;林淇瀁:《逾越/愉悦:信息、文学传播与文本越位元》,收于罗凤珠:《语言,文学与信息》(新竹:“清华”大学,2004),页587。
(11)可参见李顺兴:《超文本文学形式美学初探》: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02/002-lee.htm;李顺兴:《歧路花园》:http://benz.nchu.edu.tw/~graden/b—su.htm;须文蔚:《触电新诗网》:http://dcc.ndhu.edu.tw/trans/poem/index01.htm。
(12)见《电子诗歌》:http://dcc.ndhu.edu.tw/trans/poem/2003/works/clock.swf。
(13)关于代橘《超情书》的评论,可参见须文蔚:《台湾数字文学论》(台北:二鱼,2003),页62;曾志诚:《略论第一代网络诗的实验特质——以ponder与Elea(代橘)的作品为例》,《新竹教育大学语文学报》,第16期(2010年12月),页1—28。
(14)向阳:《乱》(台北:印刻,2005),页46—49、74—76、102—104、132。
(15)向阳:《乱》(台北:印刻,2005),页18—20。《一首被撕裂的诗》亦改编为超文本,以动画版、拼贴版及gif版等三种动态形式,于2002年的台北国际诗歌节展出。
(16)关于此诗二至四段□的详细比对,可参见孟佑宁:《文本与超文本的邂逅——以向阳“一首被撕裂的诗”为例》,《台湾诗学学刊》,第5期(2005年6月),页243—263。
(17)“后现代”一词虽有“在现代之后”、“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等在发生时间以及意涵上的指谓,但是比较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时,论者从实质上看待,时而有不同的视野。简政珍在《台湾现代诗美学》中认为,若就李欧塔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辨方式,则台湾有些貌似后现代的诗作,其精神实为现代主义。李欧塔即不仅体认到两者的接续,甚至认为先有后现代才有现代。参阅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148。
(18)关于后现代诗跨界越位的表现,可参考萧萧:《跨界越位的后现代:以林德俊〈乐善好诗〉为例》,《当代诗学》,第6期(2010年12月),页111—140。
(19)袁鹤翔:《略谈比较文学——回顾、现状与展望》,《中外文学》,第2卷,第9期(1974年2月),页62—70。
(20)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页164—170。
(21)萧萧:《后现代主义的台湾论述——罗青论》,《国文学志》,第10期(2005年6月),页105—128。
(22)参见丁旭辉:《台湾现代诗图象技巧研究》(高雄:春晖,1998),页142。
(23)杨小滨《幽灵主义写作》:“写作是幽灵与幽灵的对话,是逝者、与他人(周遭的幽灵)、与世界(万物的幽灵)、甚至与虚无(不在的幽灵)对话。”“一个幽灵,总是禁不住要喋喋不休,要噤若寒蝉,要欲言又止,要言不及义,要虚与委蛇——”“一首诗是一个说唱的幽灵,有声的文字,依赖于节奏、速度、强弱、断续、旋律、呼吸、心跳的表达——”见杨小滨:《景色与情节》(北京:世界知识,2008),页174。
(24)杨小滨:《景色与情节》(北京:世界知识,2008),页123。
(25)杨小滨:《为女太阳干杯》(台北:伤物印书馆,2011),页8。
(26)杨小滨:《为女太阳干杯》(台北:伤物印书馆,2011),页104。
(27)杨小滨:《为女太阳干杯》(台北:伤物印书馆,2011),页1。
(28)简政珍:《放逐与口水的年代》(台北:书林,2008),页135—136。
(29)简政珍:《放逐与口水的年代》(台北:书林,2008),页146。
(30)陈建民认为,简政珍诗作的后现代表现为:以意象与换喻取代再现及比喻;回避主体我的告白方式,以辩证式的质疑展现对存在的反思;着重动词与受词之间的逻辑关系,而非以主题为主力。陈建民:《简政珍诗中后现代精神的正面导向》,《兴大人文学报》,第39期(2007年9月),页229—250。
(31)丁旭辉:《台湾现代诗图象技巧研究》(高雄:春晖,1998)。
(32)向阳:《乱》(台北:印刻,2005)。
(33)李顺兴:《超文本文学形式美学初探》:http://benz.nchu.edu.tw/~intergrams/intergrams/002/002—lee.htm。
(34)李顺兴:《歧路花园》:http://benz.nchu.edu.tw/~graden/b—su.htm。
(35)孟佑宁:《文本与超文本的邂逅——以向阳“一首被撕裂的诗”为例》,《台湾诗学学刊》,第5期(2005年6月),页243—263。
(36)孟樊:《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台北:扬智,2003)。
(37)林耀德:《都市终端机》(台北:书林,1988)。
(38)袁鹤翔:《略谈比较文学——回顾、现状与展望》,《中外文学》,第2卷,第9期(1974年2月),页62—70。
(39)夏宇:《备忘录》(自印,1984)。
(40)陈大为:《中国当代诗史的后现代论述》,《国文学报》,第43期(2008年6月),页177—198。
(41)陈大为:《风格的炼成》(台北:万卷楼,2009)。
(42)陈建民:《简政珍诗中后现代精神的正面导向》,《兴大人文学报》,第39期(2007年9月),页229—250。
(43)焦桐:《台湾文学的街头运动》(台北:时报,1998)。
(44)须文蔚:《台湾数字文学论》(台北:二鱼,2003)。
(45)须文蔚:《网络诗创作的破与立》,《创世纪诗刊》,第117期(1998年12月),页80。
(46)须文蔚:《触电新诗网》:http://dcc.ndhu.edu.tw/trans/poem/in-dex01.htm。
(47)曾志诚:《略论第一代网络诗的实验特质——以ponder与Elea(代橘)的作品为例》,《新竹教育大学语文学报》,第16期(2010年12月),页1—28。
(48)杨小滨:《景色与情节》(北京:世界知识,2008)。
(49)杨小滨:《为女太阳干杯》(台北:伤物印书馆,2011)。
(50)简政珍:《台湾现代诗美学》(台北:扬智,2004)。
(51)简政珍:《放逐与口水的年代》(台北:书林,2008)。
(52)罗青:《录像诗学》(台北:书林,1988)。
(53)罗凤珠:《语言,文学与信息》(新竹:“清华”大学,2004)。
(54)萧萧:《后现代主义的台湾论述——罗青论》,《国文学志》,第10期(2005年6月),页105—128。
(55)萧萧:《跨界越位的后现代:以林德俊〈乐善好诗〉为例》,《当代诗学》,第6期(2010年12月),页11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