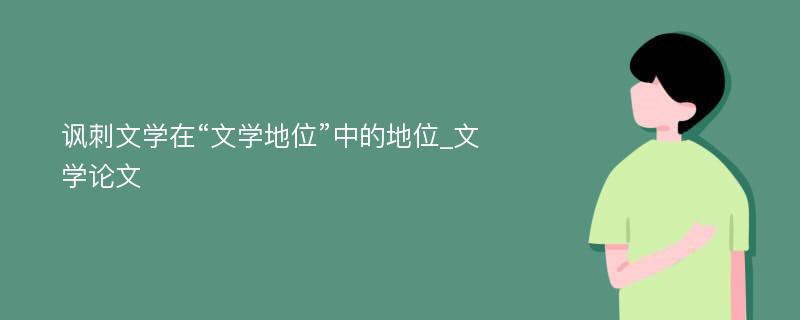
讽刺文学在《文艺阵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阵地论文,文艺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6)-01-0014-04
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的成立,文学作品几乎都笼罩着时代大转折时期所特有的热情、幻灭、痛苦、焦躁与不安,但在众声喧哗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出讽刺的主调”。[1] (P451)如果说,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鲁迅树了短篇讽刺的规模”。[2] 那么到了第三个十年,讽刺文学已硕果累累,但我们的研究却仅在张天翼、沙汀、钱钟书这几个大家中展开,这未免过于褊狭。基于期刊杂志与近现代文学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无论谈到哪一面,都会自然而然地涉及到另一面的认识,笔者想通过《文艺阵地》来研究抗战讽刺文学的生成与发展,原因与意义。这不仅因为它是抗战大刊,与《野草》、《鲁迅风》集中发表杂文,《七月》、《中国诗坛》较多发表讽刺诗,《解放日报》较多发表讽刺小说相比,它为抗战时期各种文学体裁的讽刺文学提供了最初的和最有影响的发表园地,讽刺文学亦成为这个刊物的主打品牌、拳头产品;更重要的是,以它为主场的“暴露与讽刺是否有利于抗战”的论争,为抗战文学现实主义发展的深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2月,茅盾在武汉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徐伯昕筹备抗战刊物的出版工作。两个月后,《文艺阵地》按照茅盾“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半月出一期,每期约五万字;内容包括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战地通讯等)、论文、短评、书报评述,以及国内外文艺动态,字数以三五千字为限,千字以下最好。但小说、剧本可以万字以上”[3] 的设想于广州创刊。自2卷7期起由适夷编辑,至第5卷改出《文阵丛刊》,24开本,共出两辑。自6卷1期起迁重庆出版,组成编委会,编委有以群、艾青等。改为月刊,出至7卷4期停刊。后又续出《文阵新辑》丛刊,24开本,共出三辑。1944年3月停刊。总的来说,它延续了茅盾此前成功主持的以《小说月报》、《文学》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关注现实人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一直保持论辩态势以及顽强坚韧、厚重坚实”[4] 的显著特色。
如果说主编是一个杂志的灵魂,办杂志需要一种目的性极强的理念来指导才能保证编者的想法可以得到最大的贯穿;那么,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暴露与讽刺文学创作与论争运动,就是茅盾的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1938年4月由他执笔的“这阵地上立一面大旗,大书‘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的创刊词,显示了刊物强烈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在此之前,茅盾关于《四季相思》不能装进《八百壮士》,“但何尝不可以装进一些讽刺那躲在后方犹然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的内容去?我们需要激昂慷慨,悲壮英武的内容,但我们也需要嬉笑唾詈的内容”[5] 的演讲,表明了办刊人对讽刺文学的最初设想和欢迎态度。创刊不久,茅盾深感“抗战文艺运动”的难以开展,[6] 在《文艺阵地》上正式发出了抗战文艺题材应当广博复杂,不但“要表现新时代曝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7] 的号召;同年8月,他再次上阵,发表著名的《暴露与讽刺》[8] 一文,对暴露讽刺的必要性、对象、作用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旗帜鲜明地为讽刺文学呐喊助威。时至1941年1月30日,茅盾又在《新蜀报》上发表《现实主义的道路》,呼吁大家重视杂文,要让它发挥突击队的作用。鉴于杂志对小说、报告文学的偏重,他还在《文艺阵地》第六卷第一、二期上,增加了“杂感”栏,专登杂文。[9] 应该提及的还有,茅盾一直以杂志编后记的形式来肯定、引导讽刺文学的创作,如将《差半车麦秸》视为“目前抗战文艺的优秀作品”;认为《防空——勘察加的一角》是“真正能寄沉痛于幽默的作品”;肯定《冀村之夜》、《牺牲精神》用企图讽刺和暴露的态度,写出否定的典型;高度评价《一个老地主的故事》提供了战斗文艺的新类型。
《文艺阵地》刊出的讽刺作品共有48篇,字数多在三两千之间,有不过十行的诗歌,也有超过5万字的中篇小说。从刊物的比重来看,它们占文学作品总篇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刊物篇幅的三分之一强。从影响来看,有当时就名重一时的抗战讽刺文学开山之作《华威先生》、《魔窟》,代表作《防空——堪察加的一角》、《在医院中》、《烧箕背》等。具体地说,它们是小说18篇: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沙汀的《防空——堪察加的一角》、《老烟的故事》、《烧箕背》;周冷的《胡队长》;萧蔓若的《牺牲精神》;骆滨基的《诗人的忧郁》;周文的《救亡者》;一文的《县长》、《可怜的人》;易丹的《迁厂》、李励文的《一个小学校长的奇遇》;任重的《联保主任》;陈翔鹤的《傅校长》;巴人的《一个老地主的故事》;徐盈的《刘明的苦闷》。诗歌7首:任钧的《“民族复兴根据地”》、《“救国专家”颂》、《“文明”和“野蛮”》、《校长会议与午睡问题》、《“安哥拉”的点和线》;高岗《讽刺二题》。散文5篇:林焕平的《一件小事》;力群的《“胖专员”和“糊县长”》;李石锋的《“扇”变》;田仲济的《灭口》;于悫的《英雄的像及其他》。剧本4个:陈白尘的《魔窟》;赵如琳的《转机》;陈豫源的《抽水马桶》;舒群的《吴同志》。报告文学7篇:落繁的《保长的本领》;野渠的《伤兵未到前的一个后方医院》;丁玲的《冀村之夜》;司马文森的《模范老爷》;天虚的《指挥所里》;叶素的《资本新论》;寒波的《一个赌窟的消灭》。童话2篇:周文的《长期磕头的故事》、《神经错乱病》。转载1篇:丁玲《在医院中》;译作4篇:方士人译《高等学校》;李葳译A契诃夫《亲爱的》;林秀清译美嘉塞玲坡特《他》;袁水拍译《雪莱诗钞(七首)》。
以上作品,从人物形象来看,有国民党文化官僚、基层官吏、普通小职员、知识分子,农民;有没落绅士、帮会流氓、地主。他们的被塑造,一方面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抗战讽刺文学讽刺对象由个体到群丑的变化轨迹。从行政区域来看,有国统区、解放区;也有沦陷区;还有民族复兴根据地。这种“咸与讽刺”的情况应是抗战讽刺文学的特征之一,因为稍后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解放区的讽刺文学几乎销声匿迹了。从题材和主题来看,有童话故事、新儒林外史、乡村传奇。有社会政治讽刺,有道德人生讽刺,也有风俗文化讽刺。讽刺主题自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全部出现后,在这里算是来了个集体亮相。从体裁看,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童话、散文各式齐全。其中抗战讽刺小说从短篇向中长篇、戏剧从独幕剧到多幕剧的发展脉络最为明显。文学作品现实——呈现式讽刺,荒诞——寓言式讽刺,漫画——夸张式讽刺并存的现象,也说明了抗战时期讽刺文学在语体和文体方面的丰富和完备。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说,张天翼的夸张、峭利愤激,沙汀的冷静、客观,均成熟于此。陈白尘的“怒斥”风格亦初步形成。任均的诗歌与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凡陀山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作品的或辛辣、温和,或忧郁、俏皮,或明快、沉重,使《文艺阵地》上的讽刺文学披上了多彩的外衣。
与讽刺相关的理论文章20篇,在篇幅上占刊物理论文章的三分之一弱。它们是: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抗战与戏剧》;李育中的《玛耶阔夫斯基八年忌》;茅盾《八月的感想》、《暴露与讽刺》、《我对于“文阵”的意见》;黄绳的《谈黑暗面的把握》、《抗战文艺的典型创造问题》;钦文的《实感的运用》;适夷的《暗阴的光》;景宋的《话剧在上海》;巴人的《民主与现实》;杜埃的《确立文艺政策》;西涢的《关于讽刺诗》;艾青《对于文学上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等。文章就讽刺文学的界定、目的意义、创作方法进行了阐述和评说,形成了讽刺方面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如《关于讽刺诗》就认为讽刺诗是“诗人们用吹毛求疵的眼光去窥视现实,对于那些滑稽的畸形事物,给以无情的攻击,而且诗人们在正面攻击之余,要以另一种手法去侧击那些畸形事物的弱点”的产物。这就抓到了讽刺文学的实质即它所特有的贬抑思想、讥讽态度和批判精神。文章还流露出了讽刺作家的自豪、优越感:“不是任何写诗的人都能写讽刺诗,这是和会使长矛的人未必也会使短刀是一样的道理的”,“讽刺诗,它是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方式都较为难以讨好的,它需要明锐的眼光,缜密的思维和锋利的笔。”《抗战与戏剧》则指出了讽刺文学的必要性、迫切性:“现在我们有一个比萧伯纳巴蕾更伟大的讽刺作家,幽默作家。他把一切都放到一个新秩序里,他把一切的原形都显露出来了。缺乏的是记录者。——这是很奇怪的现象,直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喜剧,差不多都是所谓硬性的东西。这种现象在现实的比例既不相侔,对于观众也不相宜,因为一个人不能一天到晚老是‘弓上弦,刀出鞘’的过着紧张的生活。”更多的文章论述了讽刺文学的作用、目的和意义。如“错误的暴露有时比正面的建设还要有力,还要重要”(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讽刺和暴露”“将成为现阶段文艺工作的特征之一”,它“可以促进军事上政治上的缺点的改革,促进对于人民生活改善的注视,矫正祗见白不见黑的浅薄的乐观派的错觉”(黄绳的《谈黑暗面的把握》)。还有一些文章对外国讽刺文学作家、作品进行了介绍和宣传。如《玛耶阔夫斯基八年忌》认为玛耶阔夫斯基的诗是典型的政治讽刺诗,中国新诗歌应从他那里取得滋养取得活力。《话剧在上海》则介绍了1939年在上海公演莫里哀讽刺喜剧《装腔作势》的情况。
《文艺阵地》中讽刺文学的盛况,是抗战时期讽刺客体丑态百出、大众讽刺意识空前凸显、现代讽刺文学发展必然和敏锐有远见的刊物编辑顺势引导等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其意义,从审美角度来说,这是文学否定型喜剧对传统肯定型喜剧的胜利,类似内容前人已有论述,在此不再累赘;从功利角度来说,则是讽刺文学与杂志的双赢。
就《文艺阵地》而言,它选择了讽刺,就选择了一条可以引领读者向前走的道路。思想是办刊的灵魂,如果思想与读者同步,甚至落后于读者,那么它必在读者的选择之外。只有独立、先进的思想才可以保持一本杂志的卓越品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大举入侵,国土大片沦陷。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官吏们的花天酒地、凡夫俗子的得过且过的现实使部分清醒者一改初期的盲目乐观,致力于现实生活中新旧痼疾的揭露、清除。此时,《文艺阵地》为讽刺的大开绿灯、护航保驾,一方面顺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办刊思想走在了读者的前面。另一方面则为杂志的生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第一,此举使《文艺阵地》团结、推出了一批老作家、文学新人。据茅盾统计,在他“亲自编辑的十八期《文艺阵地》中,经常撰稿的当时已经成名的作家或者后来成名的作家,就可以列出七十多位”,[10] 作家有张天翼、姚雪垠、沙汀、丁玲、任均、陈白尘、周文、陈翔鹤;理论家有适夷、李南桌、巴人、李育中、黄绳等。这走的显然是“有名家就有名杂志”的路子。第二,此举有助于刊物的发行。一般刊物,由于资金不足、政府不满、编者不才或兴趣转移等原因,仅出1期就遭查禁的相当多。偶有超过5、6期的,已属不易。《文艺阵地》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支撑了6年,除了编者外争人和,内把文章质量关外,努力打造辩论平台,使刊物永处论争态势应是它能将读者牢牢吸引的原因之一。由它发起讨论的有文艺大众化问题,暴露与讽刺问题,文艺创作中的公式主义问题,报告文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暴露与讽刺的论争。这场从1938年4月开始,至1940年10结束的论争,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讨论之活跃,在现代小说批评界是空前的。除《文艺阵地》外,虽然《救亡日报》、《抗战文艺》、《读书月报》、《七月》、《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月刊》等报刊,也都是批评家们质疑驳难的重要阵地,但《文艺阵地》一再为论争提供话题和导火线,提供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讽刺文学的发源地、大本营的杂志,论争显然为它知名度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寿命的延长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讽刺文学就没有《文艺阵地》,讽刺文学造就了它的辉煌。
就讽刺文学而言,《文艺阵地》为其提供了一种得以健康生长的可能。王纲解纽是文学发育良好的保证,尤其是时评性极强的讽刺文学。长达八年的战时国统区,不存在一统的对文学的“强制”力量。国民党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共势力的成功渗透和商人的唯利是图,为文学提供了一个“多价成规”的环境,这里讽刺主将们的命运比《解放日报》中的要幸运得多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文艺阵地》的编者们充分利用这个环境,他们不但为抗战讽刺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富有回旋余地的文学空间,而且通过暴露与讽刺的文学论争,为讽刺文学穿上了一件合法外衣。当下的论者提及这场论争,发出的往往是充满了遗憾的感慨:论争纠正了抗战初期小说创作的盲目乐观,为推动创作沿着革命现实主义轨道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论争的纠结点始终是“暴露与讽刺是否有利于抗战”,也即小说的抗战功利性倾向,至于小说在艺术审美上的价值判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11] (P457-461)笔者以为,这种感慨看似中肯、面面俱到,其实其定下的论争目标,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是难以一一实现的。根据布迪厄的研究,“文学竞争的中心焦点是文学合法性的垄断,也就是权威话语的权力的垄断,包括说谁被允许自称‘作家’等,甚或说谁是作家和谁有权利谁是作家;或者随便怎么说,就是生产者或产品的许可权的垄断”,[12] (P271)换言之,亦即文学论争是为了实现对文学的垄断。这似乎有些残酷,但最终的发展结果确实如此,因为“占位空间的根本改变(文学或艺术革命)只能来自于组成位置空间的力量关系的转变,转变之所以可能,取决于一部分生产者的颠覆欲望和一部分(内部和外部的)公众的期待之间的契合,因而取决于知识场和权力场之间的关系变化。[12] (P281)以此为标准,这场论争,达成了批评界幽默和讽刺无损于抗战严肃性和必胜信心、《华威先生》出国并非“减自己的威风,展他人的志气”的共识,反驳了要把暴露性、讽刺性作品的内容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数量上也应有所控制的观点。[13] (P102-105)论争使讽刺文学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和推广,使它从此以后不必遮遮掩掩而是理直气壮地出现在国统区文坛上。这对讽刺作家而言,则是他们的劳动得到公众的承认;对出版人而言,则是他们刊物、书籍的发行更有保障;对政党而言,则分别意味着他们的统治思想观念(台上的)遭到指责(在野的)得以宣传或渗透。论争完成了讽刺文学合法性地位争取的任务,为40年代后期讽刺文学的成熟与繁荣打好了基础,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实乃功德圆满,何憾之有?后来人常常不满于讽刺文学虽在40年代风光无限而后却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孰不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土壤,岂能用预设的而不是它本身的生存条件来苛求它?在这个意义上,《文艺阵地》堪称讽刺文学的“摇篮”,没有它,40年代讽刺文学无法顺利来到人间,更谈不上茁壮成长。
40年代讽刺文学在《文艺阵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生成与发展的任务,《文艺阵地》亦成为抗战时期为数不多的大刊。文学与杂志的双赢,足以表明:杂志有生以来便代表一种智慧的活动。它从旧材料中编织新的故事,配合时代的潮流改写历史及传记,伸张已经被人遗忘的真理。它向世界上黑暗的角落,以及人类文化教育的若干隐处,投以搜寻的光亮,发起新的运动导引旧的运动,高揿警铃,使酣睡中的人们自梦中惊醒,扭转那些向后张望的头颅,使它目向前方。[14]
标签:文学论文; 茅盾论文; 文艺阵地论文; 文艺论文; 小说论文; 艺术论文; 华威先生论文; 作家论文; 张天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