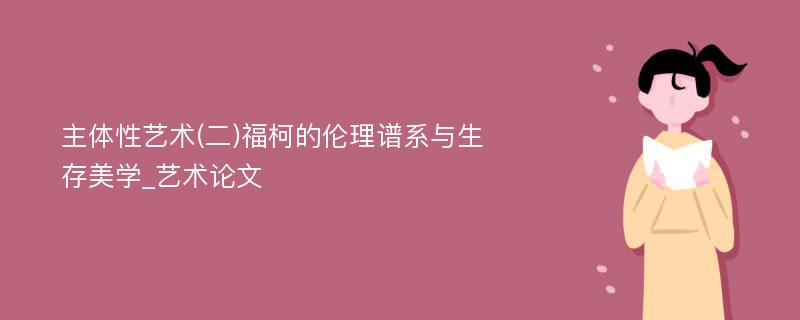
主体化的艺术(之二)——福柯的伦理谱系学与生存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之二论文,美学论文,伦理论文,主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生存艺术与强制道德
福柯称古代道德实践以及道德个体的自我塑造是“审美的”和“艺术的”,并用“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和“生存艺术”(arts of existence)来称古代伦理学,用“自我的艺术”(arts of the self)来称古代道德实践中个体的自我塑造。他强调“生存艺术”指的是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不仅为自己设立了行为规则,还力图改变自己,在自己的个体存在中改变自己,使自己的生活成为具有某种审美价值并符合某种风格标准的作品”。[6](P.10)
我们知道,现代性社会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真、善、美的分离,或认识领域、道德领域和审美领域的分离,福柯从审美和艺术经验的角度来回溯被现代人遗忘的古代道德经验其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种回溯让我们明白了与审美和艺术截然分离的现代道德并不是天然如此的,它是基督教以来的现代性实践的产物;其次,它让我们看到一种具有审美艺术性的道德实践如何造就了一种不同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一种自由的、独特的个体化主体生活;最后,福柯对古代道德实践的深入考察还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希腊式的真、善、美的统一。
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福柯说:“经常会有一种周期性的努力,要到古代中去发现一种未被基督教污染的思想形式。在这种有规律的对希腊的回归中,存在着某种怀乡的情绪,一种要还原到思想的原初形式的努力,希望在基督教以外来想象希腊世界。在16世纪,人们企图通过基督教重新发现某种希腊——基督教哲学。从黑格尔和谢林,这种努力又变成了要绕过基督教重新发现希腊哲学——我指的是早期黑格尔——在尼采那里也是如此。今天,对希腊的重新思考并不是要把希腊道德作为自我反思所必需的完美的道德,而是要表明,欧洲思想把希腊思想作为曾经存在的经验加以注意,而这种关注是完全自由的。”[2](P.115)
回到基督教之前的希腊,回到一种未被基督教污染的思想形式是为了我们的眼界不至于被后者所囚拘,一旦跳出被基督教污染的思想形式而站在希腊思想和希腊经验这个“他者”的地基上,我们便获得了一种对前者真正的看。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古代道德和现代道德之间的差异,看到了现代道德主体和古代道德主体的差异,看到了古代道德主体化实践和现代道德主体化实践的差异,此一差异让我们更深地理解了道德主体的历史和我们自己的道德现在。
不过,福柯并不认为古代道德和现代道德之间没有任何牵连,甚至在外观上大体一致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也为古代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做了准备。更重要的是,现代道德实践的根苗就潜藏在希腊道德的实践之中。在谈到希腊人道德实践中的个人风格塑造时,福柯说古希腊人“一方面在不懈地追索某种生存的风格,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把这种风格提供给他人,这就是古代道德的矛盾,而希腊人一开始就在这个矛盾上迷失了……所有的古代风俗对我来说似乎都是一个‘深刻的错误’。”[2](pp.110~112)
对福柯而言,古代道德向现代道德转化的根本标志是个人道德行为的普遍化,这在有关“风格”(style)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古希腊的道德实践中,“风格”本是指个人将自己造就成独特艺术品的方式,它有明确的个体性,然而,在古代对风格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中,风格逐渐变成了对道德行为的普遍要求与标准。“风格问题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与自我的关系的风格化,行为的风格化,与他人的关系的风格化。古代总是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描述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对不同领域的经验都是共同的。事实上,对这种风格的发现有可能会导致对主体的界定。在公元2世纪和3世纪的罗马帝国,人们开始讨论‘道德的风格’的统一性,而且把它同法典和真理联系起来。”[2](pp.110~111)
为了形成统一的道德风格,道德规范的普遍强制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在柏拉图的道德论述中,这种思想已很明显,只不过在当时的希腊实践中它还未落实为普遍强制的法规。将道德规范的普遍强制性落实为具体的法律是从早期基督教开始的,当个体塑造自我的艺术变成普遍的道德要求时,作为生存美学的希腊式道德实践就消失了。
我认为,没有大量的自我实践就不会有道德。这些自我实践可能与很多系统的限制性规范结构联系在一起,甚至当这套规范作为道德的本质而出现的时候这些自我实践可能会消减,但自我实践仍然是最重要、最活跃的道德关注点,一种反思会围绕着它们。自我实践采取一种自我艺术的形式,它相对独立于道德立法。可以肯定,基督教在道德反思中强化了法律原则和规范结构,尽管禁欲主义的实践继续看重自我的实践。[8](P.260)
在福柯看来,基督教将希腊式的道德规范变成一种强制性的道德法律是西方道德的不幸,因为“追寻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并且都必须适应的道德形态,这在我看来是灾难性的”。[2](P.120)随着基督教的道德“立法”,道德实践不再是个人对自我主体的自由创造,而成了一种社会强制性的有关道德主体的生产,这个主体就是千人一面的基督徒。
据福柯的考察,基督教道德立法以及现代主体千人一面的模铸之所以可能,与牧师权力(pastoral power)的发明和真理的追求紧密相关。福柯认为,希腊罗马的道德基础来自于对自己的关心,它表现为一句十分流行的希腊格言,即“看护自己”(epimeleia heautou)。在苏格拉底和塞内加等人的言谈著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关心自我、看护自己的激情。据福柯的分析,看护自己在希腊人那里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护,自己对自己的关切,是自己按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控制和塑造,是自己对自己实施权力并确立自己的权力,在此没有他人的强制,而在早期基督教那里出现了一种“牧师权力”,这种权力的主要特点不再是“看护自己”而是“看护他人”(epimeleia tonallon)。牧师作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者负有监管世人的责任,他看护他人是为了不让他人被魔鬼所诱惑和被自己的罪性所教唆。如此这般的牧师权力使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与自己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即人们不再自己看护自己而是把自己交托给牧师或他人来看护,这样一种关系就是福柯所谓的“管理”,一种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弥漫周遭的权力关系。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牧师是如何看护他人,他人又是如何在这种看护中失去自我创造的自由而被塑造成千人一面的基督徒的呢?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向了“求真意志”(the will to truth)。以福柯之见,将知识作为真理来追求最先是在基督教的“忏悔术”中达到高潮的。在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滋生出这样一种幻想:人有一种真相,它先在地隐藏在某处,可以通过坦白忏悔的技术而获得。而在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有权聆听别人坦白忏悔的人就是牧师,牧师是握有别人最隐秘的真实的人,因此他有权以真理的名义强制和管理别人,“看护别人”,并要求别人在对其真相的体认和认同中成为他自己。
福柯认为由基督教的忏悔术所强化的求真意志对西方历史是灾难性的。在福柯看来,人的先在真相从来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基督教先行预设或构造出来的人的真相,比如人有原罪,人之罪性就是潜藏在性实践中的欲望。所谓要忏悔者在忏悔中坦白自己的真相,不过就是引导每一个忏悔者认同基督教所构造的真相,将自己体认为“欲望的人”,进而按基督教的设计将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欲望的主体”。这样,牧师权力和求真意志的结合便为每一个人的主体化准备了一个共同的模子或原型,它的产品是清一色的基督徒。
在晚期的一次访谈中,福柯以笔记为例比较了古希腊人和基督徒在“认识自我”上的不同。福柯说古希腊人和基督徒都喜欢做笔记,并将其作为“认识自我”的方式,但古希腊人没有关于人的真相的意识,他们所谓的“认识自己”并不是要认识自己的什么先在真相,而是要反省和咀嚼自己已有的生活经历,以便为创造自己未来的生活提供参考,因此,他们做笔记“不是追求无法描绘的东西,不是揭示隐藏的东西,不是要说出未曾说出来的话。相反,它是要收集已经说过的话,重新汇集听到过或读到过的东西,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自身之构成。”[9](P.319)与之不同,基督徒做笔记是要记录自己内心的波动,以便发现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审查和考验自己,使自己认识那个真实的自己。对希腊人而言,没有一个先在的自己在那里等着每个人去发现,去认同,因而希腊人的自我塑造是自由的,没有原型的;对基督徒来说,成为主体的过程不是创造自己的问题,而是发现自己并认同这个自己的问题。基督教的这一主体化方式和信念影响深远,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运动中都能看到这一影响的痕迹。据此,福柯说牧师权力与求真意志的结合导致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基督教主体化方式,“这种权力方式直接应用于日常生活,它将个体归类,以他的个性为其标志,将他与自己的身份联系起来,将他必须认可和别人也必须在他身上认出来的一种真理的法则强加给他。这是一种使个体成为主体的权力样式。主体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以被控制和依赖的方式隶属于他人,以意识和自我——认知的方式而系于自己的身份。两种含义都暗示了一种使服从和使隶属的权力样式”。[5](P.212)
在福柯看来,构造现代主体的权力机制就是来源于牧师权力的现代“管理”权力,因此,要摆脱现代主体的主体化方式就必须反抗由牧师权力演变而来的现代“管理”权力,反抗“看护他人”和“被他人看护”的权力体系,回到“自己看护自己”的伦理关系和自己创造自己的“自我的艺术”;同时还要反抗求真意志,抛弃对所谓人的真理的迷信,抛弃对真实个性和不变本性的迷信,将自己从现有的自己身上分离出来,让自己成为自由创造的主体,从而成为另一个自己。
四、主体化历史的转折与自由
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有人间福柯为什么在研究道德问题时把注意力放在遥远的古代?福柯答曰:“我试图勾勒出它的谱系。谱系学意味着我的分析是从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出发的。”[8](P.262)福柯将他的道德研究称之为“伦理的谱系学”,他的谱系学所遵照的基本原则是研究“现在的历史”而非“过去的历史”,其意是说,他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去研究历史的,即他关注的是那个形成现在的历史和那个为现在提供参照的历史。
通过对道德主体化历史的谱系学追溯,福柯说明了我们作为道德主体的现在是怎么来的,说明了我们何以是这样一种道德主体而非那样一种道德主体。更重要的是福柯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历史处境与古希腊大体类似,即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一个“上帝死了”的时刻,一个基督教的普遍强制性正在失效的时刻,“有鉴于我们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可以在宗教中找到伦理学,也不要一种法律体系来介入我们道德的、个人的、私下的生活”[10](P.343),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与古希腊人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代人正处在一个有可能摆脱现代性“主体化”历史的时刻,一个有可能在古希腊人的“主体化”艺术实践中得到启发而别开人生的时刻。
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时刻而实现人生的转折?我们能否重建一种“生存的艺术”?福柯对此充满忧心。因为“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变成了只与客体、不与个人或生活有联系的东西。艺术成了一种专业化的东西,成了那些搞艺术的专家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人的生活不能成为艺术品呢?为什么灯和房子可以成为艺术品,而我们的生活反而不能呢?”[10](P.304)希腊的生存经验告诉我们,主要的艺术品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己,主要的艺术活动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所剩无几了。
古希腊罗马的“生存艺术”先后被早期基督教的牧师权力以及后来的教育、医药、和心理等类型的实践所阉割和驯化了,它被现代性社会放逐进了想象、梦幻、虚构、书本、画框、画廊、音乐厅和舞台,它作为一个被社会圈围起来的领域而不允许干涉任何实际的现实生活(它的反面是所谓不允许生活干涉艺术的艺术自主论),以至于我们习惯了艺术就是艺术,生活就是生活,它们是完全不同领域。福柯的研究向我们表明,生活与艺术的分离完全是现代性社会实践的结果,它只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而不是应当如此的普遍要求,因为在古希腊罗马世界,在那个“我们所失去的世界”中,生活就是艺术。
福柯的思考也许想唤起人们对一种消失了的生活和存在方式的记忆。作为一种存在方式,“艺术”不是什么特殊的文化类别,这是福柯生存美学的核心,因此,他对生存美学的研究并不是出于什么现代艺术学和美学的兴趣,而是要以此爆破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信念,使之看到另一种生活,一种被现代主体化的道德生活所遮蔽的道德生活。
令福柯欣慰的是,希腊式的艺术生活虽然在总体上被基督教之后的历史中断了,但它并没有消失。在波德莱尔等人的生活实践中,福柯看到一种使自己的存在具有个人审美风格和把自己的身体与生活变成艺术品的现代都市实践。“花花浪子的唯美主义,他把他的身体,他的行为,他的感受与激情,甚至他的生存都做成了一件艺术品。”[1](P.41)他使艺术不再幽闭于社会的其它文化之中或高飘在现实生活之上,而是让艺术成为生活本身,成为能直接发出生命光辉的现实样式。然而,现代社会中的波德莱尔们毕竟是少数,他们对艺术生存的选择还只是这个社会不起眼的动作,但福柯认为这些动作是重要的,它不仅守护着我们对一种消失了的生活的记忆,也使我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保持应有的怀疑。
经由伦理与道德的区分以及对古希腊美学化伦理实践的分析,福柯突出了人的“自由”,这纠正了他早期著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在福柯的思路上,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强制性的社会,在此,自由是艰难而隐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强制性社会,那里的自由是明显的。不过,福柯并不认为自由是人的先天禀赋,他认为自由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实践培育出来的能力,相比之下,古代社会的生存艺术更有利于人的自由能力的培育,这种艺术不仅能使我们成为自主的主体,还能为我们挑战和抵制权力结构提供动力。
福柯强调社会历史实践对形成主体自由的至关重要性,但他反对伦理研究中的社会决定论,他指出个人的伦理实践与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自我并不是给予我们的”,我们完全可以拒绝社会的强制,拒绝成为我们之所是,改变我们之所是。“人们不能把这样的想法强加于我,即权力是一个统治系统,它统治一切,不给自由留有任何余地。”(注:福柯:《自我呵护的伦理》,转引自巴里·司马特《论福柯著作中的性、伦理和政治主题》,陈永国译,见汪民安:编《福柯的面孔》,第331页。)福柯本人的座右铭是“不服管”,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不服管的一生。
对福柯来说,人生最重要的任务是成为一个自由自主的主体,一个自我塑造的主体,一个不驯服、不从众的主体,一个反抗权力的主体。不过,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自由自主的主体在塑造方式上是不同的。在一个“强制性的社会”中,反抗各种强制性规范乃是自我塑造的方式,接受这些规范便成为被社会强制所铸造的主体;而在一个“非强制性社会”,自觉地以某种规范来要求自己,自己给自己设界,抵抗欲望的奴役,便是自我塑造的方式,而放纵自己的欲望则使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在此,重要的是自由,是自己对自己的塑造,自己对自己的支配。“问题在于知道如何支配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它具有更优美的形式(在他人眼中,在自己眼中,在自己可能成为榜样的下一代人的眼中)。我力图重建的就是:自我实践的形成与发展,目的是为了把自己构造成自己生活之美的生产者。”[8](P.259)
值得一提的是,福柯不是一个浪漫的复古主义者,他强调以一种自由而批判的态度去回溯希腊伦理的实践,他肯定希腊伦理实践中自由、自主和自控的一面,但他厌恶这种实践中隐藏的等级制和对他人的无视,比如他对希腊男性同性恋之伦理问题的思考。福柯说男性同性恋之所以在古希腊是一个问题而异性恋则不是,原因在于古希腊伦理学的基础是男性奴隶制。在古希腊,妇女在性爱活动中的被动服从地位是规定好了的,因而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成年男子对少年的爱。在这种爱中,为了满足等级制的需要成年男子必须占居主动地位,但这引发了一个伦理难题:被置于被动地位的少年男子如何能成长为真正的男子汉?这一难题困扰着希腊的伦理思考。将自己塑造成男性社会的统治者和主人是希腊男人伦理追求的社会理想,这导致其伦理实践对男性自己的绝对关注而忽略他人。“我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把对方的肉体快乐考虑进去的行为和肉体的伦理学;别人的肉体快乐能不能融到我们的肉体快乐中,而无需顾及法律、婚姻、还有那些说不清的东西?”[9](P.300)
当“他人”问题进入福柯主体思考的视野的时候,死神正向他走来,这真是一种思想的遗憾。(注:福柯晚期写作突然中断于爱滋病带来的死亡。)对福柯来说,思考主体的问题决不是什么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试图培养和促进新型的主体性并改变自己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思考自己历史的努力能把思想从它所沉思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它能够思考别的事情。“他人”是福柯所思考到的别的事情吗?如果死神对他宽容一些,他还会在他的思考中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奇?
标签:艺术论文; 基督教论文; 谱系学论文; 福柯论文; 文化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古希腊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