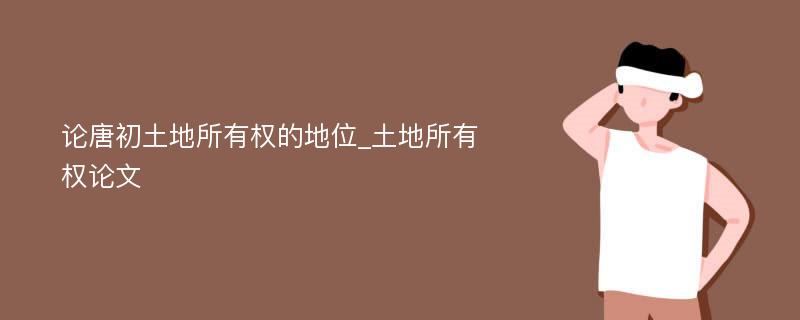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所有权论文,状况论文,土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地是中国封建帝制时期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实体,土地所有权状况是封建社会中最为主要的经济现实和利益体现,各种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土地所有权结构体现着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探讨中国封建帝制时期历代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及结构,有助于深化关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发展模式等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对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作一探讨。
需要在先说明的是,学界经常使用的土地所有权概念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土地所有权仅指土地的归属权,广义的土地所有权除归属权这一核心权利外,还包括土地的占有权、经营权、支配权、收益权、继承权等,这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产权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又称为产权,是一束权利或称为一个权利组。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概念也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土地仅指用于农业种植的耕地和可耕荒地,广义的土地除了耕地和可耕荒地外,还包括大面积的山林川泽、草原、荒地及城市、邑居、村落、道路等。由于土地概念的广狭二义,也就导致了农业概念的广狭二义,狭义的农业仅指粮食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业,广义的农业除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等。本文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农业概念的使用均注意其广义和狭义内涵,注意其间的联系和区别。
一
中国封建帝制时期的经济现实实质上是政治权益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而不具有纯粹经济的意义,这也是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社会中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特点。唐前期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实和经济结构,而是由唐前期一系列土地法规政策、土地制度所设计和规划的,这其中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国家政权对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规划和安排,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
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并非仅仅是均田令和均田制,而是更为周备、具体和较为复杂的,在律、令、格、式四种形式的法律条文和皇帝有关诏敕中均有相关内容,其中以《唐令·田令》最为详整(注:学界以往认为,《唐令·田令》主要有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1999年,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明抄本宋《天圣令》后10卷,其中第21卷《田令》共56条,前7条据《唐令·田令》旧文参考宋制修订,后49 条为宋代已不行用的《唐令·田令》原文,戴先生据以对《唐令·田令》进行了考证复原(《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2期,第36—50页)。杨际平先生进一步将《唐令·田令》56条的条文逐条排出,使人一目了然(《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第77—83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杨先生还指出,《唐令·田令》为“有唐一代之法,而不仅适用于某一时期”,其他传世文献对《田令》的征引记载,“总体而言,《通典·田制》所记最详,最接近唐田令原貌。《唐六典》次之,亦较接近唐田令原貌。其他各书《唐会要》、《资治通鉴》、两《唐书》、《册府元龟》等)所记与唐田令原貌皆有较大差距,有的还相差甚远”(第84—85页)。本文征引《唐令·田令》即据杨先生所排出的条文。),户婚律、杂律、户令、户部格、户部式及有关诏敕中也有明确的条文和规定。这些条文和规定相互联系和补充,由唐王朝以国家的名义制定颁布,共同构成了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也共同规划了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及结构。总的说来,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有关于土地国有权的规划确认,也有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规划确认,并从整体上安排了国有和私有两种土地所有权并存的状况及结构。
具体说来,唐王朝建立后,首先延续了古代社会以来,特别是战国授田制以来的传统,继承了“官山海”政策和山林川泽国有制度,将大面积的不可耕的山林川泽确立为国家所有。同时,又将隋末大乱之后无主的可耕荒地全部纳为国有,也继承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传统和制度。所有不可耕的山林川泽和无主可耕荒地,在法律上被确立为国有土地,这是国家所有的全部土地,是广义的国有土地。广义国有土地的一部分由政府有关军事、行政、事务部门等用于农业经营,进入到实际的经济生产和效益开发,完成了土地国有权的经济实现,被称为“官田”或“公田”,这是狭义的国有土地。广义的国有土地更具有主权和法权意义,“官田”或“公田”更具有土地国有权实现的实际的经济意义,是土地国有权的经济现实形态。
官田和公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职田、公廨田、屯田、牧场、牧田、驿封田、馆田、长行坊田、苑宥园池等,也都是由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所规划安排的。
职田又称职分田或职分官田,是按照京师及地方各级文武职事官的岗位授给的国有土地,在岗官员有占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以田租收入作为其禄米的补充,即白居易所云“国朝旧典,因品而授地,计田而出租”[1](卷495《问议百官职田》白居易对策)。职田制度颁行于武德元年,后来在贞观十一年和开元十年时两次停废,但都为时不长,武德元年的职田制度基本上成为一代之规制。职田的授给标准和细则见于《唐令·田令》第39条、40条、42条、43条和44条[2](P81—82),《通典》卷35《职田公廨田》也有详细记载。大体分为四个层次,具有明显的等级配置特点:第一,京师、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自一品十二顷到九品二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即百里内地少,欲于百里外给者,亦听之”。第二,州府、都护府、亲王府及京畿县官,自二品十二顷到九品二顷五十亩不等。第三,镇戍关津岳渎及在外监官,自五品五顷到九品一顷五十亩不等。第四,三卫、折冲府、亲王府及外军(即外府)的一般武官,自正四品三卫中郎将、上府折冲都尉六顷,到无品级的外军队副八十亩不等。后三个层次的职田“皆于领侧州县界内给”。法律严禁买卖职田,也不准互换,官员离任须移交下任,遵循“更代相付”原则,并实行了登录入白簿、黄籍的具体管理制度,即“内外文武官职田及公廨田,准式,州县每年六月三十日勘造白簿申省(尚书省),与诸司文解勘会,至十月三十日征收,给付本官”。“又准式,职田黄籍,每三年一造”[3](卷92《内外官职田》)。白簿登记职田公廨田四至、地段和租佃等情况,黄籍则登记租粮收付情况。有学者估计,“唐朝内外官的全部职田总数约在700万亩左右,约占唐朝全国垦田800万顷的1%,而官员人数按户计,则只占全国890多万户的2‰”[4](P144)。
公廨田是授给京师诸司和地方诸司的国有土地,由各政府部门自行经营,以田租收入作为本部门办公费用和官员的俸禄补充。公廨田制度颁行于开元初年,授给标准和细则见《唐令·田令》第37条、38条和43条,《通典》卷35《职田公廨田》也有记载。京师诸司自司农寺二十六顷到率更府二顷不等,地方诸司自大都督府四十顷到岳渎一顷不等,按照各级机构的规模和实际需要配置。对公廨田的具体管理与对职田的管理相同,上文已述。公廨田“总数约为24000顷,占全国800万顷耕地的3‰”[4](P147)。
唐前期“开军府以扞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屯田)”[5](《食货志》),屯田多为军屯。如武德初,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表请太原置屯田,以省馈运……岁收数千斛”[6](《窦威传》附《窦静传》)。武德六年十一月,“秦王世民复请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从之”[7](卷190)。贞观初,朔州刺史张俭“广营屯田,岁致谷十万斛,边粮益饶”[6](《张俭传》)。高宗、武后时期,西北边境驻军大量增加,军屯有了很大发展。如调露、永隆年间,河源军大使黑齿常之“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6](《黑齿常之传》)。玄宗开元时期,“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8](卷7《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员外郎”条),军屯形成了很大规模,尤以西北地区为盛,史载“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7](卷223)。具体经营管理上,国有屯田由尚书省工部总负责,并形成了隶属司农寺和隶属州镇诸军的两个具体系统。屯田的设置制度和规定详见《唐令·田令》第45条至56条,《通典》卷2 《食货二·屯田》有简要记载,兹不具引。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国有屯田约在300万亩至500万亩[4](P121)左右。
牧场,唐前期有著名的西北国有牧场,将大片的草场川泽用于国有畜牧业经营。太宗贞观初年,先设于秦、渭、原、兰四州,高宗麟德年间以后又扩充到盐、夏、陇、岐、邠、泾、宁、岚等州,由中央的太仆寺总管,设牧监、马坊等机构具体负责,“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马)坊岐、邠、泾、宁间,地广千里”[5](《兵志》),幅员相当辽阔。牧田又称监牧屯田,是国有牧场附近的国有屯田。史载八马坊,有“营田(屯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析置十屯。密迩农家,悦来租垦……岁中收贮二万五千石”[9](卷361 郄昂《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牧田的顷亩数也较为可观。
驿封田也称驿田,是按照各交通驿站马、驴的头数而授给的公田,授给标准见《唐令·田令》第41条,云:“诸驿封田皆随近给。每马一匹给地四十亩,驴一头给地二十亩。若驿侧有牧田处,匹别各减五亩。其传送马,每一匹给田二十亩。”[2](P82)李锦绣先生估计驿封田的数量在1100顷以上,并征引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指出与驿封田性质相同的还有馆田和长行坊田,分别为馆驿和长行坊等交通机构而授给,亩数不多,但设置普遍[10](P696—702)。
国有苑囿园池面积很大,主要供皇帝、皇室和贵族、官僚们游玩观赏,其中也有一部分土地用于农业经营,最高主管部门是中央司农寺,具体负责部门有上林署以及司竹监、温泉汤监、京都苑总监、京都苑四面监、诸屯监、九成宫总监、太和宫(翠微宫)农圃监、玉山宫农圃监、九成宫农圃监等,各有明确职掌。上林署“掌苑囿园池之事……凡植果树蔬,以供朝会祭祀,其尚食所进,及诸司常料,季冬藏冰,皆主之”。京都苑总监“掌宫苑内馆园池之事……凡禽鱼果木,皆总而司之”,京都苑四面监“掌所管面苑内宫馆园池,与其种植修葺之事”[8](《司农寺》)。京苑总监和四面监管理的京城禁苑“东距浐,北枕渭,西包汉长安城,南接都城。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二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11](卷1《西京》)。东都苑总监和四面监管理的东都苑,“东抵宫城,西至孝水,北背邙阜,南拒非山,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周一百二十六里,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垣高一丈九尺”[11](卷5《东京》)。司竹监在京畿户县、周至县和怀州府河内县,“掌植养园竹……岁终,以竹功之多少为考课”。诸屯监指的是隶属司农寺系统的基层屯田机构,分布广泛,“各掌其屯稼穑……凡每年定课有差”。九成宫在凤翔府麟游县,总监“掌检校宫树,供进炼饵之事”[8](《司农寺》)。温泉汤监“掌汤池宫禁之事……凡近汤之地,润泽所及,瓜果之属,先时而育者,必为之园畦,而课其树艺,成熟则苞匦而进之,以荐陵庙”[8](卷19《司农寺》)。著名的温泉汤监有京畿新丰温泉宫(华清宫)、蓝田石门汤、眉县凤凰汤、同州北山汤,河南府有陆浑汤,汝州有广成汤等。另外,隶属于东宫的有东宫园苑,由太子家令寺典仓暑具体管理,“凡诸园圃树艺者,皆受令焉。每月籍其出纳之数,以上于寺,岁终则审詹事府”[8](卷27《家令寺》)。
官田和公田的具体形态还有烽燧田、宴设田、城田、亭田等,面积大小不等,设置比较灵活,许多学者已征引有关吐鲁番出土文书加以论证,兹不详述。总之,官田和公田的具体形态多样,都是唐王朝根据统治需要而规划配置或准许经营的,是唐前期土地国有权在农业领域的经济现实形态,共同构成了国有农业系统。官田和公田的规划经营以国家政权为基础,以相关政策制度为保障,促成了土地国有权的充分的和优先的实现。官田和公田的形态多样及其巨额顷亩,也反映和体现了唐前期国有农业经济的规模以及它在整个农业经济中的地位。
二
对于隋末大乱之后所有权仍然明确的私有的耕地和可耕荒地,唐王朝予以明确承认。唐高祖称帝建唐伊始,立即颁布《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规定“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身往江都,家口在此,不预义军者,所有田宅,并勿追收”[12](卷114武德元年七月《隋代公卿不预义军者田宅并勿追收诏》),以诏令形式确认和保护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户的私有土地和房屋财产,对现实的土地所有状况予以法律承认。不过,这些被承认的私有土地要纳入到均田制的制度范畴之中。均田制颁行于武德七年,是对社会各阶层人户土地所有和占有的最高数量进行限额控制,并对实际所有和占有的数量进行调节管理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在承认现实土地所有状况,即承认社会各阶层人户原有私有土地的基础上,还将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用于给授,从而在总量上将人户原有私有土地和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搭配起来进行配给和确认。学界研究表明,《唐令·田令》第2条所云“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以及《白氏六帖事类集》卷23《给授田第十六》引授田令所云“先有永业者,则通其众口分数也”,其含义是唐政府在推行均田制时,承认人户原有的私有土地,但又必须将这一部分私有土地按照均田制的规定登记入人户户籍之中,将它纳入到均田制的范畴之中。这样,可能会出现几种具体情况:第一是均田户原有私有土地和均田制所规定的该户“应受田”数额正好相同,则只须按规定登记入户籍即可。第二是超额者,除按规定登记满额该户“应受田”外,超额部分要由政府收归国有。第三是不足者或者原先根本没有私有土地者,则需授给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或者全部国有可耕荒地予以补足或授足。《唐令·田令》第2条和第11条所云实施授田时“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就是针对以上二、三种情况的明文规定。这种规定虽是针对贵族、官僚户的授田而制定,实际上适用于均田制的全部授田。武建国先生指出:“将人户已经占有的土地,依照均田制所规定的款式分类登记于户籍之上;对无地或少地的人户,由国家直接授予一定数量的土地,同时依田制登记于户籍上,都是均田制土地授受的实施,或者说都是均田制的实施。”[13](P55)当然,以上只是法令政策所设计的方案,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文书已证明唐代均田户的实际授田普遍达不到制度规定的数额,出现“已受田”与“应受田”数额上的不小差距,因而对超额土地“有剩追收”的现实执行可能十分少有,迄今亦未见有关文献和出土文书资料,学界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实同具文,且超额者绝大多数当为统治阶级上层人户,也就不可能认真实行。但是,大量出土文书也实证了均田制的切实推行[14](P613),以及均田制将原有私有土地和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一同纳入到制度范畴内加以规划和分配的史实。
均田制又是一种典型的等级(身份等级、地位等级、权力等级)授田制,体现了唐王朝对土地加以等级配置调控的政策。均田制对于贵族、官僚户和民户(农户、僧尼、道士、女冠、工商户、官户、杂户等)的授田标准(最高授给数额)规定得相差很大,并有明显区别。对贵族、官僚户的授田只名以“永业田”,具体授给标准见《唐令·田令》第6条、第7条、第9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7条、第23条。自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到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按照品级授给。规定贵族、官僚户的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官人永业田及赐田欲卖及贴赁、质者,不在禁限”,一经授予和确认,便有永久的继承权,还可以买卖、贴赁和抵押,私有权十分明确。
对于民户的授田则复杂细致得多,具体授给规定见《唐令·田令》第2条至第5条以及第21条至第36条。分析起来,又区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况:(1)对民户的主体——广大个体农户以及工商业户,授田区分为“永业田”和“口分田”两类。规定:“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诸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授者,减宽乡口分之半”;“诸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授给广大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在性质上有明显区别:他们的“永业田”同贵族、官僚户的“永业田”一样,“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2](P353),同样有明确的私有权。《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也记载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的“世业之田(永业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他们的“口分田”,在非“卖充(住)宅及碾硙、邸店之类,狭乡乐迁就宽者”情况下,“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15](卷12《户婚律》卖口分田条及疏议),在入老、身死之后要归还政府,另行他授,即“口分(田),则收入官,更以给人”[6](《食货志上》),“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共给授”[15](卷13《户婚律》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疏议引《田令》),广大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仅有法定时间内的占有权、经营权而无所有权,所有权属于国家。(2)对僧尼、道士、女冠等的授田,规定:“诸道士、女冠受老子《道德经》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受具戒者,各准此。”没有“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区分,实际上这类授田“不是授给僧尼、道士、女冠本身或其家庭,而是授给寺观”[2](P87)。授田虽按僧尼、道士、女冠的人数授给,但僧尼、道士、女冠们并不拥有对所授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其所有权和占有权是属于寺观的,是寺观私有的土地。(3)对官户、官奴等贱户的授田,规定:“诸官户受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其在牧官户、奴,并于牧所各给田十亩。既配城镇者,亦于配所准在牧官户、奴例。”这其中又有区别,对一般官户只授予“口分田”,而且要减半;对在国有牧场和城镇服役的官户、官奴,只给予耕田十亩。由于官户、官奴是因犯谋反和谋大逆之罪而被籍没入官的政府奴隶,所以对他们的任何“授田”只是为了使他们能从事耕织以维持基本的衣食需要,来保障他们能够为政府服役。连人身都属于政府所有的奴隶,自然谈不上对土地有任何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不过,由于均田民户绝大部分是广大个体农户及工商业户,所以就均田民户土地的主体而言,均田制实际上规划安排了一个私有和国有并存的二元所有权结构,具有国有、私有的二重性。
从以上阐述可以看出,唐王朝通过均田制这一正式制度安排,将人户原有私田和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搭配起来,规划安排了社会各阶层的等级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其中确立了贵族、官僚户的“永业田”私有权,也确立了广大均田农户及工商业户的“永业田”私有权和“口分田”占有权、经营权等。也可以说,均田制实际上是按照社会等级来规划安排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的,不同社会等级的土地所有权和占有权是相差悬殊的。整体考察,均田制对贵族、官僚户和民户土地的总规划也是一个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所有权结构。另外,唐前期实行特定条件下土地可以买卖的政策,《唐令·田令》第19条规定:“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使“买田”成为土地私有和占有的又一种形态。当然,土地买卖要合法,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并经过政府的具体管理。《唐令·田令》第20条云:“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乡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者,财没不追,地还本主。”凡合法“买田”,也要登记入户籍,计算在“应受田”的总数里,也纳入到均田制范畴之内,这在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文书中多有实证。
除均田制确立了绝大部分均田户“永业田”的私有权和“口分田”的占有权、经营权外,赐田制也确立了一部分土地私有权。赐田是皇帝按照其意愿和需要而赐给贵族、官僚们的国有耕地或荒地,不在均田制范畴之内,实际上也是一种授田制。如高祖初平长安,赐裴寂“良田千顷”[6](《裴寂传》),数目惊人。武德二年,李袭获“赐良田五十顷”[6](《李勣传》)。唐太宗贞观时,李袭誉在京城附近“有赐田十顷”,“河内有赐桑千树”[6](《李袭志传》附《李袭誉传》)。 元结的曾祖元仁基从太宗征辽东,“以功赐宜君田二十顷”[5](《元结传》)。唐代尊崇佛道,太宗、高宗、武则天对寺观多有赐田,数额颇大。赐田制直接将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唐令·田令》第10条虽规定“诸赐人田,非指的处所者,不得于狭乡给”,但实际执行不会严格,如上述李袭誉的十顷赐田就是在京城附近,而京畿地区是名符其实的狭乡。从相关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赐田也登记入户籍中,也要向政府交纳地税,但子孙能够继承,而且“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15](卷12《户婚律》卖口分田条疏议),土地私有权也是明确的。
唐前期为了鼓励生产,在均田制所规定的应受田之外,还实行了宽乡占田不限的政策,鼓励在宽乡通过开垦荒地而多占土地,一部分国有可耕荒地供公私垦辟。法律规定垦荒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称为“请授”,即所谓“计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仍须申牒立案,不申请而占者,从‘应言上不言上’之罪”[15](卷13《户婚律》占田过限条疏议)。这就是请田垦田制度。履行此制所垦得的土地是合法的,国家承认其私有权。这些土地不入户籍,另立青苗簿[16](P136),按所种植顷亩交纳地税[8](卷3《尚书户部》仓部郎中员外郎职掌条)。这样,通过请田垦田制便确认了均田制范畴以外的一部分合法私有土地。有关史籍记载了某些人通过合法垦田拥有了大量土地,并成为富豪。如太原府祁县人王方翼,“躬率佣保,肆勤给养,垦山出田,燎松鬻墨,一年而良畴千亩,二年而厦屋百间,三年则日举寿觞,厌珍膳矣”[9](卷228张说《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
需要继续加以申论和阐明的是,无论是均田户的“永业田”私有权和“口分田”占有权,还是赐田、合法买田及垦田的私有权,都是不完全的和有条件的。这种不完全性和有条件性,一是表现在唐王朝在法律上承认其权益的同时又加以具体的限制,如《唐令·田令》规定贵族、官僚户永业田不得“舍施及卖易与寺观”,广大个体农户和工商业户的永业田同样不得“舍施及卖易与寺观”,亦“不得贴赁及质”,他们的永业田在非家贫无以供葬,口分田在非卖充住宅、碾硙、邸店及自狭乡乐迁宽乡等情况下也不得出卖[15](卷12《户婚律》卖口分田条疏议),否则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赐田出于皇帝的意愿和需要,买田和请田也必须依法进行并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同意和具体管理。二是贵族、官僚户和民户的永业田、口分田和买田、赐田都要纳入到均田制的制度范畴之内,要登记入户籍,并因获得了政府的规划授给和法律确认而须向政府交纳租调赋税和服役以尽义务。合法垦田虽不登记入户籍,但另行登记入青苗簿。青苗簿同样由政府编制,也同样是被纳入制度范畴之内的,只不过纳入了另一项制度范畴之内罢了,同样因获得了政府的同意和法律承认而须向政府交纳地税以尽义务。都有一个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唐王朝正是通过不断调整均田土地还授、不断编制户籍和青苗簿、不断征收赋税和征发劳役,来实际表明贵族、官僚户和民户的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是以政府的规划授予和法律确认作为前提的,都不是脱离了国家政权干预控制的纯粹的私有权和占有权。这种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的不完全性和有条件性,又被称为不纯粹性,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土地私有权益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经典论述,为学界熟知,不必具引。对前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的不纯粹性要认识清楚,但也不应一味强调这种不纯粹性,并据以根本否认前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的存在。因为,前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的不纯粹性,是与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的纯粹性相比较而言的,也就是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还没有发展到后来资本主义时代的纯粹的程度,还受着国家和政府的相当程度的干预和影响,具有国家既承认保护又加以限制操控的特征。如果不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体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发,而仅从一种历史发展进程前后比较所得出的相对特征出发去认识问题,势必会使认识走向绝对并进而导致片面和错误,也不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不是将问题放在历史发展之中来辩证地研究。总之,在研究前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时,既要认识到它与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在权益是否纯粹方面的差异,也要把它看作一个历史问题,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不应一味地以资本主义时代私人土地私有权的纯粹性来衡量和苛求。具体到本文探讨的唐前期贵族、官僚户和民户的土地私有权和占有权问题,则既要看到它带有明显的政府政策和制度的烙印,从而是不纯粹的,也要看到它又是明之于国家法律并受政府保护的,在法权和经营权方面都是有切实保障的,也是现实地存在着并有实际经济意义的,是唐前期农业迅猛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
通过以上阐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就广义的土地而言,还是就狭义的土地而言,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及结构。由于隋炀帝暴政及所引发的隋末社会大动乱,使“区宇分离,百姓凋残,弊于兵革,田亩荒废,饥馑荐臻”[12](卷111武德六年《劝农诏》)。当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7](《杨玄感传》);“下民困扰,各靡聊生,丧乱之余,百不存一……江淮之间,爰及岭外,涂路悬阻,土旷民稀,流寓者多”[9](卷2高祖《罢差科徭役诏》),社会经济遭受惨重破坏,一片凋敝。唐太宗“贞观之初,率土荒俭”[3](卷83《租税上》所载马周疏文)。贞观六年时,“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6](《魏征传》),广大中原地区仍然十分荒凉残破。当时,死于战乱及灾荒的人也不计其数,户口大量减少。武德六年,高祖诏文说:“隋末丧乱,豺狼竞逐,率土之众,百不存一。”[9](卷2《申禁差科诏》)贞观十一年,马周说:“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3](卷83《租税上》)贞观十三年时,河南、河北两道的在籍户数分别只有隋代大业五年的11%和15%[18](P263)。高宗显庆年间,中原许州、汝州一带仍然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9](卷7《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所以,即使仅就狭义土地而言,唐前期的国有土地也占据着土地所有权状况和结构的主导地位,如果就广义的土地而言,就更是这样的一种局面。因此,确切地说,唐前期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和结构是以国有土地占主导的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结构。同时,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故可进一步称之为“官私二元、以官为主、形态多样”的土地所有权状况和结构。把唐代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恐怕都是只看到并过分强调了土地所有权状况和结构的一个方面,没有作全面和细致的考察,因而都失之片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