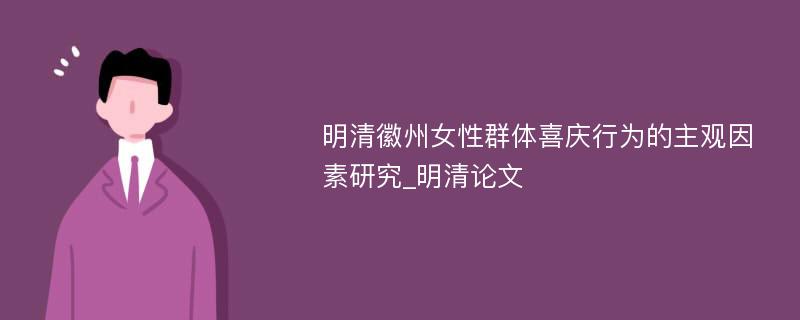
明清徽州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之主体性因素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节烈论文,体性论文,明清论文,之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08)05-0064-09
针对明清时期几近宗教化的贞节观念,不少学者试图揭示其背后的原因。杜芳琴认为,元代是理学初渐并从士大夫阶层向民间普及的关键时代。[1] 安碧莲认为,明代女教书的普及与宣扬节烈,对促进贞节观的深化有相当的影响,但明廷旌表贞节制度上的奖励才是主要因素。[2] 费丝言则从区辨“现实”(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记载”(被记录的贞节烈女)两个层次切入,析论这些贞节烈女成为文献记载的各个管道与运作过程,亦即贞节烈女的“生产机制”,及此一社会机制如何影响时代的社会心态与集体实践。[3] 张彬村则认为明清时代的寡妇普遍会守节,是一种理性的选择(rational choice),守节成为此一时期符合寡妇利益的最适选择。[4]
明清时期,徽州节烈现象与其他地方相比,尤为突出,若赵吉士所说,“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5]《卷二·镜中寄·孝》 在徽州府的地方志中,《列女传》占的篇幅特别大。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全书共70卷,其中《列女》多达14卷6册,占全书总卷数的1/5。民国《歙县志》中的人物志共9卷,烈女传竟有4卷,几乎占到一半。清代佘华瑞撰写的《岩镇志草》载,仅仅岩镇节烈妇女就有216位。据《休宁县志》记载,清代仅安徽休宁县就有2200多个“节烈”妇女。建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位于歙县城南街应公井巷口的“孝贞节烈坊”就集中表彰了“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而歙县一邑受到旌表与未受旌表的列女达8606人之多。[6]
《论明清徽州妇女节烈风气的综合动因》[7] 和《明清徽州妇女节烈风气探讨》[8] 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导致明清徽州妇女崇尚节烈的原因,其中包括封建旌表制度的推动、宋明理学的影响、宗法制度与传统习俗的束缚、当地社会经济特征以及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等等。而《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观的成因》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封建制度的极力倡导、强大的宗法势力、程朱理学的熏陶、徽商的极力推崇等方面,分析论证了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观的成因。[9] 但上述原因都属于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外在因素。
事实上,在明清徽州贞节妇女群体性节烈行为的表象之下,其实隐含了暧昧、复杂的动机——既有基于纯粹的道德理想,也有源于留名传世的愿望;既有对丈夫感情的执着,也包含了对不能承受的艰辛生活的逃避;既有自觉的伦理道德的实践,也有非理性的盲从和附和……我们在考察明清徽州大量妇女的群体性节烈实践时,当然要考察其外在驱动因素,但也必然要考察她们的主体性内在因素,毕竟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发挥作用的。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的主体性主要表现在对贞节伦理的守护、对家庭责任的担当、对困窘生活的逃避以及留名传世的愿望等几个方面。
一、对贞节伦理的守护
对传统社会的妇女而言,贞节伦理最初的含义就是保持身体的贞洁,也就是守卫住身体不受侵犯,这仅仅是一种自卫的行为方式。但在中国传统的父系社会中,女性的存在遵从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原则,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所以女性的守身并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守,一旦牵涉到为谁而守,也就是涉及到人伦关系时,贞节就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更是一种道德实践。贞节作为一种道德实践,其道德价值来源于其守身涉及的对象,即基于婚姻和性而发生联系的丈夫。因此,女性守身要守住的,不只是妇女身体上的贞操,也包含了对于婚姻的节操。这样,对贞节伦理的坚守,其道德意涵就重点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于身体贞洁的坚守,二是对于婚姻关系的信守。
在贞节崇拜的年代,女性特别注重对自己身体贞洁的保持,不受外界的各种诱惑,甚至把身体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为了自己的身体和名誉不受玷污,她们采取各种方式加以保护。
有的杜绝与男性的一切接触。
石氏,名妙容,冯曜妻,年十八守节,见十岁小郎皆趋避,寿七十五。[10]《卷十六·列女》
江满煜妻程氏……年三十,夫故,孤八龄,耐贫抚立,冰操肃然,男子与语不应……[11]《卷五十五·人物十七·列女》
有的甚至把自己封闭在户内,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郑玿若妻黄氏,于归时,舅病革,夫亦病,仓卒成礼,越月舅殂,夫继之,氏泣奠尽礼,自是登楼守志,足不履地,虽孩童莫觏其面。[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这些居于室内的妇女,有的居于楼上,吃喝都是用绳子吊上去,用具坏了也不让人修理。
槐塘贞女程,幼许字堨田蒋氏子,未婚而蒋氏子殁。女闻讣临丧哭奠,归即自经,母救得解。屡劝之,对曰:“母欲儿姑缓死,必坐卧小楼,悬绳以通食饮,然后可。”母从之,居楼中,足不履地,手织絍,以赡饔飧。二十八年中,惟闻姑病,一往视汤药,姑病愈即返。死之日,戚属登其楼,见几席宁缺陷而不令修也,所坐具宁倾欹而不令整也。无不悽然已,无不悚然起敬者。于是,乡先达衣冠张盖,鼓乐亲送其柩于蒋,蒋亦率绅士出里门数里外迎之归,与夫合葬焉。已复与继濂未婚妻,同奉主入节烈祠,有司春秋崇祀。[13]《二贞女传》
甚至有的连灾难来临的时候,也不越门户半步。
何氏,大畈汪喜妻,年二十一寡,无子守节,年六十三,家罹火灾,不出户而死。[10]《卷十六·列女》
在徽州府志的记载中,水、火等灾害频仍,在灾害危及生命时,许多妇女因信守礼教教条,怕衣不蔽体遭人耻笑,怕违背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法,在男性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时,拒绝接受而最终殒命。
洪德勋妻黄氏,潢川光斗女,名春女,十八岁适车田,阅二年母殁,鲜兄弟,哭泣尽哀,既殡奠墓恸极,烛烬燃及衣,幼妹呼救,救者至,欲裸之,女拒谢,遂焚死墓侧,怀有娠矣,人益哀之,时光绪六年十月十二日。[11]《卷六十一·人物十七·列女》
王氏,名京娥,龙池人,适潢川州佐黄声谐。顺治十八年,草寇劫掠,王扶姑出避,失姑所在,寻至渡口,水涨桥危,避嫌不受男子之救,溺水死。[10]《卷十六·列女》
寡妇的生活本来就异常艰苦,身体患病是常有的事。有些妇女身体发生疾病,往往能拖则拖,特别是当她们身体的某些隐秘部位发病,更因害怕自己在男人面前裸露,而拒绝接受治疗。元明善《节妇马氏传》载:“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明清徽州有大量妇女生病拒不接受医疗而死的。“汪氏,临河人,夫卒,氏年二十三,苦抚二孤,作女红易粟,及病笃,子跪请医,氏曰:‘子则孝矣,第吾五十余年,未尝一面外人,何可授医以手?’不药而卒,年七十九。”[14]《卷十一·人物志·列女》 蒋贞女,许字槐塘程德濂,未嫁,夫客长沙,廿年不通音问,在她得病期间,“父延医,欲诊其脉,则扃手被内,曰:‘儿未适人,虽父不可执此脉。’”[12]《卷十三·列女》
虽然先秦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性别隔离礼仪。“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15]《孟子·离娄上》 《礼记》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成物安。[15]《礼记·郊特牲》 主张男女有别的目的是防止男女婚外性关系的发生,确保父与子血统关系的纯正,以巩固父权制和父系继承制。《礼记》把“男女隔离”的思想具体化为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日常行为规范:“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15]《礼记·曲礼》 这表明性别隔离礼仪已经深入家庭内部。但是,“男女授受不亲”只是“礼”,而不是“法”。违背了“礼”,只是会受到人们的道德舆论的责备,而不是受“法”的惩罚。守“礼”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不会被强制执行。另外,这种性别隔离礼仪施行于士大夫之家,并不适用于普通百姓。所以,上述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杜绝与一切男子的接触,是主体性自觉行为。
在身体和名誉可能会遭到侵犯的情况下,她们采用各种手段以自防,甚至不惜献出生命。
黄正笏妻程氏,槐塘人,幼娴礼节,正笏死,引刀服毒吞金自缢皆为人救,或曰:“矢志守节,古人行之,何以死为?”曰:“有子守为得,无子死为宜,吾见执节者多为浮言惑,纵死难自白矣!”遂纫衣至棺所,绝粒八日死。[16]《卷八·烈妇》
妇女夫亡之后,其是否能够守贞便成为关注的焦点,人们往往会捕风捉影的猜测、议论寡妇的日常生活行为,无事生非。如果是自己的名誉受到污蔑,或者是夫死之后,惧怕谣言会玷污其名声,她们往往也以生命为代价来表明清白或使声名免遭污辱。一些出生于官宦世家或名门望族的女子把自己的贞节与家族门风联系起来。
张宠锡妻康氏,父仕荆州卫,氏归时,翁卒于乐至县任,后宠锡又客死山东,二子皆死,氏数千里扶舅姑柩归里,门祚已绝,针黹自活,或谓曰:“绝嗣家何所冀?”氏曰:“吾父吾舅皆宦,夫亦贡士,吾不敢贻羞门户耳!”[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不仅仅是生前,甚至在死后,她们也不愿让人接近其身体,因此大多在自尽前周身密缝。
洪枚效妻程氏……绝粒十余日,犹扶病拜翁,上下衣皆自缝缀,语侍者:“即以此殓,毋令见体。”绝粒凡二十日殁。[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虽然孟子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符合礼制,但是《孟子》又有这样的话:“(淳于髡)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15]《孟子·离娄上》 这说明“男女授受不亲”是一种常态之下的一般男女相处原则,在非常态下可以变通,并且一般只适合上层家庭。但在明清时期的徽州,这种理念后来变成某些妇女忠实的信条。她们把身体的贞洁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杜绝与男性的一切接触,把自己封闭在一室之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不越门户半步,即使有男子及时援助,也坚决拒绝;如果身体患病,也拒绝治疗而坐以待毙;在身体和名誉可能会遭到污辱的情况下,她们更是不惜献出生命。不仅仅是生前对身体防护备至,甚至对在死后的遗体也顾虑重重,深怕暴露或让男子接近。她们的贞洁观念达到了高度的宗教化和畸形化的程度。
对于已经成婚的女性来说,其守节与殉烈行为,实质上是对于婚约的执守与坚持。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下,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并不随着死亡而自然消灭。相对于天合的亲属血缘关系,婚姻意味着一种人合的信约,其效力并不以死亡为终结。即使其中一方已经亡故,另一方仍有信守的义务。在对初婚信约的重视之下,个人对于婚约的执守成为一种重要的节操。于是,初婚对象死亡之后不再嫁娶的行为,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实践。在中国传统父系社会里,由于男性负有继嗣之责,使得在妻亡无嗣的状况下,男子有再娶的责任,否则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孝。《徽州府志》载:“义夫者,轻财仗义,或周人之急,或济人之危,而不为己私者也。而世人多以不再娶者为义夫,然亦未见其人。永乐间,歙西南有吴斯庸者,年甫三十,丧其妻徐氏,子女俱幼,人劝其再娶,斯庸曰:‘吾闻妇人不再醮者谓之节妇,吾独不能为义夫乎?矧吾有子矣。伯奇之往事不可鉴乎?’遂不娶终其身。虽然,是皆有子者,故为难得,若无子不娶,绝先祖嗣,乃不孝之大者,何义夫之有?”[17]《卷十二》 因此对于婚姻的执守之义,虽然理念上是夫妻之间相互的义务,但实质上却只是女性单方面的实践,妇女从一而终,将对婚姻的信守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实践。
她们对于婚姻关系的信守往往是非常执着的,采用各种方式杜绝、抵抗家人或外人的逼嫁或诱嫁。有些丈夫病危时,出于对妻子未来生活的考虑,嘱其另适,但妻子则坚守从一而终的信念。还有许多舅姑、父母怜惜媳妇、女儿年少守寡,劝其改适,但她们矢志不二,守节或殉烈。如:
黄光桁妻汪氏,南源汪细红女,年十七归毕源,家贫内佐,得舅姑欢,二十五居舅丧,夫以毁继没,氏恸几绝,念姑老二孤幼,勤女红给养,姑怜其苦,命他适,弗从,命招婿,弗从,或强之,辄毁容誓以死,遇强暴,厉色叱之,族人加敬,姑没,哀毁成疾没。年四十五。[11]《卷五十五·人物十七·列女》
徽州的婚礼习俗包含了传统的“六礼”,迎娶使婚姻最终成立。世俗则普遍将妇女从一而终、夫死不嫁推广到纳采受聘,凡“一报昏书受聘财,而上以之听民讼,下以之定姻好,不必亲迎而夫妇之分定”,故“一纳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18]《卷八·贞女辨下》 许多节烈妇女把对婚姻关系的坚守上溯至未婚许字的室女时期、入夫家以待年的未婚时期。
方世炅未婚妻叶氏,方,伏塘坑人,氏,蓝田人,年十一许字于方,即以是岁适方门待年,世炅幼贾金陵,病归,氏侍汤药必依姑嫜,不亲授受,夫病革,侍者不敢近,氏禀舅姑曰:“病已如此,儿不能不亲扶持。”月余夫殁,哀毁不欲生,时年方十四岁,嗣舅姑殁,丧祭尽礼,告于宗族,为夫立继,守贞至八十一岁而殁。[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她们都在并未成婚之时,拒不改字,因为她们认为一旦许字夫家,夫妻名分已定。
也有众多的节烈妇女甚至把婚姻关系延伸至夫死之后。
汪栖岷聘妻洪氏,汪,上溪口人,氏,回溪人,名良玉,未嫁夫殁,欲往执丧,以父客外未禀命,恸哭,目为之盲。媒来议他适,更大恸呕血,以殉夫意告二叔,以手外挥,示与汪合葬意,遂卒。[12]《卷十三之二·人物志·列女》
许多寡妇认为,丈夫亡故,在无子无公婆的情况下,她们的存在已经失去了意义,所以众多的寡妇选择了从夫地下。
“使夫有父母,我当代夫养之;使夫有子息,吾当为夫抚之。今上无舅姑,下无子息,自思惟一死以从夫于九泉耳。”(九叙孺人程氏殉烈时语)[16]《卷四》
“父曩时闺教云何,今女上无无舅姑,下无子息,惟此身与婿为存亡,安知其它。苐恐异日,过伤母心,父宜引大义以解谕之耳。女志决矣,必强我食,或死缳与刃,而亲体是残,非女志也。伯祖姆尚遗孤女,故得称未亡人,今某茕茕靡遗,其将何称”(高振孺人郑氏语)[16]《卷四》
有的把殉烈当作一种终极目标,在完成应尽的家庭义务后从夫地下。
吴念祖妻黄氏……于归三日而夫病……姑卒,尽哀成礼以葬,乃喟然曰:“吾可地下见夫矣!”跌坐三日而后逝。[14]《卷十一·人物志·列女》
有的即使上有老下有小,她们也可能把从夫地下这种婚姻关系的地下延续看得比家庭的责任义务更为重要。即使按照传统的观念,她们有生存的依据,然而在没有任何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她们选择了殉烈,都是基于对婚姻关系的信守。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对所谓婚姻关系的信守在很多情况下是对宿命的一种认从。
汪氏,石冈人,许字临河程如璜,璜家贫且病疠,及议婚期,或劝少缓,以观变。汪谓母曰:“贫富寿夭,命也,奈何以盛衰改节。”遂归之,归六年,而如璜卒,汪自经死。[10]《卷十六·列女》
方本素妻仇氏,方,罗田人,侨居仪征,氏年二十五始归,甫两月,夫复贾仪征,时翁耋且贫,素负,米恒不给,氏鍼纫佐之,素亦恃氏无内顾忧,未归者十年,病革乃召氏赴仪,比至,已奄奄一息,移时而殁。时氏急欲扶櫬归里,踰年终不果,氏叹曰:“命也!”奠于夫墓,返而自经。[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在这些从一而终的妇女当中,我们无法分辨出她们对于婚姻关系的信守是出于对丈夫感情的执着,还是盲目的随从,或是相信生命的宿命。但从方志的记载中女性自己的心声,我们可以看出,她们当中的一些人把“富贵在天,生死由命”这一宿命思想转嫁到了婚姻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
二、对家庭责任的担当
从一而终,对于明清妇女来说,是一种道德理想,但是真正成为孀妇之后,要在孤苦无依的漫长人生中去实践这个道德理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明清节烈妇女当中,有的基于对家庭责任的担当,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尽到了养老育幼等诸多家庭义务。她们对家庭责任的担当,有时是出于丈夫的临终托付。
郑文英继妻吴氏,长龄桥人,年二十一夫故,病笃时,问身后计,氏许以死,文英嘱以抚侄为后,并育前室女,氏泣应。乃立节不移,及子妇复夭,更抚孙,十指自给,足不出户者四十余年。[14]《卷十一·人物志·列女》 或是家人的劝慰:
凌氏,黄一鹤妻,年二十八,鹤客死青阳,讣闻,恸绝,不食者三日。时舅姑年八十余,二子济、滋始孩齓,家人慰谕,责以二尊失养,二孤失恃,一死何足以塞责。乃强食,嗣是勤约苦辛五十余年,子臻耆艾,孙睹曾元,年八十八岁而卒。[16]《卷八·节妇》
或是出于感恩:
汪昌业妾余氏,汪,大里人,氏生长于主家,昌业艰于嗣,纳之,逾年举子,又逾年而昌业殁。有劝之改适者,氏曰:“吾感主人恩,幸而生子,祀得不斩,若舍而去之,吾弗忍也!”母子相保,苦志终身。[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更多的是她们自觉自己肩负的家庭责任。
王门双节:在城王璿妻李氏,名瑗,年二十八寡,抚子宾守节,宾妻方氏,名昺,年二十四寡,家贫,三罹回禄,艰苦不堪,而姑媳同育二孤,处之裕如,俱以寿卒。[10]《卷十六·列女》
明清徽州有很多几世守节的,“可怜两世孤孀妇,相对朝朝泪不干”[19]202 就形象的描绘了她们守节的心酸。对于中途失去丈夫的寡妇来说,只有代亡夫完成孝养公婆、教育子女、治家立业以后,才算完成妇道之职。明清徽州许多节烈妇女正是在这种孤寡无依的极其艰难的情境下,忍辱负重,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承担起众多的家庭义务。其中最基本的义务有主中馈、赡养老人、鞠育幼小及处理家庭内外事务等。
徽州方志家谱中有大量节烈妇女勤劳主持家务的例子。而且节烈妇女大多是在贫困的家庭中竭力主中馈的。丈夫去世,家庭极为贫困,在这种境况下操持整个家务,可以想象有多么艰难。
丈夫死后,往往舅姑年岁已老,子女尚幼,这时养老抚幼的重担就落到孀妇一人身上。她们大多自食粗粝,而以精细之食奉养老人。在舅姑生病或发生危险时,她们有的旦夕扶持,衣不解带,百般呵护。有的躬尝汤药,吮疮餂毒,不避污秽。更多的节烈妇女割股疗疾,乃至舍身救亲。
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尽孝道,而且抚养、教育丈夫留下的子息。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对幼小的鞠育,有时并不仅仅是自己的子女,往往兼负着养育丈夫及自己幼弟、侄儿侄女,甚至抚养孙辈等责任。
丈夫去世以后,家庭一切内外事务的处理便落到孀妇身上。从文献来看,明清徽州节烈妇女在夫亡以后,所要处理的家庭事务有料理丧事、奉主入祠和祭祀、为夫立继,以及处理债务,乃至参加各种体力劳动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由于家庭贫困,她们往往要变卖金银首饰等财产或者借贷,才能归葬夫櫬。祠堂是祭祀的最重要场所,修建和维护祠堂需要资金,其来源之一就是宗族成员神主人祠供奉时缴纳的进主费。明清徽州家境贫寒的节烈妇女大多设法凑足进主的费用,以让丈夫和祖先的神主能够入祠祭祀。她们或置办祀田,或捐产捐资给祠堂,或捐资会社,都是为了使丈夫和祖辈得以永享祭祀。有些妇女促使其不再嫁的原因就是为了祭祀夫家祖先。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生育的一个目的是延续家族的血脉和宗祧,使祖先永享后嗣祭祀。在传统男权社会里,祭祀必须由男性承担,倘若男性子嗣中断,就会“废其祭祀,馁其鬼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0]《卷八·叔教其嫂不愿立嗣意在吞并》 所以无子就必须立嗣,以延续宗祧,使祖先香火不断,这是无子夫妇应尽的义务。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有许多刚刚结婚未及养子,甚至未婚丈夫即去世,也有许多生子夭折,以及其他各种原因导致无子。为了延续宗祀,节烈妇女们往往要为夫家立嗣。明清徽州节烈妇女有的还兼负有婆家和娘家双方立继的义务。如:“洪永弼继妻程氏,洪,岩镇监生,殁,氏抚遗孤,孤夭立继孙,氏父母家贫无嗣,亦为父立继,守节终。”[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明清徽州男子大多经商于外,丈夫死后,妻子往往要处理丈夫生前账务。对于丈夫生前债务,她们往往变卖家产设法偿还。如:
王元中妻洪氏,名玉凤,洪村女,归中云元中,中商于楚而没,本尽折,多逋欠。氏年廿六,孤仅八龄,或虞之。氏曰:“决不忍吾夫作负债鬼。”倾产遍偿,自勤纺织,供甘旨,育藐孤成名,家道复昌。太守余公自怡制文表其贤节。[11]《卷五十一·人物十七·列女》
丈夫去世后,家庭缺乏男性劳动力。她们便想方设法从事以纺织为主的劳动来满足家庭所需。明清徽州众多节烈妇女为了谋生,不仅从事女红、纺织等手工劳动,而且走出家门,从事耕地力田、打柴割草、为人佣作等沉重的体力劳动,成为家庭生产的主体力量和家庭生活的依靠力量。
正是由于自身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明清徽州大量的节烈妇女毅然担当起扶老携幼的重任,百折不移,从而使破碎的家庭得以维持,使家族的血脉得以延续,也使得大批徽商的事业得以后继有人。
三、对困窘生活的逃避
《明清鲁浙粤女性自杀探讨》一文通过考察明清社会经济发达的鲁、浙、粤等沿海省份女性自杀的状况认为,明清女性自杀的数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明清女性自杀以已婚者居绝对多数,并且以殉节为最多,自杀的社会根源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21] 田汝康(T'ien,Ju-k'ang)专门讨论了寡妇殉死的问题,认为在明代寡妇殉死被视为妇女守贞不二的崇高行为,但以清人的眼光来看,寡妇殉夫其实更经常地是因为绝望,而不是受贞节的驱使。[22] 曼素恩(Susan Mann)指出,清代少女们自幼受到的严格之极的教育并没有教给她们一旦生活在冷漠或是敌意的配偶身边将如何抵抗精神上的和心理上的压力,也没有教给她们在一个将上层妇女的再婚视为耻辱的社会里如何面对守寡生涯的自贬自抑。[23] 这样,在丈夫去世之后,许多孀妇们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时,根本不知道如何去缓解这种压力,只得以自杀的方式来摆脱这种压力。她们的自杀是面对不能自主的人生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如《潭渡孝里黄氏族谱》载:
黄世学妻董祥娥者,富堨董高奇女,世学亲老,贫无以养,董事女工,昼夜不怠,而姑得养。世学卒,董鬻其器偿逋负,移居春晖堂,绝粒不食死。
丰乐溪寒山色幽,潺潺溪水抱村流,闺人入夜鸣刀尺,灯光潭影自悠悠,君不见黄世学妻董祥娥,家贫能将妇职修,姑得甘旨夫不忧,夫已死,妾无子,室如县罄那不死,死时密密纫衣裳,绝粒移居春晖堂,里人为我道其事,衣裾皆具梅檀香[16]《卷八·烈妇》
许多类似董祥娥的妇女,本来家庭就极端贫困,夫亡之后,更因没有依靠,缺乏必要的物质生活保障,而绝望的自尽了。
王槐佑妻吴氏,杞梓里人,夫殁,氏因侍疾积劳,一恸几绝,方欲立继承祧,而家产悉被亲房豪恶占据,将欲夺其志,氏痛夫死无依,号泣数日,自尽以殉。[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吴烈女,溪坎人,许字甸子上潘世璝,既归其家待年,未婚,世璝父母俱亡,门衰祚薄,竟以贫死,其上世数棺未葬,女尽鬻其所有,以营葬事,而以世璝袝焉,事毕,遍拜邻族,泣告曰:“无祀之坟,得不易坏,死生均感。”是夜雉经死。[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鲍东连妻叶氏,鲍,堨田人,贫而佣贩,氏力作相之,及病,氏为医祷,艰难万状,卒不起。无子,氏语诸族人,欲置片土葬其夫,虚右为己圹。比无应者,商之母族,亦然。氏叹曰:“命也!”乃泣拜夫柩,尽燎夫之故籍文券而自经焉。次日,邻人启户视之,氏形色如生,发丝不乱。[12]《卷十三之一·人物志·列女》 有些寡妇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不堪忍受漫长的守节之路,或是不能为家庭所容,中途还是选择了自尽。
淑姑,府学生衍庆女,适呈坎罗光祖,即保定巡抚罗闻野公之从子也。姑御之甚严,淑曲意承顺,常以身代婢妾之役。光祖病瘵,淑衣不解带者累月,痈发于尻,亲为吮舐,临终与别曰:“吾无子,我死若努力。”继而曰:“曾祖姑祖姑皆嫠也,何必然。”淑颔之。既殡,引刀自刺,以婢救免,因绝口不复言死事。祖姑察之,夜则引与同寝,且慰之曰:“若夫有言,二老嫠,足相依,无自苦。”女佯应曰:“姑言是。”因请为夫斋,斋之夕,淑得间即闭户自经。久之,屋若震极者三,众惊排户视之,绝矣,时年二十有三。闻野公为状其事,有司入祀节烈祠。事具邑志。[16]《卷八·烈妇》
徽州有一首《寡妇娘》民谣,道出了徽州寡妇们悲惨的命运:
正月提起寡妇娘,正月本是拜年忙,别人拜年有人陪,寡妇拜年自茫茫;二月提起寡妇娘,二月本是下种忙,别人种子已归土,寡妇种子高悬梁;三月提起寡妇娘,三月本是挂钱忙,别人挂钱挂上祖,寡妇挂钱挂夫郎;四月提起寡妇娘,四月本是插秧忙,插得秧来茶已老,采得茶来秧又黄;五月提起寡妇娘,五月本是耘田忙,金莲三寸泥里踩,百褶罗裙裹泥浆;六月提起寡妇娘,六月本是乘凉忙,别人乘凉成双对,寡妇乘凉不成双;七月提起寡妇娘,七月本是割稻忙,别人割得金黄谷,寡妇割得满田荒;八月提起寡妇娘,八月仍是收割忙,别人收粮仓仓满,寡妇只收半年粮;九月提起寡妇娘,九月本是赏花忙,别人菊花亲人插,寡妇菊花园里黄;十月提起寡妇娘,十月本是做衣忙,别人做衣做花色,寡妇只做青布裳;十一月提起寡妇娘,十一月本是舂粮忙,别人舂粮用担挑,寡妇家中升底粮;十二月提起寡妇娘,十二月本是过年忙,别人过年团团聚,寡妇过年守空房。
明清徽州许多节烈妇女正是在这种孤寡无依的极其艰难的情境下,忍受生理和心理上巨大的苦痛,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支撑起破碎困顿的家庭。她们要在生活的夹缝中保护自身,赚养公婆,教育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负担。她们不仅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过着缺衣少食的艰辛生活,而且还要经常忍受公婆及家庭其他成员的责难虐待,社会地痞无赖的欺压凌辱,传统礼教的约束。自杀是残忍的,是对自身生命的不负责任,可对于明清徽州许多烈妇烈女来说,自杀比起冰冷而孤寂的漫漫守节生涯,或许又是一种解脱。
四、留名传世的愿望
在中国传统男权社会里,女性被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她们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明清时期的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使得徽州众多男子跻身仕途,显身扬名。明清徽州女子受其感染,同样也会产生留名传世的愿望,但愿望与其缺乏实现途径之间的矛盾,给她们心理以极大的压力,导致了她们内心深深的焦虑,迫使她们搭建沟通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桥梁。在明清国家与社会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中,贞节旌表制度为女性提供了一条获取留名传世机会的途径。女性只要符合节烈旌表条件,便可能会获得国家和社会的表彰,从而使自己留在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记忆里。因此,明清时期的徽州众多女性,在时机到来之际,往往毫不犹豫的进行节烈实践。
同时由于贞节是一种道德实践,按照《左传》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不朽。”相对于时间的长河,人的肉体会迅速的消亡,但藉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达到精神的不朽。而且在通达不朽的途径中,“立德”首当其冲。妇女由于不能介入公共领域以及缺少文化等原因,无法“立功”、“立言”,便只有通过节烈实践以“立德”,进而资以永垂不朽。王洪度大叔母江氏之所以守节终身,其重要原因就是要扬名后世。
康熙辛酉春二月,大叔母江孺人以天年终,年八十有四。大叔母为歙江村惠州府通判世济公女,生明万历己亥年,十八归大叔父士熊公。四年,大叔父殁,时年二十有二,至是守节者六十二年。初寡时,即毁容断发,誓不出闺门一步。族属子侄非正衣冠不见,为女为妇,乡邻以是罕见其面。死之日,亲族闻讣哭奠,三朝夕会,葬者数百千人,叹曰:“真闺阁宗师也!”先是未死前数月,一日晨起敛絍端肃,泣拜于洪度之门,谓:“未亡人不能亡也,志盖有待也,乃迟之,又久而终莫之遂,岂非天哉!今日非子兄弟文不克传我。”因出手书自叙,娓娓五千言以授洪度。其略曰……[13]《大叔母江孺人家传》
虽然,有些节烈妇女在别人为其请旌时予以制止,认为妇人守节是其本分。
张氏,甲道人,适桃溪潘德缨,年二十举子,甫半载夫殁,守志事姑抚子成立,后家稍裕,或劝其子入太学,谢曰:“吾家世明经,毋以输粟,自委也,愿儿曹力学而已。”年登大耄,亲族欲申请表扬,又谢曰:“妇人分应尔,奚容多事。”其天性坚正如此。[10]《卷十六·列女》
也有些节妇在守节条件符合旌例,族人为其请旌,遭其阻止,直到死后才获得旌表的。如程可诏继室吴氏“殁时,年七十有五,守节四十九年。先是年过五十,例合请旌,母闻众谋,急止之。迨身殁日,复奉恩诏,督抚核实题请,上嘉叹,命表其闾。”[13]《旌表贞节程母传》
在明清时期的徽州,节烈妇女通过自身的实践,使自己留名传世的愿望与国家对其节烈的期许达成了默契。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使得她们名垂史册。尽管一些节烈妇女在旌表机会到来之际,有意规避,殊不知,她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其形象更好的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女性把为夫守贞当成从一而终之义的体现,把以死殉夫当成了从一而终之义的终极目标。这种守贞、死义的行为,在一些士大夫心目中常常与忠臣的忠君死国联系在一起。正是通过这种联系,肯定了女性贞节行为的崇高价值,所谓“食人之禄有死无二者,谓之忠臣;处人之室,有死无二者,谓之节妇。”[24]
男性显身扬名的机会很多,而女子只此一条路径,所以妇女的节烈实践远比男性要多,士大夫们针对这一现象,发出感叹,“今则妇人之行能合乎古人,而士君子反不逮。”[25]《卷七·桐城列女志序(代)》 “自有宋以后,妇人之以节义著者,代不可胜数,而士大夫之风节,或反不及其盛。岂天地严正之气,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欤?”[25]《卷九·枞阳节孝祠记》 刘大櫆甚至对男性提出了直白的批评:“然女子犹有能明大义者,而男子则泯然,惟知富贵利达之求。一邑之中,女子之节烈可采,常至不可胜载。至于国家将亡,其能见危授命者,百不一二睹焉。岂天地之义气澌灭之未尽,而犹或钟于女妇欤?”[26]
我们在考察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行为时,应当对其动因进行综合考察。外在因素固然是其节烈行为的重要驱动力,但她们的内在主体性因素显得尤其重要。男女两性在贞洁观念上的不平等是长期形成的。男性以自己所掌握的话语权和阐释权,为女性规定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使她们的一举一动都由礼教来约束,以母、妻、女的具体社会职能把她们纳入社会秩序之中。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大量涌现,就是这种漫长演变过程的集中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产物。贞节观念在宋明理学及女教的传播之下,发展至空前的程度,彻底的深人人心,成为妇女行为的第一准则。明、清变本加厉,通过旌表制度及贯彻机制的设立、各种表彰方式的施行、节烈妇女榜样的劝诱、文人士大夫的树之风声、大众舆论的一致引导、宗族恩威并施的奖劝与控制,加之妇女的追逐与盲从,遂使贞节观念彻底深入徽州社会,成为一种潮流。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明清徽州有无数的妇女在夫亡或面临暴徒的侵害时,或者执着而又艰难的守节养家,或者悲壮而又绝望的以身殉烈,成为一种群体性行为。虽然部分节烈妇女获得了旌表的荣耀,部分守节妇女也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但她们都是宗教化的贞节观念的牺牲品。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痛切地指出:“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28] 明清徽州节烈妇女,从青年到老年都孤守家中,其间有无数的艰难和困苦,也不乏青春的躁动和寂寞。她们要忍受生理和心理上巨大的苦痛,坚守身体的贞洁和从一而终的信念,用自己的忍耐与牺牲,强化了徽州社会的礼教秩序,维护了徽州社会的稳定;她们要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支撑起破碎困顿的家庭,用自己不完整的家庭,维护了宗族组织的完整,促进了徽商的崛起;她们在不能科举致仕的情况下,紧紧抓住旌表这一唯一的显身扬名、光大门楣的机会,徽州土地上矗立起的一座座贞节牌坊托起了明清徽州社会的辉煌。明清徽州这种突出的节烈现象是贞节观念的强化,国家与徽州地方宗族所制定的各种相关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并结合女性自身的主观因素,共同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明清徽州节烈妇女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牺牲,维持了家庭的延续,造就了徽商的辉煌,促成了徽州社会的繁荣。
收稿日期:2008-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