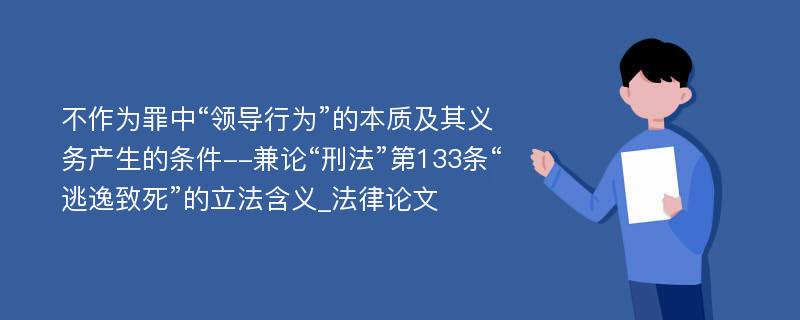
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的本质及其产生作为义务的条件——兼论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不作为论文,刑法论文,致人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相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罪而言,先行行为属于第二层面的概念,即它仅限于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之作为义务的来源时才有研讨的价值。受阿明·考夫曼(Armin Kaufmann)“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规范伦理观点的影响,不真正不作为犯罪曾经受来自各方的狂轰烂炸,并且迄今未曾消停。唇亡而齿寒,与此相伴的先行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家“关注”,尤其是个人权利大放异彩的今天,诸如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来源或曰根据,先行行为负有作为义务的条件,先行行为的外延或者范围等等,不一而足。“一切立法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一种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是法所维护的,什么样的行为是法所禁止的。”(注:(美)E·A·霍贝尔著:《初民的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刑法规范也是选择的产物,正是通过无数次的调整与选择,刑法才逐步接近直到完成自身价值的实现。而刑法对先行行为的调整,从价值观点而言,目的亦在于此。
一
十九世纪初期,个人本位主义盛行,权利保障、权利优先的观念深入人心和不可动摇,所以,“其时所谓犯罪,乃指侵害法益或侵害权利而言,故置重于作为犯,所有刑法上的问题,皆与作为犯发生关联而被展开者,原则上并未有不作为可构成犯罪的想法,仅就违反法律之规定或违反由于契约等之义务的情形,例外地认定不作为之违法性”(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61页。)。可见,此时之作为义务的来源仅限于法律的规定或契约(表明刑法选择的宗旨在于个人权利的保障)。至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个人主义式微并让位于社会本位,信用诚实的原则推行且应用于社会日常生活,不作为之构成犯罪并逐步发展。及至重视社会生活之互相扶助的团体主义或曰全体主义抬头,立法者开始对违反特定义务而消极地不实行法所期待之行为设立命令性规范,以维持并防卫社会秩序。于是不作为犯罪明文化,作为义务的来源也逐步扩大,先行行为成为不作为犯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之一(注:关于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我国通说认为有四类:(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者业务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在上述四类义务中,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仅限于第(1)类,即由其他法律规定而由刑法予以认可的义务;其余三类义务皆针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而言,故先行行为亦仅针对不真正不作为犯而言。在国外刑法中还存在其他的分类方法,如除上述义务外,还包括基于公共秩序、良好习俗(或曰公序良俗)而产生的义务、密切的共同体关系产生的义务以及自愿承担保护责任产生的义务等等。)。在此过程中,德国刑法学者斯特贝尔(Stubel)贡献突出:他从生活的实际感觉和明白的法感性中归纳而得出先行行为可以产生作为义务并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由此,先行行为作为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在十九世纪中期逐渐被理论上所确认,及至1884年10月21日,德国判例首次确认了先行行为与法律和契约同属作为义务的发生事由。该判例指出:“由于不作为者的先行或附随行为而产生的作为义务,或者,由不作为在法律上所存在的作为义务被侵害的场合中,无论是在一般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刑法典的意义上不作为都是行为。”(注: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第2版,第302页。)由是,先行行为所发生的义务被视为德国习惯法的一部分。继德国确认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后,日本、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也纷纷在刑法中确立了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地
位。(注: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但刑法理论上都认为先行行为所产生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特定义务之一。见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215页。)
那么,何谓先行行为?何谓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对于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谓先行行为,也称事前行为,是相对于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而言的。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使某种合法权益处于遭受严重损害的危险状态,该行为人产生积极行动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就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那么,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义务呢?
义务是与权利相对而言的,在初始的意义上,权利与义务具有关联性,这种关联既包括道德上的关联,也包括逻辑上的关联。但是,除此之外,“确实存在许多与权利不相关的义务的明显例子,这可能是由于‘义务’一词的发展而使之具有新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如先行行为引起的特定义务,(注:(美)范伯格:《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以下。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卷,第207页。)这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不同于法律规定的特定义务之处。但是,问题到此远未解决。法律明文规定的特定义务,其作为作为行为的义务来源根据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真正不作为犯的处罚是严格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上对此并无任何歧异;但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其根据却决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那么,其根据又是什么呢?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一般见解,先行行为之构成不作为犯罪是由于诚实信用原则推行并应用于社会日常生活的缘故,所以,先行行为作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是根据习惯的条理,是基于法精神的合理判断而推理出来的。如台湾理论界一般认为先行行为之防止义务系依据习惯、条理以及公序良俗之观念,或依诚实信用之原则;日本关于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从来的教科书都一直将之作为根据条理、习惯而产生义务的适例而予以说明的,因此,从本质上讲,德日刑法学者关于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的根据性,是基于道德的基准而推导出来的结论。”(注: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57页。)
但是,从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秩序中产生的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呢?对此,理论上存在争论。(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不作为犯罪所违反的义务只能是法律上的义务,不包括道德上的义务;另一种认为既指法律义务也涵括了道德义务(即违反公序良俗而产生的义务),有些国家的刑法对此作了规定。如德国刑法第330条C款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时,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自己并无重大显著危险而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一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法国、意大利也有类似规定。但是,在上述情况下,如何确定犯罪主体的范围及控制处罚范围等就成为一个解决的问题。)通常认为不作为犯罪所违反的义务只能是法律义务,不能是道德义务,否则,就会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是以引起一定的刑事法律后果为特征的,故作为义务也必须以其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承担某种义务为必要,只有在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才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和约束,否则,就不具有国家强制性而只能受到道德、伦理的谴责及纪律制裁。”(注: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57页。)显然,依据习惯、条理、以及公序良俗之观念,或依交易上之诚实信用原则而认为应发生一定之作为的义务不属于在一定法律关系中形成的义务,只能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这种道义上的义务在未受到国家认可时不具法律上的效力,从而就不具国家强制性。所以,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法律根据不可能是那种纯粹的道德义务,从法律范围以外的所谓“法秩序的精神”或“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中寻找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根据,“范围之广泛与无明文规定之法例并无不同,显已作超法规的解释,而有不当的扩大法律上防止义务之范围”(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72页。)之嫌。但是,“否认条理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自然也就否定了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根据”(注:(日)井上偌司著:《争议禁止和可罚的违法性》,成文堂1973年版,第20页。),而这种结论又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发生了冲突。
所以,要承认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是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就必须首先承认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不是纯粹的道德义务,而是一种蕴涵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要承认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是一种包含道德义务的法律义务,就逻辑性地得出先行行为是属于法律事实之一种的法律行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否则,就难以解释它和罪刑法定原则以及司法实践相冲突的问题,不履行先行为的作为义务而导致的不作为犯之可罚性就有理由受到合理的怀疑。
法律行为,是指能够引起一定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行为,实施了一定的法律行为,就必然产生一定的义务,因此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和后果。先行行为作为行为人自身实施的能够导致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危险状态的行为,是危险状态产生的原因和条件,当然应该承担以积极行动阻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因为“由于自己之作为而导致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负有防止一其发生之义务;盖不得侵害他人的利益之不作为义务,在其反面,当然含有‘如由于自己之作为而发生足以侵害他人法益之危险时,负有防止其发生’之作为义务故可认定此种违反作为义务之不作为,与作为可能具有同一之强度性。”(注:陈朴生、洪福增合著:《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37页。)由此可见,能够导致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危险状态的先行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能够引起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消除危险状态的作为义务就是法律义务。所以,先行行为之所以被视为作为义务的来源,决非依据习惯和条理,而是基于国家所确认的上升为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规范而产生的;由先行行为所致的作为义务决不能脱离法律规范而存在,并且只能依法律禁止规范的存在而存在。
二
如前所述,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源于法律的禁止规范,如果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产生了采取积极行动防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即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即构成要件的该当结果。但是,并不是只要有先行行为就能引起作为义务,从而可能构成不作为犯罪,否则就有过分扩张处罚范围的可能。事实上,随着二战后个人主义的重新兴盛,刑法机能更侧重于人权保障,关于此,且不说自由思想根深蒂固的法国自始至终未曾认可不真正不作为犯(从而也就否定了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就连原先全面确认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战后的新刑法均已未如战前各草案设置有关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规定(日本1974年修正刑法准备草案亦未作规定),这反映出各国对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根据性的态度:由全面确认转变为严格限制。(注:仅此并不意味着德日否认刑法中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存在,无论是在刑法理论上抑或司法实践中,先行行为作为义务都不断为两国的学说和判例所采纳,因此一般认为,在立法意图上,对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成立不是完全否定,而只是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日本1974年刑法草案理由书解释未设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原因系“并不因由于自己先行行为之发生危险而应常负防止结果之作为义务,以及如果将因自己之先行行为致发生一定危险而常负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之规定适用于汽车司机肇事后逃逸之情形时,则有过分的扩张处罚范围之虞”。见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59页。)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成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先行行为本身外延或曰范围的限制。
关于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成立条件,学说上不尽一致而且缺乏深入研究。通说一般认为必须由于自己之行为(先行行为)而致发生一定的结果之危险,且其行为必须为违法行为者,始发生作为的义务(至于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即可不问)(注:如著名刑法学者Mezger、Hippel皆持此种学说。);李海东博士认为“如果行为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法律保护的利益造成了一定的危险,他就有责任保证这一危险不会转变为损害法益的现实即构成要件的该当结果。但是,由于先行行为而产生的监控义务必须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先行行为必须导致了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其次,先行行为必须客观上是违反义务的(但不必是有责的);最后,这一义务违反必须体现为旨在保护这一具体法益的法律规范的违反。”(注:李海东著:《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166页。)但相当多的学者(如Traeger、Merkel等)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先行行为不仅限于违法行为,亦包含正当行为;先行行为不仅限于本人之行为,第三者之行为也涵括在内;等等。
刑法,就其规范意义而言,是国民自由行动的准则;从道德意义上,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但“刑法只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的适用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的自由、尊严和财产的重大侵犯和由此而导致的其他社会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须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围内适用”(注:李海东著:《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世界范围内对先行行为作为义务的转变似乎也说明了前述观点(但不尽如此,人权保障更是主要原因之一)。为此,就有必要对先行行为进行重新定位和评判。先行行为也必须限定一定的条件才负有作为义务。
(一)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基于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其先行行为应否仅限于自己之行为?抑或包括自己以外之第三者的行为?关于这个问题,理论上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如Traeger)认为应包括第三者的行为,但通说均认为由于自己之行为而发生侵害法益之危险的,始负有防止危险发生的义务(如Mezger、Hippel等)。本人认为,先行行为是相对于危险状态出现后行为人的不作为行为而言的,因此,先行行为应指行为人亲自实施的行为,即先行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为人本人,而不能是自己以外的第三者,如翻覆油灯致起火者,负有灭火的义务;驾驶汽车不慎撞倒行人,致使行人发生生命危险者,负有防止其因伤致死而采取必要措施之义务;追人而使之溺水者,负有救护之义务;相反,如果是他人翻覆油灯或交通肇事或追逐溺水人,则行为人只负有道义上的作为义务,而不负有法律上的作为义务。因此,他人不能成为先行行为的主体,对此,某些国家的刑法都有明文规定,即只有“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或引起)一定结果之危险者,始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
(二)必须有足以侵害他人法益的危险状态存在。危险指的是足以使合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但并非所有的法律危险都可成为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构成条件的危险,而只有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本身蕴涵的足以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的一种现实可能的危险才可以成为先行行为与特定作为义务之间的媒介。简言之,先行行为必须具有特定危险状态时始负有防止危险结果之发生的作为义务,具体而言,此处之“危险”涵义如下:
1.危险必须是现实的以及法律所禁止的。法律允许的危险不是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因为这类危险并不能现实实现在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之中,所以,它不能成为客观归责的基础,从而先行行为也就不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如甲说服乙乘飞机去旅行,结果乙所乘坐的飞机坠落致乙身亡,则甲的说服行为无论如何不属于先行行为,因为他的行为所导致的仅仅是允许的危险。只有法律禁止的危险才可成为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产生了足以发生危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或者说,实际损害是该危险状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行为人不中断该因果锁链则危害结果的发生就规律而言是必然的。
此外,先行行为所致的危险还必须是现实的。所谓危险的现实性,是指这种危险状态是客观真实地存在的,而不是假想和推测的;是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是正在发生的,而不是已经完毕的。如果危险尚处于潜在的状态,其是否出现具有或然性,或者危险状态在极短的时间内已经变成现实,则不存在先行行为之特定作为义务的问题。
2.危险必须是紧迫的和具体的,而不是遥远的和抽象的。所谓紧迫,即由于某种法律行为的发生,合法权益直接面临迫在眉睫的危害,而不是遥远的或者驰缓的;所谓具体,是指危险状态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趋势是确定的、必然的,而非可能的、或然的。换言之,行为人实施的事前行为造成的结果即危险状态能够排他性地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因而危险状态具有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较高的可能性。(注: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61页。)但是,就犯罪论的角度而言,这种危险与我们通常而言的“具体危险犯”中的具体危险不是同一个概念,与刑法已经评价的作为犯罪结果之一的危险状态也有质的区别。因为它并非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而是一种尚未经刑法规范评价的事实(如果认为先行行为之危险状态具有已经为刑法所否定的价值评价,则违反了刑法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抽象的危险,是指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并不排他性地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或者说,这种危险状态并不能对实害结果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力(即还存在其他人排除实害结果的现实可能性),危险状态并不一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危险的程度比较抽象。作为先行行为与特定作为义务之中介的“危险”必须是紧迫的和具体的,“如果以抽象的危险为已足者,则其范围似嫌过广,且有与将不真正不作为犯评价为同等(同价值性),应以具有一定的条件为限,以避免有过分的扩张处罚范围之旨趣相违背,故应从严解,认为限定于‘迫切’及‘具体危险’之情形为当。”(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版,第183页。)这对于判断由于先行行为所发生的一定结果之危险性,是否负有防止之特别的作为义务,极有关系。例如,汽车司机撞伤行人肇事后逃逸,如被撞伤之行人仅受轻微之皮肉伤,无需他人扶助即能行走;或者被撞伤之行人虽受重伤,但还能自救或者他人对被害人救护之可能性很大,则上述两种情形显然皆未至“迫切”及“无自救力”之程度亦无“具体的危险”之情况,故该司机只能犯业务上过失伤害罪(如我国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或基于其他法令应负的救护义务(如外国刑法上的遗弃罪),并不负有基于先行行为之救护作为的特别义务。因为这种情形下,虽也存在危险,但危险状态并没有使结果发生的直接性与必然性,危险程度属于抽象的危险,所以“仅仅为结果的发生提供一个因果契机而已的行为并不足以构成杀人罪的先行行为作为
义务根据,这种场合只能构成遗弃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将被害人搬离现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然后又抛弃在被他人救护的可能性极小的野外,使被害人丧失抢救机会的情形,由于被害人身负重伤,无法自救,其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交通肇事者的保护和救护,被害人对行为人形成排他性的依赖关系,又由于被害人被抛弃在野外,排除了他人对被害人实施救护的可能性,行为人对被害人形成了排他性的支配关系,因此,其移置行为所导致的危险状态能够排他性地支配危害结果发生的因果进程,具有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高度盖然性、紧迫性以及具体性,能够成立刑法中的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注: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61页。)从而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行为所致的危险程度不同就会构成不同性质的犯罪。“作为义务强(如合法权益面临的危险紧迫、直接或对作为义务依赖性强等)的不作为构成重罪;作为义务弱(合法权益面临的危险驰缓、抽象或对作为义务依赖性特弱——如依赖于他人或自救等)的行为构成轻罪”,所以,如果先行行为所致的危险系“他人的生命处于紧迫的危险,只有行为人可以排除这种危险,并且可以轻易排除这种危险的,如果故意不排除危险,就应认定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注:张明楷:“论不作为杀人罪——兼论遗弃罪的本质”,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269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危险是否仅限于“因先行行为而致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即原先并不存在而由先行行为才产生的特定危险)?抑或抱括增高原有危险程度的情形(比如将结果发生之可能性为5%的危险增至25%或50%,或者将80%的危险增至98%,等等)?对此,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仅限于自己之行为而有发生结果之危险的情形(如Mezger、Hippel等学者皆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不仅限于自己之行为而导致的危险,同时亦包括由于自己之行为增高已存在危险之程度的情形(如Sauer持此观点)。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过于极端,过于简单,难免以偏盖全。事实上,增高已存在之危险程度的情形是非常复杂的,原有之危险程度与增高之危险程度比例不同,则行为人负作为义务之责任亦大不相同,对此,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原有之危险程度属于驰缓、抽象、不确定或程度较弱的危险的,若行为人基于自己的行为将之增高为紧迫、具体、必然或程度较强的危险者(如将结果发生之可能性为10%的危险增至结果发生之可能性为50%以上),则行为人之行为应属于负作为义务的先行行为,如果行为人不履行特定之作为义务,应负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危险的紧迫以及具体实际上乃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原有危险状态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行为人之行为与现实的损害结果具有直接和必然的因果关系。
(2)原有之危险程度系驰缓、抽象、不具体或程度较弱,行为人基于自己之行为将之增高,但仍未达紧迫、具体、必然之程度的(如将损害结果发生之可能性为1%的危险增至5%或者10%等),或者仍属于法所容许之危险的,则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之增高不能负作为的义务。因为该增高的危险,仍属于迟缓、抽象或者不具体之危险,它与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所要求的危险具有质的差别。
(3)原有之危险本身已达到紧迫、具体的程度,即使无行为人之增高损害结果也很可能发生的,而行为人又施加了一定增高行为的,则行为人之增高危险程度的行为仍属于先行行为。究其原因,本人认为此处之危险的紧迫、具体程度虽非增高之行为人所导致,但其增高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处于更危险的状态,其增高行为与特定危险之间已经存在特定的联系,行为人也就负有了免除他人危险的积极作为义务,如不履行则应负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当然,其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大小因行为人之主观心态、行为时的环境等而各有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之增高原有危险程度的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如果行为人之增高原有危险程度的行为本身已该当刑法所规定的某一具体的构成要件,并且是违法的以及有责的,则对此直接依刑法规定处罚即可。具体原因笔者将在第三部分进行论述。
(三)先行行为与危险状态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乃行为人负特定义务的客观基础。详言之,具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确定性和急迫性的危险状态必须是先行行为直接造成的,即没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损害结果就会顺乎自然地发生,从而表明先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且系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查明某一行为并不具有使危害结果发生的直接性,而是具有一定的间接因果关系,则不能让行为人负特定的作为义务。
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先行行为人才能负有作为义务,缺一不可。
三
不真正不作为犯由于其构成要件的开放性,其处罚范围不明确的难题迄今未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决。至于先行行为的范围或外延,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讨,但研究结果同不真正不作为犯一样始终未曾达成一致,所以,对于先行行为之构成不作为犯的问题,我们今天仍需倾注一定的心血。
关于先行行为的外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先行行为是否限于有责行为。先行行为是限于有责行为还是包括无责行为?理论上有两种观点。肯定说认为,先行行为作为法律事实之一的法律行为,必须反映行为人的意志,是基于一定的心理活动而作出的能够引起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人的行为,如果该行为并不反映行为人的意志,而属于人的无意识的外部举动,则不是刑法中的先行行为,故先行行为必须出于故意或过失才能发生作为义务。此说乃德国的通论,为Merkel及Bumke等学者所采纳,我国台湾也有学者持此观点。(注:该学者认为:“关于自无责任的行为而发生一定的危险者,有无负有除去其危险的义务之问题,如自构成行为义务之基本在于该行为系属有责之思想为出发点时,则不能课该行为者之法律上的义务;盖无责任之行为,纵令谓为亦可发生义务(道德上之义务),然实际上不能将无责任之行为,作为发生义务之根据故也。”见陈朴生、洪福增合著:《刑法总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45页。)否定说认为,先行行为不限于有责行为,无责(即无故意或过失)之行为亦包含在内。“只要足以导致构成要件该当结果发生之危险者,即为已足,系有责或无责之行为,在所不问。”(注:林山田著:《刑法通论》,台北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302页。)Hippel、Mezger及Liszt-Schmit等学者皆持此说,我国也有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注: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页。陈教授认为“先行行为是否必须有责,只是对先行行为的法律评价问题,如果行为人对先行行为显然无责,但该先行行为引起作为义务,行为人应当履行而不履行,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不作为具有责任。那么,无责之先行行为,完全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美国学者阿诺德·H·洛伊亦持此说。(注:阿诺德·H·洛伊著:《美国刑法要论》,杜利、胡云腾译,西南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印,第90页。“行为人使他人处于危险状态,但没有过失,关于他们未设法救助的行为应负什么责任这是最难办的问题……若那个游泳手在游泳池旁(他无过失),孩子跑过来撞在他身上落入五英尺的深水中,游泳手有意坐失孩子溺死,他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呢?发现的这类情况的有关案例很少且有分歧,对此应追究游泳手的刑事责任是较妥当的意见,因为他的存在并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相反,没有他的存在,孩子就不会处于这种危险状态。”)
笔者认为,先行行为是否必须有责,只是对先行行为的法律评价问题,这种法律上的评价与先行行为是否能够引起作为义务并无必然性的联系,此其一;其二,刑事义务的范围限定刑事归责的范围。刑事归责的对象是违反了刑事义务的行为,而非刑事义务本身。(注: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51页。)先行行为是刑事义务的来源之一,而非违反刑事义务的行为,故先行行为不是刑事归责的对象。所以,无论先行行为是有责还是无责,只要该行为引起作为义务,行为人应当履行而不履行,即行为人对于不作为具有责任,那么,无责之行为也完全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注: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卷,第216页。)如仓库管理员下班时经巡视认为已无人在仓库内而将仓库门锁闭。正要离去时,听到里面有人的呻吟声,却仍不开锁,结果致使被关之人因窒息而死。管理员锁闭仓库门的行为即无故意也无过失,但他听到他人呻吟声仍不开门的行为,属于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由此造成他人死亡结果的,应视其对他人死亡结果的态度,分别以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过失杀人罪而处理。同时,这也意味着先行行为即使具有责任阻却事由,但对于因其行为而致他人于危险状态时仍具有作为义务。
第二,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违法行为。对此,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注:大致有四种观点:(1)主张先行行为限于违法行为,如Hippel、Mezger、Liszt-Schmit等学者;(2)主张先行行为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亦可以是合法行为,如陈兴良教授,认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具有违法的性质。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形下,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参见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卷,第215-216页。)(3)主张先行行为应是合法行为和一般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认为“无论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而引起一定危害结果危险的,行为人并无防止其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对行为人只能按其原作为罪犯承担责任”(见蔡墩铭主编:《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0页),“如果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大多数一罪变为数罪,这是不合适的,因此,即使行为人不防止其危险结果的发生,以致造成此种结果的,只成立原来犯罪行为的结果犯或结果加重犯,并不因而产生作为义务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4)主张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违法行为应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述第一种观点显然过分缩小了先行行为的成立范围;第二种观点的界定范围似有过于宽泛之嫌;第四种观点实际上没有判断标准,不利于司法实践的统一;第三种观点相对合理,但还需进一步论证。)本人认为,先行行为不限于违法行为,同时包括合法行为,但此处之“违法”一词应作限制解释,即排除犯罪行为的违法。犯罪,作为刑法中的“不法”,它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行为给法益造成了某种实际损害即结果的无价值,而同时也决定于具备构成要件行为的目的性、行为的其他特征与主观意图等,即行为本身的无价值”(注:李海东著:《刑法原理入门(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所以犯罪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统一。申言之,犯罪是已经刑法规范予以否定评价的行为(其中亦包括含于行为与结果中的危险性),无论其结果性还是行为性,甚至其所包含的危险状态,都不再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未经刑法评价的状态。而先行行为是一种引起特定危险状态的行为,这种危险状态是作为行为事实的危险状态,仅表现为结果的危险性而非行为的危险性,因而,其行为性并未经过刑法规范的否定评价(行为无价值),所导致的危险状态亦不具“不法”的特征,也就是说,先行行为之危险性在价值属性上具有客观的中立性。可见,就刑法规范的价值评价上而言,先行行为与犯罪行为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所以,先行行为不可能是犯罪行为。假如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在内,则会导致将某一犯罪既遂所要求的结果作为另一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结果进行二次评价,这显然违反了刑法上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注:齐文远、李晓龙:“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第63页。)陈兴良教授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并且认为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构成牵连犯,但并未对此进行论述。笔者认为,先行行为之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与牵连犯罪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二者不能等同。所谓牵连犯,乃指犯一罪而其方法或结果之行为,触犯他项罪名之谓也。申言之,行为人以某一犯罪为目的,而其犯罪的方法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从而其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或其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之间,有牵连关系的存在,处断时认为一罪的情形。可见,牵连关系的存在是牵连犯成立条件之一。如何认定牵连关系?学说不一(注:可分为主观说(犯意说)、客观说(本身又分为形成一部说与直接关系说)与折衷说三种。主观说纯以犯罪人主观上之意思为准,不当扩张了牵连犯的范围;客观说中的形成一部说将牵连犯之范围缩小至最小限度,失之过狭。目前学者多以直接关系说为主,兼参以主观说的精神,实则为折衷说。即必须其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在主观上有意思联络客观上有直接密切之关系者,始为牵连犯。),但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两个以上可罚行为相互间的牵连关系应界定为,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相互间,不仅在犯罪人主观意思上具有联络关系,且在客观上其相互间具有直接密切的牵连关系。如持有枪支(方法行为),意在杀人(目的行为),而其损害尸体(结果行为)为其杀人(原因行为)所毁灭罪证之结果。行为人主观上对各该犯罪有意思联络,客观上方法与目的以及原因与结果间各有直接密切的牵连关系,故应从一杀人罪处断。(注:高仰止著:《刑法总则之理论与实用》,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2页。)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即牵连犯的成立以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间存在牵连关系为必要,而牵连关系又以犯罪人所实施的二个以上可罚行为相互间主观上具有意思联络、客观上具有直接
密切之牵连关系为必要。如此必然推出如下一个结论:构成牵连犯的二个以上可罚行为中之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以及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只能是故意犯罪。但先行行为(构成犯罪的)与不作为(犯罪)之间,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既可由故意构成也可由过失构成,这一点与牵连犯的成立要件显然是不相容的。详言之,在先行行为是故意犯罪(如故意伤害)的情况下,危害结果是犯罪人所期待所追求的,法律不能期待行为人对被害人(如被伤害者)进行及时的抢救,期待犯罪人防止其意图实现或追求的危害结果出现无异于对牛弹琴,在情理或一般的观念上也是非常可笑的;同时,在被害人出现行为人所预期之外的结果(如死亡)的情形下,法律对行为人的评价也只能是其所意图之罪,而不能先定行为人一个故意罪,又因行为人故意侵害他人后应负有防止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而成立另一个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或过失犯罪,否则,就使一罪变成了数罪,违反刑法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那么,在先行行为是过失犯罪时,先行行为(构成犯罪)与不作为(犯罪)之间能否存在牵连关系呢?这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未支持这一点(注:我国刑法第133条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以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较重的故意杀人罪)一罪处理的规定实际上否认构成犯罪之先行行为具有作为义务,同时也否认了先行行为与不作为间的牵连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汽车司机交通肇事后将伤者移离现场(予以抛弃)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行为,中外法院皆认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不真正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对之应进行数罪并罚(而不是从一重罪——故意杀人罪处断),这实际上也拒绝了先行行为(构成过失犯罪)与不作为犯罪之间的牵连关系。参见(1)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刑事犯罪案例从书·杀人罪》,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85页。(2)(日)日高义博著:《不作为犯的理论》,王树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68页。)
所以,先行行为与不作为之间构成牵连犯的观点并不特别令人信服。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而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如果行为人自动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则是减免刑罚的理由;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结果发生,则负既遂罪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更严重的结果发生,则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注:张明楷著:《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页。)有学者指出,结果加重犯与基于先行行为构成的不作为犯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注:区别有两点:(1)犯罪构造不同;(2)归责基础不同(罪过形式不同)。见赵秉志、田宏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1999年中国法学会刑法学年会论文。)但笔者认为,在先行行为属于犯罪的情形下,因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当然有可能存在基本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的关系,此时之“先行行为”已非原来意义上的“先行行为”这一概念。此外,该论者所言之(构成犯罪的)“先行行为导致的危险出现后,行为人认识并利用这种危险”,其“利用”行为,要么属于(构成犯罪的)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状态的继续(不作为),要么是在(构成犯罪的)先行行为后实施的另一行为(作为)。就前种情形而言,此种“利用”是包含在该基本犯罪构成要件之中的,如汽车司机交通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径直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仍属于交通肇事的构成要件范围内;而后种情形中,实际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特定危险”已不是原来之(构成犯罪的)先行行为所致,而是行为人在(构成犯罪的)先行行为后所实施的另一作为行为所致,如汽车司机肇事造成被害人重伤后将伤者移离荒僻之地致使伤者死亡的,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危险最终是由移置行为所致,此移置行为才是本体意义上的先行行为。所以,上述观点实际上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更未论证何以犯罪行为能够成为先行行为。
第三,先行行为是否限于作为。理论上存在争论。(注:一种观点认为先行行为只限于作为,如日本1931年刑法即采此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不限于作为,不作为也完全可以引起作为义务,如携带装有子弹的手枪于他人把玩之时,未加阻止,他人因手枪走火致人死亡。见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6-237页。)有的学者认为,先行行为究其实质是一种法律行为,既然是一种“行为”,则这种行为也必然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作为与不作为;就其价值意义而言,它只是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成立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条件和根据,既然如此,则不管是作为还是不作为,只要引起了某种特定的危险状态,从而致使刑法所保护的权益处于发生实际损害的威胁之中,行为人就有义务防止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如果否认不作为能够成为先行行为,实际上也就否认了不作为具有原因力,这显然与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理论相矛盾。
但上述理解明显存在一定的偏颇。先行行为本身的“行为”性质并不能必然地推出其范围也包含了不作为,如刑讯逼供是一种行为,但据此推出刑讯逼供罪的行为方式也包括不作为岂不是太荒谬了呢?!同理,不作为之不能成为先行行为的结论也不能必然地推出“否认不作为的原因力”,刑讯逼供只能是积极的作为,但该命题本身并未否认故意杀人罪也能以不作为的方式实施,所以上述结论未免显得武断和以偏盖全。实际上,肯定论者论述先行行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时通常举如下例子:(1)携带装有子弹的手枪,未予妥善保管,他人取枪把玩时,未加阻止,他人因手枪走火致死;(2)满载润滑油的汽车,因发生车祸而倾倒,致使润滑油流满地面,该汽车司机既未将路面的润滑油清除,又未立即设立警告标志,使另一路过的摩托车滑翻,车手摔死。上述二例其实远不能说明不作为也能成为先行行为。在(1)、(2)例中,先行行为并不是“未予阻止”和“未清除路面的润滑油”及“未立即设立警告标志”,而是“未妥善携带”和“发生车祸”本身。前者充其量属于行为人应当履行而未履行自己应尽的作为义务,而后者才是导致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来源。将前者认定为先行行为,无疑是将作为义务的来源等同于不作为本身,其结果是,本来行为人仅应承担一个的作为义务现在却变成了两个,行为人的一罪变成了数罪!就犯罪构成理论而言,这合理吗?所以先行行为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的结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四
我国刑法并未明定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性,但无论是刑法理论抑或司法实践都不同程度地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但涉及刑法第133条中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及其与不真正不作为杀人罪的界限时,学者间则对此存在重大分歧(注: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交通肇事后致人重伤,因逃逸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情形。见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阮齐林“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1999年刑法学年会论文。二是将此种情况视为交通肇事罪的转化犯,即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并认为这是立法上的失误,应删除此条款或者作出修改。见侯国云、白岫云著《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50-357页。三是将此种情况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又造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情形,亦即连续的交通肇事之义。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下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页。四是将此种情况视为一、二两种情形皆包括在内。见李晓龙、李立众“试析交通肇事罪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载《法学》1999年第8期;吴学斌、王声“浅析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卷第265-266页。五是将此种情形视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见张波“交通肇事‘逃逸’的定性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总第41期。
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仅限于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将被害人移置他处或施以其他加害行为,从而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情形,见上述张波、阮齐林、李晓龙等文,以及冯军《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48页。二是不仅限于第一种情形,同时还包括“行为人肇事将他人撞伤(包括轻伤和重伤),同时具有致其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行为人逃逸,被害人因而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或者虽被抢救仍未能免于死亡的”情形。见赵秉志、田宏杰“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1999年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黎宏著《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该说的论据在于:判断(间接故意的)不作为犯与(间接故意的)作为犯等价值性的标准,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主观上的放任态度,同时必须结合行为的方式、地点、环境、情况、被害者受伤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只有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排他性支配关系时,即行为人排除其他救助被害人的可能性,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具有支配性的原因力,才是进行等价值性判断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不作为,则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
如前所述,先行行为不可能包括犯罪行为;在先行行为是犯罪行为的情形下,如果行为人没有防止更严重的结果发生,则负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而不能另外再构成一个不作为的故意或过失犯罪。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
(一)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范围仅限于交通肇事后致人重伤(有死亡的现实危险,但如及时救助则可能挽救伤者的生命),为逃逸而遗弃被害人致使其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此种情形下,行为人之逃逸行为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自然延伸(注:逃逸行为究其实质属于刑法中的一种事后行为。为了预防此种行为,刑法分则对于事后行为通常采取两种方法:其一是将此种行为视为加重构成要件;其二是将其犯罪化。在刑法未将此事后行为予以犯罪化的情形下,则逃逸行为本身并不具备实行行为性,所以逃逸行为仅是交通肇事行为的自然延伸。参见前述张波“交通肇事‘逃逸’的定性分析”一文。),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详言之,在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中,行为人之行为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以致发生重大事故,致使他人重伤的行为本身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构成要件,因此行为人已经实施了基本犯罪;在第二阶段,由于行为人逃逸出现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加重结果,并且逃逸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无前者即无后者的因果关系,因此又发生了基本构成以外的基于间接故意的加重结果。从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较之交通肇事罪(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之加重法定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来看,这种理解是合理的。也许有人对过失犯的结果加重犯持异议,但是从世界各国关于结果加重犯的规定来看,理论上还是有存在可能性的(注:国外刑法对于结果加重犯的规定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1)基本犯是故意,重结果亦是故意;(2)基本犯是故意,重结果为过失;(3)基本犯是过失,重结果是故意;(4)基本犯是过失,重结果为过失。其中,以(1)和(2)最为普遍。参见陈朴生,洪福增著《刑法总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50页。),所以,刑法第133条的规定虽名为“逃逸致死”实为“遗弃致死”,是“立法者斟酌实际情况,择其必要者加以规定,以示限制,庶免不当的扩大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成立范围”(注:洪福增著:《刑法理论之基础》,台湾刑事法杂志社1977年发行,第185页。),此与刑法对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限制具有相同的目的。据此,以下二种情形不能包括在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范围内:1.交通肇事致被害人当场死亡,行为人为逃避罪责而逃逸的。此种场合,死亡与逃逸行为无因果关系,系被害人死亡在前,行为人逃逸在后,应依第133条第2个量刑档次进行处罚。2.交通肇事后驾车逃逸行为本身再次肇事又致人死亡。此种情形下,行为对象以及分割的法益均已变化,实际上是行为人连续实施同种数罪,这和“因逃逸致人死亡”具有质的区别。
(二)交通肇事致被害人重伤后,行为人为逃避罪责,在逃逸过程中又实施其他故意“加害”行为,致使被害人丧失抢救机会而死亡的情形,超越了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立法意蕴。此种情形下,受害者的死亡结果并非由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之逃逸行为所直接引起,即受害者的死亡结果并非在行为人制造的肇事危险范围内实现,而是在行为人另外制造的危险范围内实现,即是由行为人实施了另一个单独的故意行为,则行为人应当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具体情形包括:
1.行为人肇事致人重伤后,径直杀害被害人的(如将伤者轧死或活埋的);
2.行为人肇事致人重伤后,迫于围观民众的压力或者在伤者有其他救助机会的情况下,佯装将被害人送往医院,至中途无人之地却将之抛弃,以致被害人延误救治而死亡的;
3.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后,为逃避罪责,将伤者转移或隐藏于荒郊野外人迹罕至之处(如山沟、密林、公路下的函道等),使被害人因不能得到他人的及时救助而死亡的。
在第1种情形下,行为人主观上有杀人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积极的杀人行为,构成直接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在第2、3种情形下,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与死亡之因果关系间介入了其他的积极加害行为,使自己与被害人之间形成排他性的支配关系,则行为人因其“转移”或“隐藏”之先行行为而非肇事行为负有救护被害人的义务。此时,如果行为人能够履行却拒不履行作为义务,从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则构成不真正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所以,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须具备三个条件:(1)行为人交通肇事致他人重伤后又实施了另一行为(如移置、隐藏等);(2)该另一行为(非其单纯的逃逸行为)使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事实上的依赖关系和绝对的排他性支配关系,即受害者的生命安全完全仰仗于肇事者的保护;(3)行为人对被害人之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
按照上述条件,如果这种排他性的支配关系(或者被害人之死亡结果)并非行为人之“另一”行为(如移置)所引起,而仅由行为人之单纯逃逸行为所导致,不管其逃逸行为是多么恶劣(即使此刻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具有排他性的支配关系),则行为人也仅构成交通肇事罪一罪,无论如何不能再构成一个间接故意杀人罪,否则就有“过分扩张处罚范围之虞”。(注:在“处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疑问尚存之情形下,限定先行行为之作为义务的范围,从而事实上部分限定不真正不作为犯罪的处罚范围是必要的,这是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