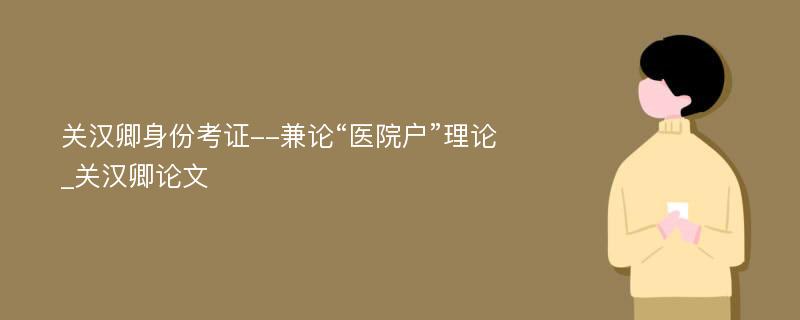
关汉卿身份考述——兼评“院户”论种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关汉卿论文,院户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关汉卿曾为“院户”一说难以成立,他所任为太医院尹,且就职于金代。
关键词 关汉卿 身份 院户 院尹 金代
一、“院户”论难以成立
关汉卿身份为太医院尹,这个事实自元至民国均很少有人提出怀疑,五十年代后开始遇到挑战。王季思先生曾推论关氏“可能只是一个通常的医士,或者在太医院兼有一些杂差。”[①]此后不久,蔡美彪先生发表了他的《关于关汉卿的生平》一文,[②]更为详尽地对关汉卿的身份进行了分析,驳斥了传统上“太医院尹”的说法,提出了“院尹”为“院户”讹误的新观点。
“院户”论者认为:一、金元两代均无“太医院尹”这个官职,而关汉卿如任元代太医院官,也与时人邾经《青楼集序》中称关“不屑仕进”的话相矛盾;二、今存《录鬼簿》明刊本均作“太医院户”。而据《元典章》和《大元通制条格》,元时确有医家“弟兄孩儿”冒入医户以求“减免若干差发赋税”,而“医户”又确由太医院管领。如果认为关汉卿身份为“太医院户”,恰恰可以解决《录鬼簿》与《青楼集序》之间的矛盾。由于“院户”论具有一定的版本和文献依据,又能解释一些具体问题,故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蔡美彪等人编《中国通史》有关章节即将其采入,韩儒林先生主编《元朝史》也接受了这一观点。
当然,学术界对此持异议的也不在少数,谭正璧、黄克、王钢诸人均曾撰文进行论辩,针对“院户”论上述各点逐一驳正(其中尤以王钢之说最为有力)。其要点为:其一,现存明本《录鬼簿》,均为万历后钞刻,在版本学上,价值与清初版本无异,其中贾仲明增补本笔误层出,尤非善本;其二,明人胡侍、李开先、王骥德、顾玄纬、蒋一葵等人著述都将关氏作“太医院尹”而非“院户”,可知他们所见所闻皆无“院户”之说,如果明本多作是记,他们必不会毫无所知;其三,《录鬼簿》体例仅载官职,不录户籍,况按元时习惯,若为医户则单称“医户”而不称“太医院户”;其四,汉卿确曾出仕,《析津志》将其列入《名宦传》,便是明证。
诸家说理透辟,持之有故,可以说是对“院户”论的有力清算。不足在于多仅从版本角度论证,而少涉及“院户”论之其它论据,即或提及其它记载如《析津志》等亦未正面展开充分论述,令人有只重一点不及其余之感。
今天看来,“院户”论可议之处颇多,即使从版本学角度讨论也还是大有文章可做。今存明刊本《录鬼簿》价值不高也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与清初本没有二致的一般版本学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可靠性不如晚出的曹楝亭本。目前已经确知,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九月重刻于扬州使院”的曹寅校辑《楝亭藏书十二种》所收《录鬼簿》,是“依据明初吴门生过录本重刊”系“至正五年以后钟嗣成原著的第二次的订正本。”[③]正因为钟氏生前对所著《录鬼簿》曾数次修订,曹本所据为最后定本,在版本学、校勘学意义上远远超过了明代各种刊本和钞本,所以其可靠性也远远超过明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元明清三代及至民国的有关论者尽管看到了各种《录鬼簿》版本却对“院尹”说未置异辞也就容易理解了。
除了版本方面不踏实之外,“院户”论的破绽还在于史实本身。即使根据《大元通制条格》,关汉卿如果属于“父兄行医”而本人不通医术的“弟兄孩儿每”,则关氏先人必有在太医院行医并颇有点声名地位,关汉卿才有可能沾得上这个光。然而我们遍查《金史》和《元史》,从中竟找不出一个关氏名医来,不仅列传没有,连专记医人等属的《方伎》一类同样找不到。唯一一部提及关氏的史书《析津志》却又将其归入《名宦传》。“名宦”者,有名望之官宦也。正如有论者所指出,将一个逃避赋役犹恐不及的“医户”列入该有多么不协调!对此又有论者解释“大概是和关汉卿在杂剧界的巨大声望有关。”[④]可惜,这只能是论者主观的“大概”!《析津志》于“名宦”一栏前明明写道,此编是记“故家遗民而入国朝,仕为美官,树勋业,贻厥子孙者。”[⑤]遍查《名宦》内所载人物,看不出可以因为“杂剧界巨大声望”而被列入的任何理由。“院户”论者只顾和《青楼集》邾经序文保持一致而忽视和正史及《析津志》的明显不合之处,加上版本方面无视后出然而更为重要的曹楝亭本《录鬼簿》(其中对关汉卿官职身份有明确记载),即难免顾此失彼了。
二、关汉卿任太医院尹当在金代
然而,事情尚未最终了结。“院户”论的要害还在于金元两代官制以及《青楼集》邾经序中所称关氏“不屑仕进”的问题。谁都知道,金元两代正史《百官志》中的确没有“太医院尹”这一官衔,对此人们还可以用“尹,正也,”“谓官正也”[⑥]这种古制来解释,将“太医院尹”理解为太医院正职官亦未尝不可(即如明清时将大学士称作宰相、兵部尚书称作司马一样),但随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查《元史·百官志》,太医院正职为正二品高官,地位优于六部尚书,而与副宰相同。即使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亦为正四品职官,与六部侍郎同。关汉卿如任此职,则《元史》不会不载。更重要的是邾经《青楼集序》中对关氏入元后的身份地位说得相当清楚:“我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⑦]“杜散人“即杜仁杰,“白兰谷”即白朴。对于他们的“不屑仕进”,有关史籍并有确切记载。《灵岩志》卷二:“元世祖闻其(仁杰)贤,与大臣议,以翰林承旨授公,累征不就。”[⑧]白朴亦同样,时人王博文为其《天籁集》作序称:“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⑨]由此可见,邾序的记载相当可靠。关汉卿既然名列“不屑仕进”之中,则说他在元代任正四品乃至正二品高官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更何况还有《析津志》,该书作者虽将关氏列入《名宦传》,却只字未提他的仕历,他到底任过何职我们无法据以明瞭,并且作者还明言“是时文翰晦盲,不能独振,淹于辞章者久矣。”[⑩]如果关氏在元时任太医院正职官,这段话同样没有着落。很清楚,如果我们认定关汉卿在元时任太医院尹,就必须先否定邾经《青楼集序》和《析津志·名宦传》,而事实证明在没有过硬证据情况下,要同时否定这两种元人文献的记载是不可能的。“院户”论者之所以能对传统上的“院尹”说提出挑战,其根源亦在这里。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我们只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将关氏任太医院尹定在金代,则上述一切疑点皆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既然是在金代任医院官,《元史》中不予记载即很自然,并且不仅不影响关氏入元后“不屑仕进”,而且正由于有了金代任官的经历,改朝换代后“不屑仕进”的遗民身份才显得真实可信。至于《金史》中未见相应记载,那是由于金代太医院官品位太低的缘故。据《金史·百官志》,太医院正职官提点仅为五品级的技术官员,既非台省要道,又无值得一书的特殊伎艺,故《金史》未将其收入,甚至连《方伎传》亦未见记载便属自然而然之事。也正因为如此,作于元末的《析津志》将其列为“故家遗民而入国朝”的“名宦”而不言其官职,是见其“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的个性声望而非“太医院尹”这个前朝的“宦”。当然,话又说回来,毕竟得有这个“宦”才能进那个“传”,基本条件具备才能谈及其它,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
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邾经语中“初并海宇”所指的时间概念。有论者定为元世祖忽必烈灭宋统一,王国维并认为关汉卿作太医院尹当在中统时的蒙古时期。如此即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即作为金遗民的杜、白、关诸人何以要等到灭宋后方才“不屑仕进”?说具体一点,关氏既然能在蒙古时期做官,到改元以后反而以遗民自居“不屑仕进”了,这显然是讲不通的。持此论者机械地看待“我朝”二字,认为“我朝”即指元朝,而“大元”,则是忽必烈至元八年才宣布改建的。事实上这是错觉。因为在元人看来,“我朝”指的是自成吉思汗开国后至元末的整整一个朝代,它包括整个蒙古时代,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即为明证。而“初并海宇”则是一个长长的过程,它包括成吉思汗西征、灭夏、灭金,直到灭宋等一系列事件。对于原处金统治区域的杜、白、关诸人来说,对其“不屑仕进”有决定影响的当为灭金而非灭宋,这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关汉卿,任太医院尹,金亡后不仕,更属显而易见。
肯定关汉卿任金太医院尹还必须涉及《录鬼簿》的编撰体例问题。有论者认为,《录鬼簿》只记元代官职,而金代人则需注明,如董解元名下则注明为“金章宗时人”。这样的话,则“关汉卿”条目中的“太医院尹”即无法理解为金代官衔,而只能是元代的事了。
如果撇开其它因素不谈,这样分析也未尝没有道理,但事实上不联系其它资料如邾经《青楼集序》和《析津志》等记载来孤立论证也是不行的。因为《录鬼簿》所记,大抵皆为元代人,由金入元的虽有几个,如杜善夫、白朴等,但他们在金世并无值得一记的官职,和元人一并处理亦无不便之处。至于董解元,因系前辈,本非由金入元之人,名列其中自当言明,而于关氏则比较困难,说是没有做官却又曾作金太医院尹,说是做过官目前又是白身。况且汉卿作官既是在金世,经过金末、宋末数番动乱,加之元初官制混乱,身处元末的钟嗣成也不会弄得很清楚。他将杜善夫等人和入元后出生的人同样处理而未特别点明其时代亦可从侧面证明这点。如其自言:“余生也晚,不得预几席之末,不知出处。”(11)材料来源于其友陆仲良,而陆又得之于吴仁卿,几经辗转,对此原不应苛求。
肯定了关汉卿的金太医院尹身份之后,我们不禁要问,他是怎么当上这个五品官的呢?是由科举正途吗?多有论者这样认为,近人林之棠在其所著《中国文学史》中称关汉卿“金末以解元贡于乡,后为太医院尹”,(12)这里的“以解元贡于乡”完全是林氏根据唐以来科举制度常规而作的主观臆测,作为关汉卿生平资料则无根据。惟“解元”二字出自元末人钱孚为宋人《鬼董》一书所作跋语,其中称是书为“关解元所传”,后世明人蒋一葵、清人鲍廷博、钱大昕、王季烈以至王国维、吴梅等戏曲史大师均相信此说,王国维并在其《宋元戏曲考》中极为认真地探考了关汉卿中解元的年代。其实这都是对《鬼董》钱孚跋语的误解。(13)解元一词宋元时人已用得很滥,如《西厢记诸宫调》作者为董解元,《西厢记》杂剧中称张珙为张解元等等,皆非“贡于乡”或乡试第一才得称之。况临安传《鬼董》一书的“关解元”也无任何和关汉卿联系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拉在一起是极其牵强的。
“解元”一说既无根据,目前同样没有发现关汉卿中过进士的记载,明人沈宠绥在其《度曲须知》中称关汉卿为“元进士”不知何据。不过金代倒有与太医院有关的医学科试,《金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凡医学十科,大兴府学生三十人,余京府二十人,散府节镇十六人,防御州十人。每月试疑难,以所对优劣加惩劝。三年一次试诸太医,虽不系学生,亦听试补。”(14)这样看来,关汉卿经由“医学十科”考试而入太医院任职是极有可能的。《元史·选举志》亦称“当时仕进多歧,权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蒙古字学,回回国学,有医学,有阴阳学,……荫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选用之科。”(15)由此可以上推下想,所谓“解元”、“进士”如果落实于此处则亦有说矣。当然这也是纯属推想的事,有待于资料的进一步证实。
金代为官,除科举外,另有世袭和荫叙二途。汉卿为汉人,非可世袭猛安谋克之女真贵族,至于荫叙,今遍查金、元两史,均无可以荫蔽后代的关姓官僚巨族。然汉卿为官亦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存在,即凭着解州关裔得以照顾这一途径(关氏祖籍乃山西解州,为“武圣”关羽之族裔,目前已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16))。关羽于北宋时即被封为武安王,设庙祭祀。金灭北宋,全盘接受了宋朝的礼法制度,至海陵王、金章宗之后,汉化尤甚,有“文质彬彬”之称,而对“武圣”关羽当不至反而轻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解州关氏一脉的关汉卿被荐出仕即为很可能的事了。据《析津志·祠庙仪祭》记载,燕京之“武安王庙,南北二城约有二十余处,”其中之一即“在太医院前”。(17)此极可令人玩味。抑或可以说,这也许是关汉卿年纪轻轻即做到太医院正职官的重要因素,否则单从“医学十科”也不会擢升得这么快,尽管这种“超擢”的结果是让作了与文治武功相距甚远的太医院头目。大概也是因为关汉卿只是武安王族裔而非直系的缘故吧。(18)资料缺乏,推想只能到此打住了。
三、一点内证及其它
关汉卿的金太医院尹身份在其作品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这一点学术界已有论者言及,惜未能正面展开论述。(19)此处着重谈谈[二十换头][双调·新水令]这首套曲。
此曲最早见于元·无名氏辑《梨园按试乐府新声》,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因之,俱作关汉卿撰,是知确为关作无疑。从时代上看还可以定为早期关作,理由有二,首先,这是一首以女真曲调谱写出来的曲子,在现存元散曲中比较少见。就〔双调〕换头这一格而言,李直夫《虎头牌》杂剧有十七换头,王实甫《丽春堂》杂剧中有十二换头,皆属女真曲调范围,然李本为女真人,王亦有论者认为系由金入元者,与关汉卿时代相侔。不过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的是,李和王所作皆为代言体戏曲,因题材背景即为金源,故以金时曲调谱入当属自然而然,而关作系叙唱体散典,本无“题材决定”之限,而所作规模又超过他二人,像〔阿那忽〕、〔相公爱〕、〔风流体〕、〔大拜门〕、〔也不罗〕、〔忽都白〕、〔唐兀歹〕这些传统的女真曲牌,关氏作为一个汉人使用起来却得心应手,这不能不从作品的创作时代上去考虑。
其次,从这首套曲也可窥知一点信息。其中有一曲〔石竹子〕云:“夜夜嬉游赛上元,朝朝宴乐赏禁烟。密爱幽欢不能恋,无标被名缰利锁牵。”曲中前二句显然表现的京都生活,后二句则道出了因贪图名利不能和爱人团聚的怨悔。这里的“名”和“利”一般应认为作者此时正混迹官场。如果说这还表露得比较含糊的话,另一曲〔大拜门〕说得即更加明白了:“玉兔鹘牌悬,怀揣着帝宣,称了俺男儿深愿。”“玉兔鹘牌”乃古代腰牌的一种,外官出入宫门的标记。宋人周密《癸辛杂识》记载:“法,凡异姓入宫门,必悬牌于腰乃可,惟宗子可免。”(20)说的就是这种特别通行证。有此特权标志悬带,且又“怀揣着帝宣”,显非一般文士所能达到,关汉卿此时正在做官可说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里的“帝宣”当然不是元朝皇帝的宣命,因金亡后他已是“不屑仕进”,事实上他也没有再做官,这支曲子说的只能是他在金末任太医院尹的事。由于太医院官虽然权势不能同显贵要职相比,但总是经常接受“帝宣”的朝官,故这首套曲表现的应当是真实情况。联系起作者使用女真曲调得心应手的因素,此曲作于金末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接近的还有〔双调·碧玉箫〕十首,其中有云:“官极品,到底成何济!归,学取他渊明醉。”显然这里说的仍旧是作者在金代为官的事,作者此时的心情与前一首所表现的基本相同。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道出如此痛切的感受。
最后,还得涉及一下王国维在这方面的观点。王氏从元末杨维桢《元宫词》中“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的诗句出发,认为关汉卿“果使金亡不仕,则无于元代进杂剧之理。宁视汉卿生于金代,仕元为太医院尹,为稍当也。”粗看起来,王国维所言亦不无道理,但细加玩味,我们即可发现其中的失当之处。依他所见,关汉卿既为前朝遗民,“金亡不仕”,即不应该在新朝“进杂剧”,但事实上这中间并无逻辑关系。作为前朝遗民,可以不在新朝作官,但也并不妨碍他为新朝建言。杜善夫(仁杰)入元后即多次上书言事,而长期在金廷作官且为亡国遗民之首的元好问则曾专程北上谒见忽必烈,并奉上“儒教大宗师”的尊号,正史赫然记载。(22)这些都未能影响他们的“金之遗民”身份,更何况关汉卿还只是以在野之身写作杂剧呢?用绝对不食周粟来要求关汉卿这样的遗民是不现实的,王国维这里显然是以自己的思想标准去衡量古人了。
注释:
①《关汉卿和他的杂剧》,载《人民文学》1954年第4期。
②《戏剧论丛》1957年第2期。
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录鬼簿提要》,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④钟林斌:《关汉卿戏剧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⑤《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页。
⑥《尔雅·释言》邢疏。
⑦《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册第15页。
⑧转引自《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⑨《四库全书》集部十“词曲”。
⑩《析津志辑佚》,第147页。
(11)《录鬼簿》卷上跋。
(12)该书第41章第2节,华盛书局1934年版。
(13)近人且有将《鬼董》著作权一并归于汉卿名下者,其谬误自不待言。此前学术界已多有驳议,可参看。
(14)《金史·选举一》。
(15)《元史·选举一》。
(16)参见拙著《关汉卿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17)《析津志辑佚》第57页。
(18)《三国志·关羽传》裴注引《蜀书》云:“庞德子会,随钟、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知关羽无直系后裔。
(19)例见王钢:《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第6~7页。
(20)参见李汉秋等校注《关汉卿散曲集》第49页注69。
(21)《宋元戏曲考》九:“元剧之时地”。
(22)《元史·张德辉传》。
